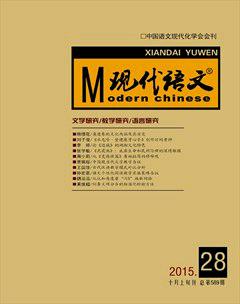从《斐德诺篇》看柏拉图的修辞观
摘 要:《斐德诺篇》被看作是柏拉图著作体系中关于修辞术的经典篇目,其中分析了修辞术之弊端,认为它只能让人远离真理,走向岐见之途。在此基础上,柏拉图提出了自己对修辞术的建议以及真正能说服人的方法。
关键词:斐德诺篇 修辞术 真理 意见
智者文化随着雅典民主制的鼎盛而空前繁荣,民主制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动力和保障,智者则为人们参与社会事务提供指导,修辞术正是这些指导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它帮助人们更好地开发语言的力量,通过对语言的妥当运用,人们几乎能“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1]。于是社会上产生了对修辞术的崇拜和迷信,但由于修辞术的关注点在语言,而非语言背后的真理,于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力量开始以真理为名批判修辞术,修辞术虽然还未遇到真正的危机,但已经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柏拉图是对修辞术攻击最为猛烈的哲学家之一,在《斐德诺篇》中,他充分表达了对修辞术的不满,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修辞术的弊端,同时他也提出了对修辞术的建议以及真正能说服人的方法。
一、传达真理
柏拉图列出修辞术的第一个弊端是它从不关心所谈问题的本质,而只关心能否说服他人。由于其目的在于说服,而说服他人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投其所好,因此修辞术的第一要务是掌握公众意见,而非真理本身。人们只要知道群众是怎样看待真、善、美即可,不需要知道真、善、美本身,衡量说服效果的是群众意见。针对以上弊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自己的观念:“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要有一个出发点,这就是必须知道所讨论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得不到什么结果。”[2](P106)
如果文章作者对所说的对象不界定清楚,那么他写出的文章只能似是而非,如果文章作者对某问题的讨论在出发点上都没有一致的看法,那结果肯定是暧昧含混,甚至会自相矛盾。以开篇的三篇文章为例,第一篇是莱什阿斯的,后两篇是苏格拉底的,三篇文章都在谈论爱情,主题是一个少年人应该接受对自己有爱的人还是没有爱的人。莱什阿斯的文章没有说明爱情的定义,而是直接谈有爱的短处和没有爱的长处,对于一个只关注表面现象的读者来说是有说服力的,但对那些擅长分析和反思的读者来说,他们会发现这篇文章是无本之木,是隔靴搔痒之作,因为所有的看法都没有赖以成立的基础。
苏格拉底的文章恰恰相反,他第一篇文章的目的是证明没有爱的人对爱人是有益的,然后抛出对爱情的定义:爱情是一种渴望获得肉体快感的欲念。[2](P106-107)这样就使讨论的基础很坚实:有爱情的人就是被欲念奴役的人,他们对爱人的一切期望和行为都围绕着自身欲望的满足,因此爱人在这种关系中被放在满足欲望的工具的位置上,不会获得,只会失去。而没有爱情的人不会被欲念控制,自然也就没有以上弊端,不会对爱人造成伤害。由于苏格拉底事先明确了对象,因此整个论述主题清晰、文气畅通,得出的结论让人难以辩驳。在第二篇文章中,苏格拉底先亮明自己的论述目的:证明有爱的人对爱人是有益的。接着他抛出了另一种对爱情的定义:爱情是灵魂渴望真理和美的迷狂。[2](P125)这种爱情建立在灵魂需求的基础上,灵魂需要的是真理和美的滋养,有爱的人从爱人身上看到了来自上界的美,对方的灵魂越接近真理,这种美的力量就越大,因此有爱情的人是希望情人接近真理的。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爱情,不会对相爱双方造成伤害,反而会促进彼此的灵魂净化,这就证明有爱的人对爱人是有益的。
莱什阿斯和苏格拉底的文章通过对比高下立判,斐德诺对苏格拉底的爱情观心悦诚服,并且看出了莱什阿斯文章的致命缺陷是论述对象不明确,柏拉图通过斐德诺对莱什阿斯文章态度的转变证明:说服他人的第一步是明确对象并掌握对象的本质。要明确对象不难,但要掌握每种论说对象的本质却难上加难,而这正是哲学家所追求的目标。
二、雄辩术
柏拉图列出的修辞术的第二个弊端是谋篇布局没有逻辑,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2](P150)在这一标准下,莱什阿斯的文章又成为反面例证,苏格拉底将之比作佛律癸亚人密达斯的墓志铭,讥笑他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每一句话都可以随便互换次序而不影响理解,而在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中每一句话都不能随意改动。
具体来说,文章首先应该有一个中心论点,它如同文章的灵魂,所有的文字都要紧紧围绕着它,若论证与论点脱离,材料不能支撑论点,那这篇文章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正如苏格拉底对斐德诺所说:“头一个法则是统观全体,把和题目有关的纷纭散乱的事项统摄在一个普通概念下面,得到一个精确的定义,使我们所要讨论的东西可以一目了然。”[2](P152)
在紧扣论点的基础上,“第二个法则是顺自然的关节,把全体剖析成各个部分。”[2](P153)把要讨论的问题分为正反两部分,先顺着正的部分去分析,直到不能再继续下去为止,再顺着反的部分去分析,同样到不能继续下去为止。另外,论证过程必须符合逻辑,不能旁逸斜出、散漫无际,这是一种分析与综合的能力,是能看出事物当中“一”与“多”的能力,苏格拉底称之为“辩证术”。苏格拉底的两篇文章就是遵循了这种写法,确定了讨论的对象“爱情”之后,先从“爱情是肉体欲望”这个方面去分析爱情能带来好处还是坏处,再从“爱情是灵魂对美的渴望”这个方面去分析爱情能将人引向何处,是好还是坏。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分析,苏格拉底对爱情这个问题实现了严密详尽的论证,证明了建立在辩证术基础上的文章才能真正达到说服人的效果。
与辩证术相反,修辞术虽然看起来无懈可击,一篇文章分为序言、陈述、证据、证明、近理、引证、佐证、结论等部分,但是这种结构上的整饬因内在的逻辑不清而流于形式。另一方面修辞术注重文辞,经常在修辞格和文章长短比例上大做文章,苏格拉底认为这些都没有触及到说服艺术的内核。他对厄文努斯、提西阿斯、高吉阿斯、普若第库斯、希庇阿斯、泡路斯、特勒什马克这些当时颇受追捧的修辞术专家逐一讽刺,挑出他们的代表作或主要观点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都不值一提。如同治病一样,他们只是对医病的方法略知一二,但对医理和病理却一窍不通。
三、心灵之书
柏拉图列出修辞术的第三个弊端是忽视或隐藏说服的对象——心灵,因为文章的对象是听者的心灵,作者若想实现说服人的目的,还必须了解人的心灵,“医学所穷究的是肉体,修辞术所穷究的是心灵,……在医学方面处方下药,来使肉体康强,在修辞术方面命意遣词,来使心灵得到所希冀的信念和美德。”[2](P160)
首先,要知道心灵的本质是什么,这一点苏格拉底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已经写得很清楚,灵魂来自本体世界,是不朽和自动的,它随着神的队列飞行在上界。它由三个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构成:驯服的马、顽劣的马、御车人。驯服的马听从御车人的指挥,顽劣的马总会受到外界引诱而拉着御车人偏离方向,这是使灵魂堕落的原因,御车人要协调两匹马的力量。灵魂回归上界靠的是羽翼,而真理可以滋养羽翼,令灵魂飞升,净化堕落的灵魂。
其次,要分清心灵的种类和特性。因为灵魂在堕落之前是跟随神在天上巡游的,宙斯是总领队,他下面分为十一个队列,分别由十一位神带领,从属于哪一位神的队列就会习得和该神相似的本性,例如跟随战神的灵魂就比较易怒,跟随赫拉的就和赫拉相似,找爱人也会偏向找有帝王相的。一篇文章之所以能打动一部分人的灵魂,而对另一部分人的灵魂无能为力,原因就在于此。
再次,应当将文章的种类和心灵的种类各自分列出来,找出哪类文章和哪类心灵有着共同特性,使之两两相配,文章只要找到了相应的心灵,自然能达到说服的效果。在柏拉图看来,“那班近代‘修辞术的著作者都是狡猾的骗子,尽管他们对于心灵懂得很清楚,却把它隐藏起来。”[2](P162)
可以看出,对柏拉图来说,写作的实质是作者心灵的呈现,阅读的实质是读者对作者心灵的应和,是两个灵魂的交感。那什么方式能促进这种沟通呢?柏拉图认为是口说文章,口说的方式能让作者直接呈现自己的心灵,能让作者与读者达到真正的沟通,不会造成误解。而使用文字的写作则正好相反,脱离作者仅仅去阅读他写出的文字,会产生诸多误解,甚至会歪曲作者的心灵,只有面对面地直接沟通,才能廓清误解,达到心灵相通。并且文字的坏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放大,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一传十,十传百,不可能永远都由作者亲自解释,人们对它的误读永远存在。因此,柏拉图崇尚那种写在读者心灵上的文章,而不是写在纸上的文章。
综上所述,柏拉图并非否认文章应具有说服人的力量,而是不赞同使用当时流行的修辞术来达到这一目的,在他看来高吉阿斯这样的修辞术鼓吹者说服人的出发点是混淆真理,而非廓清真理,单从这一点来讲就不能大力推广。他从阐明真理的立场出发,提出了理想的说服艺术,涵盖了对象、作者、文本、读者四个写作行为中的基本面,在创作论、文本论、作家与读者相互沟通的问题上提出了成体系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文章既是关于修辞学的,又是传达柏拉图文艺思想的经典作品。
另外,文章的人物安排和结构设置很巧妙地跟说服这个主题紧密衔接:斐德诺是有待说服的对象,莱什阿斯和苏格拉底是准备说服这一对象的演说者,他们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去说服斐德诺,最后苏格拉底完胜,说明苏格拉底的修辞术更胜一筹。就修辞术本身来说,柏拉图不但没有反对,反而令其走向纵深。随着雅典民主制的衰落,修辞术也日渐式微,“如果民主消失,如果代替它的是一个不再需要公众讨论的强权政府,雄辩又有何用呢?”[3]人们对修辞术的讨论再难以达到柏拉图时代的热情,修辞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蜕化为一门辞格的艺术,直到20世纪才重新成为热点。
(本论文为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由探索项目“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的解构内涵”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颜一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页。
[2]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3]王国卿译,托多罗夫:《象征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3页。
(周小莉 兰州大学文学院 73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