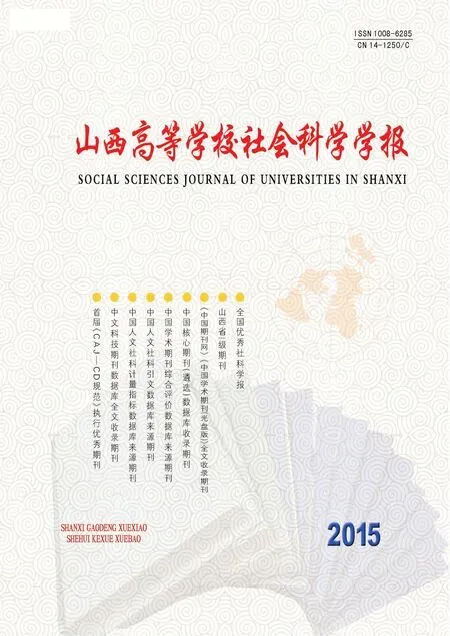论商事合伙中的单独业务执行权和单独代表权
郭兰英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2)
论商事合伙中的单独业务执行权和单独代表权
郭兰英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山西太原030012)
[摘要]商事合伙的合伙人应当具有单独业务执行权和单独代表权,原则上每一合伙人均可单独执行合伙事务并代表合伙企业。虽然这对于商事合伙而言可能是危险的,但却是基于商事实践的理性选择,而且这种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我国应当确立这一模式。
[关键词]商事合伙;单独业务执行权;单独代表权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15.03.017
业务执行权和代表权是贯穿商事合伙法始终的主线,是合伙企业①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调整手段,甚至可以说是囊括一切合伙事务经营运作的最终表现形式。然而,基于商事合伙的特殊性,其业务执行权和代表权的分配不同于民事合伙,亦有别于公司,应当具有特别的运作模式——单独业务执行权和单独代表权,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模式。但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立法并未确立单独业务执行原则,单独代表权的规定也很不完善,对于业务执行权和代表权的内外连接关系更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笔者希望,以《合伙企业法》为参照,从应然的视角对商事合伙中的单独业务执行权和单独代表权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正确理解该制度和完善立法。
一、 单独业务执行权
(一)单独业务执行权的含义
为正确理解业务执行权,以下两点应当予以阐明。首先,业务执行权界定的是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是调整各合伙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依据。这也是业务执行权外延宽广的根本原因。一切合伙事务,无论是法律行为,或是法律事件,抑或是准法律行为,必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业务执行权内在地包含着决策权。在商事合伙中,业务执行权内含决策之意。商事合伙的内部是一种高度一体化的权力结构——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即合伙企业的一切真正财产权力和经营决策权力都集中在所有者手中,商事合伙没有必要分离执行权和决策权。
①如《合伙企业法》第19条第1款规定:“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可知合伙企业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财产。
可见,业务执行权具有相当宽广的外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范围不仅包括合伙企业的法律行为,而且包括各类非法律行为的实际事务处理工作,如组织生产、会计与财务管理、通讯联络等。”[1]基于上述,笔者认为,所谓单独业务执行权,是指每个合伙人原则上都可以在通常的业务经营范围内独立于其他合伙人进行任何归属于业务执行领域的行为。由是,每个合伙人均有权合伙事务执行权,事务执行的法律后果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从本质上说,这是法律推定的一种默认相互代理权,合伙人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及责任的连带性,可以实现合伙事务的安全代理。
当然,单独业务执行权是有范围限定的,限于合伙企业的通常业务经营,对于非通常的重大业务执行,合伙人不能单独决策和实施,而应“由所有合伙人共同参与,包括合伙人共同参与但仅须经过半数同意和合伙人共同参与且须经一致同意两种情形”[2]。
(二)单独业务执行权的正当性
1.从商事合伙和民事合伙的对比中获致正当性。商事合伙适用与民事合伙不同的业务执行原则,源于二者之间的以下重大区别:其一,民事合伙是契约体,而商事合伙是组织体。虽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商事合伙之于合伙人确有一定的独立性,这在关于合伙财产的规定上得到有力印证①。在进行商事交往中,合伙人得以合伙企业的名义为法律行为。组织体的属性使得合伙人之间可以实现相互代理,同时,各合伙人和组织体可以产生单独关联,合伙人可以通过合伙企业进而与其他合伙人发生内部关系。这为单独业务执行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其二,民事合伙更加注重公平而商事合伙更加注重效率。显然,单独业务执行权是危险的,但它赋予了合伙企业很大的灵活性并使迅速决定和立即行动成为可能。
2.从商事合伙和公司的对比中获致正当性。公司具有法人资格,公司比之于合伙企业最大的特征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显然,公司的事务执行是由特定的组织机构“三会”分工完成的,适用“第三人机关原则”。反观合伙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所有者直接参与事务的执行,适用“自营机关原则”,加之合伙企业人合作性较强,且一般规模较小,单独业务执行权的实现非但没有障碍,反而有助于增加商事运营的灵活性,契合了商事合伙企业形态存在的合理性。赋予每个合伙人以单独业务执行权,更具正当性。
(三)单独业务执行权行使的制约机制
在公司法上,为了保证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董事及经理为公司及股东利益最大化而行为,对董事及经理苛以诚信义务。商事合伙中,合伙人之间关系密切且负有连带责任,而且,单独业务执行权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如此,举轻以明重,合伙人之间的诚信义务具有正当性。具体来说,商事合伙中的诚信义务包含以下两方面。
1.忠诚义务。合伙人本身即是合伙企业的所有者,有别于一般的独立受托人。他们加入合伙就是为自己争取最大限度的盈利,绝对苛以他们竞业禁止义务显然不公。合伙人忠诚义务标准的确定需更加灵活,这里重要的是进行利益的平衡。试举一例。某合伙人在一地开办了一家服装厂,而后,其所在的合伙企业亦讨论决定在同一地区再开设一家服装厂。那么此时如果该合伙人投票否决这一合伙议案,那么他是否违反忠诚义务呢?显然,他并不违反忠诚义务,要求其牺牲个人利益来服从合伙利益是显失公平的,况且,其在合伙企业中所获得的利益甚至要低于合伙企业在同一地区开设服装厂而对其造成的损失。我国《合伙企业法》第32条对忠诚义务有所体现,但正如上述所言,绝对要求合伙人履行竞业禁止义务,禁止自己交易,把他看为普通的受托人,有失偏颇。
2.谨慎义务。在我国法律体系上,似乎并无规定谨慎义务的传统,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学说理论。然而不得不承认,实务中不得不以谨慎义务为标准判断行为的过失、确定损失的分担。一般认为,谨慎义务的标准为尽到与处理自身事务同样的注意义务。同时,不能对业务执行人要求过高,否则会束缚其手脚。因此,商法上引入了“商事判断原则”,即
①《合伙企业法》第26条规定:“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
②《民法通则》第34条第1款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
③《合伙企业法》第35条第2款规定:“被聘任的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超越合伙企业授权范围履行职务,或者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④正是基于其团体性,这种权利习惯上被称为代表权,虽然其本质上是一种代理权。
如果根据现有的事实证据,业务执行人已进行了适当努力,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即使事后证明决策是错误的,他仍然可以免责。
笔者认为,与处理自己事务同样的注意义务标准对于合伙人仍显过低,理性第三人标准更为妥当。因为合伙人是基于对对方资产、信誉、能力等各方面的信任而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绝对信任要求合伙人执行业务时必须尽到一个通常理性人的注意义务。合伙事务的执行产生的是连带责任,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仅以尽普通注意义务约束之,合伙事业仍可能面临不合理的危险。以统一的理性第三人的注意义务标准,可能会对部分合伙人苛以较高的要求,但合伙人对于自己无能为力之事大可以退而避之,而无须逞强自恃,这对于合伙整体利益的维护更有保障。这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四)对我国相关法的反思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二章第三节集中规定了“合伙事务执行”,共用11个条文对合伙企业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规定。但是,存在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需要完善。
1.未确立合伙企业单独业务执行权的常态,仍然奉行民事合伙中的共同业务执行权。根据《合伙企业法》第26条①规定,我国法赋予了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平等的业务执行权,但是合伙事务仍然需要共同决定,单个合伙人无法获得处理执行特定合伙事务的完满权利,除非另有约定。这种规定显然是沿袭了《民法通则》中关于“个人合伙”的规定②。如此规定,未能充分体现商事合伙和民事合伙的差异,影响了合伙企业在商事交往中的灵活和效率。
笔者建议,首先,应当确立单独业务执行权的原则,即对于通常事务,每个合伙人单独享有决定并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即使未经其他合伙人的同意或追认,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可以表述为“每一合伙人可以单独决定并执行合伙事务,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合伙企业及所有合伙人承担”。其次,对于非通常事务,应区分情况,或者经由过半数合伙人决定执行,或者经由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决定执行。《合伙企业法》第31条有限列举了六项需要“一致决”的非通常事务,可资借鉴。最后,在内部关系上,广泛的契约自由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任何事务,包括通常事务和非通常事务,允许合伙人通过合伙协议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进行偏离性设计。
2.对于业务执行权的制约机制规定的不够合理和完善。《合伙企业法》第32条对合伙人苛以绝对的忠诚义务,有失偏颇。笔者建议引入利益平衡机制,根据具体情形,权衡合伙人自身利益和合伙利益,在牺牲合伙人自身利益显失公平时,允许合伙人变通适用。我国《合伙企业法》第35条第2款③仅简略地规定外聘经营管理人员的勤勉谨慎义务,却忽略了对合伙人的谨慎义务,不能不说是立法的疏忽。笔者认为,合伙企业关于谨慎义务的标准,应当予以明确和细化,建议区分主体、分别规定:外聘经理人员应尽到与处理自己事务同样的注意义务;合伙人应达到理性第三人的注意义务标准。
二、 单独代表权
(一)单独代表权的含义
合伙企业虽不具备法人资格,但却具有组织体的形态。当涉及外部关系时,合伙企业更被倾向于看作一个独立的团体。关于团体的规范,可以参照适用于合伙企业,包括由某一主体行使代表权④,代表团体与外界进行交往。代表权调整的是外部关系,意思自治在此受到限制,更多的强制性规范得以适用。
笔者认为,合伙企业中的代表权在性质上可以界定为一种法定代理权。合伙企业中的代表权迥异于一般的委托代理[3]。合伙企业中的代理则直接根据合伙协议关系产生,并不需要额外的授权行为。正如业务执行权一样,合伙企业中的代表权是单独代表权,即原则上每个合伙人都有代表权,并且每个人都能进行单独代表。因此,他无须一个其他合伙人的共同参与。而且,不同于调整内部关系的业务执行权——得因一个合伙人的反对而被排除,“代表权因扩展至合伙企业之外,不会基于内部合伙人反对而被排除,除非基于重大理由且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予以剥夺。”[4]195《合伙企业法》第37条①对单独代表权有所反映。但这种规定并不明确,尤其将业务执行权和对外代表权一同规定,逻辑上难以自洽——我国并未承认单独业务执行权。
①《合伙企业法》第37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二)单独代表权的正当性
代表权和业务执行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业务执行权的行使超出内部关系时便产生了对外代表的问题,因此,单独代表权的正当性可以从单独业务执行权中获得。除此之外,单独代表权还有其自身的正当性。其一,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企业在商事交往中所需要的灵活性。单独代表权意味着任一合伙人可以依据具体情形,适时地单独地作出代表行为,和第三人形成适法的关系,契合了灵活多变的商事实践。其二,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单独代表权是一种法定的代理权,法律推定每个合伙人均具有单独代表合伙企业的权能。由此,第三人便可安心与之缔结法律行为,并以商事外观固定法律行为之效力,除非第三人被证明为恶意。
(三)单独代表权的认定
代表权的认定更多地受到强制性规范的约束,当事人的约定通常不具有排除效果。笔者认为,关于单独代表权的认定应坚持以下标准。
1.以商事外观法则为依据,即根据商事外观,推定所有名义合伙人均具有单独代表权。这应是判断单独代表权的首要标准。这一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立足商事实践特性的价值选择。商事合伙法在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保护交易安全两种价值中更多地强调了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在商业运行效率和结果公平上更多地倾向于对效率的追求。
2.非善意第三人不可以单独代表权对抗合伙企业。法律上价值的选择不是取舍,而是衡量;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此消彼长。法律应坚守正义的底线。对于明知某合伙人已依内部协议而被排除代表权,仍然与之缔结法律行为者,不受法律保护。“法律不得鼓励为恶。”[5]当然应当注意,此时的证明责任归属于合伙企业一方。否则,过重的证明责任将导致第三人的利益在事实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3.合伙企业法上的登记不具有当然的公示效力,不可以登记推定第三人的知情。商事合伙的登记属于主体登记,是对合伙主体资格的确认或赋予。主体登记不是事项登记(如不动产登记),不具有公示效力,不可推定已登记事实为第三人所知晓。商事登记目的不是为了附加额外的审查义务于第三人,恰恰相反,是为了加重设立人的设立义务,防止主体失范。
(四)单独代表权的范围
单独代表权原则上是无限制的,或者说,虽是可限制的,但却仅具有内部效力。它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通常的业务和非通常的业务,而无论是否在内部关系中存在必要的职权。简言之,单独代表权不涉及基础关系,即合伙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尤其不涉及合伙协议的修改。在此唯一起作用的是外部行为的表现和法律的推定。
由此,单独代表权实质性地区别于单独业务执行权,单独代表权原则上是不可被限制的。“单独代表权在商法上是以确定的形式被加以描述的,即不能通过合伙协议也不能通过其他约束限制它。”[4]196外部第三人完全可以安心地信赖以下事实,即每一个合伙人均有单独代表权,他在完整的范围内享有它,与该合伙人缔结的法律行为将由所有的合伙人一起负担。
(五)对我国法的反思
必须承认,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了单独代表权。不过,仍然有以下重要方面应予以反思和完善。
1.认定标准过于简陋,缺乏层次性。《合伙企业法》仅在第37条略微涉及单独代表权的认定标准,这显然不能满足制度输出的需要。笔者认为,应该规定三个层次的认定标准,可以表述为:“(1)每一合伙人均有权单独代表合伙企业,其法律后果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承担,合伙协议对其所作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上文已提及);(2)合伙人举证证明第三人明知合伙人无对外代表权而与之进行交易的,其他合伙人不承担责任;(3)合伙协议的登记并不免除合伙人的告知义务。”
2.单独代表权的范围规定得不够明确。《合伙企业法》第37条所言及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是否既包含通常事务又包含非通常事务,语焉不详。故笔者建议,应当明确规定单独代表权的范围。可以表述为:“每个合伙人都可以单独代表合伙企业进行通常的业务行为和非通常的业务行为,合伙协议的约定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
三、 单独业务执行权和单独代表权的辩证关系
笔者认为,单独业务执行权和单独代表权构成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为内部关系范畴,一为外部关系范畴,二者具有逻辑上的辩证关系。
(一)斗争性
1.在反对权上具有不同的适用效果。反对权在内部关系中具有很强的适用效果,单独业务执行权可以因其他合伙人的反对而被暂时地延阻甚至排除。这是内部关系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合伙企业法》第29条第1款*《合伙企业法》第29条第1款:“合伙人分别执行合伙事务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对其他合伙人执行的事务提出异议。提出异议时,应当暂停该项事务的执行。如果发生争议,依照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作出决定。”对此有应证。相反,反对在外部关系中不具有效力,单独代表权不因合伙人的反对而受阻。这是基于外部关系中的强制性规范的适用和善意第三人的保护的结果。
2.在适用范围上的限制。单独业务执行权原则上只能适用于通常的业务,非通常的业务一般须经全体合伙人共同决定,包括全体合伙人的过半数通过、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等,尤其关于聘请合伙人之外的人进行经营管理时,需要全体合伙人共同决定。而单独代表权的范围则不受限制,既包括通常的业务行为,也包括非通常的业务行为和经理权的授予。
(二)同一性
1.单独业务执行权和单独代表权在本质上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视角,具有相互对应性。合伙事业的运营往往同时涉及合伙人之间以及合伙人与外部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分配。同一经营事实,从内部审视的结果便是业务执行权,从外部观察的结果便是代表权,二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单独业务执行权的正当结论便是单独代表权,二者是相互对应的。至于单独业务执行权和单独代表权在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巨大分别和一定程度的分歧则是源于利益平衡、商事法上的特殊价值以及其他特殊重大理由的考量。这种调整不但没有割裂这种对应性,反而从侧面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天然联系。
2.单独业务执行权和单独代表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对于代表权的内部限制虽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当有证据证明第三人为恶意时,则可以之对抗第三人,此为内部约定的外部化。相反,当合伙人进行对外代表时,他可以明确告知第三人其代表权利的限制,无论在内部协议中有无这种约束,第三人均应予以尊重并在声明之范围内与之进行商事交往,此为外部表见的内部化。
[参考文献]
[1] 高富平,苏号朋,刘智慧.合伙企业法原理与实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210.
[2] 马强.合伙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21.
[3] 朱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145.
[4] [德]格茨·怀克,克里斯蒂娜·温德比西勒.德国公司法[M].殷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 [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69.
On the Sole Executive Right and the Sole Representative
Right in Commercial Partnership
Guo Lanying
(ShanxiPoliticsandlawInstituteForAdministrators,Taiyuan030012,China)
[Abstract]Each member of the commercial partnership enjoys the sole executive right and the sole representative right and could execute affairs separately by representing the whole team. While it may be dangerous, it is based on the reasonable choice of commercial practice,and the danger is largely controllable. China should establish this mode.
[Key words]commercial partnership;sole executive right;sole representative right
[收稿日期]2014-09-23
[作者简介]郭兰英(1979-),女,山西岚县人,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讲师,法律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和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5)03-0067-05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in the Medical Tort
——Fromtheperspectiveofjudicialandlegislativedivergence
Zhou Hongjiang1,Hu Shuxin2
(1.LawSchoolof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2.People′sProcuratorateofDongying,Dongying257000,China)
[Abstract]Medical tor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technical expertise of infringement, and its uniqu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disable the judgers fail to find out the facts involved in many cases. So how to distribute the burden of proof in medical tort turns very important to the results for both parties involved, and in legislati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should be well balanced.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study about the theory and legislation for lawsuits concerning distribution of burden of proof in medical tort, points out the current conflict of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and tries to perfect legislation to further regulate the medical lawsuit activity and maintain the medical order for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 China.
[Key words]medical tort;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legislation;judicial practice;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①基于在我国语境下,商事合伙一般就是指合伙企业,如无特别说明,文中商事合伙和合伙企业为同义语。本文讨论仅限于普通合伙企业,不包括有限合伙企业及其他特殊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