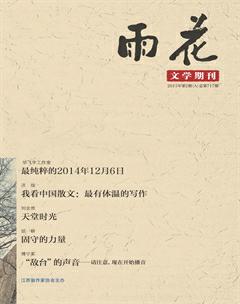当仁不让 (外一篇)
■ 姚正安
当仁不让 (外一篇)
■ 姚正安
不知哪一天,也不知在什么场合,更不知道是对哪些人,孔子说了一句话,“面对合乎仁义的事时,就是老师,也不必谦让”。(《论语·卫灵公第十五·35章》:“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遂有成语“当仁不让”。
尽管这是一句没有时间、地点、背景、人物的“孤句”,但并不影响意义的表达。我们可以假想,有一天,某一名学生与孔子讨论某一个问题时,明明有正确的观点想要表达,却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因此,孔子说,有正确的观点完全可以表达,不必因为面对老师就谦让。
这是孔子对学生的鼓励,也表现孔子与学生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大师风范。
如此之例,在《论语》中并不少见。《论语·雍也第六·28章》:“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一章是说,孔子在卫国期间,有一天,应卫国夫子南子之邀,去拜见南子,孔子的学生子路,对此很不高兴,也难怪,因为南子貌美而名声不佳,孔子怕子路等弟子有误解,因此,对学生发了毒誓,说,如果我做了不好的事,老天爷厌弃我吧(相当于天打五雷轰),而且连说了两遍。
孔子见南子,表面上只是一次会见,实际上涉及到仁义问题,更关系到孔子名誉问题,因此,为人直率而不乏鲁莽的子路,直接表现出“不说(悦,高兴)”。孔子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老师,就批评子路,或者大光其火,而是用极通俗的办法,向学生表明自己的清白。
孔子见南子,是一个公案。后来,还有人据此敷衍出一段煞有介事的色情故事,让人莫名其妙。
我这里引用“子见南子”只是证明,孔子用自己的行动鼓励学生“当仁不让”,对子路如此,对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
在西方历史上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故事。
约距孔子两个世纪后,古希腊哲学史上,有过一个很有影响的“天地之争”。说的是,亚里士多德与其老师柏拉图学术观点之争。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得意门生,跟随柏拉图二十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勤于思考,又敢于争辩,常常为某一个问题与柏氏争得不可开交。尤其是柏氏逝后,亚里士多德针对其错误的观点进行反驳,引起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认为亚里士多德忘恩负义,对此,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坚定地表明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决心。其实,柏拉图也曾经说过,“尊重真理胜于尊重老师”。
做到“当仁,不让于师”、“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需要学生有真知灼见和胆识勇气,也需要老师有博大的胸襟和包容的雅量。
这个问题,不能仅局限于师生,延展开去,官与民,上级与下级,也是这样。为官者,没有察纳雅言的气量,认为“我是官,就比民高明”,那么,民只得“谦让”;上级没有听取反面意见的气度,一味坚持“一个声音喊到底”、“我是上级,我就是正确的”,那么,下级只能“我更爱上级”。如果民与下级,明哲保身,唯唯诺诺,那么,“当仁不让”、“我更爱真理”,也是一句空话。
事实上,能做到“当仁不让”、“我更爱真理”,实在太难了。睿智如柏拉图者,虽也鼓励学生追求真理,但在关键时候,行动却走向了反面。柏拉图晚年在选择柏拉图学院掌门人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德才兼备的亚里士多德,而是选择了学识能力皆不如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学生。亚里士多德只得离学院而去。
正因为不易,所以,必须有人去做,否则,老师与学生就可能一代不如一代,真理就变成了死的教条和枷锁。
孔子做到了,亚里士多德做到了。在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如孔子、亚里士多德者,不胜枚举,所以,才出现名师辈出、真理不断发展的局面,人类文明也赖此向前发展。
敬畏生命
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曾参得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有一天,自知来日不多的曾参,叫来几个学生,让他们打开被子,看看自己的手和脚,在知道自己手足完整无损时,意味深长地说,学生们,几十年来,我一直如《诗经》所说,好像面临深渊,又好像走在薄冰上,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从今往后,我可以免除灾祸了!(见《论语·泰伯篇第八·第3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为什么曾参在临终前要让学生看自己的手脚,又为什么在确认手足完整无损后,十分庆幸地表示“而今而后,吾知免夫”?
原来曾参是一位孝子,据传《孝经》为其所作,他的事迹被编入二十四孝(啮指心痛)。曾参认为,身体得之于父母,还应该完整地奉还于父母,不应该糟蹋和损伤,临终前还不忘叮嘱学生爱惜身体以显孝心。
曾参的学生乐正子春说得更具体,“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
孔子也曾表示,做父母的最担心的是儿女生病(《论语为政篇第二·第6章》: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如果子女任意糟蹋身体,不是更令父母担忧吗,何孝之有?
从孔子的孝乃仁之本出发,直到思孟之学,程朱理学,阳明学派,无不认为人是天地间最伟大的,无一例外地将“贵生”纳入其思想体系中,要求世人珍视生命,爱惜身体。
依更为广阔的视野观之,人是家庭的,更是社会的。如果说,人之生得之于父母,那养之者不独父母,还有社会等等。对生命抱有十分的敬畏,不仅是家庭之责,也是社会之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来,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慢待生命,乃至无视生命的存在。
敬畏生命这个话题,盘桓于胸久矣。所以如此,实乃因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无疾”而逝,特别是一个个社会精英选择极端的方式了结生命。
《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才华横溢,正值壮年,跳楼自杀。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总编辑宋斌上吊而死,都市报副主编徐行跳楼身亡。
为逝者讳,我不应该点出他们的名字,为证明所录之真实,也为唤起世人之意识,不得已而为之,若三君地下有知,不会计较。
三君之死的一个共同点,都是抑郁症导致的。徐怀谦长期囿于“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而不能自拔,宋斌是“身患抑郁症多年,对生活不感兴趣”。
所谓抑郁,就是郁闷,心情不舒畅。至于抑郁症是何症状,如何诱发的,我不是医生,无法从医学的角度加以分析。但我可以肯定,凡抑郁症者,对社会、对生活存有太多的困惑,在意识和情感上形成多重障碍,轻微者悲观厌世、情绪低落,严重者无法解脱,最终以死作为解脱的手段。
本质上说,人就是一个矛盾体,无论身处何时,也不论身处何地,睁眼闭眼都是矛盾。有一位先生曾经就人与生活打过一个比方,我以为妙绝。他说,一个人处在生活里,每天都在打结,每天又在解结,打结是痛苦的,解结是快乐的。人就在痛苦和快乐中生活着。抑郁症者,每天只知打结,而不懂解结,结果一个个结绞住脖子。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都会有种种思考、种种企求,也会有想不通、达不成的,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学会放下,学会放弃。扛着一根木头往死胡同里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圣人孔子自诩“四十不惑”,也有过“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的感叹,但绝没有过自决之想。
一个人在家庭里是不可或缺的成员,于社会也是不可复制的独立个体,自决于世,对家庭是无情的伤害,对社会也是一种伤害,对生命能不敬且畏吗?社会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灰色甚至黑色在所难免,用血色涂抹黑色,黑色并没有消失,如此之为,只是掩耳盗铃,欺人自欺。聪明的做法是于矛盾处寻找和谐,在纠结中营造通道,让自己活出精彩,也为家庭、为社会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
儒家提倡贵生,起于孝,但其后的丰富发展,超出了敬畏生命,也超出了一般的孝,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贵生是关于生命的价值观,实践之,必须从敬畏生命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