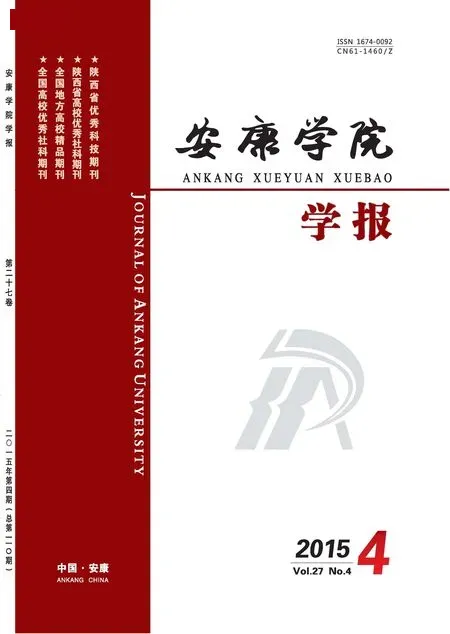浅析进化论与胡适的文学史观之关系
高亚茹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是文学革命期间新文学的提倡者们所选择的一种全新的认识评价文学作品价值和发展趋势的文学史观。而风靡全球的进化论思想,更为文学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尤其是当“达尔文主义”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生物进化论”变成了“社会进化论”以后。提起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确立,我们便会想到在新文学阵营当中首先以进化的观点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胡适。那么进化论思想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和催生着文学革命的发生?它在胡适的文学观念中又占有怎样的位置呢?
近代中国首先是通过1897年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认识到进化论的主要主张的。1898年,《天演论》木刻本出版后不久立即在国内风行起来,产生了广泛的反响。胡适曾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1]413。从胡适的叙述中,我们对进化论在中国的接受可见一斑。进化论思想是中国为富国强民的新一代知识分子,面对帝国的凌辱,民生凋敝,国民的颓靡,所做出的选择性接受。它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优越性、科学性,多半在于它的实用性,“当时的中国饱受凌辱、被压抑了许多年急需在精神上打一针强心剂,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去详细考察这诸多的影响因素,需要一种简单又实用的理论激起国人的斗志”[2]。所以,当它作为一种文学史观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这种实用性体现得更加明显。有了进化论作为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文学革命在宣传的过程中也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及至文学革命伊始,进化的思想仍然是革命家们用于宣传的最佳工具,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从思想上导致了文学革命的发生呢?这样说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一
我们都知道,文学革命的发生,并不是从梁启超所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开始的,而是以留学美国的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的。早在1915年,胡适和同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梅光迪、杨铨、唐钺等人就展开了关于文言文与白话文,活文字与死文字,“作诗如作文”等发展中国文学问题的讨论,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出发,再加上对西方文学认识与借鉴,阐发了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在1915年9月17日,胡适写给梅光迪的长诗中大胆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诗中说:“神舟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3]215。诗体语言已经采用了白话文的形式。到1916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那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1]457-458。从表面上看,胡适的观点确实受进化论的影响,但同时这也是从历史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问题的方式,这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进化论的文学观在承认事物发展变化时,本身就带有一种价值评判,那就是唯新是好,存在的比灭亡的好,这与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口号的文学观显然不是尽相符合的。我们再来看胡适后来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文学观念是怎么样一步步形成的。
胡适在发表于1934年1月的《东方杂志》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详述了从1915年到1917年,文学革命由预设到正式发起的全过程。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也是一直贯穿于新文学运动期间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白话文运动。这也是胡适提出文学革命时最先萌发的新的文学理念。胡适给“活文字、死文字”下了这样的定义:“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3]193留学期间的胡适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都德等等。他意识到对比起英文、法文这样的语种,汉文实在是一种不易学习、不易普及的语种,加之文言文教法的僵化以及“非日用之语”,使得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学只是属于少数人的文学,同时也不利于准确生动地表达人的思想情感。这样,中国文学肯定是不能够更好地向前发展的。他得出的最初的结论是,要改良汉文的教授方法,使文言更容易接受和学习;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而白话文正是活文字。另外,文学革命前期,很多新派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学的经验中就已经意识到小说、戏剧创作,对社会进步、思想传播、新民新国的重要性,梁启超甚至撰文《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繁荣小说创作摇旗呐喊。而西方小说戏剧创作的发达,与他们所使用的活文字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对种种中西文学现象的对比、反思,使胡适成为第一个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者。
最终让胡适对文学革命这条道路感到坚定不移的,还是对活文字、死文字,以及活文学、死文学之间的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的发现和认识。在1916年的争辩中,胡适清晰地总结了当前中国文学的现状,“我仿佛认识了中国文学的问题的性质。我认清了这问题在于‘有文而无质’”[1]457,因此中国的文言文学是死的文学。要想解决这一“文胜质”问题,关键就在于改革文学的工具,当用“文之文字”。有了对文言文学“死文学”的性质的了解之后,胡适接着探索白话文这种“活文字”本身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于是他开始挖掘中国千年的文学史上,白话文学的价值,从以往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经验中找寻继续向前发展的依据。在这个过程中,胡适惊异地发现白话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我到此时才把中国文学史看明白了,才认清了中国俗话文学(从宋儒的白话语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是代表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的”[1]458,这样的文学是活文学。经过对白话文学的考察,胡适对这种新的文学工具终于自信十足,并认定白话文就是可以代替文言文进行活的文学创作的活文字,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可以看出,从最初的改良文学工具,到改良文学内涵,再到肯定白话文学的文学价值,胡适的文学观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又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这时他还提出了,做文章要言之有物、讲求文法,再加上后来使用白话文,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已经有了“三事”。不难看出,后来衍生为“八事”的这“三事”,主要是从考察西方文学繁荣的现状、中国当前文学的僵死,还有中国历代优秀的文学作品,这几项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其中并没有多少进化论对胡适文学观念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可以说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在一开始对胡适新的文学观念提出的影响和作用是很隐性的,它最大的价值在于激励人心,刺激斗志。
二
中国文学革命的发生从外因上来说,它的思想理论源泉,一方面是受了进化论的刺激,一方面也是西方文学发展现状对中国文学的启示,所以文学革命是在中外文学比较的基础上结合本国文学发展经验及状况而导致的结果。因此,胡适在国外留学的经验是其提出文学革命必不可少的条件。正是从1910年到1917年这七年在国外留学的经历,使得胡适能够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以及了解西方文学的发展面貌。只是到后来,文学革命的一声炮响已经得到一些有力的回应,旧派力量也逐渐与新文学派划清界限之后,由于论战的需要,宣传的需要,胡适等人才越来越多地、自觉地从进化论的观念中寻找新文学合理性的印证。
“新文学形态先天地具有此方面的优势,因为它是‘革命’的开始时就是以叛逆、反对者的形象出现的,加之它更多地以‘进化论’来为自己的生存发展找依据,更有利于‘革命’宣传的需要。”[2]革命就是这样要有激烈的态度,不怕遭到反对,“唯其如此,才可称得起革命家,而革命的事业方才能进行得很快。因为革命的事业不怕人反对,但怕人不注意,这个时候,反对的论调多起来,而注意新文学运动的人,也特别多了”[4]38。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就是这样在众多的反对声当中,作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挡箭牌和理论支撑而存在着。
不久以后,在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了1917年的《新青年》上,先声夺人地成为文学革命的第一声炮响。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学革命在民国六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5]18。这是胡适在论证“八事”的第二条“不摹仿古人”中的一段论述,可看作是最频繁地被拿来证明胡适进化论文学史观的强有力的证据。这段论述在充分论证自己文学主张时起到了绝好的作用,它运用进化论的逻辑,说明了新文学在当时社会的合法性和科学性,将文学革命纳入了中国文学向前发展不可或缺的必经之路。同时这段话的意义还在于,它指出了历史发展朝代更迭与相应的文学作品特征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没有直接指出后来的比原有的好,新的比旧的有价值。这样看来,胡适的文学史观念更倾向于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文学史,而进化论文学史观则次之。且看他对新旧文学阵营的一个焦点问题的论述,“吾辈主张‘历史的文学观念’,而古文家反对此观念也。吾辈以为今当造今人之文学,而古文家则以为作文必法马班韩柳。其不法马班韩柳者皆非文学之‘正宗’也。”[5]33胡适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观念”,才是他的文学革命中真正提倡并且影响他文学观念形成的重要观点。同时可见当时中国文坛上旧的文学阵营中所存在的这种僵化死板的文学观念对新文学发展的束缚有多大。此外,胡适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在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角度上说,也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文学革命发生于民国六年,新的政体政权已经建立,而文学创作还停留在旧有的文学观念之上,这势必和新的国家所建立的新的社会观念、新的意识形态不相融合,这也是文学革命发生的思想上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文学革命是当时中国社会革命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难怪有人将文学革命和文艺复兴做比较,毕竟它们都发生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替时期。)总而言之,胡适这种文学观,提倡今人要勇于创作不同以往的文学作品,注重文学的创新性、创造性,以此来繁荣文坛,逐步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能切实表达今人思想情感并反映今时时代生活的文学作品。
基于进化论文学史观在看待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唯新是好,一概而论的价值评判标准,有人说,五四割裂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联系,如果说当时新文学阵营的文学史观完全体现了进化论的这样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质疑,的确是无可厚非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后来遭到的最大打击,永远不会是某种文学改良运动,或者是某种文学观念的盛行。我们不管从历史的眼光还是社会的角度去看,这都不成立。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再有说服力也绝没有如此大的力量去摧毁中国两千多年形成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学。(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是时时刻刻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为最深刻的。如果说传统文学作品遭受最大打击,一定是当产生这种文学作品的时代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被彻底否定的时候。)
三
胡适虽然是新文学的领军人物,但他对旧文学的看法也莫衷一是,并非全盘否定,即使是在新文学阵营痛恨至极的“桐城谬种”中,也不乏胡适赏识的作家作品。而新文学运动所谓的新,也不全是提倡新形式、新思想、新内容,而把旧有的文学统统遗忘,新文学之“新”,固然要创造、发明新的文学,但它更是价值评判标准的新。正如王哲甫所言,“文学本没有新旧之别,所谓新文学的‘新’字,乃是重新估定价值的新,不是通常所谓新旧的‘新’”[4]13,胡适对“死文学”“活文学”的界定,正体现了这样的观念。周作人所谓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贵族文学”,也是为重估文学作品的价值而创造的新标准。胡适后来整理国故,研究国学,同样也是他用新观念、新标准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一次经典化的梳理。总之,革命毕竟是革命,通过论战中的一些过激的言辞来评判他们各自的文学史观,毕竟不是最客观的。但矫枉必然过正,也是处于革命中的新文学阵营在所难免的。
与激烈的论战相比,如何书写文学革命视野中的文学史,也许更能体现新文学的立场。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想到思想的结。”[1]163可见,进化论思想对胡适最大的影响不在于新的压倒旧的、正确的一定压倒错误的这种过于机械化、简单化的文学发展观,而在于确立勇于创新、勇于质疑的学术思想。文学革命以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在1923年和1928年相继问世,便是运用新的学术方法,大胆创新,重写文学史的代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只有第十节中,胡适介绍了新文学这五年中的情况。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说:“第十节在认识上的贡献是,既说明了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肯定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意义;又对古今白话文作了原则的区别,肯定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进步性。”[6]关于新文学的白话创作和过去白话文学的区别,胡适认为“这五十年的白话小说史仍与一千年来的白话文学有同样的一个大缺点:白话的采用,仍旧是无意的,随便的,并不是有意的。”也就是说,过去文学作品中对白话文的使用是无意识的,而不是自觉的,“无论是唐诗,是宋词,是元曲,是明清的小说,总不曾有一种有意的吹鼓,不曾明明白白的攻击古文学,不曾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的文学”,而新文学正是使这种正确的发展趋向成为了文学发展的自觉追求。用历史的经验证明了白话文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关于桐城古文,胡适则说“这一度的古文中兴,只可算是痨病将死的人的‘回光返照’,仍旧救不了古文的衰亡。”[7]327在这五十年的诗歌创作中,胡适只举了两例,为不摹仿古人,不雕琢文字,自有个性的诗人的代表,一个是桐城派的金和,另一个则是有意进行新诗创作的先驱黄遵宪,以此阐述了胡适的新诗主张,“作诗与作文都应该从这一点下手:先做到一个‘通’字,然后可希望做到一个‘好’字”,“古来决没有一首不通的好诗,也没有一首看不懂的好诗”[7]356,这是在创作上要求向白话文的文法上去探究,提倡新诗创作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
白话文要想战胜文言文,成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除了说明文言文的“死文字”的僵化本质,俗文学入史更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胡适的另一部文学史著作,《白话文学史》是一部从中国历代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寻求白话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渊源的文学史,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胡适得出结论,“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7]22,并认定古文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死了,因为汉武帝时,各地方言很不统一,“当时的政府只能用‘文言’来做全国交通的媒介”[7]26,使文言成为了一种脱离口语,晦涩难懂,不宜沟通的“死文字”了。同时,胡适还举出各朝各代文学史上不断运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的诗人及作品,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价值。以此,既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又指明了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正统地位。当然,胡适的这一系列文学主张,有其先进性、前瞻性的一面,同时也有看待旧文学简单化的一面。比如,在“死文学”与“活文学”的判断上,胡适仅仅从文言统一与否的角度出发,认为大多数人看不懂的文章便是死的,看得懂的,符合日常用语规范的就是活的。这种提法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他却忽略了文言文这一高度提炼的语体所具有的生动诗性的表达、铿锵婉转的韵律以及多种多样的修辞等方面的优势;只强调了文言文形成的社会性的因素,忽略了文言文自身的语言价值,彻底否定了文言文作为一种独特的书面文体,对中国散文、诗歌特有的形式韵律结构等的形成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古文与古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是胡适的实证主义学术方法,受进化论思想影响以后所表现出来的片面的专断。
进化论文学史观的弊端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已有备述,但是这种文学史观在文学革命时期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却值得人们去深思。朱丕智曾指出文学革命时期的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我们不时可以看到反对文学革命的种种论调,甚至声嘶力竭的各种声讨,但几乎看不到反对者对进化论和进化论文学观的一丝责难。站在反对者的立场,可以说他们的首要之务就是应先动摇文学革命的这个理论根基,奇怪的是他们却绕道而过了”[8]。朱丕智把发生这种“有趣的现象”的原因归结为“进化论和进化论文学观的作用和威力”之大、之显。但事实上,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恰恰是当时进化论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工具而存在,而不是孕育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学观念的理论根基。就像我们喜欢一部文学作品,绝不会在乎它是平装还是精装。文学革命时期学者作家们所提出的各种文学主张,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为其正身,其实并不是当时文坛最重要的问题。其次,新文学阵营的反对者们,同时也承认文学发展变迁这一事实,新旧文学观念的最大冲突并不在于文学发展的革故鼎新,而在于革故鼎新背后的文学观念。也就是说,简单地把新文学与旧文学论战时的文学史观认定为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史观,不仅不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文学革命的内涵和影响,而且势必会扭曲我们对文学革命存在的必要性的理解,也不利于我们更好地去看待五四以后的文学史观的发展。如果文学革命的价值和内涵得不到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们将无法正确认识我们当今文学发展的缘由和未来。因为,自文学革命始,中国的文学才开始放眼全球,走向世界,走向了一条开放的、创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发展之路。因此,在研究不同文学阵营论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细细反思新文学阵营中提出的各种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和实质内容,因为后者更能反映出新文学的提倡者们对新文学发展以及新旧文学关系的真正看法。
[1]胡适.胡适文集(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王瑜.现代文学史观及其书写实践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0.
[3]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4]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M].上海:上海书店,1933.
[5]胡适.胡适文集(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7]胡适.胡适文集(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8]朱丕智.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石:进化论文学观[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42-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