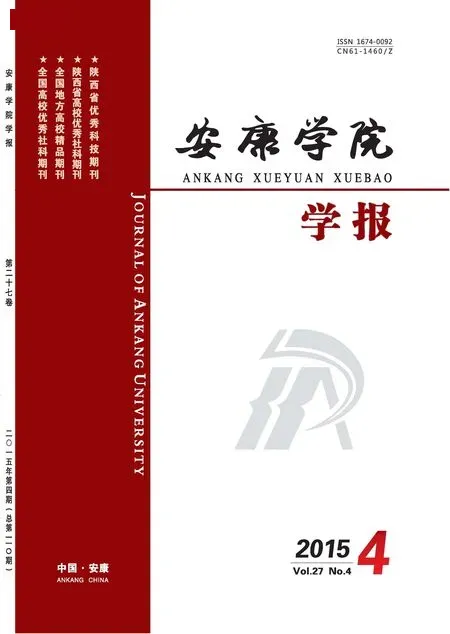《田七郎》对《刺客列传》故事的借鉴与发展
蒲 兵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内容虽多涉及狐鬼花妖,但依然不乏精彩的志人故事,《田七郎》[1]即是其中之一。《田七郎》之所以出彩,是由于其故事的跌宕起伏以及贯穿其中的孝、义精神,但任何文学都是在前代文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学的传统与惯例在《田七郎》中同样存在。蒲松龄在写作这一故事时无论是在故事结构、内容、手法,还是语言、精神上都受到了《史记·刺客列传》[2]的影响,正是基于对《刺客列传》的借鉴与改编,《田七郎》才在文学上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
一、《田七郎》对《刺客列传》故事的借鉴与改编
司马迁著《史记》,所记人物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涵盖社会各个阶层。刺客是游离于士农工商之外的一个特殊群体,与游侠同属被统治集团打压的对象,但司马迁却看到了游侠与刺客身上重然诺、轻生死的特质,故为之列传,以彰显其侠义精神。《刺客列传》共著五位刺客,曹沫要挟齐桓公还所侵鲁地、专诸为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豫让为智伯吞炭自残刺杀赵襄子、聂政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荆轲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凡此五人,与所刺杀之人均无怨隙,都受人所托,为报人恩惠而奋不顾身,完成使命。五人之中聂政的故事特别受蒲松龄注意,他对聂政故事进行了再创作,使《史记》中的刺客精神再次得到张扬。《田七郎》正是在聂政故事基础上形成的,但又有很大不同。
(一)《刺客列传》中聂政故事与《田七郎》的结构
结构是组织情节、构造形象的重要手段,结构不同,故事的节奏、艺术效果自然不同。《刺客列传》中聂政故事可以大致分成以下阶段:第一阶段聂政避仇与母、姊隐居市井,严仲子与侠累有怨仇,故重礼拜见聂政,求为之报仇,聂政因为老母在世而予以拒绝;第二阶段聂政母亲去世,他为报严仲子以富贵结交之恩刺杀侠累,并自残以死,以免拖累其姊聂荣;第三阶段聂荣毫无畏惧地认领聂政尸体,并在其身边死去。
通过上面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聂政故事结构是直线前进的,刺杀侠累是重点,但首尾部分却是聂政人格形象构成中所必不可少的成分,也是侠义、为知己者死精神之外另一重精神境界。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进行分析阐述。
《田七郎》的故事框架与聂政故事相似,都属于受人恩惠替人报仇,但蒲松龄在继承基础上进行的改编又赋予它更复杂的内涵:第一阶段喜好交游名士的武承休在梦中被人警告所游皆滥交,唯田七郎可共患难,遂四处打听欲相交,奈何田七郎母亲认为二人身份地位有差,断然拒绝其恩惠;第二阶段武承休想方设法结交田七郎,讨其欢心,田七郎有所回报,但依旧不愿深交。田母再次呵斥武承休不要交引七郎;第三阶段七郎犯法,命悬一线,武承休设法成功营救;田母迫于无奈,也为了报恩,应允相交;第四阶段武承休家仆为乱,武承休受人欺凌,叔父垂毙,武承休悲痛羞愤;第五阶段田七郎为武承休杀死作乱家仆,并杀奸吏,遂自杀。其母、子遁去,数年而归。
《田七郎》故事一波三折,武承休与田七郎相交部分几乎占据整个故事的一半,而整个故事也不再是直线前进,虽与聂政故事同属“结交—报恩—自杀”的结构,但又有很明显的区别。
(二)《田七郎》故事的新变
1.人物身份的变化。《刺客列传》中聂政隐于市井,以屠为业,想要与之结交的是韩哀侯的大臣严仲子,而刺杀对象则是韩相侠累。田七郎最后所刺杀的一为武承休家仆,一为是非不分、为非作歹的官吏。从构成故事主体的施恩者、刺客、刺杀对象来看,《田七郎》中的人物身份整体发生了下移,因为王公贵族与底层侠士相交是战国的养士风气,而这种风气在大一统的汉初建立之后逐渐被打压,以至于消失殆尽。田七郎与武承休身份差距缩小,刺杀对象下移,蒲松龄这样的改编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也突出其“刺贪刺虐”的写作目的。
2.人物的增删。母亲这一人物在《刺客列传》中已经具备,但通篇没有言语,只是聂政秉持“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的原则而不收严仲子厚礼。而《田七郎》中田母占了很大的比重,田七郎与武承休的结交一直在其监督甚至是掌控之下。从起初两次制止武承休的结交行为到最后武承休救出田七郎之后,她不得不做出让步,这其中的线索即是“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出于母子情谊,她拒绝;此后她慨然应允,则是在无可奈何之下将先前明白的道理付诸实践。《田七郎》中的田母形象不仅仅是为了配合塑造田七郎仁孝的形象,更体现出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关怀,此时的田七郎已经不再像聂政那样轻易将命许给别人了。这一点也正是蒲松龄所做出的新变,符合时代特点。
《刺客列传》中还有一关键人物在《田七郎》中被删去,即聂政姊聂荣,聂荣在聂政死后登场,占据很大比重,当时人已经意识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聂政的成名与聂荣舍身从死有很大关系,但蒲松龄却在自己的故事中将这一重要人物删去,究其原因,当是聂荣这一形象会分散主人公聂政的光芒,“冲淡聂政之死的艺术效果,几乎起到一种喧宾夺主的作用”[3]。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只得将聂荣删去,使读者的目光始终聚焦在田七郎身上,这也是蒲松龄有意为之的。
3.故事结构的平衡。在上面的分析中,聂政故事结构相对简单,即“受恩—报恩”直线发展,而田七郎故事却由于田母的存在而相对复杂。其中第一和第二阶段都是屡次企图结交而未果,故事似乎陷入一种绝境,失去发展空间,即“相交—失败”的重复。此时就需要有一个新的小故事来打破现状,使故事回归“相交—报恩”的主体叙述路线,第三阶段的故事就起这样的作用。当武承休再次被田母奚落之后,自感惭愧,遂不再纠缠。半年后,得知田七郎入狱,遂大惊,前去探望之时,田七郎托他照顾老母。武承休回去之后便张罗营救田七郎,并取得成功。经历这次事件,田母才应允相交,并似乎已做好让田七郎以命相报的准备。营救田七郎这一事件,将武承休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是故事的小高潮,也是整个故事的支撑点与平衡点。失去此,故事无法继续,也就不会有后面的报恩刺杀行为。蒲松龄生活在一个传奇、戏剧、小说都已经高度成熟的时代,因此他将故事复杂化,使其富有戏剧化、传奇色彩,也使得故事在结构上达到平衡。
二、《田七郎》对《刺客列传》主题的继承与扩展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之后的“太史公曰”里指出:“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同样在《田七郎》后的“异史氏曰”里,蒲松龄也指出:“一钱不轻受,正一饭不敢忘者也。贤哉母乎!七郎者,愤未尽雪,死犹伸之,抑何其神?使荆卿能尔,则千载无遗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补天网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司马迁称赞的是五位刺客知恩报义,蒲松龄也是赞誉田七郎的知恩报恩,“一饭不敢忘者”正是《史记·赵世家》里另一位知恩报义的义士。在这一点上《田七郎》对《刺客列传》乃至《史记》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但最后一句却表现出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对田七郎之辈的渴慕,这也就使《田七郎》虽有《刺客列传》的主题,却又比之复杂。
(一)知恩报恩
无论是《刺客列传》还是《田七郎》,其故事都是围绕“相交(受恩)—报恩”展开的。这条主线所要突出的主题即是知恩报恩:聂政要报贵族严仲子不耻下交的恩德,田七郎不但要报武承休长期以来的恩惠更要报将其从死牢中救出来的大恩大德。相比起来,田七郎要报的恩德更加具体实在,更具有现实性,而聂政所受恩德却偏向于道义,二者的差异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与人之间结交的特质,但总的说来又都没有偏离报恩的主题。
(二)报恩与尽孝的纠葛
忠与孝是人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在《刺客列传》中,聂政因老母尚在需要照料,而不许身严仲子。直到其母去世,聂政方念及严仲子的恩德,奋不顾身为之报仇,刺杀成功后为不连累其姊,又自残以死。聂政在报恩与尽孝之间,选择先尽孝再报恩,报恩不能连累亲人,正是在忠、孝问题上的权衡。《田七郎》中,武承休起初无法与田七郎相交是由于田母的阻挠。田七郎要尽孝,相交也是浅尝辄止,不肯受大恩,意即老母在,不肯相交而报恩。及至生命为人所救,意识到终须有所报,才以身相托。后来在为武承休刺杀仇人时,田七郎当是提前将老母及家人安置好才只身赴死。报恩与尽孝一直影响着聂政与田七郎的行为,尤其于田七郎,报恩刺杀时老母尚在,却又不得不在尽孝与报恩之间作出选择,尤为艰难。蒲松龄最后安排田七郎选择报恩,是故事发展的结果,也是其固有的人物使命。
(三)对英雄的渴望
《田七郎》故事中报仇的对象分别代表两类人:家仆属社会底层,但为非作歹;宰与其弟属于社会地位较高的统治阶层,但是非不分,以权乱法。这两类人最后都被田七郎杀掉。蒲松龄在田七郎报恩之外有更多的感慨,“苟有其人,可以补天网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悲夫!”结合蒲松龄“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的自序、终生遭遇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两句话所表现的正是社会统治秩序混乱,他希望有田七郎这样的英雄出来替天行道,维持人间正义。这是《刺客列传》所不具有的主题,这种“反暴政、反强权、反邪恶的精神同样感天动地,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倾向。”[4]也鲜明地表现了蒲松龄对现状的无力批判和对英雄的呼唤。
三、《田七郎》对《刺客列传》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田七郎》作为一个深受《刺客列传》影响的故事,对《刺客列传》的精神自然有所继承,但随着故事内容的新变,精神又有深化。
(一)“士为知己者死”精神
“士为知己者死”精神是先秦两汉门客精神的遗留,而刺客也属于广义上的门客范畴,司马迁写作《刺客列传》,正是对这种精神的盛赞。五位刺客受到不同程度的恩惠,怀感激之情,遂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人报仇。除曹沫之外,其余四人全部慷慨赴死,这是舍生取义、“士为知己者死”精神的最好写照。尤其是聂政,他其实并没有接受严仲子的恩惠,只是因为对方身居高位而辱身下志前来结交,尽管结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他报仇,他也在老母去世后怀着感激之情,以为对方能知己,遂以命相报。《田七郎》里,武承休因为梦中一言而决定与田七郎相交,虽有挫折,但经历几次小事之后,更坚定了相交的信念,因此在田七郎面临着生活的困境、生命的威胁时,武承休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田七郎承受着这样的恩德,田母也告知他必须要有所回报,因此在武承休身陷窘境时,田七郎才挺身而出为之报仇解恨。虽不如聂政那样单纯执着,但也是“士为知己者死”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二)悲剧精神
聂政和田七郎故事里,最富悲剧性的即是二人为报恩而行刺,最后失去自己的生命。《刺客列传》中还有聂荣慷慨赴死的悲剧,同样感人。而《田七郎》中,田七郎“僵卧血泊中,手犹握刃。方停盖审视,尸忽突然跃起,竟决宰首,已而复踣。”当是身死而志存,何其感人!而最后田七郎被弃尸荒野,“禽犬环守之”,通过禽兽的行为,来加深田七郎死的悲剧性,更加重了故事的悲剧精神。《田七郎》故事中还有一悲剧即在于武承休及其叔父的被迫害,这是统治者造成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这一悲剧具有鲜活的时代性,深刻体现出贪官污吏的残酷和野蛮。
(三)批判精神
《刺客列传》中聂政主要是为严仲子的私人恩怨报仇,而《田七郎》中却是武承休莫名含冤、受人打压,属于当权者对普通人的压迫,这一事件本身即是对社会的批判。而面对不公,田七郎以身犯险,刺死奸诈小人,更是一种行为上的批判。《田七郎》文章结尾的“异史氏曰”属于直接的情感宣泄,将对社会不公、无序的批判声色俱厉地表达出来。此外,作者还对武承休所结交的名士有一定批判。在故事的开头,梦中即有人告诉武承休“子交游遍海内,皆滥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难”。这便是对所谓“名士”的明显批判。到了后来武承休遭难时,“这些名士则畏于官府与豪族的势力,只顾独善其身,无一人与武承休出谋划策同渡难关。至此,儒生已不仅丧失了传统的舍生取义精神,连普通人之间那种同舟共济患难相持的友情亦不复见。”[5]更反映出所结交之人的不可靠,属于无声的批判。
总之,《田七郎》故事是在接受《刺客列传》聂政故事基础上的改编,它虽不如聂政故事那般慷慨悲凉,却也一波三折,深具艺术感染力。尤其是在继承“士为知己者死”精神之外,又对批判和悲剧精神进行延展,使这一故事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
[1]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52-155.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15-2538.
[3]白亚仁.《田七郎》与《聂政》关系探源[J].文史哲,1992(4):96-98.
[4]康清莲.侠义复仇精神从史传到小说的嬗变——以《史记》、《聊斋志异》为例[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49-152.
[5]别海燕.论《田七郎》中的深层悲剧意蕴[J].河北理工学院学报,2013(11):187-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