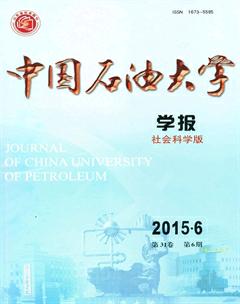黑格尔与福山:从为承认而斗争到历史的终结
[摘要] 自《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版至今,福山的思想(包括其反民主观点)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他不但从未欢呼,反而深感忧虑。福山在三个方面误读了他所依赖的黑格尔哲学:首先,福山将主奴关系中应被扬弃的要素看作是优越之人的特征。其次,他未区分生存状态上的可能性与存在论-生存论的可能性。这种混淆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使他混淆了不同种类的承认,另一方面使他错误地认为历史必有一个时间性终点,即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三个误读。尽管如此,人们仍应看到福山思想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福山;黑格尔;主奴关系;历史终结论;历史的终结;民主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6-0043-06
一、引言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包含两个核心论断:(1)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最终胜利;(2)这种胜利值得欢呼和赞美。不过,这是否是福山的本意?事实上,尽管福山使用了一些宿命论式的话语强调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但是对于这种胜利,福山却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而绝未对此感到兴奋,更谈不上对自由主义的美化;不仅如此,对于资本主义已取得胜利这一观点,福山的态度也是比较微妙的。
目前,对于历史终结论的批评有以下两类:
第一类批评通过事实(如冷战后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金融危机、中国的快速发展)来反驳历史已经终结或将要终结的观点。然而,这种批评存在两方面不足:首先,援引不属于理论本身的经验内容反驳一种理论,并不能取得摧毁理论内部逻辑的效果,因为,在评价一个理论时,重要的是检验其自身的逻辑性、全面性和完备性,以便厘清这一理论内在的矛盾和不足。其次,福山的研究方法颇具思辩色彩,而非纯粹的实证研究,如果人们借助实证研究进行反驳,只能说明其他研究者与福山的研究方法无法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同样无法完全驳倒他的观点。
第二类批评主张,福山借用了大量黑格尔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他正确地理解了黑格尔;然而,黑格尔哲学本身是成问题的,并导致福山犯了同样的错误。
本文的观点与以上两类批评不同。本文认为,暂且不论黑格尔的观点,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福山对黑格尔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有误的。因此,要想充分理解福山的观点,就必须理解黑格尔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以及福山在何种程度上借用或误读了黑格尔的思想。
本文将说明,福山没有重视黑格尔对于主奴关系这种精神形态的内在缺陷的论述,因而把被主人形态中应被扬弃的特征当成了值得赞美的状态。另外,福山未能区分现实中的承认与主体间结构性承认,这使他过分强调了现实中为承认而斗争的行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错误地认为时间历史必有一个终点——而事实上,黑格尔哲学无意设置这样一个终点。本文结论部分将简要讨论福山的反民主倾向以及历史终结论的当代意义。
二、“为承认而斗争”的局限性
(一)黑格尔论“为承认而斗争”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最初,自我意识通过否定、消灭他物而获得满足,确证自身的同一性。但是这样一种不断否定他物的坏无限无法令其得到满足,故自我意识又渴望得到另一个自我意识的承认。但是,两个自我意识都想得到来自对方的承认,且不愿承认对方。为了迫使对方承认自己,他们展开斗争,其结果,要么是把对方杀死,要么是自己被杀死。不过,其中一方意识到了生命与承认具有同等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它无法从一具尸体那里得到承认,另一方面,如果自己被对方杀死的话,承认也就不再具有意义。因此,意识到这一点的一方就主动放弃了斗争,把自己降为奴隶。而另一方也认识到,失败者可以给予它承认,因此决定不杀死失败者,这样就形成了主人-奴隶关系。
在分析主奴关系的内部矛盾(请注意,所谓“内部矛盾”在此并非指主人与奴隶之间的矛盾,而是主奴关系这一精神形态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维度)时,黑格尔强调了三点内容。首先,这种内部矛盾的一个方面是,主人作为自为存在是高贵的,奴隶作为为他(为主人)的存在是纯粹否定的,是卑微的。但是其次,这一矛盾的另一方面在于,主人的自为性是分裂的,或者说,这种自为性同时也是为他的,而奴隶反倒拥有其自为存在。再次,主奴关系最终将因其内部矛盾而被扬弃。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12月
第31卷第6期吴江:黑格尔与福山:从为承认而斗争到历史的终结
1.自为的主人与为他的奴隶
在主奴关系中,主人除了消费奴隶的劳动成果外,还会从事能够体现其卓越性的活动。主人的第一种活动,是与其他主人共同构造起公共领域。主人通过公域成为思维者、原创者,将自己当成本质来思考,这尤其体现在他们能够思考和认识自己的自由这一点上。主人思维创造了政治实体所需的伦理、权利等要素。而被排除在公域之外的奴隶世界,只是一个手段-目的逻辑的技术世界。因此科耶夫说奴隶是“按照一个主人的观念,也就是本质上社会的、人类的、历史的观念进行否定和改造。”[1]207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主人的压迫,奴隶不再屈从于自己的自然性,而是成为了因为劳动而能意识到自己的自由的人,是主人造就了奴隶,这样主人的价值就得到了解释。[1]59主人的第二种活动,就是斗争,他们要么组建一个共同体进行统治,要么以群体形式与敌人作战。主人不仅要冒生命危险在战争中实现并体现自己的自由,而且还要让他人看到这一点,借此得到荣誉。我看到他人像我一样,他人也看到我像他们一样,所以我和他人都是高贵的;只有这样,主人之间才会相互承认他人为主人。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会有公共领域;而个人在战争中的死亡则是成就共同体的意志的最高形式。
与此同时,奴隶所处的状态是:当他在劳动中与事物打交道时,他自己也被赋予了物性。只因他在与事物打交道他才是奴隶,所以为他性指的就是“相对于事物的”;只因他听从主人的命令,所以为他性就是“为主人的”。不过,奴隶与主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不像后者那样敢于追求自由。无论是在政治统治中还是在战斗中,主人之所以被看作主人,本质上并不是由于他使用了暴力,而是因为他敢于追求自由。与此同时,奴隶虽然是能思维、有知性的,但他所拥有的只是服务于主人的知性。正因为其思考要与主人保持一致,所以奴隶并不思考自己,他未认识到他自己拥有自由,因此奴隶的自由只是潜在的,而没有把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应有的自由体现出来。
2.自为的奴隶与为他的主人
奴隶与主人的身份都具有两面性,在一种视角下呈现出自为性的一方,在另一种视角下却呈现出为他性,反之亦然。
通过在劳动中与事物打交道,奴隶得到了“真正的和真实的独立”[2]。奴隶思考自然物,得到概念,掌握真理,通过行动来把概念思维的成果投射到世界上,从而否定、改变了世界,创造了一个新的、更有人性的世界。不仅如此,由于他时刻都可能被主人杀死,所以他感到恐惧。在恐惧中,一切稳定的东西都失去了意义,奴隶发现自己仅仅生存着,却没有任何本质,这为劳动所需要的那种自由的思维提供了前提,奴隶也因此得到了纯粹的自为存在,而这其实正是主人在享乐战场上得到的东西。通过否定事物的否定性和独立性,奴隶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由。奴隶比主人更清醒地看到了自我意识与自然生命的相互关系,他比主人更像人,他“按照一种观念,按照一种概念克制他自己的本能。正是这个原因把他的活动变成了一种纯属人的活动”[1]207。
与此同时,主人身份因其自身的分裂性而反倒是为他的。对此,黑格尔给出了三种相互关联的解释:首先,主人仅在奴隶眼中才是主人,它不得不依赖奴隶的承认。其次,主奴关系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直接的二元关系,而是一种有中介的三元关系:一方面,主人要靠作为中介的奴隶才能与事物发生关系(主人—奴隶—事物),这就是说,他要靠奴隶的劳动才能享受自然物并满足欲望。另一方面,他要通过事物与奴隶发生关系(主人—事物—奴隶),奴隶对主人来说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主人只能用枷锁束缚他,却不能随意杀死他。再次,在与事物的关系上,主人直接享受劳动成果,但是感官享受带来的只是无意义感。主人固然是自为的,但这种自为却没有体现在他与具有否定性事物的接触中。不仅如此,主人生命需求的满足都要依赖奴隶,因此奴隶反而成了最重要的人。
3.主奴关系的扬弃
鉴于主奴双方同时具有自为性和为他性,故一方自在地就是另一方,主奴关系表面上的矛盾就被扬弃了。黑格尔进一步列举了这一消解过程的其他特征。
第一,主人与奴隶在开展自身活动时自在地就是对方。一方面,主人虽然声称不接触自然物,但是他在战斗过程中也要利用肉体和作为工具的武器,所以主人也是奴隶。另一方面,奴隶供养参与战斗的主人,因此奴隶也在间接地参与战斗,奴隶也是主人。不过,这种渗透只是潜在的;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真正综合,即一个既是奴隶劳动者又是主人战士的人,只有在能够发动全面战争的国家中才会出现。
第二,在需要的满足上,主人在享乐的同时觉得享乐是属于自然生命的、无意义的、应该被抛弃的东西;而奴隶劳动了却不能享受成果,而且他也认为自己不应该享受。因此,主奴双方都没有正确地对待生命需要。
第三,当奴隶不渴望自由时,主人也并不能真正地对自由有所欲望,因为首先,值得欲望的必须是一个他人也欲望的、普遍性的东西。其次,主人希望有另一个和他同样追求自由的人(而不是奴隶)来承认他,而他人对自由的意愿的最终体现就是现实地得到了自由;因此,我为了得到他人的承认,反倒要先给予他人自由和承认。只有当奴隶自由时,主人才能从自由的奴隶身上看到并意识到自由的自己,才能真正成为自由的存在。
(二)福山的“最后之人”
福山对黑格尔的第一个误解在于,他把自我意识为承认而斗争中必须被扬弃的不足和矛盾,当成了值得赞赏的东西。由于这些内在矛盾,主奴关系必然会转化成更高的精神形态,因此,如果把这些矛盾当成值得赞扬的本质特征的话,就割裂了为承认而斗争与更高级的精神形态间的辩证关系。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明确承认,他所借鉴的黑格尔是经过科耶夫诠释过的黑格尔,这或许是因为他十分明白,他无法保证自己笔下的黑格尔一定符合黑格尔的本意。他声称,对历史上的所谓“最初之人”来说:“人的人性欲望一定要战胜他的自我保存的动物性欲望。……我之所以战斗,目的在于获得别人的认可,让他承认我甘愿冒生命危险,因此是一个自由的、真正的人。”[3]170“冒死追求荣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样的人在当代社会已经几乎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和苏联都是一样的。只有那些暴力组织或贩卖毒品的人才能体现这种勇敢的精神,并因此而更有人性。”[3]170
福山指出,人类有两种被认可的欲望:“获得自己比别人优越这种认可的欲望——‘优越意识”。“优越意识”一词同时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暴君想侵略并奴役邻国人民且使之承认他的权威的那种“优越意识”;一种是钢琴家在音乐会希望别人认可他是贝多芬乐章最优秀的演奏者时的“优越意识”。再就是“平等意识,即获得与其他人平等的认可的欲望”[3]270。
然而当代却只是平等意识统治的时代,因为现在普遍存在的东西无非是生命经济化和平等意识。[3]217因此他才提出:“当历史走到尽头时,自由民主便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强劲对手。”[3]239240这种历史终结之后的社会就是后历史的社会。此时,一国国内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如竞争、技术、环保等。[3]231而国际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民族主义已经与自由主义和平共处并且越来越局限于私人生活的范畴,而经济合理性将侵蚀主权的许多传统特征,把市场和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起来。”[3]314在国际和国内层面,自由民主制度已经使得平等意识取代了优越意识:“现代民主制度不是把奴隶解放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是让奴隶和一种奴隶道德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种人经过对长远利益的算计,很巧妙地以一种新的方法满足了一大堆眼前的小小需要。‘最后之人没有任何获得比他人更伟大的认可的欲望,因此就没有杰出感和成就感。”[3]代序13
可见,对福山来说,历史的终结并非什么值得庆贺的事。甚至可以说,历史终结论“把美国的霸权视为平庸在全球范围的胜利。它的使命是,把这个世界从不断的美国化中拯救出来,也把美国从它自身中拯救出来”[4]。
该如何看待福山对黑格尔的借用?首先,“最初之人”为荣誉而战争,将自己理解为是自为的。但是,对自己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和对他者的理解是不可分割的。“最初之人”拒绝与事物打交道,因此只能以暴力的形式与他者打交道,因此他并不能正确地理解自身,也无法正确地理解何为荣誉。主人固然可以为展现勇敢而投身于战斗中,这既是其优点,却也是其悲哀,因为此时那些更值得追求的东西,如道德、伦理和上帝,都未得到显现。而这种尚未与更高级的精神形态相联系的英勇最终是要被扬弃的。其次,福山正确地认识到,冒生命危险是一种动物不具有的东西,只属于自我意识。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这种状况中,自我意识与动物性同样,是片面的。由于过分强调自我意识的一面,所以福山才会把人类在当代因科技和经济发展而得到的享受和消费视作堕落。但是,如上所述,在主奴关系中,人的自然需要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对自然需要的包容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实现,这就决定了主奴关系必然会被扬弃。总之,对黑格尔来说,主人这一精神形态有无法解决的矛盾,而福山对此却视而不见。
(三)生存论与生存状态意义上的承认
该如何理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精神哲学》等作品中的主人、苦恼意识、国家、艺术等精神的诸形态?它们是否与真实时空中的人、国家……对应?答案是否定的。在此,可以借助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进行理解。正如海德格尔的此在、上手、在-世界-之中-存在、被抛等一样,精神诸形态可以被看成是一些相互联系的生存论建构(existential structure),也就是一些建构性的存在状态。与此相对的,是具体的生存状态(existentiell)或生存可能性,比如,一个人可以是老师、男人、异性恋,等等。
因此,在以下两种承认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一是日常意义上的、生产状态上的承认,也就是福山所说的承认,就是当主体因自身行动而得到的认可、尊重或赞扬。二是存在论-生存论意义上的承认,即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之间的承认,它是主体间性的本质结构,或者说,只要我把他人看成是一个人,那么我对他就有这个层面上的承认,而无论我与他到底处于哪种存在者-生存可能性层面的关系中。相应地,还应在两种暴力之间进行区分:一是生存状态的暴力,即我可能实施的暴力行为,这也是福山所赞美的暴力:为追求荣誉而斗争的人不惧怕暴力及它可能带来的死亡。二是存在论-生存论层面的暴力,即人之为人就必须要陷入其中的、作为主体间性的一部分的结构性暴力。福山通过科耶夫的解读来理解黑格尔,其结果是像科耶夫一样错解了承认和暴力。即使黑格尔对暴力给予了肯定,也不是指这种现实中的暴力。
(四)时间历史与作为一种精神形态的历史
鉴于福山明确借用了黑格尔历史哲学,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黑格尔自己看来,历史有终结么?答案是否定的。精神诸形态并不与现实中的事物相对应,因此更不可能与历史阶段相对应——精神的确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关系,而是逻辑关系,低级形态自在地、潜在地是的东西,可以通过转化为高级形态而实现和释放出来,但逻辑上较高级的东西并不与时间上靠后的东西相对应。精神范畴必然要在时间中显现,但精神与时间却处于相互外在、漠不相关的状态。若试图将精神诸形态看成是时间中前后相继的东西,矛盾就会出现。例如,在《精神哲学》中,艺术是比国家更高的精神形态,若二者是前后相继的,艺术就必须在国家灭亡之后才会出现。但显然并非如此。
因此,我们需要区分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我们暂且称为时间历史)与作为精神形态的历史(即黑格尔《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中的历史)。换句话说,福山与黑格尔分别提到的历史并非同一个意义上的历史。就福山的历史而言,其发展是生存状态上的,例如,它从实行奴隶制度发展到实行封建制度。与此相反,黑格尔的历史是存在论-生存论上的,其发展是逻辑上的,而非时间上的。精神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把自己当成认识的对象;而历史作为精神的一种形态,其内部固然也有高级、低级之分,但是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历史诸形态与时间历史上的事物并无一一对应关系,即使有这种关系,也是偶然的;因此,历史的最高级形态出现,并不意味着时间历史发展到了终点。这是我们理解黑格尔为何把他所处的日耳曼世界的第三阶段说成是“历史的最后阶段”的关键。[5]
由此可见,黑格尔并没有主张时间历史会有一个终结这样的观点。科耶夫在此无疑是误读了黑格尔;而通过科耶夫来理解黑格尔的福山也将存在论意义上的历史的逻辑展开错认成了时间历史的终结。
三、福山对历史的终结议题所作的澄清
对于所谓历史的终结,福山的看法是谨慎而微妙的,他也为自己作了许多辩护。比如,在2014年他辩解称:“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6]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在2006年澄清说,“历史的终结”绝不是像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指“美国的世界霸权的缩写,不仅在思想和价值领域,而且通过实施美国的权力命令世界按照美国的利益运行”。不过同时,他也毫不怀疑地指出:“历史演化的总的逻辑解释了随着社会的进步,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在不断增加……这个演化过程的尽头比开头有更多的民主。”[7]
人们怀疑福山转变了思想,也是有理由的。首先,他在《衰败的美利坚》[8]等作品中,表达了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不满。其次,他似乎是在妥协说:“我的历史终结论从来不是一种决定论……人民愿意为法治、人权和政治问责制奋斗。这样的社会既取决于领袖、组织能力,也取决于纯粹的好运。”[6]再次,他提出,有四个挑战可能阻碍历史向更乐观的方式演进:伊斯兰作为民主的障碍、民主在国际关系上产生的问题、政治的自主性问题、技术发展难以预料的后果。 [7]
该如何理解福山的这些论断?笔者在此进行了总结:
第一,福山自始至终都未放弃历史终结论,他坚信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及民主水平的提高有其现实可能性。
第二,历史终结处的社会形态是种理想形态,其实现前景是不确定的,充满偶然性,要面临来自宗教、国际关系等方面的挑战。但是,这些挑战是否会消失,当它们消失后,是否会有其他挑战,福山没有给出确定的回答。
第三,综合第一、二两点,可以说,福山的态度仍然是比较模糊的,历史终结论的所谓“历史的终结”是一种建立在偶然性上的必然性。
第四,对于以美国为样板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福山从未感到高兴,因为这样的终结是伪终结:它的缺陷在于尚未把它本质上是的、潜在地是着的东西实现出来。
四、结论
以上分析似乎表明,历史终结论是个漏洞百出的理论,早该被扔进垃圾桶了;还有一些人试图从福山晚近的作品中寻找他的思想已发生了变化的证明。那么,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福山的观点还有哪些价值?
或许会有人在福山近年来的作品中发现,在他的思想中出现了明显的反民主成分,他开始不断思考美国民主的缺陷。但在不同的时间段中,福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
在《衰败的美利坚》和《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中,福山指出,国家能力与民主和法治一样,都是评价国家的重要尺度,但是美国的国家能力却是比较弱的。这一是由于美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较低,使得国家权力被少数只考虑自己私利的人或群体把持,从而降低了美国的国家能力;二是由于美国对民主以及限权的强调,导致各层面的否决权被滥用,这使得政府难以做出多少实事来。福山甚至主张应减少民主化方案,削弱民众参与度,降低政府透明度。
可是,以上主张并非福山的新思想。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福山也提到了能够把人从平庸或极端行为中拯救出来的办法:一是科学研究以及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二是登山、赛车等体育项目;三是选举政治;四是对外政策,特别是战争。[3]357-361在选举问题上,福山认为,平庸的“最后之人”的一大特点就是过分强调平等,过分的平等意识造就了过分的民主。因此,福山认可选举,并不是因为选举给了选举人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而是因为选举给了被选举人在竞争和观点交锋中体现优越意志并为得到承认、为胜利而斗争的机会。[3]359因此,选举是为少数主人而存在的,而不是为多数奴隶而存在的。若选举过分平等,过分在乎大众的想法,就会使各党派的分歧越来越少,使被选上台的人无法像主人一样拥有自主观点,而是像奴仆一样忙于经营管理之类的事务。不过,福山回避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当一个卓越之人在摆脱了平庸和过分民主的束缚而成为领导人时,有哪些规则能够防止他以“卓越”之名侵犯他人利益?第二,卓越的领导人的卓越意志到底是谁的意志,他如何对其领导行为的卓越性进行定义,是推动经济发展,还是促进分配公平,或是享受更多自由,还是其他社会价值?一种尼采式(以及福山式)的回答是,卓越之人自己为自己制定规则和意义。然而,这一回答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福山高度依赖的黑格尔哲学会提出反驳:如果一个社会只能服从于领导人的这种主观任意性的话,很难说这个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其次,如果坚称卓越之人的意志创造或代表了共同体的意志的话,那么这种偏向社群主义的观点同样会受到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批判。
总之,福山的反民主情结从他的历史终结论诞生时就已经存在,而绝非他在反思当下世界发展之后产生的新想法。只不过,由于研究兴趣的转变,他最初强调的领导人的“优越意识”变成了现在的“国家能力”。那么,福山借此要告诉我们什么?他是否是在鼓励各国建立某种非民主的制度?
无疑,尽管福山对美国不乏批判之辞,但他并没有宣称其他国家(除了欧洲国家)比美国更加有优势。美国固然在国家能力上有不足之处,但其他国家却可能在民主和法治上有所欠缺,甚至在这三方面均与美国有很大差距。福山思想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强调,正在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不应把美国当成模仿的对象,而是应该寻找自己在民主、法治和国家能力这三方面的平衡点。民主的理念本身是不成问题的,但重要的是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在此,福山的劝诱对象是所有尝试建立和巩固民主制度的国家中那些优越意识尚未被磨灭的人,他们应该像主人一样带着自己的思想、魅力和拒绝妥协的精神投身到公共领域中去。
[参考文献]
[1] 亚历山大·科耶夫. 黑格尔导读[M]. 姜志辉,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2]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王诚,曾琼,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99.
[3]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 黄胜强, 许铭原,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4] 莎蒂亚·德鲁里. 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M].赵琦,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7: 304.
[5]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 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413.
[6] 弗朗西斯·福山. 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EB/OL]. (20141027) [20150501].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41027115279.html.
[7]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之后[EB/OL]. (20060529) [20150501].http://www.aisixiang.com/data/9655.html.
[8] 弗朗西斯·福山. 衰败的美利坚[EB/OL]. (20141103) [20150501].http://www.qstheory.cn/politics/201411/03/c_1113014753.htm.
[责任编辑:陈可阔]
Hegel and Fukuyama: From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o the End of History
WU Jia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Francis Fukuyamas thought (including his antidemocratic view) has experienced little chang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ukuyama worries about the socalled victory of capitalism rather than hails it. Fukuyama misunderstands Hegelian philosophy in that first, he takes as ador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perior what should be sublated in the lordslave relation. Second, he does not differentiate the existential from the existential to the ontological; as a result, he confounds different kinds of recognition. Third, in Fukuyamas (mis)understanding, the Hegelian philosophy embraces an end of history. However, Fukuyamas "end of history" is still valuable for us today.
Key words: Francis Fukuyama; Hegel; lordslave relation; theory of the end of history; the end of history; democracy
——电影《郭福山》主题歌(男中音独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