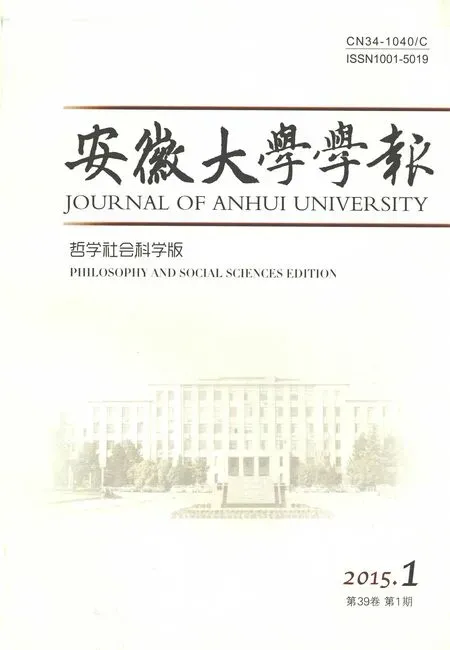论戴震礼学研究的特色与影响
徐道彬
论戴震礼学研究的特色与影响
徐道彬
摘要:“理”与“礼”是清代学术史上理学与考据学思想争议的两个重要概念。作为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戴震的礼学研究与理学批判,继承姚际恒和江永的治学路径,确立“理存于礼”的思想体系,启导凌廷堪“以礼代理”学说的建立,因而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和深远的学术影响。
关键词:戴震;江永;凌廷堪;礼学;理学;徽州;徽学
清代初期,统治者大力推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随着社会的由乱而治,朝廷由崇尚程朱理学而逐渐转向经术之学。在民间社会层面,作为朱熹乡邦的徽州学者,江永、戴震、凌廷堪等也顺应时代学风,奉行顾炎武“理学即经学”的主张,“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实;强调“圣人之道在六经”,“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戴震:《戴震全书》六《古经解钩沉序》和《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77页、505页。关于清代前期朝廷思想文化政策的变化以及当时学风的嬗变,请参阅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和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的相关章节。徽州地域学风及其特殊背景问题,可参阅拙作《徽州朴学成因的地域性解读——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戴震研究史料考辨四则》,《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1期。。他们或弃“理”而言“礼”,或“以礼代理”,“以古礼正今俗”,表现出异常的批判理学倾向。譬如江永以训诂考证手段研究古礼,纠偏和补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而作《礼书纲目》,轻视空言论“理”,注重躬行履“礼”,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学者绕过“理学”而求“礼学”,弃“理”言“礼”,减轻朱子理学和陆王心学流弊在徽州的消极影响。其后,戴震抨击程朱理学“以理杀人”,主张“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认为理学研究必须根植于经学,“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戴氏“理存于礼”和“理存于欲”的学术理念,开辟了清代礼学研究的新境界,成为反理学的急先锋,启导了清中期凌廷堪、阮元等人“以礼代理”思想的先路,在新理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一、时代学风嬗变与地域文化背景
徽州处于万山之中,“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戴节妇家传》,《戴震全书》六,第440页。。儒家的礼仪教化加之山野气质,使徽州山民知礼法,重气节,自谓:“礼者,人之干,而学者所以学为人者也。人不学,则不知礼;不知礼,则虽学而非其正。”*李菁:《茗洲吴氏家典序》,吴翟:《茗洲吴氏家典》,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礼者,天地之序也。先王知理之不可易也,乃为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盖其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家国天下,均莫能离也,夫岂可以斯须去哉。”*吴嘉默:《茗洲吴氏家典序》,吴翟:《茗洲吴氏家典》。这种儒家言行和礼仪规范,使得“家在万山中,风土犹为近古。冠昏丧祭诸大典,往往革其旧俗,庶几于礼;祸福之说中人,淫祀禁焉。又知其本在学,时时纠族人讲明约束,以培其根而达其枝,骎骎乎盛矣”*吴翟:《茗洲吴氏家典自序》,《茗洲吴氏家典》。。徽州人的“气节”和“士风”,“庶几于礼”,较之他乡尤为显著,故刘师培云:“惟徽、歙处万山之间,异于东南之泽国,故闻东林之绪论者,咸敦崇礼教。”*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刘申叔遗书》,1934年宁武南氏影印本。钱穆云:“盖徽、歙乃朱子故里,流风未歇,学者固多守朱子圭臬也。”*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0页。
作为比肩孔孟的一代儒宗,朱熹为中国传统礼学尤其是徽州宗族礼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朱子《家礼》也一直作为社会日常生活的标准而得以实施。朱熹随父居闽,也曾两次回乡祭祀、修谱和讲学,著《仪礼经传通解》,纂辑《文公家礼》(今本有后人附益成分)和《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在其周围聚集了程洵、滕珙、程端蒙等众多徽州学者,形成了以“新安理学”为名的重要学派。徽州民众也以朱子思想为范,躬行实践,以名教相砥砺。徽州六县“人习诗书,家崇礼让”,一派“里仁为美”的风俗气象。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没落,朱熹礼学的理学化趋势也日趋显著,其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贞节牌坊背后的血泪和理学“以理杀人”的呐喊,使得朱熹在徽州本土民众的心目中也逐渐失去了圣贤的光环,遭遇到猛烈批判。譬如,清初姚际恒在《仪礼通论》中批判朱熹对于礼学的无知与荒谬,曰:“《仪礼经传通解》一书,经传颠倒……吾实不解作者意指,以为尊《仪礼》耶?全录注、疏,毫无发明,一抄书吏可为也。尊之之义安在?以裁割《礼记》、《周礼》、史传等书附益之为能耶?检摘事迹可相类者,合于一处,不别是非同异,一粗识文字童子亦可为也。又何以为能?其于无可合者,则分家、乡、学、邦国、王朝等名,凭臆变乱,牵强填塞,此全属纂辑类书伎俩。使经义破碎支离,何益于学?何益于治?观其《乞修三礼札子》,欲招集学徒,大官给养,广拨书吏,迂妄至此,更有足哂者也!此书近世传本甚少,近有人重刊,然世究鲜传习,亦可见人心同然,但未能深知其非耳。至若黄勉斋之续编,吴草庐之考注,悉遵其指,又无讥焉。”“今不举臣瓒与陆,而举朱者,以朱为近世所宗,且实有《仪礼经传》之书故也。”*姚际恒:《仪礼通论·论旨》,陈祖武点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姚际恒有意挑选朱子作为批判对象,认为他裁割礼书史传,以附益为能事,“毫无发明,一抄书吏”而已,甚至比之为“粗识文字童子”。如此揭露朱子礼学的迂妄和荒谬,对乡先贤的批判直率大胆,不留情面。这种做法虽未免有所偏激,但由此也可窥见清初徽州学者与一般民众对待“万世师表”的朱熹及其理欲学说的反感。
与姚际恒相比,稍后的江永对朱熹的批判稍微间接而委婉、含蓄而蕴藉。其《礼书纲目》《乡党图考》《近思录集注》等书就是对朱熹著述思想的纠谬与补正,意欲通过古代礼制的考证,回归原典,绕过宋明理学的理欲之辩,而直接探讨古圣贤礼制的本始意蕴。认为圣贤之道在尧舜、周公、孔孟之原始儒学,绝不在后世杂糅释道的所谓道统和学统中,曰:“朱子说未备,乃采平岩及他氏说补之,间亦窃附鄙说,尽其余蕴。”*江永:《近思录集注自序》,《近思录集注》,四部备要本。关于江永思想研究,可参阅拙作《〈四书按稿〉非江永所作考》,《文献》2011年第1期。“读之既久,觉其中犹有搜罗不备、疏密不伦之遗憾。”*江永:《江慎修与汪绂书》一,余龙光:《双池先生(汪绂)年谱》,《乾嘉名儒年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江氏针对朱熹“凭臆变乱,牵强填塞”,曲“礼”而言“理”的做法,不做正面攻击,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文献考证手段对待之,名为“集注”,实为纠偏。如此做法正是遵循了朱熹“道问学”一路,而闭口不言“尊德性”,结果便是弃“理”而言“礼”,寓批判于“不言”之中。与此同时,江永又推动礼学下移,化“理”为“礼”,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在徽州的消极影响。他曾经修正朱子《家礼》,意欲恢复和保存古礼意蕴和仪式,云:“吾意亦但欲存古,以资考核,非谓先王之礼尽可用于今也。”“窃以为古礼虽不可尽行于今,今人亦当知其文,习其数。当世所行乡饮酒礼,饩羊仅存而坐席仪节皆非古。愚别有《演礼私议》,欲取《仪礼·士相见》《乡饮酒》及《戴记·投壶》篇,依古礼为仪注,选童子八岁以上、十五以下,假立宾主,教之威仪进退,以今服代古服,以蒲席拟古席,以壶代尊,以甆代俎豆,以瓦瓶代投壶,以刻木代雉贽,以茶代酒,以脯代牲。或就祠堂,或就家塾,令礼童熟娴于此,演而观之。一则使今人见先王之礼如此其彬彬郁郁;二则使童子习于礼,阴以化其骄逸之习,长其敬谨之心,亦可寓小学之教焉。投壶近于嬉戏而极典雅,童子为之,亦将有欣欣志古之心焉。”*江永:《江慎修与汪绂书》二,余龙光:《双池先生(汪绂)年谱》。江永以《仪礼》为本,“但欲存古”,对于朱子《家礼》的否定是含蓄和隐讳的,但还是遭到同乡理学家汪绂的强烈反对。
其后,戴震、凌廷堪也遵从江氏路径,从古代礼制的研究层面寻找“理存于礼”的突破口,并各有新的创获,这正是“皖派”推崇礼学、擅长礼学研究的原因所在。刘师培称:徽州学派咸精于礼学,“如江永《礼经纲目》《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释宫补》,戴震作《考工记图》,而金、胡、程、凌于礼经咸有著述,此徽州学者通‘三礼’之证也”*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刘申叔遗书》。。钱穆云:“徽州之学成于江永、戴震,江之治学自《礼》入。”“东原出而徽学遂大,一时学者多以治《礼》见称。”*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3页、275页。可以说,徽州学者群体式的礼学研究,实为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其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也非他处能及。无论章太炎的《清儒》还是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都对徽州学者专注于古奥艰深的典章礼制之事颇为疑惑,以至于发起探讨的兴趣,并一致认为: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蕴藉,盖地理感化使然。
在朝廷大力倡导实学、崇尚经术之风,以及徽州学者普遍关注礼学、反对理学的背景下,姚际恒、吴翟、江永等山村耆宿为了“志古之心”,矻矻于古礼的修正。他们的做法和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乡邦弟子的生活理念和治学方向,也影响到清中叶以后学术思想的转型与建构。
二、礼学的研究与理学的批判
戴震常言:“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段玉裁:《戴先生年谱》之“附言谈辑要”,《戴震全书》六,第714页。“明乎《礼》,可以通《诗》。”*戴震:《毛郑诗考正》,《戴震全书》一,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645页。所以,在戴震宏大的学术领域中,礼学研究占有极其重要的内容。据段玉裁《戴先生年谱》记载:《七经小记》是戴震一生的学术目标与规模,“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又分数大端,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训诂篇》《原象篇》《学礼篇》《水地篇》,而约归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段玉裁:《戴先生年谱》之“附著述辑要”,《戴震全书》六,第704页。。综观戴震的解经考证著述,如《尚书义考》《毛郑诗考正》《深衣解》《考工记图》,无不涉及礼乐制度、名物典章问题。而《戴震文集》中卷二《明堂考》论古代宫室建制结构及其礼义,《三朝三门考》论天子诸侯处理政务典礼之所,《匠人沟洫之法考》论古代井田制度,《乐器考》言古礼乐名称及设置问题。其他如《记冕服》《记皮弁服》《记爵弁服》《记朝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襦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括发免髽》《记绖带》《记缫藉》《记捍决极》等,皆绎古代礼服类别,探赜索隐,归纳义例。刘师培称此内容为“诠释礼制,以类相求,简约详明,远驾江氏《礼书纲目》上”*刘师培:《戴震传》,《刘申叔遗书》之《左庵外集》卷18。。此外,《文集》中还有《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论《周礼》中历法正朔与礼制关系,而《大戴礼记目录后语》《春秋即位改元考》《辨证诗礼注轨轵四字》《辨尚书考工记锾锊二字》《记夏小正星象》《释车》《仪礼注疏校记》《与任孝廉幼植书》《与朱方伯书》等等,也都是有关礼学典制研究的论文,或“取六经礼制之纠纷者,事各为类”,或“折衷众说,萃为一编”,皆可从中窥见戴氏对于古代政治制度、伦理规范及人生修养的探讨,及其“体国经野”、“志存闻道”的心路历程。所以,《清史稿》归纳戴震的学术领域为三——小学、测算、典章制度,其实三者皆不出礼制研究的范围。若追溯其始,戴震从徽州乡野来到京师,能够以素衣秀才的身份在很短时间内声名鹊起,也正是由于他的礼学研究得到了当时一流学者的广泛关注与推崇。如纪昀一见《考工记图》,便随即为之刻印。“时大司寇秦文恭公方为少宗伯,编纂《五礼通考》之书,延先生邸舍,就与商榷,其所采摭先生各经之说甚多”,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洪榜:《戴先生行状》,《戴震全书》七,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8页。。
戴震一生精力所萃,实在“三礼”,云:“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戴震:《古经解钩沉序》,《戴震全书》六,第377页。,如果“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书》六,第371页。。因此,他的学术切入点重在对上古社会典章礼制的研究,“稽之于典籍,证之以器数”,所以其研究成果也多为后来者所认同与传承。如论冕服云:“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后四幅,腰辟积无数,所谓帷裳者也。”论皮弁服云:“天子日视朝,皮弁服,诸侯以为视朔之服,凡诸侯相朝聘亦如之。”论爵弁服云:“爵弁服,礼又谓之玄服。”记深衣云:“深衣,连衣裳,杀幅而不积。”多为江藩、刘宝楠、孙诒让等引为证据*引文见《戴震文集·礼学十三记》,《戴震全书》六;参阅徐道彬《皖派学术与传承》(黄山书社,2012年)的相关章节。。戴氏考论礼制,兼证以文字声韵,言必有据而陈义简明,虽间有考订疏误、主观臆断者,但其探幽阐微,识断精审已令后人颔首,且取舍之间不乏经世致用之意。如《匠人沟洫之法考》云:“先王不使出赋税之民治洫与浍,而为法令民治洫浍者,当其赋税。故农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责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毕以供上,于是洫浍不治,井田所由废也。中原膏土,雨为沮洳,水无所泄,旸为枯尘,水无所留,地不生毛,赋减民穷,上下交病矣。”*戴震:《匠人沟洫之法考》,《戴震全书》六,第255页。戴震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古代的经史礼制,以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思想予以解读和阐释,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诚如章太炎所云:“衽席之间,米盐之事,古先王以是相民,而后人视之猥鄙。其中坚之言尽是也。震所言多自下摩上,欲上帝守节而民无瘅……如震所言,施于有政,上不呰苛,下无怨,衣食孳殖,可以致刑措。”*章太炎:《释戴》,《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2~123页。可见戴震礼学研究及其“理存于礼”的思想,既是他“以词通道”学术构想的最终目的,也是中国传统礼学思想与地域民风礼俗的充分展示。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故戴震与朱珪讨论丧服问题时,既尊崇古礼,又主以“礼时为大”,认为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而“归于得义”,不可与流俗相混用。云:“古礼之不行于今已久,虽然,士君子不可不讲也。况冠婚丧祭之大,岂可与流俗不用礼者同。”“后人于礼之名,无不从其重,未尝闻大夫及大夫之子,降旁期以下之为士者也,而于礼之实,几荡然不用。与其实去而名徒存,何如古人有正有降,一一各尽其实也。”“兹斟酌古今,名实两得,倘犹云失礼,则据《礼》证之固无失。倘云执《礼》太过,则必至是如于《礼》无讥。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要归于无所苟而已矣。”并且指出正服与降服、大功与小功,《礼记》中有明文,而后人对此“无不从其重”,名与实不符。“以今准古,名为期,名为大功,古礼断然为大功及小功也。小功卒哭之后,即可以取妻,况越过大功除服之后乎?然必父亦在小功之末方可。若父在大功之末,则可以冠子、嫁子,不可以取妇。凡言末者,谓卒哭之后,非谓除服之后。然则既虞卒哭,服虽未除,可借吉,明矣。大功之末,不可以取妇;大功既除服,固可取妇,甚明。”*戴震:《答朱方伯书》,《戴震全书》六,第369~370页。戴氏从冠、婚、丧、祭礼仪制度的源流,梳理古今礼俗的优劣与变迁,既有存古之功,也有适时之宜。此后朱彬《礼记训纂》、黄以周《礼书通故》对戴氏的说法都有一定程度的借鉴和吸收。
戴震学术不唯“道问学”,更在于“尊德性”,其礼学研究通过“以词通道”的实践来完成“理存于礼”的思想论证。如《考工记图》卷上“所以持衡者谓之”下云:“大车鬲以驾牛,小车衡以驾马。辕端持鬲,其关键名;端持衡,其关键名。辕所以引车,必施然后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关键,故以喻信。”*戴震:《考工记图》,《戴震全书》五,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349页。戴氏着力于从名物典制的考释中探求礼义人伦,“比类合义,灿然端委毕著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戴震:《原善序》,《戴震全书》六,第7页。,以此施于教化,自然有益于世道人心。又如《毛诗补传》释《汉广》诗意云:“礼不备不可求,犹舟楫不备不可济也。妇人谓嫁曰归,凡诗言‘之子于归’,在女子则适人之正也。秣马也者,欲驾车往迎之辞也。亲迎,礼之正也。”*戴震:《毛诗补传》,《戴震全书》一,第160页。这是从文字训诂中绎出“礼者,人道之极”(《史记·礼书》)与“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礼记·经解》)的经世之意。其《法象论》言“生生者仁,条理者礼”,“礼得则亲疏上下之分尽”*戴震:《法象论》,《戴震全书》六,第477页。;《中庸补注》言“礼,则各止其分是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此更益之以礼,即仁至义尽之谓”*戴震:《中庸补注》,《戴震全书》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70页。。诸如此类,可见戴氏在典章制度的考证中无处不贯穿对圣贤礼义的探讨,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和人文关怀。他批判“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戴震:《与段玉裁书》第九札,《戴震全书》六,第540页。,“甚或以后世之规模臆测先王之度数,殊失其真”*戴震:《仪礼释宫》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否定理学家浮谈无根、空言性理的做法,坚持“理义存乎典章制度”的观点。
《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理存于礼”思想的充分展示,开篇释“理”,即对“虚理”与“实礼”进行了深入剖析,批判理学家“其所谓理,别为凑泊附着之一物,犹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之凑泊附着于形体也”,指出真正的“理”,乃是“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是故谓之分理、条理”。戴氏释“理”重在“条理”,释“礼”本于“伦理”,追溯“理”字本义而牵出“礼”字,云:“何谓礼?条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故《疏证》尤其强调:“礼者,天地之条理也;言乎条理之极,非知天不足以尽之。即仪文度数,亦圣人见于天地之条理,定之以为天下万世法。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礼学”与“理学”的区别在于“欲”的对待问题,体现在“禁”“适”与“过”的态度,对于过度欲望,至于人情之漓,流于恶薄者,肆行无忌,是同人于禽兽。戴氏以为可以用礼治其俭陋,使化于文,将“礼”“理”“情”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辨析得清楚明白,即“理者,条理之秩然有序”,“礼者,天地之条理”,而“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既是“三位一体”,而又以“礼”为本。在《疏证》与《原善》中,戴震多次释“礼”字,皆以“条理”二字作答,弄清“心之所同然者,始可谓之理”后,戴氏指出:古圣贤之道,在于“条理之秩然有序”和“情之不爽失”,“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既是“礼”的本来意义,也是“情”和“理”的自然要求,知“情”达“礼”便是得“理”。同时强调“理”在“礼”中,人们只有通过对“礼”的切实履行,达到“秩然有序”之“理”,进而实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才能合乎圣贤经典的原始意义,即“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此段引文皆见于《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为简明起见而略注。朱熹是理学的代表,但他不能对理学的变异和后儒的道貌岸然行为负责;戴震批判朱子,意欲从根本上撕去伪理学的护身符而已,而对朱子始终礼敬。参见徐道彬《早期的戴震不是程朱理学的干城》,《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戴震对朱熹始终如一的态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戴震唯物思想的再认识》,《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纵观戴氏所论,一言以蔽之,一“礼”而已。
戴震常云:“总须体会孟子‘条理’二字,务要得其条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则无不可为。”*段玉裁:《戴先生年谱》之“附言谈辑要”,《戴震全书》六,第714页。此“条理”二字既是他治学的方法论,也是他反理学思想的有力工具。如果说《学礼篇》是戴氏的礼学考证结果,那么《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他对“理”与“礼”在文献实证与义理解读基础之上的思想剖析与哲理升华,最终归纳出理学“以理杀人”的哲学命题。此后,阮元的“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阮元:《书学蔀通辨后》,《研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62页。,以及凌廷堪的“以礼代理”说,虽然在力度上属于后出转弱,不及戴说鲜明有力,但在方向上则是一脉相承的。故胡适称:“他们努力的新方面更使我们明了戴学确然有建立新理学,恢复中国学者的哲学兴趣的大功。所以我们可以说:从戴震到阮元是清朝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叫做‘新理学时期’。”*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全集》第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8页。鉴于学界对戴震“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等相关言辞的熟知,为避免重复,此处简略。因为它“对于因袭的宋明理学作有力的革命”,“是新理学的建设”。侯外庐又以此认为戴震“复活了十七世纪清初大儒的人文主义的统绪,启导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年,第455页。。由此可见,戴震由破析“理欲二分”入手,实证于“礼”,而归之于“情”,得出“理存于礼”的结论,较之于江永置宋明理学于不顾,而暗中弃“理”言“礼”的做法,可谓有胆有识的革命者和建设者,戴震的礼学研究和理学批判确乎启导了19世纪新理学的一线曙光。
三、“理存于礼”思想的影响与发展
学术大师开辟的研究领域及其方法论的影响,往往造成一代学术风尚的转移。胡朴安说:“二百年来确有治学之方法,立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基础,衣被学者,至今日犹有受之而未尽,则休宁戴东原先生其人也。”*胡朴安:《戴东原先生集序》,《戴东原先生全集》,《安徽丛书》第六期,1936年铅印本。戴震治学“先考字义,次通文理”,求一字而贯通群经,而尤以礼学研究为重。常言:为学须先读《礼》,“为古文,当读《檀弓》”;“郑康成之学尽在《三礼注》,当与《春秋三传》并重”*段玉裁:《戴先生年谱》之“附言谈辑要”,《戴震全书》六,第714页。。所以,无论是在乡间切磋问学,还是在京师校订官书,戴震的礼学研究都对同仁与后学者起着引导作用。他早年在歙县“不疏园”中与江永、程瑶田、金榜、汪梧凤等讨论“三礼”,展露才华;中年在扬州卢见曾寓所与卢文弨校勘《大戴礼记》,显示深厚根基;以后在四库全书馆中辑佚、校勘《仪礼识误》《仪礼集释》《仪礼释宫》《大戴礼记》等,并为之撰写提要,为古代礼学典籍的保存与阐发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凌廷堪《礼经释例》皆以戴校本为底本),也因此“鞠躬尽瘁,死于官事”。钱大昕述其事云:“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先生为考究巅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职,以称塞明诏。经进图籍,论次精审,晨夕披检,靡间寒暑,竟以积劳致疾。”*钱大昕:《戴先生震传》,《嘉定钱大昕全集》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彭林《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一文,评述戴震为四库馆校订《仪礼》之事,认为:“清人最先诘难贾说者为戴震,戴氏反对贾疏强分二十字为两段,‘经既见“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传》不应重见此十字而绝不释其意,是二十一字通为郑注无疑’。戴氏所论,入情入理。今验之武威所出之汉简《服传》,亦无此二十字,其识见令人惊叹。”*彭林主编:《经学研究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第233页。
戴震的礼学成就不仅功在朝廷,而且对他周围学人的影响更为直接。程瑶田《五友记》云:“己巳岁,余初识东原。当是时,东原方踬于小试,而学已粗成,出其所校《太傅礼》示余。《太傅礼》者,人多不治,故经传错互,字句讹脱,学者恒苦其难读,东原一一更正之。余读而惊焉,遂与东原定交。至是,稚川、松岑亦咸交于东原矣。”*程瑶田:《通艺录·修辞余钞·五友记》,《程瑶田全集》三,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程瑶田与戴震交往三十余年,所受启发也最深,其巨著《通艺录》为清代杰出的礼学著作,对礼乐典章制度,博综淹贯,究明通彻,内中《考工创物小记》《磬折古义》《仪礼丧服足征记》等多有“吾友戴东原云是也”之语。而其《论学小记》对礼义的阐发也是承接戴说,笃信“理存于礼”而“礼外无学”。程、戴二人不仅在释“理”问题上是一致的,而且对于“礼”的认识也如出一辙。瑶田云:“圣人之志于学者,志于学礼而已矣。志于学礼以求其能立而已矣。是故圣人自以为三十而立也,故曰立于礼也。如其不能圣人也,吾即学礼,犹或不免愆于仪而败于度也。而乃礼之不学焉,则欲求不蔽于斯道不能也,欲求弗叛于斯道不能也,故曰不学礼,无以立也。”*程瑶田:《通艺录·论学小记·立礼篇》,《程瑶田全集》一。关于程瑶田思想研究,可参阅拙著《皖派学术与传承》上篇第六章。程氏认为,古昔圣人缘人情以制礼,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所以必待其人而后行者。其言“圣人缘人情以制礼”和“志于学礼”,皆本于戴氏“为学须先读《礼》”的思想。贵为乾隆壬辰科状元的金榜,早年在不疏园中即问学于江、戴,受戴震的鼓励和影响而专治“三礼”,自称:“岁丁亥,与戴东原同居京师。东原以《司马法》赋出,车、徒二法难通。余举《小司徒》正卒、羡卒释之,东原曰:此有益于为《周官》之学者。遂著录焉。”*金榜:《周官军赋》前小序,《礼笺》,《清经解 清经解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金氏该书引戴震说颇多,如《凫氏为钟》《明堂》等篇,多称“戴说是”、“足补郑注所未逮”之语。金榜的代表作《礼笺》,大至天文、地理、田赋、学校、郊庙、明堂,小而车、旗、器服之细,贯彻群言,折中一是。并且在思想层面上也认为古人为“学”就是习“礼”,修齐治平即是一“礼”字*徐道彬:《徽州学者金榜三论》,《安徽史学》2014年第5期。。此外,在江永和戴震治学风格引导下的一批徽州学者,如郑牧、汪梧凤、洪榜、洪梧、汪肇龙等在礼学研究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尤其是以胡培翚为代表的“绩溪三胡”以及俞正燮《癸巳类稿》等,更是在清季将江永、戴震的礼学研究与思想发扬光大。他们“以礼为用”,由研治古礼而“立保甲以卫乡,建义仓以赡孤寡”,尊亲收族,恤党赒里,扶持弱者,着力于躬行践履和人性关怀。
戴震33岁时因避仇离家后,一直在扬州、京师等地游学,对当地学风影响深远。任大椿向其请教后所作《释缯》《弁服释例》《深衣释例》等,皆以戴氏《学礼篇》为楷模。往复问难中,戴氏又作《与任孝廉幼植书》,告诫“不可轻议古人”。对于古代丧服制度中“大功”“小功”之别,以及《仪礼》中“兄弟”“昆弟”之异,作了详备的解说,并加以鼓励。曰:“以幼植所深訾为刘歆傅会者二条,今姑据此疏通证明之,其精微非圣人不足与于此,余皆可类推。戴向病同学者多株守古人,今于幼植反是。凡学未至贯本末,彻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载籍极博,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也。”“好学深思如幼植,诚震所想见其人不可得者。况思之锐,辨议之坚而致,以此为文,直造古人不难。”*戴震:《与任孝廉幼植书》,《戴震全书》六,第369页、365页。段玉裁记此事云:“先生以此箴之。《礼经》所谓兄弟与昆弟,立文大不同,至先生而其义始著。”(《戴先生年谱》之“庚辰”条)大椿得此精微之论,便奋力精进,著成不朽之作而传之后世。同时,其他学者继起,如“焦理堂作《论语通释》《格物说》《性善说》,攻乎异端,解以申戴氏仁恕之说。阮芸台作《论语论仁》《孟子论仁论》《论性命古训》《一贯解》,亦多本戴氏之说”。扬州学者不仅精深于古代典章礼制研究,而且能够辨析“礼”与“理”的源流关系,较之于苏州和徽州学者的“专精”,确乎具有“大”而“通”的特点。刘师培认为:徽州学派于礼学素有专攻,江永、戴震等于礼经咸有著述,影响波及后学。任大椿作《释缯》《弁服释例》,阮元作《车制考》,朱彬作《礼记训纂》,张惠言《仪礼图》颇精,乃徽州学派也。刘氏作为扬州学术的殿军,且对礼学有着精深的见解,坦言自己的学养根底来自于戴学启迪,并自称:“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学。”*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刘申叔遗书》。
对于戴震礼学研究及其思想阐发,继承得最为完备而又有所推进者,当首推寓居扬州的徽州学者凌廷堪*徐道彬:《论凌廷堪与西学》,《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他既得徽学之“专精”,又兼扬州学术之“通达”。与程瑶田深交多年,因知戴学之“始末”而作《戴东原先生事略状》,自称“私淑”,专力于古礼制的整理与研究。有诗曰:“儒者不明礼,六籍皆茫然。于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不明祭祀制,《洛诰》何以诠?不明宫室制,《顾命》何以传?不明《有司彻》,安知《楚茨》篇?不明《大射仪》,安能释《宾筵》?不明盥与荐,《易象》孰究研?不明朝与觐,《春秋》孰贯穿?如衣之有领,如官之有联。稽古冀有获,用志须精专。”*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4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关于清中期以后礼学思想的探讨,还可参见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陈居渊《论乾嘉汉学的更新运动》(《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等。由此诗的用词与诗意来看,完全脱胎于戴震的《与是仲明论学书》一文,其间的传承关系不言而喻。凌氏的代表作《礼经释例》一书,从归纳《礼经》内部义例入手,并作《复礼》三篇,对“三礼”学的思想意蕴加以提升与总结,云:“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7~32页。凌氏认为“礼之外,别无所谓学”,由礼意而推之于德性探讨,实为对戴氏礼学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戴震认为:古贤圣之所谓道,人伦日用而已,于是而求其无失,则仁、义、礼之名因之而生。“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全书》六,第154页。凌廷堪承续此说而加以阐发,云:“圣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也。”*凌廷堪:《校礼堂文集》,第27~32页。凌氏论礼不仅考释文字,探索礼例,解读名物制度,更能以道德仁义为依归,明确提出“圣人言礼不言理”之旨。由凌氏的言辞与意图可知,这是对戴震所言“人伦日用行之无失,谓之礼”,而非“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谓理”的进一步深化和高度概括。刘师培对此早已有所察觉,故特别指出:“凌次仲作《复礼说》三篇,谓理与礼同。洪伯初有《上朱学士书》,极论戴氏言义理有功于世道。若钱竹汀、孙渊如、孔巽轩、王德甫,其解释性理咸本于戴氏之说。”*刘师培:《东原学案序》,《刘申叔遗书》之《左庵外集》卷17。刘氏精于礼学,深知古代本理以制礼,认为理之所包者悉于礼制,古代多言礼而罕言理,凌廷堪《复礼》三篇言之最明。凌廷堪《礼经释例》与《复礼》三篇是清代礼学研究突破性的成果,他虽无戴氏反理学的大胆与气度,但能把重“礼”学与反“理”学思想加以对立与统一,提出“舍礼无以言学”的理论,已经影响了周围学者把目光由“虚理”的空谈转向“实礼”的考证,将学术由内在的“理”“礼”之争,转向外在实用制度层面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也为清季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准备。
清中叶后,因时势变迁,经世致用思想再度勃兴,而作为思想理据的经典研究,尤其是对“三礼”的阐释也方兴未艾。章太炎云:“弁冕之制,绅舄之度,今世为最微;而诸儒流沫讨论,以存其梗概,是亦当务之用也。任大椿著《弁服释例》,大椿之学出自戴氏;张惠言著《仪礼图》,惠言学出金榜,榜与震亦最相善。”*章太炎:《学隐》,《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8页。“吴越间学者有先师德清俞君,及定海黄以周元同,与先生(孙诒让——引者)三,皆治朴学,承休宁戴氏之术,为白衣宗。”*章太炎:《瑞安孙先生伤辞》,《章太炎全集》四,第224页。作为“三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详博渊奥,最合守约之法,而其中采用戴震之说近百处,如卷四十“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下,孙疏:“戴震云:王大祭,服衮冕;中祭,服冕。享先公亦大祭,而冕何也?《士虞礼》记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庙享,尸服有衮冕、冕之殊,则天子不敢一服衮冕。案:戴说是也。”此引文采自戴氏《学礼篇》之《记冕服》。又如卷七十五“察其葘蚤不则轮虽敝不匡”下引:“戴震云:‘人齿佹戾曰,凡物剌起不平曰匡。’案:戴说是也。”卷八十五“自其庛缘其外以至于首”下云:“戴震所图,以弦其内为自耒首触庛耑为直线,亦最为得解。”此二证皆采自《考工记图》,其他如“戴说近是”、“今依戴震说”、“戴氏所辨甚析”等语不胜枚举,其援引戴说以资考论,足以证明戴说的成就与影响。及至近代,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等对礼学都有精深研究,而自言受益于戴氏甚夥。王国维云:“古者天子诸侯皆三朝三门。先郑司农以为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汉唐诸儒皆从其说。其实天子仅有皋、应、路三门,而无雉门、库门。戴东原正之,是也。”*王国维:《王国维学术随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页。王氏考查古制,稽诸《周礼》郑玄注、《汉书·百官制》,详参阮元《明堂论》、焦循《群经宫室图》,又以北京朝门相参证,顺势而下,既证成戴说,也解决了历史上的难题。又如戴氏《明堂考》对于明堂结构的考证,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刘师培《明堂赋》也取正于戴氏。今之治礼学者有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钱玄《三礼通论》《三礼词典》等,采用戴说之处甚多。可见戴震对上古社会礼仪制度的考释结论经得起历史和学术的检验,并在治学思想和方法上对后世有导夫先路的作用。
诚然,戴震的礼学研究绝非完美无瑕,谬误疏失也所在多有,学界理应多加探讨。要之,戴震的礼学研究和理学批判,一是为了归还儒家经典原本,二是修正宋明以来对儒家经典的曲解和误读,故而由追溯圣贤、考证古礼入手,突破程朱藩篱,颠覆“存理灭欲”学说,建立新的义理学思想体系。可以说,戴震的礼学研究并不仅仅止于礼制的辨析与考证,而重在由“道问学”而入“尊德性”,“以古礼正今俗”,最终完成“理存于礼”的思想论证。《孟子字义疏证》批判理学“以理杀人”正是建立在《学礼篇》基础之上反理学的思想总结,并由此启导凌廷堪的“以礼代理”学说,在清代经学思想史和哲学发展史上树立起重要的里程碑。
责任编校:张朝胜
作者简介:徐道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安徽 合肥23003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ZX04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50016)
中图分类号:K295.4;B24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1-0100-09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