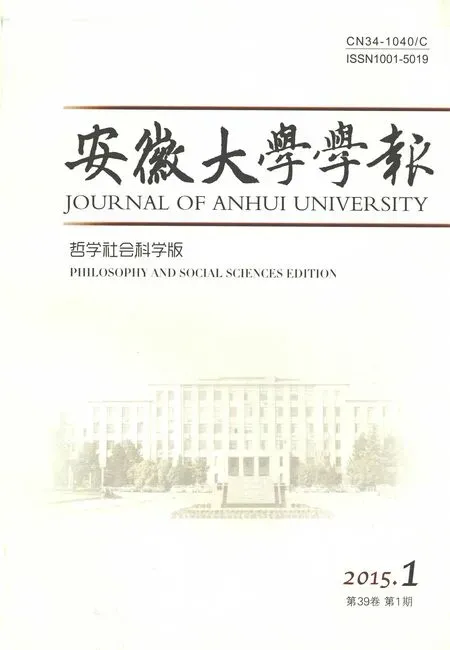“现在”:论利奥塔对现代性线性时间观的解构
余 沉,王 恒
“现在”:论利奥塔对现代性线性时间观的解构
余沉,王恒
摘要:对现代性线性时间模式的批判和终结是利奥塔后现代式“重写”的目标。对于利奥塔,线性时间模式是元叙事自我结构的基础和工具,是现代主体总体化与同一化操控的同谋。而在线性时间形式中,“现在”概念又有着特殊地位,正是这种“现在”将时间结构为一种现在—时间的同质而均匀的顺序流。因此,对线性时间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现在”的瓦解是利奥塔重写策略的关键。利奥塔以一种属于事件或发生的绝对“现在”来置换或拆除同质的“现在”,解构线性时间秩序,甚至于解构现代主体。这个绝对现在也是利奥塔后现代性的时间根基。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线性时间;现在
在现代性传统对时间的思考中,“现在”是一个特殊的视角,其不仅将时间分配给过去和未来,同时又给予过去和未来一种基于“现在”的时间定位。在利奥塔眼中,“现在”是从奥古斯丁,尤其是自胡塞尔以来所分析的时间性绽出(ecstasy)之一,这种分析依据的是一种企图基于意识来构成时间的思路*Jean-Francois Lyotard,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Rachel Bowlb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90.,意识通过对一种当下的维持构成并展开了时间在之前—现在—之后的线索上的流动。因此现代性的时间形式是一种以“现在”为核心的同质、均匀的时间流,这种时间流又被视为一种现在—时间序列。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本质上就是一种通过特权性的“现在”实现对未来以及过去的布展的时间操控模式,无论是乌托邦计划还是解放叙事都是依赖这种线性时间秩序进行自我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是现代性总体化与同一化统治的工具。在利奥塔对现代性的后现代重写策略中,对线性时间秩序的终结是其中关键性的一环。而在对线性时间秩序的解构中,特权性的“现在”便首当其冲成为利奥塔针对的目标。利奥塔的策略在于以一种绝对异质的瞬间概念来取消或置换传统时间观中的“现在”,从而瓦解线性时间秩序。这种绝对异质的瞬间也成为利奥塔后现代思想的时间性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利奥塔对时间的重写带有重写主体的企图。特别是在现象学的奠基性工作之后,时间与主体可以说成为现代性一体两面的根基。利奥塔对时间问题的处置同样关联到主体,甚至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个现象学式的计划,即通过解构现代性的时间性而解构主体性,并在一种异质性的时间中为他的后现代“人质”主体奠基。但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利奥塔的时间图景,对于时间性与主体性的关联在此只呈现为一个大致的线索。
一、现代性时间视域中的“现在”:从保罗到胡塞尔
虽然奥古斯丁和胡塞尔被利奥塔视为现代性的现在序列时间观的代表,但在利奥塔眼中,使徒保罗(Paul)的意义同样不可忽视。在对现代性的起源的探究中,利奥塔表明保罗为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时间性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正是保罗将犹太教的末世学引入了作为犹太人的“异邦”的西方,以末世学的时间构成取代了古典主义的神话时间,从而揭开了现代性的序幕。利奥塔指出,“在由塔尔斯的保罗(圣徒)、接着由奥古斯丁完成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的最初特征出现了,奥古斯丁从事这一工作是为了使古典的异教传统与基督教末世学相互适应”,也正是由保罗和奥古斯丁所重新思考的基督教,“才把确切意义上的末世学引入西方思想的中心”*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道德》,莫伟民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63页、64页。。
保罗对现代性的开创性作用并不仅在于他对末世学的引入,实际上,对于利奥塔来说,保罗对他所引入的犹太教末世学的改造才真正是现代性的革命性的开始,而保罗的改造恰恰就与“现在”时间有关。可以认为,现代性从一开始,从保罗这里,就由特权性的“现在”结构了。
可以看到,利奥塔通常将现代性的时间形态与古典主义的时间形式相对立,这种对立主要落实在二者所依赖的不同的时间基点之上。古典主义中,开头与结尾相互和谐,将来和过去总是作为整体一同到来,同一个意义单位包含着生命总体性。神话叙事是这种时间模式的典型,其体现为一种预定的命运,命运在开端处被给出,在展开中不断被诸神介入,在结尾处被落实和揭示。也就是说,古典或神话的时间性基点在过去,即在起源之中,神话叙说起源的故事。对于犹太教末世学而言,“开端到来,但结尾并不会与开始相连接,回归(return)也不是一个复原(coming back)。时间是处于退隐中的上帝之声(Voice)的神判法(ordeal)”*Jean-Francois Lyotard, Eberhard Gruber, The Hyphen: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trans.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1999, pp.13-14.。上帝为犹太人预设了一个目标,有关这个终极目标的真义随着上帝的道或上帝的律法被传达给犹太人。但在这里上帝的声音是不可重复的,能指与所指、语词与意义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因此时间将被耽搁在不断的重新的解读中,这一过程是一种无法获得解脱的痛苦和折磨。对于利奥塔,末世学开放了一种未定性的未来,未来(上帝的终极目的)不到来,其并没有被解读者占有,而是被保留给事件。
保罗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于以末世学为西方带来一个“未来”,带来一种“历史”。古典主义的命运之环被打破了。被开放的未来需要一种不同于古典主义的处理时间的方法,正是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现代性。在利奥塔眼里,现代性不是一个历史时代,而是以容纳高度偶然性的方式来形成时刻序列的方法,现代性的合法性在于未来。保罗在带来未来的同时就提供了一种对待未来的方法。可以说,在对犹太教教义的重新阐释中,保罗将一种当下化的“现在”引入了末世学的时间结构中。利奥塔认为,保罗放弃了有关上帝之道的不可理解性,放弃了律法的监护,放弃了解读的无尽性,他试图给予犹太教经文一个确定的解释,企图扮演可“欲”不可求的上帝的声音,如亚当那般以上帝的言来言说,他宣布弥赛亚的到来,宣布耶稣之死救赎了世人的原罪,宣布赦免,宣布道成肉身(incarnation),宣布时间的完成。这也就意味着,保罗实际上在末世学中树立起一种“当下”时刻,它是有特权的解释与规划的时刻*参见Christian Paul Holland, Time for Paul: Lyotard, Agamben, Badiou, Emory University, 2004, pp.11-57.Holland在他的这本博士论文中对利奥塔与保罗在时间性思想方面的关联作出了精彩的阐释,本文此处对利奥塔与保罗的分析借鉴了Holland的观点。。这个“当下”废除了掌控着解读工作的无尽的和偶然的未来,使退隐的、不可表达的Voice言说、进入在场。于是在利奥塔眼中,保罗代表了西方现代性时间观的真正开端和起点,保罗“将耶稣基督的具身化(incarnation),尤其是其复活置入历史的核心”,以此为“参照点”,“历史获得了一个‘那时’(then),一个‘在那之前’(before then)和一个‘在那之后’(after then)”,“在这一历史性(historicity)中,上帝对于人类的在场,并由此也是现在时态,成为事物的尺度”*Frans van Peperstraten, Displacement or Composition? Lyotard and Nancy on the trait d’ union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Religion, vol. 65, no.1 (Feb, 2009), pp.32-33.。这个“当下”时间使基督教获得了对犹太教的优势,“犹太人的真理处于基督徒之中”*Jean-Francois Lyotard, Eberhard Gruber, The Hyphen: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p.15.。对于保罗所培育的基督徒和为他所重新教化的西方来说,那个不能实现的、不会到来的未来是必须被排斥的东西,“犹太教的东西是必须被遗忘的东西”*Jean-Francois Lyotard, Eberhard Gruber, The Hyphen: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p.16.。在利奥塔眼中,保罗的开端开启的是一个同化与“遗忘”的历史,一个西方或欧洲几千年来排犹的历史,因为“犹太人”代表着欧洲对之有所亏欠却又将之遗忘和抹杀了的他者的证人。
需要被重写的现代性的时间性问题在保罗这里就被透露出来,保罗在把未来带给现代性的同时,就将这一未来的未来性取消了。通过这一取消,通过对特权性的现在的引入,保罗能够以末世学的部署实现一个有关主体的计划,在此计划中受失误影响的主体最后“能与自身调适并消除其分离”。保罗的末世学及其有特权的“现在”实际上成为利奥塔眼中的“连字符”(hyphen),即对差异的调和,对不可跨越的深渊的桥接。保罗的连字符实现了一个时间与主体的辩证法,被扬弃的是“结尾(l'achèvement)与他者(大写的Autre)”的距离,这二者重新获得了一种完全而整体的关系:他者本质上处于无法追忆的古老的过去,但却被允诺为最终的目的。当利奥塔说现代性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这一已失落的起源上”,其并不与他提到的现代性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作为目的的未来相矛盾,因为这个未来就是那个早已失落的起源。保罗以被当下规划、编程的未来克服犹太人的上帝的退隐、起源的退隐,未来成为起源的投射,也是对失落的起源的赎回,“末世学需要一种考古学”*利奥塔:《后现代道德》,第64~65页。,神话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被保留了。当犹太人的末世学以起源的退隐与无尽的未来瓦解了神话叙事中圆圈式的时间模式时,意味着现代性本能够“不断打开虚无的问题,事件的问题”*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4~175页。,但是当一种“现在”充当了连字符将过去与未来相连接从而将现代性重新封闭起来,现代性就产生了健忘症,这一健忘的恐怖后果不时地爆发并且无法被根治,它需要一种“彻底体验法”式的重写。
利奥塔从保罗那里发掘现代性的时间性规划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洞见,他也特别指出了保罗之规划的后果。利奥塔声称,在现代性所为之开始的连字符中,差异在同一中被遗忘了,这一同一带来一种痛苦,其可能是西方思想中最不可跨越的深渊的痛苦,是灵与肉被结合为一的痛苦*Jean-Francois Lyotard, Eberhard Gruber, The Hyphen: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p.13.。这一痛苦随着时间—历史的进程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很明显,在保罗之后,从奥古斯丁到胡塞尔,保罗式的末世学形式最终被奠定为一种现在—时间的线性序列,它构成主体性与知识学的时间“视域”,构成一种总体化的形式构架。
沿着利奥塔对保罗的描述的线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奥古斯丁是如何进一步规划了末世学的以现在为核心的线性进程。在《忏悔录》第十一卷中,奥古斯丁将时间置于心灵之内,以心灵的伸展来理解被造的时间并指向上帝的永恒,发展出一种内在时间模式。奥古斯丁时间之思的基本路径是以时间中之物作为领悟时间的切入口,将事物的时间性存在通过感知并借由印象及影像来内在化,他所谈论的时间是一种时间感,是对时间的知觉、感知。感知是一种当下具有(Gegenwärtigen),使被感知之物在其切身的当下中在场*张荣:《自由、心灵与时间——奥古斯丁心灵转向问题的文本学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8页。。因为感知,“现在”在时间三向度中获得了特权地位。对奥古斯丁来说,感知与度量是时间存在的尺度,而存在的时间只是现在:“过去与未来必然存在”,但“无论它们存在于何处,怎样存在,它们都只能作为现在而存在”*圣奥古斯丁:《忏悔录》(英汉对照全译本)(下),徐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57页。。在奥古斯丁这里,“现在”不仅成为时间的重心,也成为真实与存在的重心。要么就是现在本身,要么就是现在化的“过去”与“将来”,除此以外,无时间存在。
奥古斯丁对西方时间之思的奠基性作用不仅在于突出了现在,同时,他还将现在拉伸出一个时间的维度性与广延性。亚里士多德曾表明,“现在”是一个没有宽度的瞬间或无广延的点,仅仅作为运动的“之前”与“之后”的界限,它是一个没有存在性质的过渡。奥古斯丁则以期待、注意和记忆来伸展心灵,通过某种当下化活动而将瞬息即逝的现在滞留、拉伸、扩展、丰盈,奥古斯丁的“现在”就不再是一个瞬间的、静止的或虚无的点,而是获得了长度、存在与流动性。
借助于以期待、注意和记忆来伸展心灵,奥古斯丁不仅完成了时间的内在化、心灵化,同时还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时间进程结构,一个以注意为轴心的流动过程,即“通过注意,未来一路走过,成为过去”*圣奥古斯丁:《忏悔录》(下),第583页。。这一点被认为是奥古斯丁时间之思的一个最重要的成就,即“对时间进程的独特性和不可逆性的承认”*Herman Hausheer, St. Augustine’s Conception of Tim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46, no.5 (Sep.,1937), pp.503-512.。
奥古斯丁的作为唯一存在的现在,作为有长度的流动的现在,最终走向了胡塞尔的“活生生的当下”。现象学家关注原初的时间经验,他们同样注意到在非本源时间中被理解为现在的“当下”的核心作用,因此对原初时间的解释也仍关涉于当下—现在,试图重新构造“现在”从而为作为发生进程的本源时间奠基。在胡塞尔那里,现在成为一个在场域,有一个晕结构,“注意”通过“期望”和“记忆”向外延伸,原印象作为核心坐落到在场域的一种生发性的位置上,作为“绝对开端”生产出一个持续且顺序的流变。原印象便成为原制作,它“是所有其他的东西从中持续生产出来的原源泉”。从这一源泉流出来的是作为原印象的变异的滞留,“每一个滞留自身都是连续的变异,这种变异以映射的形式在自身中承载着过去的遗产”,“过去的遗产”就是“同一个起始点的所有以前的不断变异的连续变异”*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89页、86页。。前摄则是对即将到来之物的预期,其给予意识一个期待视域,“后面接下来的任何经验,都不可能跳出这个视域”,“即便是出乎意料的东西,也只能作为出乎意料的东西被把握”*克劳斯·黑尔德:《时间现象学的基本概念》,薛希平、孙周兴、张灯、柯小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5页。。过去与未来都处于意识的滞留的或前摄的意向赋义中。
胡塞尔希望区分客观时间和本源的时间,并指出后者如何使前者成为可能。他对本源的内在时间意识的建构实际上深化并加固了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统摄。在胡塞尔那里,“时间性也就是绝对主体性”,甚至于,“当下性就是主体性”。现代主体性哲学是在胡塞尔那里完成的,可以说,在胡塞尔完成主体性的同时也就完成了利奥塔眼中的现代性的时间性。“时间之谜根源于主体,实际上也就是主体——在根基(sub-)的意义上——之谜。”以现在或者原印象为绽出的基点,胡塞尔构建起一种时间—意识的总体性,构建起“感知—原印象—绝对主体性”这一能动的建构性本原,时间与意识、主体一同成为总体性操控的同谋。现象学或存在论所描绘的时间图景“不仅是‘滞留—原印象—前摄’或‘曾在—当下—将来’之类的绽出性结构,更是主体性在各个源始层面的表征。质而言之,这是‘理解’本身,‘理性’本身,一种统摄机制,一种权力”。于是,“现代性的过程就是总体化的历练。当资本的逻辑布展到全世界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时间被空间化了:绽出性的时间恰恰成为将一切收归己有的总体化。”*王恒:《时间性:自身与他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页、190页、194页、194页、7页。关于现象学中时间性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可参看该书。
可以看到,现代性对现在—时间的挖掘和奠基,最终挖出的是绝对自我、绝对主体,这一主体在它的时间性的发生的根源处找到的是自身触发、自我给予。在某种意义上,胡塞尔的主体性就为保罗以及他的基督徒完成了哲学上的奠基,胡塞尔不仅印证出当下时间的优先性,也印证出对当下时间有其权力的主体,证明了作为基督徒的“西方人”的无所亏欠与完整性,一个无所亏欠的主体便能自由地为自己而承担起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为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颁布律法。一切“对象”也就在绽出性的时间结构中被定位并前来照面,当其被“看”到、被经验到时,它总已经是主体的“掌”(grip)中之物了。在这种情况下,非己的、非理性的、不可理解的东西会被压制,并且在更深一层上,这种时间结构甚至必然会遗忘超出了理性—非理性、在场—不在场、记忆—遗忘之对立的他性,遗忘“原初的遗忘”。于是,在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这里,对封闭的、总体化的意识或主体的批判,对“在场”或“居家”模式的走出,总是与对时间概念的置换相联系的。而对时间概念的置换,又将同样落在对现在—当下时间的重塑上。利奥塔以及德里达等“后-”者,皆是以此来瓦解现代性或形而上学时间以之为根基的活生生的在场,终结线性时间序列。
二、利奥塔的“现在”:作为发生的时间性
在脱离传统时间秩序的进程中,列维纳斯等人已经开辟出一条异质性的时间理路。当利奥塔走在列维纳斯的“异于存在”的道路上时,其时间之思也处于列维纳斯的线索上。列维纳斯建构起的就是一种异质的当下,立足于这种异质的当下,过去和未来才既非前摄也非将来,既非滞留也非曾在,其脱离了原印象生产出的连续之流,如此才真正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才真正有时—间,在时—间中才打开了与他者相遭遇的可能性。利奥塔对现代性的现在时间的解构和他对一种发生的时间性的阐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列维纳斯的这一异质的当下瞬间的继承。在此方面,利奥塔同德里达一样,企图从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概念中发掘这种“本源”的绝对“现在”。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有过一个著名的对现代性的时间秩序的批判,他将这种通过被切除了头尾的现在来理解时间与存在的观念称为流俗时间观,对此他做了一个时间哲学史的叙述,表明这一流俗时间观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延续到黑格尔,乃至于胡塞尔的内在时间也停留在这一传统时间观的视野内。“对于流俗的时间领会来说时间就显现为一系列始终‘现成在手的’、一面逝去一面来临的现在。时间被领会为前后相续,被领会为现在之‘流’,或‘时间长河’。”*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76页。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现在序列的时间领会将时间的绽出敉平,遮蔽了现在的总体结构,它将时间领会为一个存在者。但康德被海德格尔摘出这一流俗时间观的历史,海德格尔试图在康德的先验想象力中寻找本源的时间性。德里达则认为海德格尔对时间的理解也同样处于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流俗时间传统中,海德格尔对源始的、本真的时间性与沉沦的、派生的时间性的区分和对立仍属于形而上学的操作。而在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流俗时间脉络中,康德不是处身事外,他的时间观同黑格尔一样也是对亚里士多德时间观的某种“转述”(paraphrase)*雅克·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杜小真、胡继华、朱刚、陈永国等译,夏可君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或参见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 Alan Bass,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1982, p.44.,“康德的革命并没有移动亚里士多德已经确立的东西,相反仍是置身其中,仍是在它里面整理布置”*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第194页。。因此德里达似乎是将康德置于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这样一条直接的线索上*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p.44.。而对亚里士多德,德里达又指出,亚里士多德确立的东西,既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保证,又是对这种保证的批判*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第199页。。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通过“现在”对时间的塑造既确立了一种“在场”形而上学,开启了流俗时间观的进程,也提供了脱离这一形而上学传统的资源。
利奥塔在《纷争》(TheDifferend:PhrasesinDispute)中也对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概念作了解读,并将他在纷争哲学中所阐释的发生的时间性树立在亚里士多德的“现在”之上。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从实体的运动来考察时间,将这种物理运动的“早”和“晚”纳入时间定义中,而现在(nun)就是对“早”和“晚”既联系又区分的东西:时间被认为就是那为“现在”所划分的东西(《物理学》,219 a29)*这里对亚里士多德的引用将完全参照利奥塔在《纷争》文本中提供的引用和翻译,以便对应利奥塔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解读。。区分在于,“现在”是一个原点,一个基点,先于它为“早”,后于它为“晚”;联系则在于,“早”不过就是尚不是现在,“晚”是已不再是现在。这番考察通常被视为亚里士多德建构“现在”时间序列的证据,当下瞬间似乎被授予了时间化的功能。
利奥塔为亚里士多德“翻案”的要点开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犹豫”。亚里士多德称,“时间被认为就是那为‘现在’所划分的东西”,利奥塔指出在“被认为”之后,亚里士多德又使用了非常有保留性的术语“hypokeistho”(“我们可以假设这一点”),这标志着授予“现在”以时间化功能的困难。利奥塔进一步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句表述“如果‘现在’度量时间,这是就时间包含‘早和晚’而言的”(219b 11-12),更加重了这种不确定性。尽管同一句话似乎可作如此理解:现在是时间之绽出的永恒的原点,这将通向一个时间化的“现代”版本,其流行于奥古斯丁与胡塞尔之间:一个构成性的(constituting)时间,受先验主体掌控的“活生生的当下”,与一个被构成的(constituted)、历时的时间。然而利奥塔指出,“亚历士多无视有关一种主体哲学的一切,他完全不会沿着这一现象学的方向出发”*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 trans. Georges Van Den Abbeel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73.,这其实是因为利奥塔在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中寻找到一种不可维持的、非历时的现在概念,因而斩断了这一“通向”的可能。
亚里士多德对时间化的现代版本的逃逸,首先体现在他的时间的疑难中,时间(早/晚)被现在确定,现在又受时间(早/晚)影响,即现在总不是现在,它不是尚未,就是不再,我们总无法在现在来言说现在:不是太早,就是太晚。在利奥塔看来,这意味着作为界限的现在,既非点状也非线状,而是之后者不停地吞噬之前者,“现在”恰是那无法维持的东西。因此,这样的“现在”,根本无法作为一种原初生发之物,来分配早或晚。在这种意义上,利奥塔的结论是,这种之前—现在—之后(before-now-after)序列的“流俗的”解释实际上足以挫败那种源于当下的时间建构。在此之外,利奥塔更为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逃逸路径,其发生在亚里士多德所区分出的两个“现在”上。
亚里士多德问道:“似乎划分着过去和未来的‘现在’——它总是同一个呢,还是它总是不同的一个又一个?这很难说”(218a 8)。对此,亚里士多德的回应是区分出了两种“现在”,其中的一种“现在”逃逸出了源出于现在的时间构型。亚里士多德说道,“在一个意义上‘现在’是同一的,在另一个意义上它是不同的”(219 b12)。就这一次或每一次的“现在”而言,它是同一的;就言说(tlog)(219 b20,220 a8)“现在”,将其置于一个短语中,或者将其视为一个实体(einai)(219 a21,219 b11,291 b27)而言,它不是它自身。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区分被利奥塔置于他的短语理论的框架内,他将“这一次是其所是”的现在解释为作为发生、事件的现在,即作为一个短语—事件:“就‘现在’是一个界限,它不是时间,但它发生了(sumbébèken)”(220 a21)。当发生被把握在另一个短语——此短语像指称一个实体那样去指称发生——的短语世界中时,即言说(tlog)——也即度量、排序——每一次的现在时,“now”变成了“the now”,“现在”经历了不可避免的历时变异。Now作为发生、作为呈现—事件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绝对,当其被言说,被置于“之前/之后”的关系中,它就被相对化、境遇化甚至同质化了。因此,利奥塔认为“亚里士多德将在短语世界中运作的历时算子同短语(或短语—发生)的发生区别开来”*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 p.74.,对一个当下的呈现(presentation)的呈现,或对呈现性的当下—现在的把握是不可能的,在根本上绝对现在永远无法作为自身、作为绝对而在表达或境遇中获得呈现。利奥塔以这种绝对的当下时间来对抗被维持在一种在场中,通过注意、期待和记忆获得延展的现在时间及其构成的同质时间流。当事件被保存(之后)、被期待(之前),或“被维持”(the now),事件就被遗忘了。绝对“现在”并不进入一种有本质关联的变异之连续,其先于并外在于一个历时序列,对于这个序列所进行的综合,对于意识的把握或语言的表达,绝对的“现在”瞬间是一种滞后和延迟,其表明发生的现在与短语所呈现出的现在及其构成的历时性之“间”,是一个无法被连字符所占据和填补的空—间或时—间,这是利奥塔的差异和纷争(differend)所归属的间隔。对于利奥塔,发生的“现在”对于语言与意识是陌生的、异质的,不可能为它们所构成和控制,更确切地说,“它是分解意识、解构意识的那种东西,是意识无法意识到的,甚至是意识必须忘记才能构成它自身的东西”*Jean-Francois Lyotard,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p.90.。
在作为发生的“现在”这一点上,利奥塔企图超出德里达在“存在与书写”(Ousia and Grammē)中表达的时间总是从属于形而上学的论断。他表明,如果时间的确是已然从属于形而上学,那么发生就完全不是来自于时间的问题,而是来自于存在/非—存在的问题。利奥塔的存在/非—存在的问题类似于海德格尔的Ereignis的显隐二重性,它意味着,如果时间只能通过在场而得到思考,那么事件或发生就是超出时间(当下)与在场的退隐、不在场或虚无,就将没有“时间”。
三、利奥塔的后现代时间:对现代性时间形式的重写
在对亚里士多德的“本源”时间的发掘中,利奥塔找到作为一种绝对“现在”的发生的时间性,它是利奥塔的异质或他性概念的逻辑起点,也是利奥塔“后现代”范式的时间性根基。《纷争》之后,发生的绝对瞬间概念散播在利奥塔一系列的思想漫游中,诸如在康德第三批判中揭示出的审美时间性,在杜尚和纽曼等艺术家的绘画中找到的此刻(now)概念,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情感中发展的情感的时间性,以及在思想的最后阶段所阐释的奥古斯丁的忏悔的时间性,等等,这些都共同致力于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的任务。
对于利奥塔,发生的现在作为绝对,不再处于晕结构的关联中或具有这一结构关联,它也就不是“活生生的”当下。在对情感或欲望的时间性的表述中利奥塔指出,绝对现在是欲望所知道的唯一的时间*Jean-Francois Lyotard, Lectures d’enfance, Paris: Galilée, 1991, p.136.,“现在”不接受变异,它是一个完整的因此是什么也不缺的、无关联的绝对或完满,“脱离了运动并因此忽略变形(flexion)和历时性”*Jean-Francois Lyotard, Lectures d'enfance, p.136.。也就是说,这个现在瞬间不可能进入原印象的当下感知,也就不可能成为作为原印象之变异的滞留,它不属于意识和记忆,这个现在因此是“记忆缺失的”(amnésique)。现在瞬间也无法作为将来而被前摄并进而被一个“现在”充实,它“只有通过不到达而到来”*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spute, p.77.,或者说它的来临造成一个真正的时间性眩晕,因为它“不出现于它自己的位置——一切都安排就绪要迎接它的那个地方”*利奥塔:《话语,图形》,谢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基于绝对现在,过去与未来一并得到重写。
就未来而言,对于利奥塔,未来是从属于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它不是胡塞尔的那种“已经填充在前瞻意向和充实之间的张力域中”的东西,它只有通过不到达而到来。根据黑尔德,真正的未来会使意识大吃一惊,使得胡塞尔的基本论题完全失败,“完完全全的未知、彻底的令人吃惊的,只是那种从前瞻性地预期到的充实中抽身而去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深层情绪对其开放的、让其‘到来’的那种东西”*黑尔德:《时间现象学的基本概念》,第58~59页。。未来在意识的意向性或精神的综合能力之外并且对意识造成严重打击和中断,使其震撼和麻木,它也就不是大叙事、不是资本现代性的逻辑可以按照蓝图操控和编程的未来,不是革新的技艺所能够让其到来的东西。真正的“新”在于这种未来。未来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规则和概念,对待未来需要的是反思判断力和审慎的政治,需要的不是应用规则而是为其寻找规则。
但就未来与过去两个视角而言,利奥塔似乎更重视过去。当利奥塔考察过去时,他便开始重新引入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精神分析的资源。精神分析从利奥塔思想的前期开始就被用于对现象学——无论是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还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的修正,它能够为利奥塔提供对统一性的狂热、对在某种统一话语中提供第一因的狂热和对起源的幻想的抵制*利奥塔:《话语,图形》,第12页。。在《纷争》一书对短语理论的构筑中,弗洛伊德的缺席实际上成为利奥塔的一个遗憾,因此《纷争》之后利奥塔恢复了与精神分析的对话。Bennington提到了这一点*Geoffrey Bennington, Late Lyotard,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08, p.90.,Anne Tomiche也印证性地指出,利奥塔思想后期有一个弗洛伊德的回归*Anne Tomiche, Rephrasing the Freudian Unconscious: Lyotard’s Affect-Phrase, Diacritics, vol. 24, no.1 (Spring, 1994), pp.42-62.。
借助于无意识的精神分析,利奥塔展开了一种“过去”的无时间性或悖论的时间性。利奥塔的过去指向一种开端或起源,但它是一种无起源的起源,也即无法被赎回、被修复的起源。实际上,利奥塔对现代性的可计划、可编程的未来的重写,更多的展现在他对过去的重写中。通过对起源的怀旧的破除,后现代企图保持结尾与他者之间不可克服的间隔。这个过去概念,如同利奥塔对纽曼的崇高瞬间的解读那样,仿佛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创世般的瞬间,是开启一个感性世界的开端,但同时“这种开端是一个二律悖反”。开端作为世界的最初的差异、作为历史的开端而在世界中发生,没有它“就什么也没有,或只有一片混沌”,但开端又不属于世界,它使世界产生却不是一个在世界中可以回溯到的源头,它自史前或无—历史(a-history)处降临。因此作为开端的瞬间“总是在那儿又从不在那儿”*Jean-Francois Lyotard,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p.82.,它只能根据其“有”(quod)而非“什么”(quid)来加以把握。
在《海德格尔与“犹太人”》中,“总是在那儿又从不在那儿”的瞬间以“过去”的面目出现在弗洛伊德无意识精神分析的框架内,此处正构成利奥塔所认为的无意识对意识哲学(现象学、认识论、政治学)的决裂。悖论性的过去,或者说“过去”的矛盾性的“在场”,其如同德勒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发现的那种过去,即一种没有过—去而总是在那里的过去。对于弗洛伊德,这种过去构成一种无法记忆之物的悖论,是属于无意识的时间悖论,弗洛伊德以事后性(Nachträglichkeit)概念加以表述,作为无意识的过去不是会被遗忘并且会被回忆起来的记忆对象,它“甚至不是作为一种‘空白’、不在场而在那儿,但它又在那儿”*Jean-Francois Lyotard, Heidegger and “the jews”, trans. Andreas Michel and Mark S. Rober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p.11.。
Bennington评论道,在对事后性概念的使用方面利奥塔格外地相近于德里达。Bennington指出,对于Nachträglichkeit,德里达认为这是弗洛伊德的真正发现,并且这一概念包含的时间构型通过引入一个不可凭借胡塞尔的滞留与前摄、表象与想象概念加以解释的彻底的不连续性而超出了胡塞尔的描述的可能性。在Nachträglichkeit中胡塞尔的瞬间顺序流被中断,“被一个以不连续的方式从过去跳出来的时间中断,当下对于这个过去并没有滞留性的或记忆性的连接”。事后性被弗洛伊德联系于一种创伤性的童年体验,这一“早先”的体验只在“之后”才显示出一种不可控和不可理解的后果,“在这儿时间性表现为在其中原初的‘经验’并没有在其发生之时被真正地体验到,而是在事件过去很久以后,在它的重现中才被首次体验到:但是这第二次的体验,伴随着来自它‘首次’发生时承载的情感的负荷,是作为对之后的时间—意识加工它的能力的瓦解而出现,其当然并非简单地是第一次事件的‘记忆’”*Geoffrey Bennington, Late Lyotard, p.91.。
利奥塔的事后性概念包含了两个基本内容,其一,一种本质的不对称的双重打击;其二,与意识现象学可主题化的东西无关的时间性*Jean-Francois Lyotard, Heidegger and “the jews”, p.15.。不对称的双重打击中的第一次打击,即作为一个心理装置所构成的力(force)的体系的骚乱的刺激,并不在这个心理装置的操控能力范围内,刺激发生并影响了心理装置却不被其“登记在册”。利奥塔举例道,如同人听不见但狗能听见的声音,或者如同紫外线、红外线一般无法为眼睛直接看到然而又产生影响的东西。尽管被打击者没有意识到打击,但打击的“结果”(effect)仍然在那里了。这一结果或效果被弗洛伊德称为无意识情感,弗洛伊德认为它是“一种并不打动(affect)意识的情感(affect)”*Jean-Francois Lyotard, Heidegger and “the jews”, p.12. 此处或者可作“一种并不触发(affect)意识的触及(affect)”。,利奥塔将其比作不受规则束缚的能量粒子的云团,这一云团不可能被组织成某种集合体进入到以言词和图像的方式进行的思考过程中,它像系统的热量一样弥散开来,是一种不可说、不可表象、不可转化的潜能,无法定位,无法使用,因此被心理装置所忽略。“形式和转化的缺乏是无意识情感的本质方面。”*Jean-Francois Lyotard, Heidegger and “the jews”, p.15.
简而言之,首次打击击打了心理装置却没有留下可感知的内在的效果,没有打动(affecting)它,首次打击是一个无打动(affect)的打击。而二次打击则是一个无打击的打动,仿佛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一个被刺激后的效果,或者说在效果突然产生后却无法得知它的具体原因。利奥塔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爱玛”案例,“我在一家商店购物,忽然焦躁不安,于是我逃走了,但事实上什么事也没发生。情感云团中散播的能量凝缩了,被组织起来了,其带来了一个行动,在没有一个‘真实的’动机的情况下发布了逃离的指令。正是这一逃离,以及伴随着它的情感告知了意识有某物,但又没能告诉它到底有什么。它指出了quod而非quid。这就是事件的本质:有‘先于’有什么”*Jean-Francois Lyotard, Heidegger and “the jews”, p.16.。
事后性或无意识情感的时间性就是无法被意识现象学所主题化的时间性,在其中,首次打击、原初的刺激没有在其发生的时刻被当下具有、当下把握,没有进入意识的感知领域。因此这一刺激也并没有以滞留的形式被储藏和离去,它以无法被觉察的方式在场,并在某个之后的时间、在二次打击中再次到来,“之前”在之后到来。但“过去”不是作为表象到场,不是作为记忆对象再次进入时间之流,它仍然是一种空白或匮乏,是当下化的意识的他者,被作为效果的情绪所暗指。“之前”的滞后性和延迟性是历时时间无法还原的非时间性或时间错序,利奥塔对犹太人的倾听与解读的时间性的阐释,以及对奥古斯丁的忏悔的时间性的挖掘都表达了一种类似的延迟的时间概念。延迟表明实现、完成、结束的不可能,表明规划和控制的不可能,当过去没有过—去,当过去总是在场,其在场又不被当下占有,对于利奥塔,这意味着意识、主体所欠下的债务未能被清偿,意味着赦免与宽恕的不可能。
从发生的时间性开始,借助于绝对的“现在”瞬间以及被其从接续链条上解开的过去和未来,利奥塔实施了对作为时间形态的现代性的重写,在此时间形态中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奠基于通过科学和技术解放全人类的计划”。现代形而上学的大叙事以计划(pro-ject)、设计(pro-grammed)好的展望(pro-spective),以及建议(pro-position)和提议(pro-posal)等等隐藏了属于未来的不可预料性和不可控性,它保留了神话的原则。后现代则是“‘居前者’(pro-)与他者(l' autre)之间的一种断口,或至少是一种裂隙”*Jean-Francois Lyotard,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p.34, p.68.。他者处于无法追溯的过去,过去总在之后到来,通过不到来而到来,它“不出现于它自己的位置——一切都安排就绪要迎接它的那个地方”。在后现代的怪异的、不连续的、悖谬的时间形式中,从保罗到胡塞尔的“现在”(the now)丧失了其作为可把握或把握性的点以分配、制作并统合时间的特权,甚至于,“居前者”与他者的这一裂隙就是由绝对“现在”所打开的空白和深渊,把握“现在”不是太早就是太晚表明“现在”对一种同化意图的超越(excess),即“对抓住和同化一个于此刻此地作为事情本身的‘实体’的计划的超越”*Jean-Francois Lyotard,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p.25.。
在置换了现代性时间形式核心处的“现在”时,依赖于时间的绽出结构进行总体化布控的意识、统觉或先验主体也就不再可能了。发生的“现在”瞬间是一个不可把握之物,是“意识必须忘记才能构成它自身的东西”,因此利奥塔指出,“某事发生,发生就意味着精神(mind)已被剥夺。‘……发生(it happens that……)’表达的就是自我(self)对自我的非—统治。事件使自我不能占有和控制它之所是。它表明自我本质上是对一种不断出现的他性敏感的”*Jean-Francois Lyotard,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p.59.。某种异质触发、被动综合的主体性概念被利奥塔继承,进入他后现代崇高美学领域和伦理领域,被利奥塔称作儿童、非人、“犹太人”、内在人等等,这种主体的根本要义在于它是律法的“人质”,是不可呈现之他者以及来自于这一他者的不可把握的触及的证人。
对于利奥塔,现代性的线性时间流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分期制,它的断代法(periodization),即以“前”“后”来理解时间的方式使得“现在”的立场未经审问,并使得一个“解读和书写的主体的自我—在场未经审问”*Dawne McCance, Posts: Re Addressing the Ethic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45.。主体与(现在)时间是现代性的双重根基,现象学揭示出这双重根基如何在根本上同构同源,列维纳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现在时间的同质化和同时性的打断而将异质性带入现代主体的中心,产生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利奥塔对现代性的时间性的重写展开的就是对“现在”与主体的审问,他所企图实现的正是在时间—主体的双重意义上为后现代奠基。
责任编校:张朝胜
作者简介:余沉,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恒,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210046)。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1-0034-08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