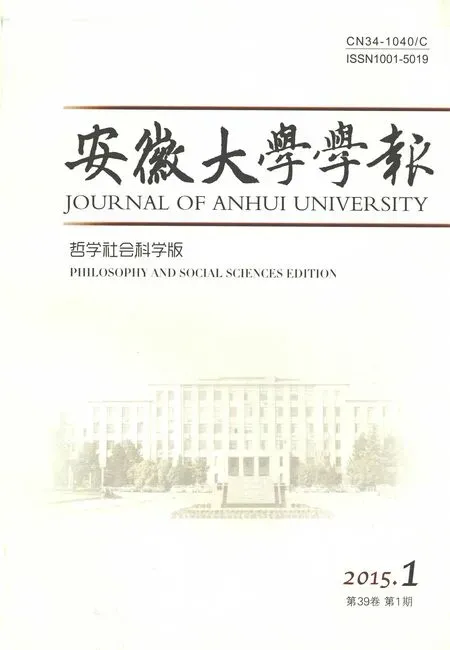曹植以赋体为中介的诗文互参
芦春艳
以铺排手法细致描摹写作对象,是赋体的重要特征。曹植在赋作类型、数量和艺术高度上的突出表现表明了其对赋体创作手法的娴熟。在汉魏之际,这种能力对于其他文体具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势能,很自然地横溢开来,带来写作中艺术表现手法的交融和互参。对此,徐公持先生指出了两汉魏晋时期“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现象①徐公持:《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两汉魏晋诗赋关系之寻踪》,《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而目前学界对曹植创作中赋的诗化问题有所论述,却较少谈及其赋体创作对包括诗体在内的其他文体的影响,对于其诗赋文创作间的关系更是少有提及。事实上,曹植的诗歌和散文受赋体铺排思维的影响极大,而从文体互参的角度看,赋体便成为诗文互参发生的中介。因此,曹植以赋体为中介的诗文互参,主要表现为对赋体铺排思维和结构模式的运用:一方面具有赋体特征的铺排、夸张修辞手法在诗、文中被广泛运用,另一方面诗歌与散文受铺排影响结构呈现赋体特征。
一、曹植诗、文中具有赋体特征的修辞
《文心雕龙·诠赋》中有:“赋者,铺也,铺彩摛文,体物写志也。”②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4页。可见赋体注重“体物”,强调对事物的刻画、描摹。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赋作便更讲究语言的铺张、华丽,这在修辞上便表现为铺排、夸张手法的使用。在曹植的诗、文中,铺排的大量使用,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夸张,都明显具有赋体的结构与风格特征。
(一)铺排手法的运用
通常情况下,人们更多地将铺排理解为排比,但在赋体中,除了修辞中的排比句式外,铺排更指以不同角度修饰对象时,句子在意义上的平行关系,因此铺排常常表现为有着明显修饰意识的、描述性语言的集合。如曹植在《大暑赋》中对炎热的描写:
蛇折鳞于灵窟,龙解角于皓苍。遂乃温风赫曦,草木垂干。山坼海沸,沙融砾烂。飞鱼跃渚,潜鼋浮岸。鸟张翼而近栖,兽交游而云散。于时黎庶徙倚,棋布叶分。机女绝综,农夫释耘。背暑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③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48~149页。
赋作列举了动植物、山川、沙石以及人类在暑热中的表现。虽然从句式来看,是几组对偶句的组合,并不能构成排比,但在意义上各句之间却构成了平行关系,这种平行关系也就是赋作的铺排。
铺排也被曹植运用到诗作中,如《圣皇篇》:
何以为赠赐!倾府竭宝珍:文钱百亿万,采帛若烟云。乘舆服御物,锦罗与金银。龙旂垂九旒,羽盖参班轮。①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24页。
诗句围绕赏赐丰厚这一中心,构成了意义上的并列,这与赋作中的铺排是一致的。铺排手法在曹植的诗歌中被广泛应用,如《斗鸡》诗中描述性的铺排:“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再如《当事君行》中用铺排说理:“朱紫更相夺色,雅郑异音声,好恶随所爱憎”这三句都是在为首句“人生有所贵尚,出门各异情”②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25页。提供依据。另外,用典与铺排相结合在曹植的诗作中也较为常见,如《豫章行》(其一):“虞舜不逢尧,耕耘处中田。太公不遭文,渔钓终渭川。不见鲁孔丘,穷困陈蔡间。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③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14页。诗中连用四个典故,都在为首句“穷达难豫图,祸福信亦然”提供依据;而《远游篇》中则大量运用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典故,来描述神仙境界,完成描写。总之铺排通过典故的连用得以实现。曹诗中有时会连续使用铺排,如赵幼文将《应诏》诗的内容划分为几个部分:“芒芒四句写途中所见农村富庶之状。爰有六句,写匆匆道路情景。仆夫六句,写车马途中奔驰。涉涧八句,写跋涉艰苦。将朝八句,描述渴求朝见之急迫心情。”④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78页。可见诗中这段对征途的描述,是由几组铺排组合而成的。这种大规模的铺排也可看出曹植诗歌对赋体的借鉴。
铺排手法的运用,也同样存在于曹植的散文中。如《求自试表》:
而位窃东藩,爵在上列,身被轻煖,口厌百味,目极华靡,耳倦丝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⑤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68页。
这与《七发》中吴客分析楚太子病情的话类似:“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膬,脭醲肥厚。衣裳则杂遝曼煖,燂烁热暑。”⑥(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60页。这段话位于《七发》的开始部分,赋作在此并没有进入正式的赋物阶段,但在表现太子生活的奢靡时,则明显使用了铺排手法。相比之下,曹植对富贵生活的描写更加集中连贯,句式也更加整齐,因而也就更具赋体铺排的特征。
与诗歌中的铺排类似,曹植散文的铺排,也分为描述、说理和用典三类。描述性铺排,如《求自试表》中写自己随曹操征战时用:“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⑦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70页。再如《前录自序》中有:“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氾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⑧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34页。这些句子连续运用叙述、比喻进行铺排描写,生动、形象地表达了文意。第二,说理类铺排,如《辩道论》:“夫帝者,位殊万国,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齐光日月。宫殿阀庭,焝耀紫微,何顾乎王母之宫、昆仑之域哉!夫三乌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丽也。云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饰也。驾螭载霓,不若乘舆之盛也。琼蕊玉华,不若玉圭之洁也。”⑨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34页。引文为了证明帝王的“位殊万国,富有天下”,使用了连续的对比,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第三是用典铺排,如《求通亲亲表》中描述自己的心情:“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棠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⑩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37页。这里用《诗经》中的四篇作品,来表明自己的所思所想,含蓄典雅,形象生动。
总体上,曹植诗、文中的铺排有以下特点:首先,铺排不仅限于整齐的排比句,还包括连续的对偶句,甚至是散句;第二,由于铺排需要通过较多同义句来表达一个中心意思,因此通常其所在诗、文的篇幅也相对较长;第三,由于表意的一致,句子间的衔接更加流畅,加之多数情况下句式的整齐,因此铺排手法往往使作品的语言更加流畅、表现力更为突出。铺排手法在诗、文中运用时所呈现的这些特点,与汉代大赋骈散结合、长篇、铺彩摛文的特征有相当的联系。
(二)夸张手法的运用
“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是对汉代大赋体制特征、表达效果的描述,这说明了汉赋追求赋物时的一种极致。这种极致首先是数量上的,铺排手法便是集中的表现。而在将数量推向极致的同时,所赋对象也在量的追加中被夸大了,即便西汉在武帝朝已开始进入鼎盛时期,但与现实相比,《子虚》、《上林》两赋中表现出的巨丽之美,仍然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由此可见,夸张手法存在于赋体的写作传统之中。
曹植现存的赋作中,使用夸张手法的并不多,《宝刀赋》中有较明显的夸张:
故其利:陆断犀革,水断龙角;轻击浮截,刃不纤削。逾南越之巨阙,超西楚之太阿。实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①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160页。
这一段采用了多个角度来赋物:先写宝刀的锋利;再与传说中的名剑“巨阙”、“太阿”对比;最后借佩刀者的不凡对宝剑进行赞美。可以看出,这类夸张的特点是,不同角度的赋物由实到虚,而对所赋之物的赞美程度,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强。夸张是在铺排的基础上构成的,更具赋体的形式特征。再如《登台赋》,其中“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②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5页。两句,是以夸张颂圣。这则更接近汉大赋以夸张表现巨丽之美的手法,带有功利性质。
曹植在散文中较多使用夸张。如《文帝诔》的序文中有:于时天震地骇,崩山陨霜,阳精薄景,五纬错行。百姓吁嗟,万国悲悼③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41页。。这段话从天、地、人的角度,表现了曹丕崩逝的影响之大,夸张明显。再如《与吴季重书》中有: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④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143页。。文章语言流畅而富有诗意的美感,是明显具有赋体铺排特征的夸张。
受赋体影响,曹植的诗歌中也有极力铺排、渲染的夸张。如《盘石篇》:
高波陵云霄,浮气象螭龙。鲸脊若丘陵,须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欐,澎濞戏中鸿。⑤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61页。
《汉书·文帝纪》中有:“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谓盘石之宗也。”⑥(汉)班固:《汉书》卷4,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06 页。孙明君认为,作为皇室成员、“盘石之宗”的曹植,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便借想象中的远游来抒发情感,而《盘石篇》的命名也正源于此⑦见孙明君选注《三曹诗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题解”。。引文中的诗句用夸张的手法,描绘出环境的险恶,折射出作者内心的忧惧。此外再如《孟冬篇》中描写狩猎的盛况时有:
万骑齐镳,千乘等盖。夷山填谷,平林涤薮。张罗万里,尽其飞走。⑧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35页。
诗中用连续的夸张、铺排,表现出狩猎队伍的声势浩大。而曹植的赋作《七启》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忽蹑景而轻骛,逸奔骥而超遗风。于是磎填谷塞,榛薮平夷。缘山置罝,弥野张罘。下无漏迹,上无逸飞。⑨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9页。
可以看出,除繁简程度不同外,《七启》与《孟冬篇》的描写内容和遣词造句,都十分相似,而这也足见曹植赋体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另外,与《赠白马王彪》中的“相思无终极”、“离别永无会”⑩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97、300页。这样的单纯夸张修辞相比,《孟冬篇》这类诗歌以铺排为基础的夸张特征更为常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夸张手法在曹植的诗、赋、文中均有使用。以铺排为基础、内容上具有歌功颂德的倾向,是曹植赋作夸张的主要特征。而其诗、文两体在借鉴赋体的夸张时,侧重点各有异同。相同点是,两者的夸张都是以铺排为基础,其中文类的铺排特征较诗歌更为明显。不同点是,诗歌更多地继承了赋体夸张的表现力;而散文中的夸张,则大多带有明显的功利倾向。总之,在参照赋体的前提下,以增加表现力为目的,是曹植的诗、文运用赋体夸张的相通之处。
二、赋体铺排思维对曹植诗、文的影响
从根本上讲,修辞方法代表的是一种组织语言和表述语义的思维方式和表意行文模式。而事实上,文学创作最终也可以归结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表意行文模式。相比之下前者更专注于局部意义的表达,其影响力是有限的;后者则是全局性的构思和表意行文。在曹植的创作中,铺排已经开始由影响力相对有限的修辞手法,逐渐转变为一种带有全局性的创作思维和表意行文模式。在曹植的作品中,铺排思维对诗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文章修饰意识的增强;二是抒情比重的减小;三是对偶句独立性的弱化。
(一)修饰性的增强
铺排手法本身便意味着对语义的多重修饰。如果单纯讲究效率,言简意赅是较为理想的表意状态。而铺排则是用一组句子来表述一个中心,其表意效率是不够高的。审美和表意是文学创作的两大目的,铺排在表意上的低效率,也就意味着它是在用更多的词语来达到修饰的目的。这里所说的修饰,一方面是指辞采之美;但更重要的是指对中心语义的具象化和多重界定。赋体所强调的“铺彩摛文”,便包含了这两个层面。如《大暑赋》中围绕暑热这一中心从不同角度展开铺排:首先作者集合了传说和典籍中与“热”相关的内容,在赋中,炎帝是司夏之神;祝融死后为火神;羲和是日之御者;南雀当即“朱鸟”,指凤,应是用凤凰涅槃之典与火关合;扶桑是日出之地,文中指太阳……①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149页,注1~8。这些典故的内容均涉及夏季、火、日这些与炎热相关的内容。在这里,作者一方面借典籍增加了赋作的文化意蕴,同时又借由文化上的联想,使读者对暑热有了形象的认识。在引经据典后,曹植又描写了龙蛇、草木、山海、沙石、鱼鼋、鸟兽、机女、农夫等一系列人、事、物,因炎热而表现出的非正常状态,用以多角度地表现暑热这一中心。而无论是用典,还是直接的描写,赋作大量铺排的目的都在于将暑热具象化。多角度的描写,实际上是想归纳尽可能多的情况,从而使暑热这一内涵更加准确地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认为,铺排思维实质上是用同类语义的句群,对中心语义进行具象化的诠释。另外,铺排在表达同一语义时用词的多样,以及赋作对辞采的强调,都使其更明显地具有修饰性。
曹植的诗、文继承了赋体注重辞采的特征,用词的不落窠臼和对中心语的修饰是铺排思维修饰性特征浅层的表现。在曹植的诗、文中,修饰性特征在更深层次上表现为:对事物的大量描写和对事理的细致阐述。由于铺排思维的本质是语义的多重具象化,因此当需要表现事物的情状时,便相应地需要大量描写;当需要阐明事理时,便要详加论述。
首先,对事物及其情状进行罗列、描述,是曹植诗、文的共同特点。如前举《圣皇篇》,诗中用铺排手法列举了所获赏赐的内容。事实上,“倾府竭宝珍”一句便可以概括铺排的全部内容。在这里,铺排的作用在于诗句意义的具象化和审美效果的提升。曹植的散文也是如此,以《前录自序》为例: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氾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②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34页。
文中对“君子之作”的一系列形容,都是为表达“与雅颂争流可也”这一意思做铺垫。与诗歌同理,即便没有这些美妙的形容,文意的表达也并不受影响,铺排中的描述与其说是在证明观点,不如说是在使文章更加形象,并富有美感。
第二,对事理进行多角度或反复的阐述,是曹植诗、文的又一共同点。如《当欲游南山行》一诗的最后四句:“嘉善而矜愚,大圣亦同然。仁者各寿考,四坐咸万年!”③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24页。是全篇的主旨,但作者却用十余句的篇幅类比罗列大量事例,从而达到证明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在用形象的内容表现抽象的意义。散文方面也是这样,如《画赞序》中阐述画能够“存乎鉴戒”时,用“见……莫不……”的句式列举了八种情况,说明画对观画者的种种影响。但从最后一句“是知存乎鉴戒者何如也”的语气来看,“存乎鉴戒”并不需要证明,铺排部分的作用更在于列举“鉴戒”的具体表现,其作用在于使内容更加生动、充实,避免单纯说理的乏味。
综上所述,赋体的铺排具有辞采和文意具象化两个层面的修饰性。受赋作铺排思维的影响,曹植在诗、文中注重对事物的大量描写、对事理的细致阐述等作品语义的具象化表述。作品因铺排的具象化而更加生动、形象、充实、富有美感,修饰性因而增强了。
(二)抒情分量的减小
在赋体中,铺排的主要作用是写物。如果将抒情归为主观性的表达方式,那么写物则应属于客观性的表达方式。那么铺排思维本身,就意味着客观性表达方式比重的增加。因此铺排思维的形成对曹植诗、文的影响,也表现为描写、叙事与抒情之间比重的失衡。
在曹植的赋作中,写景与抒情的比重是不平衡的。情景交融是理想的状态,但在情景分离的作品中,两者往往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曹植的赋作便是这样,如《节游赋》用大量篇幅先写宫室之美、游观之盛,只在赋的结尾用十句抒情言志,情与景篇幅的比例显著的不平衡。而在铺排思维的影响下,曹植的诗歌同样一方面表现出情景分离的倾向,另一方面表现出写物多于抒情的状态。如《送应氏》主要写作者登临远望之所见,诗中如实地描绘了战乱中洛阳城的凋敝、荒凉。诗歌几乎全篇都在写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用来抒情的诗句,仅有“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两句。可以看出,对景物的铺排式描写,是造成情景之间比重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情与景在文章中所占比重的失衡,与文章的抒情效果不能等同。在此消彼长的情景比例关系中,写景过多通常会减弱抒情的力度。但也存在像曹植《送应氏》一诗那样的情况:由于客观的景物无需渲染便能引发感慨,因此客观描写在量上的增加,便起到了暂时抑制读者情感爆发的作用;这样一来当铺排结束后,抒情句便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读者被压抑的感情得到集中释放,从而使文章获得良好的抒情效果。
与诗歌略有不同,在曹植的散文中,铺排思维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描写、叙事与抒情之间比例的失调。以《卞太后诔》为例,诔文用60个四字句,共240字的篇幅叙述卞后的生平,对其令德懿行进行了赞美,可见叙事部分铺排的规模之大。其中“德配姜嫄”一类的句子表明,曹植在这部分中更注重从母仪天下的层面赞美卞后。《文心雕龙·诔碑》中有:“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①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3,第212页。可见叙述生平、褒扬美德是诔文惯用的写作程式,曹植对生母的赞美固然源自真情,但无论是叙述生平的角度,还是情感表达的力度,他的赞美都没有逾越诔文的写作程式。那么如果抛开文采不谈,即便一般的文士为卞后作诔,恐怕也大致是如此。曹植对程式的遵循,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作者并不想在这一部分抒情。事实也是如此,曹植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用34句136字进行了集中的抒情。与叙述生平部分相比,抒情的篇幅较少。而同是诔文,曹丕所作的《武帝哀策文》、《弟苍舒诔》,则不存在这种叙事与抒情比重失衡的情况。由此可见,这种叙事与抒情的比例关系,是曹植常用的一种模式,这在他的《王仲宣诔》《任城王诔》《文帝诔》等抒情性散文中也有体现。而从以铺排手法叙事、注重客观写物的思维特征来看,这种模式明显显现出受赋体影响的痕迹。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在曹植的赋作中也有像《出妇赋》那样情景交融且抒情比重占优势的作品。而随着阅历的丰富,体验和感慨的加深,曹植在创作后期,也写出了一些情景交融的诗歌②吴怀东《论曹植与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确立》一文认为,曹植后期创作“减少了诗歌内容之社交性,大大发展了关注个人命运之抒情性,其诗歌创作的目的已转向抒发个人的政治压抑和生命忧思。”《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但从总体上,赋体铺排思维所导致的作品抒情比重的降低,是曹植诗、文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三)对偶句独立性的弱化
与六朝文章骈俪化的趋势相应,曹植也十分注重文章辞采的华美和句式的整饬。在注重对偶的同时,曹植在赋作中进行铺排时,往往会将几组同结构的对偶句连续使用。而由于句式结构的一致和铺排语句的流畅性,这种对偶句的连用,突破了同义反复、相反相成的对偶模式,具有了排比的性质。曹植赋作中的这类对偶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通过动词的连用来削弱对偶的相对独立,如“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洛神赋》)③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83页。。其中“阙”与“辕”同类,“谷”与“山”同类,因此这四句之中应有两组对偶句。但与此同时,由于“背”、“越”、“经”、“陵”表示的是一个相互承接的行为过程,所以本应划分为两组的对偶句,便因此加强了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排比的特征。另外,借动词消解对偶句独立性还存在一种不规则形式,如“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盼乎洛川”(《洛神赋》)④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83页。。其中“税驾”与“秣驷”是一类动作,“蘅皋”与“芝田”是一类环境,是十分严密的对偶关系。而后一组对句中的“容与”与“流盼”虽然也表示动作,但明显与前组对句的动作有差别,且词语结构也存在差异。至于“阳林”与“洛川”均为地名,也不同于前组。尽管两组对偶句都有着显著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但这组句子却仍在整体上给人流畅连贯的感觉,而这很大程度上与动词的连续出现有关。
第二类是借助某一句式、句型的反复出现,来削弱对偶的独立性,如:“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洛神赋》)⑤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84页。在这里“或”字代表的是“或……”这一句型,它的反复出现有效地连接了两组对偶。构成了排比形式,削弱了句中对偶的独立性。
第三类是借同类典故的连用,来削弱对偶关系,如“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洛神赋》)⑥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84页。。“屏翳”司雨,“川后”、“冯夷”皆为河神⑦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103~105页,第290~291页。,他们与女娲一样都是神话中的人物。四个典故的联合使用,使四组分句的并列关系显得更加突出,从而削弱了“收风”与“静波”、“鸣鼓”与“清歌”的工整对偶关系。
在上述赋句中,对偶句独立性的弱化,一是由于各对偶句结构的相同,二是与赋体铺排所形成的语言流畅性有关。但这只是表面原因,从根本来讲这是由于在造句、连句过程中,铺排思维占主导地位所致。也就是说,铺排句的成立是对偶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对偶句的各个分句,首先是以平行关系出现在铺排句中的,各分句首先要保证铺排的成立,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各自成对。因此在上述三个类别的赋句中,削弱对偶句独立性的方式,实际上也同时就是同结构铺排句的连接方式。
因铺排而使对偶句独立性减弱的情况,在曹植的散文中也是如此。首先,有借动词的连用来达到削弱目的的情况。如《求通亲亲表》中的“辞远游,戴武弁,解朱组,佩青绂”①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57页。,《求自试表》中的“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②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370页。。第二,有借某一句型的反复使用来削弱对偶关系的。如《与陈琳书》中的“披翠云以为衣,戴北斗以为冠,带虹蜺以为绅,连日月以为佩”③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176页。,是通过“动词……以为……”的反复使用来形成铺排。《诰咎文》中的“何谷宜填,何山应伐,何灵宜论,何神宜谒”④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57页。是先通过连续的反问句来形成铺排,再继之以填谷伐山、论灵谒神的对偶关系。而像《武帝诔》中的“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汉嗣,我王匡之。群杰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⑤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198页。则是在铺排中包含了四句为一组的大规模对偶句,而治理天下与匡扶汉室、服群杰与育黎庶的对应关系,却并不如大气磅礴的铺排那样引人注意。第三,有通过几种连接方式的综合使用,来削弱对偶句独立性的情况。如《求通亲亲表》中有:“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棠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⑥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437页。在这里,“远”、“中”、“下”、“终”表示的是思维在时间上的延续;“慕”、“咏”、“思”、“怀”是具有连续性的动作;《鹿鸣》、《棠棣》、《伐木》、《蓼莪》均为《诗经》中的篇章,是同属一类的典故。这三组具有连续性的词的出现,加强了句子的铺排性,而君臣与知己之义、兄弟与父母之情的对应关系则被淡化了。
与散文相比,曹植在诗歌中较少借铺排来消解对偶句的独立性,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如《游仙诗》中的“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丘”⑦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265页。,这种方位词东南西北与动词的联合使用,与上举《求自试表》中的情况是相同的。
三、结论
徐公持先生在论述两汉魏晋时期“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问题时曾指出:“汉末曹魏西晋,是诗赋二体双峰并峙的时期。在此种情势下,诗赋之间的实质性交流的内在机制,也得以形成。”而“‘化’,并非根本性质上有所改变,此物化为彼物,乃是指吸收对方的某些艺术长处,为我所用,属于取长补短之义”⑧徐公持:《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两汉魏晋诗赋关系之寻踪》,《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而赋体铺排思维对曹植诗、文创作的影响,一方面印证了曹魏时期诗与赋之间的文体交流,同时也表明至少在作家的个体创作中,这一时期的文体交流不仅存在于诗与赋之间,赋体的铺排、夸张等艺术特征也影响到了散文的创作。另外,铺排对诗、文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表明,铺排已经由修辞方法上升为创作思维。在曹植的创作中,铺排思维对诗与文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诗、文的修饰性增强、抒情性减弱以及对偶句独立性的弱化。曹植作为诗赋文三体兼擅的作家,其诗、文创作在吸取赋体艺术长处的同时,诗文两体也形成了以赋体为中介的诗文互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