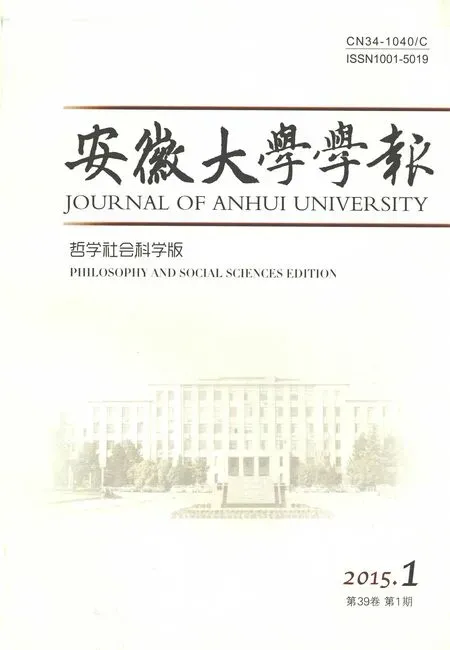吴文化对刘禹锡情性与诗歌的塑造
王志清,黄旦怡
刘禹锡是中唐诗坛翘楚,“三十年来天下名”①姚合著,吴河清校注:《姚合诗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页。,享有“诗豪”与“国手”的赞誉,堪与“韩孟”、“元白”相颉颃。刘禹锡的一生与吴地有着密切的关联,吴地生活是其生命旅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具有刻骨铭心的影响。吴地的山水人文塑造了他的文化性格,形成了他非常牢靠的吴地文化自觉,也规范了他的诗美取向、题材撷取,形成了他个性鲜明的诗歌风格与诗歌理论。
一、刘禹锡的吴地行迹与文化浸渍
吴地乃江南之核心地段,自古自然条件优越,人文环境非常富裕,才人辈出,艺术璀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刘禹锡出生于苏州嘉兴。“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②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60页。,又有“浙右列城,吴郡为大,地广人庶”③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171页。的盛誉。吴地自然环境钟灵毓秀,社会稳定,经济富饶,文化发达,较少受到战乱的破坏,特别是安史乱后北人大量涌入。刘禹锡十九岁始北游长安,贞元九年,一举及第,后又连中三科,即“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辞科”④(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28页。,此后随着昙花一现的永贞革新而经受着“二十三年弃置身”的“巴山楚水凄凉地”的放逐,这之间,也有为官吴地的经历。吴地对刘禹锡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刘禹锡对吴地也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而让他以“江南客”自许。他在吴地的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刘禹锡在日后还常常深情回忆其青少年时期快乐的日子,其《送裴处士应制举》中写道:“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钩斗得王馀鱼,踏芳共登苏小墓。此事今同梦想间,相看一笑且开颜。”⑤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302页。王馀鱼即比目鱼,是当时江南地区方言。
刘禹锡“家本儒素,业在艺文”①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1063页。,自小熟读经典,广泛涉猎,含英咀华。《刘氏集略说》云:“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行止,必操觚从之。”②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1179页。权德舆对刘禹锡很是赏识。《献权舍人书》云:“禹锡在儿童时已蒙见器,终荷荐宠,始见知名。”③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816页。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涉猎诸子百家,“纷吾本孤贱,世业在逢掖。九流宗指归,百氏旁捃摭”④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170页。。而他与当时极负盛名的二诗僧的游从,对于诗人刘禹锡来说,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机缘。他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江南著名诗僧皎然与灵澈,亲得二诗僧的精心调教,此后几十年的往来酬唱,更是深得灵澈诗法之精髓。诗僧灵澈是大历江南诗人中唯一经历中唐前后期的,对于衔接大历和贞元诗坛,尤对元和诗风的开启有重要影响,刘禹锡取其清丽放逸。灵澈圆寂十七年后,刘禹锡在为其诗集写的《澈上人文集纪》中回忆幼年与诗僧游从的情景说:“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⑤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1183页。吴中文化可谓是他们之间的枢纽。尤其影响深远的是,皎然、灵澈善于撷取民歌的养分来写诗,刘禹锡亦取法乎此;诗学上皎然讲“取境”,灵澈讲“意静”,刘禹锡亦同此理念。
吴地的温山软水,以及吴地的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培养出刘禹锡崇尚清绮明丽的诗学趣味。吴地的经历,也自然使刘禹锡在情感上偏爱南朝名士与诗人诗风,譬如南朝的“三谢”(谢安、谢灵运、谢朓)就让他崇拜至极,也对其影响甚深,具有终生精神相伴的不解情缘。诗中直言:“恩华辞北第,潇洒爱东山”(《和李相公以平泉新墅获方外之名因为诗以报洛中士君子兼见寄之什》)。东山位于今浙江省上虞市西南,东晋谢安隐居处,紧挨着刘禹锡幼时的居住地。《晋书·谢安传》载:“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⑥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79页。诗文典故上,东山即是谢安的指代,即是功成名就、潇洒风流的代名词。刘禹锡在扬州期间,最爱去法云寺游观。这里原为东晋谢安的居第,其姑母出家,以此旧宅建寺名法云。寺内两株大桧树,相传就是谢安种的。刘禹锡曾有诗《谢寺双桧》云此:“双桧苍然古貌奇,含烟吐雾郁参差。晚依禅客当金殿,初对将军映画旗。龙象界中成宝盖,鸳鸯瓦上出高枝。长明灯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年少时。”⑦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404页。那日夜常明的灯,还是曾经照耀谢安的前朝点燃的火焰,这与“古人不识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同妙。诗人怀古思今,生成念及此生的感慨。谢安成为刘禹锡的精神高标,其诗作屡屡以“东山”提及,如“从此东山非昔游”(《伤秦姝行》)、“东山旧路独行迟”(《窦夔州见寄寒食日忆故姬小红吹笙因和之》)、“谢公莫道东山去”(《庙庭偃松诗》)、“请向东山为近邻”(《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东山与东阁,终冀再经过”(《将之官留辞裴令公留守》)、“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天下苍生望不休,东山虽有但时游”(《奉和裴令公夜宴》)等,诗人大量用此典事,表现了深深的惊羡与自况之情。
刘禹锡的诗中还频繁出现“大谢小谢”的典事。用大谢诗典的如:“海峤新辞永嘉守”(《酬令狐相公赠别》)、“谢墅阅池塘”(《和乐天洛城春齐梁体八韵》)、“兴发春塘草”(《浙西李大夫示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继声》)、何必池塘春草生(《裴侍郎大尹雪中遗酒一壶兼示喜眼疾初平一绝有闲行把酒之句斐然仰酬》)、“蕙草芳未歇,绿槐阴已成”(《酬令狐相公首夏闲居书怀见寄》)、“自言买笑掷黄金,月堕云中从此始”(《泰娘歌》)等。
刘禹锡诗中提及谢朓的更多,如“谢守工为诗”(《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太平寺诣九龙祠祈雨二十韵》)、“谢公高斋吟激楚”(《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对月听小童吹觱篥歌》)、“谢守瑶华赠”(《和州送钱侍御自宣州幕拜官便于华州觐省》)、“谢守何烦晓镜悲”(《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沙浦王浑镇,沧州谢朓城”(《历阳书事七十四韵》)、“更报明朝池上酌,人知太守字玄晖”(《酬窦员外旬休早凉见示诗》)等。刘禹锡诗《九华山歌》:“君不见敬亭之山黄索漠,兀如断岸无棱角。宣城谢守一首诗,遂使声名齐五岳。”按:《元和郡县图志》卷28宣州宣城县:“敬亭山在州北十二里,即谢朓赋诗之所。”谢朓为宣城太守时有诗《游敬亭山》。谢朓还有诗“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宣城郡内登望》),古人说刘禹锡《汉寿城春望》“此篇从之出也”①卞孝萱:《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0页。。刘禹锡的诗中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就跳出了谢朓的名句,活用谢朓诗典。如刘诗《和令狐相公晚泛汉江书怀寄洋州崔侍郎阆州高舍人二曹长》“江澄暮霞生”,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刘诗《答柳子厚》“会待休车骑,相随出罻罗”,谢朓《休沐重还道中》:“还邛歌赋似,休汝车骑非。”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刘诗《河南王少尹宅宴张常侍二十六兄白舍人大监兼呈卢郎中李员外二副使》“礼成同把故人杯”,谢朓《离夜》:“山川不可梦,况乃故人杯。”刘诗《窦朗州见示与澧州元郎中早秋赠答命同作》“芷江兰浦限无梁”,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风云有鸟道,江汉限无梁。”刘诗《历阳书事七十四韵》“远岫低屏列”,刘诗《重送浙西李相公顷廉问江南已经七载后历滑台剑南两镇遂入相今复领旧地新加旌旄》“窗中远岫列三茅”,谢朓《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
刘禹锡生于吴地,长于吴地,学于吴地,日后也为官于吴地。吴地对刘禹锡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刘禹锡的“三谢”崇拜,即是其深受吴文化熏染的明证,也反映了他在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内容与欣赏趣味,并且铸成其热爱自然、崇尚雅趣的文化性格。刘禹锡的个性、才华、思想都打上了吴地的烙印,形成了吴地的文化自觉,吴地也一直牵引着刘禹锡的情思,进而也规范了他的诗歌美学取向、诗歌内容题材、诗歌风格旨趣。刘禹锡诗歌中大量的作品也写作于吴地,吴地山水人文,不仅从精神层面塑造了刘禹锡,而且为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生成了不断激发的创作灵感,以及清丽放逸的美学取向。
二、刘禹锡的吴地文化自觉与其诗的吴地印记
吴地生活成为刘禹锡创作的不竭源泉与灵感。一方面,他自觉地在创作中大量撷入吴地物象,极大丰富与充实了他的创作内容;另一方面,其诗歌中频繁出现的吴地情怀与意象,以及遗古故苑、风土民情等其他吴地元素,也使其诗歌凸显出鲜明的吴地印记。
(一)刘禹锡诗中大量的吴地物象
吴地自古就是江南文采风流地,山有灵岩虎丘之胜,水有五湖三江之饶。陆机的《吴趋行》诗对吴地大加赞美说:“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②陆机著,金涛声点校:《陆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2页。。刘禹锡自小在这种山水人文环境中浸润,吴地的草木与其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情。吴地的生态环境中,水是其特别滋润的元素。因此,“水”意象在刘禹锡的诗中频繁出现,“水”的字眼高达200余处。其他的吴地风物也触目皆是,我们将之统计为表1(见下页)。
此表可以说明:1.刘禹锡的吴地物象异常丰富;2.刘禹锡在吴地的创作多用吴地物象;3.刘禹锡不是吴地的创作(如洛阳、长安、汴州等地)也常常用吴地物象;4.刘禹锡各个时期的创作都有吴地物象出现。因此,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吴地的物候景象,对刘禹锡的浸渍极其深刻与牢靠,已经进入且流动于其血脉,当其命笔时则自然奔涌而出。
(二)刘禹锡诗中的软语吴吟
自小生活于吴地,可以肯定的是刘禹锡的方言自然是吴侬软语,也可以推断他必然熟悉吴声,深受吴歌的熏陶。而这些推论,在其日后完成的诗歌创作中也得到验证,可见其汲取乐府民歌营养的自觉,也可见诗中吴歌影响的深刻。
“侬”乃吴语中最突出的人称指代词,吴人常被称为“吴侬”。至今苏州话依然是以“吴侬软语”称之。吴人自称“我侬”,称人则“渠侬”“个侬”“他侬”。唐代嘉定隶属苏州的,有所谓“三侬之地”。高德基《平江记事》记道:“嘉定州,去平江一百六十里,乡音与吴城尤异,其并海去处,号三侬之地,盖以乡人自称曰吾侬、我侬,称他人曰渠侬、你侬,问人曰谁侬。”①高德基:《平江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刘禹锡诗中使用“侬”之口语的现象特别醒目。如“才子从今一分散,便将诗咏向吴侬”(《福先寺雪中酬别乐天》);“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竹枝词九首》其二);“何物令侬羡,羡郎船尾燕”(《淮阴行五首》其四);“君家侬定谙”、“侬入无度数”(《插田歌》)等。吴语中还常在称谓或人名前加“阿”来表亲切的语气。“阿”在刘禹锡的诗中也频繁出现,如“映叶疑开阿母桃”(《吐绶鸟词》)、“春深阿母家”(《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其二)“阿母种桃云海际”(《步虚词二首》其一)“合在增城阿姥家”(《思黯南墅赏牡丹花》)等。刘禹锡在诗中还常用吴方言“伊”来表示第三人称。如《送李策秀才还湖南因寄幕中亲故兼简衡州吕八郎中》诗中连连出现“伊”字:“岂伊山水异,适与人事并”、“惟昔与伊人,交欢在夙龄”等。此外,刘禹锡的《何卜赋》中也用“伊”:“人莫不塞,有时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穷。人莫不病,有时而间,伊我兮久而滋蔓。”《伤往赋》中还多次用“伊”,如“叹独处之邑邑兮,愤伊人之我遗”等。这些都表明,吴语的语汇已经渗入刘禹锡的血脉之中,形成了他的文化肌理。刘诗中多运用温软、婉转、甜美的吴语。比如《赠日本僧智藏》“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中的“宁馨”是至今吴中人语言表示“若何”或“如此”之意。
刘禹锡生活在被誉为“一唱值千金”之民歌盛行的吴地,即便是放逐,也多在朗、连、夔、和等江南地域,他对江南民歌似乎具有特殊的好感,也善于撷取民歌的养分来写诗。其《杨柳枝词八首》其一:“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诗人明言乃是新翻。《和乐天洛下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兼见怀长句》云:“旧相临戎非称意,词人作尹本多情。从容自使边尘静,谈笑不闻桴鼓声。章句新添塞下曲,风流旧占洛阳城。昨来亦有吴趋咏,唯寄东都与北京。”诗中“昨来亦有吴趋咏”,直言自己的诗亦乃吴咏。吴趋,即吴地,或即吴门,至今苏州还有“吴趋坊”的地名,如陆机的《吴趋行》。吴趋,还是一种曲子,即为“吴趋曲”,又叫“吴吟”,是吴地特有的音调,晋人崔豹《古今注·音乐》:“《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也。”陆机的《吴趋行》诗,早就有“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①陆机著,金涛声点校:《陆机集》,第72页。的描写。李白诗中也频繁出现吴趋吴吟:“我有吴趋曲,无人知此音”(《赠薛校书》);“试发清秋兴,因为吴会吟”(《送鞠十少府》);“昨夜谁为吴会吟,风生万壑振空林”(《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刘禹锡将自己的唱咏直接说成是“吴趋咏”,是其对吴地乐府歌谣自觉接受并主动仿作的确认。其《竹枝词》、《浪淘沙词》、《踏歌词》、《堤上行》、《采菱行》、《杨柳枝词》等都深得南朝江南民歌的韵味,是极其显著的吴声、楚歌的影响。
刘禹锡还用吴声写乐府《三阁辞四首》等,或者是把诗歌写成吴声的民歌味,如其《堤上行三首》等。《堤上行三首》诗云: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
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
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长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
日晚上帘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
是诗大约写于刘禹锡任夔州刺史到和州刺史时,即公元822年(长庆二年)到公元824年(长庆四年),明显可见吴地民歌对他的影响。诗人很善于捕捉生活形象:酒旗、楼台、樯橹、争渡的人群、幽轧的桨声,《桃叶》与《竹枝》的民歌吟唱,画面感极强,生动而逼真地展示了江南水乡的风俗画,有着浓厚的乡土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尤其是诗人兼用音响效果,江边堤上歌声四起,相和相应,而作为江南民歌代表性的《桃叶》与《竹枝》的插入,成为一种具有特殊符号性质的鲜明的地方特色,也足以明证吴歌吴吟对刘禹锡的吸魂慑魄的魔力。刘禹锡不仅将诗情与画意揉在一起,而且把诗当作有声画来描绘。身处巴蜀而有被弃置感的诗人,吴地民歌对其具有抚慰心灵创伤的精神魔力。特别是当他身处异地而听到极其熟悉的南方民歌时,自然而惹动身世之感的“情”与“怨”。“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采菱行》)。《采菱行》原本就是江南民歌,相和歌辞,诗人灵心善感,远在流地,听到南音而情动于衷。“一吟相思曲,惆怅江南春”(《酬令狐相公亲仁郭家花下即事见寄》)。“相思曲”原名《懊侬歌》,属乐府清商曲辞中吴声歌。“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竹枝词九首》其一)。一曲南音,令其驻足而听,心为之怦然,神为之飞越。南音无限感染力,一个“动”字,而异乡北人之神色全出矣。
大历、贞元时期在吴中诗人中已形成一股学习民间杂言令曲的新风,从而直接影响了与吴中文化有深刻渊源的刘禹锡。因为自小熟悉吴声,他对吴吟特别敏感,能从其他地方音乐中辨认出吴声来。《历阳书事七十韵》称和州“本吴风俗剽,兼楚语音伧”,即刘禹锡识辨出和州兼具吴楚两地特征。他在《竹枝词九首并引》中提到:“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著名曲学家任半塘在《唐声诗》中指出:“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九篇,远近传唱。”①任半塘:《唐声诗·总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5页。刘禹锡以“竹枝词”为题,新制其词,别开生面,被东坡誉为“奔轶绝尘,不可追也”②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跋刘梦得竹枝歌》,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57页。。黄庭坚也评论说:“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③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跋刘梦得竹枝歌》,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第657页。翁方纲甚至说刘禹锡“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④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石洲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85页。。
(三)刘禹锡借吴地说事的自觉
香港学者邓中龙说:“唐代的七绝诗,发展到中唐,或者也可以说是发展到刘禹锡手上,七言绝句这个工具,才说得上是开始找到了适合的题材。这题材,如果用最简单的字眼来说明,那就是‘咏史’。”⑤邓中龙:《唐代诗歌演变》,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45页。尚永亮说:“在元和逐臣中以咏史、怀古而独占鳌头的,不是韩愈、白居易,也不是柳宗元,而是‘以气为主’、‘用意深远’的刘禹锡。刘的咏史、怀古之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写得好,意悲境远,感慨无端,调响词练,高华深稳,在中唐诗坛洵为大家。”⑥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0、401页。刘禹锡的咏史作品为“三十七题,四十三首,在主题开掘、深化以及艺术表现上都呈现出独特的风貌”⑦赵望秦、张焕玲:《古代咏史诗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1页。。其中大半是借吴地说事的,重要作品如《金陵五题》(《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江令宅》)《金陵怀古》《台城怀古》《姑苏台》《西塞山怀古》《韩信庙》等。他这些怀古诗,巧用吴地物景,借古鉴今,将地志与咏史完美相结合,从纯粹单一的咏史转变为古迹的凭吊,反映了他对历史兴盛衰败的独特而深刻的体悟,发人深省而震灼古今,其《石头城》甚至被沈德潜评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山围故国”一诗“气象稍殊,亦堪接武”⑧沈德潜:《说诗晬语》,见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43页。前贤。
宝历二年(826)冬,刘禹锡由和州返回洛阳,途经金陵,寻访东吴当年冶铸之地的冶城遗迹,拿金陵说事而成《金陵怀古》:“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瀛奎律髓汇评》中纪昀道:“叠用四地名,妙在安于前四句,如四峰相矗,特有奇气。若安于中二联,即重复碍格。”⑨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0页。“冶城”“征虏亭”“蔡州”“幕府山”是四个有特殊意义的地名,四个著名的可以用来说事的历史陈迹,诗人借此以形象地表达对兴废盛衰的古今变化的感慨,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而示警当世,提出了“兴废由人事”的卓越见解。组诗《金陵五题》,则分别吟咏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和江令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着笔,反复表现“兴亡”这一核心主题。借古喻今,借题发挥,情景事理融为一体。正如吴汝煜、胡振龙所说:“由于作者是一个精通历史的哲匠,他当然会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用历史的线索贯串起来,借助历史的外衣,把自己暂时受挫的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包裹起来。透过诗中,读者仍可触摸到诗人那颗孤愤激烈之心的律动。”⑩王元明主编:《刘禹锡诗文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13页。
写于长庆四年(824)的《西塞山怀古》被誉为“金陵怀古之冠”。此诗颇受历代评家好评,堪称唐人怀古诗中的经典绝唱,“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著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洵是此老一生杰作,自然压倒元、白”①薛雪:《一瓢诗话》,见《清诗话》,第710页。。刘禹锡由夔州刺史调任和州刺史,乘舟东下,途经西塞山,即景抒怀。俞陛云说:“余谓刘诗与崔颢《黄鹤楼》诗异曲同工。崔诗从黄鹤仙人着想,前四句皆言仙人乘鹤事,一气贯注。刘诗从西塞山铁锁横江着想,前四句皆言王濬平吴事,亦一气贯注。非但切定本题,且七律能四句专咏一事,而劲气直达者,在盛唐时,沈佺期《龙池篇》、李太白《鹦鹉篇》外,罕有能手。”②俞陛云:《诗境浅说》,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8、69页。前四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有三句写到金陵,铁锁与石头,更是诗人借以说事的吴地物象、历史遗迹。诗的前四句,交代了这场战争的指挥者、进军路线、作战方式、突破江防的经过及吴主出降的情形,在怀古的内容中寓有深意:一个政权的巩固,靠的不是地形的险要,而是人心;失去人心,任何其他防御工事都形同虚设。为后四句的议论张目设势,笔调嘲弄,锋芒直指。“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后四句描写与议论结合,亦事亦议,典事物象与议论抒发并行。山形依旧,寒流常枕,然往日的军事堡垒,却已荒芜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英雄霸业,荡然无存。格意奇高,骨气端翔。落句情语,尤堪叫绝。诗人婉言规劝,情感沉郁感伤,既精警动人又含蕴无穷的美学效果。
刘禹锡的金陵怀古是继李太白之后的又一个高潮,而将咏史诗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也奠定了刘禹锡的诗坛地位。他将实地、古迹、现实与此在情感杂揉融合,触景生情,抚今思古,借史咏怀。这种以生命短暂、天地永恒、历史无情为主题的怀古,把个人命运的感喟转变为沧桑之叹,以历史之感代替一己之忧,使怀古诗的诗美与哲理和谐一体,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三、吴地对刘禹锡诗美取向形成的意义
瞿蜕园先生认为,刘禹锡的诗歌“早年纵迹足以决定后来之成就也”③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56页。。我们以为,此论除了说其深受江南自然环境的影响,同时是说其此时期幸得皎然、灵澈等人的点拨。刘禹锡的“早年纵迹”也决定了他日后诗歌创作的美学取向。而刘禹锡的诗美取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其俊爽诗风;一是其取境的诗论。
刘勰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④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94、695页。地域在文学风格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罗宗强先生说:“不同的景色,事实上是一次次地在记忆里印上画面,长期的积淀,自然画面的美的类型便在记忆里形成了一种信息定向。这种信息定向在审美过程中以经验的形式出现,成为审美判断的基础。换句话说,左右着审美趣味。”⑤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8页。可见,自然环境对诗人的审美取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吴地山清水秀,风光明丽,影响到艺术上,表现为秀美细腻,与北方的粗犷豪健、中原的淳朴敦厚,殊为不同。”⑥李学勤著,张耀南编:《李学勤讲中国文化》,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刘禹锡在《刘氏集略说》中也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⑦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1180页。吴地山水,以及六朝对吴地山水描写的美学形态以及诗美趣尚,对刘禹锡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他诗歌中蕴含六朝美学元素的风格特征。于頔《吴兴昼上人集序》曾评价刘禹锡早年的诗学导师皎然的诗作“极于缘情绮靡,故词多芳泽”⑧于頔:《吴兴昼上人集序》,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附录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70页。,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皎然既讲究风雅又追求绮丽的美学主张,代表了中唐前期的诗观。皎然公开为齐梁诗歌辩护,反驳陈子昂的“道弊五百年”论,表现出肯定齐梁绮丽诗风的态度,他指出齐梁诗“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①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第273页。。其《诗式》中提出了“四不”、“四深”、“二要”的风雅观,即“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蹶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 ”②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第17、18、20 页。。皎然所提出的这些风骨兴象同兼的创作原则,是对盛唐诗歌的总结,是按照盛唐诗歌总结出来的诗学理论。
真正的盛唐诗歌,是非常重视对六朝精华的汲取,即便是口口声声讨伐齐梁绮靡的李白,其诗中也表现出积极汲取齐梁营养的种种迹象。而自小长成于吴地的刘禹锡,受江南文化的浸渍而趋向于趣尚清俊绮丽,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自建安距永明已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朔风’、‘零雨’高视天下,‘蝉噪’、‘鸟鸣’蔚在史策。国朝因之,粲然复兴。由篇章以跻贵仕者,相踵而起。兵兴已还,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寖息。乐府协律,不能足新词以度曲,夜讽之职,寂寥无纪。”③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918页。刘禹锡以安史之乱前后作比较,乱前“因之”,而乱后“不暇”;“国朝因之,粲然复兴”,而“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寖息”。因此,他对董侹能够“因故沿浊,协为新声”而特别欣赏。这里“因之”的“之”,即指代建安以来的诗歌传统,应该是包括齐梁诗风的。事实上,古人早就认为刘禹锡的诗风酷似六朝。譬如方回称刘禹锡的《柳絮》“流丽可喜”(《瀛奎律髓》卷27);谢榛说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其一)“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二句“措辞流丽,酷似六朝”(《四溟诗话》卷2);钟惺说他自创新题乐府《淮阴行五首》“极似六朝清商曲,的是音响质直”(《唐诗归》卷28);贺裳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刘禹锡“五言古诗,多学南北朝”(《载酒园诗话又编》);陆艺香说“梦得诗如《棼丝瀑》、《秋萤引》、《生公讲堂》、乐府绝句《杜司空席上》诸作,宛有六朝风致”(《问花楼诗话》)等。刘禹锡诗清俊明丽,明眼者见出其学齐梁的迹象。王夫之说刘禹锡的七绝“宏放出于天然”④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瞿蜕园则认为此论“亦实足以概其全体”⑤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附录四,第1788页。。意思是,刘禹锡的宏放,不仅仅是他的七绝,而是其诗的全部,是其诗歌的主流风格。天然中而见宏放,是吴地赋予刘禹锡的特有精神气质与诗歌美色。“天然”是其诗之本色,是其诗的清新一面,也是其描摹景物的清丽可人的长处与特征;而“宏放”,则是一种豪健高扬的人文力量,是一种“雄浑老苍,沉着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⑥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的艺术特质,源自于诗人坚毅高洁而饶有豪猛之气的人格内蕴,源自于诗人傲视忧患而理性沉思的批判精神,源自于诗人迎接苦难、超越凡俗的乐观精神。因此,即便是《竹枝词》民歌吟唱,也有“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的怨恚。一方面是俊爽清新、绮丽婉转,一方面是雄浑老苍、骨力豪健,二者合兼,合气骨、情致为一体,熔清丽、含蕴为一炉,形成彼此相关的通融,才是刘禹锡诗歌的真正面目。因而,“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真才情之最豪者”⑦胡震亨:《唐音癸签》卷7,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9、60页。,其“发为歌咏,形之诗什,感慨沉郁,跌荡诙诡,上追杜陵,近媲昌陵,可惊可喜,可歌可泣,承风气之已开,而健笔有凌云意焉。”⑧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319页。这种评论亦非过实之词,他的不少作品,写得昂扬高举,格调宏放,风情俊爽,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6《跋刘梦得〈三阁辞〉》云:“大概刘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它文耳。”①黄庭坚:《跋刘梦得三阁辞》,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第658页。吴乔《围炉诗话》卷3说:“梦得佳诗,多在朗、连、夔、和时。”②吴乔:《围炉诗话》,郭绍虞主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65页。乐府小章优于大篇,是事实;佳作多成于流地,也是事实。刘禹锡在贬谪地的诗作,新鲜活泼,清新优美,真实地反映民俗,倾注了他浓烈的吴地恋情,而这种美学趣尚也正反映了吴地山水和文学传统对他的深刻影响。
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是中唐乃至唐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篇诗学文献,刘禹锡在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境生于象外”的诗学命题。文中有两段话很精彩: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冥,达于诗者能之。
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
刘禹锡论诗取境、以有境为高的诗学思想,明显地深受皎然诗学思想的影响,是皎然诗学思想的延续。刘禹锡深得诗人、诗歌理论家皎然的真传,深刻顿悟到诗歌言与意、词与旨的关系,继承和发展了皎然的取境说。皎然最大的贡献即是诗歌的取境说,其《诗式》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③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第69页。他在《答俞校书冬夜》中亦曰:“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④彭定求等修纂:《全唐诗》卷八百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9173页。皎然非常重视这种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认为创作中最重要的是诗人的主观心境与审美观念。刘禹锡在此“纪”以及其他文字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理念,与皎然《诗式》中的“采奇于象外”、“情在言外”、“旨冥句中”以及“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等观点一脉相承,是其诗从皎然的结果。刘禹锡的《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⑤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144页。中还提出“因定而得境”论,诗人云:“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刘禹锡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到“境”字,他的意境说,拓展了中国传统诗歌审美的广度与深度,也成为皎然与司空图诗歌理论的中间桥梁。司空图则对诗歌审美特质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理论升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与王驾评诗书》);“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⑥郭绍虞:《诗品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页。等等,以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独特方式,对文学艺术的特殊审美规律的理论概括,标志着中国古代“意境”说的确立和理论的成熟。而在“意境”说的形成过程中,刘禹锡成为从王昌龄到司空图的重要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