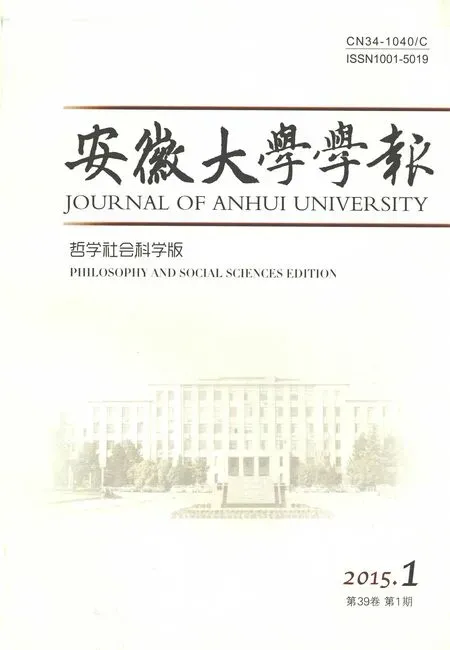论“Knowing How”的过程性
伍 龙
论“Knowing How”的过程性
伍龙
摘要:“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之辨是现代西方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对“knowing how”认识论地位的不同界定,由此可见,对“knowing how”做较为全面的理解十分必要和重要。“knowing how”属于“知”的领域,与活动/行动、智力、能力三个要素密切相关。以“神枪手”为例,无论我们将一个行为视为一系列外在行动组合的过程,还是视为内在思维对信息不断反馈、加工、转化的过程,都会发现“knowing how”的“过程性”彰显着其与活动/行动、智力、能力三要素的密切关系。“knowing how”过程性的提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蕴含的丰富内容,也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三要素之间,以及三要素与“knowing how”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knowing how;过程性;活动/行动;智力;能力;负反馈;认识论
一、问题的缘起
在当代认识论问题的前沿研究中,有关“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问题的争论,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认识论方面的研究当属一个重要面向。
1946年,赖尔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发表了题为“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的著名论文,到1949年,他出版的《心的概念》(TheConceptofMind)一书,就其关于“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的观点做了系统的阐发,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本来,这个问题已经慢慢淡出认识论问题研究的前沿论域,但在2001年,随着斯坦利和威廉姆森(Jason Stanley and Timothy Williamson)的“Knowing How”论文的发表,这个问题的讨论又被拉回到认识论热议话题的行列中来。直到2011年,Jason Stanley经过十年的思考与积淀,特别撰写了专著KnowHow,来系统讨论这一问题和阐发自己的观点。2012年,John Bengson和Marc A.Moffett继续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出版了KnowingHow—EssaysonKnowledge,Mind,andAction一书,试图对之前的讨论进行梳理和综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可见,这一问题的争论、研究从开始到现在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令人好奇的是,这些哲学家到底在争论什么?他们关于“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的看法,到底有什么不同?根本分歧点在哪里?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对于“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这两个命题,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并以这两种观点为基础,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即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和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理智主义者认为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之间没有种类差异,knowing how归根到底是knowing that;反理智主义者则反对将knowing how归结为knowing that,主张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之间有种类的差异。”*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0页。两派的分歧并不出在对于“knowing that”的理解上,而在于“如何理解knowing how的认识论地位”*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第70页。。
在2011年Jason Stanley出版的KnowHow一书的“序言”中,Stanley虽对knowing a fact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之前的研究者对于这一命题的认识不够全面,从而导致反理智主义的立场,但一方面Stanley的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援引knowing how进入knowing that,即“knowing how to do something is the same as knowing a fact”*Jason Stanley,Know Ho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另一方面,他对赖尔的反驳其实并没有成立,这主要是因为他对赖尔所理解和界定的“knowing how”的与行动相关的内容没有了解清楚。更何况,他的书就是以“know how”命名的,可见他还是以knowing how的讨论为重心。另外,在郁振华教授最近出版的新书《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中,郁教授反复强调一些理智主义者对于赖尔的反驳之所以没有力度,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地对待赖尔的思想,赖尔关于knowing how的一些重要洞见,在他们的讨论中都失落了”*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第70页。。换言之,一些理智主义者所说的knowing how并不是赖尔所认为的knowing how,如果由此出发而对赖尔进行反驳,会显得没有力度。他们根本不是针对一个概念的同一个意义(包括它的内涵和外延)展开讨论,这会让人觉得,彼此都各说各话,显得很没有说服力*参见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第69~102页。。由此看来,在这场争论中,对于“knowing how”含义的界定与理解显得非常重要。笔者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期望对赖尔的“knowing how”做一探讨,并提出自己的理解。
二、关于“knowing how”的两点说明
(一)容易产生的误解
我们在刚开始接触“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的相关英文文献,或者阅读中文翻译的文献时,往往会对理智主义的主张有所青睐,这是因为对于英文文献本身,或者翻译过来的中文有望文生义的问题。就这两个命题本身来看,“knowing how”是指“knowing how to do something”,而“knowing that”是指“knowing that something is the case”。仅从“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上述两个英文表述出发,我们往往会将“knowing that”直接翻译成“知道什么”*这种翻译出自刘建荣,参见赖尔《心的概念》,刘建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或“知道那个事实”*这种翻译出自徐大建,参见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如果从这两个翻译出发,而将“knowing how”直接理解为“知道怎样做”*这里采用的是徐大建的翻译,对于“knowing how”本身的理解,各学派存在着分歧,但是对于“knowing how”的中文翻译,却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就容易让我们对于理智主义更为赞同,或者说,在这种翻译的作用下,我们会先入为主产生一种理智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们会自然地认为,“什么”涵盖了很多的内容,“知道怎样做”当然是“知道什么”的一种。而后一种翻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理智主义所利用,“怎样做”难道不可以说是一个“事实”吗?我知道怎么骑自行车,而“怎样骑自行车”本身不可以被看成是“事实”吗?如果可以,那么,“知道怎样做”当然可以归入“知道那个事实”中。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解读知道,这两组命题并不仅仅局限在字面的中文翻译里,但是,这种翻译被初学者阅读和记忆后,会对阅读者的“前见”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从而在开始的时候,对理智主义产生同情,对反理智主义的主张有所质疑。
(二)“knowing how”是一种与行动相关的知
在赖尔看来,“knowing how”与行动相关。其实,不仅就赖尔的观点来看,单从“knowing how”自身来看,其英文的原始表达“knowing how to do something”就和“do”相关联。此外,从中文的翻译来看,“知道怎样做”的“做”也和行动相关。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虽然“knowing how”需要用活动/行动来表达,但“knowing how”说到底是“体现了智力的能力之知”*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第71页。。这就是说,它本质上是和“knowing that”一样同属于“知”的。所以,一方面,如果我们主张,“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有种类的差异,那么,这个种类的差异是它们作为两种“知”存在的种类差异。另一方面,这两种“知”,其存在种类差异的原因,可以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即“knowing that”是和“知”本身联系更为紧密的“知”,而“knowing how”则更多地与“行”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已经暗示了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已具备了将这种知识转化为现实的能力。这从“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被译成“能力之知”和“命题性知识”*这是郁振华教授的一种翻译。参见《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第97~98页。,也可以窥见一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容易将“knowing how”和“行”直接等同起来。应该看到,“knowing how”与活动/行动密切相关,但如果将其等同于“行”,则是一种误读。因为,上述关联是在其作为一种“知”的大前提下展开的。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可能与赖尔在《心的概念》一书中一再举实际行动的例子来说明“knowing how”所具有的与行动相联系的内涵有关。这一点也可以从Jason Stanley的KnowHow一书的第一章“Ryle on Knowing How”中看出。Stanley强调,赖尔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笛卡尔主义者,因为他在文章的很多地方使用笛卡尔主义的一些概念,但实际上,他是在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立场上使用这些概念的,从而表现出某种行为主义的倾向。Stanley进而认为赖尔是一个行为主义者(behaviorist)*Jason Stanley,Know How,pp.2-11.。这在向我们提示造成上面误读的原因的同时,也表明了赖尔的“knowing how”和行动、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这个“行为主义者”的帽子戴得是否正确,还可以再商榷。
总之,一方面,我们应该明确“knowing how”是一种“知”;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knowing how”是与活动/行动相联系的。
三、“knowing how”的过程性
(一)赖尔的“knowing how”包含着三个面向
赖尔的“knowing how”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活动/行动、智力和能力是完整把握赖尔的knowing how的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第71页。。
首先,“knowing how”和“活动/行动”有关。前面已经说到,“knowing how”可以表达为“knowing how to do something”,即“知道怎么做”。一个关于“知道怎么做”的知识当然是和“做”这个“活动/行动”有关。赖尔说:“通过实践我们学会了怎样做,批评和距离的确使我们受到教育,而理论上的教导却常常无济于事。”可见,“怎样做”和“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获得“怎样做”的知识,需要通过“实践”“学会”。同时,赖尔又举了孩子下棋的例子,他说,“他所具有的关于怎样做的知识的运用,主要在于他走出或予以承认的棋步,在于他不走的或予以否认的棋步”*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第38页、39页。。这说明,关于“知道怎样做”的知识不仅可能源于实践,而且还应运用到实践中,转化为实际的行为。
其次,“knowing how”总是体现着智力,并同时与能力紧密联系。上一条已经说过,“knowing how”和“活动/行动”有关系。在一个“知道怎么做”的知识变成我真正去做的行为的过程中,当然需要知识的拥有者和行为的实践者具备智力。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智力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吸纳知识的能力,它还是一种关乎行动的能力,即当一个人具备了“知道怎么做”的知识的时候,他就应该具备了一种能够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或者说,这一类的知识本身包含着人能够实践这一操作性知识的能力。赖尔说:“具有智力不仅仅在于满足准则,而且还在于运用准则;在于调节一个人的行为,而不仅仅在于被调节得很好。”又说:“理解是知道怎样做的一部分。为了理解一种特定的显示了智力的行为所需的知识乃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做出那种行为。”所以,当一个人知道了怎样做,就应该具备了知道怎样将这样的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智力的能力。除此之外,应该看到的是,这种智力还体现在“knowing how”的多轨性上。赖尔就说:“鉴赏一种行为的能力与实施这种行为的能力是同一类型的能力,这一点说明了前面所论证的一个论点:智能并不是一些单轨的素质,而是一些容有形形色色的或多或少不相似的运用的素质。”这话的意思是说,当运用智力将我们所知道的“知道怎么做”的知识付诸实践时,我们可能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而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之所以能够用“知道怎么做”的知识去应对,就是因为这类知识即“knowing how”本身具有多轨性,这一“多轨性”体现着“knowing how”所具有的智力的维度。比如,以赖尔所举的下棋为例,他认为一个普通的棋手也许能够通过研究,完全理解一个下棋冠军在某几盘棋赛中所使用的走法,但他永远也不能完全预料到这个冠军在下一盘棋赛中会怎样走棋,他永远也不会像冠军走棋走得那么敏捷或有把握*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第23页、53页、54页、58~59页。。进一步说,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普通的棋手已经完全掌握了下棋的规则和方法,或一个冠军非常慷慨地把所有的下棋技巧都告诉了这位棋手,但可以预料的是,他依然无法像冠军一样自如地下棋而成为冠军,因为,“知道怎样做”本身不应该是单轨的,而应该是多轨的。它之所以能够具有向实践转化的可能性,就在于其所具有的多轨性。这个多轨性当然体现着智力,而这一智力亦是一种能力。
(二)以“神枪手”为例说明“knowing how”的过程性
1.从神枪手外在的一系列行为过程来看
在赖尔所举的众多例子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神枪手”的例子:一个人如果有一次打中了靶心,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他是出于侥幸还是由于好枪法。赖尔对此判断的方法大体表现为一种行为主义。他认为,“假如他有这种技能,那么他能在此击中靶心或靠近靶心的地方,即便风刮大了,射程改变了,目标移动了。或者,假如他的第二枪没有击中靶,他的第三枪、第四枪和第五枪所击中的地方很可能会逐渐地越来越接近靶心”*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第43页。。简要言之,就是让这个人继续射击,通过多次的射击行为来判定他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神枪手,还是只是出于侥幸。但是,理智主义基本是付之于内心的考察,他们认为任何一个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智力的、理智的思考,但是,这个内在的思考行为却是“隐晦” “幽暗”,无法被他人体会、了解的,由此进一步追问下去就可能导致赖尔质疑理智主义的有关“无穷倒退”的问题*可参见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第82~86页。。
我们在这里并不准备详加讨论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对于这个例子的解决方案,哪一个更具有说服力。我们想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如果只是一次性的行为,没有后面再次射击的可能,如何能够判断这个人射中靶心是出于侥幸还是由于好枪法。赖尔提出的方法是:“我们应当考虑他过去的记录、他的解释或辩解、他给予同伴的劝告,以及大量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线索。”在这个所谓的“大量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线索”里,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另一个判断的方法:通过他活动的整个过程来进行判断,通过过程中各个不同阶段的射击行动,以及其他细节,如神态、射击完成之后的反应等,综合考察作出判断。赖尔认为射击“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标志,可以表示出一个人知道怎样射击,但适度地把一些不同的行为配集在一起,一般来说就可以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他是否知道怎样射击。只有在此时才能判断,他击中了靶心是出于侥幸,还是因为他是一个足以成功的射手”*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第43页。。当然,赖尔提供的综合起来看的解决方案是包括了对此后的射击行为的考察的,而我这里所说的综合考察还只是以单个射击行为的整个过程为对象作出的判断。
那么,这里所谓的单个射击行为的整个过程,是否与“knowing how”有关系?换言之,这些在行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阶段行为和其他细节是否都包括在“knowing how”中?这里需要进行分梳和澄清。首先,射击前的端起枪、瞄准靶心、射击,以及射击完之后,对射击手枪的处理、下一次射击的准备等,这些具体行为背后所蕴含的知识,都可以归结到“knowing how”里面去。换言之,这些都应该是赖尔说的“knowing how”的内涵和外延所应包括的内容。但是,除了这些具体的射击行动之外,其他的细节,如对射击结果的反应,表现出的神态、情绪等则应被理解为一种广义的行为,同样也应纳入赖尔所说的“knowing how”中。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关于“怎样射击”的知识,同时也应该包括怎样控制和表达自己在射击完了之后的情绪和神态,即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情绪与心态去对待射击的结果。如果是一个神枪手,可能已经不只一次地射中靶心,所以,再次射中时并不会反应很大,情绪激动。反之,如果是侥幸射中的,就可能会对此结果表现出意外、惊讶、非常兴奋等情绪。这些外在的表现,也可以被归结到广义的“行”中,而这个“行”背后的与之相联系的“怎样做”的知识,自然也是属于“knowing how”的内容。
不论射击活动是单个的还是多个的,单从“射击”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考察,我们同样看到其体现出全面理解和把握赖尔的“knowing how”所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即活动/行动、智力和能力。一个人所具备的“怎样射击”的知识要运用于实际的射击行动中,“假如他具有这种技能,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他是否运用了这个技能的问题,他射击时是否小心,是否控制了自己,是否注意到了各种条件并且想到了他所受到的指导的问题”*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第43页。。同时,这个行为的过程当然也体现着射击者的智力和能力。当他面对不同的情形,如“风刮大了”、“射程改变了”、“目标移动了”等,一样可以射中靶心。这是射击者本身所具有的将“怎样射击”的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射击行为进而射中靶心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其面对不同情形一样射中靶心的智力还同时彰显着上面提到的多轨性。而这也正是文章所提出的“knowing how”所具有的过程性。所谓“过程性”是指“knowing how”在一个行为的整个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多个面向,即与活动/行动、智力与能力相互关联的内容。一方面,在一个行为的从头到尾的过程中上述三个要素均得到了彰显;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对一个行为做过程性的考察时,理解“knowing how”与上述三个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
2.从神枪手内在思维的负反馈过程来看
当我们进一步思考上述问题时,不难发现另一重要问题,即我们是如何将所具有的“怎样射击”的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射中靶心的行为的?这个外在的行为是通过怎样的内在过程得以实现的?这个内在过程是否也彰显着“knowing how”的过程性呢?
如果说前面的讨论是从“神枪手”举枪射击这一外部行为的考察来说明“knowing how”的过程性的话,那么,这里从“神枪手”自身的角度来理解“knowing how”的过程性则更多的是从内部着眼,它会涉及射击者将自身能力转化为具体行为的过程。对此,“控制论”中的“负反馈”理论颇有启发意义。
“控制论”是上世纪40年代由美国哲学家维纳提出,它是一门研究动态系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如何保持平衡或稳定状态的科学,其中“反馈原则是控制论的最重要的和通用的原则”,可以说“不使用反馈原则,控制就不能实现”*茹科夫:《控制论的哲学原理》,徐世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95页。。简单来说,“反馈是控制系统的一种方法,即将系统的以往操作结果再送入系统之中”*维纳:《维纳著作选》,钟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48页。。这个被送入系统之中的“以往的操作结果”往往展现为一种“信息”。当我们展开一项活动时,通常会预设一定的目标,在行为的实际展开和目标达成之间会形成一个“目标差”,每一次“以往的操作结果”即是“反馈到控制中心的信息”*维纳:《控制论》,郝季仁译,北京:科技出版社,1985年,第99页。,这个“反馈”来的信息能帮助我们不断缩小目标差,也可能促使我们不断地增大目标差,这两种情况分别称之为“负反馈”和“正反馈”。换言之,“负反馈调节的本质在于设计了一个目标差不断减少的过程,通过系统不断把自己控制后果与目标比较,使得目标差在一次一次控制中慢慢减少,最后达到控制的目的”。由此不难看到,“负反馈”必须包括两个环节:“(1)系统一旦出现目标差,便自动出现某种减少目标差的反应。(2)减少目标差的调节要一次一次地发挥作用,使得对目标的逼近能积累起来。”*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从这一理论出发反观“神枪手”的例子则不难看到,“神枪手”在射击的过程中一定要涉及“信息”“反馈”的过程。就单个射击行为来看,一开始他举枪瞄靶,可能并没有马上射击,而是不断地重复举起放下的行为,这就是“减少目标差的调节”在“一次一次发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以往的操作结果”通过“信息”的形式反馈到“控制中心”,从而完成不断“减少目标差的反应”,最终命中靶心。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在一次次的“举起放下”中,个体的某种有限的控制能力得以积累起来,从而扩大了自身对于行动的控制能力*参见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第27~30页。。第二,内在的信息反馈与外在的行为调节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不难看到,这里形成了一种“具有反抗被控制的量偏离控制指标的趋势”*维纳:《控制论》,第99页。,也就是说这一“负反馈”的情况存在某种稳定性,它“保持被调节客体的某些参数不变”*茹科夫:《控制论的哲学原理》,第98页。,从而形成了一定的趋向和态势。相反,当我们考察侥幸射中靶心的“伪神枪手”时,则会发现他们的这种“负反馈”一方面没有形成稳定的趋势,另一方面和“正反馈”夹杂在一起,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前者的原因。
所谓“正反馈”与“负反馈”相反,即通过信息的反馈不断增大目标差。“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即是一典型例证*参见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第32页。。“伪神枪手”一方面可能表现出不稳定的“负反馈”,即通过侥幸完成“负反馈”的过程,造成自己偶然打中靶心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内在思维上可能经历一个“负反馈”和“正反馈”相互纠缠的过程。因为无法稳定地控制“目标差”使其不断减少,在反馈和调节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目标差”不断增大,即“正反馈”对其行为造成的影响,虽然这样的影响最终没有表现在结果上,但从命中靶心之后难以抑制的喜悦和兴奋之情中我们并不难看到这一影响。此外,“为了能对外界产生有效的动作,重要的不仅是我们必须具有良好的效应器,而且必须把效应器的动作情况恰当地回报给中枢神经系统,而这些报告的内容必须恰当地和其他来自感官的信息组合起来,以便对效应器产生一个恰当的调节输出”*维纳:《控制论》,第98页。。“伪神枪手”之所以是“伪”的,正在于他没能自觉而恰当地将“效应器的动作情况”反馈给“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影响了结果产生的稳定性。
不难看到,“负反馈的调节实际上跟目的性这个概念有关”*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第30页。。在“神枪手”这个例子中,目的即是“射中靶心”。就一次射击行为来看,真正的神枪手和侥幸的射击者在目的的达成上都完成得很好,但立足于“负反馈”的过程时,则不难看到两者在内在信息的加工、生成以及转化为具体行为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这里自然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射击者所展现的这种内在“负反馈”的过程与“knowing how”是否有关,它作为一个过程是否与“knowing how”的过程性存在关联。
如前所述,“knowing how”是一种关涉行动的“知”,它主要涉及三个面向,即“活动/行动、智力和能力”。神枪手在射击过程中内部产生的“负反馈”的过程是一种思维的活动,它主要体现为人的大脑将“以前操作的结果”以“信息”的形式反馈到“控制中心”。在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之后,人将内在的反馈结果付诸外在的具体行为,不断缩小“目标差”而最终射中靶心。这个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自然体现出人的一种认知能力,具体表现为人对于信息处理和行为操作的智力。如前所述,这种内在的思维能力和外在的具体行为不可分割,其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它虽然作为一种“知”,但与外在的行为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一种“knowing how”,即知道如何通过信息的反馈达成射中靶心的“知”。从“负反馈”自身的理论内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它展现为一个“过程”,信息的传递、反复地修正、不断地接近目标都体现出这一点。在这过程中,“knowing how”所具备的三个面向是相互联结、共同发挥作用的。简言之,“负反馈”在神枪手身上的达成需要施动者本身具备相应的能力,将信息传递的活动一次次地重复,最终完成如何射中靶心的“知”向具体射中靶心的“行”的转化*如果我们跳出单个的射击行为,将射击结果的判断还原到赖尔所主张的一种“行为主义”的考察,就更能够体现出“负反馈”理论的优势。如“负反馈”机制的必要环节之一,即“减少目标差的调节要一次一次地发挥作用,使得对目标的逼近能积累起来”。如果将“一次一次地发挥作用”理解为多次的射击行为促使射击者在内部产生一个不断接近目标,缩小目标差的过程,则更容易理解。此外,“控制论指出,当人的一次控制能力不能达到目的,可以用负反馈调节放大控制能力”。这样的“调节放大”放在神枪手多次射击,进而不断逼近靶心的行为上,可能更生动、形象并易于把握。当然,这里并不是否认单个射击行为不能体现“负反馈”的理论,而是说相对而言,在理解上可能需要费些时间。此外,因为本文将射击的行动限定在单个射击行为上,不采取赖尔“行为主义”的考察方式,故而对于多个射击动作和负反馈理论的关系并没有做过多的讨论。。
(三)“knowing how”过程性理论的意义
首先,“knowing how”的过程性有助于理解“knowing how”的丰富性。如前所述,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争论的关节点主要可以归结为对“knowing how”的理解与界定的不同。两派对于“knowing how”认识论地位的不同理解使得他们各自的主张截然不同。而理智主义对反理智主义所做的回应与反驳基本缺乏力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赖尔以来的反理智主义者关于“knowing how”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没有做充分的了解和细致的考察。换言之,理智主义的反驳所涉及的关键概念“knowing how”根本不是反理智主义所说的“knowing how”。而本文所提及的“knowing how”的过程性,试图将一个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加以考察(无论这一整体过程是表现为一系列的外在行动,还是展现为不断传递给控制中心的内在信息),从而使得“knowing how”与活动/行动、智力和能力三个要素的关联得以凸显,彰显出“knowing how”自身的丰富性,这或许会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而深入地理解“knowing how”。而“knowing how”的这种丰富性实质上是反理智主义得以立足并具有说服力的基础。
其次,“knowing how”的过程性在突出了其与活动/行动、智力与能力关联的同时,还凸显了其作为一种类型的“知”,仍属于“知”的领域的本性。一个行为在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所应具备的过程性的“knowing how”,是一个行动得以顺利进行的能力之知。如一个射击行为,狭义地看,是指射击行为的整个过程,广义地看,则包括射击所涉及的外在情绪的控制与神情的表达,内在信息的反馈、加工和处理等。前面曾提到,我们容易在阅读赖尔的《心的概念》一书时,将“knowing how”等同于“行”,而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则比较容易理解和把握,“knowing how”虽与“行”相联系,但仍属于“知”的领域这一理论事实。
第三,“knowing how”的过程性展现了活动/行动、智力与能力三要素之间以及三要素与“knowing how”之间的相关性。当我们将一个行为视为一个整体过程来加以理解的时候,会发现与“knowing how”相关联的三个要素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并在一个行为中同时体现的。具体来说,一个行为的主体只有具备了将“knowing how”的知识通过内部思维的加工、反馈等环节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才能说真正知道“knowing how”,否则“knowing how”与活动/行动的关联,只能停留在理论的辨析层面,而无法在实际的行为中得到体现。而这种能力的具备,离不开主体自身所具备的智力,这个智力又是与“knowing how”相联系的。当面对具体情况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能够运用“knowing how”的知识加以应对,是因为“knowing how”具有多轨性,而这一“多轨性”实质上是与“knowing how”相联系的智力的体现。立足于“knowing how”,我们看到运用智力展现着一种能力,而这一能力的运用,则保障了实际活动/行动的实现。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这三个要素之间不但是彼此联系的,而且“knowing how”与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亦是不可分割的,“knowing how”所蕴含的一种智力,体现着其作为一种能力而存在,这一能力是“knowing how”与活动/行动产生实际关联的保障。
“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的问题可能仍将成为认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面向继续讨论下去。诚然,就问题本身来看,它可能显得过于“专业化”,但我们应看到,其关联的不仅仅是纯哲学的分析与思辨,还联系着其他一些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如认识与实践、人与知识、人的认知能力,以及认识本身的结构等问题。这些将是人类追寻智慧的过程中,永恒关注的问题,而它们也都与上述单个的、看似专业化的哲学问题的思辨与展开密切相关。
WU Long, Ph. D. candidate, Si-M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责任编校:余沉
A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Knowing How”
WU Long
Abstract:Differentiating “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modern western epistemology. The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 between intellectualism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lies in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the status of “knowing how” in epistemology. It seems that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knowing how” is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Knowing how” belongs to the domain of “knowledg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ree elements, namely, action or activity, intelligence and ability. If an action is considered as a combination of external activities or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feedback, processing and transformation by the mind on information, as in the case of “marksman”, the “process” of “knowing how”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ction/activity, intelligence and ability. The process of “knowing how” could enabl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s rich connot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hree elements and how they are connected with “knowing how”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Key words:knowing how; process; action/activity; intelligence; ability; negative feedback
作者简介:伍龙,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项目(xrzz2014001)
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1-0026-08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