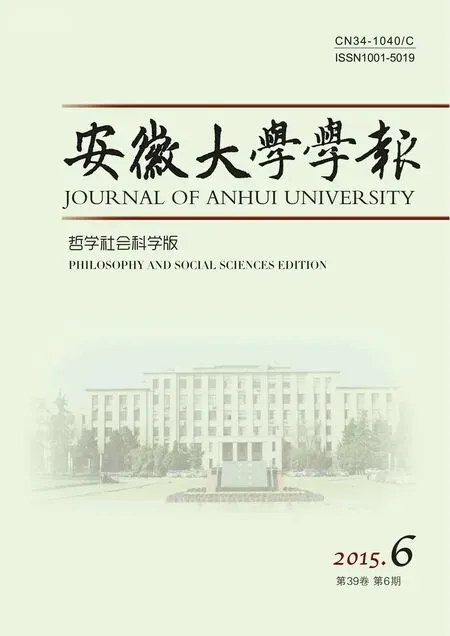洛维特对历史进步观念的批判
刘小枫
洛维特对历史进步观念的批判
刘小枫
历史进步观念诞生于17世纪的西方“新文化”运动,并非西方自古就有。洛维特的《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通过探究历史进步观念的基督教神学起源,提出了古希腊的自然循环观与基督教历史观的差异问题: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异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是两种不同的“西方文化”。又由于历史进步观念属于现代启蒙之后的西方文化观念,因此洛维特认为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的西方文化。洛维特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认识西方文明,尤其理解西方文明的深层矛盾,具有决定性意义。本文通过考察洛维特如何对历史进步信仰展开现象学式的哲学批判,力图揭示深受历史进步观念支配的中国学界所面临的内在困难。
进步观念;历史哲学;基督教神义论;自然;洛维特
历史进步论是18世纪欧洲启蒙哲学营构的一种哲学观念,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在我国学界也早就是常识性观念。尽管如此,历史进步论在思想史上的是非对错,迄今没有定论。例如,20世纪著名哲学家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在其传世之作《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①中就提出过让人难以忘怀的论点:启蒙哲学通过提供关于人类正在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观给人的生存带来无限的信心和憧憬,实际上最终把人的生存拽入了无尽的深渊。
一
1756年,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发表大著《论诸民族的道德和精神,以及论历史形成的法则》,史称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世界史”,首次以史书形式展露进步论信仰。1795年,法国启蒙志士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在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仓促完成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出版,史称历史进步论信仰的纲领性文献。恩格斯说过,孔多塞是“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之一。的确,他的《纲要》一书虽然谈不上什么思想深度和理论价值,但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通过通俗而且优美的语言把“进步”观念灌输给大众,成功打造了进步论意识形态,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史称制造“大众消费教条”的开山之作。按照孔多塞的启蒙构想,人类进步的奥秘是由极少数掌握新科学的智识人发现的,但要实现人类进步,必须唤起大众参与。这意味着,必须填平少数启蒙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毕竟,仅有少数人把基于数学—物理学的科学理性视为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还不够,必须让所有人都具有这样的意识。为实现这一目的,孔多塞号召从事启蒙教育的知识人要善于运用“博识、善思、聪
明、文才”等一切可供启蒙使用的武器①参见沃格林《危机和人的启示》,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8~150页。。孔多塞的《纲要》所宣传的进步信仰其实与如今的“普世价值论”没有什么不同,只要读过《纲要》就会发现,我们的头脑的确还处在孔多塞的掌握之中,可见他的启蒙方略非常成功。
然而,如洛维特所说:“孔多塞对人在未来将达致完善的预言不是科学推论和证明的结果,而是信仰和希望的梦想。”(《世界历史》,第111页)要让这种信仰和希望成为改变现世的精神力量,还需要把这种梦想打造成宏大理论——在法国完成这一哲学使命的主要是孔德②参见沃格林《危机和人的启示》,第151~236页。,在德国则诞生好几位历史哲学的大思想家。虽然德意志人的哲学思想比意大利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晚出,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以及德意志民族自身长期分散的政治状况,历史哲学在德意志思想中的发展更为有声有色,或者说更为观念体系化:赫尔德的人类学史观、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史观到马克思的唯物论哲学史观,构成了现代德意志哲学的基本论述传统③参见布尔(M.Buhr)《理性的历史: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历史的思考》,王步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尽管我国学术思想界在近一个世纪里已经把这种现代西方的历史哲学变为我们自己的哲学,不懈思考的学者仍然心里犯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的中译者就在译者“序言”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纪之后的人,今天读到两个世纪以前这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似乎对于他们真诚的信仰和乐观的精神,只能够是艳羡。……相形之下,两个世纪以后的我们在某些方面,虽然确实取得了他们所无法比拟的进步,但是20世纪却也见证了空前的愚昧、野蛮和残暴。能够说人类精神是在不断进步的吗?能够说这种进步就足以把人类历史逐步引入地上的天堂吗?④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序言,第3页。
早在20世纪50年代,洛维特就因提出这样的疑问而闻名国际学界。洛维特早年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在海德格尔影响下,他感受到何为哲学思考的时代重负⑤洛维特的思想生平,参见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69~181页(以下凡引此书以简称《我的生活回忆》加页码方式随文夹注)。亦参见伽达默尔《哲学生涯》,陈春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18~227页。。纳粹执政后,身为犹太人的洛维特被迫流亡意大利。1938年,意大利也开始排犹,洛维特又流亡日本,在日本仙台大学教欧洲思想史,其间写下《欧洲虚无主义:对欧洲战争的前历史的考察》(1940)和《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想中的革命性断裂》(1941)两部著述,后一部著作为洛维特带来世界性声誉。由于德国驻日使馆的压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洛维特被迫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美期间写下《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1949/德文版1953)一书。
洛维特以思想史研究的方式探究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无论人物思想专论还是辨识思想的历史流变,无不是带着时代问题的现象学考察。这与其说是洛维特的个人思想特征,不如说是20世纪欧洲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既然尼采已经终结现代欧洲哲学,一个热爱哲学的欧洲人面临的首要问题难免是思想的惶惑。在这种精神处境中,思想史研究成为重新寻求哲学出发点的唯一途径。在20世纪的西方学界,写思想史或哲学史的人很多,当我们面对这类思想史家的论著时,必须关注其思想史研究背后的哲学关切。
与施特劳斯、沃格林等思想史家不同,与新马克思主义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及自由主义派的伯林相似,洛维特的思想史研究主要着眼于17至19世纪现代欧洲思想的嬗变。不过,如哈贝马斯所看到的那样,洛维特审视现代欧洲哲学思想时的立足点并不是现代,而是古代,哈贝马斯称之为向“廊下派退却”⑥参见Jürgen Habermas,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Mainz,1987,S.195.。显然,自由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派哲学家一样,在审
视现代欧洲哲学思想时绝不会退回到现代之前的立场,这也意味着他们毫不动摇地认定:相比于古代希腊哲学(遑论中古经院哲学),现代欧洲哲学不言而喻是巨大进步。就此而言,洛维特的思想史研究更接近施特劳斯和沃格林的思想史研究,他们共同认为,现代欧洲哲学相比于古代欧洲哲学与其说是一种进步,不如说是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反映。
二
我们知道,西方的现代历史是一个所谓“世俗化”的过程,也就是摆脱罗马天主教政治法权支配的过程。与此过程相应,欧洲现代思想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摆脱基督教观念支配的过程。然而,《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却提出一个独到的论点:现代进步论历史哲学虽然反对基督教思想,但它恰恰与自己所反对的基督教历史神学不仅在思想结构上类似,而且有内在的亲缘关系。进步论历史哲学相信,历史有意义或有一个终极目的,正如基督教历史神学相信,上帝计划的救赎历史具有终末论目的。进步论历史哲学的思想架构取自基督教历史神学,因而可以说是一种反基督教的基督教历史观。
当然,洛维特并不认为,以改造此世为目的的进步论历史哲学是由以超越此世为目的的历史神学直接滋育出来的,毕竟,进步论历史哲学的根基在近代兴起的自然科学哲学那里。问题在于,进步论历史哲学的确分享了基督教历史神学的要素。洛维特对进步论历史哲学的思想史考察采用了可称之为现象学还原式的“回溯”方式: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回溯到《圣经》的历史观。为了更好地理解洛维特的看法,我们需要按历时顺序来重构洛维特的观点。
洛维特首先在《绪论》中提出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就“历史”观念指人世是一个走向某种终极目标的时间进程而言,古希腊人并没有什么“历史”观念。在古希腊,historia这个词指的是探究人世事件的自然成因,这意味着人世有自己的自然理则。在古希腊文明中,与“历史”观近似的至多是一种以“金银铜铁”为标志的循环周期论,其背景是古希腊的秩序神学。换言之,希腊人对人世变迁并不持有一种线性发展观念,而是相信近乎周期性的自然变化法则:
历史的进程是政治循环的一个圆圈;制度更迭、消亡,并在由事物的本性所规定的更迭中复归。根据历史的这种自然既成的宿命,史家就能够预言某种政治状况的未来。(《世界历史》,第11页)
古希腊—罗马文明崩溃之后,犹太—基督教的世界观取代了古希腊的世界观。由于犹太—基督教的超世创世主对人世有一个预定的救赎目的,一旦这种创造主观念取代了宇宙的自然目的理性,人世便被赋予一个从过去到未来或从起点到终点的救赎过程,作为线性进程的“历史”观念就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现世生存感觉的二分化:现世本身没有意义,超逾现世的新天新地才有意义。基督教的终末信仰要求世人不再看重现世,而是与上帝的国建立起内在关系,把生存的希望从现世挪到终末获得救赎之后的未来,从而彻底更改了人的生存在世的古典感受方式。由于《旧约》区分特选子民与异教徒,《新约》区分现世与即临的上帝国,犹太—基督教的世界观给人世带来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紧张。正是这种人世之内的神圣与世俗的内在张力,为从奥古斯丁、约阿希姆的历史神学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嬗变提供了基本动力(《世界历史》,第230页)。因此,进步论历史哲学就其致力于在现世历史中实现旧约式的终极救赎而言,是基督教式的;就其把《圣经》中的终末期待和预定信仰转换成现世历史的进步意识而言,它又是反基督教式的。这一思想嬗变的结果是,在世俗化的景观中,历史哲学本身作为基督教历史观的替代为世人提供了一种进步论宗教:
进步的非宗教依然是一种可以从基督教的未来目标中引申出来的宗教,虽然它用一种不确定的和世俗内的终末取代了一种确定的、超世的终末。(《世界历史》,第134页)
这意味着,所谓历史观的世俗化,指的就是基督教的终末论超世历史观被改写成进步论现世历史观。按照这样的观念逻辑,没有基督教的终末论历史神学,也就不会有现世进步论的
历史哲学——即便出现了新的自然科学哲学也罢。因此,在洛维特看来,现世进步论历史哲学的三阶段论不过是约阿希姆历史神学三阶段论的翻版(《世界历史》,第173~188页)。
由此看来,进步论历史哲学最终废黜的是古希腊的自然人世观,按照这种观念,人世并没有非要走向某个终点的“历史”这回事,遑论历史中的意义问题。由于犹太—基督教世界观取代了古希腊的自然人世观,西方思想不仅有了从过去到未来或从起点到终点的“历史”这回事,而且还有了历史中的意义问题,后者显然是一个宗教问题,即人世是否得救。
必须再次强调,尽管现代进步论历史哲学分享了基督教历史神学的要素,它赖以产生的直接动力并不是基督教历史神学,而是现代自然科学世界观。所谓“现代意识”指的是商业化文明和新自然科学联手给西方人带来的这样一种生活感觉:“历史变革[本身]就是一切”。就此而言,现代进步论历史哲学在性质上与古希腊的自然秩序世界观和犹太—基督教的终末论世界观都完全不同:
自然科学的进步,不仅加快了历史运动和革新的速度,而且也扩大了运动和革新的影响范围,还使得大自然成为人的历史活动中一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以监控的要素。(《世界历史》,第232页)
进步论历史哲学的出现明确以废黜基督教历史神学为直接目的,对洛维特来说,这有其历史的正确之处,毕竟,历史神学凭靠对超世创造主的信仰和对即临的上帝国的希望摧毁了凭靠自然的循环节律的在世信赖。言下之意,似乎如果现代历史哲学凭靠新自然科学废黜基督教历史神学之后回到古希腊的自然信念,就成了彻底的正确之举。然而,现代历史哲学的“历史辩证法”在摧毁对超世上帝的信仰的同时,又建立起一种“进步邪教”(Irreligion des Fortschrifts),把人引入追求实现尘世天国的绝对自信和勇气狂的状态中①参见K.Löwith,Hans Blumenberg’s Legitimität der Neuzeit,Philosophische Rundschau,15(1968),S.201;K.Löwith,Vorträge und Aufsätze:Zur Kritik der christlichen Tradition,Stuttgart,1966,SS.139-155.。这无异于说,历史进步论是一种形而上学迷信。洛维特的论点难免让我们感到困惑,或至少感到震惊,毕竟,我们的“常识”中已经有这样的信念。我们需要考察洛维特的论据,看看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说历史进步论是一种哲学迷信。
在洛维特看来,现代的科学宗教之所以是一种迷信,乃是因为其形而上学世界观虽然建基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其哲学构造凭靠的却是基督教神学:
机械的世界图景同样来自神学,而不能追溯到希腊的宇宙论。这种图景其实是把圣经中的创世论世俗化;创世论中的上帝不是秩序宇宙的一个宾语,而是一个超越世界的主体。原先的“上帝构造宇宙说”在牛顿那里还仍旧是关键的思想,到了康德和拉普拉斯手里,则替换成一种人类理性的构造,使得神性创造者的假设成为多余。(《我的生活回忆》,第177~178页)
取代基督教上帝的历史进步本身成为上帝,但这个上帝其实是机械论形而上学的自然法则——现代形而上学家人为建构的这个法则宣称能够彻底制服自然的偶然脾性,其实其仍然受自然的偶然支配。于是,现代世界成为“没有创世主的造物”,现代哲学的历史意识则带有无限制的意欲肥大症:
现代历史意识虽然摆脱了对一个具有绝对意义的中心事件的基督教信仰,但它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前提和结论,即坚持过去是准备、将来是实现;这样,救赎历史就可以还原为一种进步发展的无位格神学,在这种发展中,每一个目前的阶段都是历史准备的实现。由于转化为一种世俗的进步理论,救赎历史的图式也就可以表现为自然的和可证明的。(《世界历史》,第221~222页)
由于摒弃了“神性的世界”及其超世的上帝,现代历史意识必然造出一种无神的世界法则,以解释此世的受苦,并由此提出历史的道义
诉求,其结果是让无神的人性化世界最终走向“脱世的”世界①参见K.Löwith,Der Begriff der Geschichte in Neuzeit,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Wissenschaften,Philosophisch -historische Klasse,1960,S.11.。所谓“脱世”是指人世的生活方式脱离了生存的自然,人的生存成为无根或无家园的生存,这是现代性的不安的最终根源。洛维特的意思很清楚:就进步论历史哲学把人世引向无根或无家园的生存状态而言,它是一种“邪教”,信奉这种宗教就是一种迷信。
三
从赫尔德到伽达默尔,历史意识已经成为德国哲学思想的主流传统,而且在哲学上变得越来越精致。洛维特对现代历史哲学的批判显得是在让自己从这一思想传统中挣脱,尽管他是德意志哲人。既然在德国哲学界基于历史意识来思考都已经成为习惯,洛维特的论点难免招惹争议。与任何学术上的争议一样,这场争议既涉及学问问题,也涉及个人信念问题。学问方面的问题是,洛维特对现代历史哲学的现象学式剖析是否站得住脚?个人信念方面的问题是,相信人的生存乃至思想的基础应该是自然秩序还是历史中的道义?
通过区分形而上学化的上帝观念与《圣经》中的上帝观念,洛维特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原始基督教思想不应该为现代历史哲学的形成负责。洛维特承认,犹太人的历史“极其特殊”,且明显是一种“政治历史”。但《旧约》对犹太人历史的记叙仅具有宗教含义,从中引申不出一种“哲学”。即便可以把犹太先知称为“极端的‘历史哲学家’”,也不能说他们提出了“一种哲学”。毕竟,他们具有的仅仅是“对上帝关于其特选子民”的信仰,“犹太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可以以神学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历史—政治命运”(《世界历史》,第232~233页)。换言之,《旧约》或者更准确地说《希伯来圣经》虽然是犹太民族的历史自传,但这个历史仅仅是“特殊的”历史,而非普遍历史。以《新约》为基础的基督教信仰才使得上帝的救恩行动成为“普遍”救赎,不再把救赎“限制在一个特殊的民族身上”。然而,与《旧约》带有明显的“历史”要素不同,《新约》福音书和保罗书信中的思想并不带有“历史”要素,信靠基督的救恩注重的是个体的生存时机与基督事件的关系。《新约》中的基督教思想尽管提供了一种终末论,但这种终末论与现世历史无关:“对于信徒来说,历史不是人的努力和进步的自律王国,而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罪与死的王国。”(《世界历史》,第232页)总之,《旧约》思想虽然具有历史要素,但并不包含一种关于普遍历史的哲学,《新约》思想虽然具有普遍要素,却并不包含一种改变现世的历史哲学诉求。
洛维特的这一结论面临一个棘手的学理困难,即如何看待把上帝的救恩行动视为“普遍”救赎的《新约》与以犹太民族的历史自传为基础的《旧约》的关系。单就分析思想要素而言,洛维特的说法没问题,但就基督教思想的基础是《旧约》与《新约》合在一起的《圣经》而言,洛维特的说法就有问题。毕竟,基督教正统思想从来不会把《旧约》与《新约》割裂开来。《旧约》以特殊的犹太民族史寓意或“预表”了普遍的世界救赎史,这不仅是基督教神学的常识,也是基督教信仰的常识。否则,基督徒为何非要读或者如何才能读《旧约》呢。
洛维特面临的这一困难来自他思想上的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他想要让无论古希腊还是原始基督教思想与现代历史哲学的进步观念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洛维特又认为,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是历史意识取代了自然意识。虽然现代式的历史进步信仰与基督教世界观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基督教的救赎史观对古希腊自然循环观的取代毕竟彻底扭曲了“自然与历史”的关系,为现代式“进步”信仰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如果要克服虚无主义,就得通过拆除现代历史意识中的基督教要素,回到古希腊的自然意识,恢复“自然的人性”(natürliche Humanität)观念。换言之,洛维特是古希腊自然秩序观的信徒②K.Löwith,Die kritische Aufsätze zur historischen Exitenz,Stuttgart,1960,SS.179-207.。由此可以理解,《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的回溯式考察从布克哈特的历史思想开
始,是因为布克哈特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否弃了现代历史哲学。
由于布克哈特不仅是闻名遐迩的史学大师,而且是有哲学思考的史学大师,他才成为洛维特考察现代历史哲学的最后落脚点,成为现代历史哲学幡然悔悟的现身说法。实际上,《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是洛维特对现代式历史进步信仰采取的哲学斩首行动,这一行动明显得自尼采的启发:尼采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方案是回到古希腊的“永恒复返”的自然状态。同样,洛维特也想通过回到古希腊的自然秩序观来克服“现代主体主义的世界论虚无主义”①参见K.Löwith,Natur und Geschichte,Die neue Rundschau,62(1951),S.76.。这一哲学行动的具体步骤是“解构”历史哲学形成的“历史”逻辑,以思想史的方式对现代历史哲学实施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批判:海德格尔通过还原现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神学前提来解构现代形而上学,为回到古希腊自然哲人的形而上学扫清道路。洛维特则通过还原现代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来拆除现代历史哲学,为回到古希腊的自然秩序观扫清道路②见格雷《海德格尔的道路:从人的存在到自然》,《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2-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因此,《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虽然在形式上是一部思想史论著,实质上却是一部哲学论著,即致力于从哲学上将世界与历史的重叠关系剥离开,让“世界”成为海德格尔哲学所理解的在世,而不是现代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客观进程。
洛维特反复申言,在历史中追寻终极道义的现代历史哲学既偏离古希腊的自然神学,也偏离基督教的超自然神学。尽管如此,《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明显不仅是对现代历史哲学的批判,也是对犹太—基督教历史神学的批判,尽管为了不违背自己的信仰,他又不得不竭力让犹太—基督教信仰与历史进步论哲学摆脱干系。事实上,洛维特也明确指责说:追究历史有意义或无意义,是犹太—基督教历史神学提出的“漫无边际的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相反,希腊人就“没有无理由地要求探究世界历史的终极意义。他们被自然宇宙的秩序和美吸引,生生灭灭的宇宙规律也就是解释历史的典范”(《世界历史》,第7~8页)。可以看到,洛维特明显站在古希腊自然观念的立场上来批判现代启蒙哲学所凭靠的形而上学化自然概念,毕竟,他相信,历史的道义原则取代生存的自然秩序原则对人类生存来说是巨大灾难。
四
在把现代欧洲的历史道义思想与古希腊的自然秩序思想对立起来时,洛维特也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加以对比。他在日本的生活经验让他感觉到,古老的东方文明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异教文化”有共同之处,即“对无所不在并高于人类的力量有一种敬畏与崇敬”,“对于不幸事件的自然态度是一种无条件的顺从”。然而,“随着带有个人意识主张的西方文明在日本逐渐生根茁壮,这种顺从也就随之消逝”(《我的生活回忆》,第175~176页)。这种对比暗示的是:东方文明不像西方文明那样注重“历史”及其“意义”,而是注重与自然秩序的和谐,具有爱自然命运的在世情怀。在洛维特笔下,“西方文明”指的是采取进步论历史观的现代欧洲文明,或者称为“基督教的西方文明”。
未来是历史的真正焦点,其前提条件是,这种真理是建立在基督教西方的宗教基础之上的。从以赛亚到马克思、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从约阿希姆到谢林,基督教西方的历史意识是由终末论的主题规定的。(《世界历史》,第24页)
所谓“西方文明”在我们这里是个大而无当的含混术词,它掩盖了西方思想的历史具体性和差异。洛维特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异教文化”与“基督教的西方文明”区别开来,这意味着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西方文明”:一个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称之为“异教文明”,另一个是基督教的“西方文明”。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现代的进步论世界观并不能完全代表基督教的西方文明,它毕竟呈现为反基督教世界观的姿态,而且靠取代基督教世界观获得自己的统治法权。严格来讲,以“自然”和“历史”概念为尺度,洛维特实际上
区分了三种“西方文明”形态:古希腊的、基督教的和现代欧洲的西方文明。
在旧约和新约圣经中,并没有一个由自身所推动而运转的大自然,也没有一个由大自然来规范秩序的世界,也就是说,既没有一个希腊意义上的宇宙(Kosmos),也没有一个现代历史意识的、实存的历史性意义下的历史。大自然的“自然生成”的性质,希腊文所称的physis,在经过了近代物理学的洗礼之后,已经离我们而去;而人们原本对政治史不偏不倚的观察角度,也受到了历史研究中的思辨神学的扭曲。(《我的生活回忆》,第177页)
尽管如此,现代欧洲文明又没有彻底摆脱犹太—基督教的烙印。因为,现代政治史表明,历史进步论具体体现为一种“世俗的弥赛亚主义”,欧洲的强势民族国家无不把自己看成世界的救世主:
西方各民族世俗的弥赛亚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一种民族使命的意识相关联,这种使命植根于这样一种宗教信仰之中,即自己是被上帝为了一种普遍意义的特殊任务而拣选出来的。……无论宗教使命向一种世俗要求的转变采取了什么样的形态,世界一片糟糕并且必须被更新,这种宗教信念都依然是基础性的东西。(《世界历史》,第9页,注释1)
这段注解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充分表明洛维特已然意识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兴起还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相关。《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以思想史的现象学追溯方式最终揭示了支配现代西方民族国家政治行为的思想基础。民族国家的建构要求民族历史的正当性论证资源,历史哲学遂肩负起为民族国家提供正当性论证的大任。
不仅如此,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尤其引人兴味的是,洛维特已经看到,如今代表“世俗弥赛亚主义”的“西方文明”的国家是美国:
由于美国在现代世界发展的方向上大大超越了欧洲,以至于美国成了“西方”独一无二的代名词——如果一个外国人希望别人接受的话,就无法完全躲避这种融入美式生活方式的要求。(《我的生活回忆》,第176页)
洛维特在日本观察到一个在他看来十分重要的文明现象:如今的日本人不会期待一个在日本的欧洲人归化东方文化,反倒是拼命要从这个欧洲人身上“学到欧洲人的思考方式”。洛维特的观察出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今天,这一观察早已经是我们的现实。然而,让今天的我们尴尬的是:洛维特充满忧虑地感觉到,基于历史进步论的现代西方文明不仅摧毁了古老的西方文明,也在摧毁东方的古老文明。
五、结 语
伽达默尔在评述洛维特的思想时,对洛维特返回“自然”的哲学取向颇有微词。他特别提到,“自然”不是“德文词”,言下之意,“历史”这个语词才属于德意志思想传统。既然洛维特和伽达默尔都是德意志人,那么,信赖自然秩序或者信赖历史意识就是他们各自的个体心性使然。如伽达默尔所说,洛维特的个性精神气质是不带幻想地承纳万物,依从自然,献身当下,自然地生存在世,承受不可避免的天命①伽达默尔:《哲学生涯》,第226页、119页。。在我们看来,洛维特似乎显得有点儿道家情怀,正如我们不难看到,如今绝大多数中国学人具有伽达默尔的哲学意识。
不过,洛维特突出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至少提醒我们应该反思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进步意识,并看到儒家传统的政教之学与现代式“进步论”历史哲学在性质上无法通融。倘若如此,洛维特在现代性思想语境中所挑明的“自然”与“历史”的思想冲突,将会促使我们进入更富有刺激性的思想冲撞。
责任编校:余 沉
B14
A
1001-5019(2015)06-0002-07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6.001
① 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以下凡引此书皆以简称《世界历史》加页码方式随文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