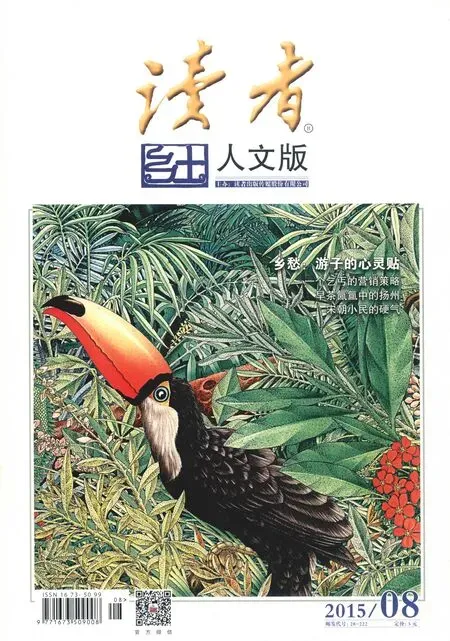我家的火车站站台地图
文/艾小羊 图/沈骋宇
我家的火车站站台地图
文/艾小羊图/沈骋宇

我父母在建筑单位工作,哪里有活儿就在哪里安家。我家六个孩子,出生在四个地方,而我的父母,一个是湖北人,一个是山东人。在我懂事之后,我的家庭才相对稳定地安顿在了一个城市。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奔波最少,然而在小时候,我是多么羡慕我的父母与哥哥姐姐,他们每个人,都至少拥有一个刻写了他们的记忆与历史的站台。
父亲的站台,在汉口。21岁,他中专毕业后已经在武汉工作了5年,却忽然心血来潮,决定去支援大西北建设,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站台上送行的人中,没有父亲的亲人,然而火红的横幅上所写的“热烈欢送”与他有关,他是光荣的支边青年,他的青春将挥洒于一片荒无人烟之处。
母亲的站台,在锦州。作为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后代,母亲的少女时代是在辽宁度过的。在母亲的叙述中,锦州火车站永远热闹而又危险,似乎每一步都会遇到坏人。那时候的她,是个漂亮的姑娘,皮肤白里透红,麻花辫一直垂到腰间,追求她的人很多,然而作为一个疑心很重的处女座姑娘,她常常觉得男人都不安好心。
母亲的行李是两只硕大的老式牛皮箱,同行的男生帮她拎上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塞进座位底下。母亲随身的布袋里装着馒头、咸菜和煮鸡蛋。而站台上,不知道谁的袋子不够结实,被挤烂了,馒头与鸡蛋撒了一地。那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一样的年代,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每个人上路的时候,口袋里都是馒头与煮鸡蛋。
火车开动,白底黑字的水泥站牌上,“锦州”二字消失在夜风里。母亲这辈子再未回过锦州,然而当二姐出生时,她坚持在新生儿的名字里,镶进了一个“锦”字。
我的大哥大姐出生在西宁。那时候的西宁火车站,奔跑的还是一种窄轨小火车,姥姥家就住在火车站旁边的坡地上,爬上红砖房顶就能看到站台。大哥四五岁的时候开始爬房顶,到了六七岁,经常在房顶上一待就是半天。
“今天,站台上有个瘸子。”他在饭桌上对姥姥说。
“有个小男孩拿了个花皮球下车,他肯定是从上海来的。”他在睡觉前对我大姐说。
站台就是他的电影院,每天上映着不同的影片。
我去过大哥大姐的站台,那时候,大哥已经去陕西当兵,火车站旁边的那处姥姥家的平房由姨妈接管。旧车站即将废弃,偶尔有一两列火车经过,站台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些提着饭盒的铁路工人,在傍晚6点的时候,等在站台上,不说话,像站台旁边野生的枸杞。
二哥、三哥的站台在河南洛阳,他们出生的时候,我父母在河南工作。
上大学的时候,每年都有同学要去洛阳看牡丹,我总说要去,却因故未能成行。工作后,终于有一次去洛阳出差,回程的时候买到的车票是发往广州的。当时正是南下打工的高潮期,我和同事好不容易挤上车,却发现同事的背包带被人齐刷刷地剪断,背带在她肩头滑稽地晃动着。车门处挤满了扭曲的脸,想要下车已经不可能了。我们透过车窗看到站台上两个20岁出头的小青年手里拿着没有带子的蓝色拎包。“抓小偷!”同事把头探出车窗,大声喊。小青年继续慢悠悠地走路,站台上跑来跑去的都是着急赶火车的人,每个人都像逃跑的“小偷”,只有真正的小偷,宛如路人。
回家后,我对二哥说:“洛阳火车站真乱。”二哥挠挠头,问:“是吗?”二哥离开那个站台的时候只有5岁,母亲背着他,他的两只鞋都被挤掉了。后来每次谈起这件事,母亲总说:“幸亏两只都挤掉了,别人捡去还能穿。”
我二姐的站台在兰州。那时候,姥姥、姥爷已经从西宁搬到兰州定居,母亲在姥姥家生完二姐,便把她留在了那儿,跟随单位的工程去了嘉峪关。3年后,我出生在嘉峪关。再过几年,父母终于调到了另外一个相对稳定的单位,地理上恰巧位于嘉峪关与兰州之间。于是,母亲抱着我,踏上嘉峪关的站台;父亲则抱着姐姐,踏上兰州的站台。
我离开嘉峪关的时候不到3岁,对于站台的印象几乎为零。听母亲说,当时正值盛夏,站台上有卖西瓜的,一个青皮红瓤大西瓜,被切成一牙一牙,花朵似的摆在一块纱布下面。母亲见我嘴馋,便花一毛钱买了一牙给我,吃完我便开始上吐下泻。
那一路的折腾,深深地刻进了母亲的脑海里。此后每一次,无论谁坐火车,母亲都要叮嘱,站台上的东西不能买。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站台都已经重新翻修,连后来我成长的那个小城金昌的火车站也在去年重新修建。新的站台有密实的顶棚,我们再也不可能踏着站台上咯吱作响的积雪,从火车上接下来一个热气腾腾的人,当他双脚落地时,豪气地感叹:“这雪真厚!”
(宋半文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