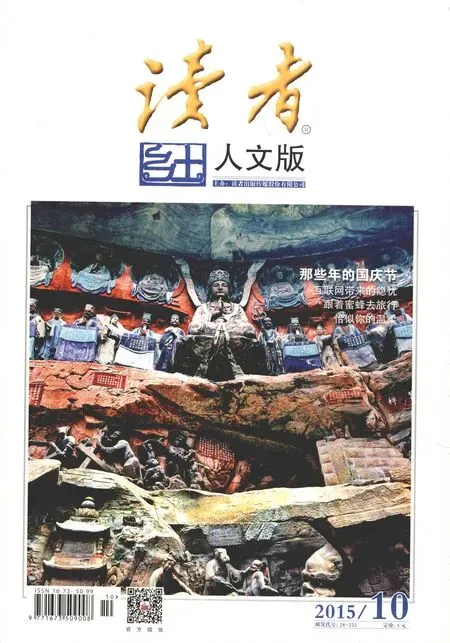难舍猪肉
文/张佳玮
难舍猪肉
文/张佳玮

中国人对动物,一向欺软怕硬。熊虎威武,于是比之上将;猪羊听话,就可怜被磨刀霍霍。猪的形象,由天蓬元帅一托生,就此奠定:贪吃嗜睡、好色轻浮。其实猪既易饲养,又很听话,若没有它舍身相助,国人千年来的饮食结构不知从何谈起。所以,我们对猪真是有些负义。
猪曾经风光过:古人举行祭祀活动,猪头总是少不了的;后来民间结拜兄弟,也要拿个猪头放着。也许因为猪头比人更通上天智慧?但是一摆脱了贫寒,士大夫纷纷抛弃猪,中医咬文嚼字,以为“凡肉有补,惟猪肉无补”,认为猪肉全是反面作用,无非生痰虚气。可是有力气在那里翻医书的诸位,都是饱暖无虞的。市井小民还来不及调和五脏阴阳,先求饱腹吧—所以猪肉所惠及的多是民间,人见人爱。

西班牙火腿卷

红烧肉

东坡肘子
苏轼在黄州写猪肉:“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这大概是猪肉的症结所在。贵人不肯吃前头言过,贫人不解煮才是关键。鸿门宴上樊哙在项羽面前大吃生猪肘子,常人见之要惊倒了。传说中的仙人或显贵,偶尔会吃吃孔雀舌之类的清贵食品,却少见吃猪肉的—因为那是下里巴人的食材,猪本身因为脂肪的缘故,有腥臭味。西方人也不爱吃猪肉,大概就在于此。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比如有名的德国咸猪手,盐下得重,香料放得扎实,如果贴骨的肉也咸香结实,那就算合格—当然得另配酸菜。德国咸猪手一方面选料极精,一方面尽量加盐,仿佛不如此便无法遮盖猪肉的本来面目。除此之外,西方人吃猪肉,最爱吃的是培根,也就是烟肉。此肉如今有名,大有喧宾夺主、压倒大贤弗朗西斯·培根的意思。烟肉是加盐腌制,迎风挂干,加糖与香料,再加烟熏,做法繁杂精细,胜过酿酒,所以好烟肉煎出来咸香适口。不过如此处理过的猪肉,已然面目全非了。
西班牙人做火腿,比起烟肉来多少手下留情,没有给猪肉画上烟熏妆,搞到面目全非,但其炮制手段还是离不了“盐腌风干”一流。不过据说西班牙人做火腿选猪如选美,肥瘦和肉质都讲究,所以风干完了,可以油煎,也能生吃,很合鸿门宴的格调。
话说回来,我国对付猪肉就厉害得多。且说火腿。欧洲有西班牙火腿,我国云南、浙江的火腿也天下知名。照例粗盐揉过,挂起风干,鲜红结实。唐鲁孙还说,浙江制火腿,还懂得用条狗腿挂在其间,以取其鲜味。只是我国火腿大多用来做借味菜,比如火腿拌芥菜,是民国时世家公子们喝粥的陪衬,类似于《红楼梦》里野鸡拌咸菜。真当主菜的,大概就是蜜蒸火方。
除了火腿,中国百姓对付猪肉别有绝技。苏轼说“贫者不解煮”其实是小看人民的智慧了。按《梦粱录》记,“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凡几”,而且已经有“臊子肉”之类名目。《水浒传》中,鲁达去找镇关西的茬,一张嘴就是肥肉臊子、瘦肉臊子、寸金软骨,镇关西也很体贴地说:“瘦肉臊子回去包馄饨,肥肉臊子何用?”可见当时市民百姓对猪肉的用途精通得很。《金瓶梅》里,宋惠莲将一条硬柴煮猪肉,煮得皮化肉烂,然后猛加葱姜作料,请太太们蘸着吃。这做法冷眼一看,很像如今的蒜泥白肉:都是将肉用白水处理,然后蘸上华丽配料。只是蒜泥白肉讲究的是片肉细薄、煮肉不可过烂,取的是个冷韧清脆,爽嫩柔滑。而宋惠莲这个白煮猪头肉走另一极端,要的就是入口即化、酥烂香融。可见猪肉也听话,好比八戒见了美女妖精—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白煮之外,余下的套路有大同小异处。上海做腌笃鲜,是鲜猪肉、咸肉与笋一起白煮,取笋与咸肉之香,试图把猪肉衬托成翩翩佳公子;湖南红烧肉,煸干后加辣椒,炽焰焦红,香辣霸道夺人之魂。浙江、广东、福建、四川都有扣肉(四川曰烧白),说来无非一个字:蒸。浙江再加霉干菜,与肉的油脂相得益彰,终于达成完美结合,入口即化,甜香酥人。苏式红烧肉就是多水纯炖慢熬,一如苏轼说东坡肉的诀窍:“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其实,中外对付猪肉大抵有两招:一是风干盐腌,一是水煮夺味。如其他炒、煎、炸法,也是重味大料,绝少平淡的。大概猪肉的原味并不好吃,但性格随和,宽厚肥硕,也就随你左右摇摆了。所以猪肉未必登大雅富贵之堂,但为小民百姓所喜。如此随意摆布、脂厚香浓,而又能满足人类对热量的那份原始热情的好东西,谁不爱呢?
(郑志鸿摘自《饮食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