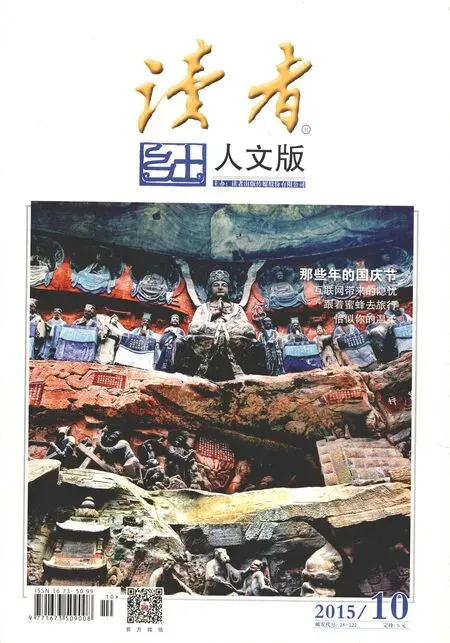老家物语
文/胡安运 图/郭德鑫
老家物语
文/胡安运图/郭德鑫

我想,老家就是承载我们童年岁月的地方。在那里,有忧伤,也有欢乐,有辛酸的眼泪,也有幸福的歌声。
老家千里一梦遥,故乡老井起青苔。
其实,无论何时,无论你身在何处,老家的山山水水,老家的一砖一瓦,老家的一草一木,总会在你的心底刻下深深的印记。
然而,老家的内涵是什么?
我想,老家就是承载我们童年岁月的地方。在那里,有忧伤,也有欢乐,有辛酸的眼泪,也有幸福的歌声。
感觉时光的车轮并没有走远,梦里回首,那一段段岁月的剪影就晃动在眼前。趴在老槐树粗壮的枝头,看父亲的大扫帚扫尽落满庭院的黄叶,院中留下许多深深浅浅的条纹;母亲做好了晚饭,照例是苞米面地瓜粥,她在灰黑的围裙上抹一抹手,拉长腔调柔声喊道:“喝汤啦—”一家五口人就围坐在黑黑的石桌旁,就着咸菜,把一锅地瓜粥喝得干干净净。晚上没有电灯,母亲点亮油灯,一道昏黄的光把四面的土墙照得朦胧迷离。我在灶台旁做算术,母亲戴上老花镜在灯下纺线。半夜,月亮挂在墙外的老柳树梢上,院子里也是一片朦胧、一片温馨。在睡梦中,吃着母亲精心熬制的地瓜糖,夜的黑暗就融化为一段甜蜜的时光,在半睡半醒之间,一串串幸福的热泪打湿了枕头。
这是老家给我的最深的印记。
后来,为求学,我离开了老家,哥哥和弟弟也一个一个离开了老家,只留下老父老母陪伴着老树老屋。父亲种不动地,春天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母亲拉不动车,就在村前地头放牧她心爱的绵羊。老家的院子里,放满了农具,生锈的镰刀挂在墙上,默对着沉寂的岁月;母亲的纺车,安安静静地待在老屋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咀嚼那些在灯光里逝去的日子。后来虽然安了电灯,但母亲总是不开灯就草草上炕躺下;父亲的小屋里也是一片昏暗和沉寂,除了偶尔传出如雷的鼾声。
只有一年一度的春节这几天,土屋里的灯光特别明亮,欢声笑语,吵吵闹闹。然而,热闹总是短暂的,喧哗不过几日,一切就又归于沉寂。过完春节,该走的就一个又一个地走了,打工的、求学的、求职的,不能走的就留在老树下,就守在老家里。离家时栽下的杨树和榆树长高了、长粗了,枝叶荫蔽了寂静的庭院,每年深秋,树叶飘落一地。老父亲腰弯背驼已经扛不动沉重的扫帚,那些灰尘只有任它随风飘扬;母亲的白发随着炊烟在秋风里飘动,飘成了一朵朵白云,在四季里游走,愈走愈慢。母亲就站在路口张望,望得很远望得很久,然后一个人蹒跚着赶着羊儿回家。她伸出粗糙的手抚摸着绵羊柔软的绒毛,像是抚摸孩子的笑脸,然后自言自语:“时候不早了,咱该回家了。”
老屋还是那座老屋,老树还是那棵老树,河里的水满了枯了,天上的月儿圆了缺了,你以为时光没有脚吗?时光的脚步总是在你的前面,你再怎么拼命也赶不上。听《常回家看看》听得心潮起伏,回家看看吧。有爹娘才有老家,有老家,你游荡的灵魂才有方向。路越来越宽,车越来越多,老家不就近在咫尺吗?
回老家的感觉真好,阳光还是那样明媚,风还是那样柔情,天空还是那样湛蓝。过了小石桥就到老家了,母亲好像知道今天我要回家,一大早就站在路口张望。老家有最贴心的话语,有最舒心的自由,有最可口的饭菜,有最香醇的老酒,有最真切的温暖。一碗炸酱面、两个荷包蛋,吃起来是那样舒坦。
怎奈时光无情,父亲说走就走了,母亲也紧跟着离去,长辈也一个一个离开老家到了另一个世界。没有了父母,没有了牵挂,老家还剩下什么呢?逢年过节回去一次,四间老屋空荡荡的,窗棂朽败布满蜘蛛网,窗台坍塌落满灰尘,老井旁长满荒草。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去了,曲曲折折的老街也是一片寂静,偶有汽车从街心穿过,扬起一阵灰尘。走进荒芜的庭院,落尘不扫,枯叶遍地,这还是我日思夜想的老家吗?走到村西的墓地,细数一座座老坟,父母的坟茔已长满荒草,我小心地将一沓冥币和一串元宝放在坟前点燃,愿老人地下安心,保佑晚辈无灾无难、幸福安康。
猛一回头,一只灰鸟鸣叫着飞向遥远的天际。
人生聚散都是缘,悲欢离合难诉说。老家,你还在我的心里吗?
(闵福贵摘自《思维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