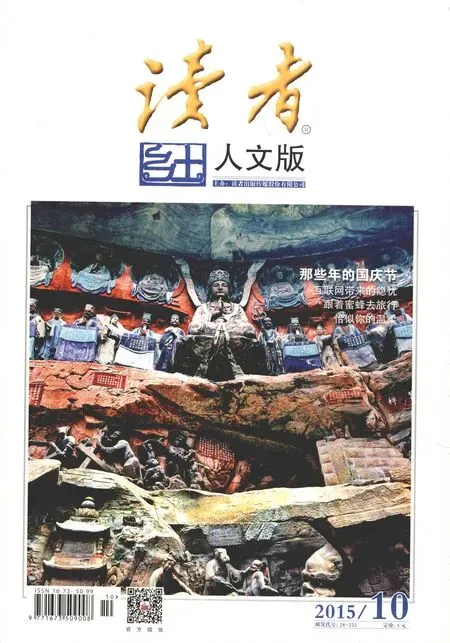向上的炊烟
文/米抗战
向上的炊烟
文/米抗战

一
见过许多乡土题材的画作,大凡描绘村庄的作品,总能找到几笔淡淡的炊烟,其中一抹炊烟会为画面平添烟火气。
缘此,画面一下子就灵动了,意境也增了几分。
初见画里的炊烟,是20多年前。那是一张乡土题材的国画,有田地、有树木、有房子,当然少不了炊烟。那幅画印在母亲糊墙的一张报纸上,皱巴巴地从墙上鼓起来,有两个火柴盒那么大,被烟熏成了褐黄色,极像黄土地的调子。
母亲做饭,我帮着烧锅,手拉着风箱的杆子,头一扭就看见了它。
那画贴倒了,母亲一定是无意的。想看得顺眼,只得弯下脖子,将眼睛倒过来。眼睛倒过来的时候,画里的炊烟就正了。
看罢,我就再没有留意过它。
我得专心烧锅,因为辛劳的父亲即将归来。
二
炊烟,总在风雨云霞的背景中律动。
炊烟袅袅的生活,永远是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日子没法过了”的话,女人说,男人也说,说了是说了,从来就没人在意。饭吃不吃都在锅里,碟子碎了还有碗。偶尔的冰锅冷灶,不过是短暂的休整。
日出日落,月缺月圆,一擀杖能擀平的疙瘩都不算疙瘩。这坎儿那坎儿的,也不过是灶前的葱胡子蒜皮子,一把火就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小磕绊。一旦炊烟升起,锅碗瓢盆重新奏响,宁静平和的生活就又回来了。
一抹炊烟激活了生活。这才是生活的常态。
生活,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男人下了原,女人做了饭”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三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炊烟不升的当儿,远望一个村庄,总觉得是残缺的。譬如此刻,我又一次站上了村外的山冈,为的是远远地望一望久违的炊烟。其实不必赶这一趟的,只要闭上眼睛,凭着记忆就能想象出村庄温情的样子。况且,来路逼仄,杂草丛生。
可我终究还是来了。
虽有淡淡的晨雾氤氲,村庄依然是不完整的。炊烟之于村庄,如同鼻息之于头颅,这一对密友,从遥远的石器时代携手走来,早已融为一体,共同经历了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
晨雾,怎么取代得了?
晨雾氤氲的村庄,总让人觉得是惺忪的,瞥一眼,都能染你一身睡意。试想,弥散的雾,怎么可能具备炊烟的精气神?
四
烟,因火而生,从来就不乏热情。
一把柴火填进灶口,袅袅娜娜的炊烟就升腾起来,合着风箱“吧嗒吧嗒”的节奏,总能将农耕生活的情趣演绎得淡定而洒脱。纵然日子平淡到“一口清水锅,三碗柴火饭”,每一缕炊烟都向着天空升腾。
脱胎于草木的炊烟,理应携带着向往天空的品性。虽立根于黢黑的灶穴,却不忘将追求向上的精神薪火相传。无论沐风还是栉雨,总是一如既往地向上升腾。若要为农耕文明寻找一种精神象征,我以为只能是炊烟了。
此起彼伏的炊烟,连绵不断的炊烟,经久不散的炊烟……林林总总,彰显和缭绕着的是一幅人间最催人向上的生活画景,宁静、温馨、和谐,哪怕只是淡淡地望一眼,也让人通体惬意。
(吴正引摘自《时代青年》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