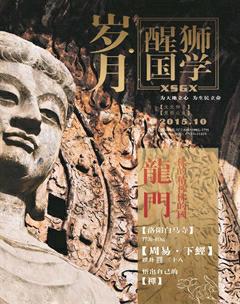“兵”的操守与“官”的操守
游宇明
在传统社会,收受“红包”一直是少数手握权力的人的一种习惯。“红包”一般是下位者送给上位者的,但少数时候,某些上位者为了笼络人心,也会给自己的权力之鞭管不到的下位者送红包。民国老报人陈纪滢写的《我的记者和邮员生活》一书,就谈到时任新疆督办的盛世才给他送红包的故事。
1938年秋天,受《大公报》指派,陈纪滢前往新疆采访“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会”,盛世才热情款待了他,并为其采访提供大量方便。陈纪滢离疆前夕,盛世才的副官长送来一包钱,说是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赠送的旅费和出席费,每个应邀出席大会的人都有。陈纪滢当即表示:盛督办的好意自己十分感谢,但钱绝对不能收,请副官长向盛督办转达。没过多久,副官长又回来了,说:督办已交代,这点钱千万要收下,何况也不止送陈纪滢一人,如果再客气,自己无法交差。陈纪滢还是坚持不收,要求当面去向盛世才说明缘由。陈纪滢说:“我来新疆是代表季鸾先生出席,目的在替大公报采访新闻。来的时候搭乘航委会的包机,一来到迪化,就由督署招待,这已经过分。走时又由督办代洽便机,也不花钱。所以我既没有事实需要钱,更没有理由接受别人的赠款。我是《大公报》的特派员,大公报虽然不是怎样了不起的阔报馆,但它既派出记者采访新闻,就有负担旅费及一切花销的责任。即使我带的钱不够了,我可以向督办借,回去了再还。万万没有跟一般代表接受旅费的理由!何况《大公报》已有小小的声望,我怎能破坏它对外的信誉呢?……我若接受了这笔款,不但毁坏了我的人格,并且也玷污了报馆的荣誉。所以虽然盛督办好意,但这件事万万使不得!”话说到这种程度,陈纪滢原以为此事已了结。没想到上飞机时,盛的副官长登机与其握别后,抛下一个纸包,立即下机走了。无奈之下,陈纪滢决定将钱交给报馆处理。五天后,陈纪滢回到重庆,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时,就将纸包送到《大公报》重庆版负责人曹谷冰手里。曹谷冰打开一看,里面是用麻绳包扎得很紧的一沓厚厚的钞票。曹谷冰与张季鸾商量后达成共识:这两千块钱决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等《大公报》在重庆复刊,每天给盛世才航空邮寄五份报纸,报费与航空费加在一起,正好两千元,先给盛寄去收据,另外以报馆名义写信感谢盛的美意,告诉他处理这笔赠款的方法。
盛世才之所以不顾当事人的意愿一定要送钱给陈纪滢,是有原因的。盛世才当年就读于中国公学,张季鸾是其历史老师,盛对张一直以师礼事之。陈纪滢是老师派来的人,盛自然要高看一眼。其二,《大公报》是中国三四十年代最具影响的民营报纸之一,它相对于国民党的所办的报刊更公正、客观,也更受读者的喜爱,盛世才觉得,如果这份报纸肯吹捧自己,自己的声望就会腾空而起。
陈纪滢的操守也正体现在这里,他是《大公报》有影响的报人,悄悄收了钱,完全有能力“悄悄”地替盛世才美言一番,但他却不为所动。要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20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它相当于算得上是高薪族的大学教授4个月的工资。
不过,在陈纪滢个人的操守之外,《大公报》主事者的做事理念也在无形中起了作用。接手老牌报纸《大公报》伊始,张季鸾就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对于“不卖”一条,张季鸾这样解释:“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故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张季鸾一生从未利用掌握报社发稿大权的机会收受过别人一分一厘钱财。《大公报》老大张季鸾都始终坚持报纸“不卖”,排名老N的陈纪滢自然也不敢私自去“卖”。
说到这里,我想花点时间谈谈领导者的操守对单位的影响。单位就像一列火车,领导者好比火车头,下属一如火车的车厢,火车头在品德的正轨上奔跑,车厢一般也不容易出轨;火车头跑偏了,车厢自然也跟着跑偏。原因很简单:领导操守好,他会欣赏、重用操守好的人,正派人就会活得如鱼得水,下属就不愿至少是不敢做污七八糟的事。领导品质不好,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单位里吹吹拍拍、投机取巧的人就会吃香,正直的人一定会感到窝囊。而人的本质是趋利避害的,既然操守好的人一路泥泞,做事走捷径,用手中的权力谋取金钱、美色之类的“潜规则”,必然成为某些下属的选择。
陈纪滢式的廉洁,说到底,是《大公报》这样的环境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