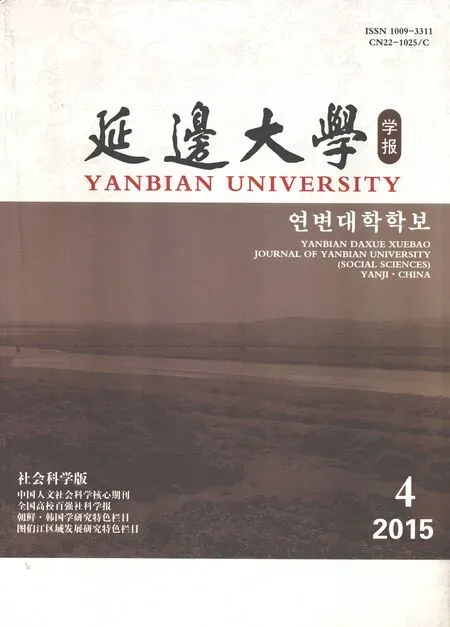“无为”之“道”对花郎道文化的映射
雷 霆
(延边大学 朝鲜-韩国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老子的《道德经》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不仅对我国后世历代君王治世起到重要作用,其影响力更遍布全球。其中,“无为而治”、“有无相生”、“上善若水”、“见素抱朴”和“虚极静笃”等思想精华深深影响着后人。古代新罗的花郎道是朝鲜三国时期兴起的半官方半民间组织,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思想内涵是朝鲜半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花郎道从组织制度到教育内容及修行方式等方面都与老子的“无为”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无为”的理念深刻浸染着花郎道思想的始终。探讨“无为”思想对花郎道文化的影响程度,是探索花郎道文化内涵不可或缺的视域。探索花郎道文化的建构背景和发展轨迹,对于研究韩国文化来说至关重要,这是本文最主要的目的。为了全面探索“儒佛道”三教对花郎道文化的影响,使我们在研究朝鲜三国时期的文化时有更加清晰的脉络和背景知识,研究道家思想对花郎道的影响是必经之路,老子“无为”思想更是重中之重;透过花郎道文化的内涵我们可以透彻地体会到“韩国型文化”构成的某些特色,因此本文从多个角度深度剖析“无为”思想对花郎道文化的映射,这是本文的现实考量。
一、花郎道与“无为”之“道”的共通性
老子从世界、个人、政治等诸多角度提出了独特的理念,但归其灵魂,当属“无为”二字。大众对于“无为”往往有所误读,认为“无为”即是“无所作为、不作为”,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这严重扭曲了老子的本意。我们认为,“无为”就是“不刻意而为”,是指人要遵循天地规律而活,做到顺势而为。从独立个体的角度讲,是指个人要跟从自己的本心;从环境角度讲,是指人类要尊重生态平衡;从政治角度讲,是指君主要做到不妄为、不非为。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于“道法自然”的关系正如同尖端之于基础,“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道德经》第七十三章),老子认为这种不相争而获得胜利,不善于言谈反而应对自如,不召唤而自动归顺的理想状态就是“天之道”,“道”是不需要刻意强求,于不经意间达成的自然而然。他主张为人君者要把作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民众既不过多索取,也不好大喜功,而是顺其自然,让民众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以达到上下平衡的和谐局面。
概而言之,在老子的运思逻辑中,“无为”只是践行“道”的态度或方式,即无条件地遵循“合规律性”的“真”;在此前提下,才能达成内在的目标追求,即极大程度地实现“合目的性”的“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即“真”与“善”的统一,恰是“道”之“无为而无不为”的根本特性充分而完满的体现。
花郎道的特质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新罗儒学家崔致远称花郎道为“玄妙之道”,在其《鸾朗碑序文》中,评价花郎道理念的践行者——花郎徒时所言:
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故金大门《花郎世纪》曰:“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①见崔致远的《鸾朗碑序文》,源自《天符经》,由崔致远先生刻于妙香山石壁;此事最早记载于《古记云》。
花郎道是讲求精神上高度契合,自然而然行事的组织。凡事不刻意而为,顺其自然地把握事态的规律。同时,真兴王作为一名佛教信徒,佛学对其影响不言而喻,他不仅大兴土木修建佛寺,斥重金铸建佛像,还有意提高新罗僧侣的地位,在记录百官和佛教徒的名讳时,还着意将佛教徒的名字记录在前。佛教对于其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如果说花郎道和儒教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着重致力于国家的现实生活方面,那么佛教则是宣扬为了世界的幸福生活以安抚人民的工具。从这种意义上说,佛教起了补充花郎道和儒教的重要作用。②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位封建社会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君主,在对花郎道的扶植过程中,并未将花郎道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设置成众僧云集的佛学组织,而是任由花郎道自由发展,郎徒每日游山玩水、唱歌跳舞,随心所欲、不受束缚。因此,花郎道中看似矛盾的特质亦有其原因。在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地方,恰好体现了老子的“无为”思想,也就是说,这些既矛盾又和谐的特点正是“无为”思想在花郎道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映射。这种映射即是“无为”之“道”与花郎道共通的价值取向——顺其自然,不刻意而为,进而无为而治。此即“无为而无不为”理念在花郎徒世界的践行。
二、“无为”思想对花郎道的影响
花郎道精神无疑受到了儒、释、道三种文化的影响,如崔致远所言: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实乃包含三教,接化众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③见崔致远的《鸾朗碑序文》,源自《天符经》,由崔致远先生刻于妙香山石壁;此事最早记载于《古记云》。
花郎道虽然看似随意,但亦有其自身的制度规约,最为著名的就是高僧圆光为其制定的“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有研究者认为在花郎道的制度中,对于道家的体现并不突出,更没有明确地表现出老子“无为”的精神;有学者就此总结,在花郎道精神中,起到主导作用更多的是儒家和佛家,而道家的影响仅仅体现在花郎徒的修炼与培养方式上。
对花郎道的这种认识,实际上并未深入到花郎道更为深刻的质性。崔致远所言周柱史之宗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是老子《道德经》中第二章中的话,也正是老子《道德经》的精髓所在。“处无为”是针对世人做事皆出自“有为”目的而言的,《史记·货殖列传》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人所作所为无不受到外在利益的驱动,都有极强的功利目的,这就违背了老子“道法自然”的初衷。老子言“圣人处无为之事”,并不是说不去做事,而是提出了一种处事方法,是要求人们顺应自然地做事情,即所谓“随缘自适”。而不是为了得到某些东西或为达到某些目的殚精竭虑、费尽心机,以至有损于生命,实际上即是强调在追求自我功利的过程中绝不能违背“道法自然”的规律性。这也就是康德哲学所主张的在“合规律性”的前提下,实现“合目的性”的功利自足。而“不言”的“言”可理解为“告诉、告知”,更可理解为“批评、判断”,是指对与外物的“有无”、“难易”、“长短”等都不做判断,因为宇宙中这些本身都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恶”就无法凸显“美”。世间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原始状态,并不应以人类的“言”为之定论。而体现到政治层面,则是为人君者不应该蒙昧百姓,以神话、迷信之类树立“真理”来欺人,以“真龙天子”等称号糊弄平民。花郎道中所涉及的“无为”精神,正是按照“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理念而切实践行的。
(一)“无为”对风流道审美体验的浸染
老子对于审美有其独特的理解:“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后人理解千差万别,有人认为老子说的是,“天下人都认为一件事物是美好的时候,这件事物就是不美好的;天下人都认为这件事情是善的,这件事情就是不善的”;也有人片面地理解为,“天下人都认为美好的东西是美好的时候,就是丑恶的;天下人都知道良善的东西是良善的时候,就是不善的”。其实结合语境并不难看出,老子所言实质上包蕴着深刻的辩证意识: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是美好的时候,说明有丑恶的概念产生了;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是善的时候,说明不善的概念产生了。花郎道初期两位原花的自相残杀,就形象地印证或阐释了老子的这一理念。真兴王在创立花郎道初期以“美”为标准选拔领导人,初衷是既能够拉拢郎徒的人心,又能够起到取悦郎徒的作用,亦有其道理;两位原花自相残杀的事实也验证了老子的另一个观点:“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如蔡美花先生所言:“世间的一切事物不可能纯而又纯,整齐划一”。①蔡美花:《高丽文学审美意识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审美具有其直觉性,托马斯·爱迪生曾言:“有一些不同物质的变化方式在一眼看到时心灵马上就判定它们美或丑,不需预先经过考虑。”在古代朝鲜,即使是生活在底层、未曾接受过文化教育的老百姓,也都具有审美能力。审美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思考和判断,也并不仰仗严密的逻辑思维,更类似于视觉、味觉和触觉等最基础的感觉。而且审美具有愉悦性,审美过程中,不管是什么类型、什么形式的审美,都能够带给人们愉悦的感受。音乐、美术、自然景物,甚至是美人,都可以让人觉得莫大的喜悦。晋人陆机在《日出东南隅行》中有云:“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与孔子的“三月不知肉味”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明美人不光好看还有巨大的审美价值,甚至能使人忘记饥饿。正因为对美的认知是最直接的认知,而外貌美又是一个人物各种美好特质中最直观的美,心灵美是最真实的美。花郎道是一个有思想的集团组织,对“美”的理解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的辩证思想。
(二)“教无言”模式对花郎世界的浸透
从中国先秦的“庠序学校”到夏商周的“大学”、“右学”,从汉武帝时期的“太学”到宋代的“官学”,都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而培养贵族子弟,并根据各人素质的不同选贤任能而设立的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的教师往往不是在政府任职的官员,就是有名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汉朝之后,政府对选用的教师提出了“通晓儒经”的基本要求,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是要用儒家思想中的“礼”来规范人民的思想,最终达到维护封建政权的目的。
然而,真兴王倡导的花郎道与其他的组织不同,它并不是简单地设立培训学校并任用官员为教师,教授郎徒知识,而是以“教无言”的方式塑造花郎徒。
花郎道的教育方式与其他封建制度教育方式有很大不同,“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其中的“道义”并非中国传统意义的上的道家思想,而是更倾向于古代朝鲜对于天神的崇拜。这种看似随意的游山玩水、唱歌跳舞、谈天说地,却为新罗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花郎道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和人才教育选拔制度”的主要形式。其成就是其他朝代的教育模式望尘莫及的,而其获得成功的主要驱动力就是道家“无为”理念潜移默化的浸润。
不管是以唱歌跳舞取乐也好,还是游山玩水也好,都体现出花郎徒绝非坐而论道的教育方式,而这种教育方式正是老子所提倡的“教无言”理念的具体实践。并没有人用强硬的手段告诉花郎徒要怎么做人、怎么做事,而是大家出于本心一起结伴而行。首先,唱歌跳舞和游山玩水,都是让人发自内心快乐的方式,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可以促使人们自愿聚集在一起,常聚会使人们产生感情和默契,这种感情体现在战场上就是一种其他规则无以替代的团结;其次,游玩虽然看似并无规矩,但实际上是有其潜在规则的,参与游玩的人一定默认并遵守这种规则才能更尽兴地玩耍。长此以往,花郎徒就会自然地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规则刻印在心里;再次,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下,互相传播知识更加利于接受和消化,“五戒”的制度在这种前提下更容易为花郎徒认同并遵守;最后,在山水之间的游历不仅能起到陶冶情操的作用,还对这些年轻人的意志和身体起到磨练的效果,在这样的锻炼下,花郎徒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更好地对抗敌人、保家卫国,进而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新罗各地的花郎道组织中出现了无数忠于国家、骁勇善战、为国献出生命的郎徒们,这种力量甚至渗透到统一三国的伟业中,使新罗一跃成为了主宰朝鲜半岛的统一大国。竹旨郎、斯多含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花郎将领,受到新罗自上而下一致的赞扬和好评,为新罗统一三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在与自然的浑融中确证自我
经过考证花郎道的修炼遗址,我们发现,花郎徒游山玩水所涉及的地方都是朝鲜的名山大川,他们在山水中修炼、祭祀,谈论古今。“永郎者,花郎之魁也,新罗时人也,率徒三千人,遨游山海,我国名山水无不寓名焉”。①一然:《三国遗事》,权锡焕、陈蒲清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这种脱离俗世的修炼方式与老子的“道法自然”的境界不谋而合。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人们所作所为出于私欲,往往纠缠于世间的俗事不能自拔,而在自然的山水间可以面对最真实的自己。这种接近自然的修炼,不是单纯的“取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的修仙修道行为,更侧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天地万物的关系。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意旨无非是人类依靠大地的作物赖以生存,大地依靠天气化育万物,天仰仗“道”的势态运行变化,“道”则顺其自然而成其所以然。道、天、地、人是组成世界的四大要素,而世界则是由四大要素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往深层里说,“人”在世界上是最弱小、最基层的要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最微末的组成部分,这与人类妄自尊大地自称“万物之灵”的现实是截然不同的。只有在面对大自然时,人类才能从心底感觉到自身的渺小,才能从宇宙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自身。
“物我同一”是风流道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方式,认为客观事物的本体和生命不在于其个体自身的发展与变化,而是独立个体间相互的融合。也就是说宇宙万物间真正守恒的定律是合为一体的整体性存在。人与自然要和谐地容纳为一个整体,从宏观来讲才是真正的和谐,才是花郎徒所孜孜以求的“游娱山水”、“相互切磋”的最高境界。因此,花郎徒只有在离开人类社会而重返自然怀抱时,才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和确证自我,对自然产生敬畏之情。这也是“游娱山水,无远不至”所生发的真正效用。
(四)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胸怀与气魄
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其意为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不能操之过急,应像细心地烹调一条小鱼一样,要安稳和缓地徐徐进行,下手准且动作轻,因为烹小鱼动作一大,鱼肉就会被弄烂。治理大国与此同理,追求徐缓、稳步地进行,这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不可估量。后世人们对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基本都认可“小鲜”为“小鱼”,“小鱼”同“大国”。对于领导者如何治理国家或者一个集体,能达到如此的胸怀,都是值得敬佩的。要知道,并不是每位君王都会有如此的操行,这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强力的治国才能。
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道理,第一要点就是老子的核心思想——无为(顺势而为)。在老子看来,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要充分信任和尊重人民群众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能独断专行,为了满足领导者一人的私欲而妄自作出决定,也不能过多地干预百姓的做法,做出一些逆天而行、有悖于老百姓的决定,而是用一种“以柔克刚”的态度慢慢地浸染人民的思维。这句话的第二要点是指——垂拱而治,这集中体现在花郎道的选拔制度上。选拔人才而非事必躬亲,简单说来就是领导者只需要能将恰当的人置于恰当的地方,使其起到最大的作用即可,而不需要对每一件小事身体力行。领导者不需要去管理组织里每一个人,作为最高统治者,只需要能够把握住根本原则,利用可用之人,就能事半功倍地将国家治理好。这与花郎道所运用的治理方法可谓“严丝合缝,异曲同工”。
然而,“无为”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做,“烹小鲜”最终的目的是“吃小鲜”,就是说统治者顺其自然的管理并不是不管。真兴王对于“烹小鲜”的化用可谓十分精到:在创建花郎道初期,他对花郎道内部和外部的事务不轻易出面,只有在两个原花相争致死时才站出来处理;而在花郎道壮大之后,他也没有过多地参与到花郎道的内部组织中去,而是直接领导“国仙花郎”,而之后的层层组织则是遵循“国仙花郎”的意旨,实质上也是真兴王的意旨。这与当时的新罗受到道家思想浓重的浸染密不可分,也是老子“无为”思想在花郎道发展过程中的集中体现。
三、结语
花郎道是儒、释、道三种文化有机结合从而加以延展的产物,但绝非只是三种文化融合的结果。“随着它的创设,为取消和防止豪族势力的纠合和反扑,把传统信仰和代表生活方式的风流道作为自己的理念”,同时还把业已传入的儒、佛、道三教作为自己的实践德育课目,“即在传统势力,即部族势力的形态上,赋予近代的国家概念,以建立新的国家并伸张国权”。①韩国哲学会:《韩国哲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它根植于朝鲜本土文化,以早期的天帝、天神等传说为源头,以朝鲜原有的风流精神为基础,又吸取了儒、释、道三方面外来文化的精华,创建了“无为”思想为暗、儒家“忠孝”思想为明,借助佛家“世俗五戒”的构架而传播的花郎道文化。学者们研究新罗花郎道,虽然都承认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但都将研究重点放在佛家和儒家对花郎道的影响层面,而忽视了道家“无为”思想对花郎道的潜在影响。
综上所述,花郎道作为一种特殊时期产生的集团组织的文化现象,其内涵值得我们一再探究。老子的“无为”思想对这个被称为“玄妙之道”的组织影响深远,不仅体现在其组织性质上,还体现到教育方式、修炼方法等诸多方面。虽然它的表现不如儒佛二教显性,但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对花郎道隐在的影响渗透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