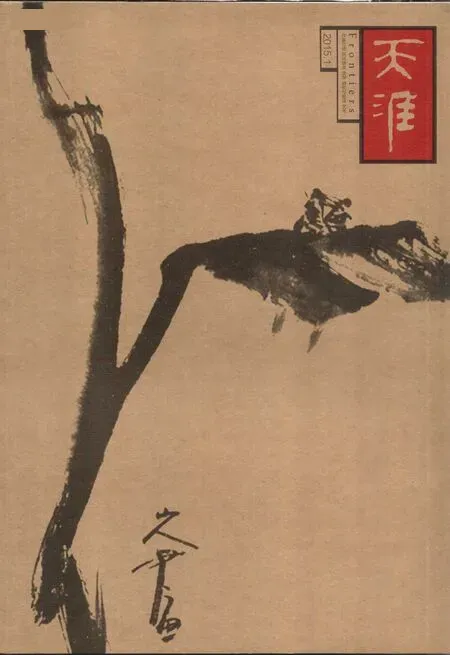种扁豆
刘庆邦
种扁豆
刘庆邦
景中海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打定主意要在自家责任田里种三分地的扁豆。
这扁豆不是那扁豆。
那扁豆通常是指夏季里的一种蔬菜,吃的是瘪瘪的、嫩绿的豆角子。人们把豆角子切成寸段,和肉片儿、肉丝一块儿放进油锅里炒,或做成扁豆焖面,味道都不错。豆角子里面一旦结了子儿,变成纤维化的老白背儿,人们就不再吃了。景中海种的扁豆是一种粮食。粮食粮食,变成粮才能食。这种扁豆与那种蔬菜性质的扁豆相比,其食用价值相反,人们吃的正是豆角子里面结的籽儿。等扁豆籽儿长得饱满了,结实了,打下来才可以吃。把扁豆磨成面,掺点儿麦面调成糊糊,在鏊子上摊成煎饼,或下进稀饭锅里当捞头儿,那是相当好吃。这时,豆角子不再叫豆角子,应该叫豆角子皮才是。豆角子皮干得变成了柴,只能和豆萁放在一起用来烧锅。“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地方豆子的品种不少,黄豆、绿豆、黑豆、白豆、青豆、紫豆、红小豆等,这些是从颜色上说的。自然界有什么颜色,几乎都可以找到什么颜色的豆子。不知是自然界赋予豆子各种各样的颜色,还是豆子模仿自然界的颜色装扮自己。从形状上命名的豆子有大豆、小豆、蚕豆、扁豆、鳖蛋豆子等。还有的豆子不以颜色命名,也不以形状命名,说不清名字是何由来。比如说豌豆、豇豆、莱豆、芸豆等。豌的是哪门子呢?芸是何所芸呢?不明白。
不管怎么说,在以前,各种豆子在地里都能看到,想吃什么豆子也不算什么难事。现在不行了,走遍大地小地,除了黄豆偶尔还看得见,别的豆子,几乎都难以寻觅。如果说以前地里的颜色是五颜六色,现在只剩下单一的黄色。想吃豆子只能吃黄豆,别的豆子就甭想了。确切一点说,生产队那会儿,地里种的豆子品种还比较多样。尽管人与人之间斗来斗去,各种豆子还可以和平相处。按道理说,生产队解散了,土地被分到各家各户,农业经济由集体经济、计划经济,变成了个体经济、自由经济,地里的庄稼更应该丰富多彩一些,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庄稼的种类逐渐变得单调起来。夏季里,满地里种的都是玉米。高粱、谷子、芝麻、大豆、红薯等,都不见了。收秋之后,地里统统种上了冬小麦。本来应该和小麦一起下种的大麦、豌豆、扁豆、蚕豆、油菜,也很少有人种。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庄稼人放着自由不自由吗?不是的,因为玉米和小麦的产量高,价钱贵,是产量取向和价值取向决定着庄稼人种什么,不种什么。说白了,是钱在发号令,人们听从的是钱老大的指挥。这么看起来,到任何时候,自由都是有限的,都是相对而言。钱和体制比较起来呢,好像钱这个家伙更厉害。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叫景中海的人,决意要种一块扁豆。
第一个反对景中海种扁豆的,是他的老婆。当他提出要种扁豆时,老婆看了他好一会儿,好像不认识他了一样。回想起来,老婆好久没这样看他了。是的,他脸上的皮一年比一年松,皱纹一年比一年多,有什么可看的呢!老婆问他傻了吗?他摇头。老婆把手摸在他脑门上,问他生病了吗?他否认自己生病。没生病,没发烧,为什么说胡话呢?景中海说他的脑子清亮着呢,一点儿都不糊涂,他确实想种扁豆。老婆让他到四面八方打听打听,现在还有谁家种扁豆!扁豆早就成了过时的东西,只有从坟里走出来的人才会想起来种它。景中海说,就是因为别人都不种了,他才要种。老婆一连问了他几个为啥,干吗非要吃扁豆呢?不吃那一口难道就不能活吗?景中海劝老婆不必着急,树上开啥花都是开,地里种啥庄稼都是种,犯不着为这点儿事着急。他说种扁豆并不是为了吃,主要是想种着玩。什么不好玩,拿扁豆种着玩,这种想法让老婆难以理解。老婆怀疑景中海没有跟他说实话,或是有什么事瞒着他。别以为两口子之间就没有什么秘密,嘴里的舌头可以互通,有的秘密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老婆说:老了,老了,你就瞎折腾吧,我看你连扁豆种都找不着。景中海说:这个你就不用管了,能找到扁豆种子,我就种;找不到,就不种,不就完了嘛!
不管种什么,都需要种子。拿种人来说,女人好比大地,男人身上的东西好比种子。如果只有土地,没有种子,土地再肥沃也是瞎搭,也长不出孩子来。种扁豆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把扁豆的种子找到了,播进土地里,种子才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收获新的扁豆。连景中海自己也没想到,为找到小小的扁豆种子,他真是费够了牛劲。他走了不下百里,问了不下百人,一粒扁豆都没有找到。附近的乡镇都有专事营销庄稼种子的种子站,他到每一个种子站都问过了,没有一个种子站卖扁豆种子。听说县里的职业技术学校有一个种子系,专门保留、研究和培育各种农作物的种子,他坐车到学校去打听,那里竟然也没有扁豆种子。凡是他问过的人,人家多多少少都有些惊奇。有人问他是不是在吃中药,要拿扁豆做引子。有人不知扁豆为何物,问他是不是豆子长扁了就叫扁豆。还有人调侃他,让他到出土文物管理部门问一问,因为有的墓葬陶罐里装有植物的种子,其中可能有扁豆。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种扁豆,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的想法是可笑的,不合时宜的,错误的。
景中海不大服气,不就是想种一点儿扁豆嘛,说什么错误不错误?以他几十年的经历衡量,人世上有许多事情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有些事情此一时大家都说对,彼一时却错了。还有一些事情,当时被判定为大错特错,过了若干时日,一下子变成先知先觉,无比正确。景中海没有放弃种扁豆的想法,就算种扁豆是一个错,他也要把错事做对,做到底。
还好,景中海终于在邻县县城一家卖杂粮的市场找到了扁豆。在众多杂粮中看到扁豆时,他的眼睛亮了一下,稍稍有些激动。但他把激动压制住,没敢明显流露。他怕卖扁豆的妇女看出他的激动,临时抬高扁豆的价码。但他一开口,还是问了一句有些可笑的话,他从敞着口子的帆布口袋里抓起一把扁豆问:这是扁豆吗?
妇女反问:你看呢?
我看是扁豆。
你看是扁豆,它就是扁豆。
景中海把手松开,任扁豆的颗粒从手指缝里流回口袋。他留了一粒扁豆,放进自己嘴里。扁豆很硬,他不可能把扁豆咬碎,品尝久违的扁豆的味道,但他愿意把扁豆在嘴里含着。问到扁豆的价钱时,妇女报出的价码并不贵,一斤扁豆比一斤小麦贵一倍多一点。景中海买了十斤。付完了买扁豆的钱,景中海才想起问妇女:你卖的扁豆是新的吗?会发芽儿吗?他懂的,任何庄稼种子里面都包含有胚芽,胚芽才真正代表种子的生机,如果种子放得时间过长,胚芽就会死掉,就失去了种子的意义。
妇女回答:我卖的是扁豆,不是扁豆芽儿。想发芽儿它就发,不想发芽儿它就不发,你可以拿回家泡在盆里试试嘛!
收完了玉米,整好了土地,紧接着,人们就开始种冬小麦。景中海找到了扁豆种子,心里有了底气,把准备种扁豆的三分地留了出来。他家的这块责任田是一亩三分,田的大头仍然种小麦,只用田的零头种扁豆。用来种小麦的一亩地用旋土机旋过了,也用租来的播种机把小麦种上了,而预留的三分地,他在用传统的手工方法精耕细作。种扁豆之前,他要给地里施些底肥。他所选用的肥料不是化肥,是自己配制的农家肥。经过在夏季高温条件下的发酵,农家肥已经腐化得很成熟。把成熟的农家肥捣碎,晾干,撒在土地的表面,再通过翻土把肥料翻在下面,就是底肥。用铁锨在地里撒粪时,景中海一点儿都不觉得粪臭,反而闻到了一种粪香,他好久没有闻到如此浓郁的香气了。粪撒均匀了,他举起三齿钉耙,一下接一下耙地。地表面是干的,一耙开却是湿润的,每耙开一钉土,像是翻开一页书,都让他感到新鲜。“书”里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有玉米白色的根须,有红色的小虫子,还有野生植物的小小块茎。太阳暖暖地照着,他耙地耙得一点儿都不快。耙到玉米的根须和植物的块茎,他拣起来,扔到地边去了。耙到小虫子,见小虫子还在伸懒腰,他把小虫子又盖到土里去了。有时他还会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攥一攥,看一看。在手里一攥,土就成了团。他松开手,重新把土揉碎,才把土放回地里去了。太阳往西边转移,把他的影子在东边的地上越拉越长,每举一下钉耙,像是直接耙到了天上。天是好天,要是把天耙破就不好了。再举钉耙时,他似有些小心,不把钉耙举那么高了。
往地里种扁豆时,景中海没租用播种机。只那么一小块地,不值得动用大机器。按说用三条腿的土耧耩扁豆是可以的,土耧在村里还能找得到,摇耧的技术景中海也没有忘记。可是,耧有腿不会自己走,需要用牛拉耧,还需要有一个人帮耧。所谓帮耧,就是人领着牛,跟牛一块儿往前走。帮耧嘛,他可以动员老婆帮忙。问题是,现在村里都不养牛了,到哪里找一头拉耧的牛呢。景中海的办法是自拉自唱。他用锄头把地开成垄沟,以手指代替耧腿,均匀地把扁豆的种子撒进垄沟里。他听老辈的人说过,不管撒什么种子,手都不能抬得太高,太高了种子落在地上会疼,甚至有可能会被摔死,不再发芽。他低头弯腰,手几乎贴着地面,轻轻地把种子往湿润的垄沟里撒。撒完了一垄沟,他用双脚相对着往沟里填土,踩实。他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就那么打着赤脚。赤脚踩在松软的土壤里,他觉得很舒服,脚很舒服,心里也很舒服。
扁豆种在地里,也像是种在了景中海的心里,他有些放心不下,一天三趟往地里跑。村里有人爱看电视,有人爱养鹌鹑,有人爱打扑克,他的爱好是往地里跑。没种扁豆时,他老往地里跑,地里种了扁豆,他往地里跑得更勤些。他明明知道,种子发芽有一个过程,五六天之后,种子才会冒尖。但他有些管不住自己似的,不知不觉就走到地里去了。这天下了雨,雨下得还不小,石榴树金黄的叶子被雨点打落了一地。他拿起一把雨伞,水一脚,泥一脚,还是来到了地头。地里的麦苗出齐了,一片喜人的鹅黄。可扁豆地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把土封上时什么样,现在原封不动,还是什么样。雨点打在伞面上丁丁响,他心里也有些打鼓:那个妇女卖给他的不是放了多年的陈粮吧?不会全都不发芽儿吧?心里打鼓归打鼓,但景中海不会扒开土,把埋在土里的扁豆看一看。好比在母鸡孵蛋过程中,人们不能把蛋壳磕开,看看里面的小鸡发育如何。倘是磕开蛋壳,会使发育中的小鸡受到伤害,停止发育,再也变不成小鸡。景中海多次见过母鸡孵小鸡,深知种庄稼和孵小鸡有着同样的道理,该等待时,一点儿都不能心急,必须耐心等待。
在一个雨过天晴的下午,景中海终于看见,他播下的扁豆种子钻出了芽尖尖。芽尖尖很细,细得像绣花针一样,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因景中海心里事先有了芽尖尖,心里有眼里就有,所以他一眼就把刚钻出地面的芽尖尖看到了。如同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又如同看到新生命的诞生,他难免有些欣喜,不停地搓着自己的手说:哎呀,出来了,总算出来了!他不怕扁豆的芽尖尖细得像绣花针,有了“绣花针”,就不愁绣出大大的花朵。他还想到了旗杆。不少庄稼刚钻出地面时都是细细的一根,像插在地上的旗杆一样。岂不知,插上“旗杆”的同时,“旗帜”就裹在了“旗杆”的杆头。随着“旗杆”升高,“旗帜”就会逐渐展开,迎风招展。他仿佛已经看见,扁豆棵子上的绿色“旗帜”越展越宽,正在长风中猎猎作响。
然而,扁豆苗子没能出齐。景中海播下的扁豆种子以十成计,长出的扁豆苗子大约只有七八成。这样一来,苗子显得有点稀,并有断垄的情况。与相邻的麦苗相比,麦苗密植合理,根茁苗壮,一点儿断垄的情况都没有。麦苗对扁豆苗子占了本来属于它的地盘似有些意见,并对稀不登的扁豆苗子有些看不起,仿佛在说:你们这些扁东西,不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嘛,不是已经走远了嘛,又回来干什么?在气势汹汹的麦苗面前,扁豆苗子似有些羞怯,有些抬不起头来,仿佛在说:对不起,麦老板。我们也知道自己过时了,不应该再回来现眼。可是,景大爷非要种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它们一起抱歉似地看着景中海,似乎在说:您要是想把我们毁掉,补种麦子还来得及。景中海赶紧为扁豆苗子撑腰打气,要它们挺起腰杆,好好活着,他决不会亏待它们。他曾担心扁豆种子存放太久,连一根扁豆苗子都不会出。目前扁豆的出苗率到了七八成,他已经很满足。他相信,等他把新扁豆打下来,明年再种,出苗率当是百分之百。
扁豆的叶子圆圆的,跟豌豆的叶子差不多。长出一些嫩绿的叶子之后,扁豆棵子就不再往上长,几乎进入一种静止状态。一直到严寒袭来,天下大雪,扁豆都保持着静止状态。通过静止,它摆脱外部世界的纠缠,开始进入自己的内心,在苦练内功。同时它的根须尽可能地往地层深处扎,并进行横向伸展,以吸收丰富的营养,积累足够的能量,准备迎接严寒和冰雪的到来。
景中海刚给他的扁豆施过一遍苗肥,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就下来了。扁豆不但不怕严寒和冰雪,对下雪好像还很喜欢。雪朵子落在扁豆的叶片上,每落下一朵雪朵子,叶片都像是轻轻点一下头,说好,好着呢!远望一片雪茫茫,天地之间变得混沌起来。回头再看他的扁豆,每棵扁豆上方都积了雪,如同开着一朵朵硕大的白花。渐渐地,地上白了,村庄白了,扁豆也被白雪所覆盖。看不见扁豆时,他一时有些紧张,这可如何是好,大雪把扁豆压坏了怎么办?他几乎要动手清除压在扁豆棵子上的积雪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紧张和想法是可笑的。麦盖三床被,头枕白馍睡。扁豆和麦子是一样的,下雪等于给扁豆盖上了被子,被子盖得越厚,扁豆就越暖和。他要是把被子掀开,岂不是把扁豆冻着了!他自己这次下地也没有打伞,没带任何雪具,不知不觉间雪落满一身,几乎成了一个雪人。
过春节时,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回来了。儿子的腰包鼓鼓的,说话也很气粗,看来把钱挣到了。儿子见到村里不少人,他们都说到了儿子的爹所种的扁豆:你爹太逗了,他种了一块扁豆;大家都劝他不要种扁豆,他就是不听,真不知道他是咋想的;你爹真是一根筋啊,真是一个怪人啊!如果只是一两个人这么说,儿子也许并不放在心上。地既然分到了各家各户,种什么,不种什么,那是各家的自由,谁都管不着。可村里许多人都这么说,儿子就不得不想一想,不得不跟爹谈一谈,问问爹到底是怎么想的。
爹,你都成了咱村的新闻人物啦!
啥新闻人物?
扁豆呗,扁豆新闻人物呗!
他们是笑话我。爹的样子似有些害羞。
他们为什么笑话你呢?
我也说不好。
你跟别人不说实话,跟我还不能说吗?
没啥不能说的,我就是种着玩。咱这里几十年不种扁豆了,我想看看地里还长不长扁豆。
你是特别想吃扁豆吗?
不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吃啥都行。
那,是不是我爷爷跟你托过梦,让你种扁豆呢?
你爷爷死了四十多年,他自己恐怕都变成梦了,他从来没给我托过梦。
儿子替爹算了一笔账。种一分地的麦子可打上百斤,种一分地的扁豆呢,连二十斤都打不了。而麦子的价钱跟扁豆的价钱差不多,就算扁豆稍贵一点,也贵不了多少。种扁豆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很不划算。
咱家里存的小麦有七八千斤呢,就算地里两年不打粮食,也饿不着人。
儿子的眉头皱了起来:我说的话你怎么就不明白呢,问题在于,别人都不种扁豆,只有你一个人种,别人就会认为你不正常。
爹不服气:谁不正常,我正常得很。别人都不种扁豆,我为啥就不能种。我种的是自家的地,出的是自己的力,流的是自己的汗,碍着别人什么事了。依我看,说我不正常的人,才是真正的不正常!
啥时候有啥时候的潮流,种庄稼嘛,还是随大流好一些。你今年已经把扁豆种上了,非让你拔掉也不好。明年不要再种了。
爹没有说明年是种还是不种。
过罢年,残雪化尽,春风吹过来了。得到春天的信息,扁豆棵子的精神为之一抖,迅速把浑身的旧绿换上了新绿。扁豆换新绿,不像人换衣裳,人由棉衣换单衣时,需要从外到里,一层一层把衣服脱掉,才能换上单衣服。扁豆从旧绿换新绿时,无须把原来的叶子脱掉,只须发一下内功,说一声变,根部储存的新鲜汁液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扁豆的叶子上,使扁豆旧貌换新颜。经过对比,景中海看出来了,扁豆换成新绿的叶子是发亮的,像是充了电一样。还有,扁豆棵子上的毛孔是张开的,仿佛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张力。他想摘下一片叶子,在手指上捻一捻,看看能不能把手指染绿。但他没舍得摘。
高粱开花,玉米开花,凡是庄稼,没有一样不开花。扁豆自然也不例外。扁豆开白花,花朵小小的,跟桂花的花朵差不多。景中海蹲下身子把鼻子凑近扁豆的花朵闻了闻,没有闻出什么明显的香味儿。春天来了百花开,以前地里花是很多的,粉嘟嘟的豌豆花,黄灿灿的油菜花,还有各种各样的野花。现在不见了豌豆花,不见了油菜花,连野花也很少很少。景中海不能明白,花应该越来越多,为什么会越来越少了呢?是不是因为人太多了,花就少了呢?扁豆开花不是把花举起来,举高,而是开在叶子下面,远看只见叶,不见花,只见绿,不见白,一点儿都不显眼。可金子再小也是金,花朵再小也是花,谁能说扁豆花不是世上的一种花呢!
一些小虫子爬过来了,在扁豆花上爬来爬去,显得很兴奋的样子。景中海隐约听人说过,扁豆花也分公母,公母之间也要授粉,授粉正是小虫子帮助完成的。小虫子从公花里爬出来,沾了一身花粉,又钻进母花的花心里,母花才会受孕。按这样的说法,小虫子担负的是传媒的角色,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活跃的性器,于扁豆不可或缺。
糟糕的是,扁豆叶子上也生了虫子。那些虫子跟人身上生的虱子差不多大小,只不过他们是绿色的,跟扁豆叶子的颜色一致。它们吸取扁豆叶子的汁液,连吸边排泄,把好好的扁豆叶子弄得黏乎乎的。这些家伙都是害虫,如果任它们糟害,这些扁豆很快就会蔫掉,景中海种扁豆等于白种。好在景中海早有准备,他用竹篮子从家里提来草木灰,轻轻撒在扁豆的叶子上。扁豆生了虫子,他本来可以用农药喷雾的办法,把虫子消灭掉。农药喷雾要简单得多,也省事。但农药难免喷在花朵上,并残留在扁豆里,那就不好了。他决计用传统的方法消灭可恶的虫子。草木灰细细的,绒绒的,他一撒,灰白的草木灰就把正在大吃大喝的虫子们覆盖住了。须知草木灰里含有碱性,对皮肤薄得透明的小虫子有很强的杀伤力。小虫子们喊了一声不好,快跑!它们刚要开跑,觉得头皮一麻,就失去了知觉。
从地头路过的村长,看见了景中海在扁豆地里除虫子。因景中海在村里当过几年民办教师,又曾教过村长,村长还是习惯把景中海喊景老师。村长说:景老师,这一次你要发财。
景中海笑笑,说今年的麦子长得不错。
我没说麦子,我说的是你种的扁豆。
扁豆不太好,苗儿出稀了。
稀点儿没关系,稀麦稠豆闪死人,扁豆种稠了反而不好。再说了,物以稀为贵嘛!
这个稀不是那个稀。
怎么不是那个稀,我看就是那个稀。道理明摆着,别人都不种扁豆了,只有你自己种,等扁豆打下来,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我倒没想着拿扁豆赚钱。
景老师,这个事你就不用瞒我了。无利不起早,不为赚钱你种扁豆干什么!你放心,等扁豆打下来,我不会跟你要扁豆吃。等你把扁豆卖了钱,我也不会跟你借钱花。
景中海没有再对村长解释什么,村长有村长的逻辑,不管他怎样解释,都不可能改变村长的逻辑。他又抓了一把草木灰,均匀地撒在扁豆叶子的叶面上。
麦子抽穗,扁豆结角。扁豆结的角子是集体性的,在扁豆棵子的分杈处集成一撮一撮。村里的年轻人大都没见过扁豆,出于好奇,有人到扁豆地边看了一下。他们没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说扁豆不就是扁的嘛,再种它也长不圆。
乡里有一个通讯员,平日里爱给县里的小报写点东西。不知他听谁说景中海种了扁豆,带了笔记本和照相机,专门到村里采访景中海。他用照相机对着将要成熟的扁豆左照右照,照了全景,又照特写,一再称赞景中海种的扁豆是独特的风景。之后,他又拿出笔记本,向景中海提了一连串问题:你以前种过扁豆吗?别人都不种扁豆了,你为什么要种扁豆呢?你种扁豆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特别爱吃扁豆?还是要拯救扁豆这一濒临灭绝的物种,保持乡村生态的多样性?
景中海连连摇头,对通讯员的话表示听不懂,说他种着玩呢。
你不识字吗?
识几个,不多。你认识的,我不一定认识;我认识的,你也不一定认识。
那不一定,你说一个字我听听。
景中海摆摆手,没有说。
你不想出名吗?
出什么名?
我把你种扁豆的事写成稿子,往报纸上一登,你就成了名人。你一出名,说不定乡长也会接见你一下。
开玩笑。
麦子用机器收割,扁豆用镰刀收割。景中海割扁豆时,割得小心翼翼,生怕弄炸了扁豆的角子,让扁豆子儿散落在土里。他割得一点儿都不着急,割完一垄两垄,就坐在地头歇一会儿。太阳当头照着,白蝴蝶翩翩地飞,地里都是扁豆棵子的气息。景中海有些走神,想得远一些。土地是不变的,恐怕几千年几万年都是这个样子。变的是人,是人的想法。人想种什么,地里就长什么。种瓜就长瓜,种豆就长豆。这块地几十年没种过扁豆,但土地好像并没有把扁豆忘记,他一种,扁豆就长了出来。好比土地的肚子装着很多很多歌,就看人们点什么。不管人们点哪首歌,土地都唱得出来,而且唱得还不错,动人肺腑。
新扁豆打下来,景中海用文火熬了半锅扁豆稀饭。扁豆是玉红色,熬出的稀饭也有些发红。他一边喝,一边感叹:多少年没喝扁豆稀饭了,一喝还是这个味儿,真好喝!老婆也在喝扁豆稀饭,他问老婆:味道怎么样?
老婆的评价不像他那么高,说:你说好喝就好喝呗。
我问你自己的感觉。
还行,就是红得有点吓人。
村里有一个人在北京工作,他秋天回老家看望母亲时,母亲一心想让他往北京带点什么。他什么都不想带,说全国各地有的,北京都有。
有人提供信息,说景中海种了扁豆,他可以带一点扁豆回去。如今扁豆可是稀罕东西。
扁豆?扁豆还没有绝种吗?真的还有人种扁豆吗?他小时候也喝过扁豆稀饭,对扁豆好像有些兴趣。
母亲去景中海家买扁豆时,当儿子的特别对母亲说:一定要给人家钱,人家说多少钱一斤,就是多少钱一斤,千万不要跟人家讲价钱。
景中海坚决不收钱,说多少钱一斤他都不卖。他用一只塑料口袋装了四五斤扁豆,说想吃就拿走,要是给钱,扁豆就不能拿走。
母亲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扁豆拿走了,说:就算欠着你的一份情吧。
到了秋后,景中海还会种扁豆。
刘庆邦,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远方诗意》、小说集《梅妞放羊》《响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