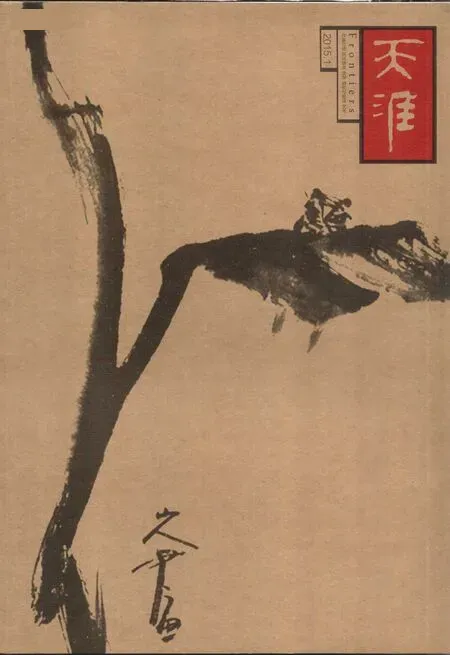种玉米记
陈照田
种玉米记
陈照田
买种
我对购买玉米种子的记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那时县里设有专门的机构——种子公司。各个镇都有种子公司的派驻机构,叫种子站。主要是销售玉米种,别的种子少有人买。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种子公司日渐式微,种子站就更不用说了。
清明前,村干部会通过村里的大喇叭下通知,大致是这么说的:各位村民请注意,种子站已到今年的玉米种子,明天是我们村的购买时间,请及时购买!种子有类,譬如:鲁单X号、潍单X号、掖单X号。如果我的记忆和理解没错,鲁单就是山东农科所配的种子,潍单则是潍坊农科所配的、掖单是掖县(今称莱州)种子公司配的,至于后边的序号,是每家单位种子更新换代的排序号。掖单的生长期最长,要一百一十五天才能成熟,自然玉米穗大,产量高;不过喜水喜肥,只能种到上等田里才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如种到中低等田里,反而收不了多少粮。有个品种产量相对低,但生产期却短,最短的生产期只有七十二天。这些种子偶尔会种到山坡田里,更多则是备用种子,如果错过正常点种季节,生长期长的种子就无法点种,只能用这类种子作补救措施。因为哪怕晚种一个多月,它们依然有充足的时间成熟。还有一百天左右生长期的玉米种子,产量略低生产期最长的玉米,不过点种在中等田里,收成不会比点种在中等田里的生长期最长的种子产量低。另外,生长期短几天,可以提前收获,这样几块田里的玉米就可以分期收获,不至于同时成熟,忙不过来。
父亲不会骑自行车,不能跑到二十里外的种子站买种子,就安排我们兄弟几个去。开始是安排大哥,接下来是安排二哥,等我长到十四五岁后就由我负责。买种子的人多,有几个村的人家在同一天购买,很早我就往镇上赶,有时还要排大半天队才能买到。买种时,我遵照父亲的吩咐,分别购买好几种玉米种子。
在记忆中,我家每年都会浪费两三斤生长期最短的玉米种。每次父亲都会心痛,那种子可是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来的。第二年,父亲还是要安排多买几斤。
父亲说:“宁肯浪费点,也不要冒险呀,不然到时饭都吃不上!”
下种
立夏前后,是点种玉米最好的时机。具体哪天点种玉米,要看老天的安排。家里的几亩薄地,只有一亩左右的水浇田,可以按农时点种;其他田地需要有场“及时雨”才能合上农时。地里过于干旱时,雨小了也不行,那样种子埋进土里发不了芽,或者发了芽还没钻出地面就渴死了。要有场大雨才好,崮前村人叫“透地雨”。小的时候,我隐约知道美国在我们脚下的另一边,听到大人说下了场“透地雨”,我从街上走,就有些担心,唯恐不小心,脚像踩进淤泥里那样,把整个人儿陷到美国去,再也回不了家。等我缝上开裆裤,七八岁的年纪,觉得自己牛皮哄哄的,雨落过后,我喜欢跟在哥哥们的后边,看他们扛一把镢头去田里狠狠往下刨几下,不见一点散土,便跑回来首先向父亲报告:下了场“透地雨”!父亲听后,满脸洋溢着笑容,比雨后初晴的天空还清亮。等田里的土不再沾脚,父亲便扛起镢头,带着家里人去点玉米。农时不等人,此时整个村外的田野里,都是忙着点种玉米的人。
准备点种玉米时,父亲或姐姐会把玉米种提前浸泡在清水里几个小时,这样种子发芽更快。浸泡种子时,父亲将那些漂在水面的干瘪种子用手捞出来,连头也不抬,一扬手便扔到院子里,几只懒洋洋的鸡,同时一个激灵箭一样扑过去,抢食那些干瘪玉米,吃完又踱回原地,恢复那副懒相。父亲告诉我,那些干瘪种子是绝不能种到地里的,万一发不了芽就耽搁了秋天的收成。
点玉米是在麦田里进行。先从离村子最近、最肥沃的田地里开始,到离村子最远、也最贫瘠的山坡地结束。麦子早已“吐穗”,颗粒也已饱满,只是还没泛黄。玉米就点在麦田的垄上。哥哥在县城做活,没时间点种玉米,大多时候是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去点种玉米。父亲倒转身子,站在窄窄的田埂上,面朝我们,脚踩镢头,镢柄立在他胸前。两边是齐腰高的小麦,他尽量缩缩身子,怕自己踩倒了麦子。父亲往手心里吐口唾沫,双手攥紧镢柄,身子一弓,人倒退着往田地深处行进,同时用镢头一下一下在眼前的田垄上刨出一个个小坑。如有微风吹来,绿色的麦浪翻滚,麦穗便正好抚摸着父亲握镢柄的手臂,麦芒一会儿就把他的两条手臂划刺得通红。父亲把坑刨得距离、深浅、大小相等。对刨玉米坑父亲非常讲究,别人家半大孩子都可以去刨坑,我家大多是父亲刨坑。二十多岁的大哥偶尔有时间来点种玉米,刨坑时父亲都会认真检查,一会告诉他要把坑刨在一条直线上,一会指挥他要把坑刨得深浅一致……
我怀里抱着一个大瓢,一个小瓢,大瓢里装着化肥,小瓢里装着玉米种子。小瓢放在大瓢里面,也可以说放到大瓢上面。两个瓢我只用一只手抱着,腾出另只手抓点化肥撒到坑里,再捏两粒玉米扔到坑里,如果感觉种子不够好,还要放三粒。化肥是日本产的复合肥,偶尔也用美国产的磷酸二铵。我两只脚踩在坑两边,既不能踩到刚从坑里刨出的土,又不能踩倒麦子,还尽量跟上父亲刨坑的速度。我身后,姐姐把刨出的土用脚再蹭到坑里填平,用脚踩实。父亲刨坑时保持着不急不缓的节奏,刨出的坑形成一条笔直的线,且坑与坑之间距离相等,坑的深度、大小像是从一个模子做出来的。现在想起来,父亲是把种地当成艺术来做的,他的每项劳作都不逊于一个艺术家。邻居从我家田边经过,无不对父亲刨的坑赞叹几句,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讲究这些。当然,父亲刨坑的速度明显比别人慢很多,说具体一点,大概要慢四分之一吧。
父亲在刨坑时,还要时不时注意检查我和姐姐的劳动质量。如果我离他的距离超过四米,父亲就会停下来,他决不让坑和土过久地被日晒和风吹。他要求刨出的坑要及时加肥、点种,并迅速填埋好。按他的说法,这样才能保持好坑里的水分,种子在坑里才更舒服些。我觉得种到我家田里的种子是幸福的,遇到这么一位考虑周全的农民侍候着。父亲站着休息时,顺便指点我们的劳动:每个坑里的化肥要加得一样多,化肥要撒在坑底,不能撒到漏斗形的坑壁上,要散开,不要成堆,种子也要扔到坑底,还要将两粒种子一左一右分开,等间苗时就不至于拔掉这株苗影响到那株苗;填埋土时要将坑填平,还尽量要将刨出的土全部填回去;田里过湿时土不能踩得过实,以免把土踏成泥巴块,种子拱出地面就要费很大力;土里水分不很多时,填埋后还要将土用力踩实,以免风吹进坑里,加速水分蒸发。为保持水分,父亲甚至不惜再挨个坑踩一遍。
我总感觉父亲没用的规矩特别多。旁边田里的叔父则和父亲完全相反,他是自由的,不受规矩所累的人。譬如:他刨坑特别快,一镢头刨一个坑,坑的大小不计、距离远近不管,一排坑望过去,弯弯曲曲像蚯蚓屎,根本不在一条线上。加肥、点种也都随便往坑里扔,根本没什么讲究。有时堂哥加肥、点种的节奏跟不上,叔父把刨了一两百米的坑全晾在那里毫不在乎,还是继续刨。叔父的种地哲学是差不多就行,粗糙打理庄稼和精耕细作的产量相差无几。其实我也这样认为。特别是两家同样大小的田地,叔父家很快就点完玉米,跑到另外一块田里点种去了,而我家还剩一大片没完成,这时我的心里就对父亲有一百个不乐意,一千个不服气。想起叔父对我说的那句话:“你爹哪是在点玉米,他是在插花!”我很想接过父亲的镢头,学着叔父的样子刨坑。事实上,直到我二十多岁,父亲都认为我不具备刨坑的本事和能力。有时实在忍不下去,就在地里和父亲顶嘴:“我二叔刨坑多快,也没那么多规矩!”父亲便一脸的不屑:“你二叔那也算刨玉米坑,也就是种子刚刚露不出土来,哪有这样种地的?”我不服气地说:“你种地本事高,也没见咱们比我二叔家粮食收得多!”我不知这句话是否刺痛了父亲,父亲竟一时无语。的确那些年,叔父家的玉米长得并不比我们家的差,甚至还好过我们家的。当然这与他用的化肥有关。堂哥在外边做事,叔父家的经济条件比我家好。我家点玉米用的底肥是日本复合肥,叔父家用的是美国磷酸二铵。二铵比复合每袋高二十多元。叔父凭借化肥的力量,击败了父亲的精细劳作。这也让我时常拿出来当例子,抗议和刺痛父亲。不过,却无法使父亲改变他的劳动作风,他依然保持着惯常的认真。
点种玉米的底肥十分重要。有一年,我家在八亩地点玉米,由于化肥少带了一大把,结果最后有七八个坑里没有化肥可加。这时差不多中午了,就剩几个坑了,不值得耽搁工夫单独跑几里路回家拿化肥,于是在父亲的默许下,就只放了玉米种子。记得埋土时,大姐还跟我说了句:“到时候看它们长成什么样!”过了一个多月,到了给玉米施肥的时候,我发现那几株玉米苗明显比其他玉米苗小很多。我感觉特别对不起它们,施肥时单独给这几株玉米加了双倍的化肥。我想,这下总该可以了吧!你可要争口气了,到时候要比它们都长得壮实。秋收时,去田里掰玉米,别的玉米株都比半大孩子的手腕粗,高大健壮的躯体上,长一个又大又饱满的玉米穗;这几株玉米却只有拇指粗细,长得又矮,病怏怏的,倒是也长了一穗玉米,却小得可怜,掰下来,撕开包着的穗子皮,骨上就星星点点地长了几粒玉米。这相当于没有收成。
这几株玉米算是被我废掉了一生。
有了这个经验和教训,我家也明白了“合垄”上邻家玉米苗长得壮的原因。点种“合垄”上的种子时,也会多加底肥。“合垄”就是两家田地的边界线,因为属两家共同所有,别的垄上点种的都是单行玉米,合垅上点种双行:每家分别在垄上自家那侧点种一行。两行玉米挨得紧,相距至多二十厘米。从田头经过,只要看到有双行垄的地方,就知道是两家田地的边界线。两行苗挨得太近,这家的一行如果开始长得快、长得高,另一家的那行基本就被“欺”下去了,阳光、水分总被高大的那行占先。到收获时候,长得慢的那行明显玉米穗小很多。在人多田少的崮前村,家家户户都很在乎哪怕一点点的收成,对合垄上玉米苗便都很重视。以往,我家跟邻居同时在合垄上点种玉米,可邻家的玉米苗总长得快,他家的收成自然好过我家。之后,我家也多施底肥,原来的成长秩序被改变了。到了收玉米时,我就偷笑,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秘密。
锄小锄
玉米苗露出地面没几天,麦子便收割了,玉米作为配角的日子结束,正式成为田地的主人。这段时间大家都忙着抢麦收,对玉米的关照并不多。麦子割走,田里亮堂了,小小的玉米苗身体弱,还保护不了自己的领地,草儿便借机蓬勃生长。这时,便要抽时间锄草。用崮前村人的说法,这是过头遍小锄。锄禾未必日当午。那个时间日头太毒,容易中暑,除非万不得已,崮前村人中午很少锄禾,都是天刚放亮就去锄地。我学锄地是在十多岁时。那时哥哥姐姐都忙着割麦打场,田里的草趁机疯长,跟玉米抢水分、夺营养。这事瞒不过父亲的眼睛,父亲对我说:“明天你跟着我去地里学锄地,小锄容易学,又不太费力,头遍小锄就交给你了!”天刚蒙蒙亮,我就被父亲喊醒。父亲从挂在屋檐下木橛上的大小四把锄头中,将两把月牙样的小锄头拿下来,递给我一把,自己扛一把,带着我去了最远的田里。点种玉米后,父亲就把锄头拿到村里的铁匠铺,让铁匠重新淬过火,更加锋利了。
天凉爽爽的,禾苗上挂着晶莹的露水珠。躲避了一天太阳光的强烈照射,加上夜晚清露的滋润,禾苗比昨天要精神得多。父亲让我站到他身边,示范着把两垄禾苗锄进去半米,然后叉腿站在禾苗垄上,胯下是一高的禾苗;让我站在他旁边另一条垄上,垄与垄相距八十厘米左右。腿脚碰到玉米苗,便有露水珠溅到裤脚上。所谓的过头遍“小锄”,就是只锄离禾苗最近的地方,确切地说是禾垄上的草。锄小锄不能急,更不能躁,下锄之处全在禾苗四周,锄要绕着禾苗走,心急会锄掉了草,顺带也把苗锄掉了。父亲开始锄地,左脚向前迈一步,略躬下身子,两手握锄柄,左手在前,右手在后,把锄头伸到离前脚五十厘米的地方,接着左手用力一压锄柄,锄头便斜斜插进地里,右手迅速往后拖锄柄,锄头便在不及一寸深的土下平行穿越。父亲直到将锄头拖至左脚前,锄柄也被半侧身子的父亲拖到身体右侧,才结束动作。父亲边示范便说:“左手既要压住锄头,又要撑握锄头在土层里的深浅。锄下得太深了,草还会和上面的土粘在一起,土里的水分够它活三五天,三五天后它又把根扎到下面的土中。草的命强着呢!锄下得浅了,只锄断草颈,伤不到草根,明后天草又长出来了,跟没锄一样。”
锄地其实也大有学问,下锄深浅要恰到好处。父亲锄地的本领很高,他的锄头所到之处,草纷纷倒下。不久,那些草就在晨风中变蔫,无须太阳的曝晒,也基本没有活的可能。父亲的锄头擦着玉米苗儿经过,不放过一棵草,也不会伤到一株苗。
父亲说,这三锄完成,算“一路锄”。说着,父亲直起身子,左脚没动,抬起右脚迈到前面,握锄的两手也趁机换了位置,右手握在前,左手握在后。这次是用右手压锄头并掌握尺度,左手拖锄柄,锄柄拖至身子左侧,下锄的顺序也变为从右到左。三锄完成,再迈左脚步,又换回原来的姿势。
在点玉米时,每个坑里都下了两粒种子,基本上也都会长两株苗,很少有不发芽的种子。两株苗到时是要拔掉一株的,所以割断或踩断一株苗也并无大碍。最怕的是把两株苗都给弄断了,或者弄断的是两株苗中出息的那株,又恰好被父亲发现,父亲就会狠狠地把眼睛瞪过来,让我十分紧张。这时,我的锄头偏偏不争气,又把一株好苗给锄断了。父亲怒道:“让你来是锄草的,不是让你锄苗的!”父亲没有读书人的方法,对子女从不说教,而是直接生硬地斥责。如果再割断一株好苗,父亲干脆说:“你看看地里哪些苗子好,全给捡着锄断算了!”听着父亲的话,我握着锄头的手就更加小心。
人的两只手做起活来,都是有一只手灵巧,一只手不灵巧,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很难做到左右开弓。譬如,我喜欢用右手拿东西,做一些细致的活,左手只是起辅助作用,用左手在前、右手在后握锄的架势锄起地来比较顺手,很快掌握了技巧,下锄既深浅适度,又不会伤到玉米苗。换成右手在前,左手在后时便感觉非常别扭,每一锄的动作都非常慢,锄头在垄上还找不到准头,很容易就会锄断玉米苗。父亲锄两垄,我锄一垄,如果再跟不上父亲的速度,就有点说不过去。年少也气盛,我尽量用顺手的姿势去锄,以跟上父亲锄地的步伐。父亲发现后,马上制止,并坚决要求我按他教的方式变换姿势去锄地。我说用另一个姿势握锄很别扭。父亲严肃地说:“习惯后就不别扭了!刚学锄地,哪个姿势都手生,很容易学会用两个姿势锄。如果现在用一个姿势锄,等习惯了,一辈子都学不会两个姿势。‘一顺架’锄地,会多受很多累!”父亲还举了一个只会一顺架锄地的邻居作例子:总用一个架势锄地受累不说,放在旧社会,不管去给人家打短工,还是去给人家当长工,掌柜的根本不用。
用一个姿势锄地的确是很累,我便强制自己按父亲教我的姿势去锄。两垄地锄完,就顺手多了,用另一个架势锄地也轻易不会锄断禾苗了。
太阳出来后,禾苗上的露水便一下不见了,再不用怕露珠打湿裤脚,天却热起来。等父亲又锄完一垄地,说收工回家吃早饭时,太阳已经有五分毒辣了,我看到自己脸上、身上的汗珠不断滴落在脚下,瞬间便消失在地里,脑子里想起那句诗:汗滴禾下土!即刻有了透彻的理解。父亲锄到田头,蹲下身子,拾起块石子,将沾在锄头上的土打磨得干干净净,也命令我把锄头打磨干净,然后起身一同回家。我发现锄过的田垄上,那些草已经被晒死,即使马上下场大雨,生还的也不多。走在回家路上,我和父亲似乎没有多少话可说,我跟在父亲身后,相距三四米的距离,清晰地看到父亲肩上的锄头,在太阳下闪着亮光。
饭后,我开始一个人下田锄玉米。父亲拿一个塑料水壶,灌满凉开水,递给我说:“渴了就喝壶里的水,以后每次下田要知道带水。”天热,锄地时汗流得更多。每天,我上午带一壶水,下午带一壶水,水全喝光,变成汗水浇灌着脚下禾苗。从我学会锄地开始,我对禾苗便有了真正的感情,每株苗儿都感觉非常亲近,下锄时不小心再割伤到苗子,便有了心疼感。一个人在自家的责任田里锄地,我感觉自己长大了,可以像哥哥姐姐们一样独当一面。扛着锄头下田或者回家,碰到村里的人,我都感觉很自豪。等我把家里所有的玉米田全锄完一遍小锄后,麦收也基本结束了。
小麦收割后,田中所有的水肥都由玉米苗独享,苗儿便蹿得飞快,等我把一遍小锄锄完,禾苗已经明显高了很多。苗儿长得快,草儿也长得快,等锄完最后一块田的时候,第一块田里的草又长起来了。“庄稼人儿不得闲,面朝黄土背朝天”,根本容不得人休息,又开始锄第二遍小锄了。
第二遍小锄和第一遍没什么两样,只是天更热了,锄地流的汗更多了。玉米苗长高了,锄地的难度加大了。雨季来了,也经常会有“过路雨”,在田里劳作时,忽然天上飘过一块黑云,人还没回过神来,雨便噼里啪啦落下来,把人淋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找地方躲雨找不到,收工回家吧,一会儿天就放晴了,干脆在田里穿着湿透的衣服继续锄地,到了吃饭时间才回家。
从记事起,父亲的腿就有风湿病,现在想来,应该是长期在这种劳动环境下造成的。
抡大锄
锄了小锄,还要锄大锄。父亲说,过去庄稼把式种地,一季玉米收下来,要过三遍小锄,两遍大锄,还要根据天气情况去“找草”,这样才能保证地里的草不跟庄稼争抢水分和营养,玉米产量也会更高。“找草”跟锄地差不多,都是扛锄头下地锄草,所不同的是,锄地要沿着一条田垄从头锄到尾,除了锄掉杂草外,还要担负松土、保墒的作用。锄一遍地就是给庄稼松一遍土,同时上边松动的土层和下边的土地形成间隔,在炎阳下不容易挥发水分。找草就是扛着锄头顺垄走,哪里有草锄哪里,没有草的地方不管。父亲又说:现在的人迷信化肥,不按老规矩办事了,省掉了好多工夫。这倒不假,我小时候,大部分人家是锄两遍小锄,锄两遍大锄,等我大些了,又减掉了一遍大锄。
顾名思义,大锄就是比小锄大很多。锄大锄的主要目的是铲除玉米行距间的杂草。小麦割完后,玉米还没长起来,就给杂草提供了大量的生长空间。小锄只是锄掉了田垄上玉米苗近处的杂草。田垄间小麦割掉后尚有半多高的根部留在地里,这块宽阔的地带,也是杂草争抢着占领的地方,如果不是太旱,只几天时间,绿绿的杂草就能覆盖那些留在田里的小麦根。必须要尽快锄掉,不然一场大雨落下来,地里又粘又湿,两天之内动不了大锄,那些草就疯长起来,把玉米地变成大草原。哪家的田若锄晚了,别看就几天的事,草就争去地里的许多养分,把玉米苗欺得瘦弱了很多。这块较大地盘的除草工作,小锄是力所不及的,只能留给大锄来完成。
锄大锄的活不复杂,从技巧上讲,甚至比小锄还容易操作。
锄大锄要不断地把锄头甩出去,因此在崮前村锄大锄又叫“抡大锄”。
抡大锄时,锄头离玉米苗尚有些距离,所以不用担心锄到禾苗,倒是比锄小锄爽快很多。可抡大锄是个力气活,大部分由年轻力壮的男人来做。一条大锄十多斤重,抡起来很耗力气,田里又有割倒小麦后留下的小麦根,锄头在土里往后拖时,这些小麦根和草根一起阻拦,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们一起锄倒。往后拖锄头时,锄头在地里,需一点点地才能把锄头从前方拖到跟前,随着锄头的拖动,人的整个身体都带动得一颤颤的。除非家里缺少年轻力壮的男人,才由女人或者并不结实的男人抡大锄。
抡大锄的壮汉子,最喜欢的行头是,赤着膀子,穿一条短裤,脖子上搭条毛巾。人在田里,太阳直直地照在身体上,皮肤晒成瓷实的古铜色,透着健康和雄壮。天热,活累,每个人浑身上下满是汗水,汗水从脸上、背上往下流,随着劳动的节奏,在阳光下显得晶莹的汗珠,雨滴样纷纷落在田里。那时年少的我,一直觉得这是劳动的壮歌,是自然、人、玉米组成的最纯朴的乡村画卷。对一个渴望长大的乡村少年,对他们除了敬重外,更想早一天加入他们的行列。父亲身体也不错,上边又有几个哥哥,我根本没有机会去摸大锄。我长到十七八岁时,每天总觉得身体里有使不完的劲,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父亲才让我扛着大锄,跟着哥哥下地。那一刻的我,有种暗喜,感觉自己终于长成一条汉子了。
我学着哥哥样子,光着膀子,穿条短裤,脖子上搭条毛巾,锄头上挂了一塑料桶水就要出门。父亲对我说:“你的皮肤嫩,经不起太阳晒,千万别不穿上衣,否则把身上的皮都给晒暴了!”我不情愿地又穿了件上衣。我在哥哥旁边的一垄地里,学着他的样子挥锄、拖锄,汗水把全身湿透我也顾不上,很快就掌握了抡大锄的要领。此时,我才感觉到上衣黏在身体上极不好受,而且抡起锄头来也不方便,便忘了父亲的叮嘱。我直起身子,摸起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身上的汗,脱掉上衣,顿时舒服了很多。我很有底气地望了望四周那些在自家田里抡大锄的人。看到有人往我这边看,我便很潇洒地把锄头抡出去,摆出一副老庄稼把式的样子锄起地来。
上衣脱掉果然爽了许多,肩膀、脊背似乎都摆脱了束缚,身上的力气也增加了不少,只是汗水丝毫没有减少,我能感觉到背上的汗珠不断滚到裤腰里或者地上,俯身挥锄时,只要稍加注意,还能看到脸上和胳膊上的汗珠摔在脚下的地上,一下便被田地收起了。锄一段时间,脸上的汗水浸入眼眶,淹得眼睛涩涩的睁不开,才直起身子再擦把脸。一会儿毛巾就湿得能拧出水来。
半垄地没锄完,我已经渴得不行,跑到田头,拿起放在禾苗底下的塑料桶咕噜噜喝一通水,接着再锄。离太阳落山还有一个小时,一桶水早已被我喝光。西边的太阳温柔了许多,禾苗也精神了许多,我却再也没有锄地的兴致。握锄的手已经磨起了几个大大的血泡,手脖子和腿肚子有点发抖,胳膊和腰酸痛得厉害,再加上干渴和早已有的饥饿感,让我变得有气无力,锄地的动作明显慢了很多。刚开始,凭着兴奋劲和虎劲,还能紧紧跟在哥哥身后锄地,现在一会儿就被哥哥远远甩在后边。哥哥知道我累了,便让我自己先回家。我虽有些不好意思,累、饿、渴还是逼迫着我提前回家了。
天完全黑下来,哥哥才回来。我问哥哥:“田里还有人锄地吗?”他说:“当然有了,泥瓦匠三叔,比我们早去地里一个小时,差不多我回来后,他还要锄半个小时。”我说他不饿吗?哥哥说:“三叔最有办法了,他带的水是麦粒做的稀粥,喝水的同时也能填下肚子,所以别人锄一下午都饿得心慌,他一点没事!”那一刻,我特别佩服这个能干的泥瓦匠三叔。
吃饭时,父亲看着我的背说:“让你穿上衣你不听,看把背晒成什么样子了,今天晚上有你好受的!”累得疲惫不堪的我没在乎父亲的话,饭后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半夜,身体的疼痛让我醒来,此刻我才感觉到背部和肩膀上的皮肤火辣辣地疼,像被热水浇了一样。我用手小心地摸了一下,感觉皮肤没有破,便放心了不少。两天后,我的背上和肩膀上褪掉了厚厚一层皮。
锄二遍大锄时,恰值崮前村的雨季,接二连三的雨落下来,田里粘得锄不了地,等玉米长到半人高时,大锄也就抡不起来了。崮前村还有句俗语:入了伏,挂大锄。意思是,进入伏天,大锄便要挂到院子里的墙上闲起来。锄挂了,草要清除,只能是人钻进玉米地里,蹲在地上用手慢慢把地里的杂草拔出来。这更不是个轻松活。人蹲在玉米田里,整个被玉米苗藏了个严严实实,一点风也吹不到,真是又闷又热,再加上蜷曲着身子,腰关节和膝关节更是酸痛得厉害。实在受不了,人起身从玉米地里站起来,虽然是在硕大的阳光下晒着,但还是感觉浑身上下舒服很多,甚至能感受到有凉爽的风吹在身上。有一年暑假,我跟着父亲蹲在玉米地里拔了十多天草,每天都累得不成样子。至今回想起来,都感到浑身上下有些酸痛。
在玉米地里拔草,也能拔出些故事。我们邻居家的二小子有点犯傻,下地拔草竟然找错了地,在人家的田里稀里糊涂拔了一天草。那天,我看到他从别人家的田里拔草出来,问他怎么在别人家地里,他才恍然大悟的样子说:“这玉米长起了,我都认不清哪是我们家的地了,今天算是亏大了!”然后匆匆走了。我看到他那副样子,差点乐得笑出声来。可第二年,那户人家的三女儿嫁给了他,我才明白玉米地里也生长爱情。青纱帐般的玉米地,藏下了许多或美或丑的事情,这些只有玉米们和那些当事人知道。
施肥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施肥也是要看天气,一般是在一场大雨过后,趁地里潮湿,把化肥施到苗上,好让水分把化肥融解掉,利于禾苗吸收。地里旱,是不能施肥的,否则化肥会把苗烧死。雨来得早,玉米苗长得未及大人的腰就施肥,雨来得晚,玉米苗长得超过大人的胸部才施肥。
施肥比较简单。雨过天晴后,崮前村的每户人家把收割小麦前后买好的化肥,用一辆独轮车推上两袋去田里施。一个人用镢头在玉米苗根部附近刨个坑,一个人端着化肥跟在后边往坑里施肥,边用脚把刨出的土再填到坑里。化肥大多都是县化肥厂生产的碳酸氢铵,也有少数人家用齐鲁石化化肥厂生产的尿素。尿素比碳酸氢铵贵不少,虽然用量也少些,但依然是家庭条件相对富裕的人家才买。尿素的好处是,挥发性不大,化肥加到坑里不用土填埋,可以减轻些劳动量。
施肥方法也有少许不同。大多人家是在两株玉米之间刨一个坑,一次施肥两株玉米,也有很少人家是每株玉米刨一个坑,一次施肥一株玉米。譬如我家。两种不同施肥方法最明显的区别是:前一种方法比后一种方法施肥速度快一倍。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我和哥哥们都曾试图说服父亲,采用两株苗一个坑的方法施肥。父亲坚决反对,父亲说:“这样化肥离禾苗远,吸收养分不方便,侍弄庄稼不能马虎,要周到!”多少年来,父亲一直坚持着单株玉米施肥,为此,每年施肥我们家都比别人家多出几个工。
掰玉米
一般来说,玉米成熟了才开始掰玉米。而在我的记忆中,有很多年,玉米未完全成熟就已经掰玉米了。
家中粮缸里的小麦越来越少。收小麦时,家里早就没有玉米了,因此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吃小麦蒸的馒头。再这样吃下去,过年蒸馒头的面都没了。玉米穗长大了,姐姐每天下午都拿着一个荆条筐,到按日期算算最早成熟的那块田里,找老相点的玉米穗,从穗的上边将包着的皮扒开一点,用指甲掐下玉米粒。如果玉米粒很容易流出汁液,便再把玉米皮包好回家。有时,我会跟着姐姐去地里,我知道这样的玉米最适合掰下来煮着吃。有家庭富裕些的邻居,偶尔会掰几穗回来煮了吃,我也沾光吃过。可姐姐不会掰,父亲更不允许。父亲认为这样掰掉吃是浪费粮食,这些玉米还能增加收成。在他的眼里,只有大面积收玉米时,那些成色不好,又来不及成熟的玉米才可以煮了吃。
当姐姐用指甲掐玉米粒流不出汁液时,便把这个玉米用力掰下来,装到筐里。确切地说是拧下来。还没成熟的玉米不太好掰,更多时候需要两手抓着玉米穗转几圈才能拧下来。拧够一筐,我和姐姐用一根木棍抬回家,将玉米剥掉壳,院子里马上弥漫着玉米的清香;那些玉米壳则晾在院门前的街上,告诉从此处经过的人们,收玉米的日子已近在眼前。当晚,我跟二姐被安排剥玉米粒。玉米还没完全成熟,玉米粒还紧紧地抱着中间的玉米骨吸收养分,努力再让自己丰满一些。骨和粒连得紧,只能用手指一颗两颗地往下玉米粒,有时把粒子烂才弄下来。粒和骨里都含有大量水分,被烂的玉米流出汁液,把整个手弄得湿湿的,起玉米来就更难了。
剥好玉米粒,天已经很晚了,大姐才带我和二姐去石碾上碾玉米。石碾在街上,是崮前村人共用的,白天每磐石碾都忙,需要碾粮食的人都要提前去排上号,有时太阳刚出来就排了号,直等到天黑了才能轮到。排号也简单,人不用在那里等着。只是去石碾那里问正在推碾子的人:“你家推完碾子是谁家推?”正在推碾子的就按顺序告诉你他推完碾子是哪家推,哪家推完又是哪家推。然后你说也给我们排上,他便把你排在刚在说的最后一家的后面,再有人来排号就再排在你家后边。乡村的夜是黑的。除非春节前的一个月,石碾几乎是日夜不停地有人用。平时,夜深了碾子就闲下来,不用排队。只是黑漆漆的夜里,有些恐怖。如果哥哥们白天干活不是太累,也来陪着推碾子,就没什么可怕的,只有姐姐带着我,就有些害怕。害怕的好处是,推起碾子来特别用力,白天推着有点重的碾子现在被推得飞快,恨不得快把玉米碾完跑回家。玉米碾碎,再用水泡在两个大瓦盆里,第二天一大早就用院子里的石磨研成玉米糊糊,姐姐就用这些糊糊在铁鏊子上烙玉米煎饼。两大瓦盆玉米糊糊,姐姐要整整用鏊子烙一个上午。接下来,每两天要烙一次玉米煎饼,每次都是两大瓦盆玉米糊糊。缸里的麦子终于可以保住留到春节用。
玉米越来越成熟,玉米穗的绿皮渐渐变黄,姐姐再去地里掰玉米,就直接挑选皮最黄甚至泛白的玉米穗掰下来。每次掰完玉米,姐姐都不忘把掰掉穗的玉米秸割倒。这是父亲教的。把掰掉穗的玉米秸割倒,第二天如果发现还有没有穗的玉米秆站在地里,就说明有人来偷掰过玉米,否则你根本无法知道是不是有人来地里偷过玉米。那些年,也的确有些手脚不干净的女人,借去地里拔草喂羊的机会,偷掰几个别人地里的玉米穗。自己掰了玉米穗不割倒秆子,别人偷掰了你家的玉米穗,你也分不清到底是自己掰的还是人家掰的。
等田里的玉米穗的皮都变成白色,崮前村的人们就正式掰玉米了。村里的人几乎倾巢出动,推着独轮车,拿着镰刀,提筐涌到田地里,村里只留下年幼的孩子和上了年纪的老人。
父亲把早收拾好的独轮车推到院子,一边绑一个大条筐,条筐里又扔了几个化肥袋子、两个提筐和一把镰刀,就带着家里人下地了。条筐和提筐都是新的,大热天歇伏的时候,父亲去山上割了几捆荆条,请人帮忙编的。到了田里,有人提筐,有人拿化肥袋子,从田头沿着两行玉米往田那头掰玉米,掰满一筐或一袋子玉米,便提到地头,倒进独轮车的条筐内。装满独轮车,哥哥就开始往家里运。父亲则用镰刀把掰掉玉米穗的玉米秆一棵棵割倒,按顺序一堆堆放在田里。玉米秆被大片大片割倒,田野里忽然变得透起气来。
哥哥往家运,我和姐姐则继续在田里掰玉米,掰满一筐便倒到田头,好等哥哥返回来时直接装到车上。玉米穗熟透了,有些肥硕的玉米穗都挣开包裹,把头露出来,将金黄的玉米粒子呈现在人们眼前。正所谓瓜熟蒂落,此时的玉米穗也非常好掰,用手攥着玉米穗的上部,用力往下一掰,随着清脆的“咔嚓”声,玉米穗便脱离了株体。株体也略有干枯,不再像往日那样绿得水汪汪的。随着离田头越来越远,我和姐姐每掰满一筐玉米穗,提到田头都要费很大的力气。有些人家把独轮车推进田里,以方便把掰下的玉米穗往车上的条筐里装,免得一提筐一提筐地提着往田头走。父亲不允许独轮车推到田里,怕把田地压硬了,压疼了,影响来年的收成。
掰玉米是要穿长衣长裤的。玉米株长大后,刀形的叶子周围布满了锋利小毛刺,人穿行在茂密的玉米地里掰玉米,身体随时会触碰到玉米叶上,没有衣服的保护,胳膊和腿难免被玉米叶划出一条条浅浅的血痕。初秋的太阳依然有点毒,人在地里劳作,没有一丝风透过来,汗水很快就将我全身衣服湿透。掰玉米时,我尽量躲避着玉米叶子,脸上还是划出了几条血痕。脸上满是汗水,汗水浸到血痕处,会有丝丝的疼。这种伤倒不重,晚上睡一觉,便什么事也没有了。
我们家掰玉米时,遇到皮泛青的玉米穗,除非它小得可怜,留着也没有多大出息,才可以掰下来扔到筐里;凡长得还算可以的父亲都不允许我们掰。父亲说:让它们在株上再长几天,就会饱满瓷实很多,反正离刨地种麦子还有段时间。于是,我们家掰过玉米的田里,总是插花一样留着几十株或上百株没掰的玉米。直等到要种小麦了,父亲才安排我们去把地里剩下的那些玉米掰回家。的确,又多长了几天的玉米穗,把皮和株上的营养和水分又吸收了不少,变结实了很多。记得有一年,有块田里的玉米熟得晚,要急着种麦子了,玉米穗的皮还泛青,父亲舍不得掰,便带着家人,费了好大劲,用镢头把玉米株一棵棵刨出来,每棵的根部都留着很大的土块,然后再用独轮车搬回家,把玉米株竖着顺院墙摆放好,直到种完小麦才把玉米掰下来。其他人家,为了省却麻烦,大多会一次性将玉米掰完。
掰玉米的时候,高大的玉米株把人全隐藏在地里,仿佛只有自家家人在田里劳作,等掰了半天玉米,看到旁边的玉米地里也有大片的玉米被割倒,才知道其实大家都在收玉米。晚上从田里回家,一路上,大片大片的田里都已经掰完玉米,玉米秆也割倒在地里,会感觉田野一下子瘦了很多。
玉米掰回家,大多数人家除了节日吃顿面粉做的水饺,春节蒸几锅白面馒头外,直到来年收了小麦,才有两三个月时间吃白面馒头。有时为了省口粮,小麦收下来后,父亲还会用小麦去换成玉米。玉米煎饼没有馒头好吃,但一斤小麦可以换近两斤玉米,这样就可以保证口粮。
实际上,一年四季,崮前村的人是靠吃玉米生活。
剥玉米
把玉米搬回家的当晚,我们家的晚餐必定是吃煮玉米。这也是崮前村大多数人家的选择。
提前从田里回家做晚饭的姐姐,从院子里小山状的玉米堆里,捡选出那些个头又小,皮又泛青的玉米穗,把包在外边的皮褪掉。这些玉米穗多数只是在玉米骨上稀疏地长了几行玉米粒,少有几个是粒儿密密排满玉米骨的,更有甚者只是在饱含水分的玉米骨上零星长了几个玉米粒。对只长几个玉米粒的,姐姐便收拾一下扔进猪圈,让那头每顿都吃糠的猪改善下生活。猪也很识趣,以飞快的速度把整个玉米穗吃到肚子里,一点残渣也不留。其余的玉米穗,姐姐放到大铁锅里用水煮。这些玉米粒能掐出水的玉米穗最适合煮来吃。煮熟的玉米香气四溢,弥漫着整个院子,甚至跑到街上。很多人家的锅里都煮了玉米,整个村子都飘浮着玉米的味道,收工后从田里回家,走到村口就嗅到煮玉米的清香,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吃完煮玉米,无论白天的劳动多累,全家人都要围坐在院子里的玉米堆前剥玉米。剥玉米就是把包在玉米穗外的皮剥去,好让金灿灿的玉米粒完全露出来,方便晾晒。秋忙的时间很长。崮前村人说:“三秋不如一麦忙,三麦不如一秋长。”意思是三个秋收都没有一个麦收忙,三个麦收都没有一个秋收长。这段时间白天都要下地干活,没时间剥玉米。掰回家的玉米堆在院子里,要不及时剥掉玉米皮,如果下场雨,大堆的玉米无法摊开晾晒,不几天就会导致玉米发霉。剥玉米的活不重,但也颇麻烦,用的工夫并不比掰玉米少,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把活儿化整为零,每晚剥三个小时,过不了几晚就把玉米剥完了。剥掉玉米皮,再下雨也不怕了。
剥玉米也有讲究。玉米穗外边包了几层皮,先将最外边又粗糙色泽又不好看的两片皮剥掉,随便扔在地上,里面又白净又细腻且柔软的几片玉米皮就露了出来,将这几片皮剥开,留三两片连在玉米穗的尾部,用它把两穗或四穗玉米系在一起。其余的全部扯下来。最外层的玉米皮全部用花篓提到街上晾晒,晒干后就是烙煎饼最好的烧柴。里面的皮则一小捆一小捆扎起来,每捆小腿粗细,摆在院墙上或院子里又干净阳光又好的地方晾晒,到时几分钱一斤卖给收玉米皮的人,或者自己编坐垫等。
有月亮的夜晚,院子里被月光照得亮堂堂的,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剥玉米也带着几分愉悦。自家院子里有说有笑,邻家院子里也有说有笑。大人们喜欢谈论玉米的收成,譬如哪块田里的玉米穗个头最大,哪块田里的玉米穗长得差些,跟去年比较今年的总收成是多还是少。也会盘算着明天的劳动安排,是去大田里继续掰玉米,还是把猪圈里的粪清理出来,抑或是将玉米秆清理出来准备刨地。秋忙时季,农活多,头绪多,是需要规划和盘算的。亮如白昼的夜晚,勾引得小孩子则有点坐不住,剥会儿玉米,就借口清理堆积的玉米皮,用柴篓把那些当柴烧的玉米皮收起来,背到街上,也趁机在街上游逛一下;或者在院里跑来跑去的,把那些扎成小捆的玉米皮放到院中的矮墙上,总之不想浪费了这个明亮可爱的夜晚。等到月亮从树冠左边转到右边,人才进屋睡觉。
没有月亮的夜晚,院子里漆黑一片,就只能摸黑剥玉米。这样的夜人也是沉闷的,大家都不说话,黑暗里只听到每个人剥玉米皮时发出的唰唰声。有时父亲来了兴致,更多的则是想提高大家剥玉米的积极性,会边剥玉米边给我们讲故事。父亲没读过书,讲的也无非是武松打虎、孙二娘开店、薛刚反唐等几个老掉牙的故事,更多则是讲他少年和青年时的经历。我们都听得入迷,忽然父亲说:“也该睡觉了!”大家才惊醒过来,一起停下手中的活,全部支起耳朵听邻居院里的动静。邻居家有口马蹄表,我们家的作息时间,除了靠父亲看星星月亮和太阳外,就是参考他家的起床时间和睡觉时间。邻居院里已没有剥玉米的唰唰声,大家就赶紧清理战场,把该弄到街上的玉米皮背到街上,然后把院门关严,将其他玉米皮也整齐地搬放到该放的位置,便开始挂玉米。
田里的玉米越来越少,各家院子里的玉米越积越多。剥完的玉米已经把檐下挂满了,就又往院子里的树杈上挂;树杈上挂满了,就再绕着树干从离地两尺的地方,一直盘到几米高,一棵本来碗口粗细的树,突然变得两个大人都合拢不过来,且变成金灿灿的;树干盘满了,就在院子里的空地上,竖几根腿肚子粗细的木头柱子,再绕着一根根柱子盘满玉米;还有直接把玉米搭在院墙上的,像给院墙戴了顶帽子,墙也突然间高出了不少。剥玉米时,还有些不小心把玉米皮全部剥掉了,只剩下一个干干净净的玉米穗,这样的玉米无法挂在树上,也不能搭在墙上,就找个朝阳的地方,放几块石头和砖,把玉米垒在石头上,或者直接垒到窗台上。整个院子一下子被玉米挤窄了很多。
这时的崮前村,已经完全成了玉米的世界。走在村里的街上,低头瞅瞅,脚下到处踩的是玉米皮,抬头望望,各家院子里的树上都挂满了金灿灿的玉米,院子的墙头搭的不是金黄的玉米,就一定摆放的是雪白的玉米皮。
崮前村迎来了一年中最丰腴的日子!
陈照田,公司职员,现居广东佛山。已发表小说、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