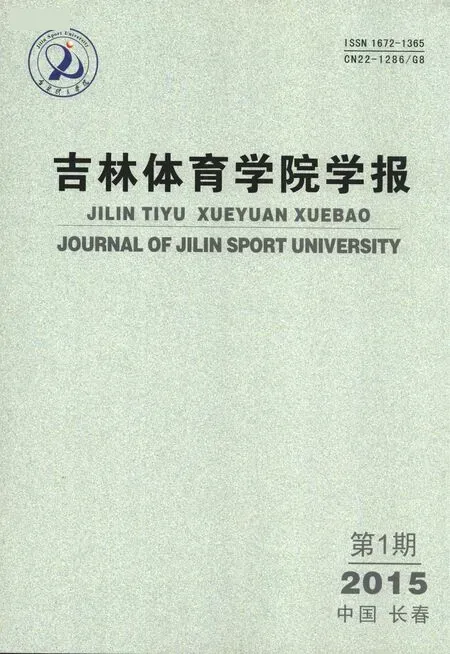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化发展政策的文化人类学展望
李晓通,陈永兵,李开文
(文山学院体育学院,云南文山 663000)
◀民族传统体育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化发展政策的文化人类学展望
李晓通,陈永兵,李开文
(文山学院体育学院,云南文山 663000)
文化人类学一直立足文化视野,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其中的“文化区域研究”理论可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化发展政策提供理想的研究范式,以此为视角,结合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结构论等可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未来发展政策进行思辨性综合研究,结论认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特定的区域与社会结构下,传承了一种以促进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为基本宗旨的生态文化伦理,折射出生态化开发的政策逻辑,以此为参照结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进行政策制定,必将进一步促进民族生态文化创造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健康发展。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化发展政策;文化人类学;生态伦理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中积累形成的稳定的体育文化,体现在健身、养生、娱乐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体育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反映并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文化,并通过社会心理结构及其他物化媒介得以世代相传[1]。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式样,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相对稳定的区域文化根基,也有与时俱进的后发优势,这些都是民族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基础。目前,我国学者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化开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化发展的相关政策研究还比较薄弱。结合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通过田野调查,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文化渊源、传承方式、体育与其他资源的结合形式等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化发展政策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文化人类学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政策研究的学理基础
1.1 少数民族文化视野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目标、范围和方法
文化人类学主要立足于民族和地域,从人的文化性追溯人类特质的源头与演变,探索人及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规律,为人类发展及人类社会的进步服务,和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共同构成相对完整的人类学学科研究体系。文化人类学是一个高度开放和综合性学科,和社会学、哲学及民族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有着深刻而广泛的联系,主要以田野研究为主,并对民族志进行分析,其理论成果与实证研究方法都能运用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政策研究之中,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保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1.2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体育生态化开发政策研究的意义
文化人类学把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视为一个动态的整体,在形成学科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特有的学科认识论主题,即将某一人群的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和看待,使人类自身适应环境,不断修正自己的社会文化系统和自然环境,调整人的行为习惯,提高生存适应性,促使社会持续发展,其最终目的就是在科学认识人类自身的基础上,使人类更好的适应和改善环境,提高生存质量,促使人类社会和自然更和谐、更美好。在民族文化视野中可以认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没有脱离人、文化和环境这一宏观范围,这和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化发展研究的要求是一致的。德奥学派理论渗入美国人类学届形成的“文化区域研究”理论为区域性体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总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能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多的智慧,对人类生态的科学认识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人类学视域下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生态化发展政策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2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生态文化元素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2.1 我国少数民族史志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渊源分析
从众多的民族史和田野民族志中不难看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文化的文化渊源在两方面不容忽视。第一,生产劳动及自然探险。体育的本质是人以自我身体活动为基本活动方式对自身自然的改造,体育和生产劳动具有活动过程的同构性和活动性质与对象的互补性[2]。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生产劳动是人生存的物质保障,也保证了人的体力、心理调适、生活节律与适应能力等在健康水平上,是人类认识和尊重自然生态规律,改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前提,具有原始生态文化特征,自然探险也可认为是生产劳动的补充。第二,民俗与民族宗教信仰。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载体,宗教常表现为某种仪式,表现了一定的民族社会和文化记忆,包含了少数民族对自然、图腾、祖先及自身生命规律等的认识,传承了最朴素的自然观,也构建了少数民族体育政策的精神基础。无论从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共时性”还是“历时性”的视角都不难发现,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经过了漫长的进化和传播过程,这个过程中出现多个文化中心和多条传播与融合路径。
当然,除生产劳动自然探险、民族宗教外,民族艺术、民间游戏和民族传统医学等也可认为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渊源,也具有显著的生态文化属性,尤其是民族艺术。程卫波等研究认为:体育与艺术尽管属于不同性质的人类活动,但一切体育运动和艺术创造活动皆始于身体,也必然要还原和服务于身体的根本需求[3]。在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生活中,这些是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永远不可缺少的文化支点和表现形式,促进了众多运动项目的产生与发展,展现了人、文化、环境之间和谐稳定,孕育了朴素的原生态体育思想,也不断强化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这些都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底蕴和力量,为文化产品开发和文化服务提供了重要基础。
2.2 文化人类学基本理论视野下的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路径
在少数民族语言中没有“体育”一词,体育往往与其他形式的文化活动相融合[4]。因此,不管从何视角认识其传承与发展的文化载体都应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所以在文化人类学的结构理论、功能理论、图腾理论、区域理论和传播论等研究范式下,以下四种传承式样值得注意。第一,多种文化的和谐共生的“文化结构”传承。一直以来,体育文化都夹杂在民族的其他文化元素中,缓慢地传承和发展着,节日、宗教、民俗、竞技等文化活动形式为体育文化的最常见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常以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为依托,体现了社会与文化的深层结构,也孕育了体育生态文化的萌芽。第二,以各种仪式为载体的“基本动作”传承。仪式是各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要以节日、祭祀、民俗等为载体,其中的思想性、艺术性、宗教、民俗及其他文化内涵要靠人体动作来表现,这些动作可看作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成分,也是民族社会历史的记忆和生态文化的活态展现。第三,以地域、民族及自然环境为基础的“项目组群”传承。从地域环境来看,每一个具有特殊地形地貌特征的自然环境都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生态和文化系统,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构筑一种相对特殊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各文化元素之间具有互动性,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系统化、有序化、人性化发展提供可能,也促进了文化生态的和谐。第四,以民族精神内核为依托的“民族特色”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表现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心理和民风民俗的一种最直观的手段,早已烙上了原始自然生态的烙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民族文化的营养,塑造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也以最直接的方式印证了人类学中的结构理论。
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文化结构”、“基本动作”、“项目组群”、“民族特色”四方面很难被认作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全部形式,但却直接体现了在当时的政策框架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然传承机制和基本功能,也符合文化人类学中“濡化、社会化与涵化”的基本规律,在不断传承、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孕育了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元素,为传统的民族体育政策的解析提供参考。
2.3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过程折射出的“政策”哲理
政策可认为是一种由人、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多种元素共同构成的社会“契约”,体现了国家、地方政权的构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某些自然法则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政策在具备阶级性、时效性、表述性等特征的同时,也应融合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之中,体现当时政策制定者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认识和把握,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明显的宏观逻辑特征。翻开我国地区民族史,不难发现,自汉代以来,国家对民族的统治几乎都体现出中央集权和地方民族自治的结合,今天看来相关政策中的科学部分仍值得人们去思考,尤其到康雍乾时代民族政策已很宽松,基本实现改土归流,因俗自治,促进了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5]。民族政策和民族宗教等社会文化元素共同构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支配了民族生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的结合,其文化渊源和传承方式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规律,具有自然生态特征,在漫长的民族发展历程中深刻影响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结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暗合了当时的“国家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也固化和传承了生态伦理。
在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政策的制定既要反映对生态文明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也要对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能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前瞻性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体育概念产生以前的时代,民族传统体育生态文化元素是客观存在的,当时的国家政策对民族体育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生态文化思想和伦理价值的保护与传承,有力保障了国家和少数民族区域的稳定、和谐、团结与进步,对现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未来政策的文化人类学审视
3.1 以促进文化生态和谐为目的的生态化发展就是惠国惠民的宏观政策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观点认为,在一定区域内,文化和生态环境之间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为因果,而且资源是文化要素的基础之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地区的休闲文化支配下的符合生态规律的特色资源,但在传统的政策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一定的传统生态文化属性,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稳定,这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态化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也将逐渐成为新时期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有力支撑。在特色经济和区域发展问题上,魏靖晖等研究认为,我国民族地区必须走一条能使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得以协调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制度建设上应注意人力资源开发、科技融入、推动区域合作交流、完善区域投资制度、完善改进社会保障制度、改进自然环境资源利用制度[6]。所以,在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新的历史时期,制度建设应体现在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开发中,尤其应结合地方实际,以环境保护为基础,以产业发展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导向,以传统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为主要保障,创造性地制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这也是国家文化政策的客观要求。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生态视野来看,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人类学研究不仅融入了生态学观念和理论方法,拓展了研究视域,同时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加强了对与环境因素相关的文化现象的研究[7]。这些都将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化发展应该是在传统生态文化元素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在一定科学政策的引导下,尽可能通过合理投资、科学规划,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和当地文化生态的和谐,促进文化产品的创造,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由此可以认为,生态化开发是最经济、最科学、最长效也应是最富创造性的发展理念,也将是一种最惠国惠民的政策,不仅总结了过去,立足现在,还展望将来。
3.2 文化深层结构支配下的生态化发展所必需的具体政策保障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化发展必须立足民族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宏阔视野,这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生态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反映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思想。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者认为,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都深藏着一种内在的、支配表面现象的结构,反应文化在深层内涵的对立与统一,是一种共生共存而又互相冲突的关联,人类行为是由深层文化结构决定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政策的制定也是立足社会活动的深层结构,结合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时代主题,对这种潜在结构的表面化、具体化、功能化。
关于政治主要体现在相关政策上。李娜研究认为:建立专项政策、与时俱进保证时效、建立多部门协调的合作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督管理机制、实施政府主导型的发展管理战略[8]。从经济的视角看,经济政策的意义在于,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不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为代价,可持续的稳定的获取经济利益。要在政策引导下科学投资,注意利益的合理分配,充分发挥经济的驱动效应,促进创意资源开发,加强文化产品价格管制,重视市场的调控作用,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现代科技发展来看,科技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科技融入是体现社会和文化进步的重要尺度。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开发的过程中每一步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科技的评判和引导,科技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的配置和保护方面起支配作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产品也应是科技产品,应具有一定的文化竞争力。在文化方面,应从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确立少数民族文化的战略地位,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转型,发挥民族文化政策的认同、导向、调控和融合等功能[9]。
但民族文化变迁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常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历史上的汉文化入侵,近代物质文明,地域权利变更及左倾思想都曾破坏过生态环境,应重建民族生态保护文化、生态文化与现代文明整合、加大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补偿、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克服小农小商意识等[10]。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中,各政策和制度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共同构筑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的政策体系。
4 结语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深刻阐述了人类自身和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其研究视野和研究成果能为人类文化发展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借鉴。作为一种历久弥新的历史文化形态,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是一种相对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反映了少数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也应属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区域研究可认为是一种宏观能包容众多研究方法的研究范式,能把多种理论结合起来,遵循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规律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进行预见性的多维审视。在我国践行科学发展观,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生态化开发是在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政策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指导下的一种文化创造,是对民族文化开发和价值转换的一种科学选择,体现了国家对文化环境和资源的高度重视,对国家文化战略思考、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和文化产品创造及文化竞影响力的传播都具有意义,必将进一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的和谐进步。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生态化发展应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一项宏观政策,相关具体政策的制定,应以生态化开发为前提,尽快上升到地方长远发展战略的高度。
[1]王俊奇.也论民间体育、民俗体育、民族体育、传统体育及其联系——兼与涂传飞、陈红新等商榷[J].体育学刊,2008,15(9):101-104.
[2]王广虎,陆虹.从体育与劳动的互补关系认识体育的价值[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9,25(3):4-8.
[3]程卫波,于军.体育与艺术的关系演进之管窥——身体社会学视角[J].体育科学,2010,30(12):87-91.
[4]方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5.
[5]李世宇.康雍乾时期民族政策与西南民族地区的开发[J].贵州民族研究,1992,1:127-133.
[6]魏靖晖,周智生,富筠.西南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7,1:89-93.
[7]戴嘉艳.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生态视域及其对农耕文化的学术观照[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6:100-105.
[8]李娜.推进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政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2.
[9]李丽娜.论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创新与发展[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3,15(3):115-118.
[10]刘新友,史正涛,唐娇艳.民族文化变迁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以云南为例[J].生态经济,2007,5:138-140.
Policy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inority Sport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LI Xiao-tong,CHEN Yong-bing,LI Kai-wen
(Sports Institute Wenshan University,Wenshan 663000,Yunnan)
Human'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vision,the theory of“regional culture”has provided the ideal research paradigm to the minorities traditional sports ecology development policy.It studi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inority sports policies,using evolutionary theory,communication theory,function theory and structure theory etc.Conclusions:minority traditional sports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nature,society in the basic of the particular area and social structure,reflecting the ecology development policy logic.As a policy formulation reference with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that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culture creation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inority sports.
traditional minority sports;ecological development policy;cultural anthropology;ecological ethics
G853/857
A
1672-1365(2015)01-0101-04
2014-11-29;
2014-12-20
2013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QN2013009);2014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立项青年项目(QN2014076)。
李晓通(1979-),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