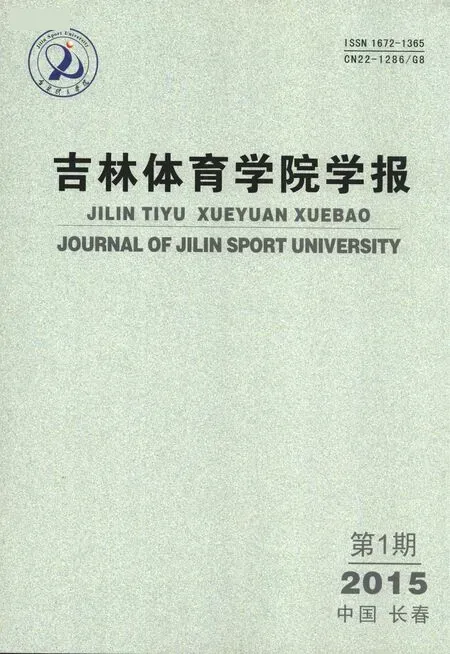论人本体育观的基本范畴
张振龙
(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山西太原 030024)
◀博士论坛
论人本体育观的基本范畴
张振龙
(太原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山西太原 030024)
体育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体育观是体育发展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以往我国关于体育观的讨论主要包括生物体育观、社会体育观和人文体育观,以人为本的体育观是对其的继承与发展。以人为本的体育观在主体上强调个人、全民和人类三个层次;在理念上强调整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具体内容上应包括以健康为核心的体育功能观,以全民健身为优先的体育发展观和以“善治”为目标的体育治理观。
以人为本;体育观;基本范畴;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体育观是科学发展观在体育领域的落实与展开,旨在把有效满足人的体育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并在其理念下实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结合。
1 人本体育观的概念
如何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与“本”,是科学理解以人为本体育观的关键与前提。
1.1 以人为本之“人”
以人为本中的“人”是主体,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前提与核心关切。
1.1.1 作为个体的“个人”
个人曾长期难以在以人为本的理论框架中获得其应有地位,盖因以下几点,其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因此社会上没有孤立的个人,社会不是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其二,通过人民的概念实现对个人的内化与消解。我国“集体主义”的悠久传统和现代化模式,民族与国家在近代以来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使命与课题,采用集体主义的进路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等有其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但由此形成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也长期存在。其三,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批判导致对个人价值的漠视。西方文艺复光以降所取得对神权和封建政权的斗争胜利,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构建,均以个人主义为其理论基础。出于意识形态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和对“集体人权”,即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强调,对个人地位正当性的认识较为薄弱。然而,无论是从个体与整体辩证关系的哲学视角,还是体育既以身体为手段又以其为目的特殊性,乃至全球社会对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的调适和我国个人权利的不断启蒙与觉醒,均要求确认个人权利的正当性。欧洲《大众体育宪章》规定“每个人都具有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体育运动国际宪章》规定“体育运动是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可视为对个人在体育中合法地位的有力确认。诚如李慎明所言,以人为本中的“人”应是指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一切社会成员,是这一切社会成员中的“每一个”个人。[2]
1.1.2 作为集体的“全民”
人民是以人为本理论的出发点和当然主体。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叙述是人民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主体地位的再现与确认,体育领域自然含括在内。无论是我国《宪法》中还是《体育法》中均以“增强人民体质”作为目的。是对这一立场的承继。然而人民不仅是一个集体概念,其还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与敌人相对。因此,以人为本体育观中的集体人格,应对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有所扩展。在以人为本的体育观中,应以“全民”而非“人民”指代集体的“人”。
1.1.3 作为整体的“人类”
随着体育国际化,尤其是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全球体育公共文化产品的不断发展,使得体育日益成为全球文化现象。首先,多数国际体育组织的目标或宗旨,无论是以推动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奥委会,还是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某一项或几项运动的发展为已任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均以全球作为其活动范围。其次,国际体育组织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也要求其在行为时更加关注全球环境保护、伦理价值、文化多样性和国际团结与合作等国际性议题。再次,全球范围内的体育公平也是国际体育组织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及对成员国全民健身的资助,还是其他体育组织或赛事组委会对贫穷落后国家运动员参赛、训练等的资助、援助等,均使得国际体育组织承担了社会责任。因此,作为全球文化现象的体育,具有全球参与、全球资源、全球流动、全球传播、全球共享、人类庆典等诸多特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人人享有能达到最高体质和心理健康标准的权利”。即是从整体人类的角度对体育权利的确认。
除体育领域外,随着对体育功能认识的深化,体育在全球性议题方面也开始显露其价值和意义。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包括八个方面:消除或减少贫困和饥饿、降低儿童死亡率、降低疾病发生率、促进教育普及、改善孕产妇健康、促进性别平等、环境保护可持续性和构建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体育被认为是辅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联合国认为:“虽然体育不能独自解决这些问题,但将其纳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广泛的整体方案中,它就极为有效。”[3]
由此,在以人为本的主体方面,不仅应该充分强调作为集体的全民的主体意识,还应该让“个人”由离场转为在场,并将其扩展至作为整体的“人类”,以实现对不同层次主体的涵摄,并确保其内涵的丰富和完满。
1.2 以人为本之“本”
“本”具有根本、本源、基础、主体、核心、本位、中心、价值目标等多重含义。有学者认为以人为人类社会的根本、基础、主体,或者是以人为人类社会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是两种不同的认识。把人看成社会的基础,代表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史观;把社会看成为人的基础,是科学的唯物史观。[4]显然,以人为本中的“本”是与“末”相对,它并非在哲学本体论上探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而是在哲学价值论上探讨何者最重要,最根本,最值得关注,与其相对的是“物本”或“政本”等观念。以人为本所要解决的为什么发展,发展“为了谁”,以及依靠谁来发展的问题,均需从价值论层面进行回答。因此,把“本”作为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更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既然体育观是对体育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5],基于上述对“人”与“本”的分析和理解,本文认为以人为本的体育观是指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终极目标或价值取向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2 人本体育观的继承与超越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理内核是人本体育观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各个时期我国体育观的辩证分析识别其合理成份,能够充实和丰富人本体育观的内涵。
2.1 人本体育观的科学精神维度
2.1.1 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可溯源至古希腊,并随近代自然科学的繁荣而勃兴。科学主义的本质可以从科学观、哲学观、价值观三个层面来理解。在科学观层面,科学主义概括了科学的特征,将科学绝对化;在哲学层面,科学主义强调形而上学的无用性,而只注重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在价值层面,科学主义则将科学神圣化,把科学看作高于人类的本体,作为评判事物的依据[6]。最终科学主义的过度扩张导致与人文主义分道扬镳并对后者形成排斥与压制。随着科学主义的日趋极端,其负面影响也不断显现,使得人类面临基因工程、生物工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态环境等诸多危机与挑战。作为对科学主义的反动,呼唤科学研究应当秉承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强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7],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广泛共识。
2.1.2 科学主义与体育
科学主义在体育中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在工具理性下将体育参与者的身体对象化,以及科技的滥用,从而导致生物体育观和其他体育异化行为。首先,在生物体育观看来,体育只是与人体生理机能相关联的事情,在运动训练中只关注运动员的生理器官、组织或细胞等,以人体为研究的最高层次,忽视运动员个性。其次,以运动成绩或运动表现为最高追求,尤其是体育商业化带来的巨额经济利益引诱,不仅在训练或比赛中过度使用身体,而且还导致服用兴奋剂等越轨行为的出现和泛滥。
2.2 人本体育观的人文精神维度
2.2.1 人文主义
杨寿堪认为,人文主义经历了人文科学、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人本学)4个发展阶段[8]。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主要是指以人为中心,通过文学、艺术形式体现人性与人文精神。后期人道主义思想,主要是以人自身为中心,提出有关人的最终本性的问题,人道主义思想意味着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发展丰富的人性。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因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哲学反思中,人们开始反对“人类中心论”,并强调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同一与和谐。此外,传统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多样性、个体性和特殊性,强调人的意志、欲望和人的本能冲动的作用与意义。但是随之而来也出现了极端的多元化倾向,绝对个人自由主义和绝对自我中心主义泛滥,对其负面作用的深刻警醒也导致人文主义开始认识到理性的功能与价值,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出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9]。
2.2.2 人文体育观
人文体育观自胡晓明批判生物体育观而引发热烈讨论,罗时铭则从认知的角度论述了我国从生物体育观、社会体育观再到文化体育观的发展演变历程[10]。陈建华等同样采用三类体育观划分模式,只不过以人文体育观替代文化体育观。人文体育观的立论基础在于:(1)体育是一种文化现象,应关注体育背后的文化意蕴。如熊斗寅就认为奥林匹克不仅是体育,而且是更具人类文明特征的国际文化运动[11]。(2)因生物体育观所造成的异化及负面影响,需人文精神的介入与调适;(3)以“人文奥运”的提出为契机而引发的相应讨论;(4)因我国以人为本观念的提出而引发的新一轮探讨。虽然人文、文化、人性、人道等均从不同层面深刻提示了体育的本质属性,但除却“人文”、“人道”等复杂的概念溯源,人文体育观本身面临着诸多缺陷。首先,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是近代两大思潮,在人文体育观下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强制整合,过于牵强;其次,对人文主义的非科学一面,尤其是对其的非理性传统的负面影响关注不够[12];再次,人文主义体育观的内涵一直不够清晰[13]。陈琦等将人文体育观划分为教育价值观、竞争价值观、休闲价值观和经济价值观[14],试图糅合事业与产业,并对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休闲体育的领域划分有所关照,但并不能令人满意。陈建华等认为人文体育观主要表现为人性体育、快乐体育和多元体育[15],并未超越罗时铭“文化体育观”的内涵。最后,“文化”虽是体育的本质属性,但本质属性与体育观并非同一概念,并非本质属性所能代表或含括。
2.3 对其他体育观研究的分析
我国学者在梳理体育观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维体育观”的概念。袁旦、谭卫和将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体育观概括为“卫生.体力体育观”、“教育体育观”和“生物体育观”。并将生物、心理与社会相结合的体育观界定为“三维体育观”。虽然该概念能够保留三大体育观的合理内核,且避免了其各自弊端,然而,该种观点仍是从影响运动员成绩的固有思维出发,且其对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领域划分的隐而不彰的借用,也偏离了其体育观是“体育总的看法和根本观念”的概念界定。
部分学者将我国建国后全面推行“劳卫制”,竞技体育强调“刻苦训练,为国争光”,获得国家和民族认同,以及群众领域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定义为“政治体育观”[16]。从其论证思路与内容来看,与罗时铭等定义的“社会体育观”内涵基本一致,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肯定其历史贡献的同时,在新时期应进行调整与修正。
由此,人本体育观是在恪守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合理内核,扬弃其片面和极端观点上的统摄与整合;是对生物体育观、社会(政治)体育观和人文(文化)体育观等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与超越。
3 人本体育观的基本内容
3.1 体育功能观
体育的功能是体育本质属性与社会需求的结合,并随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演变。我国学者关于体育功能的种类及其关系认识不同且各有侧重。熊晓正将体育功能划分为作用于个体的功能和作用于社会的功能。其中作用于个体的功能包括强身健体、人格塑造、休闲娱乐和人际交流功能,并认为强身健体是体育最基本、最直接的功能,是决定其他功能的基础[17]。杨文轩将体育的功能分为本质功能和延伸功能两个层次,其中体育的本质功能包括健身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18],强调强身健体在体育功能中的基础性地位。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完全处于良好的状态。”使得健康的内涵更加丰富。由于身体目的性与手段性兼具,即使是最接近手段意义上的职业体育,也与其他行业一样需实现职业需求与健康需求的平衡。因此,体育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功能,均应以健康功能为基础或先导。确立健康在体育功能中的基础或核心地位,而不是与其他附属或衍生功能平行并列,这有助于对体育功能的科学把握与合理发挥。
3.2 体育发展观
发展观本是一哲学概念,后开始应用于社会领域,并且形成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体育发展观是这一理论在体育领域的实践与落实。
3.2.1 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的根本目的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增强体质”作为发展体育的目的。我国《宪法》第21条第2款:“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以及《体育法》第1条:“为了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体育运动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均以“体质”作为归依。“体质论”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体育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而且也长期制约了人们对体育功能的全面认识。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体育的根本目的,不仅与科学发展观、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观一脉相承,而且随着我国现代生产生活所导致的“文明病”的蔓延和人的身体的异化不断彰显其正当性和时代价值。
人的全面发展在不同时期均为教育家们所关注与倡导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全面发展可溯源至孔子对片面发展的否定和亚里士多德对“和谐教育”的强调;近代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泛智教育”,法国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以及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所倡导的人的一切潜在能力的和谐发展等,都为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洞见并深刻影响了近代西方教育。受其影响,结合我国近代国民“东亚病夫”的身体状况和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对“强力”的需求,无论是蔡元培还是毛泽东,均将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不同时期还曾经将其摆在智育、德育和美育之前。“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它从分析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产关系入手,指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手段和途径。并主张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在体育领域,人的全面发展在《奥林匹克宪章》中的表述可谓经典,它认为“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面对各类体育异化行为,如体育训练和比赛中现代科技的滥用,早期过度专业化训练、“金牌至上”等,也需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调适与纠偏的根本准则。
3.2.2 强化全民健身的基础和优先地位
随着大众体育的兴起和人们对“金牌”价值的理性认识,理论与实践均要求提升全民健身在体育发展中的地位。2009年通过的《全民健身条例》可视为对日益增长的全民健身需求和青少年身体素质不断下降的有效回应,包括体育彩票公益金在内的新的多元渠道的资金投入也已经开始显示其积极影响。全民健身主要包括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体育观,必须在发展观层面强调全民健身的优先性,并为其构建组织体系、多元资金体系、活动体系、评价体系等作为支撑。此外,行政机关在工作方式上应由活动导向转为组织培育,由国家保障公共服务和市场满足差异化需求双向驱动,并实现由组织者到责任者的角色转变。
3.2.3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制度保障
公共行政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权活动,公共行政的目标主要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并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性是政府与公共服务连结的本质属性,人权保障是公共服务的逻辑起点[20]。我国目前体育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以及在我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情形下如何确保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即公平性的问题。易剑东认为我国当前体育公共服务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平衡,提供方式单一、运行机制不畅等问题。并主张体育公共服务提供应该坚持“政府主导、市场配置、社会参与、公众受益”的原则[21]。不断提高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与水平,无疑应当成为体育公共部门的重要职责。为此,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强调“加快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切实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迈上新台阶。”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日益多元化之际,无论政府担任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推动者还是资助者,显然,政府均应对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和监管承担最终责任,确保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以人为本体育观对体育公共行政的必然要求。
3.3 体育治理观
3.3.1 以“体育善治”作为根本目标
“全球治理”随全球化所带来的众多跨越国界,仅凭一国努力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出现和增多而引起关注。随着我国改革不断深化,治理理念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并成为新的执政基础。对“治理”内涵的准确理解是有效落实这一肇始于国际领域的现代理论的关键。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经典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治理具有四个特征: (1)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2)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 (3)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4)治理不是一个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22]。
所谓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23]随着体育组织尤其是国际体育组织因商业化而带来的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并招致不断增强的介入与干预,体育善治终于成为体育组织因应外界压力并确保自身合法性的改革趋向与目标。无论是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还是国际政治组织或国家体育组织,均发表了大量的与善治有关的文件,如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2007年提出《治理原则:体育组织的良好做法指南》;国际奥委会于2008年提出《奥运会和体育善治的基本通则》;欧盟2012年提出《体育运动的善治与伦理》。民主参与、法治、透明、效率、回应、公平和包容、问责等内容成为对体育组织运行的基本要求,并且善治逐渐成为体育组织自主和自律的前提。体育组织特有的伞状结构导致国内体育组织面临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与挑战,因而“善治”也应成为国内体育组织的改革方向与发展目标。
3.3.2 以多元治理作为基本模式
多元治理是体育善治的应有之义,多元治理意味着对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突破。多元治理关键是要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的三边关系中各自的权责体系和边界问题。在公共产品服务供给方面,多元治理模式要求实现以下四个基本方面的转变。(1)由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相比传统统治模式,治理显然强调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不再由国家或政府单一提供,而强调其他主体的参与和责任承担。无论是个人、社团还是企业,均具有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机会和职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我国各类体育主体,包括营利和非营利组织的建设提出需求。尽管对于政府在多元治理中的作用仍有“多中心”和“政府主导”的争论,但显然提升此类组织在体育产品供给中的地位的作用,是我国当前体育体制改革的重点问题[24]。(2)由重效果到重效率。治理理论以新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之一,后者从制度经济学和管理主义出发,强调经济、效率、效能。尤其是其对生产与提供的区分,为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尤其是“管办分离”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支撑。当前我国行政机关体育管理缺位与越位并存,而这显然会影响到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质量和效率。(3)由重管理到重服务。治理理论强调政府部门对社会公民的服务,而非其传统的控制与管理。作为顾客,公民或组织不仅是政府公共行为服务的对象,也要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各个环节,从而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顺利运行提供保障。(4)由重命令到重协作。传统管理理念下,政府主要是通过命令的形式,通过带有强制性的公权力实现社会管理。在治理理念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和个人是一种协作关系,因此,与协作关系相对应的谈判、博弈、咨询、参与等互动形式要求占有更大的比重或权重[25]。
3.3.3 以体育权利保障作为体育善治的基石
多元治理模式的运行无疑应以法治为基础。作为体育领域重要的制度资源和调控模式,体育法治是法治的组成部分。随着法治理念的不断落实和“人权入宪”,体育权利问题日益引起关注并成为体育法制建设的逻辑起点和基石。所谓体育权利,即人在参加体育运动或接受体育教育过程中所应享有的自由与利益。囿于立法技术与法制环境,我国1995年《体育法》虽然在立法目的与宗旨中贯彻了保障体育权利的意涵,但并无直接体现。体育权利缺失的遗憾直到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的公布才有所弥补,其第1条“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和第4条“公民有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尽管仍是一种有缺陷的表述,但毕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与体育的丰富内涵相适应,体育权利的内涵也较宽泛且与其他领域多有交叉,如学生接受体育教育的权利、公民参与全民健身的权利、运动员参加训练与比赛的权利等。关于体育权利的内涵所产生的不同认识,盖因体育权利出现较晚,且体育领域与其他领域如教育等多有交集所致。不断推进的法治进程使体育法治面临的制度环境有所变化,并提出新的需求。以《体育法》修改为契机,以体育权利保障为起点,建立立法、司法和守法各环节紧密结合有效运行的体育法规体系,是确保公民体育权利实现的法治保障,也是人本体育观的根本要求。
4 结语
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在西方源远流长并均有其合理内核,在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政权的过程中紧密配合引领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但在二者各自走向极端而相互排斥与否定之后,无力单独回应社会实践的挑战并最终在新的高度走向融合。以人为本能够直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并且在其统摄下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各自独立和有机结合。以人为本的体育观是该理论在体育领域的推导与展开,是我国新时期发展体育的根本价值取向与目标,应确保其在个人、全民和人类三个层面的保障与实现。以人为本的体育观的基本内容包括以健康为核心的体育功能观;以全民健身为优先的体育发展观;以及以“善治”为目标的体育治理观。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2]李慎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J].中国社会科学,2007,(7):4-17.
[3]任海.国际奥委会演进的历史逻辑—从自治到善治[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240,194.
[4]黄枬森.关于以人为本的若干理论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11(4):11-22.
[5]袁旦,谭卫和.论体育观和体育科学思维模式的几次重大变革[J].体育科学,1987,(01):76-82.
[6]曹志平,邓丹云.论科学主义的本质[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7(4):11-19.
[7]乔文娟,李建珊.当代科学研究的人文取向[J].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85-91.
[8]杨寿堪.人文主义:传统与现代[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92-98.
[9]张学广.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演进与生存危机[J].社会科学,2007,(1):156-161.
[10]罗时铭.从生物体育到文化体育-当代中国人体育认知发展变化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6,(11):24-27.
[11]熊斗寅.人文奥运之我见[J].体育与科学,2001,22 (6):15-18.
[12]刘宝存.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大学理论的冲突与融合[J].学术界,2005,110(1):50-63.
[13]吴翼鉴.增强人的体质,是体育“无人”吗?[J].体育学刊,1999,(3):1-2.
[14]陈琦,杨文轩,刘海元.我国当代体育价值观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6,26(8):3-9.
[15]陈建华,王浩,李锂.人文体育观视野下“体教结合”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9,17 (9):1-4(9).
[16]高雪峰.人本体育原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7(5):10-14.
[17]熊晓正主编.体育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1:64-79.
[18]杨文轩,杨霆.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3-44.
[19]于善旭.迈向体育强国的法制需求与挑战[J].体育学刊,2009,16(8):1-8.
[20]贾文彤,郝军龙,刘慧芳等.法律视野下的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3):78-81.
[21]易剑东.中国体育公共服务研究[J].体育学刊,2012,19(2):2-10.
[22]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23]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5):37-41.
[24]李泉.治理理论的谱系与转型中国[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30-137.
[25]高秉雄,张江涛.公共治理:理论缘起与模式变迁[J].社会主义研究,2010,194(6):107-112.
On Basic Category of Human-Oriented Sports View
ZHANG Zhen-long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22,Shanxi,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hould be human-oriented,which is the overall guiding ideology and basic principles for sports development.The main sports view in our country includ biological,social and cultural view,the human-oriented sports view a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view.This view emphasizes personal,national and human three levels and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spirit and humanistic spirit.The content include the sports function view of physical health as the core,the development view in which the fitness as a priority and the good governance as the goal of sports governance view.
human-oriented;sports view;basic category;all-round development.
G80-05
A
1672-1365(2015)01-0009-06
2014-11-01;
2014-11-30
张振龙(1976-),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法学、奥林匹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