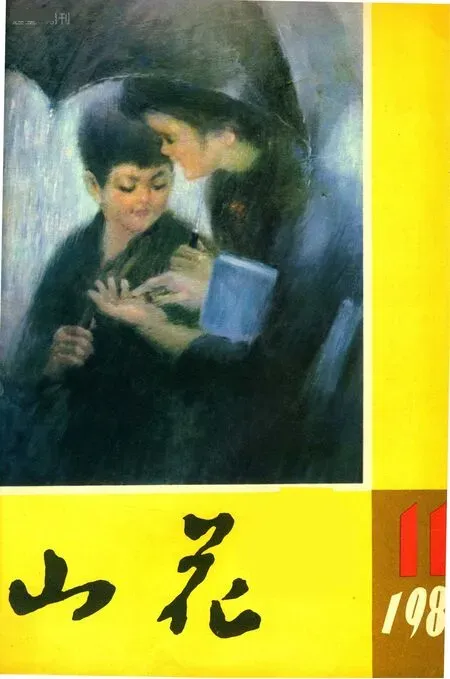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诗人批评家”——陈超的诗学研究及作为一种批评的启示性
霍俊明
较之同时代和后此的那些动辄贩卖西方文论和唯某某主义是瞻的批评家,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批评版图中“诗人批评家”陈超以其精准、独到、深迥、性情、洞见、敏识确立了属于自己的话语谱系和精神坐标。他在一贯维系诗歌的本体依据和诗人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在时代情势的强行转换中又持有了规避话语失语症的对应能力。他在深入当代“噬心主题”的吁求中,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驱动下彰显出不可替代的诗学禀赋。他以文本细读、生命诗学、先锋诗论和现代诗话构建出别开生面的“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性批评的现代诗学体系。在程光炜1998年编选的那部影响巨大的诗歌选本《岁月的遗照》中专门有一个推荐阅读的诗集和诗论集的附录。所列诗论集共七部,其中就有陈超的《生命诗学论稿》,可见陈超诗学研究的影响力[1]。
乔治·斯坦纳曾不无悲观地指认“文学批评”往往是短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的著述生命有限,难以长久流传……大多数研究著述属于过眼云烟、学术著作和学术期刊文章尤其如此。在鉴赏情趣、评价标准和使用术语进行辩论的历史上,这样的文学研究著述或多或少代表某个具体的时段。不用多久,它们有的在繁冗的脚注中找到了葬身之所,有的呆在图书馆书架上悄无声息地搜集尘埃。”[2]但是当我们罗列陈超的一系列诗学专著[3],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精神体量如此庞大、话语体系如此精密的杰出批评家。这也是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以来陈超的一系列诗学著作被很多诗人和业内同行视为诗学启蒙和精神导师的重要原因。2008年4月陈超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当时由评论家谢有顺撰写的颁奖词这样写道:“陈超的文学批评洋溢着一种诚恳的感悟力,也充满理解、对话和价值确认的渴望。他的先锋诗歌研究,是对这个时代想象力的高度、诗歌精神的宽度所作的卓越解读”。陈超的独特性、重要性以及不可替代性在于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批评话语谱系“生命诗学”和“现代诗话”,在语言与生命、生存、历史感的临界点上既尊重了生命个体和人类整体的存在意识,又坚持了诗歌的本体依据。这是对语言本体的尊重和知识分子精神的自觉。
一、“诗人批评家”与“文本细读”
1961年,艾略特将批评家分为四类,而他最为倾心的就是“诗人批评家”,“我们不妨说,他是写过一些文学评论的诗人。要归入这一类的批评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他的诗歌,但他的评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诗歌,而是有其自身的价值”[4]。必须强调陈超就是典型意义上的“诗人批评家”,与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职业批评家和学院批评家都不同。而对于陈超来说这种特殊性的“自身价值”来自于诗性直觉、会心而精准地对诗歌这一特殊文体语言特质的感受力以及诗性的持续发现能力。“诗人批评家”这一特殊身份使得陈超能够在直觉和学养间获得平衡,在感性和理性中达成一致,在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之间不断交互、往返和互相求证。这是一个“双手”写作的人,这种带有互补性质的写作无疑带有“问题”的重要性和“说话”的有效性。严谨、精密、深入、尖锐的理论思辨能力与会心、精妙的感受力和细读能力的完美结合使得陈超的诗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阅读的欢欣。
在陈超的的人生履历和身份中他排出了如下顺序:诗人,诗歌批评家,大学教授。可见陈超最看重的是自己的诗人身份。确实如此,陈超作为诗人的一面相当重要。陈超的诗歌主要集中于诗集《热爱,是的》(远方出版社,2003年12月)《陈超诗歌快递:夜烤烟草》(诗歌EMS周刊,2011年5月2日总第98期)《陈超短诗选》(银河出版社,2012年)。在很大程度上,诗界普遍关注和倚重陈超作为诗论家的一面,而这种“高拔”也造成了对他诗歌写作长期的遮蔽。而就我所知,很多年来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内行”谈及过陈超的诗歌写作(我是说在深刻和准确的程度上),如唐晓渡、西川、臧棣、刘翔。唐晓渡在陈超辞世之后回忆了对其诗歌的深刻印象,“真读到陈超的诗时我还是感到了惊讶——不是惊讶于它们出自何人之手,而是惊讶于它们出色的程度。”(唐晓渡未刊稿)西川的评价更高,“在我眼中,杰出的诗人和杰出的诗歌批评家没有高下之分。陈超既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批评家。在他身上,这两个‘杰出’也没有高下之分。陈超的诗歌创作中,既有自觉的成分也有训练的成分。无论在他进行诗歌创作,还是进行诗歌批评时,这两个‘杰出’都互相借重”[5]。是的,这就是“内行”的工作。平心而论,陈超无疑是杰出的诗歌批评家。就诗人身份来说,陈超的诗歌也是出手极高的。陈超的诗歌显然是先锋的诗歌精神与略显“老旧”的话语形式之间的完美结合。在咏叹和吟述的朗朗的诗歌乐调中呈现的却是深入当代的先锋意识和深切的个人体验。这在八九十年代的汉语诗坛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陈超的诗歌写作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转世桃花”般的阵痛与精神高蹈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深入当代和日常生活的转变过程。陈超的诗既是高蹈的又是及物的,既是面向整体的时代精神大势又是垂心自我渊薮的浩叹。
作为诗人批评家,陈超有一种极其特殊的诗歌批评方式——元诗写作,也就是他一以贯之的以诗论诗的诗,如《话语》(1987)、《终曲》(1987)、《生活在锡罐里的诗人》(1988)、《一个新词》(1988)、《再不会》(1989)、《写作》(1990)、《交谈 (组诗)》(1990)、《堆满废稿的房间》(1996)、《译诗轶事》(2001)、《旅途,文野之分》(2002)等。这种“元诗”性质的诗歌直接打通了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之间隐秘的通道。这种对话、互文、互证、互动、呼应、对称的写作方式恰好平衡了诗歌与批评之间的微妙之处。尤其是1994年之前,这种“元诗”写作在陈超的诗歌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同时必须强调的是陈超的这些对话性质的“元诗歌”并非只是简单地与其他诗人以及诗人自我的精神对话,而是在更深的层面呼应了个体精神与时代境遇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说这种共时性的诗歌写作也是一种“及物性”的精神担当。他会直接用“以诗论诗”的方式谈论他对诗歌语言、修辞和本体依据的独特理解与观照。在陈超这里诗歌的语言“不是母亲的话语/是母亲砧捣寒衣的声音/你用心听着它/无法转述/你不会感到陌生/但又永远不能洞悉/这就是诗的话语/它近乎不在/你相信了它/你活得温柔/安慰”(《话语》)。这进一步印证了诗歌写作的才能在陈超诗歌批评这里的彰显,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之间的特殊关联——相互补充、彼此观照。陈超强调诗歌和诗学一样往往从反思对方开始。在陈超这里写作和批评一样是一种“快乐的知识”,同时也是痛彻的“精神重生”。而当这种努力放置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境遇中,其难度可想而知。这是将头颅在火焰中淬炼的“美学效忠”。诗人在阴森冷酷的时代暗夜写下了亡灵书和精神升阶书。在这样的时刻诗歌批评需要勇气和坚持,更需要诗人的“历史个人化”的“求真意志”。
恰恰是这种特殊性的诗歌批评话语方式的难度形成了其难以替代的重要性、有效性和独特的诗学禀赋。这使我想到的是当年的李健吾。他感悟式的批评方式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算得上是绝对的“少数者”或者“异秉”。也就是说没有特殊的诗学禀赋、创作心得和“细读”能力以及澡雪性情的人这种方式不得为之,也不可能为之。这在陈超为中外现代诗所做的导读、细读和鉴赏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凸显。陈超从1980年代开始就践行着英美新批评和文本细读的方法。这在《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卷)《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卷)以及一系列细读文章中有着足够完备的证明。他精准、深入和独特的细读方式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赞誉。这也是陈仲义等批评家指认陈超是“新批评重镇”的因由。陈超的文本细读既从微观的文本的角度出发又和中国传统诗话的印象阐释融合。这使得他在对文本细部纹理的窥测中不时闪现出睿智的哲思和性味的会心。陈超通过细读的方式在具体文本中完成了对话、磋商、盘诘与阐释性创造。
陈超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立足于文本语境的语义学精细分析和“细致诠释”,也不是泛泛地关注构架与肌质的可转述和不可转述的部分以及对含混、反讽、悖论、张力和隐喻等修辞术语的借用,而是一直强调文本细读并不是小孩拆表的游戏。这需要解读者具备特殊的能力——这就是陈超所倚重的“诗人批评家”。这实际上也回应到了古典诗论的“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陈超的这种精准、独到、敏识、还原和发现性的细读能力使他在解读这些中外二十世纪具有探索性、先锋性特质的诗歌文本的时候是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周伦佑语)。他在一以贯之的诗人的个体主体性和诗歌本体依据的基点上坚持诗歌是“揭示生存,眷恋生命,流连光景,闪耀性情”的认知方式。在坚持诗歌的本体依据和美学性的前提下陈超立足于历史语境以及现当代诗人的生存困境。陈超尤为关注现代诗人与生存和语言之间的困境。文本细读和形式感以及建立于历史语境下的诗歌剖析揭示了现代诗人生命话语体验的特殊性。带有导读和细读性质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体现了陈超对诗歌文本独到的解析、鉴赏和细读能力。在对现当代的129位诗人的403首诗歌的精细阅读和对话中还原了汉语诗歌的历史原貌和本真状态。《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这部近百万字的探索诗鉴赏是在《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的基础上扩充、修订、再版和继续拓殖的成果。辑入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131位诗人的探索性诗作423首。陈超不仅界定了他心目中的“探索诗”,而且以精当的细读方式和串联起的诗歌史意识而独树一帜。这对于新诗教育、普及、传播以及新诗的进一步历史化和经典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的下册提供了“现代诗学常用术语简释”的附录。这不论是对于专业读者还是一般的读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在对中国探索诗鉴赏的基础上,陈超将诗学视野进一步转移到当代外国诗歌。《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正是这一成果的体现,对33个国家104位诗人的283首诗作进行了精细导读。陈超对北美西欧国家所谓的“强势文化”、诗歌脉向和处于文化弱势国家的亚非拉诗歌进行了共时性的细读。而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种族、流派、具有不同艺术风格和文化语境的差异性文本给陈超的这次导读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这部导读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文本细读与审美感悟的评析相结合,力求实现对诗歌内在的意味和形式的深层阐释。

杨兴军作品-《之前之后》 雕塑 综合材料 尺寸可变2014.(局部)(驻留计划)

杨兴军作品-《之前之后》 雕塑 综合材料 尺寸可变2014.(局部)(驻留计划)

赵建成作品-《小屋》 木 现成品 123×125×208cm 2014(驻留计划)
二、“精神游荡”与“生命诗学”
陈超的诗歌批评不仅倚重新诗的本体依据,而且一直强调每一个时代的诗论家都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生存环境中对诗歌发声和求证。在陈超的诗歌批评中个人生存体验的焦灼感与诗学立场的忧患意识在紧张而双向拉开的向度中以深入向下的勘探姿态夯击、锤打。这使得很多年他在诗歌批评中构建起一个并不轻松的“精神游荡者”形象。这在本真意义上凸显了诗歌批评在本质上就是“生命诗学”。
1994年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是陈超第一部诗学专著。这奠定了他一生追寻的“生命诗学”,即如史蒂文森所说诗歌的理论就是生命的理论。陈超直接开启了关乎生命深处秘密和诗歌血脉的批评方式。从这部诗学著作开始,陈超一直坚持的就是在深入本文的过程中揭示现代诗人的生命、生存与语言之间的复杂甚至残酷关系。尤其是对1980年代诗歌的带有现场感和知识分子精神的阐释和辨析尤为深刻而具有启示性。在陈超的“生命诗学”这里,个人经验的公开化与公共经验的个人化能够很好地揭示出来。陈超一次次走在时代转折点的“断裂”地带——那里是凛凛的风雪与陡立的绝壁。陈超的诗歌批评中不断燃起一场场死亡和重生的大火,当然随之也布满了灰烬和寒冷,“我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阳光从广阔遥远的天空垂直洞彻在我的身体上。而它在冰凌中的反光,有如一束束尖锐的、刻意缩小的闪电,面对寒冷和疲竭,展开它火焰的卷宗。在这烈火和冰凌轮回的生命旅程中,我深入伟大纯正的诗歌,它是一座突兀的架设至天空的桥梁,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向上攀登。”[6]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语境下,陈超的诗歌批评就是展现精神高蹈、生命阵痛以及完成“诗歌历史化”的过程。在《生命诗学论稿》这部诗学专著中陈超将诗学问题和更广阔的哲学命题融合在一起,视野尤为开阔,更具有历史感和文化人类学的意义。精神高蹈、美学高标和深入当代的现象学方法论具有当代诗歌批评的开拓性意义。诗歌在审美功能的前提下凸显出了诗人的世界观、立场和方法论。从宏观的视阈来考量,他对汉语新诗的诸多彼此纠缠的复杂情境进行了梳理和历史还原(如新诗与传统、具体历史语境的诗学问题和可能的诗歌发展前景),对诗歌与语言、生命、生存、历史、时代的多重关系的富有说服力的精细剖析。更进一步,陈超通过现代诗和古典诗的比照,认为二者在诗歌结构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新诗自身的传统。陈超认为现代诗较之传统诗更强调结构的包容力和形式的开放性,更强调“深层结构”的重要性,更为注重结构中的张力或紧张关系。[7]这都对现代汉诗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参照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使得陈超在“深入当代”、楔入和介入时代的“噬心主题”的同时,在回顾与前瞻的双重视角中呈示了潜心反思的知识分子立场和精当的言人未言的独特见解。《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则是陈超对“生命诗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代表了他在诗学领域中的最新见解和全面开拓。陈超以生命诗学、比较诗学和诗化哲学相结合视野,在现代诗歌的本体依据、功能和历史向度等方面进行了极其深入的辨析、论证与反思。陈超敏锐地提示出具体历史语境下当代诗歌的特质和诗学意义,又不留情面地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赵建成作品-《小屋》 木 现成品 123×125×208cm 2014(驻留计划)
陈超“生命诗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技巧”、“修辞”和“语言”的历史化。对诗歌技艺和诗歌本体特征陈超一以贯之地进行充满敏识与洞见的思考和探论。而这种对诗歌技艺和本体性的关注正是出于当代诗学的“红色选本文化”和“庸俗的文学社会学”对诗歌的长期挤压和胁迫后果的反思与警惕。在《论意象和生命心象》、《生命体验与诗的象征》、《实验诗对结构的贡献》、《论现代诗结构的基本问题》等文章中陈超深入的论述了诗歌的构架、肌质、技艺、语言、意象和经验承载力等诗歌的构成、表现技巧和诗的基本艺术符号。这并非是他对形式、技巧和形式主义情有独钟,并非是沉溺于诗歌的本体依据的自足性和对技巧的一味迷恋[8]。因为在陈超看来技巧绝非无用的手艺和装饰思想的可怜器皿。他深知技艺对诗人而言是一门“考验真诚”的必备功课,亦即与诗人的“道德”相关。斯奈德在《真实的工作》中谈及了“手艺”的重要性,“作为一个诗人,我是从我自己的手艺角度来理解的。我学习要成为一个匠人,真正需要掌握什么,专心致志真正意味着什么,工作意味着什么。要严肃地对待你的手艺,而不是胡来。”[9]也正如希尼所言“技巧,如我所定义的,不仅关系到诗人处理文字的方式,他对音乐,节奏和语言结构的安排;而且关系到他对生活态度的定义,对自身现实的定义。它也关系到对走出他通常的认识界限并冲击无法言喻的事物的方法的发现”[10]。
博尔赫斯自问“是什么命运的乖张,使我这么害怕一面照人的镜子?”而陈超关涉“生命诗学”的诗论文章则不时呈现和充溢着这种强烈的自审意识。这使他在洞明生存和历史镜像的同时,在返观事物和自身时“终得以远眺神明的宁静”(瓦雷里语)。对于诗歌评论而言,陈超既是一个“老式”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新锐”的怀疑主义者。而这理想中的个人情怀和自由精神的坚守和怀疑又难能可贵。这种坚持以及否定的两个向度成就了陈超诗歌评论的独特之处。理想与怀疑这二者之间的悖论和张力冲突,扩大和加深了他审慎敏锐的辽远视阈,提出和发现诗歌和世界的问题,维持了世界和诗歌得以以问题的形式存在。
三、先锋诗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与“求真意志”
说到陈超的诗学研究,学界会很直观地想到他多年坚持探索的“先锋诗论”。
实际上中国诗歌批评界一直误解了“先锋”这个词,甚至在有些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先锋”就是脱离日常语境的“高蹈”或者语言上的“行为主义”。而陈超用多年的诗歌批评证明“先锋”必须是“及物的”、“语言的”、“历史化”的。

赵建成作品-《小屋》 木 现成品 123×125×208cm 2014(驻留计划)
陈超在指出先锋诗歌的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同时也对其存在的问题和危险提出了策略性的应答。陈超尤其针对八九十年之交高蹈、澡雪、痛彻、垂直火焰般的维持无限向上姿态的先锋诗歌写作提出问题。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先锋诗歌在葆有了时代良知和灵魂秘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精神耽溺的危险。这种危险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写作空间的狭促和逼仄,在自我戏剧化和镜像化的同时会导致精神洁癖,会将诗人推至极端而丧失对生存现场的勘探和询问勇气。也就是说这种写作的危险性在于它有可能遮蔽和悬置了日常事物和生活的细部纹理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从而导致对“个人历史感”经验的遗漏和忽视。对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人而言,写出玫瑰、火焰、天堂、教堂、升阶书、圣杯等“大词”、“圣词”并非难事,关键在于诗人对本土语境、当下和现场的有效揭示和命名能力的长久缺失。老诗人牛汉在给陈超的信中极其中肯地说“我们需要彩镶玻璃,但如果我们对屋外一无所知,也渴望屋外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渴望的是透明的锐利的玻璃。这是一种需要,也是更深层的审美。”[11]确实如此!对于作为教堂和高蹈精神隐喻的“彩镶玻璃”与日常的“透明而锐利的玻璃”而言,后者的重要性一直被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很多诗人所忽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先锋诗歌不够“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很多年中国诗人的背后都站着几个西方的大诗人,中国的诗歌一直在借用不是来自于本土和生命本身的语言、修辞和身份在说话。
在时代语境的转换中陈超对先锋诗人的提醒是诗歌不单是“对一种神圣言说方式的祈祷与沉思”,更应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揭示。对这种转变,陈超有着深入的体察。也就是对于八十到九十年代的诗歌而言,如何调整“乌托邦精神”“理想主义者”“自我意识”与“经验论者”、“生活和事物纹理”之间的合法性内在关联?陈超就此提出现代诗的及物、容留、活力和有效性问题。陈超强调维持现代诗的活力和有效性以及难度不仅是写作技艺问题,而且涉及到诗人对材料的敏识,对求真意志的坚持,对诗歌包容力的自觉。像陈超这样在诗歌批评中如此自觉地认识到写作本土化和处理当代经验重要性的还是少之又少。如何撇开自恋的“不及物”写作而更为有效地楔入时代的核心或噬心的时代主题——而不是任意忽略甚至讥讽“平常”事物。也即陈超对那些一味高蹈的诗歌写作是持有保留甚至怀疑态度的。正如陈超所强调的“我不理解诗歌对当代的处理和把握为何使许多诗人视为畏途。处理当代主题和现实经验为什么一定会使诗歌变得不纯呢?”[12]陈超的先锋诗论一直强调的就是诗歌对“当代经验”的处理能力,一直关注于诗人的“精神成年”与“及物性”场域之间的关联,一直倾心于对时代“噬心命题”的持续发现。而陈超就此给出的答案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的陈超新书的题目就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历史个人化”和“求真意志”等概念在陈超看来是一种在时代和写作中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扩大、加深问题的手段,是自觉延宕真实指认的“极限悖谬”,是到达历史真实、个人真实和虚构真实的有力和有效途径。在诗人处理和介入时代“噬心主题”普遍失语的境况下,陈超几十年的诗学努力正体现了在紧迫的时代情境中持有“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又紧张而尖锐地“深入当代”的勇气。而在“深入当代”、揭示
时代“噬心主题”的同时又持有个人性的自由精神的乌托邦幻想,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具有巨大包容力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在陈超看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组织力的思想,对生存、文化、个体生命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足够认识,能够将自由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融合在一起。在复杂情境空前纠结冲撞的时代,“黄金,火焰,光芒,粮食,磨坊,玫瑰”等“老套”的失效的单一视镜以及古典浪漫词汇和象征体系已经很难承担和包容当下诗人复杂的经验和想象世界。实际上陈超的诗歌批评以及文本细读过程中一直坚持的就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既是对自身批评话语立场的坚持,又是对汉语新诗标准的要求。围绕着“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陈超对先锋诗歌的“求真意志”、精神深度、心灵词源、精神重力予以了沉重的辨析。作为关键词的“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具有概括了地呈现了先锋诗人的精神特质和文本特征。《中国先锋诗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台湾秀威)这部诗学著作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沉思、忧患以及担当意识。换言之,陈超先生在这些著作中体现了并不轻松的批评过程。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这些文字甚至难以分担内心和时代的双重阵痛、分裂、震荡与转捩。迷茫风雪路上的流亡作家米沃什说“对于写作者来说,二十世纪的历史还没有人动过”。尽管这话不无偏颇,但也相当深刻、精省地印证了诗人和评论者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叶尴尬失语的境遇。而陈超的知识分子良知和诗学敏识使他在时代的风口强烈而紧迫地意识到“悄然而至的挑战”,“接近诗歌是危险的,不去接近诗歌却更为危险”(《论诗与思》)。在诗人与言辞、生命与生存的彼此纠葛的复杂情势与困境中,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不仅是人类自身精神和情感体验的守护者,而且又是向公众敞开的艺术形式。因此诗的“自我”和“社会”的问题的争论就一直都没有停止和中断过。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中说:“在沙地上划字就如同写诗,是与红尘俗世的疏离,但又不是逃避”。诗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时代和当下,用诗人自己的“来自良知的共和国”和“粗暴的公共世界”进行较量。在此意义上陈超强调持有个我话语谱系并完成对当代经验的有效命名和深入开掘是诗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识”。这实际上正是陈超多年来在所坚持的“求真意志”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驱动下对灵魂和困境的双重揭示。尤其是他对“地下诗歌”和“先锋诗歌”的诗人专论以及对先锋诗歌的历史、困境和可能性前景的揭示建立起了汉语诗歌批评的当代标杆。

赵建成作品-《碎片》之一,之三 雕塑 木 24×23×45cm,29×28×135cm 2013(驻留计划)
而陈超多年来对新诗文本依据的论证以及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求真意志”的坚持就是在解决“诗与真”的难题。《诗与真新论》(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这本书带有“为新诗一辩”的重要意味。这既是对歌德的《诗与真》和梁宗岱的《诗与真》的“诗学谱系”的接续,也是陈超对汉语诗学及其存在问题的重新发现。也就是任何一个时代具有自觉意识的诗论家都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不同的角度追问并创造性地回答“诗与真”的关系问题。在陈超这里“诗”与“真”并不是矛盾关系,而是相互激发、平衡、吸引和彼此发现。这种“真”既应该是“诗性的”又应该是“历史性”的,是“美学”和“见证”的互补。新诗之“真”不仅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生命体验有关,而且也与语言修辞能力带来的深度“可信感”有关。对“历史真实”的处理和还原历史、重写历史以及历史的考古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受到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甚至“重写诗歌史”成为了时代热潮。而陈超的可贵之处又在于他在梳理勘测诗歌的当下时代境遇的同时前瞻诗歌可能的发展前景,又以谨慎、反思的知识分子立场在除魅中返观历史,穿透被历史烟云无情淹没的诗歌真相和寒冷时节坚冰下隐现的溪流。在《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和《红色苍凉时代的歌声——谈“知青歌曲”》以及对张郎郎、郭世英、食指、北岛诗人专论中陈超重新考量文革岁月中被误认为是一片荒漠的荒芜干涸的枯冷河床。在资料的整理、发掘和梳理中,陈超将被省略和淹没的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从“冰峰”状态提升出来,将“坚持个人主义自由灵魂的美丽青春”和“个体生命小小的光明”呈现出来,将当代诗学的本体性和先锋诗人的个体主体性通过历史谱系连接起来。
对于“新诗史写作”陈超则在《必要的“分界”:当代诗歌批评与文学(诗歌)史写作》中强调了诗歌批评与文学史写作的区别,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诗歌批评和诗歌史写作的密切关联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堪忧的问题,“当代文学(诗歌)史与当代诗歌批评的这种过分密切的关系,无疑有特定历史时期所带来的特殊性的一面,而且应该说受益良多。但是,长此下去,又会带来文学(诗歌)史被动受到批评制约,接受批评界彼时的‘命名’,让有可能经过时间沉淀后得到的对‘固定化’描述的自觉反思付诸阙如。”[13]
四、“诗野游牧”与“现代诗话”
多年来陈超散文、随笔性的批评文字以及类似于“诗话”的“断章”值得批评同行们注意。这些文字体现了陈超作为一个杰出诗人批评家对批评作为一种“文体”的自省意识。
尽管陈超身处学院长达30多年,但是他一直对一味“知识化”“学理化”“体制化”“掉书袋式”、“贩卖式”的没有温度、性情和见识的“学院派批评”不屑一顾。诚如他所说“我既忝列‘学者’,又在高校工作,不免要写些中规中矩的供‘圈儿里’交流的学术文章。但近年来,我日渐对那种讲坛森严、城堡傲立的学院作风心生厌倦”[14]。在陈超看来这些排斥了心灵体验甚至“奇思异想”的被“学理”、“行规”“高校”牵制的文章很多是无效无用的。尤其是对一些毫无趣味性可言的体大虑周掉书袋式的的学院派和高头讲章式的唯理论和体系为是(甚至某些时期还充当了整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帮凶与工具)的诗歌研究,陈超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和省察。由此,陈超一直倾心于自由本真心灵诉说和谛听式的体验式批评。这集中体现于《生命诗学论稿》、《游荡者说》、《诗野游牧》。这些特殊性的批评文字既带有知识分子的省思意识和精神难度,又有批评话语自身的特殊性——有诗性、见性情、有见识。也就是陈超所说的“有感而发,笔随心走,释放性情,带着热气。”这些带有趣味性、紧张感的批评方式不仅成为陈超近年来批评的动力,而且对于当代诗歌批评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性。而在我看来,这种细微、自然、原生、随性、独到、独立的话语方式无论是最初在《论诗与思》(1987-1989)、《蓝皮笔记本》(1987—1995)、《塑料骑士如是说》中展开的“诗话”实践,还是全面体现于这部《诗野游牧》的成果,这种话语方式是难以被模仿的,因为它只能属于批评家少数人中的少数人都够所为。

赵建成作品-《碎片》之四 雕塑 木 33×29×83cm 2013(驻留计划)
《诗野游牧》不是一般意义上向传统“诗话”的致敬,而是陈超多年来自身诗学建设本源性的一部分,来自于其诗学话语的核心。这种“现代诗话”是直接关乎生命与词语、精神之间相互打开的方式,是趣味,是性情,也是个人诗学的信仰。正如他所说“现代诗话”像哈根达斯一样“教我欣喜,感到甜”。而早在1994年出版的《生命诗学论稿》这本书中这种关于“现代诗话”的话语方式就已经初步建立。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之交的历史语境下这些“现代诗话”又带有着知识分子特殊的精神镜像,那些分裂、阵痛、焚毁的精神体验一再出现。这些精简、俭省而又灵光迸现、颇见性情、机趣频生的文字如一道道闪电。这种批评话语真正做到了“少即是多”。陈超的“现代诗话”做到了词语和精神之间凛冽而温暖的相互激发、性情与知识的彼此映照、经验与感应的契合、理性与感性的对应、敏感与自持的有效性平衡。正因如此他诗歌批评的独特魅力和特有的趣味、性情已为诗坛津津乐道。“现代诗话”给陈超所带来的是新的动力和真正的快乐。而长久垂心于“现代诗话”很大程度上又与陈超作为一个优秀并且具有重要性的诗人密切关联。没有对诗歌创造性的秘密和深隐的意趣深有同感和兴会彻悟的人,没有对诗歌创造的细节和蛛丝马迹、草蛇灰线抱有探幽烛微能力的人,没有对诗歌的闪电具有探雷针一样敏锐和领受力的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近乎于“诗话”但又具有明显差异性的诗歌批评话语方式的。再者说回来,“新诗”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拒绝“诗话”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倾心于修辞炫技和词语智力游戏的文本而言更是如此。
陈超先生的诗歌批评就语言自身而言是中国诗歌评论家中最为“讲究”和具有难度的。因为在陈超先生看来,“新诗学”也是一场语言的实验。他的批评文本自身几乎对每一个词语都经过了反复的斟酌、推敲和捶打、淬炼,而这一过程却又非常可贵地在保持高度精准度和直入腠理的同时维持了语言自身的生成性趣味。陈超的诗歌批评真正做到了一种写作的创造性,因为批评自身也应该是一种文体。在陈超这里追求“母语的荣耀垂直洞开”的有难度的语言方式不仅不是拒绝阅读的,更不是艰深晦涩、枯燥无味的。而这种话语方式在精神本源上是与“诗话”传统一脉相承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诗话”就比其他批评方式要更高级和进步,而是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对批评家自身的要求更高。“诗话”的吉光片羽的闪现,俭省词语与机心妙得的个人修为确实能够支撑诗歌这种特殊文体的核心,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容易造成某种程度上因话语“缩小”方式所带来的“整体性”架构的丧失和弱化。而陈超的“现代诗话”则一以贯之的是深化了这种“整体性”——批评文本与灵魂高度之间的互相激发和激活、创设。这实际上也是对批评家自身的生命力、活力、性情、趣味、兴味的超级难度的考验。而陈超不仅经受了这种近乎残酷和噬心的话语考验,而且还领受到这一过程中的快乐与慰藉。这也是为什么陈超先生能够在一个时期坚持在石家庄北郊的一个房间里常年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了。实际上那时陈超生活得并不轻松,甚至还有些沉重。

第三届明天当代雕塑奖开幕式1
《诗野游牧》所体现出来的批评话语的心态和心境也是深有意味的。与其他优异的诗评家一样,陈超先生在以往的诗学论著《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中国先锋诗歌论》、《游荡者说》、《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以及《诗与真新论》中体现的当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沉思、忧患以及担当意识是非常明显的。这实际上正是陈超所说的在“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驱动下对灵魂和困境的双重揭示的艰难过程。而到了《诗野游牧》,如此诗意、轻松、舒朗、清逸的言说方式确实给几十年来的诗歌批评话语自身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空间。从“游荡”到“游牧”这是一幅如此让人心醉神怡的场景:一个中年男人骑着一匹不染纤尘的白马,手拿一本诗集,腰间斜跨着芳醇的美酒在葱绿的花香四溢的草原上游牧,随心所欲之地处处是自然而惊心的风景。这实际上正如陈超所说是在寻求一种差异性、局部性、偶然性和“无政府状态”的表意策略,像是一场自由、开阔、流荡、丰富、散逸而鲜润的“游牧”。从“游荡”到“游牧”,其间的转换过程并不轻松。多年来,这两个批评者形象一直在陈超的诗歌研究和写作中共时性存在。“游荡”多为痛苦、孤独与沉重,而“游牧”的诗意、宽怀、放松和任性显然更带有理想主义甚至诗学的个体乌托邦的意味。在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往返和跋涉正是陈超多年来诗歌批评工作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对于这种“游牧”式的“现代诗话”而言,陈超真正做到了“以小博大”。看似词语和句段容量紧缩的过程实则展开的是一种开阔和鲜活。这正如茫茫大海上撒网的过程,收放自如,缩进然后敞开的过程正对应了“诗话”的本质。也正如陈超所言这既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写作,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世界的“思想方法”。这真正意义上回应了诗歌批评本身作为一种特殊性写作的文体与创造。唯有如此,也才印证了诗歌批评工作所需要的特殊才能——“诗有别趣”。“诗野游牧”,无论是在现实的雾霾中还是在诗歌批评的践行中都显得如此可贵、难得,当然也更携带着难以想象的难度。
我所希望的则是陈超先生继续骑着白马在逐水草而居的路上缓缓前行,任意东西。精神的游历和放牧与复杂性的、现代性的精神游荡同等重要。关键所在就是很多人并不具备这种“游牧”的能力。而像陈超这样同时具备诗歌批评的“游荡”和“游牧”精神的人只能是这个时代批评场域中的一个奇迹了。对于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三十多年的从业者,你最后一次封好了漂流瓶。这一次你是永远的转身,决绝地走在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你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批评家,我不能不又一次在泪水中重复你多年前的诗句——“我目光焚烧,震动,像榴霰弹般矜持——/在最后时刻爆炸!裸体的桃花第二次升起/挂在树梢。和我年轻的血液融为一体。/但这一切真正的快乐,是我去天国途中的事”(《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

第三届明天当代雕塑奖开幕式2
注 释:
[1] 其他六部诗论集:唐晓渡《临风的芦苇》、耿占春《隐喻》、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钟鸣《徒步者随录》、陈东东《词的变奏》、西川《让蒙面人说话》。
[2] 乔治·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严忠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 其诗学专著主要有《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上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中国先锋诗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游荡者说——论诗与思》(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2月)《辩难与沉默:当代诗论三重奏》(陈超、唐晓渡、耿占春,作家出版社,2008年1月)《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中国先锋诗歌论》(台湾秀威,2013年1月)《诗与真新论》(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诗野游牧》(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12月)。
[4]T.S.艾略特:《批评批评家:艾略特文集·论文》,李赋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5] 西川:《内行的工作》,《热爱,是的》,勒口,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3。
[6] 陈超:《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生命诗学论稿》,第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7] 陈超:《论现代诗结构的基本问题》,《打开诗的漂流瓶》,第131-14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8] 在这里需要摒弃一种曾经长期存在的对艺术和文学形式的偏误,即认为形式是内容的附属和容器。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在20世纪西方文论和中国新时期之后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与重新认识。
[9] 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第13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0] 西默斯·希尼:《希尼诗文集》,第20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11] 陈超:《 生命:另一种“ 纯粹”》,《 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第2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2] 陈超:《深入当代》,《生命诗学论稿》,第2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13] 陈超:《必要的“分界”:当代诗歌批评与文学( 诗歌)史写作》,《 诗与真新论》,第285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
[14] 陈超:《游荡者说·后记》,第284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