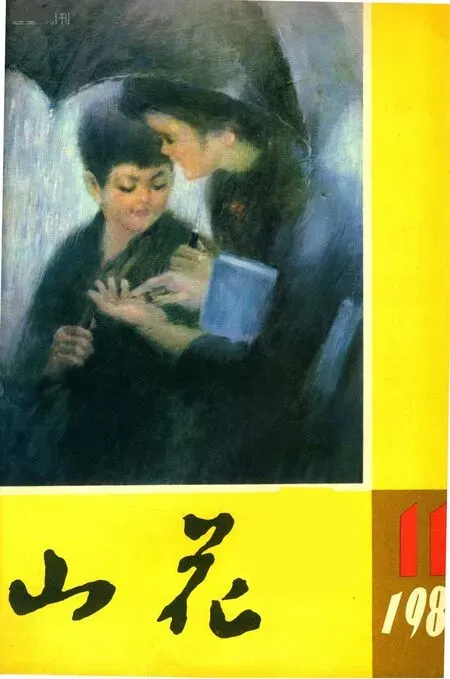恶性书写的伦理价值——我们该如何理解陈希我?
唐诗人
李敬泽在陈希我小说集《我疼》的序里说:“陈希我从来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说家。他根本不能指望人们喜欢他或者爱他。/我不喜欢他……这厮是个疯子,他不把你搞死誓不罢休。”[1]李敬泽这种带着反讽、调侃的欣赏式表达,说明了陈希我小说即使在欣赏者眼中,也是另类的、特殊的。确实,到目前为止,谈起作家陈希我,人们首先想起的还是他有多残忍、凶狠,甚至是有多变态为主。如果去查询关于陈希我小说的评论文字,其中最刺目最耀眼的还是“残酷”、“冷血”、“毒辣”、“阴狠”等词汇,平和一点的形容词也只是“偏激”、“先锋”、“异端”、“疼感”等。为此,“极端化书写”、“黑暗写作”、“非常态书写”、“深度异化的写作”等表述语,成为了小说家陈希我的个性标签,成为了人们判断陈希我小说特征时的基本维度。也许,这些判断并没有问题,某种程度上,它们确实指出了陈希我小说的特异所在,但是,如若要理解陈希我,仅仅指出一种特异性是不够的,文学的生命力不止是形式和词汇的舞蹈,更是价值和意义的探究,我们必须探究它作为时代精神作品的独特价值,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所谓“变态式写作”何以必需、何以难得。
在价值问题上,陈希我这种写作,首先遇到的就是伦理价值问题。但是,陈希我这种以表现恶和残忍为叙事风格的文学,如何思考其伦理价值呢?如果从传统的道德批判来看,很多人会认为陈希我揭示黑暗和痛苦的写作无益于社会,认为这是憎恶人生、反人性的写作,他把充满光明的世界书写得阴沉沉的,无法给予人们阅读的愉悦感,难以让人看到生活的希望。南帆总结过传统道德批评所蕴含的两种假定:“第一,它假定文学对不道德的内容再现或表现,极有可能使这种不道德的案例变得普遍化了,而且,文学的形象性和情感性又强化了人们对这些不道德事件的主观反应,而不断强化的主观反应会导致人们把不道德事件视为一种无独有偶、自然普遍的现象……其次,道德批评往往假定文学的道德或不道德内容与作品的社会道德效果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似乎再现了什么样的道德内容的文学作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道德效果。”[2]因此,如果从这种传统道德观念来看,陈希我那种不断挖掘人性恶和书写社会阴暗面的小说,只能是备受指责。确实,很多人无法欣赏陈希我,普遍被其词汇选择和故事外表的残恶阻拒在外。有很多人直接表达了对陈希我作品的憎恶,他们认为陈希我作品流氓化、极端化,读来特别压抑,使人绝望,是一种需要否定的写作方式。这种阅读感受作为个人的读后表达,无可厚非,但若要用外力去否定这种写作,无疑是一种文学偏见。为此,我们需要仔细辩驳,去探究一种理解恶性叙事的可能方式,去思考这类叙事方式的伦理价值是如何呈现的,以及该如何呈现。
从早期的《我爱我妈》,到后来的长篇《抓痒》和《大势》,以及《母亲》和小说集《我疼》,我们都可以阅读到一个无处不喜欢残忍笔法的作家陈希我,即使在《移民》里,很多妥协式的选择,也暗含了非常多的残酷情节。在《我爱我妈》里,那种乱伦悲剧刺破人心,它洞穿伦理,拷问人性,其残忍程度,让多数人无法感觉到它任何可能的积极意义;在《抓痒》里,陈希我让人物有意识地、主动地去寻求残恶的刺激,以突出小说人物生活的无聊和精神的麻木。小说中的暴力、虐待,重重地锤打着人物的麻木婚姻,敲打这一剧痒疮疤,把一种血淋淋的场面、惨不忍睹的境况呈现给读者,令人胆寒。长篇《大势》是一部伦理虐剧,小说把社会(国民性)批判和人性批判结合在一起。在人性批判层面,小说中的父亲,他对女儿的爱,如对前世情人一般,把“爱”放大到极致,把一种只能作为人性阴暗那面的、一闪即过的念头,放大式地书写出来。展示,并使用暴力、残酷的情节作为展示的途径,这无疑是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剖析方式。社会批判方面也尤其尖锐,有着当年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冷峻和锐气。谢有顺曾指出陈希我的写作接续了鲁迅、张爱玲那种逼视存在、书写黑暗的文学传统。[3]确实,在阅读陈希我作品的时候,那种与鲁迅接轨的感受异常清晰。当然也有很大不同,某种程度上,陈希我的叙事更加阴狠。如果可以比较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这么形容:如果说鲁迅是点到为止的讽刺,那么陈希我就是大加渲染的鞭打,如果鲁迅是冷峻隽默的批骂,那么陈希我可以是阴冷残酷的剖白。
陈希我这些残忍的小说,如果要用传统的分析方式,去寻觅多数读者希望见到的温情,可能会比较艰难。当然,如果分析起来,自然会有所发现。比如贺仲明就指出:“在陈希我对现实日常世界的批判和阴暗化揭示中,也偶尔可以看到隐藏在背后的内心痛楚和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在他所表现的虚无生活背后也可以看到爱的一丝光明。”[4]他举了《我们的骨》《到天堂去》《旅游客》等作为案例,认为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还是保留了些许美好的希望,对虚无的反抗,即使无力得很,也可以看到作者笔端的同情和理解。我们当然相信这些温暖之光的存在,但也必须承认,这些温情成分,不容易发现,且细微而弱小。为此,探讨陈希我作品的伦理价值,我们必须转移方向,往一种整全性意义上的伦理去思考。我认为,应该用小说修辞学的理解方式进入其中,即把这些小说从整体上看做是修辞形式。陈希我之所以要那么阴狠,要让人不舒服,特意去寻找冒犯的笔法,其实是想让故事具备震撼力的效果。为此,我们最好不要去寻找具体的悲悯细节,不从具体的语段中发现作者流露了哪些悲悯。陈希我的悲悯,不是字面上的感伤、感慨,而是让故事结束后,让读者感受到“恶”所能造成的惊惧和恐怖,进而在具体的世俗中避开恶、防范恶。正如约翰·洛克曾表达过的,恐惧是有力的当头棒,将我们从迟钝麻木中唤醒。

葛平伟作品-《·结·》之三 木 30×30×300cm 2014
以《母亲》为例,这篇小说里,陈希我一如既往地用其绝望之光,去照耀母亲去世前前后后的一切,主要是那些围拢过来的亲人之心,包括“我”自己的念头。小说始终在做心理剖析,把“我”以及亲人们阴面的人性挖掘出来。有论者也指出:“从这个文本,我们体味到的是一种无从逃离的伦理绝境。叙述者秉持人性悲观论,是一个彻底的生命本体意义上的绝望者。”[5]也许,阅读《母亲》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或者叙事人“我”的那份哀伤和无力感,通过这种无力的困境,激起读者深刻的哀思。在这里面,我们跟随着作者的叙述,体会隐藏在叙事人“我”内心里面的那些阴暗,最终,我们也成为叙事者的同谋,也沉浸在一种由作家虚构的伦理处境中,并连同叙事人一起愧疚、痛苦。但当故事结束,理性的读者,可以迅速超离文本,对小说提供的那种伦理处境进行反思,这反思有自我的、内在的道德反省,也有社会的、外在的伦理批判。
陈希我呈现的真实不是一般的生活事实,而是人性本质上的可能性真实。对于这种可能性,陈希我用的是极端化的呈现方式,如卡夫卡等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们的写作那般,他把人物性格极端化,或将某种伦理困境极端化,或者抓住人们内心深处那些只能是猛然浮现、然后迅即消失的罪恶念头,然后把这些念头放大,进行故事演绎。比如《我疼》集中的小说,都是些触目惊心的非常态故事,以追求极致效果的情节叙述把读者引入罪恶之境。在它的世界里,阅读是个感受不安的过程,这种不安逼迫我们去思考:生命的存在该如何变得有感觉?在成为有感觉的途中,人内心那些躁动不安的疼痛感该怎样去应对?它咬噬着他人、吞噬着自我吗?病痛、丑陋、麻木、仇恨、底层、背叛、炎凉的世态、虚伪等等,面对这些盛行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我们真的能够无视它们、然后自以为是地过着平静生活吗?人都希望幸福,希望生活没有疼,可我们真的能够撇开疼吗?其实,疼不是可以撇开的问题,它一直都存在着,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正视它。这个世界从不缺少疼痛,缺少的,只是对疼痛的深入审视、思考和咀嚼!而且,作者不仅要我们去咀嚼疼痛,也呈现了咀嚼这种疼痛的可怕性。沉迷于疼痛同样是一种可怕,像《我疼》一篇的“我”,溺于疼感,是种极端的受虐,它血淋漓地撕开了生命中的疼痛,却也从极端处把人的怜悯之心和憎恶之心调动起来,而最为自然的阅读效果当然是平衡:它让我们思考疼,却也让我们懂得沉溺于疼痛的可怖。
陈希我这些演绎伦理困境的作品,若要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道德,不能以文本的具体内容写了什么来判定,而是要超离文本,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应该进入一种对象化、客观化的阶段,才能发现陈希我提供的那些故事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和伦理意义。这里我们可以联系阎连科的小说观。阎连科的故事,也基本上会引起惊悚感,他叙述的也多是恶人,阐述罪恶的社会和人性。对于这种文学的伦理意义,如阎连科自己讲过的,如一个瞎子晚上经常打着明亮的电筒,目的不是给自己照路,而是让别人知道他的存在,于是避开他。也就是说,书写人性的卑琐一面、塑造恶徒形象,这种文学的伦理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看到恶的力量多么强大,让人看到人性中可能的恶性因素,进而避开它、防犯它。[6]陈希我所提供的故事,也正如瞎子在黑夜里打开的电光,虽然是黑暗的灯光,但他的书写就是照亮这些黑暗。他让我们看见各种各样的“恶”是怎么回事,引导我们去思考、去审视。他所叙述的那些故事,呈现了人性中那些可能腐蚀生活的欲望渊源和罪恶本源。他让我们去直面这些罪恶,去领悟罪恶为何会发生,以及它们又是如何被发展放大的。这种叙事,让疼痛更为直接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虽然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难受、难安,但这些虚构出来的痛苦感,总比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不知黑暗而撞入罪恶来得更为轻微,它们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

葛平伟作品-《·结·》之十四 木 尺寸可变 2014
苏珊·桑塔格在一个演讲中提到小说作为道德力量这一问题,她说:“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作家必然是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人:思考什么是公正与不公正,什么是更好与更坏,什么是令人讨厌和令人欣赏的,什么是可悲的和什么是激发欢乐和赞许的。这并不是说需要在任何直接或粗鲁的意义上进行道德说教。严肃的小说作家是实实在在地思考道德问题的。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的共同人性,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讲的故事扩大并复杂化——因此也改善——我们的同情。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7]这就是现代小说作为修辞方式本身的道德力量,它所引发的伦理效应不是在文本中给读者提供某种值得模仿的行为,更多的是提供一些伦理想象,通过故事、叙述来培养我们的同情心、改善我们的伦理判断能力。
当然,陈希我这种写作,要实现以上的理解,肯定需要读者具备特定的文学修养,普通读者难以接受。为此,陈希我也有反思,对如何呈现自己的写作伦理,他曾经对媒体表达过这样一个困惑:“写作要尖锐,但是写作的伦理何在?我这种写作在伦理上到底有没有问题呢?希望今后能有新的改变。”[8]我不知道陈希我所希望的改变会是怎样的改变,但我相信他那种挖掘人性阴暗面的写作嗜好是不会改变的,甚至不需要改变。当然,其小说也并非完美无缺,依然有需要增进的地方,过于阴狠就把作品的亲和力消弭掉了,丧失了众多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脆弱的读者,限制了自己思想的传播范围。当然,陈希我若取消了狠角的写作姿态,其小说的锋芒性就不够了,尖锐程度的减弱,可能就把他前面所树立起来的写作风格取消了。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尴尬的悖论问题。对此,我觉得可以借鉴巴塔耶论文学的“恶”时提及的见解,他说:“文学是本质,否则就不是文学。恶——尖锐形式的恶——是文学的表现;我认为,恶具有最高价值。但这一概念并不否定伦理道德,它要求的是‘高超的道德’。文学是交流,交流要求诚实。按照这一概念,严格的道德来自对恶的认识,这一认识奠定了密切交流的基础。”[9]也就是说,文学书写恶,是要实现高超的道德,实现这种道德要求作家对恶本身有着高超的认识,这种高超的认识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高超的认识即是超越世俗性的善恶判断的认识。善恶判断是一种道德问题,它呈现为人们生活在世时的各种选择。在原初的生命体中,在上帝造人的开端时刻,善恶是不分的,只是吃过智慧果后才能区分善恶,也就是掌握“知识”后才形成善恶判断。作家张大春认为只有一个大概意为“我站在高处”的希腊字,才真正适合小说的价值。他认为小说自身必须站在高处,它必须在疆界之上、之外。[10]按我的理解,张大春的意思,也是认为小说不是简单地为某一个人间的伦理观或者哲学思想服务,它超越世间既成的规则。其实也就是要保证小说要去“表现”本质的、整全的真实。作为一种虚构的艺术,小说的价值不在于作家们为了阐释某个既有的观念而虚构一个故事出来,而在于他们虚构出的故事能够自成一体,呈现自身的丰富内涵,让读者体会到一种超越现世伦理的丰沛思想。这也许才是陈希我的改变方向,如果他要有所改变的话。

葛平伟作品-《·结·》之十六 木 10×10×400cm 2015
文学本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学,其伦理学内涵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作品对人的价值生活和伦理处境的深层次关切。布罗茨基说:“每一新的美学真实,使人的伦理真实更精确。”[11]陈希我的小说,虽然在语言应用上偏爱带有刺感的话语,其故事也主要是着力于挖掘社会阴暗面和人性罪恶面,但这其实是一种极为难得的文学选择,他努力去呈现最为真实的面目,用一种审判式的写作,审判人心也审判这个社会。他的故事呈现赤裸裸的伦理真实,这种呈现暗示了陈希我的道德考量,他用故事去刺破虚伪和残恶,也用残恶的笔墨来鞭挞人心的麻木和懦弱。韦恩·布斯说,小说的道德问题归根结底是责任问题,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小说的“伟大之处和实际效用在于其孜孜不倦的努力,将读者本人引入道德生活中去,邀请他审视自己的动机,并暗示现实并不是传统教育引导他所理解的一切”。[12]陈希我的文学选择,其实就是要承担根本责任的写作,他相信作家应该在根本上去承担道德职责,即把小说创作看做一种叙事修辞,在叙事中呈现超越世俗规则所界定的伦理场景,极力去发现人生与社会中的各种伦理困境。在这些可能性的伦理真实中陈希我希望读者明白:何为真正的道德生活,以及何为本质的伦理诉求!
注 释:
[1] 李敬泽:我疼·序[A].陈希我.我疼[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 南帆、刘小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83-184.
[3]谢有顺.为破败的生活作证——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J].小说评论,2006( 1):12.
[4]贺仲明.尖锐的撕裂与无力的唤醒——评陈希我的小说[J].当代文坛,2007(3):34.
[5]廖述务.不可焚毁的遗像——评陈希我中篇近作《 母亲》[J].名作欣赏,2011( 7):30.
[6] 阎连科.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Z].见:http://cul.qq.com/a/20141022/039677.html
[7] 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18-219.
[8] 尚晓岚.陈希我:写作的伦理在哪里?[N].中国青年报,2014-5-30.
[9] 巴塔耶.文学与恶[M].董澄波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2.
[10] 张大春.小说稗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0-111.
[11] 约瑟夫·布罗茨基.美学乃伦理学之母[Z].汪剑钊译.见: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09-07-04/36646.html
[12] 莱昂内尔·特里林.知性乃道德职责[M].严志军、张沫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