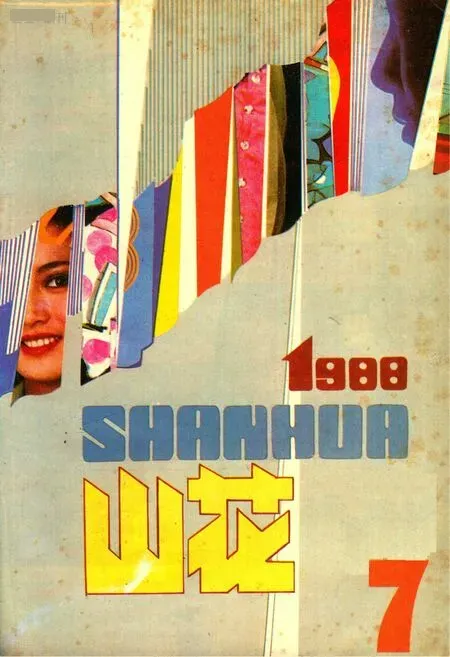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外一篇)
墨 白
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庄子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变化成了一只翅膀上布满了美丽图案的蝴蝶,于是感到非常地愉快与惬意,在充满阳光的花丛间自由地飞翔,他忘记了自己原本是庄周。突然间醒过来,惊慌不定之间方知原来是他庄周。可是,看着眼前黄昏暗淡的光线,庄子迷惑不解,“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庄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1]庄子是一个天才的哲学家,《庄周梦蝶》超脱了具体的论说,直接从心灵感悟入手,让我们进入了梦想与真实、物质与精神、生与死等等这样繁杂的哲学话题。
我之所以提到《庄周梦蝶》,那是因为这个故事和“物质化时代,如何安顿我们的欲望”的话题有关。这在里,我们所说的物质,毫无疑问,是对我们所处社会现实的隐喻,而“欲望”,则是对我们精神世界的隐喻。《庄周梦蝶》里的“梦想与真实”、“物质与精神”、“生与死”这些哲学话题,恰恰和我的长篇小说《欲望》三部曲里所包涵主题不谋而合。
《欲望》分红、黄、蓝三卷,蓝卷《别人的房间》所探讨的就是生与死。著名画家黄秋雨神秘失踪,两天后,他的尸体被一个渔夫在颍河里发现。锦城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方立言受命对此案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渐渐发现,黄秋雨,这个曾经留学具有西方哲学与文化背景、内心充满激情的艺术家,在我们庸俗不堪的日常生活中,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黄卷《欲望与恐惧》探讨的是物质化时代的欲望。吴西玉是一个从某高校下到县里挂职的副县长,一方面是家庭,婚姻是和社会合作的性,然而在这个被社会认可的性里他却是一个被压抑者,是一个受害者,一个逃亡者,他企图从这个合法的性里逃脱出来;另一方面是他所追求的爱情,这是被我们视为与社会抗争或者反叛社会的性,然而欲望的无度却让他感到了恐惧。合法的性与抗争的性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本质,从而使吴西玉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和自我。他因欲望而产生的恐惧、焦虑、忧郁,他的迷惘,他的怯懦,和现实中的我们如此的相似;红卷《裸奔的年代》所呈现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梦想与真实”。小说写一个名叫谭渔的乡村小学教师,通过自己的奋斗,在他34岁那年终于以作家的身份来到了城市。他提着自己的行囊,在小学的操场里告别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暗暗发誓,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家人带来幸福。然而,七年过后,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经历了纷乱现实的洗礼之后,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的妻子和儿子视他为陌生的路人。在深秋寒冷的一个夜晚,当他坐在人祖伏羲的陵墓前回想往事的时候,他经历的所有一切都仿佛一场可怕的梦境,就像几年前他前往项县寻找师范时那个曾经给他生下儿子的恋人遇到的汪丙贵的灵魂,谭渔无法分辨自己身在何处,他经历的所有一切都化成了梦境。谭渔在不停地追求自己的梦想,然而他却在现实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他梦想到达天堂,然而他终始都没有弄明白,其实,天堂就是一个梦,是我们人类的心灵所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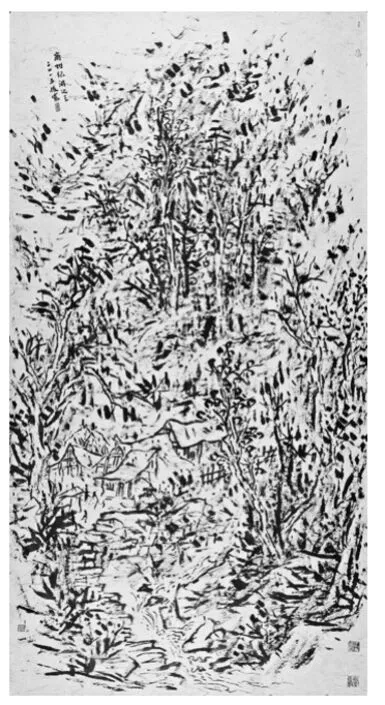
崔振宽作品-《商州纪游之三》 232×119.5cm 2015
“从明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2],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海子所表达的是他绝尘弃世的生活态度,在他的生活里,他所渴望的不是我们平常人一般的世俗的幸福,而是“从明天起”,海子获得幸福的立足点不是今天,而是明天,是永远没法到达的明天,因为现实生活永远停留在今天,停留在当下的一瞬之间,在我们的生命里,明天就是永远无法到达的未来,“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向大海”[3],海子面对的不是当下的现实,不是我们身处的无法避开的日常生活,他把自己理想中的幸福世界与世俗现实对立起来,将神性与平庸的日常生活对立起来,他面对的是我们无法探求的隐藏着无限秘密的大海。所以,在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的三个月后,年仅25岁的诗人来到了山海关,他在铁路边一直徘徊了很久,我们不知道在海子那里都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推猜一下,当海子在铁路边徘徊的时候,如果海子生命里曾经过的那个几个女性,无论是哪一个在那个时候向他发出真诚的关爱,他还会抛弃他的母亲在铁轨上躺下来吗?
加缪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如同在情节剧中一样,自杀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所超越或者他并不理解生活。”[4]加缪还说:“降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的唯一真正的职责就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途经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5]现实与梦想是人类生存的两个世界,现实与精神各自独立存在又不可分割,所以加缪说:“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6]生活是做工低劣的产品,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我们又没有办法拒绝购买它。如果我们没有梦想,怎么来面对黯淡的社会现实?尽管费尔巴哈说“天堂是人们编造出来的谎言”,但是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梦想,不能没有天堂,我们要坚信我们的梦想,哪怕我们的梦想只是像赫胥黎在《美妙新世界》里所描述的“乌托邦”,我们也一定要坚信梦想,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
1942年7月10日,西斯托·罗德里格兹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在他28岁那年出版了音乐专辑《冷现实》,但只卖出了35张;第二年他又制作了《从现实来》,这张唱片的销量比第一张还凄凉。随后,他就被唱片公司除名,去了建筑工地当了一名工人。

崔振宽作品-《南国神游之三》 232.5×119.5cm 2015
1971年,一位美国女孩随意带着一张《冷现实》来到南非,送给她的男友听。意外的是,罗德里格兹对现代城市的控诉、对底层艰辛的表达和他清澈的嗓音在南非那些信奉自由主义的年轻人中产生了共鸣。20世纪七十年代的南非人非常保守,种族隔离严重,没有电视,一切都被禁止被审查。“一早上醒来头就很痛,一跃而起穿上衣服,我打开窗户听新闻,耳边只有体制下的音乐。”罗德里格兹《冷现实》中的《底层蓝调》给南非年轻人以启示,在他的歌里,那些受压抑的人心得以释放。于是,他成了反叛的标志。在罗德里格兹的音乐走红的时代,南非正因源于1910年的种族隔离制度而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制裁,1974年,南非被取消参加联合国一切活动的资格,之后又被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和石油禁运。南非人听不到来自国外的任何消息,到处是军事戒严,完全闭关锁国。不安、反感、渴望自由,罗德里格兹的歌十分准确地描述了当时处于孤岛中的南非人的普遍心态,在南非,罗德里格兹的歌仿佛一种正义的声音,给人希望和出路,罗德里格兹的歌仿佛无处不在,他的专辑加上盗版卖出了上百万张。
然而,在开普敦,你可以得到关于“猫王”或者“滚石”的消息,而罗德里格兹,这位戴着墨镜身穿红色背心盘腿坐在唱片上的歌者,却像一个谜语,没人能猜出他的年纪和身高,更看不清他的相貌,甚至有人传言,这位伟大的歌手已经去世——在最后一场演唱会上,因为音乐事业走向下坡路,罗德里格兹遭到满场嘘声。他温柔而安静地感谢了在场观众,在唱完最后一曲之后开枪自尽。另一种传言也堪称摇滚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场景:他在舞台上点火自焚。为了解开这个巨大的秘密,南非两个执着的乐评人,斯蒂芬和克雷格开始艰难的寻找。没有资料,他们就从罗德里格兹的歌词中寻找线索,歌中有阿姆斯特丹,他们就去荷兰;歌中有纽约,他们就去美国;歌中有底特律,他们就去密歇根;就在他们无望地将要放弃时,在他们的网站上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那个神秘歌手并没有吞枪或自焚而死,这个被工友称为“诗人”、偶尔会穿着燕尾服来上班的建筑工人仍然活着。
1998年,在退出歌坛25年后,年近六旬的罗德里格兹踏上了南非的土地。在开普敦机场,他和女儿们小心翼翼地绕过前来迎接他们的豪华加长车;在酒店里,低调的罗德里格兹睡在沙发上,他不忍心把酒店的大床弄乱。但他是如此的平静,在山呼海啸、座无虚席的演唱会现场,他平静得就像回到了家。像是年轻时在小酒吧里唱歌,仿佛这一切早已在梦中演练过无数遍。他平淡地接受生活给予他的一切,即使25年之后,当这世道又让他开口,他站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仍然像过去的每一天那样平常。在此之后,他陆续在南非开了40场演唱会,每一场都爆满。巡演结束后,我们的歌手再度回到美国,一如既往的进行劳作,每天去工地工作八个小时。现在,这位年过七旬的歌手已经没有力气去干那些重活,白天,他默默的走在小镇的人行道上,身子有些歪斜,但他行走的姿态却让我们感动;晚上,他回到家,喝喝小酒,弹弹吉他,他有些沙哑的歌声,仍然是那样的动听。是的,生活是美好的!而我小说里的我的那些兄弟,谭渔、吴西玉和黄秋雨,他们却没有认识到这些,现实无情的时光已经刻满了他们的额头,他们活得是那样的痛苦,活得是那样的艰辛,活得是那样的没有尊严。让我深感痛苦的是,对此,我们而又无能为力。

崔振宽作品-《高秋图》 178×96cm 2006
1950年12月,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演说时说:“我感到这份奖并非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劳作的——那是深陷在人类精神的痛苦与汗水中的一辈子的劳作,之所以劳作,不是为了荣誉,更不是为了利润,而是想从人类精神的材料中创造出某种过去未曾有过的东西。”[7]是的,这正是我想要表达的。是的,我们的生活要有梦想,同时,我们的生活也要脚踏实地,我们要好好地生活,我们要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朋友,给生活在这个纷乱社会里的人们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最后,请允许我把一首名为《你鼓舞了我》的歌献给您:“每当我心情低落,我的灵魂如此疲惫/每当麻烦接踵而来,我的内心苦不堪言/然后,我会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直到你出现陪我小坐片刻/有你的鼓舞,所以,我能攀上高山/有你的鼓舞,所以,我能横渡狂风暴雨的大海/当我倚靠着你时,我是如此坚强/因为你的鼓舞,让我超越了自己/没有任何人的人生,可以不经历痛苦/每一颗跳动不停的心,是如此不完美/但当你出现,我的生命便充满惊奇/有时候,我以为我看见了永恒/因为你的鼓舞,让我超越了自己。”这首歌的原唱是西域男孩,2010年,在“荷兰好声音”上,一个57岁的中年男子演唱了这首歌。二十多天前,我的朋友前往故乡新疆莎车奔丧,在安葬了父亲之后,她把这首歌传给我。当我听完这首歌,我真的泪流满面。
做一个气质高贵的人
物质和物质化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拥有物质和一个物质化了的时代,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被物质化了社会,只有丧失了理性的欲望。丧失了理智的欲望就像一列高速奔驰的列车,人们乘坐这趟列车,发疯地去追求金钱,权力、地位、异性和荣耀。而物质,则是人类获得生存、获得自由、获得尊严、获得高贵的精神世界的基础与保证。
迪拜是从上世纪70年代起凭借“石油美元”由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中东乃至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被高度物质化了的大都市。可我们在谈论迪拜这样的城市时,却很少涉及文化层面,当我们在谈论人类的文化遗产时,怎样都无法避开像俄罗斯、法国、英国这些曾经产生过众多的人类精神偶像的国度。所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是在拥有了丰厚的物质的同时,又要具有高贵的精神世界。
昨天,我从我们街区的街道里路过,看到路边寒风中站着的一个卖烤红薯的老乡。是的,我们没有谁不同情这些劳动者,可问题是,在夜晚来临的时候,他炉子口的四周还摆放着一圈没有卖完的烤红薯。我们有谁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一下?我们的兄弟站在灰红的路灯下面,那一刻,他一准是用乞求的目光看着过往的行人来光顾他。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仍然留在炉子上的烤红薯使他满腹的愁肠,他甚至有些胆怯地看着那些从他身边川流不息的车流,在这种境遇里,他精神的高贵从何而言呢?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为生活而奔波。一个秋雨如注的夜晚,我拉货的人力车就停在公路边,我身下铺着身上盖着同一块塑料布,躺在人力车下面,没有人知道我的饥饿;在寒冷的冬夜里,我躺在人力车上单薄的被子里,任由我的小毛驴顺着公路拉着我往前走,没有人知道我的寒冷;在寒风里,我运货的人力车车胎没气了,我要把车支起来,然后把车胎扒下来,拿到公路边的跑沟里就着火盆补胎,我身上浸满了汗水的衣服开始渐渐变凉,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我所承受的苦难;在我寄人篱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自卑;在我浑身长满了黄水疮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的伤痛……所以,我深深理解我站在街边卖烤红薯的兄弟,在本质上,我们有着相通的血缘,就像从梦中醒来的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大甲虫一样,我们卖烤红薯的兄弟同样被残酷的现实生活所污辱,并丧失了做为一个人获得尊严的勇气。所以,我们应该深深地懂得,物质是获取精神高贵的基础。然而,一个人能成为精神贵族,在拥有了赖以生存的物质之后,还需要用一生的时光来历练。
庄子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清晨的菌类不会懂得什么是晦朔,寒蝉也不会懂得什么是春秋,这就是短寿。楚国南边有叫冥灵的大龟,它把五百年当作春,把五百年当作秋;上古有叫大椿的古树,它把八千年当作春,把八千年当作秋,这就是长寿。“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8]朝菌和寒蝉叫做小年。灵龟和椿树叫做“大年”,“小年”是不会了解“大年”的。世人都说彭祖活了八百岁,是人间最长寿的了。彭祖对于灵龟和椿树来说,不也是“小年”吗?世人把彭祖认为是长寿,不就是“小年”的悲哀吗?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故事的寓意:人在不同的境遇里,心中的理想是不同的。我们精神成长的历史,也是有阶段性的。
我的老家是淮阳县,我幼年居住的那个名叫新站的镇子由于靠近颍河,一个人只有半亩耕地,由于那个时候的农业生产落后,我们在一年当中就有半年缺少口粮。所以,我对饥饿有独特的感受,对于吃,也有着特殊的经历。我父亲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因为所谓的经济问题被判了三年徒刑,对于我们家来说,那是雪上加霜。我母亲只好带领我们兄妹在夜间给供销社推麦面,因为白天要到生产队里劳动,去挣工分,所以只有在夜间推石磨,来换取麦麸充饥。一天夜里,母亲把我们兄妹从睡梦里叫醒,让我们吃饭。那顿晚饭母亲给我们做的是好面叶,淡的,可是没想到的是,我们竟然在碗底下捞到一块红薯。那时红薯刚下来,鲜物。记忆里,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后来我才知道,世界上有无数种比这好吃的美食,可是我压根就不知道。有一年的春季,我拉人力车运货往漯河去,在路上,我看到两个城里的青年,他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脚上各自穿着一双雪白的球鞋,穿着天蓝色的确良布做成的裤子。我真的羡慕他们,那一刻,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穿着雪白的球鞋,穿上天蓝色的的确良布做成的裤子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行走。可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白球鞋更好的鞋,还有比的确良更好的布料,我就像庄子说的朝菌一样,我不知道世上有日月,我就像庄子说的寒蝉一样,不知道世上还有春秋。庄子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的科学,如果那个时候有今天对宇宙的认识,他一定会说我们世间的一切对于宇宙都是这样的渺小,对于动辄上亿年的地质,对于茫茫为我们所不知的宇宙,我们人类不就是朝菌和寒蝉吗?
是的,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有人可以一夜暴富。可是我们也要明白,如果要培养一个贵族,是需要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努力。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在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住了刽子手的脚,王后立刻停下来习惯性地向刽子手轻声道歉:“对不起,您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即便是即将到来的死亡,也无法遮盖一个人的高贵。
1919年西尔维娅·比奇从美国来到巴黎,开办了著名的只出售英语著作的莎士比亚书屋。1920年7月,38岁的乔伊斯和他的家人来到了巴黎并结识了比他小五岁的比奇。当比奇读过乔伊斯被美国新闻当局查封的正在纽约《小评论》连载的《尤利西斯》后,决定以书店的名义出版这部著作,在后来的日子,她致力于《尤利西斯》的出版,为了发行,包括后来成为了英国首相的邱吉尔都成了她征订的用户。她本计划用《尤利西斯》的出版来作为庆祝乔伊斯的40大寿的贺礼,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延误出版,但是为了乔伊斯的寿辰,她特意请印刷厂先印制了两本《尤利西斯》,当乔伊斯看到样书时,感动得满眼泪花。《尤利西斯》从初版到1930年,一共印制了11版,这使乔伊斯一下子成为了巴黎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学名人。尽管后来比奇被乔伊斯以及家人在《尤利西斯》的发行上产生了误解,使莎士比亚书店遭受到了经济损失,但是,在1929年当《芬尼根的守灵》连载遭到非议时,比奇仍然邀请了十多位作家给这部作品召开评论会,并把作家们的发言结集出版,随后,又帮助乔伊斯出版了这部小说的摘编版。
哈里特·肖·韦弗年长乔伊斯六岁,这位英国女性不但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资产,而且受过良好教育,青年时她阅读过大量书籍,成年后从事妇女平等权力的斗争。韦弗通过作家庞德认识了乔伊斯,并在自己主编的《唯我主义者》的刊物上连载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还自己出资刊印了这部小说。当她获知乔伊斯生活困难时,从1917年开始就通过庞德给乔伊斯提供资助,并要庞德不得透露自己的姓名,仅在1930年以前,韦弗就向乔伊斯资助了2.3万英镑,大抵相当于现今的七十万英镑。乔伊斯去世后,她不但支付了他的全部丧葬费用,而且帮助出版《乔伊斯书信集》,自愿做乔伊斯的文学代理人。
应该说,比奇和韦弗都是具有高贵精神气质的女性,由于她们的无私与慷慨,我们人类才得以认识到乔伊斯这样伟大的作家。物质是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有了丰富的物质就可以拥有高贵的精神气质。从1912到1936的24年中,鲁迅的收入总数目为十二万四千四百元左右,这些包括薪水、讲课费、稿费和版税的收入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430万元左右,平均每年18万人民币[9]。当下年年都有作家排行榜,而那些每年都有上千万稿费收入的作家们,未必就有鲁迅先生的骨头硬。《史记·陈涉世家》里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陈涉年轻时,曾经和别人一起被雇佣耕作。一次他停止耕作走到田埂上,感慨恼恨了很久,说:如果将来富贵了,彼此不要相互忘记。一块受雇佣的伙伴笑着应声说:你是受雇替人耕作的农夫,怎么会富贵呢?陈涉叹息说:“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10]我们也可以把这故事用在人类的精神境界上。精神境界低的人,是不能够理解精神境界高尚的人的行为的。

崔振宽作品-《嘉陵烟雨》 70×68.5cm 2006
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渴望财富;当我们拥有了财富之后,才发现只有财富并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在拥有了财富之后,还要做一个精神高贵的人,要成为一个精神高贵的人,那么你的一生就要不断地修炼。
一个人的修养,是要依靠大量的阅读来完成的。所以,阅读对于我们来说就变得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时代的阅读十分的功利,读者大多都选择和自己职业有关的书籍,把别的书籍都看做没用的闲书。因此,闲书就可读可不读。不错,对于被物质化的人们来说,读闲书确实无用。可是我们应该明白,正是读闲书毫无用处,它才是一件大事,我们阅读,正是因为它无用。这就是道家的最高境界,无为而为,道法自然。从1163年到1345年,法国人用了180多年来建造巴黎圣母院;从1386年到1897年,意大利人用了511年来建造米兰大教堂;从1248年到1880年,德国人用了六个多世纪来建造科隆大教堂,这就是人类对精神没有功利的阅读。如果一个亿万富翁他只拥有金钱,那么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庸俗的穷人。是的,一个人获得物质是不那么容易,但是一个人要成为精神贵族,成为一个气质高贵的人,那需要像建造巴黎圣母院、建造米兰大教堂、建造科隆大教堂一样漫长的修养过程。
注释:
[1]《庄子·齐物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45页。
[2] 《海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3] 《海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4]《加缪全集·散文卷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70页。
[5]《福克纳随笔》(美)威廉·福克纳著,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15页。
[6]《加缪全集·散文卷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69页。
[7]《密西西比》(美)威廉·福克纳著,李文俊译,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149页。
[8]《庄子浅注·逍遥游》,中华书局,1982年10月版,第4页。
[9] 见《文化人与钱》陈明远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0]《史记》,司马迁著,延边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16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