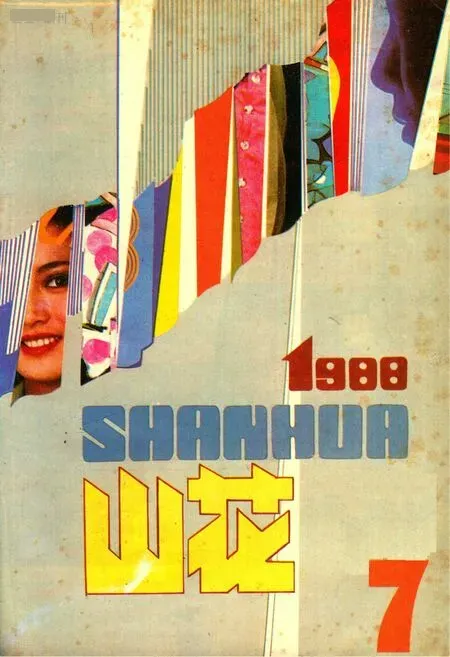豹诗典(之五)
蒋 蓝
有欲则变豹
由保罗·施拉德导演的电影《豹女》,1982年上映,娜塔莎·金斯基(Nastassja Kinski)担任主演。她16岁即与比她大25岁的波兰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同居,在其指点下于1980年主演《苔丝》。如果说《苔丝》展示的是一个少女的内心苦闷,那么,她在《豹女》当中的忘情与投入,就是灵魂与肉身的大搏杀。我以为,电影名字叫《女豹》更合适:在于性别修饰了豹性,“人”不过是豹子身上的另外一种斑纹。
豹经过长期的修炼终于变成了人,一个靓丽非凡的人,开始在现实社会里过着和平常人一样的生活。她一旦动情与男人云雨交欢,人的所指已经无法宰制豹的能指了,她必须返回豹子的躯体,最后把跟她做爱的人吃掉以后,力比多平息如夜光下的丝绸,她才能重新变成人。在她的地下室里人们发现很多人骨骷髅,这是女豹周而复始的欲火之骸。某天,她爱上了动物园的领导奥利弗,她渴望与这个男人做爱,这个男人自然也是手忙脚乱。但是,她知道这样不行,一做爱她就要变成一只豹子,把男人干掉。后在他们两人克制不住的危急时刻,她成了豹子。豹女还有一丝理智,打开身体风一般逃走了。从这一感情之劫流亡,她就变不成人了,就是一只紧张的豹子。最终她被追捕,并被关在动物园的铁笼里。动物学家常到铁笼子里去看她。隔着铁栅栏,这全然不是里尔克面对的那头旋转的黑豹,因为女豹眼角的裂纹,流出来的,是蜜。这个结尾反而让人欣慰;:他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尽管隔着一道铁栅栏。
显然,有欲则变豹,不是中国人的有欲则“豹变”。观众在这种“西方画皮版”的惊悚片里心醉神迷,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当中的艺术样品。而人、兽之恋的同类题材,集大成的《聊斋志异》展示了很多类型:海螺、蚌、鱼、蛇、狐狸、树精、花妖甚至老虎,但在中国的修炼文化里,没有豹。豹是高度谨慎的动物,举勺而称量欲望,岂有如此“豹行”。
黑豹与白豹的意象之变
艾滋拉·庞德在《石南》一诗中咏叹道:
黑豹走在我的身边;
在我的手指上,
飘着花瓣一样的火焰。
牛乳一样白的少女,
从冬青树中直起身子,
她们雪白的豹子,
注意着跟随我们的足迹。
庞德说:“意象不是一个意念。它是一个放射的光点或簇。”由此,作为一种奇妙的植物,石南花的根虬结多节,具有浓稠色彩,开花一如古典主义者的秋风大吐血。其意象在庞德想象里如同精怪的杜鹃一般,勾勒出了凌空而飞的豹子。叶维廉的翻译也的确老道,深得事物精髓。诗人采用两个极端的色彩之喻,也可以视作阴阳之比,“白豹”只好跟随“黑豹”的踪迹而行,其“白与黑”的柔滑镶嵌,美得不可方物。按照庞德说法:“我们不得不称之为‘漩涡’,许多不同的意念向其中冲出冲进。”石南花激发的“漩涡”,是男女之欢,抑或是濒死之和解?
上帝就在细微之处
作为小说家的雷蒙德·卡佛,其神妙的圈套设置与突然的工笔化描摹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淹没了他的诗歌。在我看来,他的小说是披雪之山——我们不知道雪原之下的陷阱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他刻意为之,而他的诗歌则是无雪也无云的山巅孤石,他贴地而行的精微描述,呈现出一种朴素与静立的大美,如同“上帝就在细微之处”的论断一样,卡佛的诗歌进一步印证了卡洛斯·威廉斯著名的诗学箴言:“Noidesbutinthings”——不要观念,除非在事物之中。诗者应忠于现实,反映认识现实生活的美,而不必雕琢,不必引经据典,观点早已经是事物的蜜汁。细节是诗的起点,无数的细节构成了生活的终点——它们为生死搭建了一个绝美的斗拱。
但是,保罗·瓦雷里也讲过一句反话:“感觉是万物,实则是虚无。”
我读到孙仲旭先生翻译的雷蒙德·卡佛《豹子——写给约翰·海恩斯和基思·威尔逊》,与其说是豹子,不如说是记录追寻豹子的历程,具有小情景剧的结构。直到豹子现身,“我也看着它,忘了开枪。随后它又跳起来,跑出了我的生命。”这一精妙的结尾,不禁让我联想起法国作家柯莱特《兰花》当中,豹子以自己的美,在枪口下获得了一次美的历险。柯莱特的“兰花豹”是以香气直达猎手善的本源;卡佛的豹子,则是以踪迹打开了无以复加的细微之物,被那道横贯苍穹与土地的柔情之光普照下,得到了灌浆。这是一头“最文学”的豹子。
我曾在克里基塔特镇和同名河流附近
哥伦比亚河峡谷的一处人迹罕至的箱形峡谷跟踪过
一头豹子,我们是要去打松鸡。十月份,
灰色天空延伸到俄勒冈州乃至更远,
一直到加利福尼亚。当时我们还都没去过那儿,
去加利福尼亚,可是我们知道那里——有种餐馆,
你想多少次加满盘子都可以。
我那天跟踪了一头豹子,
如果跟踪这个词用得对,在那头豹子的上风头一路
扑通扑通地走,擦碰着身体,也抽烟,
一根又一根,状态最好时也就是个
紧张还淌着汗的胖小孩,可是那天
我跟踪了一头豹子……
后来我在客厅里醉得摇摇晃晃,

崔振宽作品-《苍山图》 69.4×137.5cm 2009
一边找词语把这件事讲出来,零散点缀着关于此事的
回忆,在你们两个人已经把你们的故事,
黑熊故事,讲了之后。
突然我回到了那道峡谷,在神智不清的状态下。
好多年我都没有再想到过的事:
那天我怎样跟踪一头豹子。
我就讲了,反正是试着讲,
我和海因斯这时很醉了。威尔逊听啊,听啊,
然后说,你肯定那不是一只山猫吗?
我私下认为这句话是奚落我,他来自西南,
是那天晚上朗诵过的诗人,
随便哪个傻子都分得出山猫还是豹子,
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喝醉了的作家,
多年以后,在自助餐厅里,在加利福尼亚。
去他的。后来那头豹子从灌木丛里稳稳地大步出来,
正好到了我面前——天哪,它长得多大多漂亮——
跳到一块石头上扭头
看着我。看着我!我也看着它,忘了开枪。
随后它又跳起来,跑出了我的生命。
崩塌的山岳
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一生硕果累累,汉语读者最熟悉的应该是《白轮船》和《断头台》。《断头台》描述了两只狼(公狼塔什柴纳尔以及母狼阿克巴拉)的命运,大结局惊心动魄——狼崽被人偷走,两只狼终于被激怒了,它们疯狂地袭击羊群……作为“动物诗学”叙述的高手,2006年推出了艾特玛托夫的封笔长篇《崩塌的山岳》(谷兴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7月版),博大精深,饱含忧患,深入反思了全球化时代精神和生态的双重危机,批判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侵蚀。
小说在天山山踝一线展开了利润对生态的攻城掠地场域:山脉绝顶处被猎杀的雪豹为象征,以失败的独立记者萨曼钦为线索,以吉尔吉斯新兴起的经济寡头、来自阿拉伯的石油大亨和天山脚下穷困潦倒的山民为对照,以当地民间传说为背景,展示了全球化风潮之下,古老文化与生活节奏被席卷的命运。
那是一只雄性雪豹(当地民间称之为箭雪豹),飞纵于天山的河谷与沟壑之间。它有不少后代,现在年老体衰,筋骨松软,衰老得在潜伏猎敌时,它竟然听见了自己的喘气声;在交配权的决斗中它已经不是独耳朵雄雪豹的对手,眼睁睁看着昔日的伴侣被夺走,等待它的只能是寂寞与死亡召唤。艾特玛托夫展开了他细致入微地描摹,雪豹被自然法则淘汰时的悲哀绝望;另一方面,雪豹也能够从大生命的法则来接纳生命更替的轮回。小说写到,当老雪豹离开族群,形影相吊、茕茕孑立时,它突然看到了出双入对、缠绵不绝的雪豹:“它站在巨石嶙峋的高原之巅,倚靠着刺柏的弯曲多瘤的树干,漫无目的地环顾四周,猛然看到,在下面,沿着峡谷,一对新婚的雪豹在飞奔,——一雌一雄,青春年少,首次结合,充满力量与欲望,且奔且舞,戏谑地相互啃咬,为的是点燃激情,以便摆脱自己凡俗的躯壳,飞离尘世,凌空翱翔……”
如果说海明威把那头著名的豹子放置在了人迹罕至的灵台之上,如果说柯莱特的兰花豹以香气融化了猎手的内心,那么,艾特玛托夫的雪豹却不幸置身于一个经济时代。雪豹的世界观与商人无关,更与全球化无涉。
老雪豹并没有抵达自己的终点,它被设计猎杀。雪豹连同保护雪豹的记者萨曼钦在山洞里一并死于乱枪之下,这个意外扭转了上帝的意志。雪豹之死也隐喻了萨曼钦纯真爱情的彻底破产。那时两位阿拉伯石油大亨乘坐波音737专机,从西亚阿联酋到中亚吉尔吉斯坦山区狩猎,在那么多随从和当地商业经营者乃至政府官员的精心安排下,去猎杀雪豹。但富翁们又被当地人绑架了,最后,石油大亨说过:“这就是我们的全球化,我们也要拿自己的那一份。”分明表达出一个古老民族在面对新世界、新秩序和不义之时的无奈、愤怒和疯狂。
亿万富翁克鲁奇(John Kluge)曾说:“为了运动而杀生这是形而上学家们时常在寻找的那种纯粹罪恶的完美典型。……打猎者喜欢死亡胜过喜欢生命喜欢黑暗胜过喜欢光明。”我敢说,喜欢打猎的富翁们,喜欢掠夺他者的生命胜过了一切。热爱全球化的他们,自己一定是最怕死亡的。
诗歌中的亚里斯多德
《诗歌总集》也译作《漫歌集》,不但是巴勃罗·聂鲁达文学生涯最高的光,也是美洲现代诗歌的觇标,又因为在汉语里的巨大发行量,某种程度上已然是诗艺之圭臬。全书分为15章,共有248首诗,约1.5万行,是一部足可以与古代经典比肩的诗歌巨著。诗集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的1400年一直写到1949年2月,以浩繁卷帙展现了拉丁美洲长达500多年的漫长历史:包括古印第安文明时期、征服时期、殖民地时期、独立战争时期、独裁统治时期和美国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时期,再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和典型场景,《诗歌总集》不但是磅礴无俦、绚丽斑斓的美洲英雄史诗,而且,聂鲁达俨然就是诗歌中的亚里斯多德。1986年6月8日,我参加自贡市文联组织的一个笔会,在四川乐山市区的新华书店买到了王央乐先生翻译的这本已经被翻阅得颇为陈旧的巨著,心中的狂喜压过了三江汇合口的波涛。
在这本厚达761页的汉译诗集里,聂鲁达展示出的对动物、植物、矿物、历史遗迹、人物的描绘,宛如修建金字塔所必需的一个漫歌似的坡道,他将诗性慢慢推举到马克丘·毕克丘之巅。他从一只黑鹰、一只巨嘴鸟、一棵巨树、一条大河、一个面具乃至一座孤峰、一个独裁者开始,当然还有美洲豹,像吹笛人一样,将之汇聚成一个大地歌者不可分割的音域。第一章《大地上的灯》即是拉丁美洲大地的自然风貌:6节诗分别描写了植物(树木、玉米、黑莓等)、兽类(鬣蜥、蚂蚁、羊驼、骆马、猴子、美洲豹、美洲虎、大松鼠、水蛇)以及各色奇妙的鸟(红冠鸟、巨嘴鸟、蜂鸟、鹦鹉、老鹰、秃鹫、椋鸟、火烈鸟、信天翁),还有蛛网密布的河流(奥林诺科河、亚马逊河、特肯达马河、比奥比奥河)、丰富的矿藏(绿宝石、煤炭、铜、、钨、钒、蓝宝石、黄金)和文明遗址(玛雅人、阿兹台克人、瓜拉尼人等)。
Jaguar,作为世界上体格第三大的猫科动物,美洲豹无声,在丛林里晃动它壮硕的腰身,聂鲁达数十处撷取了它的姿容与气息。
在《一些兽类》一诗里(见《诗歌总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10页),他在空气里捕捉到了鸟音,指出置身的语境——“这是大蜥蜴的黄昏”。诗人眼中的黄昏看来是宁静的,他将美洲的动物渐次铺排,动物们进一步加剧了黄昏的色度,铺天盖地,弥漫游移。大蜥蜴确是一种耐得住寂静的动物,但美洲豹的美丽却渐渐被黑夜一片一片衔走——
……
美洲豹以它失去的磷光
轻擦着叶簇;
美洲豹在树叶之间奔跑,
仿佛吞没一切的火,
同时在它身上,树丛的
沉醉的眼睛在燃烧。
……
这看不见的火在奔突,搅动森林里全部的树叶,那是豹的子民,它们开始舞蹈。但火的危害总是与树叶擦肩而过。“从你的树丛里,/豹子射出火焰,/那是你的种子所产生。”(见《西梅内斯·德·克萨斯(1536)》)火如何成为生命之水?魔术师是豹。奔突的火,终于在《气候》(见《诗歌总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373页)里尘埃落定:
秋天,从白杨树上落下
高处的箭,那重新恢复的遗忘;
双脚陷进了它的纯洁毯子;
激恼的树叶的寒冷,
是一处黄金的沉重的泉源;
一阵棘刺的光辉,把
矗立的身材的干枯烛台,置于天边;
黄毛的豹子,在爪子中间
藏着一滴生命之水。
到了生命晚期,诗人在“天问”式的短语集《疑问集》里,诘难人们对大自然贴出的标签,而词语的石头似乎有些靠不住了,符号依然是不可还原的意指单元。他发问:“和平是鸽子的和平?/花豹都在进行战争?”
豹是无法被确认的
美国小说家、诗人罗恩·拉什的《炽焰燃烧》收录了12个短篇小说,基调是美国南方阿巴拉契亚山野的幽暗与沉默,在那里出没的人与动物,好像都是陌生而簇新的,又因为背景的遮蔽,人与动物,获得了一种中国写意画里宣纸的浸润与自然变形。
如何在一个十分具体的地域空间,让人与自然的恩仇吸允足够的普遍性的汁液?这一直是拉什思考的终极方向。他的语体简洁,有一种岩石的特质,而他对情感的表达、人物的刻画却是异常富足的。《信仰美洲豹的女人》展示的是一个女人在南卡罗来纳山区疑似与美洲豹相遇的故事。中年女人露丝的心理危机源于因为新生儿出生时死亡,留下了浓郁的阴影。她参加母亲的葬礼归来,疑心自己在路上看到了美洲豹。第二天,她去动物园与专家交谈时,误将一对母子当成了被拐买的儿童以及拐买者……
小说中,美洲豹是若有若无的,不但显示出作家拉什对于神秘事物的偏好,也暗示了人总是容易被不确定的事物所诱引。

崔振宽作品-《山村清晓》 90×40cm 2010
这个高于尘世的物种一旦显现,她就忘情投入寻找,是让失去孩子的女人忘记悲伤,还是寄托了她另外一种思念?我们不是很清楚,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也颇为迷惘。在我看来,思念一如美洲豹,或者说美洲豹是母爱的一种赋形,因为这本身就是无法被确认的。心盲的俄狄浦斯,已然无法确认自己的血亲。
在小说结尾,那个长久的、不肯离开的凝视,一片模糊,她仍然紧紧凝视,带来了强烈而普遍的人性关怀:“在她的体内深处,有样东西挣脱了束缚”。同样,在小说在《萨琳娜》中,罗恩·拉什也隐约地描写了一头从未露面的美洲豹。这种写作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拉什作品中另一个常见的主题:“另外一个美国”在当代社会中留存的美国精神。
围绕《萨琳娜》里的对话,美洲豹被话语定在在传统的天幕上:
“美洲豹,”萨琳娜说,“美洲豹在这里很常见吗?”
“潘伯顿夫人,美洲豹在这里几乎已经绝迹了,”威尔基安慰道,“我可以负责地说,本州的最后一头美洲豹在1920年就被人捕杀了。”
“但当地人坚持认为还存活着一头,”布坎南说,“关于这头美洲豹本地流传着不少流言,工人们对此都深信不疑。据说这只美洲豹身型庞大,但是关于它的颜色却说法不一,从浅黄到乌黑都有。我倒情愿这只是流言而已,但你丈夫却希望真有这么头美洲豹,他希望豹子能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这样他就可以猎食它了。”
“那是他结婚以前的想法,”威尔基说,“现在潘伯顿先生已经是个结了婚的男人,他一定放弃猎豹的想法,而去选择一些更为安全的消遣方式。”
“我倒希望他去捕猎那头美洲豹,如果放弃的话,我会对他失望的。”萨琳娜转身面对着潘伯顿的同伴们,但这番话却好像是对丈夫说的。“潘伯顿是个不惧挑战的男人,这正是我嫁给他的原因。”
加莱亚诺心中的美洲豹
20世纪80年代,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写出史诗《火的记忆》三部曲,用神话和诗篇回溯美洲千年历史。汉语版终于在2014年年底才推出了第一部,真可谓姗姗来迟。书中有《美洲豹》一节,加莱亚诺颠倒阴阳,讲述了作为美洲豹的猎手,与巴西印第安卡亚波部落的年轻人波多科之间的恩仇。分明是“农夫和蛇”的他者版本。不同之处恰在于,善良的是美洲豹,不义的是人。
美洲豹教会了年轻人波多科使用火,用火烘烤食物,用火取暖。卡亚波人把所有非印第安人都称为“库本”,毫无例外,即使这一头救了自己性命的美洲豹也被视为入侵者。年轻人波多科痊愈后最后杀死了美洲豹的妻子,并带领族人血洗了美洲豹的家园,抢走了火……
加莱亚诺写道:“那时候起,美洲豹就憎恨人类。关于火,他只剩下瞳孔中闪闪光的火的影子,狩猎时,他只能依靠尖牙和利爪,生吃捕获的猎物。”他到底想说忘恩负义呢?抑或另有所指?比如,人的这种凶残性是亚马逊丛林所固有的?还是人性比豹性更恶劣?奇妙的加莱亚诺却闭紧了嘴。
梭罗渴望的母豹之力与豹色语法

崔振宽作品-《春雨》 144.5×75cm 2011
大仲马在《布拉日隆子爵》里调侃:“那个阴险的女人刚才的话音里有着最亲切的语调。她摆出女性的样子说话,藏匿起一只豹子的本性。”将凶险的女性比之于母豹,毫不奇怪。亨利·戴维·梭罗却并不这样看。他于1847年9月6日离开瓦尔登湖,重新和住在康科德城的他的朋友兼导师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一家一起生活。他决定研究自然史,纯是出于天性。他承认“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条猎犬或是一头豹,如果他生在印第安人之间,一定是一个残忍的猎人”。
梭罗认为生命是与野性相伴而存在,最有活力的东西是最野性的,它没有被人所征服,它的存在能使人恢复清新的精神。而时代标榜的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文明,梭罗感叹道:“这里有广袤的、野性的、荒僻的自然,我们的母亲,她无处不在,如此美丽,对她的儿女如此爱抚,就像母豹一样;而我们却很早就从她那里断了奶,投向了社会,转向只有人与人交往的文化——这种近亲繁殖充其量只产生了英国的贵族,是一种注定要很快达到极限的文明。”母豹所具有的爱,是利齿上的舞蹈,是布满倒刺的舔舐,是不顾一切的呵护与捍卫。
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表达过他接近于梭罗的理想,是成为“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让设备不停运行,但在其他季节里随着驼鹿迁徙的计算机工程师”。梭罗标举的母豹之爱其实是大地母性,他看出另外一种品质: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与大自然更好地相处而不只是从她身上强取所需,有这样的可能吗?即使是以语言为性命依托的诗人,语言也不是逻各斯式的,诗人应该像蝴蝶一样从荒野花卉里获得给养。梭罗在《散步》里说:“西班牙语中有一个对于这种野性而幽暗知识的绝佳表述:棕色语法(Gramáticaparda,西班牙语,也翻译为豹色的语法)——一种母亲的智慧,它就来自我刚提到的那只母豹。”语法不仅属于语言,而且也属于文化和文明本身。这样的语法规则就如同森林中长着苔藓的小溪,沙漠散落的砾石。(《禅定荒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84页)
扑朔迷离而又充满玄机的世界,“豹色语法”是诗人刻意捕捉的目标。但万物以自己的语言在说话,以自己的语法在精微地表述情感,真正的诗人探寻奥义的过程也就是在探寻万物的语法,即“找到自身进入象征结构的方式,给予了我们数以千计的有关人类语言的豹子语法。”修辞学和宇宙哲学同时选定了同一个实体:是一个渴望融入野地、痛饮露水的人。荒野是野性的贮存库,所谓写作,斯奈德说:“写作就像是驼鹿在雪中留下的足迹”。
参考书目:
《尔雅注证——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的历史记录》(上下卷),郭郛注证,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山海经注证》,郭郛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埤雅》,【宋】陆佃著,王敏红点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山海经新探》(论文集),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山海经研究》,张春生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修订版),袁珂编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
《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版),袁珂校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
《中国神话传说》(上下卷),袁珂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神话资料萃编》,袁珂、周明编,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古神话选释》,袁珂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大禹及夏文化研究》(论文集),巴蜀书社1993年版。
《禽虫典》,蒋廷易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本草纲目校点本》(全4册)李时珍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版。
《博物志校证》,【晋】张华撰,范宁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
《汉语动物命名考释》,李海霞著,巴蜀书社2005年5月版。
《岭云关雪——民族神话学论集》,王孝廉著,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全2册),巴蜀书社2001年版。
《邓少琴遗文辑存》,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日本怪谈录》(第二版),【日】柳田国男著,印祖玲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