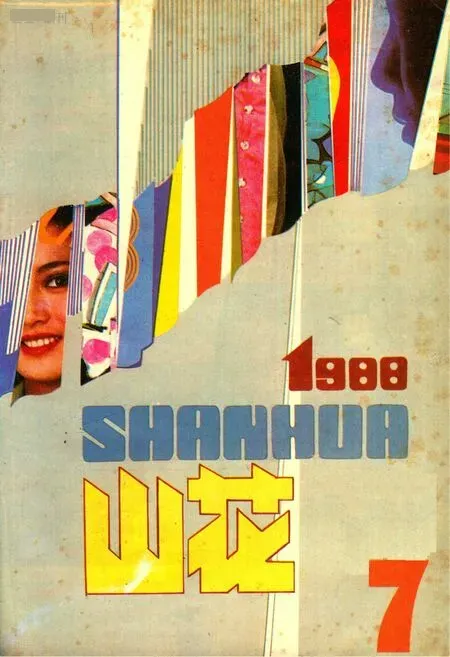人民艺术家
前面还有两个人。时间已经接近十二点。
会议要推后,这是一定的。座谈会正式开始时,已快十点了。大领导很意外地推迟光临。我们不能说领导迟到,领导来晚那不叫迟到。她的发言排在第十位,也就是最后一个。开始时主持人说了,今天共有十位同志发言。现在是第七位,一位独角戏演员。
她再次看自己的发言稿,拿起笔,改改画画。会议通知时说,每人准备十分钟左右的发言。她在家里试过了,十二分钟,在标准之内。前面人的发言,大部分都在十分钟以内,只有俩人,超过了限定。
一会儿觉得有句话要加上,一会儿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简练一下,打印稿很快被涂得五抹六道。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不管大会小会,每次都是亲自写发言稿,再请当编辑的侄女把关修改。侄女有时候不在本市,她就打电话将稿子念一遍,请她给遥控指导。
“只要人民还需要,我就永远唱下去。”去年,在她从艺六十周年庆祝会上,她给记者这样说,之后这句话作为标题,出现在报纸上,她被报纸称为人民艺术家。那次庆祝会的余温还未散尽,起码在她的心里,还未完全散去,或者说一辈子都不会消散,想起来就热热地滋润身心,让她有种重返青春的感觉。时机真是好啊,忽如一夜春风来,举国上下,又大力提倡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了,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了,大家又想起了她。这就对了,在她心中,艺术何尝不是为人民服务呢?没有人民,哪来艺术?她这一生,为人民唱戏,为戏迷唱戏,她就是为唱戏而生的。十五岁被选到剧团,经过几年的艰苦学艺,二十岁后逐渐崭露头角,从此走上一条听惯掌声,见惯鲜花的道路,没有了这两样东西,她真不知怎样生活。当然,这两样东西,也是世上最短暂最昂贵的,要拿汗水和青春抵押,要用痛苦和枯燥兑换,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恰似毒品,没有人能摆脱它的魔力,那么就拿整个生命去换取它。哪怕它转瞬即逝,见风使舵,最爱易主,我们也要像摘取天上的星星一样,搭了天梯,奋力去够它。
花木兰,穆桂英,李双双,梁秋燕,张梅英,这些女中豪杰,坤界翘楚,她都演过,李双双还作为现代戏被拍成电影,全国公映,成为她永恒的经典,那时人们都不叫她的本名,只叫她李双双。这么说吧,在几十年里,她雄踞本剧种一号女主角的地位,金刚底座,水泥镶嵌,像这座城市雄伟的城墙根基不可撼动。当然嘛,威胁也是有的,世上任何一座王位之侧,都会有觊觎,进攻,挑衅,有暗中的诅咒和策反。当然能感到四面射来的目光,不只是爱慕,不仅是顺随。也有独处时的心惊和担忧,更有暗里的加固与周旋,处心积虑的防范与反击,表面上要装作淡泊得很,根本不在乎,随时可以禅让。她也曾在五十三岁时以老迈之身,再次争演新排传统剧目《穆桂英挂帅》,惹得年轻演员怨声四起,哟,真把自己当穆桂英了,五十三岁又领新军。有几位急着出头的演员,在心里咒她,走出剧团大门碰上车祸才好。胜者为王,胜者宽容,她暂且不管这些众怨。不争,不抢,不跑,不要,那金光闪闪的桂冠,难道能自动飞到你头上不成?
第八位发言者,是一位网络作家,不用说是年轻人,一个圆脸姑娘。她很谦虚,很简洁,首先表明她能参加这样高级别的,隆重的会议,并被安排发言,是她最大的荣幸,她为此备受鼓舞,今后也将怎么怎么着,反正就是那一套吧,不必细说。
昔日李双双坐在她旁边,看到她侧面脸蛋,真年轻啊,面部、脖颈的线条均呈向上趋势,顶多有三十来岁吧。想自己三十来岁,啊,那是四十年前,全国只唱样板戏,作为地方戏来说,抒发革命情怀,歌颂大公无私,跟风排了一些小戏,她扔下家里嗷嗷待哺的女儿,下乡,进厂矿,给革命战友演出。
年龄大了,脑子不好使,很多确凿无疑的事,转眼就忘。那天,她在短信里问侄女,是“呆在家里”,还是“待在家里”,这两个字,应该用哪个。她在写自己的回忆录,和侄女说好,写完后,由侄女给她把关润色,给她找出版社,如果出版社不能正常出版,需要作者自己掏钱,侄女再帮她找人赞助。戏曲不景气,她收入不高,更没有什么巨额出场费,她和老伴,基本靠退休金生活。出一本书几万块钱,那对她确实是个问题。侄女说了,就不信你当年的戏迷里,这会儿没有几个大款?
侄女没有回信,她想,或许出差了,不在本市。她也没有打电话,年轻人都忙,满世界跑,去这学习,去那开会,常常一打电话,她小声说,开会呢,一会儿给你打过去,或者,火车上呢,信号不好,前面到站给你打。可常常她就忘了再打过来。第三天,侄女来短信:姑姑,前天那会儿正忙,一打岔忘记这事了,今天突然想起。两个字用哪个都行,只要全书统一就好。对不起啊,年龄大了脑子不好使,请原谅中老年妇女噢。她嗔怪地骂一声,你才多大,四十来岁,就在我跟前儿卖老。啊,想想她当年四十多,才拍完李双双,功成名就,你去问问一个工人、农民,可以不知道省委书记是谁,但都知她的大名。进京演出归来,省委书记手捧鲜花亲自接机,几步走上前来,将并不老的她搀扶着,只为把她的胳膊握在自己大手中。天天收发室送来一沓子信,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出。那才是她人生的黄金时代。可这会儿她看着短信,痴痴地想,我问的是哪两个字呢?她跟自己较上了劲,就不看前面的短信,只在这里锻炼自己大脑。执着与执著?唯一与惟一?作料与佐料?当作与当做?天哪,才过去两天,就彻底想不起来了,没办法,承认自己已然老透,翻出前天短信,噢,呆在家里。她是写,现在,我呆在家里,安享晚年。回忆人生,我对生活与观众充满感恩。当然,在这之前,她也写到,退下来后,剧团有活动不再叫她,按说这是顺理成章,可她失落啊。她一个不能离开舞台的人,一个到处出席会议的人,怎么能一下子在各种场合消失了呢?不,她要发挥余热,她要为人民唱戏,没有舞台不要紧,社会就是大舞台,观众买不起票没关系,她义务演出。不论何时何地,一旦人民需要,一旦有机会,她还是要为人民唱戏,哪怕站在环城公园,清唱一段,哪怕是在建筑工地,随口唱两首流行歌曲。

崔振宽作品-《秦岭大壑》185×96cm 2012
轮到第九位发言时,会议室里的钟表,两个指针就要向最高处聚拢了。主持人说,现在,最后一位,著名画家高利奥同志发言。嗯?怎么回事?这,这,难道是把她的发言取消了?时间到了?之前也常有会议,主持人控制时间,留给领导足够发言机会,后面的人,管你王五麻六,齐齐掐掉。那,今天,就多我一个?把我安排在最后,难道是这意思?可是,大领导快十点来到会议室时说,对不起耽误大家的时间,今天的会议推迟一个小时,大家要有个思想准备,等到一点进餐噢。高画家开始发言。她向对面的主持人举了举自己的发言稿,用那双善于传情达意的眼睛问,这是怎么回事啊?主持人也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她曾经的戏迷,年轻时候作为记者采访过她,在那激情洋溢的长篇报道中,大力渲染她的魅力与风采。现在那人,被岁月磨蚀成一张清苦庄严的脸,似乎再了不会有激情了。那张脸迷茫地看了她几秒种,突然如梦方醒,张了张嘴,双手合十,在桌面上露出指尖,向她拜了拜。她知道这是一个误会。她最后一次,又低头看看发言稿,在第三页的一个括号“发挥”那里,用笔重重地画了一下,提醒自己不要忘了。
人不认老,是不行的。常常她从椅子上沙发上站起身来,觉得自己的腰,无疑是老腰,自己的腿,分明是老腿,它们是那么僵硬委顿,弹性尽失,全然忘记了年轻时候的灵巧笔挺。娘曾经说过,没钱时别说你有钱,人老了别说你当年。这是在教人用随遇而安的态度对待人生。可是,怎么能不说呢?尤其你曾经那么有钱,尤其你当年是那么辉煌,搁谁也是一件不得不说的事。可是大家都很忙,没有人停下脚步听你说,年轻人压根不看戏,更不知她是谁。近年来她出门,好像是为了测试大街上还有多少人认识她。她伤心地发现,认出她的人,都是五十岁往上走的,大多是她这样的老家伙,他们惊奇地停在她对面,哟,史老师,真的是你吗?那时她真的会有热泪盈眶的冲动呢,像是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偶有一个中年人说,哟,史老师,我是听着您的戏长大的。她非常幸福,恨不得挥手之间,招来三两伴奏,一抹脸,将自己变作张梅英,站在街头深情唱起:高文举读书三更天,梅英添油拨灯盏,高文举读书四更天,梅英端茶润喉咽,高文举读书到五更,梅英陪他去安眠。她,也只有她,才是永远的张梅英,最美的张梅英,无可超越的张梅英,那些在她之后跻身的,扮相不行,嗓音也弱,气质更是谈不上,以为穿上那身戏装你就是剧中人吗?错错错,要是那么简单,哪里还有艺术这一说呢?有一个,充其量是个演粗使丫头小跑腿的,七捣鼓八折腾,竟然也荣登女一号了,收拢不住喜悦和轻飘,身子夸张地扭呀,竟然把个悲情端庄的张梅英唱出喜感和轻浮来。过眼烟云的张梅英,一个不胜一个,一代不如一代。在她内心深处,她们还有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一个人,能把张梅英唱出神圣的性感来。是的,性感。花亭相会这段,是离人相见,采用倒叙手法,忆的是峥嵘岁月,沉静长夜,红袖添香,一更又一更,直至夫妻双双去安眠。咱们戏曲在多少年里,受着影像不发达的限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声音里如没有那销魂蚀骨般的性感妖娆,没有那完全无辜的单纯懵懂,怎么可以呢?不能将二者结合得恰到好处,制衡得天衣无缝,从而达到乐而不淫,怎么好更上层楼呢?观众为什么迷你恋你?奉你为大众情人而你又神圣不可侵犯。能让他们失魂落魄,不计成本地去追你爱你,还能有什么比这只可意会的尺度更精妙更牢固呢?大比年间王开选,举家人送他去求官,闻人说强盗得高中,把一张休书捎回奴家园,捎回奴家园……还是当年的嘤咛婉转,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只让当街行人泪水涟涟,唏嘘不止,不说是绕梁三日吧,也要在耳畔萦回半晌,用以回报人们的不忘之情。当然,也有年轻人多瞅她几眼的,不是认出了她,不,他们看她的目光,一片蒙昧,绝不是好像此人哪里见过的意思,而是觉得这老太太,必有来头,她穿着讲究时尚,头发乌黑,括号,染的,发型讲究,是那种烫了后又拉得半直不直,吹得似卷非卷的样子,一丝不乱,喷了发胶,似一团妙不可言的硬壳壳,尤其是那张不平凡的脸,曾经沧海难为水,被一种夸张到不是生活妆的东西涂抹得直白不拐弯,嘴上是鲜艳的口红,这样,她的面部被黑白红三种真理一般确凿的颜色书写,分明是告诉世人,我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可那又怎样呢?人们步履匆匆只投过一瞥,就是对她的注目礼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她失望而归。我从前那些粉丝,都到哪儿去了?

崔振宽作品-《堡子》179.5×96cm 2012
画家高利奥同志只用四五分钟,就结束了发言。
对面那个貌似清苦的人说,我这个主持人应该检讨,刚才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请史老师原谅,现在,请我们今天最后一位交流者,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史香云同志发言。
她面带微笑,扫视对面一排领导,就像当年出场时检阅观众,启朱唇,嗓音明媚而清亮,自信还是动听。同志们,今天有机会新老朋友相见,非常激动。由于时间关系,我用最快的速度,念一念我的发言稿。
她声情并茂,陈述自己艺术要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讲述自己在近年来戏曲不景气的情况下,安于清贫,不计报酬,坚持义务演出,深入农村厂矿工地学校免费唱戏,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只要能有机会唱戏,只要大家还爱听,不管路远近,我都去唱,不要对方单位招待,不要人家的纪念品,自己乘坐公交车往返,有多少次,车上乘客认出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哟,史老师,您这么大的名人,怎么还坐公交车呢(当然,更多人说,哟,您这么大的年龄,怎么还坐公交车呢?这个被她忽略)?我说,我坐了一辈子公交车,我就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呀。念到第三页,在括号“发挥”那里,她迟疑了一下。前面高利奥只用了四五分钟,那么,他的时间,是否我可以借用呢?
在这里,我想说几个小故事。她抬起头,扫视了一下会场,对面正中间的大领导,微微皱了皱眉,主持人的脸,闪过一丝形势严峻的云朵,她像当年一样甜甜地笑笑说,不会用太长时间。
她所讲几个故事,当然都是退休之后的。

崔振宽作品-《龙门竞渡》178.5×95.5cm 2013
那年护城河清淤,广大人民子弟兵在烈日炎炎下,每天在污泥里劳作,晚上睡在河边。我找到指挥部,说了我的想法,他们热烈欢迎。我赶快回家,找了几个老伙伴,连夜创作了几段小戏,第二天早上加紧排练,下午就跟两个伴奏的老同事去了护城河清淤现场。就在七月的大日头下,老同事伴奏,我唱,歌颂年轻战士的英雄事迹,哎哟,那些子弟兵,腿陷在淤泥里,站得直直的,给我敬礼。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给他们唱一辈子,都值得!她有些哽咽。她能控制,现在还不到要掏出纸巾的时候。后面还有俩故事呢。
还有那年,修那个亚洲最长遂道,我从报纸上看到工人们在难以想象的困难环境下工作,我要去给他们唱戏,我自己坐着班车就去了工地现场。要求在隧道里给他们唱。工作人员说,这些施工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听不懂地方戏。我说,那我唱歌吧。他们又说,史老师你不能进去,里面会有岩爆。我问啥叫个岩爆,他们说岩爆就是岩石爆炸。她念发言稿,一直用的都是普通话,就像电台的播音员一样标准,现在突然转了频道,用方言说,我就说咧,那岩石,迟不爆,早不爆,我一进去,它就爆?类似于她唱戏时的道白,将音色、语气拿捏得稍许夸张,诙谐动人。会场里一阵轰笑,恰似当年的满堂彩。大家想想啊,修路工人白天黑夜在那种环境下工作,都不怕岩爆,我怎么怕呢?哎哟,进去看了才知道,他们是多么不容易啊,为国家做贡献,拿命在那拼,置生死于度外,跟他们比,我这点危险算得了什么?她重度哽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随时,随时,都会滚落而下。不过,她能控制。还不到时候,她告诉自己。
还有那一年,跟着中央电视台走基层栏目,进到矿井下的掌子面,才亲眼所见煤是怎样挖出来的,巷道里面最窄的地方,工人们只能爬着通过,可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没日没黑地为国家挖煤。我当时啊,恨不得给他们跪下来歌——唱。是时候了,热泪喷涌而出,哽咽得也很汹涌。她不得不停下来,掏出纸巾擦泪。会场上有短暂的尴尬,大家都有点吃惊,不知该怎么办,静得没有一丝声音。领导带头鼓掌,几十个人的掌声汇合起来。她长嘘口气,一场演出又成功了。
“到底是演员,说哭就能哭出来。”一个半小时后,在返回的车上,画家高利奥说,然后回过头训斥迟小萌,“小迟你管那个老婆干什么?害得大家这么多人等你。”迟小萌说,“我觉得扔下她一个人,那么大年龄,怪可怜的。”
“可怜啥?没神!大家都等着吃饭,她还没完没了地说,也不看看领导脸色都成啥样了。”刘主任说。
“啥活动都要参加,啥场合都要发言,连卖墓地的搞活动,她都去唱戏,真是的,那么大年纪了,不好好在家呆着。”张画家说。人们将被拖延一小时吃饭的账,全算到她身上,至于领导来晚嘛,大家已经忘了。
“上个月,北京那个知名女作家,七十七岁,开了个画展,画得还真不错,比咱有些专业画家还有水准,关键是画展上人家说的话,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她的爱护,此次画展,算是与大家就此道别,让大家忘了她吧,遗书也写好了,死后不开追悼会,不发表纪念文章。同样是老太太,人家什么境界?”
车上暂时没有声音,画家们安静下来,就像此刻会场上的安静一样。
她这才意识到,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她擦干眼泪,收住哽咽,算是完成了整个表演程序,及时地收尾,结束了发言。
“好,老太太说得多感人啊!”主持人慢着声儿说,重点强调老太太三个字,“在座这些年轻的作家、艺术家,要学习史老师这种无私奉献、与人民心连心的精神。现在,请省上领导同志做重要讲话。”省上领导说,今天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全省文艺工作者汇聚一堂,老中青几代人,咹,写作的,画画的,跳舞的,吹拉弹唱,各个门类的交流,十分难得啊,本来,今天我有很多话要跟大家说,可因为上午我晚到一个小时,致使会议推后,现在马上就十二点半了,我不能耽误大家的吃饭嘛,是吧?想必同志们都很饿了,我把我的讲话,总结成几点,简单说十分钟吧。
是的,大家都饿了,尤其是她,因为她早上就没有吃饭,因为她没找到吃饭的地方。开会是在一个山庄,昨晚在家里吃完饭,儿子把她送来,在报到大厅拿了房卡,又驾车在山庄里将她曲曲绕绕地送到房间。早上她才发现,所住房子,一座一座散落在山坡上。会议本是两人一间房,可会务组给几位老艺术家安排单人单间。可能郊外安静,她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见观众们呼唤她重返舞台,她像是佘老太君一样,重新挂帅出征。花团锦簇,一派繁荣,观众那个欢呼啊。她起床晚了。她化好妆,穿戴好,在镜子前照了又照,确信风采基本依旧,又想到中午饭后直接就走,不用再爬很多阶梯回到房间收拾,她全部东西拿好,提着一个稍大的包,背着随身小包,款款走出房间,四下里望,一个人影都没有,人们都到哪里吃饭去了呢?本是昨晚报到时给发了张会议须知的,上面有说明在几号楼用餐,还发了自助餐票,就在她的口袋里,可那张会议须知,她装到那个大点的包包里,现在走在路上,天上下着小雨,她一手撑伞,也没办法再把包放在哪里打开寻找,就算知道在哪个楼,还得找人问,哪个楼在哪里?算了,直接问在哪吃饭吧。可是问谁呢?怎么也不见个服务员。本来时间就有点晚,她在园林般高高低低的路上走来走去,硬是见不到一个人可以问问。等她终于见到人影的时候,是他们吃饭回来。遥遥地给她指了,大坡上的一座楼,许多台阶托举着,屹立于几百米外,可以看到人们陆续吃完饭出来,去往另一座楼上的会议室,离会议开始只有二十分钟了。她又不是年轻时候,可以步履如飞地跑去,三下五除二吃几口了事。她每次吃完饭,要照着镜子,重新涂口红,理头发,整围巾。算,不去吃了,小包里有两块奶糖,含在嘴里得了。从前下基层演出,也经常是饿一顿饱一顿的。她随着人群,往会议室里去,就像她也是刚吃了饭似的。有年轻人要帮她提包,她那个大包就交到了人家手里。那里面有她的一双轻便鞋,一身睡衣,一个披肩,一袋阵容庞大的洗漱化妆用品,轻便鞋本是打算今天若起得早了散步穿的,现在脚上穿的是带点跟的黑皮鞋,配她的黑色紧腿裤,浅灰色羊绒大衣,小碎花丝巾,是正式场合的穿着,大场面的装扮。
坐进会议室。吃好早餐的人们都高高兴兴的,相互打招呼、问好,间或有人来到她面前,将问候和赞美献给她。九点多,却还没有开会的迹象,这么重要的会议,没有按时开,挺奇怪的。有人通知,今天参加会的省上领导因一个突发事件,必须在另一个地方露一下面,现在正在往这里赶的路上,会议将推迟几十分钟。几十分钟呢?够不够她赶到餐厅吃饭呢?她在内心跟自己斗争,但总害怕她刚一离开,大领导来了,所有人抖擞精神,种种面庞全部变作葵花,掌声唧喳鹊起,会议开始,只有她桌签的后面,座位是空的,那多不像话。她长年的职业道德,使她从不迟到,从不缺席。会场设计是长方形,对面一排是领导,中间是大领导,两边是各艺术门类的具体领导,这面是要发言的十位作家艺术家,发言者后面,是参加会议的各路神仙,排排坐好,一个萝卜一个坑,都乖乖栽种在自己的名字后面。
领导讲完话,主持人总结完,快一点了,她肚子饿得发出了叫声,觉得快没有走路的力气,她想,或许有人会好心为她提着包,回头目光扫视,果然有个年轻女子走来,“史老师您好,我爸爸是您的戏迷,我从很小时候就看您的戏。”
“啊,是吗?”她脸上荡起幸福的笑意,亲切地问,“你叫啥名字?”
“我叫迟小萌。”
“哪个单位的?”
“省画院。我给您提着包吧。”迟小萌提起她那个大包,伸手搀扶住她一起走。侧脸看了看她,“史老师您还是那么美,跟年轻时候一样。”她的心都要醉了,“不行不行,老了,就眼睛还可以。”她最满意的,是自己的眼睛,自信它们还是水汪汪的。
她问迟小萌,“你今年有……三十岁?”
“我,四十多了。”
“噢,有那么大吗?真看不出来。”难道自己真是老眼昏花,还是现在人都显得年轻,怎么判断人的年龄,总是差距很大,或者,以她现在的眼光看,世人都年轻。她再问,“你属啥的?”这又完全是她们那个年代的交流方式。
“属猪。”
“噢,那跟我女儿一样大,哎哟,可就是四十多了。我女儿出国多年了,也不常回来,要是像你这样陪在身边,多好。”
两人刚下得楼来,有个年轻人迎面拦住。“史老师,我们是电视台记者,您能接受采访吗?”
“能啊,当然能。”她给迟小萌说,“你先去吧。”
“那我给您把这个包拿到餐厅里。”
她一想,包里还有披肩,还有化妆品,或许,她需要补妆,一会儿面对镜头会用上披肩也不一定。她有这方面经验,电视台有时候要求多摆几个造型,多拍几个镜头。迟小萌把包交给她,轻捷地走了。
她反反复复告诉记者的,还是那句话,只要人民需要,我会一直唱下去。这话成为了她的标签,也是她将要付梓自传的书名。当然,记者们都是懂事的孩子,她们也不会追问,那,人民要是不需要呢?记者没那么多额外的问题,也不要她再摆造型,只十几分钟,结束采访,更不需要她补妆,戴披肩,只告诉她,史老师那您快去吃饭吧,我们要赶回台里做节目,就不在这吃了。摄像师已经收了机器,钻进张大嘴等在旁边的面包车里。
“哎,那你们把我送到吃饭的地方吧,我找不到。”记者搀她上车,开到吃饭那个楼下,告诉她在二楼。她下车来,面包车逃一样跑了。

崔振宽作品-《秦岭大壑图》258×620cm 2014
她刚要上楼,吃完饭出来的又一个年轻人拦住她,“史老师,我是晚报记者,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
“好啊,当然能。”面对镜头,她又重新焕发出神采。
餐厅里人群稠密,已经少有空位。找个边上的空座,放好大包小包和外套,她先盛了一小碗汤,喝了两口,这才端着盘子,慢条斯理地给自己盛饭。人们都在狼吞虎咽,不再有刚才会议上的斯文劲。刚好迟小萌也在这个桌上,跟她打招呼,史老师,我也是才来,刚才回房间收拾东西了。
她坐下来,刚吃一口,有吃完饭的人走过,给她打招呼,她站起来应答,坐下又吃一口,又有人走过来叫她。谁也不知道她早上没吃饭,谁也不知道她刚坐下吃。她不断被打断进食,面前丰盛的午餐堆放,肚子里咕噜噜响,连五口饭都没吃进去。就要离开的主持人特意走过来,拉着她的手,隆重地向她道歉,问候了她的身体,再说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然后挥手道别。她一个个应酬,眼看餐厅里只剩下一少半人,她突然想起一个关键问题,拦住一个会务上的年轻人问,我坐哪个车回?年轻人回答,昨天来坐哪个,今天回就坐哪个。
昨天晚上,她给儿子说,明天回去你不用管我了,会议上一定有车的。这会儿,让儿子从几十公里外的市区来接,显然不合适,昨天仿佛听儿子说,要接待一个什么参观团。
迟小萌说,“史老师那您坐我们画院的车吧。”
“那好那好。”她安心坐下来,吃了两口,不那么饿了,抬头问身边这唯一的小伙伴,“你叫啥名字?”
“我叫迟小萌,在省画院工作。”
“噢,刚才问过了,你是个画家。”她自嘲地笑笑。
“史老师,十几年前,我和我爸在安西街一个饺子馆吃饭,一回头,见您坐在另一个桌子上,我爸激动得呀,给我说,快看快看,那是史香云。他一直想过去跟您打招呼,可到底也没好意思,我俩就在一边看着您,简直不敢相信,您竟然在小饭馆里吃饭。您吃完饺子后,拿个小镜子出来,又涂了涂口红,提起包包,就从我俩身边走出去了。不知您有没有印象?”
她简直陶醉了,无限甜蜜地回想起,或许是有那么一天。十几年前,她家就住在安西街附近,她经常去那家饺子馆。那时她刚退休一两年吧,还有着一股执拗劲,常常要上街验收人民群众对她的反应,看广大观众是不是忘了她。现在叫迟小萌一说,她不能怪人们不上前来跟她打招呼,那是人家害羞,胆怯,并不是冷淡她,遗弃她。嗯,这一点,要写到书里。那两年,是她心情最低落时候,刚回家呆着,还不能很好地调整过来。生产不久的侄女带着孩子住到她家里,算是陪伴她,侄女正在读一本书,巴尔扎克的情妇,比他大二十一岁,两人交往二十多年,引领他从青涩之年走向人生的辉煌,她在六十二岁的时候,被功成名就,风华正茂的小巴逐渐离弃,“一个六十二岁的女人,无论如何不再适合情人角色了”,侄女大声给她念这一句。那么,六十二岁的戏曲演员,是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站在舞台上了。
一个男人走进餐厅,大声问,“还有没有画院的人?走了,走了。”

崔振宽作品-《洛南之二》179×96cm 2014
迟小萌挥手说,“刘主任,还有我,让史老师坐咱的车吧。”
刘主任走过来,懵懂般地问她,“史老师你家在哪?”那表情好像从来不认识她。
“我家在永青路,南二环下去就是。”她说。
“那我们车不走那,不走那。”刘主任头摇得很夸张,眼睛里全是眼白,脸蛋上的肉都甩来甩去的,一副非常无辜的样子。
“那,那,你们走哪?把我放路上就行,只要有公交车的地方,我就下来,再倒公交车回家。”
“可是我们要出发了,人都在车上等呢,我们高院长下午回去还开会。”刘主任黑眼珠落回来了,拿眼睛盯了一下迟小萌,使个眼色。“赶快下楼啊。”
迟小萌站在桌边,左右为难。突然看到大厅里正往外走的一个作家。迟小萌叫,“肖老师,您不是在南郊住吗?把史老师捎一下吧。”
肖作家停下脚步,头仰着看天花板,扳着指头数,“我车上有陈老师,冯老师,加上我,刚好还有一个位置,好吧,史老师你要不嫌挤那就坐我们车吧,现在就走,来,我给你把包拿下去,楼下等你啊。”肖作家提起她的大包走了。
可是,可是,她其实进到餐厅十多分钟到现在,半饱都没有呢,她对着盘子里那一堆菜,碗里那半碗米饭,乍着双手,唉呀唉呀这可如何是好呢?一下子,真的像戏里演的遇到难题的老人家了。我吃不饱无所谓,可是不能浪费啊,要不,让服务员找个饭盒打包,我拿回家吃,这么好的菜扔下,多可惜呀。
迟小萌叫服务员找饭盒,服务员走到一个角落,没有,再去另一个房间。她就那么站着,乍着双手,对着那一盘子菜苦恼。迟小萌说,史老师别着急,啊,我陪着您。话音刚落,电话响起,迟小萌对着电话说,就来就来。挂了电话,对她说,史老师对不起啊,他们又催我了。她说,你去吧你去吧,噢,对了,来来来,给你,我的名片,你也给我留个电话吧。她对眼前这个新认识的小伙伴简直恋恋不舍了,现在哪还有这么乖的年轻人,愿意在她身边多呆一会儿呢。迟小萌接过名片,我会给您发短信的,把我的名字、单位发给您,约时间和我爸爸去看您,再见啊史老师。小伙伴快速说完,转身跑了。
大大的餐厅里只剩她一人,等着服务员拿饭盒来,可偏偏拿不来,服务员大声问另一个服务员,饭盒在哪?又推开另一扇门。
“史老师,好了没?”大厅门口,肖作家提着她的包,再次出现。他一定是走到楼下,等了一会儿,才发现她没跟出来。他嘴上叼着烟卷,皱着眉头,表情是感到生活很不美好的烦躁。这个成天鼓吹是痛苦和焦虑成就了我的作品的作家,楼下他的车上,还坐了两个搭顺车的大腕,叫他上来催催。肖作家的表情秉持着他一贯的心路历程,痛苦地看着她。心里一惊,她走过去,从他手里接过包。“我侄女刚才打电话了,她来接我。不麻烦你了,你们快走吧。”
她把包放回座位上,对服务员说,不用找饭盒了,我在这吃完吧。
餐厅里静下来,服务员轻手轻脚地挨桌收拾,从她身边经过,微笑送给她。对不起,我吃到最后,耽误你们时间了。她说。没关系没关系,需要什么您尽管说。她说她想再喝点汤,服务员用小碗给她端来,轻轻放在她面前。她歪着头,用当年在人民大会堂进餐时的风韵说,谢谢。服务员还是个小姑娘,被这隆重而高雅的致谢吓了一跳,害羞地笑笑,说,不客气不客气,然后退到一边,偷偷打量她。十几张收拾干净的大圆桌上,白净净厚墩墩的桌布垂吊下来,像是谢幕后的舞台。让人无法相信它们半个小时前还是那么喧闹,各色人物穿梭其间,真真假假地问好,握手,赞美,道别。
我着什么急呢?人家都是在职在岗,忙着下午上班,赶着奔赴另一个会议、场合,我又不用。她缓缓地喝汤,慢慢地吃饭,她问服务员,从这里怎么回到市区?服务员说,要从山庄走出去,大概一公里,有公交车站,就能到市区了。
有公交车就好,只要有一个,就能倒第二个,第三个,再怎么麻烦,天黑前,总能到家吧。嗯,且安生吃了饭,补了妆,换了鞋,从容走出山庄,走到公交车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