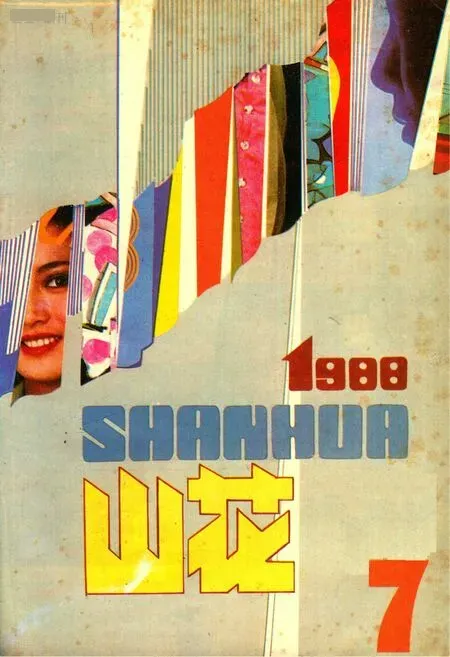原路返回
“还有谁没来?”赵丰成对着几个同伴喊。
老头们都不作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又一齐看着赵丰成。
赵丰成就说:“都来了吧,出发啦!”
赵丰成问的那一句纯属多余。“超期颐”登山队总共才六个老头,他自己站在最前面,其余五人面对着他一字排开,谁来谁没来,一目了然。但这已经成了赵丰成的习惯,每次出发前他都要这么问一句。这也是老队长彭胜华留下的口头禅,被赵丰成顺理成章地接了过来。六年前,彭胜华组建这支老年登山队时,不管是出发时还是从山顶上下来时,他都要问一句:“还有谁没来?”特别是下山前,他一定要一个个地清点人数,一个都不能少。那时的队伍比现在要庞大得多,有二十多人。六年来,那些人有的老得爬不动了,比如周大林;有的病得下不了床,比如吴天宝;还有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比如彭胜华。
不在人世的,有五个,其中有两人万中民和李有中是病故的,另外两个,伍右斌和陈百通是自杀的,还有一个,就是队长彭胜华,他的死至今没有定论,有人说他是自杀的,也有人说他是失足摔下悬崖的。“超期颐”的老头们至今还分成两派,对彭胜华的死因争论不休。
伍佑斌和陈百通都是从玉屏山独秀峰跳下去的,那是三年前,他们跳崖的时间相差不到两个月,那时赵丰成还没有加入“超期颐”登山队,他俩的自杀原因和死亡细节赵丰成是后来听彭胜华和朱大海说的。赵丰成认识伍佑斌,知道他是物资局的退休干部,但现在这个局早就没有了,撤销了。以前他们打过几次交道,但不是很熟。据说伍佑斌是查出肝癌的那天下午跳崖的,死后他的上衣口袋里还装着医院的诊断书;另一个老头陈百通,赵丰成不认识,听彭胜华讲他倒是无病无灾,只是想讨个老伴,那个妇人比他小十来岁,他们相好了七八年,儿子和儿媳妇一直不赞成他们结婚。跳崖那天他跟儿子吵了一架,被儿媳妇推了一掌,额头撞在墙上,划了一道血口子,爬山的时候,他的额头上还贴着膏药纱布。彭胜华后来一直很自责他那天太大意了,没有注意到陈百通心情沮丧、神态不对,他说他那天要是稍微关心一下陈百通,甚至只要下山时等一下他,他也许就不会跳崖自杀了。
一年后,赵丰成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否则,也许队长彭胜华就不会死了。

崔振宽作品-《巴山秋韵之二》136×69cm 2009
彭胜华爬到独秀峰顶后再没有下山的那天,是冬月的一个下午,大约四点半的时候。那天赵丰成也在,他跟彭胜华、周海民和朱大海四个人爬上了玉屏山的最高处——独秀峰,赵丰成是第一个爬到峰顶的,他记得第二个上去的就是彭胜华。由于独秀峰顶只有一块比簸箕大不了多少的小平台。赵丰成上去后,在上面只做了两分钟的扩胸运动就下山了,“超期颐”的队员们都是一登上峰顶就下来,因为峰顶上的平台太小,最多只能容得下三个人,先到的人要给后到的人腾位置。赵丰成走下小平台两三米远就与彭胜华碰面了,两人一下一上,侧着身擦肩而过。接着,周海民和朱大海也上去了。赵丰成往前走了十来米,还听到彭胜华对着他喊了一声:老赵,在下面等我们,一起下山!从独秀峰顶下去约三四里,有一个大平台,那天除了他们四个人登上峰顶外,其他人都只爬到那个台地上,坐在那里歇息。赵丰成转身答应了彭胜华一声:好咧!说这一声“好咧”时,赵丰成一脚踩虚,崴了脚脖子,疼得他停下来坐在地上揉踝关节。揉了不到两分钟,他看到周海民和朱大海已经下来了。赵丰成的脚崴得不严重,站起后跟着周海民和朱大海往前走,走了一阵,他的脚就不痛了。他们仨往前走了大约三百米后,来到有几株松树的那个小斜坡时,赵丰成回头看了一眼,没见彭胜华下来,就问朱大海,老彭不会走另一条路下山吧?朱大海说他是队长,怎么可能走别的路。就扭头大声喊了几声老彭,彭胜华没回答他。他们又往下走了几十米,朱大海再次回头望了望,说,他好像还没下来,我们上去看看吧。他们仨人一起喊了几声老彭,怎么没下来?彭胜华还是没应,于是他们仨人又往峰顶爬去。爬上峰顶,小平台上空空如也,没人!彭胜华的外套挂在一簇灌木上,人却不见了。三个人一下子急了!这个山顶两面悬崖,除了他们返回的那条路,还有一条可以下到城北去。但不说彭胜华不可能走那条路下山,他就是走了,也得带上外套吧?他一定是出事了!后来彭胜华的尸体果然在山脚下找到了。彭胜华是失足跌下悬崖的还是自杀的后来一直成为“超期颐”老人们猜测和争论的话题。但再怎么猜测和争论,这将永远是一个谜。赵丰成一直倾向于彭胜华是自杀的,彭胜华有病,癌症。他是鼻炎癌,化疗过几次,据他说非常痛苦,头发都脱光了,脸上脖子上全是白斑。他这病大约得了七八年,后来好了一些,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认为自己没事了,爬山像只小老虎一样有力。两个月前赵丰成还听他说他的病基本上算是痊愈了。赵丰成之所以猜测彭胜华是自杀的,是在彭胜华的丧事期间听他老伴华嫂说,他癌细胞扩散了,整夜痛得睡不着,嗷嗷叫唤,华嫂说本打算过几天跟儿子一起带他去省城住院治疗的,想不到……
赵丰成听后心里一阵悲怆。为彭胜华,也为他自己。
六年前,“超期颐”登山队甫一成立,就被酉北人讥讽为“老残登山队”。残在酉北话里,也有病的意思。确实,这支以彭胜华为队长的登山队,所有的队员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儿,而且,近二十人中有半数以上的人身患绝症,彭胜华自己是鼻炎癌,周大林是皮肤癌,杨小华是白血病,伍佑斌是肝硬化,吴天宝和周海民是糖尿病,等等。没病没痛的健康人,不到百分之四十。五年前,也就是“超期颐”组建仅仅一年后,伍佑斌和陈百通前后五十天内从独秀峰跳崖自杀后,酉北人就把“超期颐”登山队不叫“老残登山队”了,改叫“老年自杀队”。彭胜华就是那时候邀请赵丰成加入登山队的,自从伍佑斌和陈百年连续自杀后,登山队不仅声誉一落千丈,再没新人加入,很多老队员也退出不来了。“超期颐”的人数一夜间锐减过半。“超期颐”最红火时有队员二十六人,等赵丰成加入时,连他在内,只有十一个人了,此后的几年里,也再没进一个新人。其实赵丰成也不想加入“超期颐”,原因倒不是因为“超期颐”被人叫成“老年自杀队”,而是他不喜欢聚会,更愿意独来独往,但他架不住彭胜华的劝,他俩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不好意思驳彭胜华的面子。二十年前,赵丰成在乡里做乡干部时,彭胜华就是乡中学的体育老师,那时他们就常在一起打球,一起爬山,一起喝酒。后来彭胜华先他两年调进城里的县体育局(那时酉北还没有撒县建市),赵丰成进城办事,碰到彭胜华了,他也常请他喝酒。这么铁的关系,彭胜华劝了他三次,赵丰成就没有退路了,只能加入,但他一加入,爬了趟独秀峰,出了一身臭汗后他就尝到了登山的甜头,再也离不开“超期颐”了。彭胜华死后,他就接过了老哥们留下的队帜,当了“超期颐”的队长。

崔振宽作品-《巴山秋韵之三》136×69cm 2009
赵丰成跟彭胜华、周大林他们一样,也是个癌症患者,但跟他们不同的是,没有人知道赵丰成得过癌症。赵丰成是直肠癌,七年前就确诊了,他是在省肿瘤医院动的手术,当时在单位请假他只说切除直肠息肉,他自己和家人都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得了癌症。他没有化疗,在省城住院时,来看望他的单位领导和同事也没人怀疑过他得的是癌症。虽然没有经历过化疗的折腾,但赵丰成住院治疗时和出院后经历的痛苦并不比化疗轻。他先后动过两次大手术,第一次手术是切除直肠癌变的部位。那个部位离肛门太近,手术后医生给他在腰上装了一个粪袋。半年后,赵丰成动了第二次手术,把原来切断后连接粪袋的小肠再次接上。两次大手术,不仅把赵丰成折腾得皮包骨,还几乎击溃了他的精神。特别是戴粪袋的那半年时间,刚好是三月份到九月份的春夏时期,大热天的日子居多,赵丰成几乎足不出户。他把自己在家里关了整整一百八十八天。赵丰成是羞于出门,大热天穿的少,戴着个粪袋,藏不住掖不着,黄色粪水在腰上晃来荡去的,人人见他还不避而远之?就是穿得厚点,遮得住粪袋,那股味儿,不说别人,连他自己都觉得臭气熏人。赵丰成检查出癌症时才五十一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又是个很讲究外表的人,平时出门穿戴整洁,头发要梳,衣裤要烫,牙也要刷,容不得自己身上有半点异味,现在突然戴个粪袋,他怎么可能会出门,让别人嫌恶他。因此一等半年期满,他就迫不及待地去接肠了。很不幸,第二次手术虽然很成功,但他的伤口却感染化脓,本来只要住十天院的,结果他住了四十天院。住院时间太长,他得了创伤性精神病,老是有幻觉,出了肿瘤医院,他又进了精神病院住了十天。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就病退了。本来病前他还有一次提升正科的机会,市委组织部找他谈过话了,他一病,就彻底黄了。赵丰成的精神打击主要不在于当没当成局长,得了这种绝症,他不可能还在意官不官的,摆在他面前的可是生与死的大问题,他的癌症是中晚期,住院时医生就建议他化疗,他坚决不做。他看过一些关于化疗的报道,太恐怖了。医生还说他的癌细胞有可能扩散了,若不化疗,最多就是两三年的光景。这话,医生不是告诉他的,是他后来听老伴说给他的。赵丰成后来一直寻访中医,吃中草药,吃了很多种,光野生猕猴桃他起码就吃了上千斤。反正三年后,他没有死掉,也没有复发,但多年来他也吃尽了苦头,受尽折磨,原因就是他接过肠子,大解不畅通,有时好多天解不出来,要用泄药,一用泄药,又一天要跑几十趟厕所。起初的几年,这种不畅通还不频繁,一月只有那一两次。后来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各种器官老化,他的大解更加困难,经常三五天解不出来,一吃泄药,又要拉上一两天。那段日子,赵丰成不仅体质非常脆弱,内心更加焦虑不安,老伴说他夜里常常发癔症,半夜里起来,在床上自言自语,或者到处走来走去,有时还大声哭泣,赵丰成矢口否认。虽然否认,但赵丰成知道泄药副作用大,常用的话只会加重他的病情,他必须寻找一种药物外的方法治疗他的便秘。赵丰成试过好多方式,譬如多喝水,饭前饭后喝一大碗汤,每天吃五根以上香蕉,但效果都不明显。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强度大的运动有利于他排便通畅。那是前年的清明节时,赵丰成回乡下的老家给父母上坟,父母的坟头在一座大山的半腰上,他爬了几里的山路,到达父母的坟头,他发现那里杂草丛生,荆棘遍地,把父母的墓碑都淹没了,他动手修理那些杂草和荆棘,又给父母的坟头添了新土,累得出了一身大汗。那天晚上他的大解就很顺畅,老伴也说他睡得很香甜,一觉睡到大天亮。
从那之后,赵丰成就开始进行体育锻炼,他早上起来到公园里跑步,跑出一身大汗才回家,晚上到广场学打太极拳,也要出一身汗才回家。这些锻炼,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他不仅大解通畅,也心情舒畅,吃得好,睡得香,老伴再没说他发癔症了。但也不是完全正常了,便秘的次数只是没有原来那样频繁,但时不时还是发生。锻炼不能停,停了一两天,就会旧病复发。不管是跑步还是打太极拳,都是户外运动,要看天气出门,一下雨,就不能锻炼。那时正值春夏之交,梅雨时节,下雨天比晴天的日子多,赵丰成的家只有两室两厅,八十多平米,家里东西摆放得满满的,他想在室内放个跑步机也没地儿,一碰到下雨天,他只有在客厅里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独自一人在家里做运动,很难做出一身大汗,不出汗,对于赵丰成来说就起不到明显的效果,第二天还会便秘。
大约就是那年秋天,有一天彭胜华上午九点时从公园里路过,碰到正在跑步的赵丰成,他对赵丰成说:“老赵你一个在这里绕着草坪跑有什么意思,跟我们‘超期颐’登山队一起爬山去吧?”
赵丰成停了下来,喘着粗气说:“我习惯一个人单独活动。”
彭胜华说:“试试来嘛,我们‘超期颐’现在人气不足,来凑个热闹吧。”
赵丰成摇了摇头,说:“不想去。”
赵丰成知道彭胜华的”超期颐”登山队,但那时他不知道登山队出了两次自杀事件,被很多酉北人称为“老年自杀队”。赵丰成的家住在城西,老年登山队的集合场所在城东,他们爬的玉屏山也在城东,跟赵丰成家隔有至少五里路。赵丰成得癌症后的几年里,活动范围就在城西,他很有规律地出入家门,与“超期颐”登山队的老头们没有交集,自然也就没有信息来源。关键是,赵丰成自从得癌症后,把自己封闭惯了,他不想凑什么热闹。
彭胜华好像是铁心了要拉赵丰成入伙,一连三天,九点多时他都在城西公园等赵丰成,劝说他跟他们一起去爬山,并给他说老年人爬山的诸多好处,说得头头是道,唾沫横飞。彭胜华从事了一辈子体育运动这个职业,他是真心热爱体育运动,得了鼻炎癌之后,像打篮球这类竞技性强的运动再不能参加,因此他才组建这支老年登山队。他一方面是想自己健身,与病魔抗争,延年益寿,这从他给登山队取名“超期颐”就可以看得出来;另一方面,也是还想延续他的体育梦。最终打动赵丰成让他决定试试,是彭胜华的一句话。
彭胜华说:“你没病没痛的,还没有我们一帮子得绝症的人有勇气吗?再说,我们那帮人都是六十大几七十了,至少有一半人得癌症都有五六年了,医生说活不过一两年的有好几个,天天爬山不都活得好好的。你不想活到八十岁还身强体壮吗?你要是不想,你天天来公园里跑步干嘛?”
谁不想活得长久些?赵丰成心里想,我还想活得超期颐呢。他跟彭胜华约好了第二天下午跟他们一起去爬山。玉屏山赵丰成以前也爬过几次,他知道那山高大陡峭,年轻力壮的人爬一趟往返差不多要花一个小时,所以第二天早上他没有去公园锻炼,下午三点半,他来到顺和街的小公园集合点,跟着“超期颐”队队员们一起爬山。赵丰成是登山队里最年轻的老头儿,第一次他就充硬汉,爬山的途中也没歇息,一鼓作气地爬上了独秀峰。到了峰顶,他满头满脸的汗水往下滴,不仅外衣汗湿透顶,就是内裤也湿得拧得出水。爬这一趟山太累了,回到家里赵丰成全身骨头酸痛,一吃晚饭就睡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老伴说他昨晚睡得像一头死猪,鼾声也打得酣畅均匀。爬山带给赵丰成最大的甜头还不是睡得好,而是此前三天赵丰成都没有大解出来,爬山的当晚,他的大解就很顺畅和轻松。此后三天,秋雨绵绵,既不能爬山也不能进行户外锻炼,但赵丰成一直睡得香,大解也正常,天一放晴,他就死心踏地地跟着登山队天天爬山了。坚持了一年,赵丰成感觉自己的体质明显地增强了,困扰了他八九年的便秘也彻底解决了,从那之后他再没便秘过一次。
就在这时候,彭胜华自杀了,他的死,让赵丰成突然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彭胜华这么热爱生活,执爱体育锻炼,但登山锻炼也没有挽救得了他鼻炎癌复发,阻止住癌细胞的扩散。那么,他自己的锻炼,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幻灭感,他在动第一次手术醒来后伤口疼得他整夜睡不着时也曾经有过,那时他的念头是,活着要受这么多苦,有什么意思呀,还不如就在手术台上去了,更好!
赵丰成接任队长后,只要不是下雨天,他都是第一个到达集合地点顺和街小公园,夏天的集合时间是四点半,春秋季节三点半,冬天则是三点钟。清点人数后,他就带着队员们开始爬山。下山时再一次清点人数,他殿后压阵,回到顺和街小公园后,大家才散开,各自回家。
赵丰成的幻灭感只是一闪而过,他最终接下了彭胜华的担子,被老头们推举为“超期颐”登山队队长,老头们都说登山队不能解散,他们还得继续锻炼下去。又说不爬山能做什么呢,总比坐在公园的亭子里打麻将要有益得多吧。赵丰成接手的时候,还有十个人,两年下来,万中民和吴天宝年纪大了,爬不动了,杨小华和周大林病故了。现在,连他自己算起来,只剩六个人了。这六个人中,年纪最大的彭洪已经七十六岁,年纪最小的,是赵丰成自己,也有六十四了。有一天,六十八岁的钱云南说他把六个老头的年纪加起来平均了一下,平均数刚好是他的年纪。其实早在彭胜华去世之前,赵丰成已经跟这些老头们混得很熟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底细他也很清楚。这些老头们都是中下层的劳动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家境是很优渥的,钱云南、朱大海和周海民是下岗职工,靠领社保金生活,张发是中学教师,彭洪是乡下农民做小本生意进城的,儿子考学后分配在外地工作,他跟开服装店的女儿住一起。六个人中,也就是赵丰成曾是干部,当过副乡长和副局长,境遇算得上是最好的。这可能也是他虽然年纪最小,一众老头们还是推举他做队长的原因吧?这些老头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轻闲,不要带孙子,也不要受老伴或儿女们管制,每次都能准时来报到,一般不会缺席,除了走亲戚去一两天,他们没有更多的外出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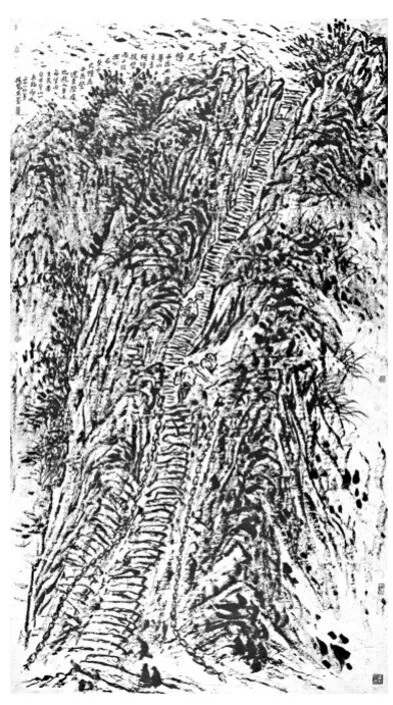
崔振宽作品-《华山千尺幢》257×144cm 2010
赵丰成当了队长,他就想把队伍带好,至少不想老头们再出什么意外事故了。每一次上山前清点人数时,他都要注意观察一下每一个老头儿的精神状态,有谁心绪不宁,或萎靡不振,爬山的路上他就紧跟着他,边走边跟他聊天,摸清他心情不好的原因。若是他不愿意开口,那么他就一直紧跟着他,把发生意外的机率控制在最小的程度,甚至没有发生的机率的程度。只要心情不好的老人肯跟他说,赵丰成又帮得上忙的话,他一定尽力帮忙。有一次,彭洪一连两天没来,第三天赵丰成邀张发一起去他家探望,才知道他老伴摔伤了腿在住院。彭洪正为几千块钱的药费发愁,赵丰成帮他写了一个报告给了民政局,申请了两千块钱的农村大病救助款。民政局主管社会救助的副局长原是赵丰成的下属,报告一递上去,他就签字批款了。还有一次,朱大海在爬山的时候给张发说,人年纪活大了,没意思,害人害己。第二天,赵丰成专门在老茶楼请朱大海和张发喝茶,想探下他的口风,是不是跟家人怄气了,但朱大海的性格很固执,他什么也不肯说。爬山的时候,赵丰成一连五天都跟紧着他,心怕他一时想不开,像伍佑斌、陈百通那样从独秀峰顶上纵身一跳,但此后他再没有发现朱大海有什么异常。
最令赵丰成担心的是周海民。周海民今年七十二岁,他一直有糖尿病,有二三十年病史了,他自己说跟他一起得糖尿病的人,都骨头可以打鼓了,就他还活着。他总结自己活着的原因,一是忌口忌得好,坚决不吃甜食,少吃油,多吃粗粮;二是坚持锻炼。周海民虽然是烟厂的下岗职工,他是司机,下岗后跑运输挣了一些钱,在城北买了地皮修有一栋三层楼房,自己住一层,其余两层出租,本来日子可以过得很富裕,但他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不仅没工作,年近四十岁还没成家,光棍一条,整天跟社会上的一些人混在一起,吸毒,打架,没钱了就问周海民要,不给,周海民就会挨他打。好几次来聚会,周海民都是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大家都知道他又被儿子打了,但谁也不说破,更不会调侃他取笑他。
有一天,周海民是手上缠着纱布来集合的。他最后一个到,大家都准备出发了,他才匆匆忙忙地赶到小公园。大家一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又被儿子打了。周海民一看大伙儿怔怔地看着他,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他说:“那个忤逆子问我要一千块钱,我身上只有五百块,他逼着我讲银行卡密码,我不讲,他就用锒头砸我的手背。”
周海民越哭越伤心,一直爬到半山腰时,他还在用那只没有受伤的左手抹眼泪。他们爬到山腰的台地时,天空下起了细雨,很快就把砂石小路打湿了。大家都说不往独秀峰爬了,坐在那个地台的石礅上歇息。赵丰成刚坐下来,听到张发喊:“老周,你去哪里?”
周海民说:“我去解个手。”
等了一阵,雨下得更大了一些,大家都起身下山时,周海民还没有回来。彭洪说:“他就是拉屎也不要这么长时间吧?”赵丰成听彭洪一说,心里大惊,拔腿就往独秀峰上跑去。快到峰顶的时候,赵丰成追上了周海民。此时的周海民,正站在只差两三步就能登上峰顶的地方,定定地站着。他脚外两步开外就是万丈深渊。两年前,彭胜华就是从这个地方“失足”跌下去的。
赵丰成看到周海民站在那里不动,他自己一下子吓傻了,大喊了一声:“老周,你别做傻事呀。”
周海民回过头说:“我走到这里突然双腿无力了。”
赵丰成走过去,拉着他的手,让他的另一只手扶着自己的肩膀,慢慢地下来。下山的路上,赵丰成一直扶着他,到那个台地时才放手。

崔振宽作品-《山寨》256×144cm 2010
从顺和街爬玉屏山,到达半山腰的台地有三条路,两条是在山脊上开辟的沙石路,坡度很陡,路也窄,比一只成年人的巴掌宽不了多少,说它们是羊肠小道一点也不过分。这两条路一般只有酉北那些爱冒险的青年爬。还有一条是石阶路,比那两条小道平顺、宽敞得多,适合于老人和小孩走。多年来,“超期颐”队员们都是走的这条石阶路。从台地到独秀峰,只有一条独路,也是砂石路,也是走的山脊,但路面还算宽,路况也好,这条路走的人多,常有人刨一刨,挖有土阶或石窝子,虽陡,除了登上峰顶的那脚路,都算不危险。到独秀峰顶上,下山又有两条路,一条是原路返回,回到半山腰的平台上,另一条是从峰顶的北面下山,直达城北的纱厂路。那条路从峰顶下去大约三十米远,有一道悬崖,伍佑斌和陈白通都是从那个地方跳崖自杀的。有一次,赵丰成和朱大海一同登上峰顶,在小平台上歇息时,朱大海指着那里一株小松对赵丰成说,他是看着陈百通从那里纵身一跳的。每次,爬独秀峰的时候,赵丰成都要给队员交待一声:原路返回。爬独秀峰时,不是每个队员都会上来,像年纪最大的彭洪,他一般只爬到台地上就不上了,坐在那里休息,等着他们一起下山,还有像体质最差的张发,他也很少爬到独秀峰去。有时某个人某天因身体状况差一些,也会不想爬上去。除了赵丰成是必会爬上独秀峰,基本上每次只有三到四个人真正爬到峰顶。从山腰的台地爬到峰顶上,至少还有四里路,队员们的体质不一样,速度也不一样,往上爬的人不可能同时到达峰顶,所以在峰顶上清点不了人数,赵丰成就给他们喊一句原路返回,意思是不准他们走北边那条险路,要他们返回到山腰的台地,他要在那里清点人数,统一下山。这也成了赵丰成的一句口头禅。这句话说多了,也逐渐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只要谁先到独秀峰顶,下山时看到后面的人在往上爬,都要给他交待一句:原路返回。
中学老师张发说赵丰成这句话非常富有人文关怀,原路返回不仅仅是一句交待,在他们登山队里是有特殊的含义的,它的意思是不准大家走那条险路,平平安安下山,也是对那些有轻生冲动的人的警醒。赵丰成倒没想到这句话能有这么多的意蕴,只是对张发嘿嘿地笑,说什么话被你们文人一演绎,就大不相同了。
在整个登山队里,赵丰成跟张发的关系最好,他们以前不认识,张发一直在市民族中学里教书。进登山队后,和张发聊了起来后,赵丰成才晓得张发是他女儿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女儿上初中时,赵丰成还在乡政府工作,那时他虽然进城到民族中学给女儿送过很多次东西,但他从没见过张发。后来更熟了,赵丰成又知道张发不仅是他女儿的语文老师,他俩还是大学的校友,他们都是州城大学毕业的,只不过张发比他高两届,赵丰成学的化学专业,张发是中文专业。熟了之后,两家就互有走动,最先是赵丰成在州城工作的女儿逢年过节回来时,赵丰成带她去张发家拜访,后来张发又回请赵丰成喝茶什么的。两人就是不爬山时也时常碰面,小聚一下。

崔振宽作品-《雨打芭蕉》232×119cm 2011
张发体质弱,但身体一直没什么大毛病,他脸色红润,看起来很健康,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好几岁。但谁也想不到,张发却是自赵丰成当队长后第一个退出登山队的人,当然他不是自愿退出的,而是病倒了。他的病很奇怪,咳嗽时咯血,在市医院里查是肺结核,治疗了半个月没效果,转到州医院查出的却是胃癌。张发在市医院住院时,赵丰成看过他两次,发现他脸色蜡黄,人也消瘦得厉害。他转院时是赵丰成帮他联系便车送去州城的,可没等赵丰成抽出时间去州城探望,张发就死在了州人民医院的手术台上了。
送张发灵柩上山的那天早上,登山队的老头们都去了。赵丰成记得那天彭洪的状态还很好,张发的墓地离城里有七八里路,他们都去山上了,来回走了十多里路,大家议定当天下午就不再爬玉屏山。第二天下午集合时,彭洪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彭洪一直不用手机,打他家里的座机没人接,周海民说他可能去省城儿子家了吧,过两三天会回来的。
五天后一个上午,赵丰成陪着老伴去步行街买衣服,看到彭洪的老伴坐在一间服装店里烤火。彭洪的老伴也是七十八九岁的年纪,老态龙钟,坐在椅子上打瞌睡。赵丰成走进店里,他知道她耳背,大声地喊她:“嫂子,彭哥呢,他去哪了,好多天没见他出来了。”
老妇人抬起头,一脸懵懂地望着他。三年前她腿摔伤了,赵丰成去过她家两次,她可能已经认不出他了。赵丰成又问:“彭哥呢?”
老妇人突然嘴巴一瘪,呜呜地哭了起来。
赵丰成忙问:“嫂子,彭哥他咋了?”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体胖女人,看脸型就知道她是彭洪的女儿,赵丰成一眼看到她的头上包着一条白孝帕,他的头皮轰地一响,晓得彭洪已经不在了。彭洪的女儿告诉赵丰成,说他爸昨天就上山了。她还说她爸是无疾而终的,三天前的早上,他从厕所里出来,走到客厅时摔倒了,她去扶他,扶不起来,她把他的头抱在怀里,不到一分钟,他就落气了。
赵丰成在店子里愣愣地站了好久,不知道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只是反复地对彭洪的女儿说,你爸走了,应该通知一下我们,我们几个老头也好送他一程。
张发和彭洪走了,登山队只剩下赵丰成、钱云南、周海民和朱大海四个人了。自从赵丰成接任“超期颐”登山队队长后就再没一个新人加入进来,送张发上山的那天,朱大海说迟早有一天,“超期颐”这面旗帜会倒的,要成为历史的。以前,彭胜华组建“超期颐”时,搞得很正规,就像酉北市那些暴走队,骑行队一样,制作了队旗。“超期颐”的队旗是一面绿蓝相间的三角旗,彭胜华说绿色代表健康,蓝色代表快乐,他希望登山队的队员们人人都健康和快乐,人人都能活过一百岁。赵丰成接任队长后,开始几个月大家集合时也打着队旗。队旗一直是由朱大海保管,上路时也由他举旗。旗帜不大,旗杆不足一米长。赵丰成接任队长后,朱大海举了半年旗帜,后来他说总共才五六个人,队伍太小,天天举个旗帜没必要,举得他手都麻了。又说以前彭胜华要他扛旗帜是想招揽更多的人加入登山队,现在登山队被人称为自杀队,名誉臭了,反正没人加入,完全没有必要再举个旗帜了。从那以后,他也就再没带着旗帜来集合。
这天集合时,朱大海是四个人中最后到来的,老远的,赵丰成、钱云南和周海民就看到朱大海举着“超期颐”队旗。那面旗帜显然不是以前的那面,新崭崭的,比以前那面更大,被朱大海高高地举起,迎面招展,猎猎作响。
钱云南喊他:“大海,几年不搬旗帜了,怎么又想到搬了?”
周海民也说:“你新做了一面旗帜?比原来那面有气势。”他又伤感地说,“可惜没有以前的人气了!”
朱大海不说话,举着旗帜向前走去,开始爬山。
从山上下来时,到了顺和街,大家分手回家后,朱大海把旗帜交给赵丰成,说:“老赵,我从明天起来不了了。”
赵丰成惊讶地说:“你好好的,咋不来了?”
朱大海说:“我可能时日不多了。这半年来一直屙血,前天在市医院查了,医生说是直肠癌,明天要去省城医院确诊,查明了就要住院动手术,其实我晓得,一查肯定是晚期。”
赵丰成安慰他说:“直肠癌,问题不大,好好治疗,好好休养,等你出院了再一起爬山,登山队不能少了你这个旗手!”
朱大海说:“我都七十五了,真是癌症,还能挺到出院吗,难!”
赵丰成突然很动情地拍了拍朱大海的肩膀说:“老朱,直肠癌真没什么,我五十一岁就得了直肠癌,当时就是中晚期,医生说我最多能活两三年,今年我都六十七了,活了十六年了,你看我现在的体质,像个癌症病人吗?”
这回轮到朱大海吃惊地看着赵丰成了,他说:“老赵你不是安慰我故意说的吧,你是直肠癌,怎么没一个人知道你有病。”
赵丰成说:“我看起来没病,人家当然就不会知道我有病。老朱我告诉你,直肠癌手术后,会大解不畅,要进行锻炼,才会通畅,等你出院,我们还一起爬山,保证你活到八十五岁没问题。”
朱大海说:“你把旗帜收起来,等我出院恢复了,我还给你们当旗手。”
三个月后,周海民也没有再来了。这天赵丰成和钱云南在小公园等周海民,左等右等,从三点半点等到四点半,一直没等来他,赵丰成打他电话,也没人接。最后钱云南说:“今天不爬了吧,就我们两个人,没味道了。”
他俩就怏怏地回去了。
第二天,钱云南来了,赵丰成给他说周海民住院了,我今天中午打通了他的电话,他儿子接的,问他住在哪家医院,他儿子又不肯说。钱云南说:“我晓得他住在哪家医院,我们去看看他吧。他一般住院都是住城南医院,他女儿在那家医院上班。”赵丰成在小公园前的马路上拦了一辆的士,两人往城南医院去找周海民。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周海民的病房,周海民的身上插满了管子,已经不能说话,他儿子也不在病房,只有女儿和女婿守着他。周海民完全处于昏迷状态中,赵丰成和钱云南跟他说不上话,坐了一会儿,就下楼了。
到了马路上,钱云南给赵丰成说:“老赵,明天你不要等我了,我不来爬山了。”
赵丰成说:“明天你有事?”
钱云南说:“不是有事,是我再不会来爬山了。儿子和女儿都说我年纪大了,若是摔一跤,受不住,他们也没钱治。以前他们也这样说,我没听,现在得听他们的了,不然……要是……万一……”钱云南嗫嚅着,不肯说下去。
赵丰成点了点头,说:“老钱,你别说了,我明白。朋友一场,有什么事时给我打电话,行吗?”
钱云南的家就住城南,一转身,他就走了。他的背影消失后,赵丰成还怔怔地站了好久,才走回家去。
现在赵丰成天天一个人爬玉屏山。他恢复了好几年前独来独往的状态,现在是夏天,他还是每天下午四点准时赶到顺和街小公园,然后一个人爬上独秀峰。这山赵丰成还是得爬,一是爬习惯了,停不下来,二来他也担心好久不爬山,会旧病复发,又解不出来大溲。其实,这几年来,他的大溲已经非常正常了,跟他没得癌症前一样的正常。早在两年前,就是碰上梅雨季节,一连十多天出不了门,做不了锻炼,他也一天一次定时大解。自从他爬山之后,就已经跟泄药彻底说拜拜了。现在,赵丰成的自我感觉就像从来没有得过病一样,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更是吃得好睡得香,连感冒都很少有。比他小四岁的老伴常说这里疼,那里闷,赵丰成却从没有过哪里闷哪里痛的感觉。
赵丰成知道他体质好,是得益于常年爬山锻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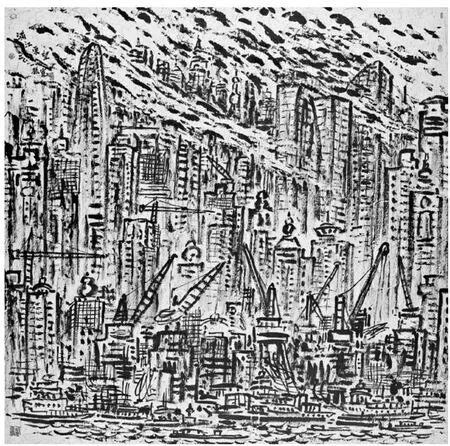
崔振宽作品-《城市组画之一—浦江东望》160×160cm 2011
他不能停下来。
下午四五点时,山上几乎很少碰到人,这个时段年轻人都在上班工作,大多数老头老太在幼儿园和小学校门口等着接孙子放学,山上空旷静谧。玉屏山上树木不多,但偶尔还是有一只或一群鸟儿飞过,留下一串串清脆的鸟鸣的回音。赵丰成感觉到一个人爬山和跟一群人爬山,是有明显不同的。一群人热闹,一个人清静;一群人有伴,一个人孤寥。一群人有一群人的好处,互有照应;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妙处,可以思考,还可以不必将就别人,想歇多久歇多久,想不歇就不歇。更重要的是,原来作为队长,赵丰成得时时担心别人,心怕出事故,压力很大,现在他只需要照顾好自己就行,心里头轻松多了。如果不休息的话,赵丰成看过表,他从顺和街小公园爬到独秀峰顶,再下到小公园,往返一趟只要一小时二十分钟。以前,他带队时,往返一趟最少要一小时四十分钟。
最初一个人爬山时,赵丰成很不习惯,每次从独秀峰下来时,他都要对着路边的小松树唠嚷一句:原路返回。嚷完,赵丰成会失声哂笑起来。
每次,赵丰成也确是原路返回的。
“原路返回”这四个字唠叨多了,赵丰成不免就不满足于仅仅原路返回了,他想,自己爬这么多年山了,上下一趟轻松自如,一点也不觉得累,完全可以爬一爬那几条险路,让自己再“年轻”一把。以前,跟大部队走时,他就有这个想法了,但那时他是队长,不能这样做,现在不同了,反正是自己一个人,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爬哪条路就爬哪条路,万一要是爬不上去,返回下来就行了。
赵丰成说做就做。第二天,他没走石阶路上山,而是从山南那条最险最陡的路上山。这条路是在山脊线上开辟的,很多地方至少有七八十度的坡度,爬的时候要手脚并用,还有一段几米高的砂石坎,完全是人工开凿的一个个石窝子。赵丰成爬上去时出了一身大汗,往回一望,顿时吓得一身热汗变冷汗了。要是他没爬上去,掉了下去,就得一路滚到山脚下,就是不摔死,也会摔得全身不会有一寸好肉。下山的时候,赵丰成再不敢走那条路了,他想到那路腿上的肌肉就一跳一跳的。后来,赵丰成又走了另一条山脊线上的小路,那条路倒不那么险,比山南的那条路线舒缓得多,他只花十多分钟就到达了半山腰的台地上。
这天下午,赵丰成参加朱大海的葬礼后,一口气爬到独秀峰顶。他在峰顶那个簸箕大的平台上,做了一阵扩胸运动,又做了几个俯卧撑,出了一大汗,起身后就静静地站在那里吹风。五点钟时,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城西赵丰成那栋楼房的五峰山上,但阳光却不炽热了,山顶上风大,吹得赵丰成的头皮一紧一紧的。朱大海从省肿瘤医院出院不到半年,就癌细胞扩散,疼痛难挨,白天黑夜都在嚎叫。他死的前一天,赵丰成去看他,他已神智不清,只是大声地叫嚷,痛!痛!痛!朱大海从发现病灶到去世,只挨了不到一年时间。赵丰成站在峰顶,思绪纷飞,如同风过林梢,脑子里呜呜作响。他想,比起朱大海,他们是同样的病,在同一家医院动的手术,朱大海只挨了大半年,而他已经挨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六千多个日子,他可以算是白捡回来的。这么一想,他觉得自己非常划得来。但他转念又一想,这六千多个赚来的日子里,除了爬山锻炼,还是爬山锻炼,他又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
赵丰成觉得他脑子里有些乱,干脆就不去想了。他看到太阳还在高高地挂在五峰山上,决定今天不原路返回,他要从峰顶北面的那条路下山,从那里下到纱厂路,去找他的一个老朋友喝酒。自从他患直肠癌后,十七年来,他一直滴酒不沾,戒了。今天他突然想喝酒了。于是,他从小平台的另一端下去,这条路他从没走过,一开始坡度很大,赵丰成下坎时弓着腰,走得小心翼翼的,下了陡坡,往前走二三十米,路就平坦了。赵丰成直起腰后,才想到住在纱厂路的那位朋友,早在三个月前就查出了胃癌,他不可能还喝酒。
赵丰成苦笑了一下。
此时,赵丰成的心里突然升腾起久违了的那种幻灭感。他很伤感地想,他身边的队友们都一个个地去了,他的朋友也跟他喝不了酒了。现在自己的身体这么好,再活个十年八年绝对没有问题,到时身体一直不太好的老伴肯定要先他而去,还有一些老朋友老熟人,也会先他而去,他活得越长,就是为了跟亲人、朋友和熟人告别吗?
赵丰成觉得他的身子在晃动,他低头看了一眼脚下的路,路没有晃,难道是山体在晃吗?他又看了一眼身边的那株松树,松树没晃。他看到那棵松树不大,但从根部就开杈了,是双树杆。赵丰成突然想起来,有一年,朱大海曾指着这株松树对他说过陈百通就是从这个地方跳下去的。当时赵丰成不理解陈百通,想他无病无痛的,不就是被儿媳妇推了一掌,至于要自杀吗?现在他明白了,人因为绝望可以自杀,因为尊严也可以自杀,还可以因为什么都不是的幻灭感,而自杀。
赵丰成对自己的发现或者说总结非常满意,他嘿嘿地笑了两声,他觉得他的笑声有点古怪,但这时他已经控制不住把他的身体往小路外歪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