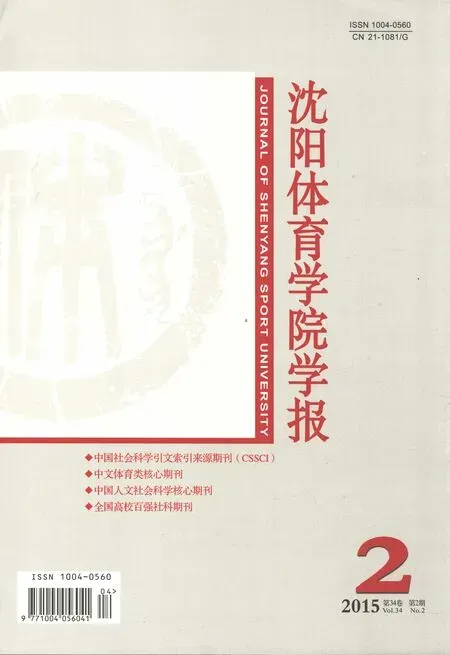中国武术发展的视觉范式研究
侯胜川,林 立
(闽江学院体育教学部,福建 福州 350108)
◀民族传统体育学
中国武术发展的视觉范式研究
侯胜川,林 立
(闽江学院体育教学部,福建 福州 350108)
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从视觉的观看功能切入,对武术的发展进行了梳理。认为在人类视觉的特定“视框”中,由“现实的看”师从于动物的攻击而形成武术的搏斗形式;由“表征的看”使武术具备了对动物“形”和“意”的模仿而进入套路系统;继而人们把目光转向大自然,以全新的视角超越了对动物“形”和“意”的模仿,用自然规律来指导武术的创造,从而使武术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现代社会,人们开始转向对武术纯美的艺术价值追逐;最后对未来武术的发展做出了探索,认为未来武术以游戏性和虚拟性为特点。基于范式的概念,把武术的发展分为原始视觉范式、古典视觉范式、现代视觉范式和后现代视觉范式4个阶段。
武术;视觉;范式;发展
在里德看来,“整个艺术史是一部关于视觉方式的历史,关于人类观看世界所采用的各种不同方法的历史”[1]。也有学者认为:“当代视觉文化就是世界的视觉化,它关心的不是世界的存在本身,而是世界如何被视觉感知和表达的。”[2]数千年来人们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视觉观看,总结和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武术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成果之一,亦是在观看—模仿—创造、再观看—再模仿—再创造的递进中发展至今。武术的缘起,普遍认为与原始人类的生产采集活动相关,即对动物的观察、模仿,然后创新性地“再现”了与动物的搏斗过程。“再现”实际上是人们对“观看”结果的重新编码。著名审美心理学家冈布里奇认为“再现”应当“是一种翻译,而不是一种抄录”,是一种“转换式变调,而不是一种复写”[3]。通过“再现”,武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系统,从技术到理论,中国武术在数千年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庞杂的体系,这一切源于们在生产活动中的观看。所以,观看与其说是观者之看,不如说是作者之看,观者最终要成为作者。本研究试图从人类视觉的“观看”切入探究是否存在一种范式,可以解读武术的演变历程,并为武术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1 视觉范式与武术演变
视觉是人类最重要的生理和心理现象之一。研究表明,至少有80%以上的外界信息经视觉获得。在原始社会,人类在与动物的搏斗过程中学会了使用工具,投掷野兽的石头、击打的木棍都可以在军事武术和民间武术中的飞镖、弓箭、长矛、刀、剑中找到原型;而各种武术招式同样可以从原始人类的生产采集活动中找到雏形。为了在与动物和自然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人类就不得不使用眼睛去寻找便捷、有效的攻击、自卫方式和工具。人类的眼光从来都不是被动的、机械的、单纯的,而是一个在先验的时间、空间范畴中主动发现和选择的过程。笔者认为武术的发展历程是人类视觉选择不同“视框”、视角的观看结果。本研究中把“视框、视角”以范式的概念切入。
范式概念和理论是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的。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4]。可以说范式存在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而所谓视觉范式的研究,是基于范式层面上对视觉形式进行考察及归纳、分析[5]。千百年来,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中国武术从来都是在人类视觉的感知、记忆、思维运用中不断升华、改进,逐渐和中华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中国武术所独有的范式结构。先人对个人和集体在搏斗中所获得的视觉体验积累在集体的方式中,作出带有历史色彩和文化痕迹的视觉范式,归纳成中国武术发展历史。本研究套用文化研究和艺术研究的分类概念,将武术发展的视觉范式分为4个阶段:原始视觉范式、古典视觉范式、现代视觉范式和后现代视觉范式。
需要注意的是,严格意义的武术在原始范式阶段并未真正形成,因此,本研究是一种“泛武术”的概念形式,即一切与武术有关或者相近的前期形式都归为本研究的对象。
2 朴素的视觉和图腾—原始视觉范式
原始人类通过视觉的观看,对动物的某些超人类能力进行模仿,以期获得类似于动物的攻击和防御能力,这就需要人类把目光锁定在动物的攻击、防御“视框”内;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困惑现象和难以征服的凶猛动物使原始人类敬畏且疑惑,原始人类也把它们放在特定的“视框”内,形成特定的图腾现象。一般意义上,“视框”有两层含义,一是观看主体生理上的视力范围和“基于观看经验的注意力范围(即观者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找到他所要关注的东西并确立自己的观看范围)”;另一种是基于表征的运作而形成的视框,它由视像的承载物等构成的表征所呈现的视觉边界和经过表征运作体系处理过了的视像本身所具有的视觉吸引力组成[6]。引入“视框”的概念在于对表征和现实做以有效的区分,从而引入“表征的看”和“现实的看”两种概念,进而在本研究中引入原始视觉范式和古典视觉范式。“现实的看”是指从人类自身的客观生存需要出发而选定的观看“视框”。
2.1 朴素的武术启蒙—现实的看
原始社会的文化活动并未出现分化,生产是唯一的社会目标。动物作为原始人类天然的对手,关系着原始人类生存资料的多少,缺失动物意味着原始人类缺失充足的食物和强健的体魄。但是,除了智力上的差别外,在捕食的技能上动物占据了上风,于是原始人类朴素地认为只有向强者学习才能挑战强者。人类在狩猎的过程中,“为了保护自己而与动物搏斗中,练就了击打、闪躲等格斗技术,为武术的形成准备了一定的先决条件”[7]。“它(武术)的源起与原始人对于石器、骨器、木器的制造和使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8]与猛禽野兽的尖牙利爪相比,原始人类知道无论如何模仿都无法企及动物的攻击防御能力,于是粗糙的石块和木棒成为伸长肢体、借物打物的狩猎工具。工具的使用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对于武术而言,它是兵器的雏形。“原始民族最初由狩猎的部落构成,原始狩猎者在与自然界打交道、作斗争的过程中,接触最多的是动物,头脑中形成的表象也多为动物。所以,在原始艺术中,以动物为摹仿对象特别多。”[9]我国最早的诗歌集中记载有人们徒手与虎搏斗的场景,“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暴虎,献于公所。”[10]。
获取更多的生产资料是原始人类“现实的看”朴素的动机,最为朴素的动机也最能激发人类的潜能,于是,原始人类在集体配合(军事武术的原型)、矫健身体(锻炼的目的)、便利工具(武术兵器的原型)、徒手踢打擒拿(武术招式的发轫)等方面师于动物,为武术的徒手搏斗和兵器的形成创造了启蒙条件。
2.2 图腾崇拜—敬畏动物
并非所有的动物都能经过视框“现实的看”而成为搏斗和兵器产生的原型。在凶猛恐怖的动物面前,人们极度恐惧,奢谈模仿。恐惧由视觉延伸至心灵而为敬畏,敬畏长久挥之不去,必然成为信仰,于是图腾出现了。图腾一词最早出于18世纪末的文献中,由印第安人的土语转化而来,意为“他的亲族”“家庭”等。维尔金对东印度群岛土人的宗教信仰进行了考查,认为图腾制是由人类死后转生为动植物的信仰而来[11]。原始人类的经济生活以对单位区域的动物狩猎和植物果实采集为必然的集团生存体制。在自然灾难面前,人类的自卫保护能力极为薄弱,于是对所赖以生存的动植物,以及自然的敬畏产生了图腾崇拜。因为各民族、部落所在区域的不同,因此所崇拜的对象也不尽相同。如埃及国王惯用鹰为保护神,而且称为鹰的子孙;希腊人崇拜的神,以蛇居多;英格兰人以动物、植物为姓的习俗居多。中华民族普遍以龙为图腾。实际上,我国原始社会部落和各民族的图腾并不相同。中国古代部落以兽为名者甚多,如共工、三苗、鲧等。日本学者井上芳郎称中国上代传说的帝王,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均为动物的变形[12]。龙是中国古人对蛇、鳄、鱼、马、牛、鹿、虎,以及雷电、云、龙卷风等多种自然多元现象融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是我国古人对动物崇拜和自然崇拜的结合体,也是中华民族崇拜的结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
3 理性的视觉和仿像的再现—古典视觉范式
古人并不满足原始视觉范式“现实的看”,人们开始把“现实的看”进一步深化为“表征的看”,而人们观看的“视框”并未稍出动物左右。通过视觉的观看,人们在武术的创造中运用了理性的思维和对动物仿生性的“再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胸怀创造性地对武术进行了再生产、再编码,由此中国武术超越了对动物“形和意”的模仿,进入了古典视觉范式的海洋,武术从原始的搏击而象征化、套路化、理论化。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也由此显现出来。
3.1 视觉象征而武术化
在中国的武术拳种和动作形象中,有一部分是象征化的武术拳术和动作,如龙拳、骀形、凤点头等,它们并不存在,却不妨碍被人们象征化为肢体动作并赋予特定的观念。如流传在广东的龙拳拳决云:“动若神龙游太空,静似玉女守深闺”[13]。虚幻的“游龙”在观念化后演变为武术的动作诀要,这是人们在特定视框下“表征的看”的结果。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不断前进,恶劣的原始环境逐渐消失,视觉的观看随即从“现实的看”转入“表征的看”。按照斯图尔特·霍尔的说法,表征有两层含义:“表征事物即描绘或摹状它,通过描绘或想象而在头脑中想起它;在我们头脑和感官中将此物的一个相似物品摆在我们面前;……表征还意味着象征,代表,作(什么的)标本,或替代。”[14]人类师从于动物的历程并未裹足不前,换言之,在古典范式中,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野兽猛禽的简单动作模仿来强化自身的攻防技术,而是“现实的看”的结果系统化、概念化和符号化,师法动物的同时也开始兼顾人的主体创造性,主张模仿和自我创新的统一。在创新的过程中,抽象的动物被提炼出来,具备了特殊的象征意义被动作化、拳术化,形成了中国武术特有的一类武术拳术和动作。
3.2 形似而神似以套路化
“象形术(拳),顾名思义,是从禽兽动态、山河之变的现象中得来的。”[15]从历史来看,把动物的一技之长纳入中国武术体系中延续了数千年的时间,也因此而“拟百兽之形,树武林百家”:明末清初福建流传对狗的模仿,形成了“踢打捆绑擒”狗拳[16];清顺治年间方七娘“见白鹤振翼有力、走跳轻盈,创编成白鹤拳”[17];明末清初山东王郎“见螳螂捕蝉之巧,……融入攻防法创编成螳螂拳”[18];“(少林十三抓)是古人通过对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观察和提取动物的在自然界为生存而互相搏击的动作为素材,不断提炼加工,象形取意创编而成的。”[19]“对武术而言,人们通过对动物动作、活动方式、生命力等仿生,再生产了套路的象形拳系统、养生系统与游戏方式,以及武术的动物化意向。”[20]人们对动物形和意的模仿,使武术进入了仿生的套路系统,武术发展跳出原始的搏斗形式,呈现出了崭新的气象。
这是人们跳出“现实的看”转向“表征的看”的必然结果,也由此使“观看”具备了诗学的维度。“表征的看”的武术套路是对原始范式武术(技击)的“再现”,即套路虽然脱离技击,却在招式动作上逼真地再现技击的场景。“表征的看”虽不看重技击,但却并不忘本,处处体现技击的意识,并把“现实的看”的搏斗场景链接起来,使武术搏斗具备了连环画的艺术功能。在套路的拆招和太极推手中,套路更是在虚拟的场景中逼真“再现”了技击的神明效果。为技击(搏斗)而生的武术在“表征的看”后,艺术功能逐渐和技击功能平分秋色,成就了中国武术美不胜收的仿生套路体系。
3.3 观看自然而理论化
人们显然也不满足于对动物“形”和“意”的模仿,逐渐跳出“视框”的约束,以全新的观看方式——视角,从更高的观看位置和观察角度把目光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的自然空间。武术的创造终于跳出对动物模仿的局限,人类从与自然对立开始转向与自然和谐共生,用整体观的视角使武术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伟大时代。以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为代表的内家拳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以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创造了中国武术的新华章。
拳起于易,理成于医,即认为《易经》是中华文明的源泉。《易经》并非是街头占卜的一种教科书,而是古人总结自然规律的智慧结晶,它提出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关于宇宙万物的产生、演变和辩证统一规律的理论体系。“它在三千年之前就揭示了宇宙演化的核心‘一分为二’的辩证统一规律;在世界上第一个创造了‘二进位制’的计数法‘八卦’;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21]。同样,中国武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易经》的理论指导。武术真正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这也使武术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和国际上的国家符号之一的原因。
3.3.1 太极拳与太极图 太极拳起源的传说之一为张三丰“仰观浮云,俯视流水”,察蛇鹤相斗而悟自然生克之理:“长蛇摇头微闪,躲过雀翅”而悟“蟠如太极,以柔克刚之理,由按太极变化而粗出太极拳。”[22]太极拳在动作表现上并无明显的“浮云、流水、蛇鹤”痕迹,可见张三丰对自然万物的观看提炼出的“冲虚圆通”之道和以柔克刚之理才是太极拳的真正成因。中国武术的发展从“看得见”的动物模仿进入“看不见”的混沌之境,观看方式的变化颠覆了武术发展的轨迹。法国学者让·皮埃尔·韦尔南在阐释“偶像”和“神像”时,对“看得见”与“看不见”有着深刻的见解“当偶像产生了把它为瞄准对象的目光的时候,神像却召唤着视觉,让看得见渐渐充满着看不见……。神像,不属于看得见,而恰恰属于看不见,于是它意味着,尽管由神像表现着,看不见仍然停留在看不见中。……人们的目光,远远不能把神明凝结为一种跟它那样固定的形象,反倒是在神像中,不断看到看不见之物的浪潮一阵阵的袭来”[23]。在中国武术中,看得见的“偶像”——动物逐渐淡出,看不见的“神像”——理论逐渐成熟。罗时铭[24]认为中国武术的真正形成应该是在宋代基本完成,其主要原因是理论基础的形成,代表作品包括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张伯瑞的《悟真篇》。
假设太极拳与张三丰对蛇鹤的观看有关,则张三丰“视框”中的蛇鹤给了他顿悟太极拳的契机。然而任何顿悟都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基础上。无论太极拳与谁相关,它一定是受到《易经》的影响。太极拳的思想直接源自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而《太极图说》乃是受《易经》的启发而来。太极图被称为中华第一图,因为图似两条一明一暗的鱼交相呼应,又称阴阳鱼。有学者认为太极图源自河南洛油伏羲台下黄河与洛书相汇后形成的一浊一清“涡漩”,并认为这是人类阴阳辩证思维的起源。
先人用特定的“视框”观看了蛇鹤、漩涡等自然现象,切入了全新的观看方式——视角,把观看的结果归纳演绎为理论,以理论来指导已有的武术,使其创造成为更为高明的武术。这是武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
3.3.2 五行学说 金、木、水、火、土是自然界最为常见和人类生活最为紧密的东西。古人把最为常见的东西按照金、木、水、火、土归为五类,即“五行”,所以金、木、水、火、土不再指代具体的实物,而是符号化的万事万物。“五行”一词出自《尚书·洪范》,认为世间万物相互生息又相互克制。自然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形成稳定的生态链。人们对动物的观察中发现了生物的生、克关系链(古人在“现实的看”的引导下表征的创造了金狮拳、蛇拳、鹰拳等具有生物生克象征意义的拳术),领悟了自然界中没有“常胜将军”,任何凶猛的动物都要受到其他制约,唯有掌握了动物的习性,才能驾驭它们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古人以“相生”“相克”的“五行”理论“再现”了蛮荒时代的武术技术——形意拳。劈、崩、钻、炮、横五拳代表了自然五行,“并根据易医理论,把内五脏肺、肝、肾、心、脾以及外五官鼻、眼、舌、耳、人中与五拳相匹配,形成一套形意拳独特的健身技击原理”[25]。五行相生关系为“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衍生成劈拳变钻拳,钻拳变崩拳,崩拳变炮拳,炮拳变横拳;五行相克关系为“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借此演化为劈拳克崩拳、崩拳克横拳、横拳克钻拳、钻拳克炮拳、炮拳克劈拳的攻防原理。然而,源于动物生克原理的武术并没有忘本,动物依附于理论框架下依然存活于武术体内。“人与动物的关系,并不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减弱,变化的只是形式的改变,没有本质的改变。”[26]形意拳中的基本拳法依然取材于最为原始的动物,如十二形拳中包含了龙、虎、猴、马、鸡、鹞、燕、蛇、鼍、骀、鹰、熊12种动物。
4 纯美的表现—现代视觉范式
1957年,查拳名家常振芳指出:“打查拳要像龙一样空中飞舞;像虎一样勇敢猛扑;像蛇一样柔软;像鹤一样动中求静,像猴一样灵活善变,动作应力求上下相随,内外相合,这就是功夫所在。”可惜的是,现在很多练查拳者都没有这样的功夫,为此,他发出了“现在很多(人)打查拳,都离开了这个精神”[27]。的确,步入现代社会以来,武术“变味”了。既不同于原始视觉范式武术的“练为战”,也不同于古典视觉范式武术的“练为验”,在现代视觉范式中武术转化为“练为看”,而且是纯美的看,这标志着武术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现代视觉范式。在武术的现代视觉范式,一个重要的改变是观者的变化。在武术的前两个范式阶段,观者即作者,而在现代视觉范式,观者仅是武术的观赏者,即追求狂欢、纯美、浪漫的,用眼睛在生活中审美的普通观众。所以,笔者断言,因为作者的缺失,人们再也无法创造出太极拳、螳螂拳这样极具内涵和象征的武术来;而现代社会中影视武术、舞台武术的泛滥,不过是现代技术的机械复制而已。
4.1 现代技术的新“视框”
在现代社会,以“屏幕”为代表的平面新媒体区分了外在和现实的边界,人们的视觉观看重新回到新媒体的“视框”中来。罗埃默尔说:“绝大多数电影导演把银幕看作是一个‘画框’然后精心的构图,……构图优美的镜头所构成的段落往往使观众处在画框之外,成为对导演构图慧眼赞赏不已的旁观者。”[28]在现代社会,观众的眼睛被“屏幕”锁定在特定的视框中,作为主角的武术在威亚、爆炸、剪辑等新技术的处理下,成为人们心中的“真实”武术。
现代武术的现实已经完全超越了武术的“真实”,“这已经不是模仿或重复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戏仿的问题,而是用关于真实的符号代替真实本身的问题。”[29]原本在民间神秘流传的武术,在现代传媒的狂轰滥炸中走进千家万户,在报纸、杂志、电影、电视、网络的推介中平面化和生活化了,人们总是在一个有限的“屏幕”中观看经过现代化包装的美轮美奂的武术。于是,在现代人的印象中,武术是李小龙的功夫、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李慕白的竹林飞翔、张无忌的“九阳神功”,武术是浪漫的、唯美的、令人向往的;所以,香港功夫片(武打片、武侠片、动作片)盛行的时候,香港武馆就很难招收到学生了,任何学生看到不会飞的武术家都会摇头走人的。
4.2 武术的“再现”与复制
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并不意味着旧有生命的死亡,但却会掩盖旧生命的光芒。古典视觉范式开始退居幕后,现代视觉范式走向舞台中央。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后半叶,现代主义思潮不断涌动,以及工业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的深入,武术“再现”的理想已经不同于原始和古典“再现”的范畴,同样,武术的生产彻底摆脱了数千年来因因相袭的传统,武术技术的发展被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取代,照相机、电影、电视、网络等新媒介的发明使武术跟随者其他艺术形式进入狂欢化的发展。现代人虽然无法创造出类似太极拳、螳螂拳的武术,但却可以对这类拳术进行无限制的复制。武术发展一直所依赖的“再现”已经完全错乱。在一次次的复制中,“再现”已经“走进迷狂的状态”:快太极、跪滑、街舞、体操、戏剧、杂技等被排列组合在武术中,现代武术仅保留了外壳,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5 虚拟和体验—后现代视觉范式
黑格尔曾经把史学划分为白描性历史、反思性历史和哲学性历史三个层次,分别来回答过去“是什么”、过去“为什么”和将来“干什么”的问题。已有学者对未来武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邱丕相教授以人类生态文明的视角认为:“自然的武术、智慧的武术、艺术的武术是未来武术的发展方向。”[30]后现代是相对现代而言,武术在经历了原始视觉范式、古典视觉范式和现代视觉范式后,必然在未来进入到后现代视觉范式。后现代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后现代武术必将超越影像、纯美、浪漫的现代武术,以游戏和虚拟的真实体验为方向。
5.1 游戏性
后现代的图像逐渐超越了“观看”的范畴,电影、电视、网络越来贴近人的真实生活,甚至把人囊括其中,主体和自我陷身其中,在约定的范围自我放逐。以网络游戏为例,当代以暴力、武侠、功夫、任务为题材的网络游戏占据了游戏的半壁江山,无数青少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可以想象在未来的后现代社会,游戏的发展必然更加“真实”、超越现有的平面虚拟场景,在3D、Maya等软件和硬件的支持下,人们不再是平面地享受游戏的快乐,而是整体全面、身临其境地进入游戏。武术以其特有的魅力包含了功夫、武侠等网络游戏的特点,必然实现人在游戏中狂欢式的放逐。
5.2 虚拟性
经过现代社会图像的无限制“复制”后,后现代的武术开始超越自然存在的“物”,甚至于转化为完全不存在的幻想之物,不再是简单的平面化,而是虚拟的更加“真实”化。虚拟是科学技术、设备不断更新和发明的产物,“虚拟是人们利用计算机创造出来的电子表象,它既可以是对实在世界的一种模拟,也可以是一个想象的世界”[31]。由于虚拟无所不能,人们可以在虚拟的场景中真实地参与其中,和想要的对象切磋武术,或者合作闯关。“博物馆里还设有立体影院和数字化多媒体互动的区域。在‘时空隧道’里,参观者可以进入未来的生态武术区;喜欢搏击游戏的参观者也可以亲自上阵,试试身手,体验和李小龙‘过招’。”[32]上海体育学院中国武术博物馆中有一项人和李小龙虚拟图像对打的设计,设计了李小龙的音效和经典武术动作,任何人站在特定位置都可以和偶像一决高下,最后计算机给出对打的分数值。
当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虚拟也不局限于历史的真实,也可以是诗的真实——任何可以想象的都可以拿来(武侠、科幻小说人物等),关公战秦琼将不再是虚妄。相信在不久未来,武术人可以在设置的场景中化身钢铁侠、绿巨人用中国武术拯救世界。在传感技术高度发达的后现代,除了视觉上的体验,还可以有触觉的体验。武术的实战完全可以不含危险性的情况下比试,并在特定技术的测试下得出自己的武力值以及需要提升的训练方向,以确定在即的“江湖”中的位置。任何一个习武的后现代人都可以在自我武术修炼的“知己”功夫层次上找到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在特殊的设备中,任何人都可以体验三维图像、音响效果和具体的武术动作,从而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完成真实的武术训练。
6 结语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33]本研究并非认为中国武术的发展一定是按照视觉范式而来,且在后现代视觉范式中,视觉并非唯一的因素。以视觉范式的武术研究只想提供一个阐释中国武术演变历程的切入视角。诚然,历史中走来的中国武术,历经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熏陶,其“文化成因”错综复杂,对应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包罗万象,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的视角来探究中国武术发展,才会发现隐含其中的“历史真实”一面。
[1]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M].刘萍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5.
[2]李鸿祥.视觉文化研究—当代视觉文化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5:100.
[3]朱立元.西方审美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4]范式.百度百科[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 26218.htm.
[5]孙晶.视觉范式[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7.
[6]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0.
[7]编委会.中国武术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3.
[8]邱丕相.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9.
[9]张宏梁.论艺术与仿生学的结缘[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84.
[10]诗经·国风·郑风·大叔于田.
[11]转引自岺家梧.图腾艺术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2.
[12]转引自岺家梧.图腾艺术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8.
[13]编委会.中国武术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99.
[14]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
[15]李仲轩.逝去的武林-1934年的求武纪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222.
[16]周金伙.福建少林狗拳(上)[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9-10.
[17]康戈武.中国武术实用大全[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215.
[18]康戈武.中国武术实用大全[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219.
[19]王培锟.漫步武林[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174.
[20]戴国斌.武术的仿生性生产[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33(6):10.
[21]于志钧.中国传统武术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7.
[22]杨澄甫.太极拳使用法[C]李天骥.武当绝技·秘本珍本汇编.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276.
[23]让·皮埃尔·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1:440.
[24]罗时铭.寻觅武术产生的历史足迹—兼谈中国武术的概念问题[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0.
[25]佚名.形意拳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拳学依据[EB/OL].中国功夫网,2009-09-12.
[26]戴国斌.武术的仿生性生产[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33(6):28.
[27]丁艾.看鲜花朵朵壮丽—在全国武术评奖观摩大会上[J].新体育,1957(13):11.
[28]罗埃默尔.现实的表层[M].周传基译,转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f59bf7010007n8.html.
[29]让·鲍德里亚.拟像与仿真,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M].汪民安等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37.
[30]邱丕相,王震.人类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未来武术[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41(7):4
[31]孙晶.视觉范式[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106.
[32]刘轶琳,曹子琛.中国武术博物馆:读“武林秘笈”与李小龙“过招”[EB/OL].东方网,2012-09-06.
[3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郭长寿
Visual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 ushu
HOU Shengchuan,LIN Li
(P.E.Department,M injiang University,Fuzhou 350108,Fujian,China)
Using the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ual function of watching,the authors reviewed theWushu development.Studies suggest that in the human vision specific“frame”,from animal attacks“reality”and the formation of Wushu fighting form,the“representation”of the Wushu had the animal“shape”and“meaning”im itation into routine system and then turned toward the human nature,w ith a new perspective to go beyond animal“shape”and“meaning”to im itate,creating natural law to guide the Wushu,and Wushu development reached a hitherto unprecedented height.In the modern society,people began to pursue the Wushu artistic value;at the end of the study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ofWushu wemade an exploration and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ofWushu w ill show characteristics of games and virtuality.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paradigm of the concept.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of the original visual paradigm,classic visual paradigm,modern visual paradigm and post-modern visual paradigm four stages.
Wushu;visual;paradigm;development
G852
A
1004-0560(2015)02-0130-06
2014-10-28;
2014-11-15
2014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A类(JAS14256);闽江学院2013年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MJUC2013072)。
侯胜川(1980—),男,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术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