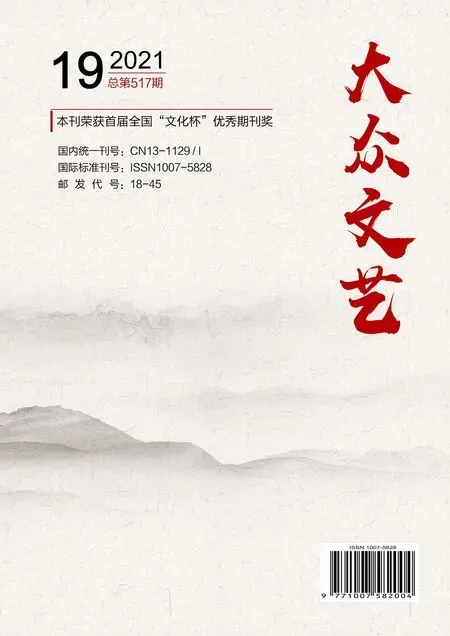论《大宗师》之“一”
徐 敏 (汕头大学文学院 515063)
论《大宗师》之“一”
徐 敏 (汕头大学文学院 515063)
“一”作为古代哲学当中一个重要的字,在庄子的哲学思想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有着齐同万物、天人合一的含义,也代表着天地未分之时自然、纯一的状态。在《大宗师》当中,“一”的这两层意思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一;一样;万物之源
《大宗师》为《庄子·内篇》中极为重要的一篇文章,本文以“道”为宗师,自此展开论述。在《齐物论》当中,庄子就提出了“道通为一1”“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2”等重要观念。到了《大宗师》,庄子依旧秉着此观念,阐释作为“宗师”的“道”。庄子也并未离弃“一”这个字。从“故其好之也一”到最后“乃入于寥天一”,这个字在本文中出现过十四次。
“一”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3在道家的观念中,“一”象征着“整体”和“同一”。在《大宗师》中,这十四个“一”中也有着复杂的含义。
一、《大宗师》概述
《大宗师》是论述“道”及得“道”者的一篇文章,全文的根本主旨是以“道”为宗师,“道”即为“自然”。文章开篇即开始说明当人有了“知”之时,便已破坏了生命的整体性。在否定了人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后引出“真人”和“真知”的辩解。庄子在此强调了“道”的作用,从“道”的角度看来,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同一的。他描述了得道之人——真人的种种状态。
紧接着,庄子回归到“道”本身。在庄子看来,“道”即为“顺其自然”。他认为人们运用知识来有心而为,不如顺乎自然。之后,庄子在下文解释“道”是“自本自根”的,在天地产生之前,道便已经存在,它不仅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生存的根据,也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本原。得道之人便能体验“天人合一”的精神。下文的寓言故事引出了“得道”的方式,即“外”,亦为“忘”——忘天下,忘物,忘生死。忘掉一切,依乎自然,就能获得生命的本真体验。
从某种角度上而言,《大宗师》即为一篇歌颂“道”的文章,文中无不体现出庄子顺乎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通过“忘”到达“物我为一”的境界,从而成为得道的“真人”。如同庄子其他的篇章一样,混同世间万物而为“一”同样是《大宗师》中的重要命题。
二、《大宗师》之“一”的释义
1.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在这个句子当中,“一”的含义应当理解为“相同,一样”。在这里,整个句子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他对于事物的爱好是一样的,对于事物的不爱好也是一样的。庄子是不赞成“成心”的,成心即为偏见,喜欢与厌恶在他看来即为有“成心”,“好”与“弗好”两者的区分不存在,因此在他看来那么对待事物的态度当然是相同、一样的。
2.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
在这里,“其一”指能同于天道,与天为友的人。曹础基说:“天包罗万物,故从相同方面说,与万物同,就是师于天。4”与天交友的人,应该去除“成心”,对待事物都是同一的,这样的人才能与天相交。“其不一”,即为束缚于凡情,与人交友的人。在社会当中,一个人对待所有的事物都一视同仁是及其困难的,而当“成心”出现,我们能够与他人相伴之时,便只能与人为友,而不能与天为友。真人的魅力之处便在于,无论是对人对天,他的态度都是同样的,这种“一”便是他以“道”为宗师能够达到的目标。
因此,在这个句子中,“其一”指对待天地万物秉持同样的态度,是抛弃世俗情感的束缚的,是与天相交时的态度;“其不一”则代指凡情,受凡情影响,对于不同的事物人们会有着不同的态度,这是用于与人相交的。得道的真人不管是与天交友或是与人交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一样的,在他们眼里,天与人都是同样的。“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当中,第二个和第四个都当理解为“同样”。
3.善妖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又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
曹础基在《庄子浅注》中解释到:“一化,一切变化。”5张默生则解释为:“一化者,万化之原也。”6在此,笔者认为“化”为“变化”,“一”即为万物之源。变化是为追求混同万物的境界,天地合一,所有的东西都不再有区分。这里的“所待”即为“道”,而“道”所能带我们走到的世界是混同万物的,因而,在这个句子当中,“一”可以解释为“一切”,但它的同时也包含着“整体”的概念,这个“一”,不仅仅是“一切变化”的“一”,更是“万物合一”的“一”。
4.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也。
生死存亡在普通人看来是不相同的,生者欢乐死者哀伤。而对于子祀、子舆、子犁和子来这些得道之人来说,他们要忘生忘死,对于他们而言,生与死是相同的、一样的,“生死存亡是一体的”。这个“一”,在这里的意思同样可以解释为“相同,一样”。能够忘记生死,知道死生没有什么区别的人,就是他们要找的道同志合的朋友。
庄子在本文中解释了“道”之后,便回到如何得道这个问题。他说明要得道就得忘生忘死,知道生死本是一体的,它们无从分开,也无需区别对待。这是修道的人必须要理解的。
5.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本句中的两个“一”当是相同意思。从整段看来,这里是说:一个用模子作的人形,说:“我是人!我是人!”造物者必定会认为它是不祥之物。那么把天地当成这个炉子,把造化者当成锻冶的工人,人生存在这个大炉子之中,哪里会有不适宜的地方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一”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旦”的意思,一旦用模子刻成的人有了人的自觉,造物者必定会认为它是不祥的,而一旦能够将天地看作一个大炉子,将造物者看成那个冶金的人,就会明白天地之间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合待的,生与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命运也没有什么不能顺从的。
6.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
成玄英解释“一气”为“天地未分的混沌状态7”。“一”作为一个重要的古代哲学概念,指万物的本源,也指由“道”派生的原始混沌之气。曹础基解释“一气”时说:“道的作用是支配着天地万物的,所以叫天地一气。游乎天地一气,即顺着道的作用而游。8”庄子希望能够顺着道回归到天地初开的原始状态,追求的是混同万物、冥一变化的境界。子桑户他们要与造物者为相交,必然要回到造物者造出的万物为一的世界当中去。因而,“一气”便是天地未分时候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之下,物我不分,忘生忘死。
7.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
对于“乃入于寥天一”,林云铭的解释为:“乃入于寥而不纷、天而不人、一而不二之域。”9庄子在《齐物论》中说过“道通为一”,《大宗师》的主题是“以道为宗师”,而在“道”的视野之中,从“道”的角度来看,所有事物的本质是一般无二的。在本句当中,我们可以读出如下意思:完全听任自然的安排,就能够进入到自然的纯一境界。这个“一”,有着纯一、无二的意味。
总体看来,在这十四个“一”当中,包含着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和“天人合一”的理念。
三、《大宗师》之“一”的含义
在上面的分析中,庄子在《大宗师》中间的“一”,主要是将其放在哲学意义的层面上来讲,从这个方面来看上述的十四个“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将“一”作为“相同、一样”的意思,另外就是“万物之源,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的意思。
1.作为“相同、一样”的“一”
《大宗师》中很多的“一”释义为“一样”这个“一”与“二”相对的。道家认为道生出天地未分的混沌之气,随后天地分开,便出现“二”。有了“二”,就有了两极的区分,阴阳的不同,也有了喜与恶,好与坏,美与丑的区别,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环境之下,人难以不带偏见的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成心”也就随之而来。
庄子在《齐物论》中说过要去除成心,因此,就不得不将这种二元对立“合二为一”。庄子不时地提及到要将不同的事物看作是一样的,并提出“道通为一”的概念,从道的角度来看,无论貌美的王嫱,还是丑陋的癞子,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在天地之间,站在道的高度上,无论生死、美丑都无需计较。真人作为得道之人,看待世间万物就应等同视之,表面上一样的东西是一样的,表面上不一样的东西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与其痛苦地喜生恶死,相濡以沫,不如回归到道的世界里在天地之间欢快地畅游。
庄子在这里用“一”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二元对立的世界让人活得痛苦倒不如“两忘而化其道10”,秉着“道通为一”的立场,去除个人偏见,将万物等同视之,从而顺乎自然,活得无忧无虑。
2.作为“万物之源、混沌之气”的“一”
“一”在古代中国有着很强的哲学意味,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生一”的思想,这个指代万物之源的“一”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同样很重要。
庄子认为最原始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是最完美的状态,文明的出现打破了原始社会的生态结构,人类应该要回到那种原始的状态当中去,回归到生命之本源。《齐物论》中庄子提出的“复通为一”正是如此。
《大宗师》中的真人以“天人不相胜”为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这里的真人通过“忘”的方式让自己与天地混为一体,将万物合一,自己的心境则回归到天地未分之时。
庄子看到了二元对立的世界中的种种苦难,追本溯源上去,自然是回归到天地未分,“一”未分成“二”的世界当中去,这种苦痛自然就能终止。那是未曾破坏生命的本真状态。在混沌日凿七窍而死的寓言里我们也能清晰的看到,混沌遭到破坏的时候,死亡也随之而来
因而,“一”在这里是代表着生命之初的纯一状态,它不能被抛弃,不能被破坏。在庄子的眼里,人类文明破坏了这种自然的生命状态,得道的真人和凡夫俗子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能够通过“坐忘”“心斋”等方式来“游乎天地一气”,不被凡情所束缚,在自然的状态之中过着顺应自然的生活。这种顺乎自然的思想,即是庄子哲学思想的最根本。
“一”在整部《庄子》当中出现了上百次,它不仅仅是作为量词的“一”,更是庄子哲学思想当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一”是万物之始,天地未分之时便是“一”,它象征着生命之源、天人合一;在天地分开,私心出现之时,它亦象征着去除成心、齐同万物。总而言之,庄子的“一”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并且最终回归到了他“顺其自然”的根本哲学思想上去。
注释:
1.郭庆潘.《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1月版,第70页.
2.同上,第79页.
3.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上海书店,1985年4月第一版,第1页.
4.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10月第一版,第93页.
5.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10月第一版,第95页.
6.张默生.《庄子新释》.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第131页.
7.郭庆潘.《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1月 版,第269页.
8.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10月第一版,第104页.
9.转自:杨柳桥.《庄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79页.
10.郭庆潘.《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1月 版,第242页.
[1]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郭庆潘.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杨柳桥.庄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张默生.庄子新释[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