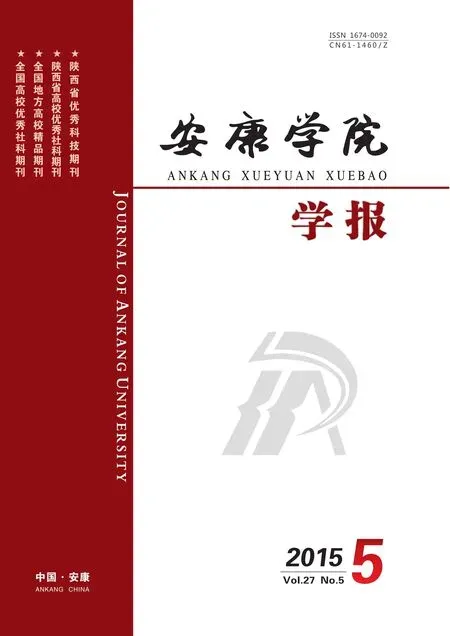现实与观念:中国侠文化的双重性解读
白贤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现实与观念:中国侠文化的双重性解读
白贤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中国古代的侠,应该有现实之侠与观念之侠的区别。大约唐代以后,由于观念中的侠符合人们的许多心理期待,从而日渐取代了现实生活中的侠,成为人们对侠的主体认识。在此过程中,侠也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标志。把握侠的这种现实与观念的双重性特征,是解读中国侠文化的关键所在。
中国侠文化;现实;观念;唐代
一
侠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特殊群体,约产生于春秋战国,兴盛于秦汉魏晋,转型于隋唐五代,消歇于宋元明清,其流风余韵则至今不绝。顾颉刚先生说:“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1]冯尔康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中亦云:“汉以后游侠消失。”[2]但若翻检有关典籍,便不难发现:汉代之后以侠名者大有人在,岂可谓汉代以后无侠?正如日本学者增渊龙夫所言:“《汉书》以后正史不再立游侠列传,这并非意味着游侠活动的衰退,而是因为历史记载的视角固定到另一面。”[3]彭卫先生说得好:“一些学者在观察游侠在中国历史上的步履时,把汉代(尤其是西汉)作为侠者终结的休止符。实际上,如果我们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侠者,便可以相当清晰地发现,游侠在中国古代以不同的表现,始终顽强存在着。它存在的本身,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一个表现;而其存在形式的多样化,则是通过一个社会群体的命运,映现出中国历史的变迁。”[4]
可见,侠在历史上虽历经几度兴衰,但始终以其形形色色的变种活跃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尤其是侠的人格与精神,更具某种“超越意义”,产生出广泛而持久的心理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华传统道德的构建与民族性格的塑造。学者陈晋即将侠客的“赖力仗义”与儒家的“归仁养德”,道家的“顺天从性”并列为中国传统人格的三大理想模式[5]。蔡尚思先生视墨侠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化九大支柱中“最闪光的一支大支柱”[6]。沈从文先生认为,在民间社会,“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7]。尤当一提的是,就连向来鄙薄武事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深受侠与侠文化的影响,乃至“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几乎成为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8];而“儒、隐、侠”亦被视为“中国学者之三态”[9]。此外,每当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总会有一些有识之士挺身而出,大倡侠风。如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维新志士康有为发出“士无侠气,则民心弱”[10]的感慨,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有“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11]的喟叹。时至今日,每当提及侠,人们多半仍会产生莫名的崇敬之情。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侠是正义的化身,他们除强扶弱、打抱不平;侠是诚信的代表,他们义无反顾、一诺千金;侠是英雄的模范,他们身怀绝技、力挽狂澜;侠是自由的象征,他们来去不定、天马行空……总之,侠有着太多太多的地方值得我们憧憬和向往。
然而,翻检史籍记载中的侠,却往往令人大失所望。如汉代著名“游侠”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12]。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至奸人妇女,持吏长短,纵横郡中”[13]。汉末以“健侠知名”的董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14]。北齐“粗侠”毕义云“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及贵,恣情骄侈,营造第宅宏壮,未几而成。闺门秽杂,声遍朝野”[15]。唐代郭元振在任通泉尉时,“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以遗宾客,百姓苦之”[16]。诸如此类之侠,不胜枚举,而符合我们道德期待的“侠”却寥寥无几。毫无疑问,我们如今观念中的侠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侠有着较大差异。
二
其实,侠在诞生之初并无令誉,且长期以来被视作异端。如最早将侠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并加以论断的韩非子说:“人臣肆意陈欲曰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17]西汉的司马迁虽对侠之“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12]的精神盛赞不已,但并不否认其“不轨于正义”的行为。而司马迁所谓“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的议论,实际上透露出时人对侠的普遍不满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又有“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之语,隐晦地道出了司马迁对游侠的态度与时人的一致之处。此外,正如历代学者所指出,司马迁之所以称道“侠客之义”,乃“彼实有见而发,而激而云耳”(秦观《淮海集》卷20《司马迁论》),是将自身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上《正史类》)的悲愤情结蕴含于《游侠列传》之中,实为“幽而发奋”之作,难免有偏激之词。。东汉班固也说:“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13]因此,在他看来,游侠“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13]。之后,荀悦更是明言:“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并称其为“德之贼也”[18]。《史记》《汉书》之后,正史不再为侠单独立传,但在《后汉书》《三国志》乃至魏晋南北朝历代史书中,每提及侠,亦多贬损之辞。如“王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14]。“(石)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19]。“高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数为劫掠,州县莫能穷治。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15]“(李)元忠族叔景遗,少雄武有胆力,好结聚亡命,共为劫盗,乡里每患之。”[15]“毕众敬……少好弓马射猎,交结轻果,常于疆境盗掠为业。”[20]“(沈)光独跅驰,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21]据笔者观察,这种对侠一味的排斥与批判,直至唐时方有所改观。有唐一代,不仅各种各样的“侠”空前活跃,使传统侠的类型大为丰富,而且随着侠义文学与咏侠之风的兴起,使历来备受史家批判的侠于唐时大放异彩,渐获佳称。从此之后,侠逐渐由历史记载转为文学创作,从史家“实录”转为文士“幻设”[8],人们对侠的认识也由“肆意陈欲”的代表转为“主持正义”的化身。隋唐五代,是中国侠与侠文化发展历史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尤其是唐代,其上承魏晋南北朝宗族豪侠之遗风,下启宋元以降江湖义侠②宋元以降,由于深受儒家之义的影响,侠已由“以武犯禁”的化身变为“主持正义”的代表,故曰“义侠”。与此同时,类似汉魏时期横行乡里的宗族豪侠,则被摒除出侠的队伍,并成为义侠打抱不平的对象。义侠是中国之侠近代化的开始,亦即今人心目中所认同的侠客形象。有关义侠的发展,可参见陈山《中国武侠史》第四部分《侠的世俗化:宋以后的义侠》,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汪涌豪《中国游侠史》第二章《游侠的发展历史》相关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林保淳《从游侠、少侠、剑侠到义侠——中国古代侠义观念的演变》,收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侠与中国文化》,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版,第91-130页。之先河,影响至为深远。但需特别指出的是:唐宋以降的“侠”已远非历史现实中的侠,若从实质而言,则日渐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标志,我们也很难再将其与现实生活中的“侠”对应起来。
但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在探讨中国侠文化时,往往不辨此中之别,将历史记载的侠与文学创作的侠等而视之,现实生活中的侠与人们观念中的侠混为一谈,以致常常聚讼纷纭而莫衷一是。笔者以为,欲论中国侠文化,必先明确现实之侠与观念之侠的区别。所谓“现实之侠”,是指现实生活中真正存在的侠;而“观念之侠”则是人们受文艺创作的影响所产生的对侠的观念上的认识。其中,“观念之侠”实际上是一种幻想的侠,但因其符合人们的某种心理期待而很容易被接受和喜爱,并以之作为衡量侠与非侠的标准。笔者以为,把握侠的这种现实与观念的双重性,实乃解读中国古代侠文化的关键所在。
三
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所称道的“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布衣之侠”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侠往往并非如此。这是因为:
首先,侠之行事多“不轨于正义”,也就是缺乏基本的依据与是非标准。当然,对侠自身而言,可能觉得自己是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即使如此,谁能保证他永远会站在正义的一边呢?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伦理社会中,要做到绝对的大公无私是近乎不可能的。其次,侠所信奉的“义”纯属个人之私义,即“背公死党”[13]之义,因此注定不可能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那么他所主持的“公道”又从何谈起呢?假使那些自命为侠的人各持一套“义”的标准,只顾行己之“义”,那结果又当如何呢?再者,从实际结果看,自从有了侠以后,社会并未因此而获得稳定,反倒有了许多“冤冤相报”的惨剧。因为侠的一方在“肆意陈欲”之后,遭受损失的另一方绝不肯就此罢休,定然会伺机“讨回公道”。其后的仇杀与争斗自然在所难免。以致如此循环,了无尽期。许多人在击节赞叹侠之快意恩仇时,往往会忽略被侠所枉杀的诸多屈魂冤鬼。
可见,在实际生活中,要做真正主持正义的“侠”是非常困难的。他需要高尚的情操,过人的胆识,雄厚的才力,足够的背景……如此等等,绝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因此,现实生活中所谓的“侠”更多的表现为豪滑无赖的型态。陈宝良先生指出,秦汉流氓群体中总有“轻侠少年”之类[22]。葛承雍先生也称唐代之侠是流氓恶少与豪侠武雄的统一体[23]。韩云波先生则干脆将流氓性格总结为侠的重要特征之一[24]。这样一个所谓的“侠”群体,带给人们的只能是暴力与杀戮,而非正义与建设。如备受后代之侠推崇的孟尝君在被赵人讥以“渺小丈夫”后大怒,竟会“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12],可谓残忍之极。西汉著名大侠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12]。唐代豪侠盛彦师由于先前王世充委任的刺史“处其家不以礼”,及其得势后,不仅将该刺史“因事杀之”,还连带杀了“平生所恶数十家”,使“州中震骇”[16]。总之,“任侠”往往会成为侠之残忍好杀的借口。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江洋大盗、流氓无赖正是打着侠的旗号称霸一方、胡作非为的。
无论是作为“救人厄困”还是“为害一方”的侠,由于其“不轨于正义”,“以武犯禁”的特点,都是历代统治者——无论专制与开明——所绝不允许的。自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统治模式要求将整个社会置于其严密的控制之下,像西汉时那种“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的豪侠之属无疑是被严厉打击的对象。而且,随着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封建法网的日趋严密,侠的生存空间必然会日益减少,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此亦为势之所趋。
四
然而,也正是由于现实中侠的衰落,为世人对侠的重新想象与文化再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现实之侠虽然一再衰落和萎滥,但侠的精神却被屡屡保留和升华。因此,侠并未因其日益衰落而淡出历史舞台,反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此种变化,自然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
首先,侠是社会普遍不公的一种对抗物和补偿物。由于侠“不轨于正义”的反正统倾向,使其极易成为对社会抱有不满情绪者的精神慰藉。正如有论者指出:“游侠的兴盛和延续,是以封建王朝的深刻内在制度的缺陷为基本诱因的。”[25]退一步讲,在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国家纲纪有常,官吏奉公守职,根本不需要所谓“主持正义”的侠客,侠也会丧失存在的基础。然而,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往往却是政治混乱,奸吏横行,百姓深受其苦而奔告无门,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侠士身上。但事与愿违,现实中的侠带给人们的只有失望,于是人们只有把心目中的侠进一步理想化,进一步祈求“真侠士”的出现。之后再失望,再将其理想化,以至如此循环下去。
若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讲,正是现实之侠的缺位激发了人们对理想之侠的向往与推崇。如果举世皆是打抱不平的侠客,那就实在没有好侠与咏侠的必要了。但随着咏侠之风的盛行与现实之侠的衰落,反而使侠的真实状态逐渐模糊,观念中侠的形象日益清晰,并成为人们对侠的主流认识。在此过程中,侠按照人们的心理期待,被一次次的改造和美化。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中侠的队伍也在一天天发展壮大。其结果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即中国历史上侠客众多,且多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但稍加考察就会发现,此类“为国为民”的侠客多为文学之想象,而现实中的侠却总是良莠不齐,真伪难辨。只是,长期形成的对侠的善意期待往往使人们有意无意的忽视这种差别,将观念混同于现实。结果,观念中侠的形象被无限夸大,人们的咏侠也越发热烈。
其次,侠是对诸多不甘平凡之人的一种心理满足。张业敏即认为,“人们对侠客的向往与倾慕”实际上是一种对男性人格的崇拜,是一种对“打斗勇力,流血牺牲的向往”[26]。韩云波先生用更为诗意的说法解释道:“世界上多数人,平平淡淡活。平平淡淡死,虽然平平淡淡才是真,心底里却总是冲动着寻求刺激的欲望或性情。武侠小说,乃至更广泛一些的暴力文学,乃异曲同工的言语快餐,岂不正是满足了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一种冲动?那一种激情?”[24]
对于广大文士而言,“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死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侠客更容易成为他们向往的对象。因此,好侠或咏侠成了中国文人的一大嗜好。陈平原先生说:“中国文人特别向往游侠那样的生活,不守法律,不守规章,不守制度,可以自由自在地独立不羁的生活,”并将其称之为“千古文人侠客梦”[8]。易中天先生又将此“千年一梦”细分为“救星梦”“英雄梦”“国士梦”种种[27]。“梦”者,不能实现,然心向往之也。但结果却是,侠梦得多了,竟有点分不清梦与非梦起来,并出现一种所谓的“大侠情结”。乔力、张亚昕曾对文人的这种“大侠情结”有过精辟的论述:“借武侠的独立特行来寄托文人的价值观念,大侠情结的重心不在于武侠有多少令人叹为观止的真功夫,而在于他们能做到文人想做却又办不到的事。……所以,大侠情结所代表的文化心态也属于文人,武侠已被文人的价值观念所同化,侠非侠,侠是人的性情。”[28]
再者,侠是对儒家正统文化的一种补充。中国自秦汉以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思想界一直弥漫着理性主义的传统。儒家文化以“仁”为最高之人格,“礼”为等级之差别,“中庸”为行事之原则,其本身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颇有益处。但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儒家的道德被不断强化,甚至走向极端。尤其是“忠”“孝”等具体功用更是被极度强化,变成了对君主和家长的绝对服从,从而成为对人性的极大束缚。以致在封建社会中,个人丧失了个性的独立,只能以家族成员的身份而存在。本来,道德规范是具有实践性的社会准则,但如果道德过于神圣,超出了人之常情,便会导致所在人群的过度压抑,或者流于虚伪矫饰,表里不一。而与之相反的是,“赖力仗义”,不避法禁的侠之精神恰恰是对儒家文化负面影响的一种校正。侠的放纵不羁使其表现出另一种独特的魅力,因而很容易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
还当注意的是,侠在发展过程中,其思想内涵被不断扩大和泛化。如从思想渊源讲,先秦之时,侠与儒泾渭分明,汉唐间二者则渐趋混合,至近代更有以儒兼侠的说法。明代陈继儒称:“子侠乃孝,臣侠乃忠,妇侠乃烈,友侠乃信”,完全将侠义思想纳入儒家伦理的范畴。侠与墨、道之间的关系也形同此类。又如从社会身份而言,先秦之侠仅为公族重臣,汉魏时加入许多豪强地主,唐宋以下则更趋世俗化。近代则有“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29]之说。总之,侠由诞生之初的特定集团发展成为适应一切阶层之群体。时至今日,我们区别侠与非侠的标准,不是社会关系,也非行为方式,而是人格特征。或者说只要有“侠”性者,皆可称侠。因此,中国的侠文化无疑已达到一种所谓“隐性文化”的层次,埋藏在每个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需要指出的是,侠的含义不断被扩大和泛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将各种理想附着于侠客之身的过程。因此,我们看到,本来是“肆意陈欲”“以武犯禁”的侠却每每与儒、墨诸家攀上了关系。而且越往后世,越被强化。借用顾颉刚先生的说法,侠文化的发展似乎也经历了一个“层累的构成”之过程。
五
综上所述,我们通常所谓的侠,应该有现实的侠(社会实体)与观念的侠(精神象征)之分。唐代以前,上述两者基本吻合,自唐以后,则发生了较大分化。具体言之,则是作为社会实体的“现实之侠”走向衰落,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作为精神文化象征的“观念之侠”不断升华,并占据了人们的视野。显而易见,如果没有侠的这种双重性特征,我们就无法解释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衰弱,却在中国文化中拥有广泛影响这一看似相悖的事实。总之,国人所崇尚的侠并非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侠,而是与其近乎现反的观念中的侠,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标志。按照台湾学者龚鹏程的说法,我们所崇拜的侠客实际上是由文学的想象、历史的诠释、正义的神话以及英雄的崇拜所共同编织的美丽神话。其实,我们只要对侠文化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虽然历代对侠褒贬不一,但褒之者多赞其文化性格,贬之者多恶其实际行为,二者各有所循,并不矛盾。
最后还需赘言的是,当代蔚为壮观的武侠文学与影视作品以及由此而生的慕侠思潮,很容易使人们将侠视为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但实际上,当侠及侠义精神被无限夸大后,不仅会造成一些无知少年对侠“以武犯禁”的盲目效仿,还往往会将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甚至掩盖。侠在当代只能是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标志而存在,充当人们对世间公平、正义的美好寄托,但真正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只有依靠国家法制的不断完善,而非寄望于崇尚“私义”且自身难保的侠客群体。
[1]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91.
[2]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54.
[3]增渊龙夫.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M]//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
[4]彭卫.古道侠风[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234.
[5]陈晋.悲患与风流——中国传统人格的道德美学世界[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26-27.
[6]蔡尚思.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九大支柱[C]//中华书局.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中华书局,1992:32.
[7]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412.
[8]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209.
[9]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M].台北:学术出版社,1978:12.
[10]陈永正.康有为诗文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497.
[11]章太炎.訄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30.
[1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8]荀悦.汉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9]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0]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1]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2]陈宝良.中国流氓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8.
[23]葛承雍.唐京的恶少流氓与豪雄武侠[C]//史念海.唐史论丛:第7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98-214.
[24]韩云波.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13-135.
[25]周丹.中国古代游侠现象的法学探微[J].湖北社会科学,2003(2)34-35.
[26]张业敏.“侠”议[J].学术论坛,1996(6):77-82.
[27]易中天.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245-269.
[28]乔力,张亚昕.“大侠情结”阐释[J].辽宁大学学报,1992(5):8-13.
[29]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校 杨明贵】
The Dualism of the Reality and Ideas:Chinese Chivalry Culture Interpretation
BAI Xian

I209
A
1674-0092(2015)05-0040-05
2015-05-14
白贤,男,陕西宝鸡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