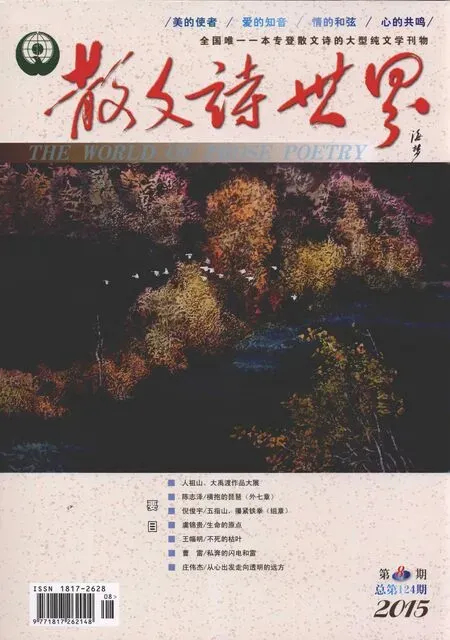乐山大佛(三章)
内蒙古 四 木
乐山大佛(三章)
内蒙古 四 木
杜甫草堂
这偌大的园子,长得最高的要算香楠树了——
它们遮天蔽日,抬眼可见;
它们散发出的淡淡清香味,如同细密耐腐的材质一样顽固。
若非生长缓慢,当年那个秋深的八月,怒号的狂风,怎会卷走你屋顶上好几层茅草?
即便,茅草乱飞,也定会环绕回廊,就近扬尘于廨堂之间。
怎会“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这偌大的园子,长得最矮的要算园中菜了——
草堂前的大片菜圃,辣椒经雨后由绿变红。
恰逢有客过茅宇,即采摘时令蔬菜——有辣椒,稍早自然少不了韭菜——
一句“夜雨剪春韭”或早脱口!
饭,是新煮的掺有黄米的香喷喷的二米饭或拌面。无关紧要。
韭菜的绿,经你点染,在唐诗中扎根发芽。
即使,宋苏东坡眼中的荠菜——“春在溪头荠菜花”,也不妨韭菜的绿,是最正宗的绿!
我宁愿相信洪烛先生所言:韭菜如同春天案头的供物;而你,更像一个素食主义者,有着草食动物的温柔与怜悯——
一身素衣着身。过早看破红尘。眼睛凝视远方。
你沧桑的眼神,透过亭、台、池、榭,怎能洞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偌大的园子,见得最美的要算如画的风景了——
漫过香楠林,梅苑傲雪迎春,兰园清香四溢,翠竹苍松茂密如云;东穿花径,西凭水槛,几间茅屋,暖色浪漫。
怎见,“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这偌大的园子,见得最多的要算千万间广厦了——
如今的浣花溪畔,红墙夹道,修竹掩映,唐风遗韵,明清联袂;亦不乏盛世下合围的高楼矮屋鳞次栉比。
1400多年,“吾庐”不破,突兀,若你激愤郁结的唐诗!
乐山大佛
像几个做事不计后果的愣头青——
凌云山下,岷江横切,大渡河携青衣江,迎头撞面。
它们的清澈与浑浊搅在一起,泾渭分明又同流合污;它们的暴躁与咆哮掀起大浪,使过往的船只触壁粉碎。
江岸上,又有几盏渔火,彻夜亮着,或者熄灭。它们的野蛮入侵,碾碎了多少人间烟火啊!
凌云寺的海通法师看得一清二楚。
这时的乐山大佛,还裹在临江峭壁的红砂岩中沉睡。已逝的漫长岁月:盛世与乱世难解难分;富足与贫瘠一目了然。
我来了。可来晚了。整整晚了1300多年!
三江六岸(或一江两岸)暮色低低,树影怜怜。像在当下,又像在遥远的过去。
我一个采药之人,逢山登高涉远;我一只倦怠的飞鸟,想飞,又想栖息。
此时的凌云山安歇江之对岸。此时的乐山市高楼隐隐攀月。
此时的神秘的大佛挟裹着瑟瑟寒风。
冥冥中,仿佛又传来海通法师的匆履碎步。与三江角力,在巨幅的摩崖造像上,叮叮当当的凿击声不绝于耳,拍打着客栈的低床矮案。夜纠结难眠,梦游般踏水临崖。仿佛早与佛结缘。谁,恍惚在脱胎换骨?
第一次用耳聆听人世。
第一次用眼通观人世。
第一次用心感悟人世。
大佛坐高71米。我从后山登顶。临近,让一米八的个头与佛首平齐,却不及大佛的一个耳垂。
大佛如此之巨,震撼起祥云。
我小心翼翼,沿一侧千年古栈道下到佛脚。尔后,从另一侧攀爬至上。每一步都是艰辛与虔诚。心灵与大佛零距离互动——
佛最初听到了什么?可曾听见,三江水轰鸣,巨浪拍岸,众生四野唱衰;
我此刻听到了什么?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佛九十年艰难转世;
佛最初看到了什么?可曾看见,两岸的渔火,忽明忽暗,灯芯一息奄奄;
我此刻看到了什么?辽远的八方,天高云淡,映衬万家灯火;
佛最初感悟了什么?断不敢妄加猜测了。
走着走着,忽想起,岷江东流,众生恋家,今天的所历不是目的地,它只是沿途的一道风景而已……
黄河壶口瀑布
吟诗泼墨——
自下而上的怒吼;自上而下的奔放。
以五千年为一个时段,这壶神酒,谁人敢喝?
等不及的,躲避不及的,跌落的梦魇。
要么上了天堂,要么下了地狱。
冥冥中,伫立飘忽的,呼号跑位的,化作壶口肆虐之大风,在更长岁月助长了波澜壮阔或冰封雪冻。
此时,我攥紧陕西或山西的地界(却不敢确定究竟是哪)。此时或许注意力没在这上。
知道你不在。知道你当年在。却不知道,你当初足踏何方畅饮高歌?想想初到这神的酒坊,我断不敢造次与狂言——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是神的来龙。
也是神的去脉。
遥想你,当年,一定站在一个不为人知的高度,一个既不是陕西也不是山西的绝对高度,凌空俯瞰或眺望,方破译壶口之滔滔。而我,听得入迷,如听天书。
呵,终究无缘与你相遇!我们之间,隔着五千行的诗句(或诗篇)须仰视得见。
仅在要转身的刹那,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雨。听说有个叫狄焕然的,死缠烂打的牡丹江人,于×年×月×日曾纵身一跃,为壶口加了点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