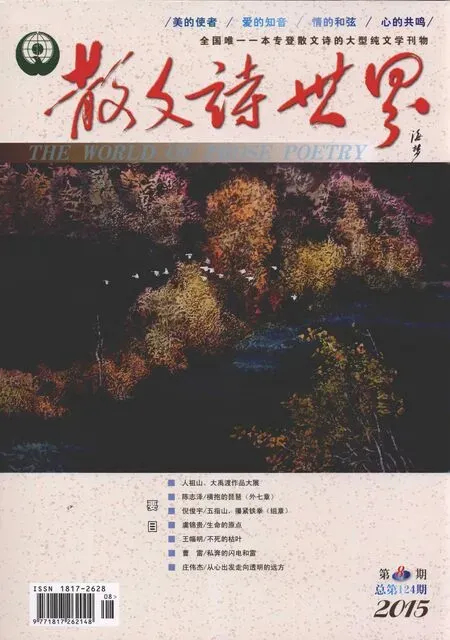从心出发走向透明的远方
——文榕散文诗集《比春天更远的地方》散议
澳大利亚 庄伟杰
散文诗研究
从心出发走向透明的远方
——文榕散文诗集《比春天更远的地方》散议
澳大利亚 庄伟杰
一
春花秋月,晨昏更替,总在召唤生命不息地前行;世道人心,上善若水,足以照见灵魂飞翔的弧线。
写作本身如同一场回归生命的心灵运动。与其说文学是人学,不如说文学是心学,诗歌写作尤甚。因为头脑中的智慧容易被人发觉,而心灵里的精彩却容易被忽略。对美的发现,并非靠肉体的眼睛,只能靠心灵的眼睛。有感于心,动之以情,从心出发,潜心写作,方能以心发现心,让心走近心。以此观之,诗歌的写作过程本身既是一种“冒险”的心灵之旅,也是一种修心养性、安顿灵魂的语言艺术。因此,太过精明者往往写不出真性情真精神真文章,唯有保持天真烂漫且用心写作者,诗才有可能从心底蜂拥而出——
当我们顺着来路回归时,季节已交出所有,一切留在昨日,今天在匮乏中生长,翠枝的嫩芽指向迢遥的海岸,那儿有一张永恒的笑脸?
从心出发!
再一次抖落内心的尘埃,向远方望了又望,诗歌在每个角落茁长,当我们反复衡量自身的缺陷。
从左手到右手之间闪过,不致贫乏?像在春天的室内坐成一丛盛开的鲜花。回到昨天并非空想,奔向脚印的源头,洗净每一阙过往。
从心出发!
时令的眼神把我们唤醒,仿佛返回梦里挽住夭折的誓言,一步一回首的颤动,是那束恒久的牵挂。
誓言不怕失去,回归一抹笑容。
当海在海上,心在心内,我们扭转身,爱仍在爱里。
读着这章题为《从心出发》的散文诗篇,眼前依稀浮现出一个不断抖落内心的尘埃,向远方望了又望的女子,面带诗意的笑容,一步一回首地走在通往家园的路上。透过沉静有力的字里行间,一个着力于内心合漩的景观与创作主体精神图景的履痕跃然纸上。“当海在海上,心在心内,我们扭转身,爱仍在爱里”。读这样的妙语佳句,可以窥见,女诗人用心营造的文字里,隐含的是坚忍与刚毅所孕育的深沉而丰饶的灵魂,交织着温婉而独立,深情而智性的意蕴。这时,那个外表文静清爽、内心清澈充盈的女子,与如今生活于香江之畔的名叫文榕的女诗人交相迭现一起。于是,当笔者打开她即将推出的散文诗集《比春天更远的地方》时,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浸透于心灵的诗性魅力,而非是难以自拔的哀怨宣泄和满纸伤感的呻吟。对于某些现代女性来说,文榕诗文的“表情”看上去似乎有点“古典”,我则觉得,若以女性写作的美学气象审视,她的这部散文诗集,其审美趣味是可观可赏的,其品相是个人内在气质的灵动显现,其内蕴则弥漫着浓郁与难喻的人生况味。此刻,女诗人似乎是具象的,而文榕的情绪内涵也是特定的。
当我们面对一个人、一篇诗文、一个人的写作空间时,无论是感动与惊喜,抑或是沉思与质疑,都是一份感知和收获。在一个喧嚣浮躁的浅阅读时代,能静下心来进入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或生命风景,语词透析的意义和诗意形式早已跟作者神合同构。而其间形成的“气场”,常常令人发现到作者在漫不经心中用一以贯之的沉静气息,向我们徐徐吹拂而来。
香港女诗人文榕,自从踏上文学之路,似乎就是以这种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廿年前,一个原名叫“顾锡群”的江南才女,早已披上一身清丽,舞动着春天般的步伐,在探索中亦步亦趋地走在通往“透明的远方”的路上,并且总是用一双聪慧的眼睛洞察天地自然,用一颗淡定的诗心寻求走出一条用文字精神铺展的通道——“追寻穿越远方,目光引领燎原,旷野星星点灯”(《当风掠过河流》),去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
印象中,文榕的生活舒适安逸,写作,出书,获奖;继续写作,获奖,出书;可谓一路顺风顺水。从她恬静柔美的语词花丛里,从她早期撩拨的那些幽远缠绵的篇章里,我们似是听到诗文中的天籁之音,如同爱与美的月光交相辉映于那些有着共同经历和感受的读者的心灵。
然而,正如一个少女在一夜间变成了女人,徜徉于诗与散文诗之间的文榕,在蓦然回首间,学会从自己的“绣房”中走出来,面带微笑迎风走向大地和《走在旷野》——
大风的旷野,梦香飞扬,诗句俯向金黄,笔墨炙得滚烫。
泛金岁月流过,穿透了将来的寓言,一个不朽的梦,行进在永生的途中。
带着轻浅微笑,走在大风的旷野,看花朵哺育大地,荆棘纷披往事,阳光修饰了所有山脉,风拉近云水的距离,旷野深处现出虹影!
走在大风的旷野,还原了祖先的记忆,思源的明灯燃起,雪花的笑容飘落,染亮了人间华美的情节……
随着岁月的递增,生活经验的积累和视野的日渐开阔,她把思想放在文字背后,以诗画的语言让作品闪耀智慧的灵光。她往日笑意盈盈的眼神里,开始有了沉凝与神思;而平素温柔天真的细语中,开始有了问号和重量。文榕依然冰雪聪明,但如今的她,已经不仅停留于沉湎“轻飞的月光”,不止迷醉于“都市舞蹈”,好像是一棵豁然撑开枝丫的榕树,枝干结实,枝叶茂盛,沉稳且空灵,坚实又从容,似有一番遮雨蔽日的气派。加之禀性天赋与感觉异常灵敏,她的散文诗从心出发,逐渐“走向透明的远方”,去深度感知万事万物,沉静地呈现出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最真实的当下。在这部由“月亮泉”、“风起时”、“夏日梦舞”、“从心出发”、“写给远方”、“从海到海”、“缱绻香江情”等七个分辑组成的集子里,女诗人以静美流转的笔触、以色彩斑斓的笔调,写山写海、写花草写风月、写春秋写冬夏、写果园写物事、写乡野写城市,既有梦想与祈求、疼痛与忧思,又有爱与期盼、美与希冀。就像“叶脉和露水的抒情”,或如“贴近绿茵草地上的歌吟”,处处回荡着深挚的呼唤——那是对于颤动着生机的自然生态的呼唤,是对人类美好诗性的精神生态回归与提升的呼唤。
二
一个在时光中自在行走的女子,向往的是“比春天更远的地方”,她在旅行中放逐心灵,将双足所踏之地、双目所及之处、心灵所悟之境,用旖旎而洒脱、清越而悠远,甚至略带忧伤与随性的文字,如“天河石语”般舒展的思维图谱,引领自己也引领读者,去抵达生命最初也是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去处——那是宛若“灯影照临,树木高挺,临水而居城市的森林”的别样美境,是带有女性唯美与寻求诗意栖居的自然理想,是一种“走向透明的远方”的愿景生成的幸福感。
颇有意味的是,相对于西方女性生态主义的激越,或许文榕的写作实践和审美取向更富于东方神韵与古典主义情怀,尽管她生活在中西交融、华洋交错的大都市香港。无疑这与她身上中国式温婉、内心深处对造物主的虔诚垂顺有关。她遵从古老而神秘的物之法则,注重驱动原始生命力的身体和精神仪式。于是,当“清晨冥想,似第一次为你写诗,无须任何理由”;当“时光已交出自己,季节收获所有”。因而,当女诗人“再次提笔,绿为一枚叶子,祈祷花香的播种,遍布悠远时空”。当不期而遇的文字自内心外化,她“诧异这不打腹稿的语句来自何处,仿佛清晨浮游的一抹微笑,神祗一个眼神,也似我心中的触及与挂虑,迢遥地伫守岁月的风口”(《栽种》)。
习惯于在时光中捕捉物事风情的文榕,时而在《辨认》中,“掀起心上烟云,洒下陌生的甜蜜”,只为在纸上静静地留下一道印痕;时而在《聆听》中,把“多愁交付远山,善感随顺轻云,走走看看,溶化情绪阴影”;时而在静观中,倾心与《景色的邂逅》,“为了等待彩虹在你我之间升起”。而为了“赎回崭新的自己,放逐那生生世世的相见的印痕”,她还是一个可爱的《捕梦人》。毋庸置疑,她所钟情和神往的是自然的洗礼与心灵的盛宴,是天人合一的生命景象。当她全身心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与天籁中,无论在山那边、在落霞水边、在向阳的山坡,还是从海到海、从青山到碧水、从田野到都市,抑或是在日落月升时分欣赏《月亮泉》,在夏日梦舞之际倾听《蝶语》,在薄雾笼罩当中默读《暖冬的紫荆花》……这些对于文榕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切身体验,更是一种精神的畅游和生命的祈祷仪式。由此诗人在“回归一抹激情”中找回一种“飘香的心韵与希望”,找到了源自本心天性的善与敏感、美与灵性。当女诗人感受到山的起伏与海的壮阔,当远山被雪影染亮,当真挚的湖水发出动人的微笑,当苍松翠柏映入眼帘,当顺着河流回溯看风掠过,诗人与大千有灵万物默契的亲近感一旦被真正唤醒,一切外在的束缚与桎梏随风而去,身心中的纯情性灵便在回旋中复活了。那些弥漫在海天与空气中的神迹,在落霞与秋水之间的冥想,在山峰与飞鸟之间的遐思,以及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徐徐降临了。而在造化的神奇与馈赠面前,学会拾起内心的谦卑与虔诚,还有什么灵感和妙悟不被点燃呢?于是,读文榕这些诗性散步留下的跫音,若看到空谷幽兰、看到橙红鲜花,在文字间、在天地间散发清香,含笑绽放。那种因自然的触发生成的体悟与飞翔,是女诗人被释放出来的丰沛想象与感受力,是心中升腾的彩虹和原始创造力迸发的神秘智光。在这部散文诗集的开篇《月亮泉》中,文榕如此写道:
月亮又来床沿亲吻我了,并将我唤醒,这样宁静的夜晚,我感到生存的美好。
将手伸出窗外,感受一下风的抚摸。
这样宁静的夜晚,安详,和谐,不再向生活索求什么,存在的本身已经丰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泓甘泉吧,这样的夜里,我被它洗净。
白日的喧嚣远了,所有的绚烂都归于平淡。你远了,我安于心上的淡漠。我明白,由生至死,所有的绚烂都必归于平淡。
我满足,为已拥有的一切。
将来的岁月将会怎样?这一刻,不再惶恐。我们都是沧海上的一叶浮萍,偶然浮现于这世界,世界曾多么温柔地注视过我们。眼下,一卷诗,一壶酒,一块面包,不已是很逍遥了么?
诸多的美、诸多的情思、诸多的彻悟,哪怕曾经喧嚣过或惶恐过,只要拥有这样宁静而安详的月夜,能用清泉来洗涤心灵,就无须彷徨了。诗酒趁华年,如此足以自在逍遥了。何等潇洒,何等达观。因为“这是生命赐予我的慰藉——最诗意最浪漫的时分。”
懂得,所以满怀感恩,心存慈悲。然而,世间万物,变幻莫测,岁经衰盛,放随荏苒;明月升起,群星失色,四季更迭,落叶萧萧。用心领悟,心如明镜。请听文榕笔下《叶子的独白》:“一个雪花纷飞的黄昏,我上路了。呀,天地怎么这么白呵,将要跌落的地面,也这样美好了,这样清寂。慢慢飘下来,飘下来,以感念之姿,铭天地之美,雪把我染白……”读到这里,听叶子的诉说,看叶子从春天朦胧苏醒来到世上,到夏日烤成静默的燃烧,再到秋为之带来成熟风韵,直到冬日一无所惧,即使被雪染成白,依然心存感念。如是,想想早生白发,人生如梦;想想四季轮回,终极命运。也许心就坦然自在了。如果说,前者是女诗人期冀用月亮的深情、诗意、浪漫来对抗现实社会中的浮躁、低俗与粗陋;那么后者乃是用叶子(植物)生动的色泽和姿态、原始生命力及天然的对美的创造力,来对抗机械、刻板和急功近利所制造的行为,唤醒女性生命中的自然天性和美的回归。
看得出,作为一个美的追寻者和探索者,文榕一直在不停地用美来打磨自己。她之于散文诗,犹如一块璞玉伴随着时光的流程在她手上搓磨而日渐光鲜,以至于成型时,与她的生命体温和灵气融化为一体,佩戴身上,晶莹剔透;一经摇曳,则泛化出散文诗万千旖旎的底色。可以说,她的散文诗,有几分灵悟几分雅致,还有几分唯美几分妖娆。欣赏她弹响的文心诗弦,时而让人忆起梅雨时节的江南,时而叫人想到海风吹拂的东方之珠(香港),甚至想起花间词和小令。或清气横溢,情思缱绻;或幽依婉约,如蝶曼舞;或芳菲尽歇,傲枝犹香;或色泽缤纷,满纸生辉。那篇名为《风中的白手帕》,分明是一幅用文字挥洒的彩色图画,那块白手帕则如一个特写镜头。整个画面的背影除了如无色歌谣的风,有溪流、鸟语与琴声的交响,有云朵、星星与牛羊的织就,有流水与落叶之和声,有鹅蛋石之色彩,还有阳光的浅笑……可谓远近上下亲近,吐纳铺陈有序。以此凸显了白手帕的纯净、美感和温婉。当天地间“挥动一片风,扬起幸福的白手帕,反刍青春,依恋和情感,跟随一抹翠绿走向远山。”这时,以轻盈的呼吸,以一种生动的姿态,“凝望云的方向,我可以我的白手帕扎住长头发,束起纷乱的思绪,驶往幸福的航道上……”作者层层渲染,细心勾勒,巧用通感,鲜活的文字质感和扑面而来的旷远与辽阔,令人如临其境。显然的,“风中的白手帕”是一种能指,一种隐喻。作者滑翔于丰饶情思和独到感觉之中,赋予其高洁的精神喻象。或者说,这白手帕,作为白云(朵)的喻象,别有一番风情,且独自承担风给予的力,有一种意境上的孤清之美感。诗人在篇末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对孤清的喜爱和对高洁的向往。说到底,“风中的白手帕”彰显的是一种人生姿态或生命追求。这份来自于大自然的灵感、启示和赐予,多么富有情趣,多么值得珍惜!
三
文榕散文诗固然更多地倾向叙写被大自然点燃的天性与敏感,去找寻属于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生命印痕。同时,又无法摆脱自己身处的城市(环境)。因而,关注此在,关注当下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城市生活而书写的篇章,同样值得令人为之驻足。
然而,如何看取城市生活,并用散文诗的形式来加以呈现,这是颇费心思的问题。文榕散文诗写作一向讲究审美品位,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写作欲而漶漫的简单铺排,而是赋予文字以灵魂的品质,是注入了散文诗所必需的重要审美元素。浏览她笔下城市生活的每一个景观、每一片风情,本身就像一首首诗篇。既非是浪漫的抒怀,亦非是现实的批判,它似乎属于“别一种去处”,即把城市置之于一个更大的自然视界和生命图景中,用目光平静地作美学的打量,用心灵真诚地作诗性的传达。基于个人独到的自然观,她将城市看作与非人工化的第一自然相对应的“第二自然”,是一种近乎存在意义上的“大自然观”。这种诗歌观念和写作姿态,使她获得了观照城市的新视点。“不再摹拟过去,不再设划未来,熟悉的灯光自有另一番美境”(《临水而居城市的森林》)。于是目光所及,有时近看,一丛花木、一束花蕾、一座小桥、一处亭榭;有时远观,黄金的潮水、魔术的月亮、遥远的星空、悠远的记忆。有时小处落墨,一棵春夜的凤凰木,一角滨海小景;有时大处着眼,临水而居城市的森林,一座中央公园。有时是灿然而温馨的画面:“当浅黄色的花朵装点着回忆,日影廊返照久远的灿美,季节都是深挚的款待”;有时是沉重而压抑的镜头,如在一个普通的黄昏,走过熟悉的隧道看到一位弹唱者,让她心灵为之一颤,感觉“城市拨不开低迷的云。交错的倦容,织成背景的灰,携着疲惫、困惑,我低沉地走……”这是对都市审美的一种有价值的拓宽与引申。而她笔下凸现的大陆地方城市风光及异域都市风情,同样不失灵动和诗意,诗人摄取的是城市富有意味和特色的景观。可以说,文榕笔下城市题材的散文诗篇,不只是对城市生态和存在状态的一种诗性书写,更是经由诗人心灵过滤后的一种城市精神的灵动展示。在“大自然观”的映照下,现代都市在一定程度上被自然化了,形成具有相对开阔的审美意义的“别致世界”,焕发出不同于以往的精神质地和理想诉求,表现出诗人不愿随波逐流的写作品格和审美特色。
作为当代华语诗坛一位颇为活跃的女性诗人,文榕创办主编的香港《橄榄叶》诗报,已渐成气候,影响日广;作为香港文坛一位专注于散文诗创作且颇具代表性的女作家,文榕这部命名为《比春天更远的地方》的散文诗集,堪称是十年磨一剑的精心之作,其中不少作品曾获过奖,并入选多部权威性的散文诗选集、散文诗年度选,或被海内外诸多读者在博客上收藏和称赞。而这恰恰与文榕始终追求作品的生命精神和诗性有关。加之她的散文诗拒绝自娱的情调,让读者可以触摸到一种别样的女性文字韵味及美学质感。
从总体上观察,文榕散文诗是其富饶而自足的心灵之泉的涌现,多数篇章乃是“心学”的记录与呈现。难得的是,相比于早期的书写,其散文诗常常超越事物的表象,不再局囿于女性的清新柔美之气,却在深情的描述中,常有发人深思的洞见和剔骨般层层深入的追问。并在对美的发现中赋予语言、画面以智性因子及思辨色彩,从而在喧嚣世界里守护自己内心的一处独特空间。当然,文榕依然有梦,有更多彩的梦想和美丽的期待。在《甜梦的流转》中,她怀抱信心:“毋庸置疑逝水的倥偬,那屐痕足以使我朝向光明的旅途,不再俯仰于日夜的折痕,莅临的快乐是翻卷自由的浪波”;她眺望来路:“我须从时间的另一端出发,回归一抹激情”;她自由畅想:“天空的幽蓝让我想起前景、命运,想起时空和一些恒常的事物”(《归来的时分》);她坦然问询:“无际浮云诉说着万物的逝去,又何必计较此刻的得失?烟波浩渺的湖面啊,那么平静,是哪一位神祗的安抚?”她了然顿悟:“花谢了,倒了水。哦,你送我的水晶杯,原装着空空的禅”(《穿越你的眼眸》)。她满怀期待:“明朝是收获的季节,像红百合一样绚烂,麦穗一样金黄”(《等待》);她胜券在握:“我握着一把通往天空之门的钥匙,去远方,开始从未开始过的生活”(《比春天更远的地方》)。
拉扯至此似乎该收笔了,却有意犹未尽之感。我想补充的是,作为同道中人,笔者深知题目是诗文的眼睛。会写文章者众,但并非人人都具备取好题目的命名能力。就好比谁都能画龙,而关键处却在于如何点睛。因为题目在一首诗、一篇文章中往往起到举足轻重的特殊效应,小视不得。我发觉,文榕特别擅长于给自己的诗文取题目。拥有这种命名能力,使她散文诗的篇名充满灵光,且颇有奇趣。比如:《月亮泉》《回首:一串青春的珠贝》《天河石语》《景色的邂逅》《捕梦人》《夏日梦舞》《纯洁的沉寂》《生也柔弱:致海洋》《路的回想》《宁馨犹如火花》《心园的风声》《草叶唱着抒情的歌》《雪落尘宇寂无声》《举杯,遥金秋的明眸》《魔术的月亮》等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题目之于诗文亦然。文榕那双明亮的眼睛,总是温婉地直视着读者的灵魂。
古人有云:“真境道出神境”。瑞士思想家阿米尔有言:“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境界可以是大江东去,也可以是小桥流水;可以是黄钟大吕,也可以是浅吟低唱;可以是骏马秋风,也可以是杏花春雨。浓烈的、素朴的、繁复的、简约的、律动的、沉静的,皆是一种境界。诚然,追寻境界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畅通无阻。因此,有境界的诗人作家,不仅杂质很少,而且心地澄明。并在天启神示中让笔情墨韵透露出浑然交融的气息,从而形成强大的精神气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人生都在求道,都得追求境界,而境界取决于理想。最美的东西永远在理想之中。如果不言理想,人类或许就没有美和希望可言了。写作犹如登高,每上一层,视野愈见开阔,这是一种理想境界,需要写作者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
有感于斯,遂发感想:风骚者,诗文也;风华者,才情也;风神者,性灵也;风流者,文采也;风韵者,优雅也;风骨者,笔力也;风采者,个性也。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王国维语)。如是,具备以上诸多要素者,其诗文必自成风貌,卓然独标风格。
笔者知晓,直面人生,文榕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对于诗文,又充满着审美理想。于是,以上云云,哪怕有点苛刻,但为了驱动华语文学走向更加理想境界的新天地,我想借此与文榕、与所有有志于文学事业包括散文诗创作在内的文朋诗友们共勉之。因为,比春天更远的地方——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灵魂里……
(作者系旅澳诗人作家、新锐批评家、文学博士后,现任国立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