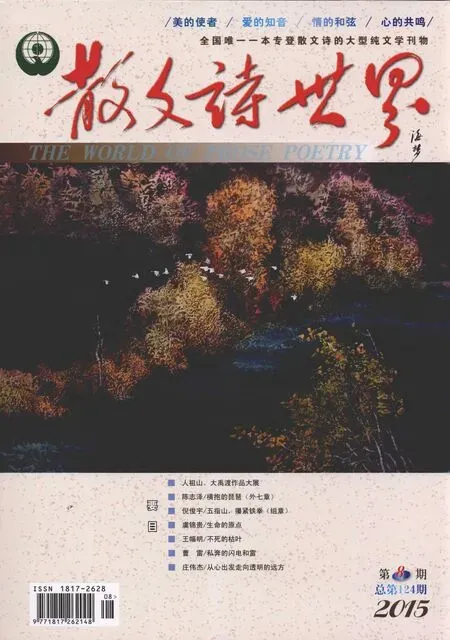从大禹渡到人祖山(十四章)
许泽夫
从大禹渡到人祖山(十四章)
许泽夫
大禹渡与大禹合影
从你站着的地方,放眼望去,黄河尽收眼底,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水,从你脚下低眉顺眼地流过。
那些浑黄的水啊,曾经受过怎样的冤屈和苦难!它们汹涌澎湃浊浪排空桀骜不驯,四周都在筑堤,四周都在堵截,四周的路都被堵死了。
实在无路可走了……于是它们咆哮着、奔腾着,夺路而逃,冲出一条生路,江河泛滥,房屋倒塌,妇孺悲号着被一个个巨大的漩涡吞噬。
你三过家门而不入,在黄河的转弯处驻足了。
你就站在这里,手搭凉棚。逃难的百姓呼天抢地被洪水追向山顶。几个赤膊的汉子刚投入一块巨石,人和石都被巨浪的舌头卷走。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啊,你至善至柔,与人无争又包容,为什么变得恶魔似的面目狰狞?
仿佛受到神祗,你茅塞顿开,改堵为疏,凿开三山五岳,引水归道。
黄河之水顺着大禹指定的渠道,浩浩荡荡,奔流到海不复回。
水患消失,黎民百姓安居乐业。
在大禹渡,我虔诚地与大禹合个影,我似乎听见一个声音从他巨人的胸腔发出:
治水如治民,治民如治水……
定河神母
我不相信那个千篇一律的传说,天帝的女儿相中凡尘的后生,然后便是有情人偷吃禁果,然后便是生死离别。
我不相信你出生在虚无缥缈的天庭,难道只有仙女才出落得这般楚楚动人,黄河的水就养不出貌若天仙的女人?
我不相信你怀中的孩子已经死亡,为什么要杜撰这些催人泪下的悲剧?凝视那个和我孙子一般年龄的孩子无力地躺在母亲的怀里,我泪满襟衫。
是的,我不相信!
我相信这个神情庄重而又充满慈爱的美丽女性,就是喝黄河水长大的,她是贤淑勤劳的妻子,是任劳任怨的媳妇,是母亲膝下孝顺的女儿,是儿女眼中伟大的母亲。她能担水劈柴,能下河张网捕鱼,汛期来了也敢奔上堤埂肩挑手提与洪水一决高低。
黄河两岸的女人,是真正的定河神母。
在黄河的河床上
气垫船像一阵风,将我驮到黄河的河床。
踏在松软的黄土上,我好像回到了母亲的产床。
脱下鞋袜,光着脚丫来回嬉戏走动,略带腥味的风在脸上摩挲,一股暖流从脚掌心顺着血管涌动到每一个神经末梢,心骤然加快了跳动。
在黄河的河床上,我想脱下衣裳卸下所有的伪装,只想做一个赤裸而无知的婴儿,打滚、撒泼、撒娇,无忧无虑,无拘无束。
在黄河的河床上,我想把自己种下去,成为一粒沙子,一把细小的绿色植物……只要能偎在黄河母亲的怀里。
气垫船像一阵风,将我带离了河床。
站在大禹渡,望着宠辱不惊的黄河水,我想引吭高歌……
神 柏
即使是一块砖、一片瓦,经历了4600年,也是一件珍贵的文物。
何况是一棵树。
何况是一棵有生命的树。
何况是一棵树大禹亲手栽下的树。
因为是大禹手植,便有了大禹的灵气,预测吉凶预测黄河泛滥或温顺预测太阳能否照常升起。
因为是大禹手植,便有了大禹的基因,仪表堂堂俨然帝王之相。其实更像神话中的仙人,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保佑天下万物和谐共存。
我也来焚炷香,我不求钱财不求前程仕途,唯祈求这棵树长命万年青。
浦津渡大铁牛
远远地,从浦津渡的方向,传来一阵阵牛哞,苍凉而悠长。
黝黑如墨的大铁牛,蹲在黄河故道上,保持着随时起立的姿势。
你不知道黄河已经改道了吗?
你不知道马放南山铸剑为犁了吗?
你不知道那座天堑变通途的千年古桥已在时光的流水中不见踪影了吗?
铁牛兄弟,你还是那个犟脾气,固守在古老的渡口,守候着一个幽远的梦想,就像我乡下的耕牛,土地变更为商业区,村庄在逐渐地萎缩,耕田的人扛着蛇皮袋挤上了南来北往的客车,但它们依然留守在乡村,陪伴着同样留守的老人、孩子和炊烟。
我来到它们中间,每一头都似曾相识,我拍拍这个大脑袋,摸摸那个鼻子,我相信,只要我吆喝一声:得儿——驾,它们就会一跃而起,紧随我走向原野,或耕,或耙……
普救寺断章之一:莺莺手印砖
谁个少女不善怀春,谁个书生不善多情。
定然是前世所定,东廊之下,怀春的少女与多情的书生不期而遇。
书生张生,把这桩天赐的良缘当作比题皇榜中状元还珍贵的赶考。
相府的小姐崔莺莺,养在深闺无人识,她已在梦中多次描绘未来相公的才貌,恰与眼前这个风流倜傥的多情公子吻合。像是被人发现了心底的秘密,她心慌意乱,三寸金莲哪躲过穷追不舍,你追我赶几个来回,不慎跌跤,左手挡地,沾满香脂的素手在地板上印了清晰的痕迹。
一个手印,一段风流佳话,流传千古而不衰。
傻呼呼的书呆子啊,你可悟出崔莺莺面向佛祖面向大地摁下的手印,这是爱情的佐证,更是爱的誓言。
普救寺断章之二:张生逾墙处
东厢南段的一段墙,像一座山峰横亘,将一对有情人天隔一方。
那株杏树还在,枝更繁叶更茂了,乱颤的枝头,从这头伸向那头,挑动着少男少女心中的欲望。“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风流才子,满腹经史子集,病体方愈,面对高墙,心有余而力不足。
墙的那端是西厢,一阵悠扬的琴声如高山流水潺潺波动,书生的心,驿动不已。
我似乎看见,又一次从墙头摔下来之后,他甩动双臂做了几个准备动作。
后退几步,拼尽全身力气,几步助跑,手脚并用,奋力攀上了墙头,重重地跌在翠竹与太湖石之间,落入梨花深院。他拍拍身上的灰尘,顾不得斯文和疼痛,约会心中的女神。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让一介文弱书生,瞬间成为飞墙走壁的强人。
普救寺断章之三:莺莺小路
月黑风高,暗香浮动。
一盏摇曳的灯笼从梨花院飘出,顺着高大的墙根急急行走。
提灯的红娘,引领意乱情迷的莺莺,一会轻声提醒金枝玉叶的小姐注意脚下,一会略作停顿,等候微微娇喘的主人。
两双绣花鞋,在碎石小径上鼓点般踩落。
不要问世间情为何物,也不须解释,因为所有的语言在爱面前都是苍白的。且不说门不当户不对,且不说千重山万重水,纵然是生与死,也要相许。
薄暮冥冥,我不想走了,伫立在这条莺莺必经之路,心里默默地许愿……
鹳鹤楼
登楼人多了,鹳鹤受惊了,绕楼三遍,各奔东西。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鹳鹤楼,站在黄河岸边,耸在白云深处,迎候着一拨接一拨往高处走的人。
登上楼顶,极目远望,望见大河往东流,望见中条山脉云雾起,望见芸芸众生熙熙攘攘或为利来或为利往。
那些锦绣目标似乎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涯,达到它,不可能一步跨越,须一个脚印接着一个脚印丈量。
攀得再高,总要回归大地原点。
高处不胜寒啊,那些在楼顶眺望欲穷千里目的人,在楼下平地上的人眼里,只有很小的一个点,离得越远,看得越小。
回到大地的怀里吧,在阳光下担柴、种地、喂马……无论是谁,都是幸福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幸福的事。
在黄河漂流
穿上红色的救生衣,坐上充足气的气垫船,我们在黄河漂流。
其实我们选择的是黄河平静的一段,河的两岸,有两尊雕像,一尊是大禹,一尊是观音。大禹导向着水流的方向,观音保佑我们平安。
我们划桨,我们唱着与黄河不沾边的抒情歌,我们竞相用专业的相机和不专业的手机互相拍照。
黄河母亲把她的温柔一面露给我们,只要不触犯她的尊严,她就是这么母性十足。
惊涛拍岸却有惊无险,她举着一朵朵浪花在船的四周恭候我们,有时也有一道漩涡,那是她露出的开心的酒窝。
在黄河漂流,我们都是一尾尾快乐的红鲤鱼。
壶口瀑布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吉县壶口,一股脑地倒入壶中。壶口,就是这壶的瓶口。
五千公里长的壶啊,装下了黄河的全部。
浑黄的黄河水,正是母乳的颜色,也有乳汁的营养。
倒一点给秦岭淮河,浇灌杂粮小麦棉花和工业。
倒一点给暖湿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种出平原和旅游。
还剩一点,全部倒进了渤海,一滴不留。
阅读黄河,就体验到了一位母亲的爱,博大而无私。
亿万生灵期望她的滋润,她便源源不断地将爱装入硕大无朋的壶中,像观音菩萨手中的净水瓶, 洒给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华夏子民。
与朱朝晖握手
相握的那一瞬,我感受到他双手的力量。那是一种与黄河亲近与黄河较量的人才有的坚强。
上个世纪最后一年,这双24岁的手,驾驶一辆普通的摩托车,凌空一跃飞越黄河,飞越天险,他像一个顽皮的娃,和黄河母亲做了一次恶作剧。
因为这次壮举,黄河母亲深爱着这个孩子,犹如深爱她的万千子民,赋予他勇敢和智慧,也赐给他财富和梦想。
这双手和死神扳过手劲,终将死神摁倒。
这双手和命运近身搏击,终将命运的咽喉扼住。
朱朝晖黝黑的脸上露着憨实的微笑,我和他相握,分明感受黄河正在他胸中一泻千里,一股正能量的潜流从他的手传递到我的手,直到全身。
人祖庙
攀到1742米的海拔,几间小屋,恰似丘陵上的农家小院,让我联想屋内住的是人,不是神。
跨过几级台阶和一道门坎,娲皇迎面端坐,我双腿发软,不由地双膝跪地,叩头膜拜。
人祖啊,开天辟地,天地洪荒,上天安排兄妹成配,生儿育女繁衍人类……你用泥块捏人,有男有女,活蹦乱跳,成双成对,你用藤条抽打着泥土,溅出碎末纷纷扬扬落地成人。
人祖啊,见到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了,我的根在哪里。
人祖啊,请你告诉我,我是哪一块泥土捏成。
恍惚之中,娲皇伸手将我扶起,告诉我:
你是最优质的泥土造成,因为你是一个诗人。
人祖山狙击战
请历史镌刻着一天:公元1938年3月18日。
请我们铭记这支铁军:中国国民革命军晋绥军66师206旅431团。
强盗在步步紧逼,逼过东三省,逼进卢沟桥,逼近黄河。
国军在节节败退,126条汉子退到人祖山顶,就无路可退了。身后就是人祖庙,供奉着伏羲和女娲的神像,神像之下是他俩的遗骨,那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啊,怎能让魔鬼玷污。
岩石构建的防御工事,这是第一道防线。
单薄的军服紧裹着滚烫的血肉之躯,这是第二道防线。
不屈的中国人,不屈的中国军人,不屈的中国魂,这是第三道防线。
三道防线,铜墙铁壁般铸在人祖山的最高峰,拱卫着人祖庙。
端上简陋的武器,但大刀和刺刀是锋利的,奔涌在体内的血是炽热的。勇士们跃出战壕,以永不屈服的气节,划破武士道的面具。
雨雾飞扬,黑夜像倒扣的锅,分不清敌我,只有凭呐喊的声音来判断,太原的临汾的吕梁的方言,当然也有安徽的河北的山东的四川的,铿锵而带着血丝,汇聚成黄河的波涛,压住了倭寇的狂妄。
誓死不能后退半步,身后就是人祖庙,祖先在凝望。
126个生命,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吼出最后一声誓言,流出最后一滴鲜血,倒在人祖山补天石旁。娲皇啊,你用泥土造就了我们,我们用血肉报答你了。
126个女娲的后裔,126个母亲的儿子,壮烈殉国了。而侵略者下场更惨,仅焚尸后的铜扣就有几升。
126个壮士,一个标准连的建制,从山上列队走到山下,再不分离。
当地百姓说,每到风雨交加的深夜,雷鸣即是集结号,战士们都集合要操练、报数:
“张炳文。”“到!”
“牛保国。”“到!”
“中国人。”“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