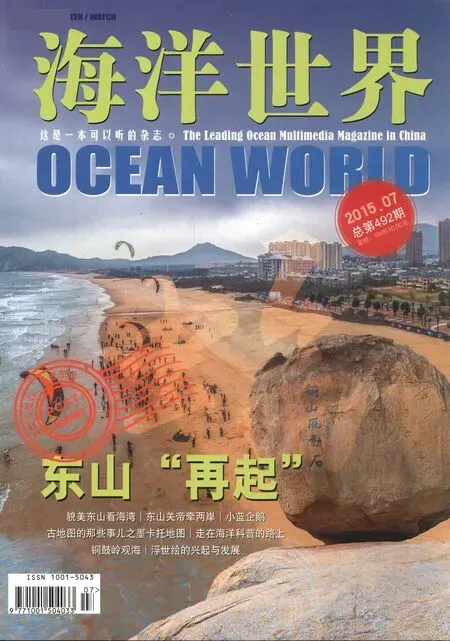南极追踪(上)
撰文/凌晨
1 南极大陆·罗斯陆缘冰
惠灵顿时间19点,史蒂夫·阿奇又打开了通讯机。耳机中,所有既定的波段上都是一片噪音。他立刻关掉机器,以免消耗电力。
“我也需要断电吗?”机器狗PT问。
“不,你不需要。你得一直跟着我。”史蒂夫说,“你能找到方向。”
“是的。”PT举起前爪,“这个方向,距离37.56千米,是中国维多利亚地科学考察站,全年站,目前有35个人在站内工作,包括一个7人的后勤保障小组,您在那里能得到很好的医疗救助。”PT的前爪转动,指向另一个地方,“那里,距离48.91千米,是中国峨嵋科学考察站,夏季站,他们有一个机器医生。”PT的声模拟器发出类似干笑的“呵呵”声,继续说:“多功能全科机器自动治疗站Ⅳ型,我觉得对您来说足够了,它还有专业技师5级按摩推拿功能。”
史蒂夫的目光顺着PT的爪子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晶莹璀璨的蓝天之下,阳光笼罩的大地上除了白茫茫的雪就是白茫茫的雪,这里和那里,没有任何可以标示的区别。
“麦克默多站在哪里?”史蒂夫问,强调:“我们美国的麦克默多站,那可是南极最大的科考站!”
“在147千米外。”PT说,“太远了。”
史蒂夫明白PT的意思,对于PT,把他拖上这冰原并走了这么远,已经是能力的极限了。毕竟PT只是机器伴侣狗,除了能帮他背个挎包,找找路外,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说个笑话唱个小曲倒是在行。史蒂夫看看自己被急救包包裹的受伤的腿,微微叹息:“我不能去找中国人。”
PT跺脚,这个仿生机械的危机处理系统面对史蒂夫的固执,找不到任何应对方法。
“得了,”史蒂夫拍拍PT的脊背,“不关你的事。飞机坠海又不是你的错。我不讨厌中国人。但是,”他迟疑,即便面对的是一个机器,有些话还是希望烂在肚子里。史蒂夫闭上嘴,回头看。雪地上清晰的两行脚印,一个人和一条狗,延续到他目力所及的尽头……在那足足有9千米远的地方,冰冷的海水已经吞没了他的飞机以及他的助手和飞行员。为了追踪神秘的鲸的叫声“鲸歌52”,他的飞机在雪雾之中进入了地图上没有的海湾,然后就一头撞上足有6层楼高的冰崖。他能侥幸逃生全靠PT,它在飞机坠落的瞬间打开机门,奋力将他推出飞机。
“都怪那头鲸!”PT说,作为伴侣机器狗,它的心理干预系统对史蒂夫的理解只能到这种程度了。
史蒂夫没说话。智能机器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联想性。不能去中国站,是因为他追踪的“鲸歌52”中国人也在追踪,这是一项绝密的研究计划。
一般鲸的声音频率在1至25赫兹,但有一头鲸的声音却达到了52赫兹,由于这个声音频率不在任何已知鲸类的声音谱系之中,研究者们不知道如何给它分类。50年前研究者就监听到了这头鲸的异常声音,称它为“鲸歌52”,但却一直找不到它的行踪,断断续续监听了30年后,这个声音在大洋中消失了,人们再也听不到了。按照一般鲸类45岁的寿命来计算,这头鲸应该已经死亡或者被人类捕杀了。但在去年,就在旧金山水母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海军又意外监听到了“鲸歌52”的声音。从那时起到现在,“鲸歌52”会出现在每一个异常海洋事件的现场。
史蒂夫拧开电子烟,深吸一口。巧克力味的尼古丁烟雾在他口腔中蔓延,让他的心情轻松了一些。每一个异常海洋事件的地点各不相同,时间上却从来没有重叠,所以每一个事件要都在场,并非不可能,但一头鲸出现的地方都会发生异常事件,这无论如何不寻常。
“那头鲸,应该有70岁了。”PT忽然说。
史蒂夫难得地笑了,关掉电子烟,说:“不知道。也许吧。我的一些同事不相信它真是一头鲸。”是的,海军中有人怀疑那是敌对势力,甚至拿出当年纳粹跑南极建立秘密基地这样的传言,于是他就被海军派来追踪“鲸歌52”,找到“鲸歌52”的吟唱者,或者发出“鲸歌52”的那个东西。那东西也许是这场该死战争的关键。
是的,战争,史蒂夫疲惫地站起身,在海洋中,和看不见的敌人进行的完全不能预测未来的战争。处在极昼阶段的南极令他烦躁,太阳正向地平线靠近,却还要有三个月才会落下。史蒂夫看看综合仪,地面温度在降低,一场风雪40分钟后就将降临。他最好能尽早和总部取得联络,哪怕是找到一个补给站的备用通讯机都可以。时间消耗不起,也许战争的胜负就决定于他的报告——在南极罗斯湾,“鲸歌52”的声音信号稳定、清晰,而且近在咫尺。
2 肯尼亚内罗毕·联合国总部
内罗毕时间11点35分。联合国的这次专题会议,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在一系列用汉语、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发言进行的冗长报告之后,与会者都产生了强烈的饥饿感。及时送来的午餐分西式和中式两种。西式是章鱼状面包,腌鲑鱼搭海藻酱;中式则是酱爆鲑鱼盖浇饭,配凉拌海蜇和海藻汤。无论哪种都令人生厌,毫无食欲。
美国代表最先提意见:“内罗毕离最近的港口也有400千米,我不认为海产品会是这地方的主食!”
会议主席来自尼日尔,他对美国人的抱怨嗤之以鼻,反驳:“尼亚美都以海鲜为主食了。难道您不知道,海产品养活了整个非洲吗?”
法国人打着哈欠,懒懒地对美国人的意见表示赞同:“我们不指望工作便餐上烤肉大菜,但起码应该有开胃沙拉、甜土豆和鱼香肉丝吧。”
俄罗斯人点头附和:“哪怕是酸黄瓜也好哇。”
尼日尔人不耐烦地回答:“这些海产品,味道不错的。我不明白,有什么不对吗?”
美国人很郁闷,喊道:“有什么不对?我们一上午在干什么!在讨论我们可能受到了海洋的攻击!是整个海洋,都在与我们为敌!你明白吗?”
尼日尔人满脸“你们在说什么”的奇怪表情,他说:“如果海洋与我们为敌,我们吃掉我们的敌人,不正是最应该的行为吗?有什么问题吗?”
在场一众各国代表都被尼日尔人的耿直噎住了,说不出反对的理由。
尼日尔人憨厚地笑了,继续说:“非洲一直在遭受粮食短缺的折磨,成千上万的儿童营养不良甚至夭折。但我们有了海洋农场之后,丰盛的海产品使我们远离了饥饿。”说到这里,他向中国代表竖起大拇指,“这还要感谢中国朋友的帮助。”
中国人摆手,将话题从食物上转移开,他说:“我想大家的情绪可以理解,毕竟这大半年我们都吃了太多海产品。”
“是的,”美国人沮丧,“我们一直在吃海蜇。从旧金山到西雅图,20亿只越前水母!”
“我们在吃鲸。”日本人说,“除了鲸我们什么渔获都没有。”
尼日尔人脸上奇怪的表情又出现了,他说:“我其实不明白,海洋给了我们那么多丰盛的食物,可你们却说它是敌人,怎么解释?”
美国人火冒三丈,指着中国人:“这个你要问他!问问一向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在干什么!”
中国人不慌不忙地反驳:“诸位,一个上午我们都在听各位海洋专家的报告,关于海洋的种种异常,没有任何一个数据能证明是中国所为。”
美国人怒气冲冲叫嚷:“难道是我们美国干的!整个太平洋都不对劲!海洋动物们的行为越来越不能理解,就像你们自己的专家说的,”他忽然用蹩脚的中文说:“海洋动物都成了神经病。”
俄罗斯人劝:“二位,二位,整个上午我们坐在这里打瞌睡了吗?那些专家的报告,到底谁听懂了他们在说什么!”
法国人拿起面包蘸了一块酱,使劲儿咬了一口,才慢吞吞地回答道:“他们说,这场混乱,水母攻击海滩,海蛇咬坏海底光缆,海豚不再救人反而任人溺死……这一切,都是因为,”法国人停顿了几秒钟,欣然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因为海洋疯了,是海洋在攻击我们。”
俄罗斯人看看中国人,再看看美国人:“是海洋生物集体无意识?还是它们有一个领袖?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美国人忽然精神起来,认真而得意地说:“我们很快就会搞明白,得出一个结论,真的,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