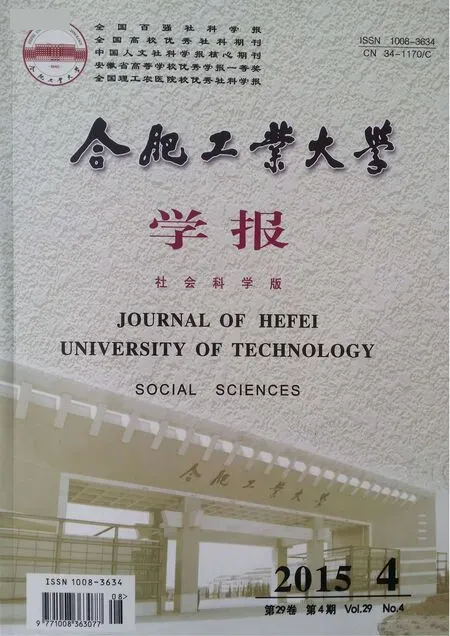艾青“湘南旧作”研究
魏文文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艾青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影响了一大批青年诗人。特别是在诗歌意象方面,艾青不仅打破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现代派诗歌缺少时代生活气息与现实生存体验的诗歌意象,还在诗歌意象世界里撑起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找到属于诗人自己的“缪斯”。艾青既找到了具有理性内涵和艺术审美功效双重效用的典型意象,又赋予它们鲜活的时代气息与生存体验,并致力于营构一个严谨而有机的结构系统,把中国现代诗歌意象世界推进到了一个更宏大开阔的境界。
1939年9月,艾青为躲避战乱,携爱人韦荧离开桂林,到湖南新宁衡山乡村师范任国文教员。新宁虽然是湘西南的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但是山清水秀,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更有闻名遐迩的莨山风景区。艾青蛰居新宁八个月里创作成果异常丰实,不仅创作出诸多优秀的田园短诗、著名的叙事长诗《火把》,还完成了诗歌理论经典论著《诗论》。诗人这一时期高产的诗歌中有不少描写乡村景致、充满田园情调的小诗,它们大都拖着低沉、忧郁的尾巴。这些小诗是艾青深居战乱时的“世外桃源”新宁所作,其中充斥着诗人对生存及时事的沉思与担忧。聂华苓说过:“艾青的诗,好在那雄浑的力量,直截了当的语言,强烈鲜明的意象——可以看到、闻到触到的意象,这也许因为他不仅是个诗人,也是个画家吧。艾青是一个有时代感、历史感、使命感、同时又有艺术感的诗人。”[1]4由此,艾青诗歌在意象艺术上的独特性是研究其诗歌的突破口,新宁时期的诗歌研究也不例外。
一、抒情与意象的交融
艾青主张诗歌创作必须围绕“意象”这一中心,他指出“一首没有形象的诗!这是说不通的话。诗没有形象就是花没有光彩、水分与形状,人没有血与肉,一个失去了生命的僵死的形体”[2]93。诗人只有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缪斯”(意象载体),使“意”、“象”交融,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诗。艾青这一时期诗作的突出特征便是抒情与意象的交融,诗人通过不同意象的组合传达着蛰居山中的焦躁与不安。这种杂糅的情感包括对感情受挫的无奈、对故乡的惦念以及对光明世界、和谐生活的渴望。
艾青的感情生活总是一波三折,从留法时期偶遇的气质文雅的波兰姑娘,到才华横溢的漂亮女记者高灏,她们都让诗人可望而不可及。阳太阳曾说:“艾青是个很矛盾的人,他一方面很孤独,有流浪感,同时又很骄傲,自视甚高。他自尊心强,又极脆弱,感情容易激动突变。他一生爱美,对女性的期望甚高,然而,他又要求过一种很具体的现实的生活。”[3]210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和沉重感伴随着艾青,即便在新人韦荧的陪伴下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安静的乡村生活,他的感情生活仍然危机四伏。韦荧年芳17,对于家庭琐事尚不能顾全,于是产生了去新四军根据地投靠同学的想法。刚刚失去家庭的艾青,新的家庭再次面临危机,这让他措手不及。一首写给韦荧的《冬天的池沼》记录了诗人内心的压抑:“冬天的池沼,寂寞的像老人的心——饱经了人世的辛酸的心;冬天的池沼,枯干得像老人的眼——被劳苦折磨失了光辉的眼。”在同一时期《愿春天快点来》中,他再次提到“池沼依然凝结着冰层”。艾青用“冬天的池沼”暗示内心的“寂寞、枯干、荒芜与阴郁”,他的感情生活像池沼一样结着冰层。诗人渴望用迟来的温暖消融心中的冰层,但现实却让他对感情再也没有理想主义的乐观和自信,诗人感受更多的是自我的渺小和不堪一击。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寻找精神家园的主题,大多数是在故乡的怀抱中,在想象的童年生活的土地上,让漂泊的或受伤的灵魂得到暂时的栖息[4]103。艾青也不例外,他心里记挂着生养他的畈田蒋。新宁如画的风景、恬静的乡村生活不时地唤醒诗人心中对于故乡的记忆。故乡的“水牛”、“松树林”在艾青心中划上了最浓重的记号。“巨大而丑陋,老实而呆笨,他们散开在那些土墓堆上。皮肤像泥块一样坚硬,灰黄的毛稀疏而无光。”水牛的模样让诗人记惦起畈田蒋那些沉默的农民,“它们天真如农夫,而又呆钝如岩石”(《水牛群》)。在《矮小的松树林》中,松树林也唤起了艾青情感上的共鸣:“被遗忘的松树林!乞丐般的松树林!谁来理睬你们呢?只有我却欢喜你们——在我家乡的山背上,也有这样矮小的松树林啊……”(《矮小的松树林》)艾青在赞美生命的同时也赞美着令他朝思暮想的畈田蒋。
如果对感情生活无奈的表达和对故乡的惦念是诗人深居新宁诗歌创作的常态,那么对战事的关怀则成为艾青田园诗中特殊的主题。艾青虽因远离烽火,闻不到“战斗的气息”,但诗人久久沉于莽原的粗犷与无羁,不自禁而有所歌唱。每一草一木他均寄以真诚,只希望这些歌唱里面,多少还有一点“社会”的东西[3]264。艾青在蛰居新宁期间所作的以自然为描写对象的诗中,依然渗透着诗人对国事民情的关心。1940年,艾青得知桂南战役失利,敌陷宾阳时,他痛苦地写到:“在两个环着云的高山相接的地方/在两个山峰突然向下倾斜的下面/在几尺高的芝草的密丛里/横着一根棕榈的树干/独木桥连住了两个高山。”(《独木桥》)艾青没有亲临战场即已感受到两军交战的“危险程度”,他徒有一腔热血,却无处挥洒,只能用“火把”为浴血奋战的士兵照亮前进的路。“我们是火的队伍/我们是光的队伍”,“软弱的滚开/卑怯的滚开/让出路/让我们中国人走来。”(《火把》)这种坚持抗战,反对妥协的气势恢宏强大、振奋人心。艾青运用“独木桥”、“火把”等隐喻性意象表达出最真切的感受,他在洪流一般的诗句里夹裹着对战争的愤恨以及对人民生活的担忧。
二、独特的意象结构系统
骆寒超在《论艾青诗的意象世界及其结构系统》中,把艾青诗歌的意象世界分为三个敏感区域,即土地系列意象、波浪系列意象及太阳系列意象,并指出艾青诗的意象世界是一个相当严谨而有机的结构系统,即诗人在处理三大系列意象之间的关系时是按照土地系列意象向波浪系列意象再向太阳系列意象递进的[4]49-53。深居新宁的艾青在复杂的情绪下创作的田园诗却另有一番风味。特定的时代环境及个人感情忧郁的背景下,诗人在处理诗歌意象三系列的关系时逐渐地淡化了太阳系列意象,相反在诗作的结尾增加了中性及冷色调的语词,偏向突出土地和波浪意象系列,并用“人”(主要指被侮辱受损害的农民、找寻生存空间的浪子)这一意象作为贯穿诗作的骨骼,传达出艾青深切的忧患意识及悲悯情怀。这一意象结构系统下衍生出的诗作内涵在创作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从写苦难递进到写抗争,再到因失败而带来的浓重的忧郁感,这也是艾青田园小诗的独特之处。
“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桥》)诗人先向我们展示出土地系列意象与波浪系列意象的交融状态,再用艰苦跋涉的人类拉近与波浪系列意象(桥)的距离,并在诗作的结尾点名了主旨“桥是土地与土地的联系;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桥是船只与车辆点头致敬的驿站;桥是乘船者与步行者挥手告别的地方。”(《桥》)艾青用“告别”这样感伤的语词结束全诗,使诗作笼罩着一股淡淡的忧伤。“你们阴郁如土地/不说话也像土地/你们的愚蠢、固执与不驯服/更像土地呵。”(《农夫》)艾青笔下的农民愚蠢、固执,他们的脸是土地的颜色,手像木桩一样粗拙,身上融合着土地的气息。诗人把“土地”这一意象与苦难的劳动人民糅合在一起,揭示出农民真实的精神状态,让人充满同情与无奈。
意象是直觉情绪的具象体,故艾青诗中的意象组合是他直觉情绪的具象反映。他在《诗论·出发》中说:“真、善、美是统一在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5]2这意味着作为诗歌灵魂的三大意象系列与真、善、美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即艾青从土地系列意象中延伸出对“真”的象征;从波浪系列意象中延伸出对“善”的象征;从太阳系列意象中延伸出对“美”的象征——这是最高类象征义的延伸[4]56。艾青这一时期的诗作中突出的是土地及波浪系列意象,而太阳系列意象是相对缺失的,这与诗人的现实遭遇有关(见第一节)。与之相对应的是诗作中呈现出的多是“真”与“善”的世界,“美”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苦难、迷茫”的状态,这让原本清新的田园诗拖着忧伤的尾巴。
三、意象色调的曲折回环
艾青主张“把每个日子都活动在人世间的悲、喜、苦、乐、憎、爱、忧愁与愤懑里,将全部的感情都在生活里发酵、酝酿,才能从心的最深处,流出无比芬芳与浓烈的美酒”[6]17。他把自己五味杂陈的感情全都灌注到诗歌中,并精心挑选最适合的意象表现出来。这一时期艾青被新宁这个蕴藏无限丰富宝藏的地方吸引,新宁的自然万物与诗人的情感相遇合,激发他创作出风格迥异的田园诗。艾青的诗歌呈现给读者的大多是色彩鲜明、情感丰富的意象世界,诗歌意象在色调上具有曲折回环的特点,而且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条件下所呈现出的情感色调还具有差异性,见表1。

表1 艾青新宁时期创作一览表

续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艾青深居新宁时期大致的情感变化,由初到新宁时期恬静、充满希望的乡村田间生活,到1月初与妻子韦荧之间的矛盾及家庭琐事给他带来悲伤和苦痛。1月中下旬随着矛盾的缓和,艾青渐渐对生活充满希望,心情“解冻”,又到2月桂南战役失利,艾青在漂泊的乡村生活中体会到“无岸可靠”的不安。3月艾青调整好情绪回到正常的田园生活状态,创作出大批类似静物的小诗,这些“吹不起半点涟漪”的小诗像是艾青诗歌创作的沉潜期。4月诗人厚积薄发,创作出充满悲愤力量的诗歌,特别是5月创作出的叙事长诗《火把》更是激发了诗人的斗志,指引他朝着最“光明”的地方奔去。
艾青的诗歌意象充满生命力,他的情感变化一波三折,带来的是在诗歌意象选择上的变化。可以把艾青新宁时期的诗作看成一个整体,并按意象情感色调分为三次光明期、三次低潮期。有意思的是,艾青在第一次低潮阴郁期诗歌创作时选择了土地系列意象,如“田野”、“池沼”;第二次低潮不安期选择了波浪系列意象,如“船”、“沙”;第三次低潮愤怒期却选择了太阳系列意象,如“太阳”、“火把”。在艾青感情低潮期,每次“拯救”他的正是他心中的“缪斯”——三大系列意象。艾青诗的意象世界是一个相当严谨而有机的结构系统(前文有述),不仅在一首诗作中,诗人由土地系列向波浪系列再向太阳系列的顺序递进;在特定的时期内,艾青的诗歌创作也是按照这样的意象排列顺序递进的,诗人营构了一个完整的诗歌意象世界的结构模式。艾青以土地系列意象开始以太阳系列意象结束的诗作体现了诗人对光明理想的向往与坚定的信念,与郭沫若笔下充满自我崇拜意识与创造意识的太阳礼赞不同的是,艾青的太阳系列意象更是一种融入自己生存体验与时代精神烙印的崇拜。
另外,同样是“池沼”这一意象,艾青1940年1月所作的《冬天的池沼》充满哀愁,全诗飘荡着灰暗、阴郁、沉重的格调,而1940年3月所作的《青色的池沼》则清新、平静了许多,“平静而清敛……/像因时序而默想的/蓝衣少女,坐在早晨的原野上。”(《青色的池沼》)对于“秋天”意象,艾青更是运用得挥洒自如:1933年左右创作的《我的季候》中,秋天是那样忧郁低沉;1939年于新宁创作的《秋》、《秋晨》则萧瑟凄凉;而1941年作于延安的《秋天的早晨》,却充满喜悦,意象质朴亲切。
四、哲理性感悟
晚年某日,牛汉等人就《艾青作品欣赏》一书的编选询问艾青的意见时,他对书中“湘南旧作”所占的比重“深以为许,认为是“触及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的”[3]268。艾青深居“世外桃源”,陪伴他的是一种更加难以忍耐的孤寂感,这种孤寂感是独特的,它夹杂着诗人对人生状态、乡村与城市等问题的哲理性思考。
乡村的宁静让艾青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往事:求职、婚姻、写作、去与留等等,艾青在人生道路上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结束是开始,开始也是结束。此刻,“船夫与船”进入了诗人的视线,船夫“老是阴郁地凝视着空茫,他们的桨单调地/诉说着时日的嫌厌”,船夫与船的生死像是早已注定一样,永远“在困苦与不安中旅行。”(《船夫与船》)他们没有目的亦无岸可靠,只能空茫地漂着,携带着忧伤与苦痛。艾青借船夫与船的生存状态暗示其孤独虚无、无能为力的漂泊状态,他无力反抗乃至改变,只能顺从地接受。诗人继续沉思历史往复循环中的不变性,这种不变性是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难以言明的东西。艾青赞美生命,也思考生命问题,他不仅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还深深地同情农民无法摆脱的代代相传的宿命感,他用“沙”揭示出了农民生活彻底的虚无状态:“太阳照着一片白沙/沙上印着我们的脚印/我们走在江水的边沿/江水在风里激荡/我们呼叫着摆渡的过来/但呼声被风飘走了。”(《沙》)人的一生中难免会遇到命运的挑战,但是无论你怎样努力坚持,最终的结局都会显得徒劳、悲惨。这种关于个人生存悖论的思考贯穿艾青新宁时期诗歌创作,与他骨子里的深深的忧郁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
乡村是艾青最为眷恋的地方,他热爱乡村亦如他爱恋的土地一样,土地是农民的衣食来源,农民失去土地则意味着失去乡村的文化传统,失去一切。而“乡村的城市化”渐渐引起艾青的注意,并在他心中蒙上浓重的阴影,诗人不禁担忧起来,“但城市扩大着/无厌止地扩大着/把路一条又一条地占据了/用毗连的住房来占据/用电杆和电线来占据”(《街》)。城市的拥堵、喧哗与商业化的冲击打破了乡村原有的宁静,快节奏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是人心的躁动。这“突如其来”的恐怖震惊了艾青,他连用7个“占据”发泄心中的恐惧。未被“街”取代之前“原野”,这个诗人心中的圣地渐渐消失,乡村的衰败不可逆转。这种担忧在艾青1937年创作的《浮桥》中就已经出现,尽管城市守卫的是贪欲、淫逸与荒唐,它却“吸引了万人/向它呈献了劳动的血汗”;乡村充斥着颓废和荒凉,农民体味到的是“无言的失望和空虚”,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浮桥暗示出乡村城市化的不可逆转性。艾青新宁时期对人生存状态及生存环境的哲理性思考虽然不及他晚年具有极强批判性和哲理性的小诗那样深厚,但这些哲理性的感悟却发自诗人内心,令人深省。
艾青坚持“诗人须比一般人更具体地把握事物的外形和本质”,无论哪个时期,他都在创作实践中致力于诗歌意象的营造,从诗歌意象系列的找寻到意象世界结构系统的营构,其中无不充斥着诗人浓厚的情感与哲理性思考,这为艾青成为优秀的民族诗人奠定了基础。1940年5月4日,艾青与韦荧告别了难忘的山城新宁,转道达重庆。至此,诗人结束了深居“世外桃源”的山城生活,开始了人生旅程的又一段漂泊。艾青深居新宁的诗歌创作,是研究其诗歌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出的田园诗歌有别于诗人其他时期的诗歌,更有别于其他诗人的田园诗创作。但这些独特性并不意味着艾青该时期的诗歌创作是完美无缺的:诗人选择简约的具体意象,虽然象征性喻意深刻,却少了他此前诗歌意象所具有的审美色彩与鲜活的生机;同时诗歌意象的过度重复容易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
[1]聂华苓.漪澜堂畔晤艾青[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4.
[2]艾 青.艾青选集(第三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93.
[3]程光炜.艾青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4]王泽龙.走向融合与开放:艾青诗歌意象艺术的探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03.
[5]骆寒超.论艾青诗的意象世界及其结构系统[M].文艺研究,1992,(1):47-59.
[6]艾 青.诗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