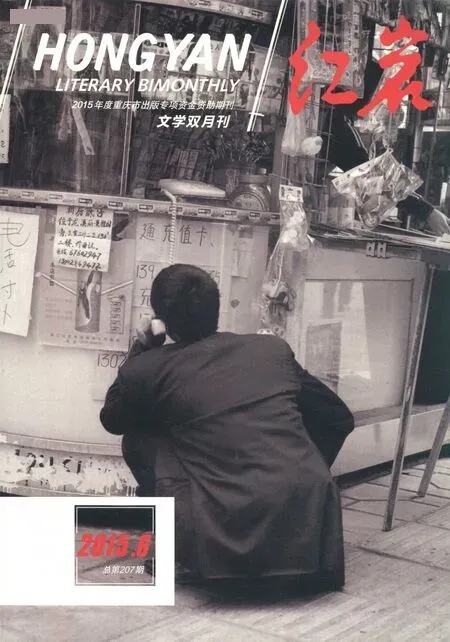胡中华诗六首
胡中华
说起某天
说起某天,雾就散了,云就淡了。
阳光的羽毛,飘过稀疏的树影。
花朵摇曳,那些蕊,和蜜蜂蝴蝶捉迷藏。
说起某天,雨后叶子上椭圆的清露,
润着喉舌。泥土的芳香滋养着心肺。
说起某天,你带着越来越长的影子,
向着缓缓的山坡行走,
林子里的小动物,向着树枝上攀爬。
一滴,两滴,清脆的鸟鸣,
把我遥远的记忆,从电线上震落。
说起那天,就有一大堆米粒一样的言词
将我淹沒,就有一条暗河,将我围困。
说起那天,黎明就来临,黄昏就来临。
风过竹林
祖辈说,这竹是祖辈的祖辈
从山野移栽到老屋门前来的
移栽到老屋来的野竹就长成了家竹
它的根,以潜伏的方式
一年一年地将我们的老屋包围
竹根所到的地方就有了翠竹
它把我们的老屋抱在怀里
母亲,把我抱在怀里
小时候,我看风过竹林,我听风过竹林
风过竹林,我的秋千荡起来
鸟儿跳出旋转的窝,在竹枝上荡起来
一丝柔软的羽毛,伴着清脆的鸟鸣
荡起来,我的梦想在竹林,荡起来
那时,笋向上长,小鸟向着天空飞
风过竹林,我和我的老屋荡起来
在高原
海拔越来越高。
睡眠和倦怠走过四十年光阴。
从生活的合川逃离,到米亚罗,到红原
从若尔盖,再到青海湖。
蓝色、紫色、黄色的植物之花,
随着高原的风,摇摆,跟着汽车和打望的眼神
搔首弄姿。沿途的花,被尘埃覆盖,又被诱惑擦亮。
蓝天高远,白云切近。那个放牧牛羊的人
背对看客的方向,一直向前。他能否寻到
从海拔四千四百四十多米的大地下长出的那一缕花香
把我们的生活搓得更结实
她放下锄头,摘下麦秸草帽,
脱去蓑衣,往墙钉上一挂,
使劲甩动滴水的长发,
抖动,拍打身上的泥水。
高卷的裤管,露出两条瘦长的腿。
活像一只风雨中归来的雌鸟。
她,静静地靠在门框上。
望着对面雨中那片青葱的玉米和
绿油油的秧苗。然后,我的母亲,
满意地坐在门槛上,搓麻线……
吐一口唾沫在手心
双掌合一,或是,
抵着大腿,一阵搓捻,
干涩的麻丝跳跃着团聚。
难道,她是要趁在田地里劳动的间隙,
把我们的生活,搓得更加结实?
春节里的母亲
用翠绿的竹叶,扎成扫帚,
教生活的尘埃落地出门。
把青葱的艾草,请回家,
看守贫穷的门槛,保佑多病的孩子。
擦亮生活的器具,焕发新的光彩。
关好粮仓,别把老鼠的肚皮撑坏。
一切就绪了,不忘
把灶神送上天,把财神供起来。
土神这边放鞭炮,祖先那边烧纸钱。
无事可做了,
发给儿孙压岁钱。
你自己,大年初一,
端来箩筐,弄针线,做咸菜……
桃李有颜
高高的山上桃花开,
竹篾,泥墙,瓦屋边。
高高的白,高高的红。
妹妹啊,你洁白的身体,
安放在每一朵桃花温润的床沿。
高高的山上李花开。
泥墙,竹篾,屋檐边。
高高的红,高高的白。
妹妹啊,你红润的躯体,
蜷缩在每一朵李花如雪的床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