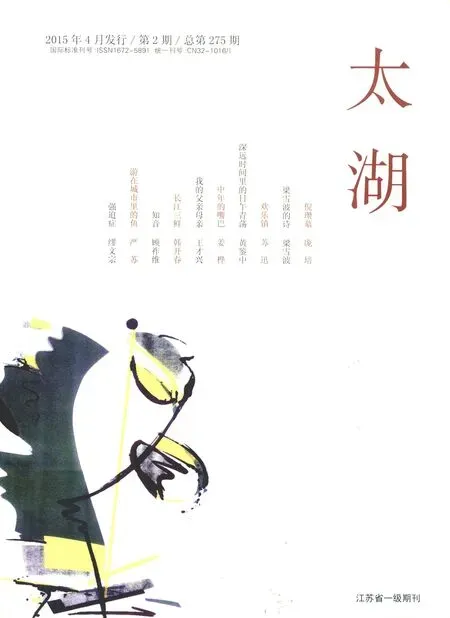倪瓒墓
庞培
倪瓒墓
庞培
一
倪瓒墓前有一挖土的老头,穿一身旧的20年前的海军装,脚蹬解放鞋。我因为刚从芙蓉山头的乱石岗上,翻山过来,四处寻觅云林先生的坟冢而不得,就隔着一丛荆棘和这老头攀谈起来 (边说话边试着跨越那些荆棘)。
“这位师傅,我想打听——一个古代倪先生的坟,你知道在哪里?”
“姓啥?”
“倪——倪瓒!”
“泥?……”他停下手里的锄头,偎在胸前,茫然地瞪视着我。他有一双北方蒙古人似的小眼睛,土黄色而很和善的脸,留着上古式子的小胡须。他定下神来看人时下巴略略上翘,因此整个头部的形状,像一只扁平的螳螂俯伏在树桠树顶上。
“这山里……”他顿了顿脚上的烂泥,改口说:“这芙蓉山上上下下那么多坟,你要寻一个姓泥的坟,倒也——”
“这是叫芙蓉山吧?”我打断他的茫然。
“对的,芙蓉山!”
我看看四下里无人,愤愤地说:“这个山也差不多全没了,全挖空的了……”
他竟然很憨厚地摇摇头,不同意我的激愤,用一种没有的声音,但富于表情的面部语言说:“没……没有——”
那老头站在他刚掘开一半的黄土堆后,俨然一幅古代山水画里精神矍烁的老者形象,只是,因为常年的乡间劳作而显得身架子枯萎黯淡,欠缺了古代画幅中点缀于山水竹石间的一两人物身上那股飘逸气;服装,也自然是现代式样。我不知道如若云林先生再世,画人物到山水中,是否要把他一堆黄土边上那双解放牌跑鞋的样子画出来。
老头脸还有另一副神情——在偏僻的荒村野店里兀然一身,灌 (喝)了一辈子黄酒而又不常跟人搭腔的表情。这会儿,他满怀同情,看着我,因为不能够帮助我而流露出很是稚气的怅惘遗憾。
“你是……来上泥先生坟?”
我点点头。“就是不知到哪里去找……山也全挖空掉了。你呢?”——我突然问。
一刹那,他放下偎在锄头柄上的手,换了个姿式,用很安然,但仍显出了乡间的忸怩的声音,低下头说:
“我也是,来挖个坟……”
山野的静谧里时闻庞大吊臂的挖土机声音,在原地打转,辗转半天,却没有近旁油菜籽田里飞来的一只蜜蜂的 “嗡嗡”声音来得明丽耀亮。我骑脚踏车从江阴转道乡间,到芙蓉山一路上,已见各处的养蜂人在道口、马路边、堤坝上把一只只积木形的蜂箱盖子掀开——不过是昨天、大前天,一两天里,刚刚掀开。
但原野各处,满目绽开的菜籽花,那花骨朵朵耀眼的速度,还是比小蜜蜂们胖嘟嘟的翅膀来得更为迅捷——几乎跟浩荡的春风同步!只两三天功夫,太阳就跌到田野的新鲜裙子的海洋里了;太阳的脸上被映染上很多丝绸缎子的光亮——油亮的菜籽花水旺旺一片,正在乡野各地的麦田、青菜莴苣田、野坟场和河塘边,风卷残云般四处蔓延。
二
倪瓒的墓是在无锡的北边、江阴的南面;在两地交界处一个名叫东北塘 (现属锡山市)的乡下。我从江阴的马镇乡开始,踩脚踏车一路寻访,先后经堰桥、长安镇而至芙蓉山下。倪瓒的墓在芙蓉山脚,我是听江阴祝塘乡的李中林说及。我一听说后,就几乎一刻未停,只隔了一夜就往南面的乡间赶。前一夜落雨,我动身的一日,则是雨后初晴,气象澄明。
江阴的祝塘乡,传说就是 《水浒传》里的祝家庄。如今祝塘的街上仍有一条小巷名叫“景阳岗”,这是题外话。施耐庵老先生曾有数年时间躲避战乱而在江阴祝塘一大姓人家隐居,这个说法,也大部分为后代人认可。据说 《水浒》一书有半部是在江阴写出,这里只是顺便插话。
李中林先生,现在祝塘中学教书,已有三十三年,为人师表,一生操劳,是我在江阴乡间多年来惟一觅得的良师益友。家中藏书13000余册;早年曾去部队当兵,归乡后参加挖河泥、抗洪及乡间学校代课。每谈及各地乡贤生平事迹,则声若洪钟,慷慨激昂。
江阴地方上,南有无锡东林党,北有抗倭史迹和黄山炮台,东有明末忠烈举全城百姓抗清81天的悲壮史实,西乡尤有季札墓,缪荃孙、杨名时故居,真所谓 “晴川历历芳草树”,而 “青山处处埋忠骨”了。我在祝塘和中林先生多次晤面,感触颇深。前一日,我讲到我在江阴境内的斗山游历,李先生立即两眼放光,大声提示我,“你再往前走20里,有一芙蓉山,山不高,却是元代大画家倪瓒先生的长眠之地。”我一听说,心头不禁大惊!
前不久,我还僻居家中,读美国方闻先生的中国绘画史著作:《心印》①。里面写到倪瓒的篇幅文字,历历在目 (“云林先生瞳色绿。”②)。以前只晓得这名有 “洁癖”的古代画家是无锡县人,想不到他的墓地,离我平时的居家这么近!于是只隔一夜,天气好,就不假思索地跨上我那辆外出寻访的破脚踏车。
季节是在寒食节的前一天,沿途各处乡间的野坟场上已见新填上去的土和坟帽子。新插的柳枝。五颜六色祭祀用的小彩旗——天气本身却要比坟堆上的彩色纸旗更绚丽耀眼,灿烂的阳光在田间矗立的松柏四周闪亮;在喜孜孜的麦田深处,油亮的菜叶子边上催开了一年一度江南的村落上空蔚然壮观的油菜籽花。仿佛为了庆贺这自然界的盛典,天上的鸟雀,田地的野花也一路尾随,纷纷挤到一垅垅无边无涯的油菜花后面轧闹猛。各式各样的鸟儿,都飞到这春天的柳荫和电线杆上来,张望一阵,又“忽刺”一声振翅飞去,仿佛大气各处,嵌满了各种型号的梳妆用镜子,鸟儿的注意仪表和不停打扮,在这一两天油菜花开的耀眼亮光里,已频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一路停下车,向村子里的老农、老太太和副食店门口的姑娘打听去芙蓉山怎么走,但我却发觉自己不断讶异着、惊喜着,心思静不下来。喜鹊、白头翁、燕子、百灵鸟纷纷落在离我几步路远的田埂上;各处的菜籽花儿那么炫目、新鲜。而到了上午10时,田埂草地上的露水,还是那么丰厚湿润,宛如多情的恋人的嘴唇,使我在这样的对季节的欢喜之余,又平添上一层无言的感动。
再说回到倪瓒墓前那老头,把挖土的锄头在脚底下松一松,指着他身边那一座寺庙的大院墙说。“那边有一个……名字叫泥英的人,就那边——”
三
我后来才知道,这一带很多乡民,都把倪瓒的名字读作 “泥英”。读这一名字时,老头脸上有一种十分恬淡、亲切的表情,仿佛他提及的墓主名字,是他儿时的一名小伙伴,或同一家庭的亲戚。
“泥英?”我偏过头。“……你说哪里?”
因为他用手指的地方,我只看见一座巍峨高耸的寺庙。
那寺庙叫 “芙蓉禅寺”,有新修的 “大雄宝殿”和 “长生殿”两部分。庙的整个地基面积宽阔、气势很大。原址肯定更加辉煌,大概后来被毁了,近两年则刚重建。
我离开老头挖的坟坑,往山脚外的空地上退去。我只约略退出五六十米,就看到了当时实际上已经在我身边的画家的墓园。
一圈庭园风格的、平实的围墙,沿芙蓉禅寺的一侧和山下的树林蜿蜒向上,砌成一个林木葱茏、气氛静穆的墓园。园中约十步路进身的墓道、台阶、碑铭和半圆形坟墓。站在墓园外的空地上看,竟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宛如晴天霹雷,山洪喷泻——一泻千里……
我简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得晕晕乎乎。我说不出我的心情是感恩、幸福还是悲戚!我本以为这山也和江南其他乡间的很多山麓、荒冈野岭一样,遭了 “现代化农村建设”的殃祸,被推土机挖没了,挖空了。倪瓒的坟和尸骨,大概也如很多逝世乡民的野坟场下场无异,早已零落成泥,不知所终。我想不到这样好的墓园竟真的保全下来,而且弄得这么齐整、幽雅、体面、古朴!一整个古代田园的气息就这样扑面而来,藉着一名江南大画家馥郁芬芳的心跳;藉着他生前的那种枯索、荒寒的画笔;那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③的高士风度。我当时毫无准备的心情,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像家中忽然来了一位令我仰慕多年的贵宾——而自己还披着上衣,汲着拖鞋,坐在床沿上。
——我被漫山遍野绚烂的野花,撞了个满怀。
首先,我不能够就这样子莽撞地走进去。我必须先扣上衣裳的钮扣,把鞋子换好,洗个脸 (镜子是来不及照了……)。把隔夜的手脚和睡眼惺松的模样弄弄干净妥贴,然后,我发觉我在墓园的大门外面做深呼吸。我想到了我的两只手是空的,于是返转身,到田埂山坡上去寻些像样点的花草。幸亏今天来得及时!清明节还不到——我心里想。
我定了定神。
我就这样跟生逢乱世的大画家在僻静的山野晤面了。
倪瓒在著名的 “元四大家”中的地位,有点像早期印象派中的塞尚。无论做人的品格以及其绘画作品的独特方式、对后世的影响,都跟那名居住在埃克斯镇上的法国人十分酷肖。倪瓒墓前的芙蓉山,也等同于塞尚故乡小镇上后来以画家的同名作品闻名的圣维克多山。两者都是供其主人不断临摹学习的对象,他们都有同一观点:伟大故乡生活的艺术表现力;同一绘画的基本母题:创世的奥妙。两位画家在世时的生活方式也很相似,在大自然怀抱中度过了多年不问世事,冥想式的隐居生活。
这两座山,一个在欧洲,一个在遥远的亚洲,相距万里,却通过自然奇幻的造化、艺术的灵感,而在各自的民族历史之间唇齿相依,心心相印——我不知道欧洲的那座芙蓉山是否已被地方乡镇的挖土机采挖掉了大部分;我只看到,亚洲的圣维克多山,已陡具空洞的山壳壳,在不到20年时间里,仅剩下了一副被挖得面目全非的山林的表层……
现在的游人再来到倪瓒墓前,来到芙蓉山下,那山的样子,就好比一只肉的主体已被啃吃净尽的苹果——只剩下了一圈四周耷拉下来、松松垮垮的苹果皮了……
没有这只苹果,我们怎么有石头砌房造屋!——工人们说。
我是一路啃掉了数不清的苹果来的,岂在乎眼前这区区的一小只?——嵌到岩石缝里的那些炸药凶巴巴在说……
四
倪瓒墓的面积,是一般江南人家两三个天井的大小。墓园大门口原有两扇漆成暗红色的原木栅栏,现仅剩左边的一扇,故墓园大门看上去始终半开半掩。大门进去,地面为竖砌的青砖地,铺成菱形图样。墓道两侧,是一长排女贞树篱墙隔开的种植松柏花草的园圃。左右分别种植九棵共18棵松柏,以每行3棵的行距依次往前排列。但墓台的右首已有两棵松柏枯死,只剩下枯木的树桩。庄严肃穆的墓台两侧,种着画家生前嗜好的江南的竹子。墓园深处轻风摇曳,蜜蜂的 “嗡营”声在这个季节环绕耳畔,气氛十分恬淡。从地上的印迹看,一年四季前往谒拜的人也寥寥无几。而从地面上升到墓台有三层俭朴式样的台阶,登上台阶,一块年代并不太久的青石墓碑耸立眼前,上书:
“元高士倪瓒之墓”。
七个苍劲大字——没有任何其他的碑铭文字,没有日期,没有碑文落款。
我绕着坟冢走了一圈。圆肚形水泥砌成的墓冢上端草色已泛青,闲花野草,点缀其上。旁边的竹林则显得有些矮小稀落,似乎难以形成寻常乡间竹林风声的规模。但青翠的竹头叶子却一片片沐浴在暖热的春阳下面,相互轻擦抚摩,依然是一派故人还乡途中使人眼热的古朴景致。
著名的 “元四大家”中,另有一家我去过的墓地,是在常熟虞山脚下的画家黄公望的。那同样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对一颗古代心灵的朝谒。那墓地有一股跟整个大小逶迤的虞山相称的伟岸气质。墓道的台阶层数、长短规模,也要比倪瓒的多而大出数倍,使得虞山脚下的那颗心灵,有一种沉吟良久的男低音气质,显得格外博大精深、古朴庄严。所不同的是,黄公望先生的墓没见围墙,整个墓台直接跟周围山麓郊野融汇成一体。站在那上面四处远望,周围层林尽染的乡野风景,仿佛仍握在画家持笔的手中,仍是一幅无限永恒的中国江南田园的漫长画卷;一幅悠远的男耕女织图。这大概也是画家在九泉之下愿意看到的、始终凝望到的罢。站在黄公望墓的虞山脚下,你能自始至终,冥冥之中感觉到空气里有一双画家凝视着的眼眸,那么诚挚、和善地凝视在这天地之间。踏上此条墓道的每一名游人——都能感觉到那一双神秘眼睛的凝眸。倪瓒的墓呢?看的成份也同样幽僻旷达,或者更隐秘挑剔些,但除此之外,嗅觉和听觉的成份则增多了。
顶空固相微萃取(HS-SPME)装置、DVB/CAR/PDMS(50/30 μm)、固相微萃取纤维头和SPME采样瓶,美国Supelco公司;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型号7890B-5977A,美国Agilent公司;Milli-Q超纯水系统,美国Millipore公司。
墓园的气息——在建筑上的体现——相比黄公望,似乎更强调了画家生前所居幽迥绝尘的清闷阁那江南 “小桥流水人家”的乡野背景。它一方面溶于乡间田野;一方面又以围墙和醒目的门楣式样独立于其中。因为所倚靠的芙蓉山山体并不巍峨,墓园又筑在山脚小坡上,故云林先生的墓,有一种似在山中又不在山中的超然飘逸之气。在建筑上,则强调了门楣、围墙、墓台三位一体。在墓园之外,它强调了乡村、我 (倪瓒)两者的关联,它比黄公望的墓看上去要更舒适,更像一座私人憩息的庭园,一个秘密的梦境——又与其主人一生悠游其间的江南农村紧密相连,犹如孩童紧紧依偎在母亲的怀抱……
“三十六陡春水,
白头相见江南。”
——王安石诗
死后葬在这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中国乡村的心跳,听到江南历朝历代风土人情,秋天的碧树落英,春季的莺飞草长;或鸟雀啁啾,或月落乌啼……他离他生前泛舟太湖之畔,泊岸于荒村野郊的那只小船并不遥远。仿佛远远的山脚底下,公路旁,村子里 (山下一村名“王巷”)吹拂而来的和暖春风,仍饱含有画家生前的墨意诗情,他的 “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倪瓒语)。他仍听到乡间手艺人的箩筐声在深巷的墙边上轻擦而过;听到吹笛人在遥远晚风里的一缕唇音!……谁家出殡的气息在粉白的土墙上留下太阳光的烘热。春风吹来,在碑石表面铭刻的姓氏笔划上停了一停……
整座墓园,可用 “闲寂”两字来形容:闲寂的后面,却又深藏着雅致。我抱了侥幸一试的心情,从田埂上采来一束米黄的雏菊,又到别的田里拔了象征性的两棵菜籽花,拿来放到了这名艺术家的墓前。可以说,那天下午,我在墓园周围能够找到的花,全找来了,田间还有一种风中颤巍巍的蓝色小花,因为其茎杆太过短小,我便放弃了采撷的念头。我敢说,从未有人拔了油菜花,作为献祭的鲜花放在任何形式的死者墓台上,在大画家倪瓒这里,我则开了先河。他不会欢喜我的主意。他那举世闻名的鼻子,一定不能习惯我手里头那束太过朴素的花。此刻,他脸上或许将有嗔怪鄙夷的表情——想象至此,我不禁微微一笑,在那清寂、荒凉的墓园台阶上坐下来,点了根烟。
“产于荆蛮,
寄于云林,
青白其眼,
金玉其音。
十日画水五日石而安排滴露。
三步回头五步坐而消磨寸阴。
背漆园野马之尘埃,
向姑射神人之冰雪。
执玉拂挥,于以观其详雅,
盥手不悦,曷足论其盛洁。
意匠摩诘,
神交海岳,
达生傲睨,
玩世谐谑。
人将比之爱佩紫罗囊之谢玄,
吾独以为超出金马门之方朔也。
——张 雨:《云林逸事》
五
我离开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穿旧军装的老头仍在墓园旁边的山脚挖土。挖出来的山土,看上去比田岸头里挖出来的颜色要红,深重许多。“那泥英的坟看见了吧,泥英的坟?”我朝他点点头。看来附近一带的乡下很少有人知道倪瓒的画名了。先前我也问过那老头。问的时候,说了 “画画的、大画家”之类的话,可是他无动于衷。我也曾爬到高约五六十米的芙蓉山头,在尚未完全被夷为平地的山脊头上朝下面看。不知为什么,在这一大片荒凉凄惨、被人们活生生地一铲铲用机器吞噬掉的山麓各处,我都看到倪瓒本人近乎于狰狞鬼厉的画笔墨迹。那犬牙交错,仿佛遭鲨鱼牙齿咬了几口,咬碎了的山体和山脉竟像极了画家生前苦心旨意了一辈子的中国古代山水画——那里面的写意的瘦石、山岩、西风古道……整个芙蓉山的中间主体,都被基本上挖空了;被炸药炸开之后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宛如渺无人迹的山谷,谷底下这里那里又积起一层层铁锈红的黄水,像是地底棺材里渗出的血、腐水。人们兴师动众,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这山地上挖开这么大一个坑,似乎是要给复活的丛林恐龙、或其他巨无霸怪兽预备下一个生育孵蛋的窝巢。从那可怕的山头下来,我再一次地眺望倪瓒墓园、右边的寺院、山野上一个个碑石错落的野坟,并向挖土的老头喃喃地道着别。我听见围墙另一侧的禅寺里飘来阵阵风铃声,更为这春日的暮晚平添了几份幽冥的清寂萧瑟。
“群必求同,求同必相叫,相叫必于荒天古木,此画中所谓意也。”(恽南田语)
斑驳的夕阳此时照射过来,透过几丛青竹叶子,在墓台四周投下一团团细碎的光影。油菜田里的仿佛刚出炉、熔化了的金箔似的光闪,也渐渐黯淡下去。这样的油菜花,墓园大门口空地边上,就有十分艳丽的一大垅,盛开着,摇曳着,迎风招展。
这墓园有内外两景,我也许忘了说大门口的门楣式样。那是一个矗立着的、十分俭仆乡气的砖砌门楼。没有其他的砖饰,惟门楣处用显眼的白石灰粉刷过,并在上面用墨笔题写了墓园主人的姓名。
这样一来,如果不看院内,先看外面,从公路上沿小路,或者贴芙蓉禅寺围墙脚跟蜿蜒前行,来到墓园的正门,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这肃穆墓园的样子和门楣上几个黑体大字:“元高士倪瓒墓”——以旧式的排字法从左至右排成:
“墓瓒倪士高元”
字要比里面的墓碑上少了一个。字体的书法也稍有出入。门楣书法更显圆润古朴,而又不脱飘逸气象。门楣右上首一行小字的落款为:
“廿一世裔孙倪小迂敬书”。
夕阳的光斑。
大门右侧的围墙上分别镶嵌两块石碑,一块是 “无锡县人民政府,1984年10月立”;另一块则是 “江苏省人民政府立”的,后者年代较晚,但碑石较为讲究。
在无锡县立的碑上,有一个有趣的文字说明:“时代:元”
仿佛,倪瓒墓碑和门楣上首书的汉字 “元”字,不足以说明艺术家生平年代似的,只有到了县人民政府不久前刻写的碑上,艺术家生活的年代才得以真正被认可,且其中的 “年”被偷换成了 “时”——时代。
一个多么时髦新鲜的说法啊!
墓园的门楼、书法、庭园式样,与周围荒山野岭相映衬,显得格外俭朴庄重,流露出一份小小的抒情次序;一种不太显眼的古色古香——略带挑剔的忧伤,大度而荒凉的韵味……
那书法,那刻写在褪了色的白石灰粉底子上的一行墨迹——我频频回过头去观赏——蓦然觉得——大概也就是倪瓒先生灵魂的笔法了……一种写意的个性,一种深谙江南之美的悲凉命运的洞见之体现了——
远远地屹立在那山脚下面。一个遗世独立的声音的墓穴。
六
“风雨萧条歌慨慷,
忽思往事已微茫。
山人酒劝花间月,
秦女筝弹陌上桑。
灯影半窗千里梦,
泥途一日九回肠。
此生传舍无非寓,
漫认他乡是故乡。”
——倪瓒 《风雨》④
① 《心印》李维琨译,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② 《清閟阁全集》卷八,第400页。
③陶渊明:《桃花源记》。
④ 《清閟阁全集》卷五,第239页。
2001年秋
责任编辑/麦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