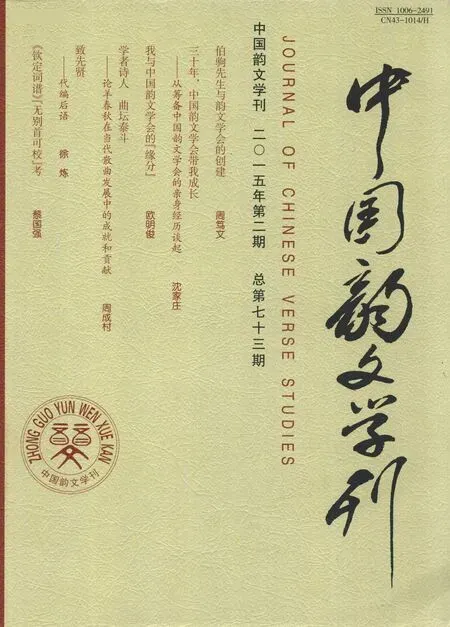群体书写及词境拓充
——论晚明女性词人及其词史意义
余 意
(东莞理工学院 中文系,广东 东莞 523008)
群体书写及词境拓充——论晚明女性词人及其词史意义
余 意
(东莞理工学院 中文系,广东 东莞 523008)
晚明时期女性词人大量出现,呈现出群体化存在特征。群体化存在不仅改变女性词人的精神气质,具有名士化倾向,也改变了女性词人以往个体书写的模式,进而改变了女性词的整体面貌。对于作为整体意义的女性词人,晚明是书写状态从个体进入群体的历史时期,是女性词史的重要发展阶段。
群体;晚明;女性词;新境界;词史意义
邓红梅《女性词史》“把女性词的发展轨迹描述成一段花史……女性词史与一切事物的历史一样,经历了由初生——发展——繁荣——衰歇的过程”。的确如此,词在早期,由于产生于歌楼舞榭、宴饮享乐的环境之中,各方面的条件限制了女性参与到词的写作中。那时,女性参与到词的过程多是歌伎,她们以其艺术才能将作为文字状态的词表现为曲子状态的词。随着词在现实生活领域的扩大以及士大夫“以诗为词”的出现,一些士大夫家庭对于女子教育的开明,逐渐出现了诸如李清照、魏玩、朱淑真等闺阁词人,但女性的词写作尚不能称之为繁荣。金、元时代,女性词人寥若晨星,到明代,女性参与词的创作人数逐渐增多,但各个时期仍然是不平衡的,元末明初,没有女性词人记载;永乐到正德时期,仅仅出现了2位女性词人;嘉靖时期突然相对增多,出现了19位女性词人;特别是到万历时期以至明清之际,女性词人数量与前期比较不啻井喷,竟高达322位,犹如拔地而起的峰峦,成为女性词发展史中的奇观。关于清代女性词,张宏生先生以“繁荣”概之。如果以历史连续性来看,万历到明末这段时期的女性词人增多,实则是清代女性词繁荣的前奏。张宏生先生认为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造就了许多世家大族,生活在具有丰厚传统的文化氛围中,使得女作家的出现更加具有普遍性”、“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为女子创作提供了鼓励而不是扼制”等两个方面造就了清代女性词的繁荣,从外部上来看女性词人的生存环境,万历直到清代,确实如此。但认识到这一点似乎还不够,因为万历之后的女性词人不仅人数大量增加,而且女性词整体风貌出现重大变化,外部原因的寻索只能解释前者,而不能很好地解释后者。为此,我们有必要还原女性词人创作的具体环境以及追问她们作词的动力,发现这些人数众多的女性词人的存在并非是松散、自发的,虽然处于在强大的伦理规训之下,她们没有像前代的女性各各被家庭、社会分隔阻绝于深闺大院,即使真有那么一些文学女性发出声音,其中多不免在无意识中呼应着既定的伦理规训,孤立存在的文学势力被化解于无形。然自明代中后期迄清代,主要在文化较发达的江南地区,开明的文化态势使得家庭内部女性之间,或者是同一地域不同家庭的女性聚合于一起,不再孤单地局限于家庭之一隅写作,而是群集到一起,进行文学活动,形成了文学群体,以群体的力量改变着先前的文学地位以及文学维度,词的创作不再是松散的、不再是自发。对于她们形成的群体现象,学界已有关注。但本文并非重在清理这段历史时期有哪些女性词人群体,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关文献理解晚明女性词人的群体组织方式对她们整体气质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创作的新境界。
群体是类人群的组织方式,也是某种活动的实施方式,因此群体方式必定显现出不同于单独个体的表现特征。以群体组织起来的明代女性作家与前代迥乎不同的表征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作家个体因文学交往如和答、酬赠等形式关联到一起而进行创作,我们不妨称之为“群体书写”;而前代女性作家因缺乏女性之间的文学联系,文学创作生成于个体的孤立状态,我们称之为“个体书写”。由此我们认为,明代是女性作家从“个体书写”进入“群体书写”的分界点。当然,在正常状态下,一般作家创作有时是纯“个体书写”、有时则是“群体书写”。但在古代,被伦理规训束缚的文学女子,一直处于“个体书写”状态,个体的人生、文学等经验因缺乏声气相求而呈现单一化写作;晚明以来女子“群体书写”方式的加入,使得她们跳出独自封闭的狭小圈子、构建一个同性别的文学世界成为可能。这些对女性文学史而言当有特别的意义。
女性词人创作:从个体独白到群体书写
词自晚唐、五代从民间步入文人化轨道之后,因当时演唱环境的规定,男性文学家多以“男子而作闺音”,词体于是具备了女性特征,成为最利于女性书写的一种文体,但词的写作在女性世界中并未得到蓬勃发展。虽然唐、宋、元代,参与填词的女作者不乏其人,她们之中甚至也出现了诸如李清照、朱淑真等著名词家,但若从组织方式来判断,她们彼此缺乏词学关联,每一女词人只是独立地存在于词学发展历程之中,属于典型的闺阁式写作。被割断词学联系的女性词人创作要么自抒其情,要么只能与男性或其夫、或其情人之间互答,词中情感的指向和创作组织方式均表现为依附男性的典型特征。宋代花仲胤妻的两首词《伊川令·寄外》、《失调名·答外》都是写给她的丈夫花仲胤的,花仲胤也写有一词《南乡子》与其妻进行互答,表面上看是夫妻情深,内里仍旧是男女文化关系的象征性表达。这种象征在宋代女性词人的写作中是比较明显的,闺房、庭院、雁字、锦书、罗衣、泪湿等自怜幽独的意象充斥其中,将闺房的孤单、离别凄苦以及对别后重逢的期待与期待不来的失望、惆怅表达得几乎穷形尽相。如“独自临池,闷来强把阑干凭”;“教奴独自守空房,泪珠与灯花共落”;“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这些被隔绝于各自深闺大院的女子,一方面见闻未广,一方面一些仅有的思绪只能投射到所依附的男子身上,对男子的纯真感情与一往情深的倾诉几乎成为她们的唯一存在的价值和唯一书写的形式。这种以静态的自言自语诉说自我的喜怒哀乐,实为个体独白的典型情态。在有些女性词人的周围,或许存在着一些姊妹或者闺中密友,但依据今天所能见到的资料,词人的姊妹或闺中密友似乎都不会作词。即使词人作词以寄,如李清照《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延安夫人《临江仙·立春寄季顺妹》等四首等,词人的姊妹等好像没有以词作相往还,彼此之间缺乏词学意义上的联系,词学创作只是单向度的存在,故她们之间不能视为女性词人群体,仍只能称之为“个体书写”,情感抒发还是的个体独白式的呓喃。虽然,她们这种抒发对姊妹或闺中密友的情感,情感对象与类型已经得到适度的改变,但创作组织方式的单一性决定了她们言语方式依旧属于静态的个体独白抒情。
唐、宋、元时代,女性无法从创作上形成群体,一方面与社会集体意识相关,认为女子作文有妨德行,社会文化开明程度普遍不够,何况是以写爱情等内心隐秘的词,所以她们有的作词也只能偷偷为之,正如宋朝有一卢氏《凤栖梧》“题泥溪驿”前序云:“因成《凤栖梧》曲子一阕,聊书于壁,后之君子览之者,毋以妇人窃弄翰墨为罪。”,将社会意识的开放寄想于“后之君子”,可见当时如果不具备极大勇气,女性是很难参与词之创作中来的。另一方面,当与词体音乐环境的严苛限制有关。李清照以其创作的切身体验写作《词论》,对其前辈词人臧否抑扬,无非是表达了“协音律”和“词语”二者配合之难;南宋末期的张炎,对这个二难问题依然没能解决,发出了“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的倡导。可见,在宋代,作词的门槛很高,既要具备相当高的音乐素养,同时也要具备相当高的文学禀赋。因此,只有极少女子能突破此限制,否则只能被拒之门外。而到明代,虽然一方面理学形成的社会意识强化了对女性的控制,但是在江南地区,特别晚明时期,一些文化意识比较开明的家庭主张女性受教育,如汤显祖《牡丹亭》借虚构人物杜宝之口说出了当时一些殷实家庭的实际情形:“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虽然主观上是夫唱妇随等陈腐观念的驱动,但客观效果上启发了女性的情思。更有甚者主动让女性学习诗词,如沈自征《祭甥女琼章文》:“迨三四岁,口授《万首唐人绝句》及《花间》、《草堂》诸词,皆朗然成诵,终卷不遗一字。”这种有意识的诗词教育,培养了女性的诗词意识和技巧。另一方面,词在明代已经徒诗化,音乐的严苛讲究已被词谱的简便易行所替代,客观上降低了作词的准入条件。于是乎女性参与词创作的广泛度大大超越前朝,终形成明“中后期,女性词人成批涌现,遂构成前所未有的词坛景观。”
与前朝不同,成批涌现的晚明女性词人并非松散地存在,而是借助于家庭、家族以及同乡地域等有利条件聚合到一起,彼此创作时切实发生词学联系。她们发生词学联系的首要组织形式是家庭,如王凤娴、张引元、引庆“母子自相倡和”:王凤娴有《念奴娇》“寄女文珠”;张引元有同调同韵《念奴娇》“春日怀家寄母”;张引元还有《点绛唇》“答母”,吴山《减字木兰花》“思母”,母女以词为媒介交流着感情。类似于这种母女词人的还有黄德贞及其女孙兰媛、孙蕙媛;沈宜修母女等。除了母女关系之外,还有亲姊妹关系,如张学仪七姊妹、章有娴三姊妹等。第二组织形式是家族,如表亲关系,如沈宪英与沈树荣,前者沈自炳女,适叶绍袁第三子;后者叶小纨女,于行辈前者乃后者舅母,于是沈宪英有《满庭芳》“中秋坐月,同素嘉(即沈树荣)甥女”,沈树荣有《满庭芳》“中秋同妗母坐月和韵”、《水龙吟》“初夏避兵,惠思三妗母棲凤馆有感,追和外祖母忆旧原韵”,其中外祖母无疑是沈宜修;顾贞立《南乡子》“和秦表妹”;商彩《虞美人》“赠表妹胡小姐”;张琮《满庭芳》“题柴季娴姨母书回文汗巾”等等。其次,是地域相近、性情相投的女性词人走到一起,如同一地域因趣味相投的女性之间形成词人群体,她们相互酬唱,如徐媛“与寒山陆卿子唱和,……称吴门二大家”。具体到词学中,有朱玉树《西江月·赠闺友》;如黄德贞送徐灿《五彩结同心》“送湘蘋徐夫人归里,时陈素庵相国没塞外”;顾贞立和王朗的词《浣溪沙》“和王夫人仲英韵”;申蕙《长相思》“赠月辉孙夫人”、《锦帐春》“元夕和孙夫人”;归淑芬《卜算子》“和黄月辉韵”、“和湘蘋徐夫人”等等。此外,由于晚明士人对妓女才性要求的提高,善诗词的妓女更受到士人的普遍欢迎,出现了青楼词人。她们由于聚集的邻近以及业缘相近,群体内部既存在竞争,甚至有些不能为诗词的妓女甚至“假手作诗词曲子,以长其声价”;也出现相互交流互答的情况,如王微《忆秦娥·月夜卧病怀宛叔(指同为青楼词人的杨宛)》等。甚至闺秀与青楼之间也经常以词相赠,如黄媛介《眼儿媚·谢别柳河东夫人》等。这些例证表明,晚明的女性词人已经形成群体,这一切的根本基础是家庭,所谓“宗族和姻亲纽带不是限制,它们反而助长了女性社交网的扩展”。而且切实地以群体方式来组织她们的创作活动。从女性词发展史来看,虽然她们可能因为文化习惯过于强大,有时还会抒发对于男性的个体独白;但是一种新的组织方式——群体已经介入到她们生活创作中来。置身群体中的女性,从此有了属于她们的另一世界,她们的写作方式不再仅仅是闺阁化的写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进入女性群体社会化的写作,因此女性主体精神得到舒展,书写气质得到张扬,由此她们也借助于群体顺利完成了女性在词的书写中的另种表述。
名士化:女性词人创作的群体行为及其特质
晚明女性词人已经形成群体,这应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群体内部的词学交往与男性世界相同,无非是赠、和、答之类。如要深入了解晚明女性词的艺术世界,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她们作词时的群体行为以及所透露的群体气质特征。
就家庭、家族而言,《词苑丛谈·纪事四》载沈宜修和其女儿们所进行的一次家庭内部小型的诗词创作会:“天寥又有侍女随春,年十三四,即有玉质肌凝积雪韵,仿幽花笑盼之余,风情飞逗。琼章极喜之,为作《浣溪沙》词云:‘欲比飞花态更轻,低回红颊背银屏。半娇斜倚似含情。 嗔带淡霞笼白雪,语偷新燕怯黄莺。不胜力弱懒调筝。”以女性写女性,没有丝毫的欲望成分,完全是对随春的体态作有趣味的描写。就是这首有趣味的词,引得了姊妹们的群和。这种小型的诗词会并非是偶一为之,而是经常进行,正如沈大荣说,沈宜修“居恒赓和篇章”,赓和的对象固然有叶绍袁,也有沈宜修的女儿们。类此还有商景兰一家,《两浙輶璇录》载:“夫人有二媳四女,咸工诗。每暇日登临,则令媳女辈载笔床砚匣以随,角韵分题,一时传为胜事。”这些小型的家庭内部诗词会类同于男性文人雅集,拈题斗韵,角胜词艺。家族如沈宜修与张倩倩为表姊妹,沈宜修有《浣溪沙》“时往金陵,赠别张倩倩表妹”;如果说,家庭、家族的聚会让词中洋溢着欢笑和甜美,然人生更多的是生离死别,女儿、姊妹出嫁以及意外变故,在前面欢笑、甜美的底色之下,家庭、家族内部以词来纪念则出现了些许凄凉。
就闺中好友而言,她们会经常雅集,或延请家中、或纵情山水,如词人吴琪“时与二三闺友,抚丝桐而弄笔墨,意殊慷慨,不作男女态。慕钱塘山水之胜,乃与才女周羽步(周琼)为六桥三竺之游”;黄媛介(皆令)“青绫步幛,时时载笔朱门”,“入梅市访之,一时传为胜事”。组织雅集之事在她们的词中均得到反映,如黄媛介《长相思》“春日,黄夫人、沈闲靓招饮”;孙蕙媛《兰陵王》“春日邀沈蕴贞夫人登楼野望”;顾姒《佳人醉》“余与表妹林亚清、同社柴季娴最称莫逆。早春晤亚清时,曾订春深访季娴于牡丹花下”等。其中感受刘淑表述得比较充分,《秋词四首答康夫人赠》序曰:“夫人康雪庵,予素仰,丰神若月明云汉,可望而不可亲也。今秋偶偕诸媛过访,倾茗观慧,不减昭仙雅集。独以奇句出示,使予一唱三叹,其琬琰璀璨,真所谓眉飞色舞,旭日升而晚霞坠矣。聊酬数韵,以代击节”。所谓“昭仙雅集”,乃指以叶纨纨(字昭齐)一家为代表的女性聚会,可见在当时女性心目中,这是风雅的标杆。当然,这些闺中好友也会表达彼此之间的想念,如顾姒《小桃红》“询柴季娴病起”等等。
明代青楼女子也经常组织集会,沈周曾经描述道:“南京旧院有色业俱优者,或二十、三十姓结为手帕姊妹,毎上节以春檠巧具殽核相赛,名盒子会。凡得奇品为胜输者,罚酒酌胜者中有所私,亦来挟金助会。厌厌夜饮弥月而止,席间设灯张乐,各出其技能。赋此以识京城乐事也”,或展示各自奇品,类似于文人以艺术才能相斗;“厌厌夜饮弥月而止”,其规模之盛大不亚于文人集会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这是早期明代妓女群体雅集的情况,晚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妓风较前更盛。青楼女子文艺素养的要求提高,自然妓女群体雅集自然比设诗词等项目了。难得的是,晚明有些闺秀与青楼之间也能发展比较良好的私人关系,从而发生词学交往,如项兰贞《鹊桥仙》“七夕,和女冠王修微”等。
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评价明代女性曰:“女性同伴是闺阁内最显著的一种存在。不仅如此,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批评群体在同一邻里的存在,与增加了的同远方之人交换书信和手稿的机会一道,推动了明末清初江南女性社团的激增。这些社团经常采用非正式的诗社形式,他们为来自相同或不相同家庭的女性提供了相聚找乐或更严肃的学术探究的场所。因此,这些女性是栖居于扩展了的社会空间内的。她们与官方所说的与世隔绝之人大不相同。”她们没有与世隔绝,相反女性群体一道构造出一个类同于男性文人的世界形式,与男性文人群体模式类似,女性群体也具有名士化特质。上述家庭、家族内部以及闺中好友之间的雅集正是这种名士化的具体体现。同时,女性群体的名士化特质也得到同时代女性的认同,如明末范文光《望江东·赠金陵顾姬》:“作眉如作兰与字。笔影偏饶香味。多材多趣兼多艺。十载江南名士。 到门词客俱怀刺。宛如良朋相似。图书钟鼎俱环伺。难记起风流事。”后有跋:“姬工诗能书,善作兰。每对客挥毫,顷刻立就。又时高谈惊四座,凡文人墨客之聚,必姬与俱。而姬亦雅意自托,思与诸人入伍,每有文酒会,必流连不肯去,故吾党益重之。每当含毫伸纸,其眼光鬓影与笔墨之气,两相浮动。今年年廿有六,而得名已十年,姬又好楼居,诸友争咏之,故有《眉楼集》行世。”从范文光的这段话中,我们理解当时女性被称为名士应具备如下条件:其一“多材多趣兼多艺”;其二与男性“词客”“宛如良朋相似”,以这两点审诸当时主要的闺秀、青楼词人,均符合。前者“多材多趣兼多艺”,作为青楼女子,除了具备传统所应具备的歌舞等素质之外,还掌握了士人特别是名士所要求的诗词曲赋书画的能力。如赵如燕,“年十三,录籍教坊,能缀小词,被入弦索,予尝得其书画扇,楷法绝佳”。同样闺阁女子,她们崇尚李清照、管道升等文艺素养全面的女性,于是出现了诸如黄媛贞的书画被世“盛传”;徐小淑“善绘事”等。当然,词作为先朝遗留下来的艺事之一,无疑是以“多材多趣兼多艺”为要求的女性的必然选项。另外因为这些文艺女性“多材多趣兼多艺”,使得当时男性文人既艳赏其艺、又钦羡其人,的确做到了“宛如良朋相似”。明代江南开明的文化对于男性意识中的女性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女性与男性之间有词酬赠,难能可贵的是陈沂亲自授朱斗儿诗法;对于女性取得的文学成绩,男性作家往往文、人同赞,不吝美誉,如王伯榖序马湘兰的诗歌:“秣陵佳丽之地,青楼狭邪之间,桃叶题情,柳丝牵恨,胡天胡帝,为雨为云。有美一人,风流绝代,问姓字则千金燕市之骏,讬名则九畹湘江之英。轻钱刀若土壤,翠袖朱家;重然诺如邱山,红妆季布。尔其搦琉璃之管,字字风云;擘玉叶之笺,言言月露。翻庭花之旧曲,按子夜之新声。奚特锦江薛涛,标书记之目,金昌杜韦,恼刺史之肠而已哉”,既赞其文艺才能,又赏其个性风采;如徐祯卿誉孟淑卿之诗曰“直欲与文姬、羽仙辈争长。”男性文人与文艺女性在对待艺术才能等方面,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正是男性世界的支持,文艺女性得以全面发展自身的素养,词作为一门艺事由此被文艺女性群体青睐。
总之女性词人群体及其名士化特质,自然会整体改变女性词的写作趋向与艺术风貌,下面就明代女性词境界的新变化来缕述之。
女性词之新境界及词史意义
女性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群体,群体内部之间的文学交往、文学活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见闻的增长必定塑造了不同于女性纯属个体书写、见闻狭窄时代所不可能有的新境界。首先,因群体的形成多基于一定的血缘或姻缘关系,因而她们词的书写自然添加不同于前朝的一些情感质素,如母女以及姊妹之间的深情厚谊等,以及具有这些情感意义的新意象。如王凤娴、张引元母女的和答词,王凤娴《念奴娇》“寄女文姝”:
花娇柳媚,问东君、正是芳菲时节。帐暖流苏鸡报晓,睡起悄寒犹怯。乌鸟情牵,青鸾信杳,追忆当年别。临歧泪滴,衷肠哽哽难说。 凄凉望断行云,柴门倚偏,空对闲风月。屈指归期无限恨,添得愁怀叠叠。镜影非前,人情异昔,怎禁心摧折。凭谁诉得,一宵满鬓华发。
张引元就此赋《点绛唇》“答母”:
时节朱明,暖风初入芭蕉院。归期日盼。鬆尽黄金钏。 病起南楼,愁睹将雏燕。无由见。白云何幻。十二栏凭遍。
王凤娴有两个女儿,其一引元,其一引庆,均工文学。初,“母子自相倡和”;后引庆早卒、引元出嫁,王凤娴此词即写于此种境况中。然我们谛视文本,发现这两首词的写法基本是传统的,但由于词中植入规定情感指向的特定意象,如“乌鸟情牵”以及“将雏燕”,母女情感在词中得到了实现,而这种情感在以前的女性词书写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如果说王凤娴以及张引元采用旧的表达,只是在局部改进而实现情感品质改变的话,那么杨彻《阮郎归·忆女》则完全采用母亲慈祥的口语诉说对女儿的深切思念:“灯前梳裹带娇啼。牵衣难别离。犹闻兰麝在深闺。几回错唤伊。 风日淡,暮云微。凄凉泪湿衣。梦中惊喜汝来归。觉回依旧非。”词中意象选择以及情感流动完全来自于一位母亲对女儿多年来的观察与体验,特别是上阕完全摒弃了传统的写法,语言不假修饰,母爱自然流露于笔下。喻撚是一位特别的母亲,自己热爱文艺,却规劝女儿勤理女工,调寄《浣溪沙·示女莲》曰:
晓日当窗理绣丝。莫调脂粉莫拈诗。倦余聊倚碧梧枝。 道韫才华妨静女,少君风范是良师。躭诗休似阿娘痴。
如同口语,一派天然。言教讽,身教劝,中有一股谐趣。当然除了母女之间的感情表达之外,还有姊妹之间,即有嫡亲也有表亲,如叶纨纨(1610-1632)《水龙吟》“次母韵早秋感旧,同两妹作”:
秋来忆别江头,依稀如昨皆成旧。罗巾泪滴,魂消古渡,折残杨柳。砌冷蛩悲,月寒风啸,几惊秋又。叹人生世上,无端忽忽,空题往事搔首。 犹记当初曾约,石城淮水山如绣。追游难许,空嗟两地,一番眉皱。枕簟凉生,天涯梦破,断肠时候。愿从今、但向花前,莫问流光如奏。
这首词由沈宜修首倡,时叶绍袁在京城,也许是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一家人分为四地。秋日来临,对于敏感的他们一家人而言,自然凄凉万端。叶小鸾、叶小纨、叶纨纨跟进和作,词作均能选取冷色调景物抒发人生难得圆满的无可奈何之感。当姊妹亡故,她们也会用词表达情绪。叶纨纨早卒,叶小纨、叶小鸾均有悼念词。《踏莎行》“过芳雪轩忆昭齐先姊”其二:
萱草缘阶,桐花垂户。阴阴绿映清凉宇。轻风摇曳绣帘斜,画屏难掩愁来路。 世事浮云,人情飞絮。恹恹愁绪丝千缕。无聊常自锁窗纱,娇莺百啭知何处。
芳雪轩当是叶纨纨未出嫁时的闺房,可是人永去楼恒空,楼台沉浸在幽暗之中。回想往日,词人于斯体会到的人生无常之感,词人全词用语精整,境界精致,词人将传统词中无可奈何的人生失意之感的写作经验整体置换成本性体验。另有沙宛在《江城子·哭姊》:
萧萧庭院暮春天。花带泪,柳含烟。云窗雾阁,笑语十三年。回首床空香钿冷,人已去,梦犹连。 当时争羡共婵娟。明月下,晓风前。秋千踘蹴,携手并香肩。可事狂风吹一夜,摧粉堕、把脂捐。
沙宛在是金陵名妓,通过词意可知其姊当也是妓女。“人已去,梦犹连”,可见姊妹情深。在传统词的意象之中渗入切身体验,自然情深意切。不管是新意象的出现,还是使用旧意象,明代女性词因女性群体由家庭、家族组成,词中的亲亲之爱的情感内涵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造成这一改变的根本原因得归结于女性词人群体的存在。
其次,因明代女性词人普遍存在名士式的精神意趣,所以她们词的美学趣味主张脱俗;同时存在着将她们掌握的一些艺术素养向词领域渗透的趋势。所谓脱俗,即以名士为则,化去女性脂粉气息;就词学传统而言,远女性阴柔气质较重的朱淑真,近偏男性文士气的李清照。如《江南通志》载:孟“淑卿,吴人,工诗词,自号荆山居士。尝论朱淑贞诗云:‘作诗须脱胎化质,僧诗贵无香火气,铅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与语耳。’”朱淑真词典型地体现了作为古代女性的柔弱意识,而李清照词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一些限定,体现了清雅的审美情趣。明代明确以李清照为典型女性词人大有其人,有“写恨盈篇。几度追思李易安”的童观观;有“敢将清照才同比”的汤莱,正有如此追求,她们的词脱去女性静观喁息之悲戚,而具丈夫倜傥跌宕之意气。如叶弘缃《西江月》“三十初度自遣”:“半世和愁混过,而今只剩单单。凭人笑我气酸寒。生小性甘恬淡。 天地尚为屈陷,人生岂得全完。但能守分自然安。且耐炎凉情面。”叶弘缃年未三十而寡,三十岁生日那天她并非表现出悲凄无路,而是用“尚为”、“岂得”、“但能”、“且耐”等语气词书写正视人生惨淡的勇气和力量。她们这种脱去女性本体的抒情方式正是名士化精神意趣的真实展现。李清照给后代女性的启示除了气质的越位之外,还有文艺素养全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孙瑶华》载:“瑶华,字灵光,金陵曲中名妓,归于新安汪景纯。……景纯好畜古书画鼎彝之属,经其鉴别,不失毫黍。王伯榖亟称之,以为今之李清照也。”汤莱甚至在词中宣扬耽沉古董秘笈中的快乐:“图书秘府。丹黄姓字成文谱。月旦攸归。引领春风到竹扉。 郢歌谁首。可许巴人幸列否。逸兴全消。翻愧新诗度玉箫。”同时,女词人将所习得的文艺素养向词中转移,或将画意向词中延伸,明末董斯张评“徐小淑词”:“如中调《霜天晓角》为归舟之作,有云:‘露浥芙蓉茜。翠涩枯棠瓣。傍疏柳、西风几点。行行尚缓。家在碧云天半。念归舟游子,一片乡心撩乱。对旅雁沙汀,盼杀白蘋秋苑。’小淑善绘事,此为画中词,词中画,吾不能辨。”充分肯定了徐小淑的艺术才能以及将词画互鉴的词学意趣。或直接创作题画词,用词来再现画的意趣。
再次,名士作风使得女性群体雅集或选择于私家园林,或选择于名山秀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女性活动的区域,改变了女性对于外界的认知和审美体验。如赵承光《江城子·偕闺友泛舟》:
花香日暖透妆楼。晓烟收。巧梳头。赢得偷闲,联袂荡兰舟。最爱湖山新翠霭,吟好句、漫凝眸。 莺声呖呖柳丝柔。泛金瓯。兴偏幽。为惜韶华,瞬息去难留。还向花前寻韵事,弹一曲、古梁州。
全词采用叙述体,娓娓道来,笔调轻松,游兴高涨,“还向花前寻韵事,弹一曲、古梁州”,情致清雅,与闺房中一往情深、缠绵往复、欲说还休迥乎异趣。另有动辄“无故轻为百里游”(黄媛介《一剪梅·书怀》)的黄媛介,有词《长相思》记“春日,黄夫人、沈闲靓招饮”、《眼儿媚》写“谢别柳河东夫人”、《蝶恋花》“西湖即事”欣赏西湖美景等。其姊黄德贞“少工诗赋,与归素英辈为词坛主持,共辑名闺诗选。二女兰媛、蕙媛,俱能文。”因为在其周围有一群文学女性的存在,所以她写词或载其游玩时美好心情,如《万斯年》“偕女伴游鸳湖”;或写词抒发面对山水而生的历史体验,如《莺啼序》“西湖怀古”;或惊叹自然天地之伟观,如《望海潮》“乍浦天妃宫观潮”、《雨中花慢》“游北山草堂看九松”等。特别是《望海潮》“乍浦天妃宫观潮”:
扶桑缥缈,霓光龙采,金宫砥柱银涛。烽堠星罗,营屯棋布,惊看碧浪迢遥。万叠捲鲛绡。恍琼鼇驾水,白马凌霄。一蹴春霆,千寻秋雪势滔滔。 几回目眩魂摇。羡东南形胜,奇绝神皋。云佩庄严,绣幢屹峙,沧浪昼夜腾骄。浴日海门潮。更昏微胐魄,时共盈消。闻说蓬瀛,鼍梁虚架笑秦桥。
全词将汹涌而至的江潮写得光怪陆离,无一丝孱弱气息。女性词人能有如此胸襟,其词能有如此境界,毫无疑问自然得之于女性词人群体之雅集。由此可见,女性词人之雅集的结果,使得女性词突破先前女性词人多局限于闺房、庭院,情感从执著于闺怨、孤独以及寂寞无聊中跳脱出来,转而关注女性之间的情谊,或体验着山水之间或清雅、或雄浑等意趣。
总之,晚明女性词人依托群体的力量,并且以群体共同参与的书写方式改变着女性词惯有的词学面貌,对清代女性词人参与创作词,实有创风气之先的意义。其一,晚明女性词人群体的兴起,虽然在空间上还只是“丛簇”的群体形态,但正因此,借助于家庭、家族以及地域之间的带动,“丛簇”的女性词人群体形态,带动大批女性涌入词的创作,所以才会形成张宏生先生所描述的清代女性词“繁荣”局面,然张先生仅以词学创作实绩来判断清前女性词,说:“考察清代以前的词坛,我们发现,那基本上是一个男性作家的天地,女词人既少,知名者更不多。”的确,如从个体词人创作实绩来断定,张先生确切道出词史真实。但我们发现,清代的一些女性词在一定的程度上仍旧保留晚明时期女性词的印记,这不能不说是晚明女性对后来者的影响。同时,群体书写以一种竞争的态势影响于创作者,自然从整体上有力地提升了女性词的质量,自然一些才情优秀者被得以凸显。因此,我们说,清代女性词的“繁荣”局面是建立于晚明女性群体拓荒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二,群体参与改变早期女性只是词中欣赏、描述的被动角色,而将表达的主动权回归。成化年间聂大年词《卜算子》曰:“杨柳小蛮腰,惯逐东风舞。学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妇。 忙整玉搔头,春笋纤纤露。老却江南杜牧之,懒为秋娘赋”。杨慎以为:“聂大年尝赋卜算子二首,盖自况也”;严迪昌先生品评该词说:“聂大年此词……表现一个新出教坊的歌妓很有点不甘心任人拨弄的主心骨,新颖处也就在这里”,并说词中歌妓“孤傲”,颇为赏心之论。联系当时女性群体的存在以及由此创作主体意识的高扬,此词还可视为当时妓女已经摆脱依赖士人、回归自我抒发的形象写照。如吴琪《踏莎行·咏怀》:“不愿为莺,何须似燕。也休派作鸳鸯伴。空山松雪半生宜,蒲团梦影随云便。 鹤舞闲庭,香飞画卷。楞严读罢桐阴转。莲冠未解道人妆,羽衣新样梨花片。”前三句抛弃了传统意识加给女性的形象,后面紧接着对自己的理想生活进行描述,完全是站在女性本体意识之上进行创作。的确,女性词的写作经验建立,其中既有体现真挚的亲亲之爱、有朋之情,更有她们的清雅情致以及面临广阔天地时的奇情异想。女性从此依据自我的所思、所见来表达,这不能不说是群体组织以及群体参与带来的功效。
其三,女性写作回归个人经验,组成群体之后的丰富生活使得她们的词学风格多样化。从小世界中的亲亲之爱、赏月吟风,到广阔天地中登临游观、唱酬啸咏,甚而怀古伤世,在在可以潇洒才情,既有温婉之气,也有豪放之风。邓红梅先生评价李清照时说:“她是两宋词坛的‘例外’,而不是‘代表’,她的出现并不能改变人们对于宋代女性文学创造能力的评价。”的确如此,不仅文学创造能力,而且李清照词学风格多样性也是宋代词坛的例外,因为两宋词坛女性词人更多地体现出风格的单一性,这不能不说是当时女性词人普遍“个体书写”的必然呈现。晚明女性词人在“个体书写”之外,还普遍存在着“群体书写”,词学风格的多样性从此不再是例外,这对于女性词史而言不能不说是一莫大的进步。相比较而言,虽然晚明时期没有出现比肩李清照的女性文人,但若以时代的整体文学能力作为评价标准,晚明女性词创作实绩当超过宋代。
[1]邓红梅.女性词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2]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3]田同之.西圃词说[C].唐圭璋.词话丛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唐圭璋.全宋词[C].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倦游录[M].江少虞.事实类苑[C].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 张炎.词源[M].唐圭璋.词话丛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沈自征.祭甥女琼章文[M].黄宗羲.明文海[C].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 张仲谋.明词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9]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0]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2] 高彦颐.李志生.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3] 徐釚. 王百里.词苑丛谈校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4] 饶宗颐.张璋.全明词[C].北京:中华书局,2004.
[15] 沈周.石田诗选[M].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6] 周明初.叶晔.全明词补编[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7] 王奕清.历代词话[C].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江南通志[M].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9] 杨慎.词品[M].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严迪昌.金元明清词精选[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王晓芳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词史”(12FZW039)研究成果之一。
余意(1971- ),男,湖北浠水人。教授。研究方向为词学及古代文学。
I207.23
A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号:1006-2491(2015)02-0088-07
1006-2491(2015)02-008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