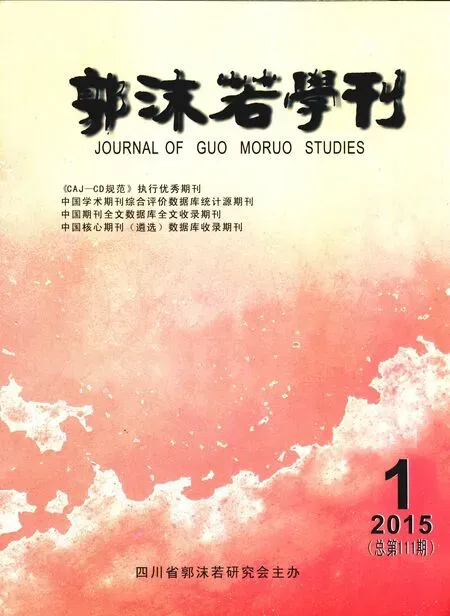《虎符》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
颜同林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现代作家跨越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之后,便逐渐步入不同尺寸的文学轨道。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的生态大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入而全面地影响了作家们的耕作与收获。作为文学体制的内核之一,“普通话写作”成为50年代年代文学的主要范式。从50年代初期开始,伴随着对作家思想改造运动展开的是对方言文学的遗弃、对欧化与文言的清除,全力加速了语言的统一化、规范化进程,这一过程几乎可以概括为朝普通话写作方向迈进。典型事例是,50年代中期召开的文字改革会议、现代汉语规范会议,重新定义了普通话概念,并合法性延伸到独尊普通话写作维度之上,对当时的作家创作产生了最为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不论是面对沸腾现实生活的重新创作,还是对民国文学阶段诞生的代表性旧作之修订重版,都体现了普通话写作的强势覆盖。具体到郭沫若《沫若文集》的出版,就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普通话写作的意图与规约。此套文集一共十七卷,大部分出版于50年代中后期,个别延到60年代初出版,差不多成为郭沫若作品的定本。《沫若文集》绝大多数作品中,“经作者校阅”“全部经过作者修订”是每一卷编辑说明中的常见语汇,普通话写作一以贯之。现就《沫若文集》第三卷中的历史剧《虎符》为例,试图揭示这一历史剧是如何修改的,作者在哪些层面适应了新的文学体制与语言规约。也就是说,《虎符》在50年代的版本校释所呈现出的版本变迁,与普通话写作具有怎样复杂的关联呢。
一
作为一个横跨20世纪不同时代而又不断与时俱进的作家,郭沫若选择的途径之一便是通过文学作品的修订与重版来实现这一理想,因而其作品版本大多比较繁杂,比如戏剧版本便很典型。作者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一直不断地修订、改动旧作,构成其文人生涯的主要侧面。其中有些是主动追求,有些是被迫卷入,哪怕在50年代以后,当他在居庙堂之高时,也均是如此。在他的整个作品体系中,《虎符》虽然在版本上不算最复杂的,但也屡经修改,幅度有大有小,版本校释与修订中传递出的信息相当丰富而且芜杂纷呈。
从《虎符》版本谱系来看,郭沫若于1942年2月2日开始创作,历时十天至11日全部完成,随后在重庆的《时事新报·青光》副刊发表。初刊本面世不久,1942年10月,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其中还纳入了《〈虎符〉缘起》《〈虎符〉后话》诸篇,此版本再版(即再次印刷)过一次。1948年,郭沫若避居香港时审时度势地修订了一遍,由上海群益出版社重新出版,其中包含有作者标注在香港所作的《〈虎符〉校后记》一文,说“此次改版,我把本剧重新校阅了一遍,添改了一些字句。第五幕实在是蛇足,应该删掉。”这一修订过的版本又在1949年8月和1950年2月先后再版。1951年7月,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前身包括群益出版社)根据群益出版社1946年6月纸型重印,繁体竖排,累计印刷多次。从版本来看这次则是从头再来,系根据初版本而不是修订本重印。1951年7月,《虎符》收到由北京开明书店出版中的《郭沫若选集》,也是以初版本收入。1957年3月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三卷),收入了《虎符》,此次是作者1956年7月30日前后在北戴河休假期间亲自修订改定的,修改幅度最大,后来成为该剧的定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沫若文集》第三卷说明中是这样介绍的:“《虎符》是1942年的作品,初版于1942年,现在是根据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版并经作者作了较大的修订编入的。”而这里所说的“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版”恰恰是根据1946年群益出版社的纸型重印。换言之,郭沫若舍修订版而取初版本来进行修订与重构。在《沫若文集》第三卷的《校后记之二》中,郭沫若自己这样夫子自道“这次改版,我又把全剧校阅了一遍,删去了好些冗赘的话。第五幕我也加了一些修改。在第一景的末尾,我终于让信陵君的幻影出现了一次(写作期中本有此意),使如姬最后说了几句话。经过这样的修改,我觉得第五幕依然可以保留。”在此后记中,还有二段短的话,都集中于对第五幕内容去留的辩驳。落实在其他内容与语言表述上,“添改了一些字句”,“删去了好些冗赘的话”是郭沫若对大力修改此剧本的交代,从字面来看作者说得很轻松,一笔带过,研究者一般也忽略过去。但事实上,我们到底该怎样理解这些说法的所指呢?在我看来,具体比较郭沫若当初修改时用的底本,以及修改后的版本,一一对校便可以详细地得知这一情况,了解其“添改”之内蕴,“冗赘”之所指。
正是因为这一想法,当笔者将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虎符》复印一份作为底本,用红笔标识出它与《沫若文集》(第三卷)中《虎符》的差异时,在这一历史还原与搜索的过程中,发现到处是红笔字体的狂舞,而且并不均匀。换言之,郭沫若从内容到语言对此剧修改的幅度是相当显著的,远非郭氏所说的那样轻松与简单,其修改的心态也较为复杂。这一点,可以联系叶圣陶类似的做法与解释。1957年,叶圣陶在编选《叶圣陶文集》(共三卷)时十分努力与自觉。他在前记中是这样说的:“这回编这个第一卷,我把各篇都改了一遍。我用的是朱笔,有几篇改动很多。看上去满页朱红,好像程度极差的学生的课卷。改动不在内容方面,只在语言方面。内容如果改动很大,那就是新作而不是旧作了。即使改动不大,也多少要变更写作当时的思想感情。因此,内容悉仍其旧。至于旧作所用的语言,一点是文言成分太多,又一点是有许多话说得别扭,不上口,不顺耳。在应该积极推广普通话的今天,如果照原样重印,我觉得很不对。因此,我利用业余的时间,诸篇改了一遍。改了之后不见得就是规范的普通话,我还抱歉。”另外叶圣陶文集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以同样方式进行。——其实叶圣陶当时出版文集时的所作所为,在郭沫若那里何尝不同样存在呢?只是前者坦承实际,后者有所隐藏而已。以纸本印刷品而言,《虎符》是一个不足十万字的剧本,但修改之处高达一千多处,修改字数达万字以上;有些段落几乎是重写,有些页面修改的文字超过了原来的文字;没有哪一页纸没有改动过,一次删改三十字以上的部分就有三四十处。早先也曾有研究者发现《虎符》从初版本到群益版共修改了190余处,从1948年群益版到1956年文集本共修改了930余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1953年到1957年短短的几年之间,新中国作家的思想改造、普通话写作的兴盛,是其中的主要事件,思想改造与普通话写作又相互纠缠,难以分离。这一切无疑造成了《虎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版本变迁,其校释及其版本文化充分反映了50年代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文化的嬗变。新中国成立开始的随后几年之中,思想改造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席卷全国,久久不肯停息。“思想改造”意谓思想的洗澡,它作为当时最为流通的中性词,随后却变成了一个让人退避三舍的贬义词。1950年代中期现代汉语规范化运动,促使现代作家进一步对自己过去的创作进行一番清理。“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不同程度存在语言混杂、不甚规范的问题,与普通话写作要求相距甚远。在以上历史大事件中,都不可能离开郭沫若的身影,相反而是他时时处处会成为适应新社会规范的作家们的榜样。譬如郭沫若在思想改造的运动中身先士卒,不但在讲话与报告中决然告别旧我,而且在作品重版中大量修改以便矫正修饰自己的文学形象。50年代初接受毛泽东交代的任务,为文字的拼音化、现代汉语规范化定调宣传,指南针式地参与普通话写作的建构。50年代中期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代作家的文集本,当时仅仅是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等少数作家享有此一殊荣,除郑振铎因飞机失事去世无法旧题新作外,其他几位作家全都顺理成章地按照思想改造与普通话写作的要求大量删削修订旧作,以新的姿态凝定于纸墨之上。
《虎符》历史剧从40年代到50年代,形象地说是此《虎符》不是彼《虎符》,它是以上所言语境中的标本之一。对于郭沫若《沫若文集》这样的繁浩工程,非本人能力所及,也不是这一篇短文所能承载,这里仅仅选择《虎符》为样本,试图作一切片式或以管窥豹的分析,以便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思考。
二
作家思想改造的首要方式当然是作品内容与主题。郭沫若在《虎符》修改中,对作品原有主题思想的适当偏离,对正反人物形象与性格的部分重塑,对历史观念的微调细改,都随处可见,因为不是本文的重点,暂且不予详述。可以肯定的是,思想改造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语言形态变迁来承载,思想改造抵达语言层面,迫使作家改变并接受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就意味着改变并接受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由国语而普通话,便是上个世纪40—50年代之交的主要环节。从压制知识分子语言,到提升劳动群众语言,从漠视群众语言,到力倡标准而规划的民族共同语——普通话,都是短短数年之间水到渠成之事。大面积的语言伸缩与规训,我们通过50年代现代作家忙着修改旧作,改头换面之后以新的语言形态与文学形象重新面世,便可一览无余。当然,这实际也是作家们无可奈何的事,“语言的规范必须寄托在有形的东西上。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的规范主要是通过作品传播开来的。作家们和翻译工作者们重视或不重视语言的规范,影响所及是难以估计的,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提出特别严格的要求。”
郭沫若通过修改旧作企求达到思想改造与普通话写作的双重目的,在诗歌、小说、散文、历史剧中是如此,在文论中也是如此。譬如《女神》,“语言的修改与润色,比之内容变化、结构更改,数量多得多,从首刊到《女神》1957年本,《女神》的57篇作品中,找不到多少在语言上一点儿没改润过的。这些改动,有的是改掉使用不当的,有的是将生僻的改换成通俗易懂的,还有将不流畅的语句改得流畅。”当然,也有一些没有察觉出来,在新版中仍旧保留了旧的不合规范的语汇,个别拗口的句子也还普偏存在。这一种自我修改的过程,表面看是语言的改动,实际也可以看作思想改造的凭条。以同样的眼光来看《虎符》,情况大体是类似的。在重版中,有校正误植、错漏的,如改“攀析”为“攀折”,作动词用时改“槌”为“锤”,改虎符上错金书文字个数“十二个”为“十一个”。为了第五幕的合理性,删去原版第五幕下说明“(此幕应删,姑存原样,以供读者参考。——作者。)”剧尾写作日期中的“三十一年二月二起稿”系指民国纪元,也已改成1942年。在内容上,诋毁秦国的部分得到了删节处理,以“虎豹豺狼”“洪水猛兽”譬喻秦国的语句基本删除了,主观性极强的语气也温和而节制了些。剧本扩展了信陵君台词部分,其主见性、预谋性有所加强,明君形象开始清晰、高大起来,而不是一个言听计从、毫无主见的空洞形象;把中国改定为中原,将偷符救赵的主题进行缩小化处理。另外,标点符号改动大概有五十处以上,主要是把逗号改为句号的最为普遍,这自然与五十年代初新的标点符号使用法的颁布与流行相关。
从普通话写作的角度来看,对欧化的清理,对文言的规避,对方言的限制,均是其中的核心环节。首先,文集本中的《虎符》版本启动了对欧化的清理与整顿。在反欧化的旗帜下,在欧化语言中寻找欧化本身的缺点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消除欧化的直接手段,是将欧化腔进行自我辩识与修改。在具体处理过程中,郭沫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进行:一是对长句进行压缩处理,调整语序,大体符合中国人说话的习惯。汉语中的欧化句特别是复句之中,各分句层层增添,使句子变得累赘,将此类比较拗口的欧化长句改短,调整词序与句序,努力使语言表述规范化与本土化,达到去欧化的目的,这是50年代去欧化的习用法。在《虎符》中到处可见此类方法的沿用。二是对欧化句式进行“清污”,典型的是“是……的”这一句式的大量删改,另外还有“假使……的话,就怎么”或“……的时候”这些句式也减少了不少。在《虎符》中将判断句改为描写句,去掉欧化的“是……的”这一造句结构的就有四十六处,将“是……”或“……的”改动的有二十五处,将“……的时候”改动的有七八处之多。譬如:“我是没有告诉别人的”改为“我没有告诉别人”,“万一有人来的时候,还是以咳嗽为号”改为“万一有人来,还是以咳嗽为号”。从全剧来看,改“假使”句为“如果”句贯穿始终,这样英文“when”、“if”的翻译型句子便大量冲淡了。
其次,对文言的扬弃也在《虎符》中全面体现出来。具体表现之一是将文言词汇删除,改为现代人的口语,包括实词与虚词两类。比如:姊妹→姐妹(箭头前为《虎符》原版语汇,箭头后为文集本语汇,全文均此),黥墨→黥刑,投之→投掷,子息→儿女,顽嚣→不好,乖僻→不好,劫取→打劫,兵士→士兵,人众→众人,拜见→请安,丫嬛→丫头,忖度→揣测到,反为不美→反而不好,在所难免→难免,祖宗所留下的国祚→祖国,来蹈你们的覆辙劫取→来做替死鬼,分工而作→去工作,血食→江山社稷。另外删去表连属关系的文言“之”共五处,如左侧之一半→左侧一半。表现之二是调整语汇,主要是变单音字为双音字,比如:叩→叩头,如→如果,受→遭受,救→援救,恩→宏恩,疲→疲敝。表现之三是将古代的说法,换成现代的说法,显得通俗易懂,便于普及大众。在第一幕开头魏太妃与如姬谈话中谈到邯郸被围的严重困境时,有这样的话“他们竟闹到‘易子而食,析骸而焚’的地步了”改为“没有东西吃,有时吃死人肉,没有柴烧,有时烧骸骨。”另外是将剧中人物的名称全部添加成完整的人名,不但在安排人物台词时标识这样,而且在正文台词之中,也同样类似处理。譬如,母→魏太妃,信(信陵)→信陵君,夫人→平原君夫人,姬→如姬,侯→侯赢,这样带来一个好处是比较清楚人物的言行,特别是遇到两人同姓时不用去费力辨识了。表现之四是历史剧的人物对白大面积地现代口语化。仔细分析《虎符》的语言风貌,大体介于现代语言与浅显文言之间,没有古化,也没有现代摩登语言。虽然布景介绍、戏剧动作、神情暗示,以及第二幕中大梁市民为信陵君等饯行的祝词是文言化了的,但考虑到历史剧的语言观,似乎略有存在的理由;而且郭沫若也没有推倒重来之意,保留了一部分。
再次,减少方言成分。表现之一是删除方言语汇,典型的莫过于删吴语语汇“事体”,事体→事,事体→故事,事件→事情显得比较频繁。这一带有吴语标志的名词,郭沫若在40年代也有删除调整的,但没有清除干净。另外譬如晓得→知道,打救→搭救,等起→等,好多→多少也甚常见。删除的虚词有连词“而且”、“因为”、“但”,副词“其实”、“大概”等。句尾的语气词“吧”、“啦”、“吗”等改动甚多,其中以语气词“啦”结尾的句子改动最多,一共达50余次。表现之二是作者私人性的一些不太准、带有未定型的语汇大量微调,如:整理→整顿,最终→最后,苍皇→仓皇,不只→不止,坐位→座位,援救→救援,带面具→戴面具,那→哪,分→份,像→象,他→它,得→的,好的→好,吧了→罢了,的→地,他们→她们,络续→陆续,攻击→攻打,打战→打仗,便→就,笨→愚蠢,疲→疲敝,窘迫→危险,搅→搞,讲话→说话,好多→多少,利害→厉害,雄壮→英勇,章法→调子,那吗→那么,花子→叫花子,黑狗→黑狗肉,歼灭→打败,乱子→岔子,大口→海口,法术→本领,黑巾→黑纱,恐骇→恐吓,要得→好,狗子→狗,便→就,每每→往往……类似的语汇改动颇为多见。在这诸多改动中,可以看到语言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的变革,比如到了 50 年代,“那儿”与“哪儿”、“底”与“的”、“吗”与“么”就分辨得清楚了,导致郭沫若修改时在两者互换改动就较为频繁。表现之三是大量减少口语表述,大多数句式从舒缓、迟疑的口语状态变成了陈述句或肯定句,干净利落的句子大量增加,有语言体温的感性的句子自然减少。这一变化估计受毛泽东政论性的语言影响较大,当时毛泽东的政论语言被奉为普通话的标本。像“慷慷慨慨地送死”改为“慷慨牺牲”,意思没变,但整体给人感觉语言质地变动显著,句子节奏、伸展程度、语言韵味完全不同了。另外句首表示判断、商量、犹豫、不太确定的语气成分大多被删,“我看”、“真不知道”、“差不多”、“恐怕”、“我是听说过的”、“本来”、“你怕还不知道”等大量被砍掉,便可略知此端。表口语状态的句子还涉及到大量语气词的去留,改动较多的句子结尾是“啦”字与“呢”字,前者减少五十四个,后者减少二十九个,这样撒娇式的、诙谐式的口头语减少了,语言的质地趋于板结与硬化。
众所周知,在普通话写作的建构与实践中,要算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更为复杂,比较语汇与语法两个方面,明显是后者最难处理。口头语与方言比较接近,政论式的书面语则离方言较远。由于去方言化,口语形态则逐渐被淘汰,一方面是句子不断生硬化,韧性减弱,语言形态变得单薄而贫瘠,一方面是有头有尾、语言成分完备的规范句子拥挤到一起。在现代诗中以口语写作著称的于坚,曾称“普通话把汉语的某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这是同一个舌头的两类状态,硬与软,紧张与松驰,窄与宽”。于坚指出的这一状况,其实是很普遍的,在郭沫若50年代的修订中便开始蔓延了。
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郭沫若大量修改的《虎符》纳入《沫若文集》出版,在郭沫若生前,《沫若文集》的诸多作品入集便具有定本的性质,自然唤来学术界的喝彩声。不过,在我看来,像当时的许多同道一样,在新的时代语境与意识形态下,反复修改旧作带来一个潜在的问题,即是改好了还是改错了呢?是改多了还是改少了呢?也许从版本学考察,仅仅是版本本性发生了变化而已。但不容否认,50年代匆促上马的诸多文集出版,存在良莠不齐现象,许多修改也并没有起到积极的正面效应,有好有坏。而且这一修改变化的背后,我们不能不深思其中潜伏的思想根源。每一次改动都残留着思想的痕迹,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后退,都搀和在文本之中。
郭沫若当时创作《虎符》历史剧只用了十天时间,而且这十天时间大体还有应酬与工作,一天大体完成七八千字,可以看出当时郭沫若写作时痛快淋漓的快感,也大体可以洞悉郭沫若的语言功底与文采风流。郭沫若在写作时,一般具有惊人的写作速度,加上作品发表的便利,郭沫若在20世纪上半叶很少大量修改。而纳入文集本的《虎符》,作者大量修改之时实乃1956年7月郭氏在北戴河休假之中。查郭沫若年谱之类资料,这一次他在北戴河只呆了几天,给人一种几乎是在改稿而不是休假的印象。从改笔来看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好坏与起伏。作者在校后记中强调修改过的《虎符》第五幕,其实修改幅度是比较少的,比较而言,修改幅度最大的是第二幕,其次是第一幕、第三幕、第五幕、第四幕。从每一幕内部来看,也不均匀。比如第一幕开头二三页修改不大,随后几页开始逐渐加大了修改力度,到此幕最后又修改不多;第二幕第一景修改少,第二景则大改特改;第三、四幕则是前一半改动多而后一半改动少;第五幕是前后改动多而中间部分改动少。通过这一改动的痕迹,可以适度推测郭沫若在修订时的心态与心情。在50年代繁重的政务活动与政策性的讲话稿写作之外,郭沫若承担着对自身文学历史的重塑,心态时见烦躁,改笔轻重、厚薄之一。从作者文笔来看,郭沫若在50年代以后,因受理性化因素加强的影响,他逐步疏离或不能适应自己原先浪漫而抒情的诗化风格,文笔略显板滞、流畅性减弱,笔端常带感情也在下滑。在我看来,30—40年代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盛年,其语言质地处于巅峰状态,既不似初期那样汪洋恣肆,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尚雕琢,有呆板之嫌。郭沫若在他第一个历史剧创作高潮阶段,剧本中台词相当饱满、充满水分,语言张力控制有力、张驰合度。比如,语汇就相当丰富,语言的修饰成多,形象化成分浓,显得生动准确,与后来在普通话写作指导下的语汇单调、个性语言缺失相比,不可混为一谈。——这一点可能与作者当时对普通话概念的理解偏至有关。譬如表达“说”的意思,原版中就有“讲”、“主张”、“追述”、“吐露”等说法,文集本中就只剩下“说”;原版中有“假如”、“假使”、“如果”、“如”等词汇,在文集本中大多只留下“如果”了。随便举一个例子,第一幕中魏太妃劝如姬不要对魏王不满的台词中有这样一句:“父母纵使是顽嚣,子道不可不讲;丈夫纵使是乖僻,妇道不可不守啦。”文集本《虎符》中便把“顽嚣”“乖僻”全部改成“不好”,语言质地大打折扣,给人语言贫乏之感。
其次,思想改造也好,普通话写作也好,具体落实到版本变迁上,驻足于文学语言上,实际是将普通民众的“懂/不懂”作为一种直观的、普遍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普及”大于“提高”,“求同”胜过“求异”,导致语言的调和、扭曲不可避免,文学语言的丰富与含蓄也逊色不少。一些表达情绪波澜的生动比喻失去水分,名词之前代之以各种形容词、副词,句子平铺直叙,从合唱变成独唱。比如,简直不敢赞同→不敢赞同,虽然意思大意不差,但两者绝不可等同。有些句子意思本身有多重含义,但大多也删繁就简了。譬如第一幕中侯生去魏太妃那儿为女儿请假,谈及到如姬父亲之死,又谈到明后天去扫墓,为以后情节发展作铺垫,原文中如姬是这样说的:“好的,我一定准备在同一天去。”变成“好,我一定一同去。”仔细比较,句子意思实有不同。这一方面的例子甚多,反映出作者对语言表达丰富性、层次性的漠视。
再次,在《虎符》修改中,上下的异文异动较多,使上下文的衔接与连贯性大打折扣,作品中人物为什么这样说,能否接上话,为什么这样接腔,倒让人费解起来。剧本中说话人似乎是前言不搭后语,或者是自言自语不顾及旁人,或者是接话人也没有听懂对话者的意思,这种双向交流的效果出现逆转,有十数处之多。举两个例子,一是第一幕侯生去魏太妃家替女儿请假,与同在魏太妃家的如姬一起说到如姬父亲师昭被害的事,讲到唐雎先生的本领不小,如何用法术教凶手吐露出一切真情,魏太妃接着说:原话是“唐雎先生的本领真是不小,他今年怕快九十了吗?改成“唐雎先生今年怕快九十了吧?”一句话两个信息,删除一个,不连贯。第二幕第二景中,有醉者一、二的对白,因涉及一些低俗粗痞描写而被删除三百余字,附带删除的还有对女兵的一些说法。表面上看是语言纯洁一些了,但原话内容其实可以与朱亥的屠户生活比较,与赵国当女兵的开风气之事相对照,也可以与底层民众喜用性话语的形象相吻合,实在有多重功效。这样大笔一挥予以删除,它所起到的伏笔、对照、俚俗化等语义功能全都消失了,而且此处上下文的断裂也明显可见。
以上几个方面还不是最大的毛病,最大的毛病还在于混杂。因为作者语言思想不能统一,自身的语言能力有延续性,使文集本《虎符》呈现一种不统一的混乱局面。比如,中国换成中原,但也有个别地方保留了,显得前后矛盾;比如“阿姊”“姊姊”“晓得”“行伍”“花子”“打救”“那(表“哪”意)”也时有保留,反而显得杂乱;比如几句口头话?口碑载道,反其道而行之,与全文不统一;比如“团集”、“疯癫识倒”、“偏偏倒倒”生造的语汇也有不少,没有被及时发觉。而较显著的还有,有不少地方句子成分太完备,过分直露,交代过于明白,倒没有回味的空间与余地。——这一过程与郭沫若对文学语言的判断,对普通话写作的认识,以及与他当时在休假期间的心态有一定关联。告别旧我,走向新我这一思想改造过程并不见得非常愉快,走向普通话写作的语言之途也不见得十分顺畅。这一现象并不只是郭沫若修改《虎符》时有,在修改其他作品时也同样存在。以上归结为一点,便是个性化语言的部分消解,语言的原生性、丰富性、芜杂性随之消失,这一消失并不都是好事。思想改造也好,普通话写作也好,并不能真正做到泾渭分明。像鲜花不能存放而人工假花可以长存一样,我们不能仅仅在一个标准上衡量作品,鲜花自有胜于假花的地方。以此看来,《虎符》的修改现象并不值得大声喝彩。这种功过参半的结局,既是经验也是教训。
总而言之,通过50年代郭沫若文集本《虎符》的版本校释,我们可以以管窥豹地瞥见普通话写作思潮的渊源与兴起、普及与深入等方面的轨迹。内容的增删与语句的修饰、调整,都形成特定时代的版本文化。郭沫若靠近普通话写作的努力,以及通过旧作新版来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都有十分丰富而芜杂的时代信息。作为一部获誉甚多的历史剧,《虎符》版本校释传递并负载着这样不可重复的时代风云,是郭沫若留给后人的历史沉思。
[1]彭林祥.郭沫若戏剧版本谱系考略[J].四川戏剧,2009(4).
[2]叶圣陶.《叶圣陶文集》前记[A].叶圣陶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李畅.历史剧《虎符》的版本与修改[J].四川戏剧,2008(3).
[4]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N].人民日报,1955-10-26.
[5]陈永志.《女神》校勘记略[A].《女神》校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颜同林.《女神》版本校释与普通话写作[J].广东社会科学,2012(3).
[7]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A].拒绝隐喻[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