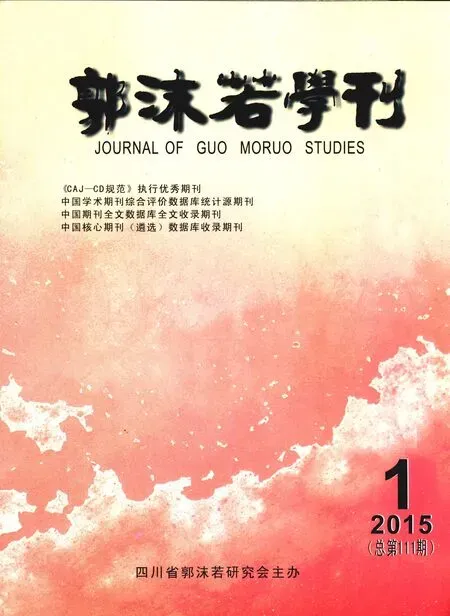王阳明心学与早年郭沫若同苏轼思想的承变关系研究*
申东城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王阳明心学与早年郭沫若同苏轼思想的承变关系研究
申东城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王阳明心学批判继承程朱理学而新变,“其说非出于苏(轼),而血脉则苏(轼)”。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接触到王阳明思想,并赞美、学习、研究王学。郭沫若早年经王阳明间接学习苏轼思想,他们三人在坚持正义、积极进取、创新求善、穷达超然、崇尚自由、肯定自我、弃私求公、个性解放等方面的一致性、相通性、继承性,是不可被忽视和否定的。
苏轼;王阳明;郭沫若;承变
“陆王心学”绍“程朱理学”,又变化出人欲即天理、私心为公道的泰州、龙溪等派,其突显人欲和人性的客观规律,与苏轼“内圣外王”等说一脉相承。王学后经中晚明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发展及清黄宗羲改变而为近代民主思想,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时始精读王阳明心学,赞王学使自己净化扩大彻悟。早年郭沫若学习王阳明成人成己、顿悟哲思、超然物外等思想,可看作他对苏轼哲学思想的间接继承。
一、王阳明心学“血脉则苏”
“元祐之学”中司马光早逝,元祐时二程官位不显,唯苏轼兄弟文著名盛,元祐年间为帝师、知贡举、升宰辅,苏门学士又齐聚京城等,故“蜀学”一度鼎盛。虽后来新党执政者对“蜀学”多斥责打压甚至禁止,但苏氏蜀学仍有非常大的市场,深得人们喜爱。蜀学尤其苏轼哲学思想,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颇深,郭沫若就是受其影响很大的蜀地后学之一。
苏轼之学的思想光辉照耀千古,一直影响到现在。期间,朱熹、王阳明等皆从反面、正面,或多或少接受了苏轼哲学思想,只是他们学而知变,成就了自己学术体系的圆满,但苏轼思想的合理因子,在他们的学说中依然能见,并闪闪发光。正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言:
董思白太史尝云:“程、苏之学,角立于元祐,而苏不能胜。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说,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其说非出于苏,而血脉则苏也。程、朱之学几于不振。紫柏老人每言,晦翁精神止可五百年,真知言哉!”
元祐时,苏氏之学应较二程洛学为重,北宋末“新学”衰落时,在南渡初期,“蜀学”曾一度风靡天下,只是没有立为官学,只能私下相传。“洛学”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始盛,但因毁誉参半,并秦桧执政时程氏之学又被大禁十二年。而南宋孝宗仍对苏轼之学倍加青睐、仰慕不已,称:“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傥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明董其昌所言元祐时程学胜苏恐不确,程学胜苏,应该在南宋中叶朱熹死后,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时。不过,董其昌看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姚江学派对苏轼思想的继承,堪称慧眼。王阳明“心学”的出现,改变了程朱理学的发展方向和繁盛态势,程朱理学走向衰落。朱熹学说的五百年性命已经是多说了,二百多年后,明中叶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就遏制了它独霸天下的步伐。
董其昌说王阳明“心学”“非出于苏(轼),而血脉则苏(轼)”,那么阳明“心学”渊源何处?自身有何内涵特点?又怎么“血脉”苏轼思想的呢?
明武宗正德元年,王阳明因触犯了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龙场万山丛密,苗、僚杂居,使他重新审思《大学》,“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进而自悟到心为万事万物根本,心生万物。与先哲一样,若要“立言”,必须正名,争取儒家的正统地位。朱熹为宣扬己见,首要之事即按己意解释、篡改《大学》。王阳明亦然,其心学正是在批判朱子之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自己立论找依据,就需著书立说,王阳明著《大学古本》,正名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不敢直接正面攻讦朱子,又煞费苦心地撰写《朱子晚年定论》,强言朱熹晚年已逐渐向心学靠拢;又把儒家思想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一番。王阳明在回复罗钦顺、王廷相等指责时,为心学学说的真理性进行辩白:他以孟子拯救天下思想自居,自己独立“格物”新论,虽“包罗统括”了“朱子九条之说”,但因“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与朱子之学并不一样,“格物”新论招致非议是必然的。他认为朱子之学如杨、墨之道一样,是“学不仁不义而过者”,对百姓苍生来说,势若洪水猛兽,需要自己心学来救赎其弊。王阳明自言其著《朱子晩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是为了自重己说。他解释自己这样另立新论,是为了不欺自心,坚持“天下之公道”,天下公道、公学,重点在“公”字上,不以朱熹、孔子等圣贤而“私”,是更朱子之过。我们说宋人包括苏轼正是在疑经、非孟基础上,提出诸多思想见解,也开启了文化高潮和盛世,王阳明怀疑既定几百年的程朱理学,创新自立,这本身就值得赞扬,何况其学说圆通合理,贴近时代发展呢。后世将历代能成全“三不朽”的人归类,独有王阳明与孔子并称,实非虚言。
阳明心学渊源于南宋陆九渊学说,又有发展变化,与陆九渊心学合称为“陆王心学”。陆王心学始于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集大成于王阳明。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同属宋明理学,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和补充。陆九渊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认为治学主要方法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明代方学渐有《心学宗》四卷专谈心学,四库馆臣“提要”是书:“自尧舜至于明代诸儒,各引其言心之语,而附以己注。其自序云:‘吾闻诸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闻诸孟子,仁人心也;闻诸陆子,心即理也;闻诸王阳明,至善心之本体。一圣三贤,可谓善言心也矣。’”认为舜、孟子、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嬗变一脉相承,“一圣三贤”,可谓极尽褒誉。
王阳明虽称赞“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但也批评陆对程朱理学沿袭,“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王阳明反对程、朱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故“理”全在人“心”。“龙场悟道”后,阳明提出著名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本论断,“心者身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凡知觉处便是心”。“心”即“我的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者”。
王阳明反对朱子之说,体悟何谓“格物致知”,“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上级,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大学问》)。格,就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目的是去恶为善;物,就是思想想到的事。进而提出著名的“致良知”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心、理合一,正我们心中不正以归正,去恶为善,就可达到天理,此即为格物致知。何谓“良知”呢?“是非之心,不滤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明明觉者也”(《大学问》),“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良知是道,是人人皆有的“天命之性”。如何方可“致良知”呢?“致良知,不假外求”,“若能向里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为什么内求“自己心体”即可得道呢?王阳明打了个比喻,“臂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心就是树根,一切培壅、灌溉、扶植、删锄的行为或学,都是以心之根的澄明为目的。要想心体通明,就要“致良知”,要去恶存善,阳明称心中恶为“心中贼”,并道出常人去恶的困难,“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王阳明有著名的“四句教”,它是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心“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是无善无恶的,是也需要追求的高境;当心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并着于事物,这种意念就有了善恶差别,是“已发”,事物也就有了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之别,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能自在地感知善恶,因“吾心之本体自然明明觉者”;一切学问修养最终目的即是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正不正归于正,万事万物皆能得其理。当心判断失误,善恶不分时,是因心被私心、物欲遮蔽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努力使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只有回到无善无恶状态,才能格物致知。可见没有私心物欲的心,才是格物致知的本心,这个心才能拥有世间万物之理。
“吾心之良知”就是天理,天理是靠格物,靠自省、实践,即“知行合一”方可得。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以内心去求仁、义、理,方是知行合一,心一,故知行一,不能二。
天理在人心,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的规矩、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方圆,并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王门四句教阐述了心体、性体及良知,在其心学体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指出心、性、理三者的新内涵。阳明所说的心性“至善”,是超越道德善恶的不可执之善。可见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是:“夫退身以全节,大知也;敛德以亨道,大时也;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大熙也”的智慧明理,及“江日熙熙春睡醒,江云飞尽楚山青。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形。未须更觅羲唐事,一曲沧浪击壤听”的静观真乐。这种境界是超凡脱俗,摆脱个人名利毁誉、贫富穷达束缚的自由状态。在这种“随地乐”境界之中,人“流形”、逍遥于万物之间,实现了人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真美善的统一,达到了一种活泼怡悦、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阳明倡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其也旁证了知行合一的真理性,它们至今仍然适用。
王阳明心学如何血脉苏轼的呢?先看苏轼关于心的哲学观。蜀学本体论源自佛、道,又异于佛、道,其化用了佛、道本体为儒家本体,是儒学本体论。换言之,蜀学会通诸家,以儒为本,以儒学去填充儒道本体,是儒、道、佛三家同“一”的、有别宋前儒学本体的新儒学。苏轼《东坡易传》多以老庄思想解《易》,并从王弼、郭象的以老、庄解《易》中国汲取营养。苏轼以《老子》的“一”作为宇宙本体,王弼注《老子》强调“体无”,提出“无心”,“天地虽大,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天地任自然,万物从其真,道性自然,德合自然。“无心”“无为”,为苏轼所法,他在有无间加了个“易”,认为“道”的本质是运动。“水几于道”,老子以水喻道,苏轼亦然,苏轼将物态水性上升到精神层面。苏轼本老子柔能克刚思想,认为水心是“志于行”“无已”的,其终能克刚的原因,是“惟不以力争而心通”,水心外柔中刚,通于本体之道。水心是道的显现,其心性不争,运动不已,可导向至善。水心即是万物,包括人的本性的代表,只有尊重事事物物的自然规律和天性,方可全善至理。天地之间的“贵贱”“刚柔”“吉凶”都是“自位”“自断”“自生”的呈现,自然万物和现象,都是“杂然施之而未尝有择也,忽然成之而未尝有意也”,男、女分别是乾、坤的刚、柔之德“为之”而成。“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矣。圣人者亦然”,圣人的“恻隐之心”“分别之心”,都是“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也”。强调物性自然,心灵自由。自然本真的水心,全善自由的人心,都是事事物物的自行其事,“物各得之”,都是对“道”的自然显现,“道”对万物自然运动的本性有隐形的作用。“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水无常形,遇物无伤,故能自足自由,心通天道。人心处于“无心”状态,就能顺应自然,淡然自若,独立自足。人心若蒙蔽于物,就要求心自达,去蔽正心;
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虽甚,终不能没其正。战于内,以求自达,因其欲达而一发之,迎其正心,彼将沛然而自得焉。
时中也,圣人之于蒙也。时其可发而发之,不可则置之,所以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也。此圣人之功也。
“战于内”,正心自达,去恶为善,格物致知,正不正于正,自然可致良知,阳明之说,与苏轼之学如出一辙。“凡有心者,虽欲一不可得也,不一则无信矣。夫无信者,岂不难知难从哉!乾坤惟无心,故一,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从之也不难”。苏轼舍弃了佛教根本否定心的思想,从本体上肯定心,故事事物物才能在“无心”状态下自由生成和独立自足。“无心”与“有心”相对,若“有心”,事物就不能为“一”,就不能独立自得,只有“无心”,方可得“一”,全性生成。“夫无心而一,一而信,则物莫不得尽其天理”。苏轼“体无”,是通过体静、静观默守方式得以进入的。
苏轼主“无心”,以顺应自然,非庄子的消极虚无、放浪形骸,而是尊重自然天理,尊重人身自由。苏轼认为“无心”同样适用于现实政治,建功立业也要顺性自然,无心而为,“因天下之已能而遂成之”。苏轼“无心”强调物各自得,一物有一物之道,一物有一物之性,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和实践性,非纯粹从理论上探寻,已着眼现实事物。“体无”,实为反观事事物物,“乘天下之至顺,而行于人之所说,必无心者也”,已是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了。苏轼认为自然无心,顺应自然、全物之性,发展到人身上,圣人就可“备位”,人就可成就事功,从而提升人的心性修养和道德境界,实现内圣外王的“道之动”。朱熹由道问学,强调穷物理,认为学习知识非常重要,人的道德水准与知识的增长成正比。可见王阳明心学与苏轼“无心”本体观一样,皆非空谈。程朱理学少有苏轼这种理论、实践的相结合,而陆王心学,尤其王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理论,却与苏轼这种思想有很多一致处。
苏轼倡以静、柔、阴、虚等达“无心”,如水心通天理,且“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无心”是要全顺万物之理,王阳明之格物致知与之相类,即“致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良知求于本心即可,“心明便是天理”(《传习录》上),心若不明,就要去蔽,和苏轼“战于内”、正心自达,去“有心”,求“无心”不是很神似吗?二人皆将心作为本体。去蔽方式,王阳明倡格物致知,通过它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之心,此时的心中之理,就是世间万物之理,就是天理,即公心才是天理。王阳明答罗钦顺时,提到主张格物的关键,是因为其时已“道不见”,并称道和学皆是天下之公,非某个人包括圣人之私,天下之公道、公学,就是客观的、去蔽的本然公心。其与苏轼“无心”称呼不同,本质却相类。陆、王心学之心,与朱熹之心异,朱熹将心分为道心、人心,认为道心是天理体现,人心是气质表现,道心主宰人心,即“心统性情”,陆、王心学认为道心人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二者是一,非二。陆、王对道心、人心之辨,与苏轼类。苏轼的“无心”说,并未将道心人心分视,人心若无心,便可备位成圣人,乾、坤因“无心”,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顺其全性的,包括政治统治,也应无为而治,统治者最好的方式是导引,而非专制独裁。苏轼并不认为道心主宰人心,人若“无心”,如水心一样,就可通道心,二者是一体的不同表述,这种意义上说,陆、王心学的“心”与苏轼思想血脉实同。
人性方面,苏轼之前孟子、荀子、扬雄、韩愈等人性论,提出“性无善无恶”论。苏轼认为人性本于人的自然之性,是“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是恒久不变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得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的。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性无善恶,性动生情,性上溯是命,下沿是情,性、命、道是一,非二。“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情是性的“散而有为”,情整体抽象总称即为性,情是性的具体表现。对于人来说,情是论人性的基础,无情就无法论性,认识全部之情,就可得到性。善恶皆从情上呈现出来,性本身无善无恶,“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自然之道赋予人自然之性,性只能通过情体现善恶,而性本身并无善恶。朱熹主张“心统性情”本张载,朱熹持性善论同孟子。朱子和孟子一样,同将上下级概念错位放置,苏轼曾批评孟子只见到性的“继之者善”,善只是“性之效”,非性本身。朱熹“心统性情”同样如孟子,从哲学层面看,其“心”实为苏轼所言之“性”,其“性善”,实是情的层面。王阳明“四句教”首句就说到“性之本”,“无善无恶心之体”,良知或者良心,“未发”之前,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善恶只是意念动后的产物,是“已发”之后。王阳明之“心”,与苏轼“性”类,王阳明之“意”,与苏轼“情”同。人只有全顺至善,方可至道命,也只有格物致知,方可致良知。
苏轼不迷信圣贤,认为圣人只是备了自然之位,顺应了自然发展规律,是“无心”而然。苏轼正是疑经非孟,批扬雄韩愈,不同流俗,方成就了其蜀学大宗,及独具创新特色的哲学思想。王阳明这方面与苏轼类,阳明认为若道、学不公,可更圣人之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阳明强调“求是”精神,与苏轼主张从实际出发,将理论和实践结合思想类。
王阳明心说在当时以反程朱理学的姿态出现,与苏轼蜀学在北宋当时的标新领异及追求自由思想异曲同工。王学在明代中期以后影响很大,泽被日本、韩国。国内有“王学七派”之称,其中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门人焦竑,作为万历己丑进士第一人的显赫身份,对苏轼学说非常重视,编刻《两苏经解》,并在序中对时人膜拜“一先生之学”(即朱熹理学)表示不满。值得寻味的是,焦竑将苏轼学说专门拿出作为反传统、反专制的载体和武器,进一步印证了苏轼学说异于后来的程朱理学,而“血脉”王阳明心学及王学流派的事实。
二、郭沫若早年思想是经王阳明心学间接学习苏轼的结果
郭沫若集中对王阳明的提及约分散在九篇文章中,但对王阳明生平和思想的阐述,集中体现在为《阳明全书》(又名《王文成公全书》)写的序,名为《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后曾改题为《儒教精神之复活者王阳明》和《王阳明礼赞》)一文,及其四条附论中;另有零星散存于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文中,余皆琐琐。王阳明思想对郭沫若早期思想影响之大,堪称转变性的。郭沫若不仅崇拜阳明的文治武功,更崇拜他的心学思想。郭自认为是阳明的知音,认为“我对于他的探讨与哲学史家的状态不同,我是以彻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普通的哲学史家是以客观的分析去求智欲的满足的”。“彻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是身心两悦、心神两合的体现,是本情自然而发。
郭沫若赞美王阳明的什么精神呢?郭沫若最喜欢王阳明的《泛海》诗,他想将之“当成凯旋歌一样”,与志同道合者“同声高唱”:“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他认为该诗体现了阳明精神:
他(王阳明)的精神是不是如象太空一样博大,他的生涯是不是如象夜静月明中的一只孤舟在和险恶的风涛搏斗呢?但是他是达到光明的彼岸了!我们快把窗子推开,看看那从彼岸射来的光明!我们的航海不幸是在星月掩蔽了的暗夜之中,狂暴的风浪把我们微微的灯火吹灭了,险恶的涛声在我们周围狞笑。伟大的灯台已经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快把窗子推开,吸收他从彼岸射来的光明!
王阳明精神博大精深,正如他临终遗言一样,“此生光明,亦复何言?”他已经到达了“光明的彼岸”。郭沫若所在时代,正处于黑暗蔽日的水深火热之中。就在郭沫若写序的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天下午郭沫若亲自路过现场,他说“我平生容易激动的心血,这时真是遏勒不住,我几次想冲上前去把西捕头的手枪夺来把他们打死”。星月掩蔽了的暗夜、吹灭灯火的狂暴风浪、险恶的涛声,象征社会现实,残暴的帝国主义罪恶应是其一。五卅惨案激发、波动、澎湃了“我国空前的民气”,使得人们认清形势,看透帝国主义丑恶嘴脸,青年们觉醒过来,为全世界大革命而联合奋斗。这正是王阳明精神吸引、启迪、鼓励郭沫若的地方,王阳明为了正义,得罪了刘瑾“八虎”,36岁时被谪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却始终坚持心中理想不变,这是阳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精神的体现,郭沫若赞美王阳明扶病出山,和病魔和自己的“心中贼”搏斗,更与丑恶的环境搏斗。“刘瑾阉宦之群舞弄朝政”,“正义已扫地无存,而他独以铁肩担负,抗议入狱”,九死一生,“他的精神又是怎样的宁静,他的行为又是怎样的沉勇呢?”
刘瑾在王阳明南下路上派心腹拟杀之,阳明在钱塘江畔“把一双鞋子脱在岸头,把斗笠浮在水上,另外还做了一首绝命诗,假装着他是跳在钱塘江里死了”。脱险后,“投身到一只商船上向舟山出发,船在海上遇着大风,竟被飘流到福建的海岸。上面的一首诗(《泛海》)便是咏的这回航海的事情”。王阳明这种宁静沉勇,是孔子以后真儒家精神的真正体现,是他一生自强不息奋斗精神的缩影。正如苏轼解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因为“不息”,天方“健”的,阳明不断进取奋斗,大智大勇,故能一如孔子,实现圣人之道。这恐怕正是郭沫若崇敬王阳明精神的所在。
郭沫若何时何地何接触到王阳明思想的呢?日本豫科一年毕业后,郭沫若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王阳明思想安抚了他的躐等躁进、恶梦频繁、屡想自杀的悲观精神,也治愈了他的心悸亢进、胸部震痛、头脑昏沉炽灼等生理之病:
民国四年的九月中旬,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里偶然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不久萌起了静坐的念头,于是又在坊间买了一本《冈田式静坐法》来开始静坐。我每天清晨起来静坐三十分,每晚临睡时也静坐三十分,每日读《王文成公全集》十页。如此以为常。不及两礼拜功夫,我的睡眠时间渐渐延长了,梦也减少了,心悸也渐渐平复,竟能骑马竞漕了。
身体上的恢复健康是外在的,王阳明对他有什么内在影响,或者说王阳明使得郭沫若思想认识起了什么变化呢?通过体悟王阳明思想,郭沫若精神上“彻悟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从前“眼前的世界只是死的平面画,到这时候才活了起来,才成了立体,我能看得它如象水晶石一样彻底玲珑”。因为眼光、识度的提升变化,郭沫若之前的混沌思想渐渐明朗清晰起来,从而兴奋并指引他看透了庄子的“道”、“化”,“我从此更被导引到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度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期欧洲大陆唯心派诸哲学家,尤其是斯皮诺若。我就这样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从王阳明的开启,透悟了庄子,导引到老子、孔门哲学、印度哲学及欧洲泛神论,郭沫若泛神思想从此趋向定型和成熟,从而指导他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思考及生命实践。这种意义上说,王阳明心学思想对于郭沫若来说,既是良师益友,又是康健身体的力量,更是发现“内圣外王一体,上下天地同流”[32](p35)后,洞彻天地万物万事的动力源泉。
郭沫若眼中的王阳明的人生和思想分别是什么样的呢?郭沫若认为王阳明一生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浮夸时代(三十以前)
——任侠……骑射……词章——
第二期苦闷时代(三十至三十九)
外的生活——病苦……流谪
内的生活——神仙……佛氏……圣贤之学
第三期匡济时代(四十至五十七)
——文政……武功……学业——
他的一生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两个特色,便是:
(一)不断地使自我扩充,
(二)不断地和环境搏斗。
郭沫若认为王阳明30岁以前的生活经历,对于阳明后来的成长必不可少,颇有意义。阳明淑世精神本于任侠气概;武功、学业通过骑射、词章呈现。从世俗功利角度看,是年轻气盛,追求上进体现;从精神层面说,是“自我扩充”的努力使然,因为他“努力想成为伟人,他便向一切技能上去追求。人所一能的他想百能,人所十能的他想千能,人所百能的他想万能”。王阳明异于常人,普通人“迫以事追求,在他所追求的目的尚未明了时只是漠然的一种伟大欲望”。30岁前的阳明,在郭沫若眼里仍然“未能免俗”。
28岁时,王阳明中进士,30岁肺病加剧,31岁告病归养,始在四明山阳明洞中静坐,并四处求仙访佛。郭沫若认为阳明求佛道“动机是出于积极的搏斗精神”,但是”佛氏出而不入,老氏入而不仁”,详而言之,“道是全无打算的活动的本体,而他说的德却是全是打算的死灭的石棺。他的末流会流为申韩的刻薄,这是势所必至。至于佛氏无论它是大乘、小乘,他的出发点便是否定现实,他的伦理的究竟只是清净寂灭。它是极端侮蔑肉体的宗教,决不是正常的人所能如实归依的了”。只有孔子的儒学,“所以异于二氏的是出而能入,入而大仁。孔氏认出天地万物之一体,而本此一体之观念,努力于自我扩充,由近而远,由下而上。横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纵则赞化育、参天地、配天。四通八达,圆之又圆。”儒家思想能出能入,万物一体,人钟灵毓秀,积极进取就可达到内圣外王,这是儒家伦理的极致,“要这样才能内外不悖而出入自由,要这样人才真能安心立命,人才能创造出人生之意义,人才不虚此一行而与大道同寿”。故王阳明终放弃求道求佛,转向从儒家教义中汲取营养,并从中“彻底觉悟”,得出自己的独到体悟:“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道在人心,若想延年益寿,不是从道家外在的炼丹所能及,而是需从儒家思想出发,向人心内在出发进行涵养,这都是阳明心学的基础理论。
郭沫若认为王阳明丢弃了注重章句解释儒家经典传统的歪变凸凹镜,转而拂去暗云和虚像,用平明的镜子重新审视儒家精神。“天空的真相要待能够拨开云雾的好手才能显现,王阳明便是这样的一位好手了。王阳明所解释的儒家精神,乃至所体验的儒家精神,实即是孔门哲学的真义”。郭沫若进而列出阳明思想的梗概表式:
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
公式——“心即理”。
二知行合一的伦理论:
公式——“去人欲存天理”;工夫(1)“静坐”,
(2)“事上磨炼”。
这里列出的的确命中了阳明心学要义,郭沫若称之为阳明思想的全部,也是儒家思想的全部。这里的“理”,即是天是道是本体,它是普遍永恒且变化不定的,是“‘亦静亦动’的存在,静为“诚”,动谓“易”。“这个存在混然自存,动而为万物,万物是它的表相。它是存在于万物之中,万物的流徙便是它的动态”。王阳明从而得出心即理的心本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载著名的阳明解“心”:“先生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心与物同在,“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与理是一,非二。“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已,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这是对程朱理学派注重外在知识学问,反对求诸于心的反驳。“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听言动,即事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可见阳明之“心”,既是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又是至善普遍的道德伦理原则。上文已说,郭沫若认为孔子之儒持天地万物一体观,故郭氏进而得出王阳明“心即理”万物一体宇宙观,深得孔门真义,与儒家哲理万物一体宇宙观一脉相承。
郭沫若认为天理运行“无善无恶,纯任自然,然其运行于自然之中有一定的秩序,有一定的历程,它不仅周而复始,在作无际的循环,而他的循环曲线是在逐渐地前进。它在不经意之中,无所希图地化育万物。万物随天理之流行是逐渐在向着完成的路上进化。”继“道”之“善”,是“天行”,是“至善”,是“无目的、无打算地随性之自然努力向完成的路上进行”。强调的是万物自然本性发展论,“至善”是万事万物自然发展向“全”而成。仁者称之“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智者谓之“良知”,即“仁一”和“良知”是“至善”的一体多面,是性之继的呈现。正如王阳明答郑朝朔“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问所言:“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这便引出郭沫若对阳明“良知”“四句教”的理解,郭沫若认为“无善无恶性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中的善恶,“是相对的善恶,这相对的善恶之发生是由于私欲(即占有冲动)的发生,执着于现相世界之物质欲占以为已有。于是以私欲之满足程度为标准,能够满足私欲的便是善,不能便是恶。这是相对的善恶之所由发生。但这相对的善恶观念阻碍物化之进行,使进行之流在中途停顿,这与绝对的善(无目的无打算随性之自然努力向完成的进行)对待时便成为绝对的恶”。“知善知恶是致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中的善恶,“是这绝对的善恶。知道这绝对的恶是人欲,知道这绝对的善是天理,便努力‘去人欲而存天理’,努力于体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努力于‘致良知’,这便是阳明学说的知行合一的理论了”。去相对善恶,存绝对善恶,通过“致良知”、“格物致知”便可接近至善。正如王阳明云:“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徳,穷理即是明明徳。”去不正归于正,意念不正也要去,意念发处就是行,需彻底根除之,这也属知行合一之范畴。郭沫若说王阳明思想“入手工夫,一方面静坐以明知,一方面在事上磨炼以求仁,不偏枯,不独善,努力于自我的完成与发展,而同时使别人的自我也一样地得遂其完成与发展。——孔门的教义是如此,这是王阳明所见到的”。静坐和实践合一,实为内圣外王的两阶段结合,完善自我,发展别人,这都是王阳明对孔氏儒学真谛的继承发展。
早年郭沫若通过王阳明间接从苏轼那学到了什么思想呢,换言之,王阳明在中间起到了什么样的津梁作用呢?我们认为郭沫若对王阳明思想的接受是复杂的,要之有以下五点:1.去欲存理,求仁至善,“一秉大公”。2.静坐修养,自我扩充,善我善人。3.怀疑创新,兼收并蓄,自得其全。4.心胸光明,坚持正义,积极进取。5.“格物致知”,追求真理,“知行合一”。
我们认为王阳明对苏轼思想的营养汲取,也可概括为四点:1.去蔽存正,全顺至善,“格物致知”。2.顺应自然,“无心”至道,物各自得。3.说做结合,修身养性,“内圣外王”。4.敢于怀疑,独立自主,求是求真。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王阳明在苏轼与早年郭沫若思想之间所起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三人思想继承新变昭然:1.三人都崇尚自然,求公去蔽,正心诚意,不断进取。2.同样重视不囿陈说,求新求变,求真务实,知行合一。3.皆尊儒求仁,修身养性,“内圣外王”,行藏自如。时代不同,尤其郭沫若经历乱世,其五四前后泛神论思想,多导源于王阳明,又颇类苏轼自然观。4.郭沫若后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秉大公思想,也有与苏轼、王阳明思想精髓的相通之处。
总之,三人在坚持正义、积极进取、创新求善、穷达超然、崇尚自由、肯定自我、弃私求公、个性解放等方面的一致性、相通性、继承性,是不可被忽视和否定的。
注释:
①关于郭沫若《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一文的不同写作时间,黄淳浩的郭沫若《〈文艺论集〉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注解写作时间应为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阳明全书》同(“十年六月十七日脱稿”)。订正本作:“十三年六月十七日脱稿。”文集本作:“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脱稿。”另据作者《创造十年续篇》:“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翻译了之后,在箱崎海岸上还替泰东书局尽过一次义务,是替《王阳明全集》做了一篇长序。”黄淳浩认为该序就是《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一文,此说较合理。郭沫若在该文中说他最初接触王阳明是在民国四年九月中旬,即一九一五年郭沫若二十四岁时,而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堪称郭沫若从泛神论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换的界碑。换言之,至少从接触王阳明思想到撰成王阳明文章的近十年时间内,郭沫若对王阳明思想是持赞美和接受态度的。这十年时段正是郭沫若早年泛神思想形成发展,后又苦闷彷徨另寻救国救民思想道路的关键期,之后他埋首“水平线下”,在实践中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大变自己早年思想。故本文定义王阳明心学对早年郭沫若有影响,且由此去看待评价郭沫若对苏轼影响的接受,应较客观中允符合实际。
[1](明)沈德符.紫柏评晦庵[A].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M].中华书局,1989.
[2](宋)苏轼.东坡全集·宋孝宗赠苏文忠公太师敕,文渊阁四库全书[M].
[3](清)黄宗羲.“江右相传学案九”之《征君章本清先生潢》[A].明儒学案·卷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M].
[4](宋)陆九渊.“书”之《与吴显仲》[A].象山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M].
[5]“江右相传学案九”之《中丞宋望之先生仪望》[A].明儒学案·卷二十四[M].
[6]《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一之《絜斋家塾书抄》“提要”,《永乐大典》本。
[7](宋)陆九渊:《象山语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心学宗》“提要”[A].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六[M].浙江廵抚采进本。
[9](明)王守仁.“文录”之《与席元山》[A].王文成全书·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M].
[10]“语录三”之传习录下[A].王文成全书·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M].
[11]“文录四”之《紫阳书院集序》[A].王文成全书·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M].
[12]“语录二”之《答顾东桥书》[A].王文成全书·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M].
[13]“语录二”之《答陆原静书》[A].王文成全书·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M].
[14]“文录一”之《与杨仕徳薛尚诚》[A].王文成全书·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M].
[15](清)黄宗羲.“姚江学案”[A].明儒学案·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M].
[16](明)王守仁.“语录一”之传习录上[A].王文成全书·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M].
[17]“语录二”之传习录中[A].王文成全书·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M].
[18]“外集一”之《睡起写怀》[A].王文成全书·卷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M].
[19](魏)王弼注.《老子道徳经上篇》三十八章,文渊阁四库全书[M].
[20]苏轼.东坡易传·卷七,“系辞传上”,文渊阁四库全书[M].
[21]苏轼.东坡易传·卷三,“行险而不失其信”,文渊阁四库全书[M].
[22]苏轼.东坡易传·卷一,“蒙亨匪我求童蒙”,文渊阁四库全书[M].
[23]苏轼.东坡易传·卷七,“系辞传上”之“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和“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文渊阁四库全书[M].
[24]苏轼.东坡易传·卷八,“系辞传下”,文渊阁四库全书[M].
[25]苏轼.东坡易传·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M].
[26]“记十四首”之《思堂记》[A].东坡全集·卷三十六[M].
[27]“保合太和乃利贞”[A].东坡易传·卷一[M].
[28]“论十一首”之《扬雄论》[A].东坡全集·卷四十三[M].
[29](明)焦竑.序[A].两苏经解[M].明万历刻本.
[30]郭沫若著,黄淳浩校.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A].《文艺论集汇》校本[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31]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六卷[M].
[32]彭放编.我的作诗的经过[A].郭沫若谈创作[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中国分类号:C912.1文献标识符:A1003-7225(2015)01-0025-08
*本文系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2012年立项课题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GY12C02,项目负责人:申东城。
2015-01-04
申东城,男,博士后,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文论及巴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