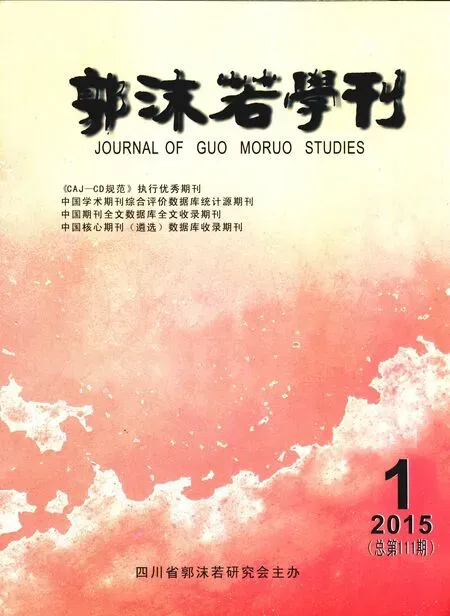郭沫若著译作品盗版本的考察辨析(上)
蔡 震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沫若纪念馆,北京 100009)
郭沫若著译作品的出版,是郭沫若文学活动和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而在考察梳理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的时候,有一个情况特别需要关注,即,郭沫若著译作品的盗版本问题。盗版本书是郭沫若著译作品出版过程中一个相当突出,而又难有定说,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它会直接影响到对于郭沫若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其创作著述活动的历史记述,需要予以甄别、辨析。
一、几则出版启事
1936年5月27日的上海《申报》广告栏登出一则律师启事:“顾苍生律师代表叶灵凤郭沫若警告侵犯著作权启事”。“启事”中这样写道:
兹据叶灵凤郭沫若二君委称,灵凤有著作物……沫若有著作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沫若诗集》、《水平线下》、《橄榄》、《黑猫》、《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银匣》、《法网》、《石炭王》十种,交现代书局出版,《文艺论集》、《沫若小说戏曲集》二种,交光华书局出版。以上各书著作权均属著作人所有,去岁光华书局及现代书局因营业亏损相继停业,积欠本人等版税甚巨,迄今尚未清偿。兹闻有人拟将上开各书旧有纸版私自抵押变卖翻印出版,本人等为顾全著作权蒙不法侵犯起见,为特委请贵律师登报警告,如有人未征得本人等之同意,擅将上开各书用旧纸版或改换方式翻印发卖,定予严究等语前来,据此合亟代表登报警告如上。
光华书局和现代书局是出版郭沫若著译作品最多的几家出版社中的两家。光华书局由沈松泉、卢芳、张静庐创办于1925年,沈松泉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书局在1935年因经营不善而歇业关闭。现代书局略晚一点创办于1927年,创办人为洪雪帆。书局先是设在上海海宁路,后移到福州路山东路171的商报报馆二楼。此时,张静庐、沈松泉等人先后加入,张静庐任经理。1931年,现代书局改组为股份公司,门面也扩大了,但后因经营业绩不佳,洪雪帆与张静庐之间产生了分歧,最终导致张静庐退出书局。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书局因负债无力维持,也不得不于1935年关闭。
两家书局在营业期间之所以出版多种郭沫若的著译作品,当然是因为沈松泉、张静庐与郭沫若之间的朋友关系,他们三人当年在泰东图书局有同事之谊。但这种关系并不能代替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契约关系。两家书局恰在1935年均因经营业绩不佳而歇业关闭。而在此之前,郭沫若尚有多种著译作品正由两书局出版,也就是说两书局与郭沫若之间应该会有一些著译作品的版权、著作权问题,是需要善后结清的。是年9月20日郭沫若有一封致叶灵凤的信,就是谈及与两家书局关系的事情。信中说:
“光华现代事已告一‘段落’否?
现代清单本有保存,但一时难得查出,请你把现代的纸板替我取回,以书籍抵算现款也好,请你费心早告一个‘段落’。
集子可以重编,重排由作家自费却未免便宜了书店。此事留待有相当的书店时再考虑罢。
张静庐愿意替我出全集,只要他改变从前的态度,我是可以同意的。请他提出一个办法让我们商议罢。”
在信中,郭沫若请叶灵凤替他将在现代书局的“纸板”取回,并请叶帮忙将现代拖欠版税的事情了解。但是从上引《申报》上那则律师启事看,现代书局,以及光华书局所存郭沫若著译作品的“纸板”仍在书局手中,叶灵凤未能替郭沫若索回,而且这些“纸板”还有被私下抵押变卖的可能。
“纸板”(纸型)如果被私下交易到另外的书局或出版社,并印制出书,那就是盗版本书了。郭沫若请律师发出这则启事,显然有防备其在光华、现代出版的著译作品被私下交易盗版印行的目的,未雨绸缪。郭沫若这时应该是很注意自己的著译作品被盗版印行的问题了,并且藉在传媒上刊发律师启事,将问题公之于世。
事实上在几年前,郭沫若就发现并注意到自己作品被盗版的情况。1931年8月24日,他在写给容庚的信函中说到,于东京文求堂书店见到北平中华印刷局盗印他的著作,以及被盗名为夏目漱石《草枕》一书中译本的译者。信中向容庚询问道:“前门外杨梅竹斜街中华印刷局系何人所经营,兄知否?该局盗印弟旧著多种,……国人如此不重道义,殊足令人浩叹也。”
再往后,1937年4月29日,郭沫若给上海北雁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委托该出版社追查他的作品《北伐途次》的版权问题。这是他明确就一部著作申明著作权,追责盗版本的出版问题。信是这样写的:“我的《北伐》前委托北雁出版部出版。坊间有一种《北伐途次》第一辑,乃妄人任意偷版。这种侵犯版权的行为,现亦托北雁代表清查,遇必要时自可提出诉讼。此证。”
《北伐途次》是郭沫若旧作的一个长篇自传散文,从1936年7月开始在《宇宙风》半月刊分作十五次连载。连载毕,郭沫若即与《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商议出版单行本的事情,但后来为帮助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孙陵,将书稿交给孙陵初办的北雁出版社出版。然而,北雁出版之前,《北伐途次》即已被盗印出版。郭沫若明确指认了这一本盗版书。
1946年6月14日,郭沫若又就著作权问题,在《联合日报晚刊》上专门刊登了声明启事:
“敝人译著多种,二十年来多被坊间盗印,或原出版者未经同意自行再版或将版权连同纸型转让,或擅自更改书名或著译者名,诸多侵害权益之事,殊难枚举。兹请群益出版社吉少甫君为本人代理,清理所有译著,无条件收回,自行整理出版。请承印各出版家,将收税清算结清,并将纸型交回或毁弃,如承上演、广播,或装载,均请代理人洽立合约。日后如有危害本人著译权益事件发生,当依法请沈钧儒沙千里二大律师保障追究,特此登报声明如上。”
群益出版社是在中共党组织帮助下于1942年8月成立的,以出版郭沫若著译作品为主业的出版社。群益成立后,郭沫若著译作品即主要放在该出版社出版,以前在其它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作品也陆续收归群益出版。这当然会涉及多家书局、出版社,郭沫若刊登这样一个声明,也是广而告之吧。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为防止因纸板的流失,而造成著译作品版权被侵害,即盗印、盗版情况的发生。
上述几则有关出版事宜的启事、声明,都是涉及到郭沫若著译作品盗版书问题的,虽然它们并不能给我们描述出这个问题出现的开始,以及来龙去脉,但我们从中可以很切实地看到郭沫若著译作品出版中所存在着的盗版本现象。当然,像这样能直截了当为我们呈现史实的有关史料都是零散的,而且非常有限,所以,郭沫若著译作品盗版本问题需要做专门的查考。
二、盗版书的出现及种类
(一)盗版本书的出现
郭沫若著译作品盗版本书最初的出现,以及大量的盗版本印行,主要是在郭沫若流亡海外期间。将上海图书馆萧斌如、韶华所编《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中专门列出的“翻版书”(即盗版书)项下的书目,做一个统计比较,从几个数字中就可以看到这一情况。
该书目所列盗版书的印行,起自1929年,讫于1949年。盗版书目总计:
著作39种,55个版本或版次;
译著11种,11个版本;
无出版年份著作6种。
其间自1929年至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归国止)盗版书目总计:
著作27种,37个版本或版次;
译著4种,4个版本。
不考虑无出版年份的几种出版物,在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所出现的盗版书,在著作方面,无论是种类还是版本或版次,都占近到百分之之七十,只译著的种类和版本少于百分之五十。
何以是这样一个状况呢?原因应该主要出自四个方面:
其一,郭沫若的文名在国内文坛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由于他在大革命期间的经历和以被通缉之身流亡日本的现状,给这种影响力格外增添了分量。这从出版的商业角度来看,就是非常好的出版资源。
其二,自1929年2月创造社出版部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以后,郭沫若的著作失去了专门的出版渠道。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于1926年3月,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出版部门,在创造社中后期的文学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此开始,郭沫若以及创造社作家的大部分作品译著等,都经由出版部出版发行。这使得郭沫若的著作有了一个稳定可靠的机构,为其出版发行作支撑。创造社出版部遭查封以后,郭沫若著作的出版完全转入商业出版机构的操作,这自然给盗版书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和很大的空间。
其三,郭沫若人在海外,且行动受限,相对来讲获取信息(出版发行方面)的渠道、方式会比较滞涩,不那么畅通,获取信息的时间也会比较迟缓。特别是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例如,有著作被盗版印行的情况,他实际上会处在一个鞭长莫及的状态。当然这是从制作盗版本的角度来看问题。
其四,应该与中国当时具体的出版环境有关。
国民政府1928年才制订并公布施行《著作权法》。按照该《著作权法》规定,著作物“依本法注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为有著作权”。“著作物之注册,由国民政府内政部掌管之”。注册后发给执照,并刊登政府公报以公告。该《著作权法》还规定,“本法施行前,已发行之著作物,自最初发行之日起,未满二十年者,仍得依本法呈请注册”。按照这一《著作权法》的规定,在当时,郭沫若所有已经出版过的著作,都需要在内政部进行注册,才能得到并享有著作权。
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著作权法》施行前,由出版行业业内行规所保障和遵从的著作者的权力,在该法施行后,必须经由注册登记之后方可得到保障,如若不然,则其著作权即可能被随意侵犯,但却无法得到保障了。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空子可钻。
我们现在虽然无法知道郭沫若在《著作权法》施行后是否为其“著作物”办理了注册手续,但依他当时的身份处境——作为一个被国民政府通缉的政治人物流亡日本——他自己应该是难以,甚至无法去申办这样的注册手续的。曾出版了他的著译作品的出版社是不是可以代他办理“著作物”注册呢?
泰东图书局,虽然还在继续出版《女神》等作品集,但已经与郭沫若没有了新的出版关系。
创造社出版部,《著作权法》刚刚开始施行,就遭政府当局查封。创造社出版部所出版的著译作品,多转到光华书局和现代书局。
光华书局、现代书局在《著作权法》施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出版郭沫若著译作品的主要出版机构。他们应该会重视所出版的郭沫若著译作品的著作权问题。
在已经结集出版的作品之外,郭沫若还有许多未曾编入集子的作品,它们的作者权益如何得到《著作权法》的保障,没有相关的史料可以为我们提供信息。
以上这些情况让我们可以这样推断:郭沫若当时特殊的境遇,使得他的许多著译作品在《著作权法》刚刚开始施行时的出版环境中,反而暂时有了更大的被盗版的可能性和操作空间。郭沫若著译作品盗版本出现的时间,以及其数量变化的走向,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当然,这是不正常的出版现象。
(二)盗版本书的种类
盗版本书并非都是一个面孔,存世可见的郭沫若著译作品盗版本书,大致可以区别为两类:
其一、盗用郭沫若某一作品由某一出版社所出版印行的版本。譬如: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新书店1930年3月20出版(正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由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2月初版印行,3月20日再版印行);
《沫若诗集》,上海复兴书局1936年5月出版(正版《沫若诗集》先后由上海出版社出版部、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印行);
《反正前后》,上海立社出版部1939年3月出版(正版《反正前后》1929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1931年改版作《划时代的转变》);
《我的幼年》,上海全球书店1947年4月出版(正版《我的幼年》1929年4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初版发行,后更名作《幼年时代》,1942年8月重庆作家书屋更名作《童年时代》初版印行)。
比较而言,这一类的盗版本书数量不是很多,但在这一类型的盗版本书中,很可能有一个情况是我们现在所无从查考到的,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因为它是《郭沫若著译书目》所列“翻版书”所没有触及,也是关于郭沫若著译作品盗版所未曾触及的问题,即,由于出版社“纸型”(纸板)流失或转移所可能出现的盗版本书。
前文所提到的两则“启事”,都涉及到“纸型”(纸板)的问题。《申报》上刊登的那则“顾苍生律师代表叶灵凤郭沫若警告侵犯著作权启事”就说到“兹闻有人拟将上开各书旧有纸版私自抵押变卖翻印出版”,然后申明“如有人未征得本人等之同意,擅将上开各书用旧纸版或改换方式翻印发卖,定予严究”。郭沫若在致叶灵凤的信中,特别嘱托叶灵凤“请你把现代的纸板替我取回”。其中所说的,都是在光华、现代两书局所存郭沫若著译作品的“纸型”。后来没有史料表明,这些“纸版”已如郭沫若的律师声明中希望的那样收回了。而从1946年《联合日报晚刊》刊发的那则“郭沫若启事”所言来看,其谓“原出版者未经同意自行再版或将版权连同纸型转让”的情况中,或者就有光华书局和现代书局所存的那些“纸型”。
这种情况表明,如果盗印者利用这些“纸型”,原封不动地(包括出版社名称、版次、印数等等相关信息)印行了这些著译作品集,那意味着从印刷物本身恐怕是难以辨别的,只能从对于某著作集某个版次在当时市场流通情况的察觉来作判断(或者还要结合纸、墨等情况的比对)。郭沫若应该是发现有这样方式盗版的情况,才会发表了那则“启事”,但有哪些版本的书,他没有具体说明,而从如今尚存世的版本书中我们当然也就更无从辨别这样盗印出来的书了。
其二、盗用郭沫若作品、署名,编辑印行的版本。譬如:
《黑猫与塔》,由上海仙岛书店1930年9月15日出版;
《黑猫与羔羊》,由上海国光书局1931年1月出版;
《今津纪游》,由上海爱丽书店1931年4月5日出版;
《沫若文选》,署“请秘馆主选辑”,由上海文艺书店1931年出版;
《郭沫若杂文集》,由上海永生书店1936年10月出版;
《北伐途次》,由上海潮锋出版社1937年1月出版。
这一类的盗版本书数量多,盗印作品的内容、形式也庞杂,基本上都是由盗印者任意择取编选若干篇郭沫若作品而成书。编选的随意性很大,编成的出版物即使撇开著作权不论,其本身也缺乏专业水准,甚至是些非驴非马的东西,像《黑猫与塔》《黑猫与羔羊》那样的本子。
在上述两类盗版本书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盗用郭沫若之名(包括也盗用出版社之名)出版,但非郭沫若所创作或翻译之出版物。譬如:
《草枕》,由上海美丽书店1930年出版。这是一部翻译作品,原作者为日本夏目漱石,是一部小说。该译著署名为“郭沫若译”,并有“译者序”,也署为“十九年五月三日郭沫若序”。事实上该译本是由崔万秋翻译并作序的。
《断鸿零雁记》,署“郭沫若著”,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31年4月15日出版。《断鸿零雁记》实为苏曼殊所著。该书不但盗用郭沫若之名,且盗用了已经被查封的创造社出版部之名。
《文学评论》,署“郭沫若著”,上海爱丽书店1931年4月15日出版。该书所收《新文学之使命》《士气的提倡》《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等文学批评和理论文章,均为成仿吾所作,实为成仿吾的一本文论集。
《苏联短篇小说集》,由上海新文艺书店1932年4月初版,为一部译作,署“沫若译”。正文前有一篇相当于译者序的文字,但没有署名。书中收录爱伦堡、左琴科等7位作家的11篇小说。郭沫若曾有几次翻译过苏俄作家的文学作品:屠格涅夫的诗歌与小说《新时代》、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部分),与李一氓合译的《新俄诗选》,但至今为止所有关于他翻译活动的文献史料中,都不曾记载有他翻译过《苏联短篇小说集》中任何一位苏联作家的小说作品。事实上,郭沫若没有翻译过苏联(包括俄罗斯)文学中的短篇小说。该译著应该是盗用了郭沫若的名义。
《黄金似的童年》,为一本译作,原著赛甫琳娜,署“郭沫若译”,由上海正华书局1931年印行。赛甫琳娜是苏联作家,《黄金似的童年》是其一本短篇小说集。
《野花丛中的恋爱》,署“郭沫若著”。书中实际上辑录的有鲁迅《野草》中《秋夜》、《影的告别》等十篇散文,以及另外六篇散文。该书未署出版社名。
这样的一些出版物,虽然盗用了郭沫若的署名,但因为其所选所印并非郭沫若的著译作品,所以,我以为不能将之归类为郭沫若著译作品的盗版本书,它们只是伴生于郭沫若著译作品盗版本问题而出现的一种出版现象。当然,不妨记录在案。
三、一纸著译书目
1941年,在左翼文化界纪念郭沫若诞辰五十周年暨创作二十五年之际,柳倩整理了一个完整的《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年著译编目》,刊登在1941年11月16日印制的《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刊》上。柳倩当时在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这份“著译编目”是他自己起意整理还是受郭沫若之托,不得而知,但“著译编目”应该是得到郭沫若首肯,起码一些资料是需要郭沫若提供的。北京的郭沫若纪念馆至今仍保存有一份该“著译编目”的手抄稿。刊载于《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特刊》的该“著译编目”原文如下:
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年著译编目——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止
文艺之部(创作)
一、诗歌
女神 (泰东)
星空 (泰东)
瓶
(泰东)
前茅 (创造)
恢复 (创造)
沫若诗集 (现代)
战声 (北新)
二、戏剧
王昭君
卓文君
棠棣之花(聂嫈)
(以上收入三个叛逆的女性) (光华)
甘愿做炮灰 (北新)
三、小说
塔(商务)
水平线下 (创造)
橄榄 (创造)
落叶 (创造)
一只手 (大光)
豕蹄
归去来 (质文)
骑士(曾在《质文》发表五分之一)
四、自传
我的幼年 (光华)
反正前后 (现代)
黑猫 (现代)
北伐 (北雁)
创造十年 (现代)
创造十年续编 (北新)
五、随笔
山中杂记 (泰东)
六、文艺理论
文艺论集 (光华)
文艺论集续编 (光华)
民族形式商兑 (南方)
沫若近著 (北新)
七、其它
卷耳集 (泰东)
三叶集 (亚东)
沫若书简集 (泰东)
断断集(未出)
文艺之部(编译)
一、诗歌
德国诗选 (创造)
雪莱诗选 (泰东)
浮士德 (创造)
赫尔曼与窦绿苔 (生活)
鲁拜集 (泰东)
沫若译诗集 (乐华)
华伦斯泰 (生活)
查拉图斯屈拉抄 (创造)
新俄诗选(与李民治合译) (光华)
二、戏剧
法网 (创造)
银匣 (创造)
争斗 (商务)
约翰沁弧戏剧集 (商务)
三、小说
茵梦湖 (泰东)
少年维特之烦恼 (泰东)
石炭王 (乐群)
屠场 (南强)
煤油 (光华)
新时代 (商务)
战争与和平 (光明)
异端 (商务)
日本短篇小说集 (商务)
四、文艺理论
艺术的真实 (质文)
五、美术
近代美术史略 (商务)
美术考古学发现史 (湖风)
科学之部
生命之科学(一、二已出,三未出) (商务)
社会科学之部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商务)
政治经济学批判 (神州)
德意志意识形态 (言行)
考古学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联合)
甲骨文字研究 (大东)
金文丛考 (文求堂)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大东)
卜辞通纂 (文求堂)
殷契粹编 (文求堂)
古代铭刻汇考 (文求堂)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 (文求堂)
金文余释之余 (文求堂)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文求堂)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文求堂)
石鼓文研究 (商务)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商务)
周易之制作时代 (商务)
屈原 (开明)
隋唐燕乐调研究 (商务)
羽书集
零篇补遗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民八、九有诗未收,小说《鼠灾》未收。)
北伐时代革命军日报(武昌版、南昌版)
创造日汇刊
创造周报
创造季刊
创造月刊
文学杂志
救亡日报
杂文——质文光明
上海立报言林
上海大晚报火炬
东流
留东新闻
改造(日文)
文艺(日文)
日本评论(日文)
这个篇目中有一些内容并不十分准确,也有个别舛误。但总体来看,它应该是已经出版的郭沫若著译作品集至此时(1941年11月)的一个书目汇总。把这一纸书目抄录在此,可以做一个历史参照物——一个考虑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情况的参考文献。
同时,若将这一著译书目与前文所引几则出版“启事”联系起来看,它们实际上能够为我们在考察郭沫若著译作品盗版本问题的时候,从正反两个方向上给予某种提示,或是引出一个参考的线索。(待续)
注释:
①见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11月。
②用铅字排版印刷,要做成纸板(型),一个印次完成后,纸板保存起来可继续使用。
③《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
④见《北伐》,以手迹形式刊载,上海北雁出版社1937年6月初版。
⑤萧斌如、韶华编《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第2版。这是迄今唯一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郭沫若著译作品盗版本书情况的文献资料,故本章讨论到的一些问题会与该书的内容相联系。
⑥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乙编),
⑦其中有若干舛误,明显为误植者,径予订正。
⑧原文作“李霖”。
⑨原文作“泰东”。
⑩原文作“闻言”,有误。
⑪原文作“求文”,有误。以下应由“文求堂”出版的著作,均作“求文”。
⑫以下所列为发表过郭沫若著译作品的报纸刊物。
⑬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