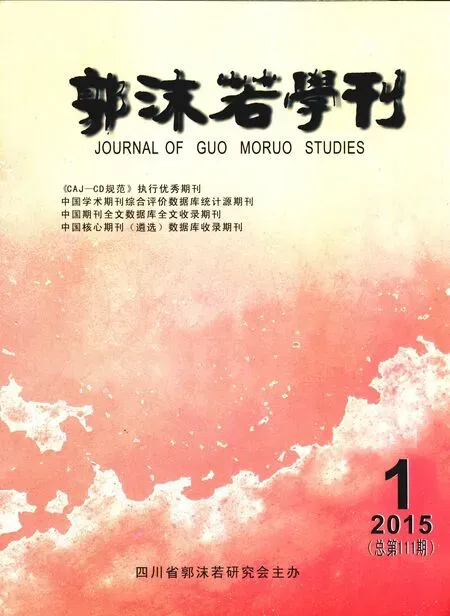诗的“写”与“做”的争议
陈俐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诗的“写”与“做”的争议
陈俐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1920年,郭沫若在和宗白华相互通信中,提出了“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观点,在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郭沫若这一见解产生了“放大”效应。郭沫若被视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而成为他在文学史中定位的基调,及后人解读郭沫若诗歌的依据和出发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郭沫若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郭沫若;诗歌观;文学史
从1919年秋天开始,上海《时事新报》之副刊《学灯》上陆续发表了笔名为“沫若”的诗作《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鹚》《凤凰涅槃》《天狗》等,郭沫若这些情绪丰富复杂,风格多样化的生命之诗,全面表达了五四时期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压抑了几千年的精神能量在瞬间的爆发。它那洋溢着巨大生命气息又焕然一新的形式,把无数青年煽得如痴如醉,但“学院派”诗人对这些诗歌却保持着相对的冷静。
1920年8月,郭沫若致长信于《学灯》编辑宗白华,就新诗及其它的问题与宗白华探讨,在这封著名的长信中,郭沫若提出生命诗学观,其间他描述了雪莱、歌德作诗时的情形,同时抛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我想诗这样的东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来的,我想你的诗一定也不会是做了出来的。……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
郭沫若这一观点,引起宗白华探讨新诗的强烈兴趣,宗白华当时正在编辑《少年中国》杂志,他一边将郭沫若的这封信在《少年中国》公开刊出,随即在《少年中国》连续两期出版诗歌专号,以此为话题,引发社会对于新诗的关注和讨论。宗白华本人并不完全赞同郭沫若的说法,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新诗略谈》,与郭沫若商榷:
近来中国文艺界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新体诗怎样做法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好的真的新体诗?(沫若君说真诗好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这话自然不错。不过我想我们要达到“能写出”的境地,也还要经过“能做出”的境地。因诗是一种艺术,总不能完全没有艺术的学习与训练的。……
宗白华在与郭沫若的通信中,明确表示“反对直觉”,而且还从诗的形式美的角度,直率地批评郭沫若的诗“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
比郭沫若出名更早的四川诗人康白情也加入了讨论。巴蜀诗人共有的浪漫率性,使他更容易与这位巴蜀同乡产生共鸣。郭沫若在那封长信中阐发的观点,他总体上是赞成的。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九期“诗歌专号”里,康白情发表了谈新诗的专文《新诗底我见》,这篇文章与郭沫若的观点大同小异,他为新诗所下的定义为:“在文学上,把情绪的想像的意境,音乐的刻绘的写出来,这种的作品就叫做诗。”康白情进一步地比较了旧诗与新诗的区别:
新诗所以别于旧诗而言。旧诗大体遵格律;拘音韵,讲雕琢,尚典雅。新诗反之,自由成章而没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节而不必拘音韵,贵质朴而不讲雕琢,以白话入行而不尚典雅。新诗破除一切桎梏人性底陈套,只求其无悖诗底精神罢了。
文章将“情绪的、想像的意境”作为诗的主要元素,有力地声援了郭沫若诗歌主情重质的呼吁。康白情明确表示:
诗要写,不要做;因为做足以伤自然的美。不要打扮而要整理,因为整理足以助自然的美。做的是失之太过,不整理的是失之不及。
但是在当时的诗坛,像康白情这样有力地支持郭沫若的观点,还真是找到不几个。那怕是同样以抒情为主要特色的青年诗人群体。当然,从康白情对新诗的定义中,也涉及到新诗的形式问题。他主张以音乐的、刻绘的手段进行表现。这里已经触及到闻一多后来提出的诗歌“三美“主张中的音乐美和绘画美。当然,由于康白情是将新诗对于旧诗的改革方面作为重点,因此,没有更深入地讨论诗歌的音乐性问题,只是笼而统之说“依自然的音节”。
由郭沫若引发的诗歌是“写”还是“做”的问题,也引起另一个诗人群体的关注。时为青年诗人的章衣萍(洪熙)明确表示反对沫若的观点,他和同乡诗友胡思永一块讨论诗时,共同表示:
我们很反对郭沫若诗是写的,不是做的话。我们以为热烈的情感和巧妙的艺术手段是同等重要的。单有热烈的情感而没有巧妙的艺术手段也不会做出好诗。郭沫若是一个有些做诗天才的人,只可惜他的艺术手段不高,所以女神并算不得一部成熟的作品。现在的诗人不可救药的大病,便是糊里糊涂的写……,我们忠告现在的诗人,诗虽然不能矫揉造作的做,也不可糊里糊涂的写。
章衣萍,本名章洪熙,又曾署名“章鸿熙”,安徽绩溪人。是胡适的小老乡,曾任过胡适的私人秘书(用龚明德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是胡适以这种可以接受的名义,来接济贫困的青年同乡的一种方式),关系很好。章衣萍与当时年青诗人汪静之、胡思永等一帮绩溪老乡过从甚密,常常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写诗作文的经验,也常常受到胡适的帮助和鼓励。上文中提到的思永,即胡适的侄儿。喜欢作诗,因患疾病,21岁即去世。后由友人程仰之(晨光社同人)辑其遗作,成《胡思永的遗诗》三卷,由胡适作序。胡适对这个早夭的侄儿很是怜爱,且对他的诗也评价甚高,序中称:“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嫡派”。
章衣萍和胡思永等人与胡适的特殊关系,当然不希望横空出世的郭沫若对当时的诗坛盟主有所威胁。再加之年青气盛,凭一时兴会,对郭沫若写诗的观点明确表示反对。但胡思永在与衣萍的对话中同时又表示,须得“诗来找我才做诗”,这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写诗需要有诗情、有灵感时,才能作诗。应该说,他所描述的写诗状态,与郭沫若的主张并无二致。显然,章衣萍、胡思永等绩溪诗人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的。他们的主张浅尝辄止,多有意气用事的成分。这些文学青年不求甚解地批判,并没有将讨论引向更深入的学理层面。
胡思永等人的矛盾之处却让当时在天津的一批敏于思考的文学青年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还在天津文汇学校读书的诗人于赓虞与好友赵景深也开始对新诗进行热烈的讨论。于赓虞写了《写诗与艺术》一文,赵景深也作《诗是写的》一文,共同探讨新诗的特质和创作问题,并指出胡思永和章衣萍观点的矛盾之处。他和文友赵景深在来往书信中,就新诗是“写”出来的,还是“做”出来的这一问题进行反复的辩难和讨论。这些书信充满了理性色彩,与其说是书信,不如说是短小的论文。为更真切地展示他们的观点,现就他们书信的主要观点作一摘抄:
景深兄:
《诗是写的》,我已拜读过了。我的《写诗与艺术》,只谈“诗来找我方作诗”,和“诗是写的”是相成的,不是不容的。是为主张“诗来找我方作诗”,而反对“诗是写的”者作的。并没谈到写诗后与修饰问题。咱两(俩)的意见,完全相同。
赓虞兄:
我未得你允许就将你的信发表了,请你原谅!
我极赞成你的话,“诗来找我才作诗”和“诗是写的”自然是相成的,不是不容的。我知道你所指的是《晨报》上章洪熙的《一知半解的诗话》里的话。其实不但你和我的意见相同,就是他的意见也未尝不和我们相同哩。他所以反对“诗是写的”,我想是他误解了“写”字,所以我才将“诗是写的”这句话拿来解释一下,说明写的内包。他以为“诗是写的”是等于“诗是完全写的,一点艺术功夫也没有”,自然他要反对,所以有这样的矛盾。如果他知道“诗是写的”这句话只不过是指着有感想时说,作成后的修饰另是问题,我想他一定和我们的意见一样;只因名词范围大小的关系,他便有如此的误会了!
我那篇杂谈《诗是写的》是为章洪熙写的,以及一般误会这句话的人写的,不是为你的文而写的,不过也是因你的文而联想到的罢了。
他的误会是:“诗是写的,在全诗告成的起点和终点中的一切时间。”
我们所见到的是:“诗是写的,在全诗的起点。”
弟,赵景深
上述讨论中,郭沫若关于诗的“写”与“做”被置换成诗歌的情感(内容)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围绕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展开。事实上,从逻辑的角度来说,“诗只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暗含着下列的推理:只是做出来的诗,不是好诗,却不包含“只是写出来的诗,是好诗”。但人们在讨论时,就将这个并不存在的推理作为讨论的前提了。从而将郭沫若的意思理解为只要有热烈的情感就可以做诗。赵景深为人通达,善解人意,其学术思维也多灵活圆通,所以,他求同存异,最后总结说:
我想四四方方的中国字,有些定义太含混,即就“诗是写的”这句话看来,怎样才算是“写”,各人的说法便不同了。好在我还承认“有深的感想时才写诗”,或者你不至于到“不敢请你赞同”的地步罢?
于赓虞作为一个很有锋芒,敢于创新,又善于理性思辨的青年诗人。他并不止步于书信中点到为止的观点表露。由郭沫若的观点,引发这个年青诗人对新诗的理性探讨,在个性方面,他与郭沫若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共同追求的是诗人“真我——自然的我”的纯真人格。但是理性的冷静,使于赓虞又重视艺术的修养和形式的表达。在《诗的自然论》中,于赓虞对新诗的质和形进行了阐发:
a.个人要自然化,绝对不受拘束,依情之所以为归宿。该憎恶时便憎恶,该痛哭时便痛哭,该慷概(慨)悲歌时,便慷概(慨)悲歌。而被黑雾迷困的假我,自然根本推翻,创出自我的宇宙,慢慢发现、发展人的本性天性,而达于真我——自然的我。个人既自然化了,还要对于自然界中的事事物物,直接观察他们的现象,窥测他们的神秘,听听他们的声调的美意。所以才能够流露真情,不至落于无病呻吟的旧套里。所以我以为个人自然化,和在自然界中的活动,是养成诗人人格的前提。
b.个人要自然化,和个人在自然的环象中,所接触的神秘,固然能得着真实性的了解,为诗的源泉,但这都是“质”的方面的事情。其次顶重要的,就是须有音乐和图画的修养。如有深刻浓厚的修养,就能写出自然优美的音节,良好的词句,可以写成一种自然的美景。使读者不觉生出自然的愉快和美感,所谓艺术的功用,也就在这里了。
一九二二,十一,十七
与新的形式革命相比较,于赓虞更倾向于新诗的质的革命。直到1925年,于赓虞在《诗歌与思想》仍然将情绪的表达推为诗歌“质”的首要元素:
几年来诗歌解放的运动已有端绪,但只是由文言变为白话,仍是形式的变迁,若不就根本的思想上着想,仍和五七言等的变转没有两样,只是不受韵律的束缚罢了。努力于诗歌内涵的拓张与丰富,实从事诗歌的人应负的责任。诗歌的灵魂是情绪——是人生和宇宙中间所融化成的一种浑然之情绪的表现。从此看起来,诗歌最要紧的质素是这样情绪的表现,而非思想的叙述,是很浅近的道理了。我们如果不愿意伟大的艺术流产,如果欲在诗歌的园地里建筑起一座奇伟灿烂的宫庭,实不能不注意到两种混合体为诗歌宝库的东西:
思想领域的拓大,深致,雄伟与锐利;生活中有一个生动,活跃与独自性的我在。
七月一日北京旅寓
很有意思的是,于赓虞在这篇短文的“附后”中,说他作此文时“曾翻开五六种英文书,两三种中文书,”可见,他的上述观点并不是随手写作的杂感,而是有充分学理和学术含量的见解。遗憾的是,于赓虞许多关于诗歌的真知灼见,没有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以致于他的许多重要而精辟的诗歌理论被后来的文学史遮蔽,大概是和他当时社会知名度,以及诗歌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有关吧。
总而言之,郭沫若关于诗歌创作的这句话在社会讨论和批判过程中,产生了放大效应。他的观点并没有获得诗坛的满堂喝采,相反,招致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郭沫若关于诗歌创作的这一自我陈述成为“主情主义”的代表性言论,并成为后人解读郭沫若诗歌的依据和出发点。他的诗歌和关于诗歌的见解,在学院派诗人那里遭到较为剧烈的批评。最有代表性的是孙大雨的一篇评《女神》与《星空》的长文。作者锋芒毕露,认为中国初期白话诗完全不值一提:
六七年来的成绩不过如是而已!所谓学者底新诗,除了喊几声努力,抛几个炸弹而外,再没有别的技能了,此外如康(白情)、俞(平伯)、刘太白、郑振铎、朱自清、叶绍钧、汪静之、徐玉诺,以及各处大学中学里车载斗量的“诗人”,没有一个做过一首真是可称为诗的,赏过我们的眼福。稍有成就的只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郭沫若四人,而就中郭诗尤受人赞誉,共尊为艺术底艺术,未免言过其实。这一半确因佳作稀少之故,一半也因群众井底窥天所致。”
在此,孙大雨还是将郭沫若与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并列,看做中国新诗人中少有几个代表性人物。他也赞扬郭沫若做诗,贵在人格的真诚。但也仅此而已。紧接着,孙大雨在与外国许多著名诗人的对照中展开对郭沫若诗歌,特别是对《女神》第二辑的尖锐批评:
没有深沉的人格大概可归原于没有特具的内心境界,有时修养与训练却能把这境界开辟出来。反之,如作品有了个性之后,往往容易失之过激。力量丰厚的作品容易变成粗暴坦直,色彩用过分了会麻痹感觉的成分,……郭君底作品(尤其是初期的)热烈是热烈了,但在这一点上是幼稚得可笑。——情感潮汛时粗暴坦直,不粗暴坦直时便很不深挚有力。
基于上述看法,孙大雨认为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便是两匹溜缰的劣马,驾驶者已失去统驭的能力,烈火烧尽了尾鬣,痛得他们两目失明,只向前狂奔乱窜。”
以不同的诗学观去评价,肯定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无论是以温柔敦厚为诗美的中国传统美学观,还是以暗示和象征为基本手段的象征诗派,郭沫若这种对生命本体的直接呈现方式,他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孙大雨的看法其实代表了学院派诗人群体的看法。当然,他还是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女神》中第三辑诗歌的诗意美。平心而论,孙大雨的评论看到郭沫若风格的多样性,并从诗歌形式美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评价,总体还是从艺术和美学的角度作出的判断。
问题在于,郭沫若是一个天才诗人,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他要为新的世界鸣锣开道,还真是需要这种突破一切的呐喊。他将疯狂情感表达到极致,这种呼叫绝对突破了中国传统美学可以允许的极限。在对中国古典美学有着深厚情感的学院派诗人那里,郭沫若成为一个只重质,不重形的自由诗、白话诗的代表人物就是必然的了。郭沫若之后的有些诗人,以郭沫若为幌子,东施效颦,将空洞无物的滥情和无病呻吟,都视为浪漫主义的表现,真是误解了郭沫若。所以,上世纪30年代朱自清在《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
“诗是写出来的”一句话,后来让许多人误解了,生出许多恶果来;但于郭氏是无损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20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瞑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
朱自清这段话,几乎成为文学史对郭沫若诗歌的定评。朱自清虽然承认郭沫若这个观点遭到文坛的误解。但是最终还是将郭沫若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而排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无论是后来文学史中倒“郭”派,还是挺“郭”派,最终都忽略了他那些平和冲淡的诗歌。这样,郭沫若那些充满古典风及东方风味的诗歌被遮蔽,而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21世纪重新被发现。而在文学史中,只留下了一个豪气冲天的怒吼诗人形象。
而郭沫若本人,关于由他引起的众多争论,倒并没不太在意,也没有介入争论,他只在《创造》季刊的插入的短评中感叹道:
“我说诗是写的不是做的,有些人误解了,以为是言不由衷地乱写;或则把客观的世界反射地誊写。啊,说话真不容易。”
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个看法。时隔十年后,他在其自传体作品《创造十年》中再一次重提:
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乍寒乍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当时的实感。
这段话再次强化了他对诗歌写作的原初见解,勾起人们对于那场大讨论的记忆,从而加深了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印象。的确,作为中国现代转型初期的诗人,他强调文学是“生的颤动,是灵底喊叫”,是情绪的直写。诗歌的功能就是情感的渲泻,要渲泻就要有声音,有感叫、有叹息。他提出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世界。这些诗歌观上承《毛诗序》诗歌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情发乎声,声成文谓之音。”更多地回应着诗、乐、舞三位一体和诗歌口语化、歌谣化的原始风,回应着中国诗歌的屈骚传统,冲击了后来中国文人温柔敦厚的传统诗学观。所以在上个世纪引发如此多的讨论,受到如此多的质疑就是必然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学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诗学观。就像莎士比亚戏剧在古典主义时期不为人重视,百年之后又才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一样。郭沫若的诗歌在破旧立新五四时期产生轰动是必然的,在后来的歌舞长升平的时代不被重视也是必然的。
(责任编辑:王锦厚)
注释:
①《新诗之我见》最早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九期发表,后经修改后改为《新诗短论》再次发表。修改稿中对诗的定义改为:“在文学上,把情绪的,想像的意境,音节地戏剧地写出来,这种的作品就叫做诗。”
②于赓虞《写诗与艺术》,这篇文章曾在他与赵景深的书信中提及,他后来的书信中也引用了其中的话语,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这篇文章的全文。
③下引于赓虞与赵景深的书信,初载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朝霞》,1923年1月7日,引自解志熙、王文金编校.于赓虞诗文辑存(下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09月第1版。
④孙大雨署名“子潜”的长文《郭沫若——〈女神〉与〈星空〉》,连载于《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六期(1924年10月)、第七期(1924年11月)、第八期(1924年12月),文章没有结尾,显然是作者意犹未尽,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写完或继续刊载。不知何故,该文一直没有收入目前所见的郭沫若研究资料汇编本。
⑤2007年,朱寿桐先生的论文《郭沫若早期诗风、诗艺的选择与白话新诗的可能性——论《女神》集外散佚诗歌》对郭沫若不同风格的诗歌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2008年,蔡震先生编辑的《女神》及佚诗(初版本)出版,对于人们完整的、历史地了解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文本。其后,人们对郭沫若早期诗风的多样性开始更多的关注。
[1]郭沫若.致宗白华.三叶集[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宗白华.新诗略谈[J].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诗学研究号”(1920-02-15).
[3]章洪熙.萌芽的小草·一知半解的诗话[N].晨报附刊,1922-12-20.
[4]诗的自然论[J].虹纹(季刊)第1集(天津直一中学出版部,1923-01-01日出版).解志熙,王文金编校.于赓虞诗文辑存(下册)[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5]于赓虞.诗歌与思想[J].原载《京报附刊·文学周刊》第27期(1925-07-11).解志熙,王文金编校.于赓虞诗文辑存(下册)[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6]子潜.郭沫若——《女神》与《星空》(一)[J].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六期),1924-10.
[7]子潜.郭沫若——《女神》与《星空》(二)[J].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七期),1924-11.
[8]朱自清.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
[9]郭沫若.曼衍言6[J].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号),1920-08-25.
[10]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1]关于《女神》与屈骚传统的关系[A].李怡.《女神》与屈骚·跨越时空的自由——郭沫若研究论集[C].东方出版社,2008.
中国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符:A1003-7225(2015)01-0033-05
2014-12-25
陈俐,女,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