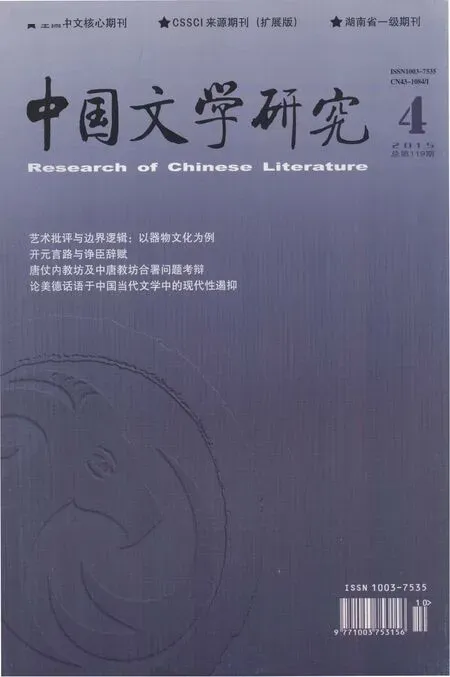金圣叹文学评点的女性观
钟锡南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从来没有构成一个封闭而独立的社会;她们只是男人统治下的集团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个集团中,她们处于次要地位。”我国古代也同样如此,长期存在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人数同等的广大女性则是其附属品,这种情况自有文字存在以来就与历史相伴,而在女性贞节观念至上的明清时期尤为突出。在叙事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是,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多处在男权阴影之下,在一些明清章回小说的有关情节中,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观更是显示了作者的男性主义写作文风。相应地,在明清文学评点中显示出来的女性观也说明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复杂性、矛盾性。明末清初的文学评点大家金圣叹就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突出典型,他在文学作品评点中流露出来的对女性的态度,同渗透在他个性鲜明的评点文字中的观点一样,既有其民主性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暴露出其传统文人因循守旧的一面。
一、金圣叹文学评点女性观中张扬其个性之民主、进步的一面
明末清初,随着江南城市经济生活的繁荣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蓬勃涌现。这个时期,思想家和文学家纷起,他们讨伐戕害人性的程朱理学,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解放。金圣叹就是这股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员,他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狂放不羁,坦荡无违,敢于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甚至大胆地诉诸情欲。这种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等文学作品评点的字里行间。
金圣叹在其女性观上有着超越时代的民主、进步的一面,这体现出明清之际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萌芽,闪耀着人性解放、男女平等思想的光芒,蕴含着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进步因素。金圣叹生活在当时资本主义因素较为发达的苏州,贫困潦倒的生活使他易于接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他汲取并发扬了泰州学派何心隐及李贽的“自然性情说”,反对程朱理学,反对将情与理对立的禁欲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李贽的男女平等、人性解放,高度赞叹梁山泊女英雄的不让须眉、义烈助人的精神,大胆肯定女性的智慧、才干和胆识。
金圣叹个性张扬,他一反传统格套,打破封建礼教“闻见道理”的拘束,见解超凡,卓然不群,敢于直白地表露自己内心真实的愿望、要求,甚至是赤裸裸的性情和欲望。他在《西厢记》中《才子西厢醉心篇》的“治相思无药饵”条下夹批道:“饮食男女,大欲存焉。”他认为男女间的情欲是人的正常本能,没必要对其回避遮掩。因此,在《水浒传》第二十回的夹批中,金圣叹写道:“人每言英雄无儿女子情,除是英雄到夜便睡着耳。若使坐至月上时节,任是楚重瞳,亦须倚栏长叹。”基于这种认识,他在《西厢记》的评点中,对待崔张第一次结合的那出戏的态度,就不像许多道学先生那样大骂其为“诲淫”,而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肯定。尤其是在崔张于五更天分手时,金圣叹更是动情地写道:“诗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此最是不可奈何时节也。”这是从人的正常本性和真实的心理感受来看问题,而不是从传统的道德条律出发机械地裁判。在那个视女性为淫恶之首的社会里,发出这种款款之心声的确难能可贵,这可以看成是尊重女性的一种隐曲委婉而又真实自然之情感的大胆流露。
在《水浒传》的评点中,金圣叹很多地方都传达出对生活于其中的女性人格的尊重,对女性要求自由平等的肯定。如第十二回“急先锋东郭争功,青面兽北京斗武”一节,梁中书“在后堂家宴,庆贺端阳”时,对夫人(蔡京之女)说道:“世杰自幼读书,颇知经史,人非草木,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金圣叹夹批道:“妻前夫名,势在则礼然也。”他认为梁中书之所以“妻前夫名”,是由于处于权势、家庭身世不如妻子的弱婿地位决定的,但同时在这些文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金圣叹肯定“妻前夫名”所生发出来的是夫妻间平等、和谐关系的不可或缺,这种思想可视为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夫权主义的反抗和冲击,体现了新型的夫妻关系平等的思想萌芽。
金圣叹不仅肯定了夫妻平等,也肯定了夫妻间应恩爱情深、互敬互让、白头偕老。如林冲与妻子互敬互爱,后林冲得知妻子被逼身亡,一往情深,“潸然泪下”,金圣叹在此由衷地感叹林冲“哭得真”,是“真豪杰”,可见金圣叹在价值取向上视夫妻间真挚感情为夫妻关系构成因素的主体。“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一回,虔婆说宋江和婆惜“你两个又不是泥塑的,做甚么都不做声”处,金圣叹由“泥塑的”联想道:“赵松雪《戏赠管夫人词》云:‘我侬两个,忒煞情多。好一似练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却将来一齐都打破,再团再练,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时节我泥里有你也,你泥里也有了我。’”无独有偶,在《西厢记》的评点中,金圣叹似又一次随意写道:“昔赵松雪学士信手戏作小词,赠其夫人管曰:‘我侬两个,忒煞情多。譬如将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忽然间,欢喜呵,将他来,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团再炼,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其间,我身子里有你也,你身子里也有了我。’”两处意思全然相同,仅在文字上有些差异,可见是喜爱这一典故的金圣叹凭记忆于不经意间随手写出的。在金圣叹的潜意识里,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夫妇关系是他取舍男女关系的最高标准,所以这种看似随手在其评点的相关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文字,其实是他一以贯之的思维定式使然。
同样,在《西厢记》的评点文字中,金圣叹通过对崔莺莺的“护惜”赞美,也集中表达了他对女性的尊重乃至仰慕。“双文,天下之至尊贵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有情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灵慧女子也;双文,天下之至矜尚女子也。”“双文,国艳也。国艳,则非多买胭脂之所得而涂泽也。抑双文,天人也。天人,则非下土蝼蚁工匠之所得而增减雕塑也。”“《西厢记》是《西厢记》文字,不是《会真记》文字。”为突出莺莺在《西厢记》中的地位,金圣叹多处用了相应的比喻,“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譬如药,则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在情真意切的金圣叹看来,莺莺就是他心中的女神,“见我莺莺有春雨闭门,下帘不卷之句,我犹恐连阴损其高情;又见莺莺有隔窗听琴,月明露重之句,我犹恐湿庭冰其双袜;又见莺莺有压衾朝卧,红娘弹帐之句,我犹恐朝光射其倦眸;又见莺莺有杏花楼头,晚寒添衣之句,我犹恐线痕兜其皓腕。……”一连串排比句的铺设,将其对莺莺的喜爱敬重,甚或说是怜香惜玉之情和盘托出。
《水浒传》塑造了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等几位勇敢的绿林女杰形象,展露出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的曙光。她们不仅有粗豪、勇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更有临危不惧的胆识、计划周全的精细、善于应变的机敏。作者在对她们的描写中冲破了传统的封建妇女观,让她们和其他男性英雄一样平起平坐,在梁山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以说这些女主角摆脱了“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藩篱,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深受皇权、族权、父权、夫权等绳索束缚的时代,开创了一片属于她们的天地,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儒家传统所倡导的男尊女卑的模式,反映了作者妇女观中积极进步的一面。
与前述相应,金圣叹的女性观进步之处,表现其对梁山泊女性英雄行为情节描写的相关评点文字中,他高度赞颂了梁山泊女英雄义烈勇为、疾恶如仇的品质。如书中对顾大嫂的描写,她绝非严守妇德妇容妇言妇功的“窈窕淑女”,相反,她是一只“母大虫”。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仗义执言,拉起丈夫、伯伯等人劫狱,救出解珍、解宝兄弟,并果敢地带头上山造反。对此,金圣叹连连赞叹,“写顾大嫂,活是黑旋风”“亦可号之为母旋风,意思实与李逵无二”,“写顾大嫂何等肝肠”,“绝妙大嫂,佩服其言,可以愈疟”。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金圣叹在女性观上,汲取了男女平等、人性解放的进步思想,尊重敬佩女性的才能和品德,一定意义上冲击了封建落后的女性观,体现了启蒙时代进步女性观的萌芽。
金圣叹在其《西厢记》评点前的序二《留赠后人》中写道:“我请得转我后身便为知心青衣,霜晨雨夜侍立于侧而以为赠之。”青衣是中国戏曲中旦行的一种,北方剧种多称青衣,南方剧种多称正旦。按照传统来说,青衣在旦行里占最主要的位置,所以叫正旦,扮演的一般都是端庄、严肃、正派的人物,大多数是贤妻良母,或者是贞节烈妇之类的人物。金圣叹希望自己来世能变成后人的“知心青衣”,且不说这一想法如同今天许多的变性人一样,有着强烈的异性心态,单就其换位思考的角度来说,说明金圣叹对女性有着尊重甚至是羡慕的心理,透露出明清之际的金圣叹超迈前伦的现代意识和进步之处。
二、金圣叹女性观中封建道德意识消极落后的一面
平心而论,金圣叹的女性观念中,有着进步意识的同时,也积淀着封建伦理道德的糟粕,程朱理学影响之下的重理轻情,注重女性贞操,赞扬所谓贞妇,力贬淫妇,承袭“女子祸水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封建婚姻的宽容。中国自古以来皇权统治就重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包括对生活在男性社会底层的女性思想上的钳制,女性被套上“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枷锁。尤其是宋元以后,理学盛行的时代,女性更在根本上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而成为男权的附庸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性的自然性情被进一步扼杀,官方为女性指定的一条光宗耀祖之路是做节妇或烈女,在明史上记载的节妇烈女竟逾万人。可见明清时代对女性贞操的规范要求已经成为官方哲学之一部分,最可怕的是它已经为全社会所普遍接受和推崇,甚至渗透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思维模式当中,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纳入了他们的基本价值评判体系。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金圣叹当然也不例外。
金圣叹将赞美之词倾注于其眼中的贞烈女子,如他在《水浒传》评点中,对唯一坚守妇道的贞烈女子——林冲之妻大加褒扬。面对高衙内的几番调戏,林冲娘子严辞拒绝、奋力反抗,当林冲去寻陆虞候,林娘子苦劝丈夫不要去报复时,金圣叹批道:“只一‘劝’字,写娘子贞良如见。”“又好娘子,真是壮夫良妇。”以“好娘子”来叹赏这位符合“温良恭俭让”的贞节女子。可见,品行的贞烈与否是金圣叹评价女性形象美丑的突出的标准之一。
与其对女子贞良的欣赏和赞扬相对,金圣叹的女性观也表现在其对那些不守妇道的淫妇的贬斥上。在《水浒传》评点中,金圣叹以“淫妇”论来评价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因淫乱而被杀的女子。《水浒传》中那些年轻貌美的女性几乎都被冠以“淫妇”之名,且置她们于水浒英雄势不两立的对立面,视之为导致宋江、武松、杨雄、石秀、卢俊义等豪杰被逼上梁山的直接动因,这无疑暴露出作者“女人祸水论”思想。金圣叹的论调与之一脉相承,如在《水浒传》第三十二回中,花荣对宋江提及为什么不该从清风山上救下知寨刘高之妻时,说道:“兄长却如何救了这厮的妇人?打紧这婆娘极不贤,只是调拨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对此,金圣叹批道:“贪图贿赂,未有不残害良民者;残害良民以图贿赂,未有不奉其婆娘的;婆娘既识贿赂滋味,未有不调拨丈夫多行不仁者。借花荣口中,写得如秦镜相似。”金圣叹把贪官贪贿害民的根源归结于女性,同样表现了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女人祸水论”的影响。平心而论,在贪贿害民、祸国祸家的因素中,刘高妻之类仅仅是表面的因素,如果没有封建统治者内部的荒淫腐败、纵容奸佞、鱼肉百姓这些根本性因素,就没有后面祸国败亡的后果。而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和地位,在鱼肉百姓之余,又炮制了愚弄百姓、混淆视听的“女人祸水论”的幌子,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天下那些不幸的读书人都成了受其蒙蔽的牺牲品。
金圣叹的“女人祸水论”突出地表现在对潘金莲的评点上。《水浒传》在潘金莲出场时写道:“那清河县有一大户人家,有个使女”,金圣叹对此批道:“可见来历不正。”这可以看出金圣叹对出身于非正统人家的女子之鄙视。从其正统的道德观念出发,金圣叹层层深入地剖析了潘金莲对武松的言行举止和态度,将其“凡叫过三十九个‘叔叔’,至此忽然换作一‘你’字”,解释为“淫妇心动”,纯属“淫妇情性”,“淫妇”一词,出现了数次,可见金圣叹对潘金莲深恶痛绝之极。虽然金圣叹注意到潘金莲与武大郎的婚姻是不和谐的包办婚姻,并流露出对封建包办婚姻不幸者一定程度上的同情。但对于潘金莲不甘顺从屈辱性的包办婚姻而顺应本能和对理想生活的渴求去大胆追求英俊孔武的武松之举,在金圣叹看来是“淫妇情性”而加以贬斥,认为这是“潘失嫂嫂之道矣”,须先“正名分”,她的举动不合“叔嫂不通问”的封建伦常。正因为此,金圣叹不是从人的自然性情上肯定潘金莲对武松的真性情,而是极力嘲讽、挖苦潘金莲,全盘否定潘金莲渴求正常情感生活的一定合理性。
金圣叹面对潘金莲在门前叉帘子,叉竿失手打在碰巧经过的西门庆身上这一偶发事件,也做出了“淫妇情性”论的解释:“此一滑,我极疑之。不然,岂前日雪天向火之日,亦失手伸将过去,不端不正,却好捏在叔叔肩胛上耶?”潘金莲为此向西门庆道歉,本是顺乎自然、情理之中的事,也遭到了金圣叹的攻击,将之视为令人作呕的淫情浪态:“看他两个,一个如迎,一个似送,一个轻怜,一个痛惜,一个低头,一个万福,倒教我看书的羞得倒躲倒躲。”由于“女人祸水论”的思想作祟,金圣叹出于同一立场,斥潘金莲为“淫妇”,在他看来,潘金莲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淫妇情性”,但他没有正视潘金莲并非天生淫妇这一事实,忽略了她从人到非人的畸形发展过程中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因素,这是她变为“淫妇”的根本原因,而反复强调的是她畸形发展后的变态,谋杀亲夫成为“淫妇”的极端行径,这可以看作是金圣叹对女性认识上的偏颇。
历代统治者,尤其是宋明以来的统治者都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大肆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以此作为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诸如《女诫》《烈女传》《女论语》等纷纷出笼,成为规范女子恪守贞孝节烈的教科书。在这些官方哲学的指导下,金圣叹痛斥贬损淫妇,便顺理成章了。他认为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等是“淫妇好色”,是“败坏风俗”的“猪狗”,“刁时便刁杀人,淫时便淫杀人,狠时便狠杀人”。对于不满封建包办婚姻,敢于反抗并大胆追求理想生活的潘金莲等,应该说她们在开始反抗时是带有合乎人情和人性的合理性质的,但金圣叹则认为这属淫妇淫情,从侧面反映出金圣叹对不幸的封建包办婚姻并没有深刻认识,未能从自然性情上对其加以肯定,体现了他评点《水浒传》的保守态度。
当然,金圣叹对所谓淫妇的态度也有区别对待之处,如对于同是杀嫂,当谈到武松与石秀之间的差异时,他就辨析道:“前有武松杀奸夫淫妇一篇,此又有石秀杀奸夫淫妇一篇,若是者班乎?曰:不同也。夫金莲之淫,乃敢至于杀武大,此其恶贯盈矣,不破胸取心,实不足以蔽厥辜也。若巧云,淫诚有之,未必至于杀杨雄也。坐巧云以他日必杀杨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未必遂服巧云之心也。且武松之于金莲也,武大已死,则武松不得不问,此实武松万不得已而出于此。若武大固在,武松不得而杀金莲者,法也。今石秀之于巧云,既去则亦已矣,以姓石之人,而杀姓杨之人之妻,此何法也?总之,武松之杀二人,全是为兄报仇,而己曾不与焉;若石秀之杀四人,不过为己明冤而已,并与杨雄无与也。”按照金圣叹的法理逻辑,他肯定了武松的杀嫂,认为武松是在为被嫂谋杀的亲哥哥报仇雪恨、伸张正义,而石秀则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挑唆义兄杨雄残杀巧云和丫头迎儿,武松是为兄,而石秀是为己,“写石秀只为明白自己,并非若武松之于金莲”,所以“令人可恨”,而且“何至于此,可畏可畏”。金圣叹痛恨石秀的狠毒,同情潘巧云的惨死,其出发点是从封建伦理道德开端的法律精神,流露出的是其情理平衡并重的价值观。
金圣叹对封建包办婚姻的认识一如既往,并不比他的前辈们高明,整体上依然是传统的。如一丈青扈三娘与王矮虎的婚姻是宋江做主,众头领为媒的,扈三娘竟然毫无反抗地顺从了,嫁给了才貌武艺各方面都配不上她的矮脚虎王英,“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面对这种明显不合情理的姻缘,一向谈锋犀利的金圣叹则没有发出什么不同的声音,相反,却于此凑趣道:“(两口儿)三字骤合,为之一笑。”这“笑”的含意,着实让人有些费解。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三十三回评点中,赞花荣为留秦明上山入伙定的妙计,是“不惟善用其兵,又善用将”,为了对秦明结以恩惠,笼络降将之心,不惜牺牲妹妹幸福,以妹妻之,对此,金圣叹赞赏花荣是“善用其妹”,“绝妙花荣”,而无视花荣之妹沦为政治工具和斗争牺牲品的可悲境地,这暴露了金圣叹评点中封建知识分子保守落后的一面。功利婚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普遍现象,它往往成为获得某种政治权益、家族利益、血统等级等功利的媒介和工具,只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里也包括兄长之命、之言,就是合理合法的,是不容违抗的,根本就没有顾及男女双方的感受,尤其是身处“三从四德”压迫下的女性,更得不到人格尊严和尊重。而金圣叹又默认了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对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性的人格和人性的践踏,这确是他女性观中落后的一面。
三、对金圣叹女性观之评价及其思想意义
综上所述,金圣叹在女性观上,既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其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既有资产阶级人性自由、平等、解放思想的萌芽,也积淀着封建伦理道德的糟粕。他的女性观上的这种二重性,不仅表现在其女性观总体上存在着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的冲突,也表现在其对一人或一事的评价上所交织着的情与理的矛盾。
在评论《水浒传》时,尽管金圣叹在对待三位被杀女性持“淫妇论”,把“花娘好色”当作潘金莲等堕落为“淫妇”的主观原因,但他同时也注意到“淫妇”的产生也有其客观原因。他注意到封建社会风气的淫乱、败坏,是“淫妇”产生的客观原因之一。统治阶级道貌岸然,在训诫女性恪守妇道的同时,自己却荒淫无度,妻妾成群还嫖娼狎妓、强占民女,败坏了社会风气。而虔婆、媒婆也应运而生,为中饱私囊,她们穿梭于好色之徒与婚姻不幸的女子之间,凭三寸不烂之舌,把不谙世故的年轻女子推入陷阱。金圣叹清醒地认识到虔婆的推波助澜更助长了社会风气的败坏,“所以六婆不许入门,后世切戒之。”以此警醒世人勿重蹈覆辙。
金圣叹更进一步触及所谓“淫妇”淫风产生的另一重要的社会原因,即封建礼教和封建包办婚姻像双刃剑束缚、压抑、摧残着女子的人性,使她们生活在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中。在王婆贪贿说风情这回中,王婆与西门庆故意对潘金莲夸武大是“好丈夫,好性格”,潘金莲应道:“他是无用之人……”金圣叹批道:“‘他’字妙,‘无用’字妙。……好妇嫁得呆郎,第一怕人提起,气不得,不气不得,真有此六字之苦。”这段批语已触及封建包办婚姻是这段痛苦而不和谐的夫妻生活的原因,金圣叹感叹的“好妇嫁得呆郎”,意即造成的女性正常的心理生理需求受压抑是“淫妇”产生的客观原因。一个是“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三分象人,七分似鬼”的“三寸丁谷树皮”,一个则“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的少妇;一个是“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儒弱本分人”,一个则是“平生快性”,不从大户淫威、“看不得”懦弱的女子。无论是相貌、个性还是能力,武大都远不如潘金莲,当然也绝不合潘金莲的心意。对这段畸形婚姻,金圣叹在一定程度上是寄予同情的,但这并未因此改变他对潘金莲所持的“淫妇”观,也未认识到潘金莲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是她自身的反抗个性与不合理的现实间矛盾冲突的结果。
金圣叹已触及潘金莲等人的悲剧根源,即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抑、扼杀人性导致了其悲剧命运,这无疑有进步思想的萌芽,也正因为仅仅是进步女性观的萌芽,所以尽管金圣叹注意到“淫妇”也有合理的情感需求,也承认她们对中意的男子有情和爱,而并非只为放纵情欲,但封建时代的文人,对“淫妇”的情和爱,更多的是以封建伦理纲常加以否定,这中间交织着情与理的矛盾。
如潘金莲初见武松时,寻思道:“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之后,屡次以言辞试探、挑逗武松,并感叹道:“自从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清河县里住不得,搬来这里。若得叔叔这般雄壮,谁敢道个不字!”金圣叹批道:“忽然斜穿去,表出心中相爱来。”又如,潘金莲说道:“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金圣叹批道:“忽然又表出自己与武二一合相处来。”武松答应哥哥搬来同住,潘金莲又说:“叔叔是必记心,奴这里专等。”金圣叹对潘金莲这种大胆表露爱慕的言辞,只是从“淫妇心动”、“淫妇淫极”上分析,否定了这种不合封建“叔嫂不通问”观念的大胆追求。再如《水浒传》第四十五回,石秀定计翠屏山上,让潘巧云当面对质,迎儿先招出实情,潘巧云求饶无果,也只得说出与人私通之事。对此金圣叹批道:“迎儿说一遍,巧云又说一遍,却句句不同,迎儿所说皆是事,巧云所说皆是情也。”由此可见,金圣叹不自觉地承认“淫妇”有“情”,但却并不认为这种“情”也是人的真实性情的自然流露,应予以肯定,而是从贞操观上对此予以否定。
在很多场合,金圣叹对男女之情都给予了大胆的肯定和赞美,是“圣人之所不禁”,这尤其体现在他的《西厢记》评点中。面对世人普遍认定的诲淫之书《西厢记》,金圣叹反驳道:“《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金圣叹在男女色欲之间,不受旧习惯之拘囿,大放“人所欲说而不敢说”之词,大胆肯定了情。如张生与崔莺莺幽媾后,有“破工夫今夜早些来”之语,金圣叹于后批道:“诗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此最是不可奈何时节也。圣叹自幼学佛,而往往如汤惠休绮语未除,记曾有一诗云:‘星河将半夜,云雨定微寒。屦响私行怯,窗明欲度难。一双金屈戍,十二玉栏干。纤手亲扪遍,明朝无迹看。’亦最是不可奈何时节也。”
金圣叹每每痛斥道学先生于男女之事但见其鄙秽,一叶障目,却不见其文学之美及其时代的意义。“自古至今,有韵之文,吾见大抵十七皆儿女此事。”他捍卫爱情文学,并向儒家宣扬的诗教“发乎情此乎礼义”、“好色不淫”之类宣战,以情抗理。如崔莺莺简召张生逾墙,对这种违背封建礼教的大胆行为,金圣叹并不怪罪,批道:“我亦以世间儿女之心,平断世间儿女之事,……此亦人之恒情恒理,无足为多怪也。”还主张崔莺莺不妨和张生“私一握手,低一致问”,并认为“此亦人之恒情”。并进而把崔莺莺改成了“至尊贵,至灵慧,至多情,至有才”的少女形象,把张生改写成志高才大却坎坷不遇,执着于爱情而又不流于放荡的青年。
金圣叹的女性观存在情与理的抗争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向来尊崇的儒家,一直宣扬“发乎情,止乎礼义”,发展到宋代,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了系统的先验道德论的人性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封建伦理观,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赋的、人性固有的天理。他宣称:“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强调“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受统治阶级推崇。到明朝中期,王守仁心学也宣扬“寡欲”、“专欲”,进一步从封建义理上禁锢人的自然性情。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金圣叹不可避免地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制约,这就构成了其女性观封建、保守的一面。这种消极面,又由被评点本身存在的落后的女性观而凸显出来,所以金圣叹的女性观残存着封建伦理道德意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反道学”的“自然性情说”,倡导“尽人之性”、“随心所欲”的观点,针对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提出了“以孝我父者孝我妻,谓之良;以孝我父者孝我子,为之慈;以孝我父者孝我百姓,谓之有道仁人也。”正是这种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抨击,情对理的抗衡,昭示了男女平等的资产阶级进步民主的人性观、女性观的萌芽,闪耀着具有市民色彩的反封建光华。
[1]波伏瓦著,王友琴等译.女人是什么〔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2]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三)〔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3]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一)〔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4]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二)〔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5][宋]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