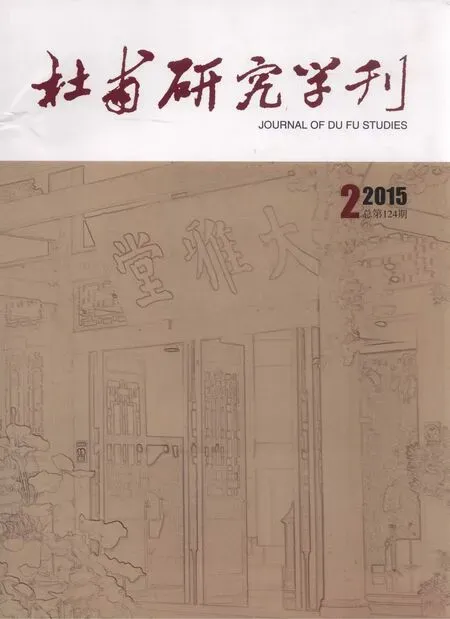从“诗史”到“词史”——论杜甫诗史观对清代词史观的影响
祝 东
“诗史”一词源于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用诗歌记录其流离陇蜀的生活经历,指具有纪实性质的诗歌,后经诗学理论批评家的推扬,发展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诗学概念,并影响到词学批评领域。清代的“词史”说源于诗史观,却又与当时政治及学术生态环境关系密切。结合诗史、词史的发展轨迹及清代词史观与清代学术嬗变关系来考察这一文学、文化现象,对把握清代文学思想史较有意义。
一、导论
“诗史”是唐宋人对杜甫诗学成就的礼赞,晚唐孟棨《本事诗》首次出现“诗史”之称:
(李白)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羁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在孟棨看来,杜诗将李白生平遭际“备叙其事”,并把自己在安史之乱中遭受的苦难也“毕陈于诗”,兼有纪实性与叙事性的特征,同时很好地展现了自己内心世界和忧国情怀,“推见至隐”,故而号为“诗史”。然而翻检中国诗学史可知诗史观念在唐代实未昌行,直至宋代,诗史说影响才逐渐扩大,“诗史”甚至成为对诗歌的最高评价。但是“诗史”观念在明代却遭到了质疑,明人对诗史说的辨正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其次从叙事技巧的角度指出杜甫并非唯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最后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而这种质疑的目的本是为了摆脱诗史观念的束缚,却使得诗史说在明代一度沉寂不闻。直至明清易代这一天崩地解时代的到来,诗史观念才开始抬头,并被不断推扬。黄宗羲、钱谦益、吴伟业等学者诗人无不对诗史说推崇备至,如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就明确重新肯定诗史说:
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晞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死,宝幢志其处所:可不谓之“诗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鹤年、席帽之痛哭,犹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尽矣。明室之亡,分国鲛人,纪年鬼窟,较之前代干戈,久无条序,其从亡之士,章皇草泽之民,不无危苦之词。以余所见者,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声、苍水、澹归十余家,无关受命之笔,然故国之铿尔,不可不谓之史也。
易代之际提倡诗史说显然具有以诗存史的目的。在黄氏看来,易代之后,历史将会被重写,有些史实甚至被篡改,而诗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一些史书上看不到的历史真实,这比前人论杜诗以诗证史更进一步:诗歌不仅能与历史相互参发、证明,而且能补史之缺。特别是在易代之际,国破家亡,史官流落,历史往往记载于时人诗文之中,一如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诗文,在此时起到了史书的作用。明清易代之际,吴伟业的诗歌亦是记录了大量史实,如《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写清军下江南学校被毁、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相,及福王朝马士英、阮大铖作乱的史实等,其《圆圆曲》揭露吴三桂卖国投降的罪行,《打冰词》叙写民间疾苦等。“梅村体”的风行正是明末清初诗史观念重新焕发生机的明证。既然诗歌能补史之缺,那么保存这类诗歌就有保存史料文献的价值意义。
此外,明清易代,满清贵族入主中原,不仅在政治上进行高压统治,还对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消解,而汉民族素有“华夷之辨”,满清贵族属于所谓的“夷族”,本身就会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排斥。故易代之际知识界有“亡国”与“亡天下”的说法,一姓王朝的灭亡是亡国,文化的灭亡则是亡天下。为了不至于“亡天下”,汉族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文献辑佚保存工作,比如钱谦益编著《列朝诗集》,就是为了保存汉民族历史文化。如其《列朝诗集序》所言:
毛子子晋刻《历朝诗集》成,余抚之忾然而叹。毛子问曰:“夫子何叹?”余曰:“有叹乎?余之叹,盖叹孟阳也。”曰:“夫子何叹乎孟阳也?”曰:“录诗何始乎?自孟阳之读《中州集》始也”。孟阳之言曰:“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
钱氏认为元好问编纂《中州集》系对金源历史的保存,意欲仿之,采诗庀史,保存文化血脉。在诗史观念的抬头及词学尊体观念的影响下,清代“词史”观念亦随之出现,如陈水云先生研究指出的:“清代词学从‘词史’意识的出现到‘词史’说的提出也是有其具体的理论背景的,这就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明确肯定诗史说复兴对词史观的影响。不仅如此,清代词史思想的发展,与清代学术嬗变关系密切,明清易代的学术思潮促进了词史观念的形成,而嘉道学术的转变则导致了词史观念的新变。因为学术背景的不同,清代词史思想对杜甫诗史精神的取舍各有侧重,概而言之,杜甫诗史内涵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为纪实性,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二即是忧国情怀与兼济天下的思想感情。
二、诗史观在清初的影响
论及词史,学界一般喜欢与推尊词体联系在一起。诚然,词史概念的提出,确实有益于词体文学地位的提高,因为“史”仅次于“经”,在中国古代文类等级体系中的地位较高,词有存补史实之功能,其地位理应提高。但是笔者认为清初词学界提出“词史”这一概念,决不仅仅是为了推尊词体,这与清初学术文化思潮有密切的联系。
明清易代,汉族有识之士为了保存文化命脉,词这种向来不为人重视的文体也受到了关注。如陈维崧《乐府补题序》就认为:“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以成声。此则飞卿丽句,不过开元宫女之闲谈;至于崇祚新编,大都才老梦华之遗事也。”即是说词体文学亦有存史之功能,像赵崇祚之《花间集》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一样,都能够补阙存史,词作同样能够保存史事,词体文学亦有史料文献意义,那么就需要注意保存;而朱彝尊《乐府雅词跋》则云存词乃是“所谓礼失求诸野也”,据《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诸子百家被视作为六经之流裔,亦可补史之阙,朱彝尊引用此言,即是明清易代之际存经存史学术思潮影响下,词体文学纳入正统学术视野受到保护的明证,在这种学术思潮下,陈维崧推出词体文学“存经存史”也就很自然了。陈其年在《词选序》中云:
客亦未知开府《哀江南》一赋,仆射“在河北”一书,奴仆《庄》《骚》,出入《左》《国》,即前此史迁、班椽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而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胜国词流,即伯温、用修、元美、徵中诸家,未离斯弊,余可识矣。余与里中两吴子、潘子戚焉,用为是选。嗟乎,鸿都价贱,甲帐书亡,空读西晋之阳秋,莫问萧梁之文武。文章流极,巧历难推,即如词之一道,而余分闰位,所在成编,义例凡将,阙如不作,仅效漆园马非马之谈,遑恤宣尼觚不觚之叹,非徒文事,患在人心,然则吾与两吴子、潘子仅仅选词云尔乎?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
在陈维崧看来,苏东坡、辛稼轩的长调与杜甫的歌行体一样,照样有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感,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不仅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而且对苦难中的人民抱有无限同情,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感,如萧涤非言“实际上是一代的史诗”。从内容上说,其价值意义堪与《庄子》《离骚》《左传》《国语》《史记》《汉书》比肩,并由此得出“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的命题,也即文人士子可以通过自己独特的禀赋才情选择合适的文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同体裁的作品本质上都是人的才性情感物化的外在形式,是一代文人心史的载体,故而“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诗词与经史的价值意义是一样的,不容低估。但是当时词坛却依然因袭有明词风,以《花间集》《兰畹集》为模范,崇尚艳词、俚词,使得词的体格不振,“音如湿鼓,色弱死灰”,因此,像这样的词坛现状亟须改变。清初邓汉仪在《十五家词序》里亦曾表达过相似的观点:
词学至今日可谓盛矣。顾理与体有不能不深讲者。夫词而谓之诗余,则犹未离乎诗,而非下等于优伶之杂曲也。感旧、思离、追欢、赠别、怀古、忧时,昔人皆一一寓之于词,而今人顾习山谷之空语,仿屯田之靡音,满纸淫哇,总乖正始,此其理未辨,而伤于世道人心者一也。温、李厥倡风格,周、辛各极才情,顿挫淋漓,原同乐府,缠绵婉恻,何殊国风,而摭拾浮华,读之了无生气,强填涩语,按之几欲昼眠,此其体未明而有戾于《花间》《草堂》之遗法者一也。
词作为诗之余,照样可以感旧怀古、忧时叹世,但如果词体文学立意不高、流连恋情悲欢的话,就会流于浮艳之途,不能与经史并称。相反,如果词体文学意格提高了,就可以取得与经史并肩的地位。“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把这种一向不被人重视的文学体裁一下子提升到与传统经史并肩的地步,这透露了清初词人的良苦用心,即用词这一清代文字狱高压之下相对安全的文体记录他们特殊的不敢轻言的感情。同时期的朱彝尊在替陈维崧的词作序时也透露了时人的这一思想:“词虽小技,昔之通儒钜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俞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即诗人不能用诗表达的情感皆由词而出之,词体文学能够委曲婉转,将词人隐秘的主观情感表现出来,这与杜甫“诗史”中含有叙事抒情的特征不谋而合。前文已述,杜诗谓为诗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用诗歌记录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发忧国情怀,表现内心活动。以词记载历史事实,表达兴亡之感、亡国之痛,在顺康之际不胜枚举,如吴伟业《满江红·感旧》,万寿祺《双调望江南》,李雯《浪淘沙·杨花》,金堡《八声甘州·卧病初起将还丹霞谒别孝山》,龚鼎孳《贺新郎·和曹实庵舍人赠柳叟敬亭》,陈维崧《满江红·秋日经信陵君祠》《贺新郎·赠苏昆生》《八声甘州·说尽西江》,朱彝尊的《迈陂塘·自题词集》等。试看吴伟业的《临江仙·过嘉定感怀侯研德》:
苦竹编篱茅覆瓦,海田久废重耕。相逢还说廿年兵。寒潮动战骨,野火起空城。门户凋残宾客在,凄凉诗酒侯生。西风又起不胜情。一篇《思旧赋》,故国与浮名。
清顺治二年(1645)颁布剃发令,而在汉族文化传统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割弃,故而剃发令遭到了汉族的强烈抵制,尤以嘉定为最。嘉定人民奋起抵抗满清暴政,结果惨遭屠戮,史称嘉定三屠。词人把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熔铸词作之中,正是以词存史的写照,这也正与杜甫号为“诗史”的作品多是反映安史之乱这一转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诗人生活心史相应,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首》等,不仅客观记录了当时君臣骄奢淫逸与老百姓饥寒颠沛的生活,同时也详细再现了诗人当时内心的各种不同思想情感,如刘文刚先生所言:“所谓‘诗史’,就是杜甫用诗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记载了自己的经历与生活、思想与感情。”只不过“词史”之史事和情感都相对含蓄一些。而陈维崧的《贺新郎·纤夫词》则秉笔直书,客观记录了康熙帝征剿吴三桂叛乱时强行征兵服役弄得人民妻离子散的凄凉史实,如钱仲联言“这是运用杜甫《新安吏》《石壕吏》的乐府精神与艺术手法入词”,所谓“乐府精神”即指词能指陈时事的实录精神。词人们借用词体文学大胆记录了社会现实,词在他们笔下不再是歌儿舞女浅斟低唱之什。如叶恭绰在《广箧中词》中所说的那样:“清初词派……丧乱之余,家国文物之感,蕴发无端,笑啼非假。其才思充沛者,复以分途奔放,各极所长。”他们在词体文学中寄予了自己的家国文物之感,甚至能够“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那么保存词籍就与保存经史一样具有同样的文献价值意义。如陈水云言:“陈维崧提出‘选词其即存经存史’,实际上就是强调词和‘经’‘史’一样记载人的行为和心态,有保存一代文献典章制度的功用。”
我们再回头重新审视陈维崧的那篇词序,其逻辑起点虽是在给词体文学辨名,强调提高词体文学的意格,其落脚点则是“存经存史”,用词体文学保存记录时代变迁中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保留词籍文献,则是从另一角度保留史料——词人心史的保留,为后世了解当时历史情况提供史料,其文献价值堪比杜甫“诗史”。这种思潮化及词学领域,使得一向不为人注意的“小词”也被文人重视保存,以期达到存经存史、保存文明之用。由此,清人不再把词体文学的研究视作小道末技,而是上升到保存一国文献的高度予以重视。像《倚声初集》《词综》等词学选本,都有保存故国文献之用心在内。从根本上说,从唐宋杜诗学“诗史”观念的发展,到清代陈维崧词史观念的提出,是对明清易代之际为了不至“亡天下”而在学术上提倡保留史料文献思潮的回应,从词体文学的角度对杜诗学的锋面进行了扩展,丰富了杜诗学史上“诗史”的内涵。
三、诗史观在清中后期影响
陈维崧的词史说第一次把词体文学上升到保留家国文献的高度予以重视,但随着满清王朝政权的稳固,其统治的“合法性”逐渐得到汉族士子的认同,加之朱彝尊主导的浙西词派倡导清空醇雅词风,适应了点缀升平的需要,词史说逐渐不为词坛重视,直到嘉、道之际,常州词派兴起发展,词史观念经词学家周济推扬才重新大放光彩。而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学术思潮的变化,人生体验的差别,周济的词史说已与陈迦陵不同。周济词史说的提出正值嘉道学术思想转变之际,是新的学术思潮影响下对词体文学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杜诗学“诗史”观在清代的进一步发展。
周济为常州词派的理论旗手,常州词派到他这里才真正开始发扬光大。而周济的词学思想基于常州学派的的学术思想而产生。清代常州词派、常州学派与阳湖文派三个学名,其组成成员基本重合,实是三位一体,如梁启超言:“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常州学派开创人庄存与独辟蹊径,研治今文经学,以《公羊春秋》为重心,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其目的在于阐发经术的经世致用之道。庄氏之学传其侄庄述祖,再至外孙刘逢禄、宋翔凤,今文学经刘、宋二人推扬,旗帜大张。同期稍后的张惠言治经学以虞氏《易》为重心,亦注重阐发微言大义。刘逢禄游京师,曾与张惠言同治易学。而张惠言的女婿董士锡曾从庄存与的侄子庄述祖学,彼此交织在一起,这样使得常州派词学打上了很深的经学烙印。张惠言论词强调比兴寄托、注重发掘词作的“微言大义”则正是其治今文经学的方法。周济的词学学术思想与词学观承接董士锡而来,如其所言:
余年十六学为词,甲子始识武进董晋卿。晋卿年少于余,而其词缠绵往复,穷高极深,异乎平时所仿效,心向慕不能已。晋卿为词,师其舅氏张皋文、翰风兄弟。二张辑词选而序之,以为词者,意内而方言外,变风骚人之遗。其叙文旨深词约,渊乎登古作者之堂,而进退之矣……余不喜清真,而晋卿推其沈著拗怒,比之少陵。牴牾者一年,晋卿益厌玉田,而余遂笃好清真。既予以少游多庸格,为浅钝者所易托。白石疏放,酝酿不深。而晋卿深诋竹山粗鄙,牴牾又一年,予始薄竹山,然终不能好少游也。其后,晋卿远在中州,余客受吴淞。弟子田生端,学为词,因欲次第古人之作,辨其是非,与二张、董氏各存岸略,庶几他日有所观省。
董士锡即是张惠言的外甥,据史料记载,董氏曾受业张皋文:“年十六,从其两舅氏张皋文宛邻游,皋文以文学伏一世,君承其旨,授为古文、赋、诗词,皆精妙,而所受虞仲翔《易》义尤精。”在学术上董士锡受到舅氏张皋文虞氏《易》的熏陶,此在其《张氏易说叙后》《庄氏易说序》亦有自述,“余为张先生惠言弟子,学《易》谨守师法”,在词学上亦是如此,“师其舅氏张皋文、翰风兄弟”,因而董士锡的词学思想亦不免受到今文学思潮的影响,注重比兴寄托。董氏与周济相互切磋词学,互为影响,而周济受董士锡词学观影响尤多,最后服膺常派词学观,其词史观念自然也受到了这种词学思想的影响: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
这段词论用典颇多,所谓“绸缪未雨”,语出《诗经·豳风·鸱鸮》:“殆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对即将发生的变故要有预感和准备;“太息厝薪”,语出《新书·数宁》:“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即劝诫不能苟且偷安,要有忧患意识。“己溺己饥”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告诫士子要有积极进取、兼济天下之志气。“独清独醒”语出《楚辞·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不可为之的情况下亦要独善其身,而不能随波逐流。这些语典之用意很明显,即提倡士大夫要有忧心天下的兼济意识,要有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这一点正与杜甫“诗史”中表现出来的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相合,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浸染,具有积极用世的思想感情。提倡文学干预社会现实,文学要有补于世,要熔铸个人的才性、学问,把由衷之言抒发出来,抒发真情实感,这样才能为后人提供知人论世之需。这样的词作,才配称得上是“词史”。由此可见周济的词史说有强烈的经世思想,而不是玩文字游戏。而当时的词坛现状确实令人堪忧:“一蔽是学周、柳之末派也。二蔽是学苏、辛之末派也。三蔽是学姜、史之末派也。”无论是学周、柳、苏、辛还是姜、史,如果言之无物的话,大抵就会堕入淫词、鄙词、游词三类恶札之中。而医治则是靠祖师爷张惠言的词作要“有寄托”这一药方,如谢章铤言:“皋文词选,诚足救此三蔽。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蕴藉,是固倚声家之金针也。”词人可以把自己的身世之感、经世之意、愤世之气等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用巧妙的笔法熔铸词作之中,使词有“史”之用,用詹安泰的话来说即“能于寄托中以求真情意,则词可当史读……作者之性情、品格、学问、身世、以及其时之社会情况,有非他种史料所得明言者,反可于词中得之也”。因此周济词史说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挥文学的政教功能,做到“言有物”,能有补于世,能为后世提供知人论世之需,而这也是晚清词坛主流的普遍创作态势。
铁甕严更月,红桥静夜霜。数交阳九颇仓皇。几载疮痍未复,浩劫又红羊。忠悃神应鉴,雄师力可降。么魔肆毒狠如狼。谁养群奸,谁使尽披猖。谁使藩篱自撒,楚汉达吴江。
词写太平天国动乱之事。当然由于受作者阶级立场的局限,其是站在统治阶层的角度对太平天国起义进行评价的,据《听秋声馆词话》记载云赵起于“咸丰十年佐团练事,贼踪近,大吏已遁,犹力守不懈。城陷,一门七十馀口投所居约园池中死。”词人亲自参与了镇压太平军的事情,并在词作中多有反应,此词直面当时的“国难”,而不再流连于词写歌儿舞女、悲欢离合,亦没有“流连景光,剖析宫调”,而是大胆反映社会现实,直面现实人生。难怪谢章铤对词作评价颇高:“予尝谓词与诗同体,粤乱以来,作诗者多,而词颇少见。是当以杜之《北征》诸将陈陶斜,白之《秦中吟》之法运入减偷,则诗史之外,蔚为词史,不亦词场之大观欤。”认为其记录现实、反映社会人生的深广度与杜甫号为“诗史”的《北征》等诗歌一样,具有较强的纪实性,并且真切反应了词人的经历与情感,故“蔚为词史”。鸦片战争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当时的词作中多有反映,充分说明“词亦有史”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而光、宣以降,西方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甚至连京师都一度沦陷,国内国外矛盾日益尖锐,晚期常派词人的词史意识更为加强,如王鹏运的《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戌军台》云:
荷到长戈,已御尽、九关魑魅。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惨澹烽烟边塞月,蹉跎冰雪孤臣泪。算名成、终竟负初心,如何是?天难问,忧无已。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愿无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
这首送别词作于光绪二十年(1894)。安晓峰,名维峻,甘肃秦安人,与王鹏运同官御史。中日甲午战争时,上疏痛斥李鸿章投降误国,并指责慈禧太后辖制光绪,后被革职发配军台。王鹏运写了这首词为他送行。词的现实针对性很强,一方面对安晓峰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赞赏,另一方面对投降派的卑劣行径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权奸为“魑魅”,祸国殃民,罪不可赦。最后勉励安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以天下大计为重。全词指陈时事,针砭时弊。钱仲联先生曾经评价此词“是辛弃疾、文天祥词作法乳真传,大为清代词史张目”,可谓的论。而晚清词史意识的高涨从根本上说是乾嘉以来今文学经世思潮对词体文学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词人们不再把词视为艳科小道,积极发挥了词体文学反映现实记录事实的功能,这些与杜甫“诗史”观中倡导的诗歌纪录社会现实、提倡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与经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杜甫具有浓厚的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反映在诗歌上即是要求诗歌有内容,有益于国家和人民,清代词人在这种精神感召下,认为词与诗一样,不仅可存史,而且可为兼济天下、激励人心加油鼓劲。
因此,如果说陈维崧的词史说还只是在易代情况下对学术界要求保存一代文明及文献史料的思潮进行回应的话,那么周济的词史说则是在嘉道以来今文学思潮影响下要求文学回归记录现实、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经世传统的发扬,也即文学向儒家政教传统的回归。词史说内涵的转变,其实是词学在语境中对当时学术思潮做出的回应,也即学术思潮和方法往往或明或暗地影响着词学思想和方法,词史说仅是其中一个个案而已。
四、余论
当晚唐孟棨用“诗史”来指称杜甫诗歌时,诗史一词从此正式步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殿堂之中,经历代批评家的运用与推扬,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概念,当然,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各个时期对诗史的运用和阐发也并不完全相同。曾有学者对历代“诗史”概念的考察发现其内涵竟达十七项之多,当然也有一个贯穿其间的核心,也即“强调诗歌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和描写”。而这一精神也正是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用诗歌记录社会现实和诗人心史中传承下来的,而且这种日益发达的“诗史”观也影响到了词学批评领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词体文学一直被视为小道末技,是一种不入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但是词体文学发展至清代,由于特殊的文化环境与历史背景,文人士大夫乐于弄笔填词,使得词体文学得以中兴。受易代之际学术思潮的影响,陈维崧等提出词史观念,指出词能存经存史的学术价值,从保存史料文献和汉族文明的角度而言,“存词存史”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分内工作。但是随着满族贵族政权的稳固,以及汉民族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加之嘉道学术转向,今文学思潮复燃,注重文学的经世精神,常州词派正是在这一学术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新兴词学流派,周济的词史说更加注重词作的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精神,与陈维崧的词史观有所不同。
相较与杜诗学上的“诗史”观,清代词学史上的词史观,前期主要是对“诗史”精神中的反应社会现实、记录历史事件及易代之际词人心史、隐秘含蓄地抒发情怀相应,后期的词史则主要是对“诗史”中蕴含的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兼济天下的忧国情怀等相呼应。由于社会背景学术思潮的不同,清代词史对杜甫“诗史”精神的取舍各有侧重,但是总体上来看,是对杜甫“诗史”精神的拓展。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词体文学这一向来不被重视的文体逐渐登上大雅之堂,提高了其文体品格,使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拓宽了“诗史”的锋面与意涵。
三组重度患者治疗前MMRC评分、6MWD、FEV1预计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策略1组MMRC评分、6MWD、FEV1预计值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和策略2组(P<0.05),见表3。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1LZUJBWZY005)
注释:
①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②陈文新:《明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4页。
③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④钱谦益:《列朝诗集序》,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⑤陈水云:《清代的“词史”意识》,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619页。
⑥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89页。
⑦⑫朱彝尊:《曝书亭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521页;第487-488页。
⑧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6页。
⑨陈维崧:《迦陵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1页。
⑩萧涤非:《杜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⑪孙默:《十五家词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⑬刘文刚:《杜甫学史》,巴蜀书社2012年版,第3页。
⑭㉜钱仲联:《清词三百首》,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7页;第301页。
⑮叶恭绰:《广箧中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⑯陈水云:《清代的“词史”意识》,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615页。
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⑱㉑㉒㉓㉔㉘㉙㉚㉛ 唐圭璋:《词话丛编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7页;第1630页;第3485页;第1618-1619页;第3485-3486页;第3529页;第2815页;第2815页;第3529页。
⑲钱仪吉等:《清碑传合集》,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921页。
⑳董士锡:《齐物论斋文集》,道光刻本,第1卷。
㉕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㉖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页。
㉗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3页。
㉝张晖:《中国“诗史”传统》,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