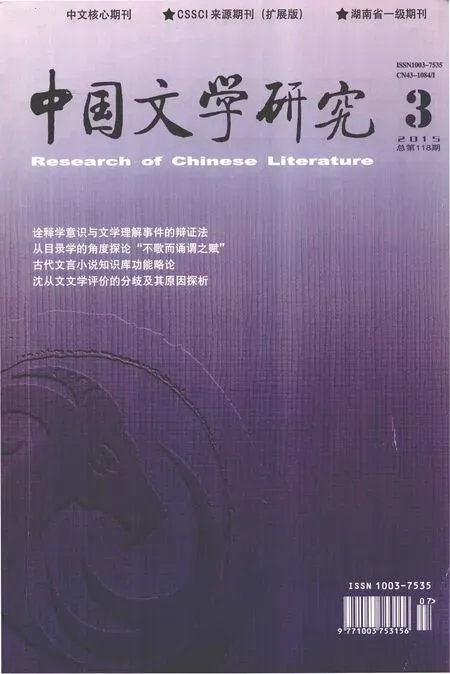“文”“史”纷纭说浩然——以1960 年代和《艳阳天》为中心
王再兴
(怀化学院中文系 湖南 怀化 418000)
1961-1962 年国家经济的调整、整顿时期,关于如何扭转困难局面和延续国家政策的方向,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之间可能产生了理解上的差异。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于搞“单干”(当时农村所谓“单干风”的包产到户风潮)可能迅速导致的“阶级分化”景象,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同时,在1961-1962 年这个相对宽松的间歇期,知识分子们一方面以专业技能受到调整、整顿方针的鼓励,另一方面因为表达了对于官僚主义等的抱怨和抨击,也争取到了某种与旧传统相通的道义正当性。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当然包括了作家们,上述政治矛盾因而也无可避免地被呈现在文学领域。1961-1963 年间,部分作家和理论家曾经创造了不同于跃进时期“全新的人”(陈伯达《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1958 年7 月)的诸多“中间人物”,并极力恢复过“真实”、或者“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如今,对于人物形象之阐释与塑造的合法性,再次成为被各方话语激烈争夺的对象:1963 至1965 年,一些大多带“新”字的组合命名开始大规模出现,如“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新英雄人物”、“新英雄形象”、“革命英雄人物”等等;《人民文学》1965 年还发起了“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的征文活动。并且,类似名词同时也被大量带入到针对“写中间人物”论、“中间人物”小说等的批判,以及其他倡议塑造“新英雄人物”的文章中。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或许也就诞生了:这样的“新英雄人物”将怎样再度申明其自身的意义合法性?他们与前此的跃进“新人”和现实主义深化时期的“中间人物”,到底有何区别?同时,在“革命之后”的中国,它又将以什么样的状态承载着继续革命和教育民众的宣教功能呢?在一个相对来说艺术手法只能算是纯朴现实主义的年代,它将如何完成一个自有阐释逻辑的讲述?在此,谨以浩然出版于这一时期的三卷本长篇“经典”《艳阳天》为例,来尝试展开一些相关的讨论。
一、什么样的“新英雄人物”?
《艳阳天》里的东山坞是一个像极了赵树理笔下的“阎家山”(《李有才板话》,1943)、和“三里湾”(《三里湾》,1955)的北中国村庄。正是这个东山坞村,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既向上接续了革命年代阶级斗争的封建性乡村空间作为前提,又向下提示了革命之后农村正在展开的社会主义斗争与建设的语境。于是,它暗中将“革命”话语——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者”的概念生产了出来。那么,在这种革命叙述的语境下,作者是如何引出一组被革命话语所笼罩的人物的呢?在相当于整部小说开篇的第一、第二章,小说的重要任务似乎就是主人公萧长春的“出场”。在此,我们想指出作者讲述《艳阳天》故事时的一种相当特别的方式:即在试图确定如何“塑造新英雄人物”的策略时,作家浩然先生引人注目地借助了“时间”(可称为拟象“历史”)的模式。因为,无论是三年前童养媳妇的死亡,头年秋天农业社的免于解体,几年后东山坞可能的“和美幸福”景象(“发展蓝图”),以及被追述的1947 年护送文件的出生入死故事,它们无不既是复沓的、涉及“私事”和“公事”的,同时又是互为注解的,即隐喻着萧长春身上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某种逻辑关系。我们无法不将其视为一种强烈的阐释冲动,尤其是当它们成为这样整齐的序列时更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它们看起来才更像是一个齐泽克意义上的“闭合的叙述”(《幻想的瘟疫》),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精心构设的说服企图。这种方式与稍早时期赵树理、周立波等的作品中往往凭借性格化的故事让人物登场的做法,是如此地不相同。这种出场形式实际上也同样适用在了《艳阳天》里作为反衬人物的马之悦身上,当然,其中作者并没有忘记在每一步都将事主描述成虽有胆气、但“心多手辣”“食亲财黑”的负面道德人物。耐人寻味的是,萧长春、马之悦的这种“出场”方式,不仅早在当年就已经被读者和批评者觉察到,认为是过多的和无必要的“回述”,而且它们在小说中并不是罕有的,反倒是绝大多数的通例——大脚焦二菊、韩百仲、马立本、马子怀、马连福、马翠清、韩百安、韩小乐、喜老头等等,都莫不如此。甚至在第一卷中已经有所表述的马之悦、马凤兰和孙桂英,第二、三卷时却又继续补述了他们更多的过往经历。这样的处理方式大多随着小说人物的登场随后不久就出现,它们如此集中、有序,让人难免不联想到激进政治时代至关重要的个人档案。
这样做,对于作家来说很难说是无意识的。如以马之悦为例,它们确实出于浩然的“历史”指认(“马之悦翻腾着自己那一套历史,胸口堵得难受……”)。但作家是如何理解这个他所谓的“历史”的呢?其一,它意味着选择和“虚构”。浩然后来曾以《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为例,谈到过写作中对于“英雄人物”与历史档案材料之间关系的个人处理方式:“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写一个英雄人物的一生并不是作为历史资料存档,而是为了让读者看,通过这个英雄人物一生的道路来看我们时代的斗争发展,从而得到经验,受到教育。”作家因而首先不是出于理解,而只是出于“依据中心取舍材料”的需要,轻易地避让了“真人真事”的原则。当然,他也同时舍弃了生活细节本身所具有的繁复、纠结的真实互文逻辑。这实际上是一个游离真正现实主义的微妙契机。事实上,这段话虽然是浩然1972 年说的,但他对于真人真事(“历史”之基)与如何写新人物的关系的类似见解,倒是由来已久的。其二,它意味着拔高及“改造”。浩然曾经多次非常明确地将“改造”视为处理素材的重要办法,如“把不正确的和落后的东西,用我们的原则精神、正确的思想标准加以改造,同时把与之对立的正确的、先进的萌芽状态的东西加以发扬——把不合尺寸的原材料,加上钢,放进我理想的‘模子’里溶解,脱出个全新的‘型体’,树立一个榜样,让做了错事的同志看了以后有所启示,有所自觉,而且效仿它”。——由于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项探讨和阐释的事业,如果轻率地这样去做,结果或许就是致命的。所谓“历史”,在浩然那里居然成了某种暧昧而又游移不定的东西,如小说中乡党委书记王国忠劝说马连福时所指出的,那一大堆各有主体、又实难区分的“公道话”等。作者甚至曾借马之悦劝说马连福的声口说出,“历史”似乎还是可以被“编造”的,“不服,瞅冷子给你扣个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再把你的历史加在一块儿一编造,那可就完了!……”这不能不让人觉得相当讶然。
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社会现实与历史材料之间严肃的互文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萧长春这一“新英雄人物”的身上,可能存在着更多无法弥合的裂隙。
首先,被浩然所承认的萧长春的主要原型人物萧永顺,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妻子、子女并且夫妻感情甚好的。但是在小说中,作者似乎为了凸现萧长春革命意志的坚定,其对于妻子和亲密生活的情感需要与安慰,可能被转译成了对“个人”的压抑与牺牲,以作为诠释的代价。如萧长春说,搞革命的也要娶媳妇,也要结婚,但是得分个时候,如果不管什么时候,总在想这种事儿,那么他就不是真正革命的;即便干工作,也是为了自己。小说甚至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升华,指其革命的“同志关系”在意义上要远胜过(可能的)夫妻关系。这是一个“革命”生活覆盖了“私人生活”的典型例证。有意思的是,虽然作家在小说中严肃地批评了马之悦、马立本、马同利、韩百安、焦振丛等人的个人主义、或者个人利益思想,并且特别提到了萧长春对于自身“个人主义”的坚决压制,但是如果这一内容确如作家在不同的创作谈里所称的那样,本身被视为“宣传”或者“教育”的功能的话,它能够达成的效果则显然是颇为令人生疑的。因为,作为上述故事讲述者和宣谕者的作家本人,在现实生活的实际中也极难达到同样的要求。《浩然口述自传》曾以他十四岁那年被推选为王吉素村儿童团长时的感受为例证,说道:
在一片很使劲儿、但极不整齐的拍打巴掌的声音中,我当上了王吉素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儿童团的团长。……掌声使我陶醉在幸福之中。这幸福里边,除了神圣、雄壮、博大之心的成分之外,在当时,在我那幼嫩的不成熟的思想意识里,还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优越感和出了风头的虚荣心。以后我被时代的大潮卷进献身血与火的革命斗争行列,再以后我倾心于文学创作,那种早就扎了根的优越感和满足感一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自觉地或下意识地起着一定的作用。随着我的年龄增长、知识增长、经验增长,以及真正的革命目标和唯物史观的确立,我曾经努力地用最伟大最无私的观念管束和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强制自己沿着最美好、最干净的轨道塑造自己的灵魂、移动人生的脚步,然而那种优越感、满足感依旧顽固地、阴魂不散地、时隐时现地伴随着我,干扰着我,折磨着我了,十有八九将要跟我同生共死。为此苦恼与怨恨也无济于事。
浩然先生上述的坦率之言,几乎从他自己十二、三岁刚成为孤儿时的“我长大了要去当官儿”,直到后来作家本人的起起伏伏的创作生涯,在这本“口述自传”里无一不得到了佐证。另外,浩然当年不仅一度被周围的人戏称为“作家精神病”,而且终其一生视写作为个人至关重要的事业,为此不惜置日常工作于不顾,甚至与上级发生顶撞,或者乃至为此撒谎而获得休假。就此来看,不知浩然先生执着于对读者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以及抨击个人主义时,是否忘却了将他自己也包括在内?而对于妻子杨朴桥所带来的家庭安慰与温暖,浩然先生自己实际上也是极为依赖的,这与小说中的萧长春又多有不同。
其次,事实上,即便浩然本人多次宣称萧永顺是萧长春的人物原型,并称萧永顺的言行给予作家的教育和影响“不仅难以计量,也难以说清”(浩然:《我与萧永顺》),但是,或许其中也有一些因素是引人思索的。河北顺义县最边远的山旮旯里的焦庄户原是萧永顺的姥姥家,农业社豆腐坊里做豆腐的老人是萧永顺的本家舅舅,类似状况被作家略有改动写进了《艳阳天》。也就是说,按照农村传统的伦理认同方式,萧长春家并不是东山坞村的“坐地户”,而是投奔而来的“外来秧”户。这一点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家来说是非同小可的,它意味着萧家可能实际上多多少少面临着融入当地社群的生存压力。这一问题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里也曾经被谈到过,从而使得小说中萧长春的模范带头作用,或许存在着一方隐蔽的意义阐释的空白“飞地”。这种“外来户”/“坐地户”的划分也是中国20 世纪农村小说中很常见的现象,如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中作为“外路人”、“外来户”的铁锁、二妞夫妻等,就是如此。此外,现实中的萧永顺在与浩然交往的数十年中,大跃进时期就曾经批评过报纸上亩产万斤的稻田高产卫星“纯粹是一派鬼话”,还在文革未结束时的1975 年,也曾私下里提醒过作家要注意与江青“少掺和为好”。后一事例虽然在时间上晚于《艳阳天》的问世,但作为萧永顺的生活态度,应该是有其一贯性的。但是显然这些带有独立思考性质的材料或者态度,都被浩然先生在写作《艳阳天》的过程中彻底地“舍”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萧长春在小说中对于党的上级和指示的坚决的信赖与服从。
再次,事情可能尚不止于此。在“个人”因素的深处,或许正缠结着难以弥平的“欲望”推动力。比如,《艳阳天》中萧长春与马之悦之间的斗争,虽然被解释成了“阶级斗争”事件,但有趣的是,这一斗争无论是在萧长春、马之悦那里,还是在王国忠、马连福、马同利等人那里,都被称之为一场东山坞领导权的“争权夺势”运动。新队长和新会计的人选之争,也因而被令人惊悚地称之为“纯洁组织”或“东山坞大清洗”事件。这么说来,权力——小说中反复提及的所谓“东山坞的印把子”,或者“稳坐江山”,难道不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欲望”吗?真实的情形毋宁说,小说开篇的“第一章”就通过萧老大对于儿子做干部的支持,对这种权力的欲望进行了确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说法在小说中并非唯一,而是弥散在整部小说中的。权力作为一种利益或者诱惑,不仅出现在萧长春、马之悦的内心独白中,同样也出现在马之悦对于马立本、萧长春对于马连福的劝说里。——甚至于它也体现在焦振茂对于儿女的自豪里,因为焦的儿子是解放军的指导员,在外边指挥着上百个人,还立过功;他的闺女则是团支部书记,“管”着整个农业社的青年男女,争强好胜,连乡里都拿她当人看,等等。特别是,这些“××个人听你的”以及“走区上县平趟”的优越感,并不是每一个普通社员都可以拥有的;马之悦甚至将这种别人对于自己的尊崇所带来的个人满足感,直接称之为“利润”,更是难以否认的将东山坞的“印把子”,即权力,诠释为“欲望”的明证了。总结起来说,种种方面可能都说明:萧长春这一“新英雄人物”形象,不仅无法否认其确实存在着诸多内涵的暧昧,而且从他与现实生活的互文逻辑上来看,也的确逊色于他的原型人物萧永顺本人的丰富品质。如果对照作者后来风格平实的《我与萧永顺》(1989)一文,这种情形可能更加明显。
二、1960 年代与“青年”问题
《艳阳天》在文本中将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解释成“革命”的继续,这并不奇怪;引人关注的,倒是这部小说在对于“革命”或者“革命者”的叙述背后,似乎还带来了新的更为复杂的意义空间。当然,这些特殊的意义空间之所以诞生,也是缘于某种特殊的语境。
例如,1960 年代前期“革命”一词的高调提及,对于文学来说出现了哪些较为特别的意味呢?其一,它是借大规模批判此前的“写中间人物”论,来申辩并倡导“塑造新英雄人物”的正当性的;同时,前者连带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深化”论,同样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借助于这一批判,重新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正当性。如发表于《文艺报》1964 年第8、9 期合刊的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等。诚然,通过否定前一时期的理论主张,来为后一时期的理论主张阐明其合法性,这本是当年波云诡谲的“斗争”年代非常常见的论述逻辑。但随之带来的悖谬,也将是在所难免的。其二,从各方面看,当年的“新英雄人物”形象在坚强的“革命”意志之外,也总让人有某种似曾相识之感。如柯庆施《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讲话,其修辞和所述“新英雄人物”形象的具体特征,与1958 年有过的赞誉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及“地方首创精神和群众首创精神”等说法,何其相似?显然,1960 年代前期关于“新英雄人物”形象的意义阐释,可能是在针对所谓“资本主义的道路”、“修正主义”等展开高调政治批判(即“革命”意谓)的基础上,一个曲折的、对于“大跃进”时代激进浪漫主义精神的某种回返。——甚至当年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内涵上也与1950 年代末的情形多所类似。其三,无论当年的“批判”文章还是“教育”运动,还同时带有一个既醒目又引人深思的内容,那就是:要切断与“旧”事物、“旧”思想的一切联系。跟前述逻辑一样,它成为确立“新英雄人物”形象所必须的另一种相形而明的阐释方式。如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中批评说,“对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感觉兴趣,可是,对那么几个谁都没有见过的已经死去很久的古人……倒是那么有兴趣,这岂不是怪事?”柯庆施则将“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的特征之一概括为:“他们……不为旧思想、旧影响所侵蚀,永远保持着无产阶级战士的本色”,并因此呼吁革命的戏剧工作者要“和一切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等等。当然,这些批判更可能是因为人所共知的、毛泽东早在1963 年12 月对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中就曾经有过的严厉指责。
然而让我们瞩目的,正是在上述“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革命队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切断与“旧”事物、“旧”思想的联系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就像1950 年代末一样,关于“青年”的话题也被再度寻找了出来。结果,“青年”话题在同时代的《艳阳天》里,也留下了自己明显的印迹。如第1 卷“第十五章”金泉河边小河滩上,东山坞“第一青年苗圃”里所发生的一群年轻人快乐劳动的场景:
年轻人为什么不欢乐呢?他们没有马之悦的那种阴谋,也没有马连福的那种烦躁,更没有弯弯绕、马大炮这般人的那种贪心。他们的心里充满着春天,春天就在他们的心里边。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欢乐和追求。这片绿生生的树苗,是他们共同的、绿色的希望。在他们的眼前,常常展现出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给他们指出来的美景。这幅美景是动人的:桃行山被绿荫遮蔽了,春天开出白雪一般的鲜花,秋天结下金子一样的果实;大车、驮子把果子运到城市里去,又把机器运回来。那时候,河水引到地里,东山坞让稻浪包围了;村子里全是一律的新瓦房,有像城市那样的宽坦的街道,有俱乐部和卫生院;金泉河两岸立着电线杆子,奔跑着拖拉机……人呢,那会儿的人都是最幸福最欢乐的人了,那些爱闹事儿,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都觉悟过来了,再不会有眼下村子里发生着的那些怪事儿了。……
然而,在这段颇为抒情的文字背后,那些所谓的“马之悦的阴谋”、“马连福的烦躁”、“弯弯绕、马大炮的贪心”到底指的是些什么呢?如果我们在此暂时悬置政治化的立场判断,我们大概可以说,马之悦、马连福、弯弯绕、马大炮等人之所以有各自的图谋或烦恼,是因为他们各自的个人欲望或者利益在他们的“经验”里曾经与现实环境产生过多次严峻的冲突;这些冲突所累积下来的压抑与仍然无法消泯的“欲望”(或者“利益”),才使他们为之困扰不已。这种个人化的“经验”,显然会参与到各主体对于眼前现实处境的解读当中。我们颇感为难的是,小说中所谓“我们”和“他们”(地主或中农)的各自不同的“经验”,实际上却来源于历史时间、空间里的同一个事实。这个异常麻烦的问题在蔡翔先生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一书中,被敏锐地称之为历史化的“记忆”。但问题更在于,同种“记忆”的真切体验,或许还有它的几乎必然伴随着的深度察觉与思虑,往往正是一般青年所缺乏的。如果我们不否认这种记忆所代表的历史事实背后,其实是难以为任何个人所全部操控的复杂现实生活本身的逻辑的话,这是否也同时意味着,青年们在通常情形下所缺少的,正是对于这种严峻生活逻辑的亲历性体验与真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就像上面引文里叙述的一样,代替可能的对于现实生活本身逻辑的理解而填充到东山坞青年们的思想里的,是高度纯化的全新浪漫图景。但是无论如何,在不否认当年先驱者们可贵的勇气与创造的热力的同时,我们确实无法否认,生活自身的逻辑依然在各个独立主体间隐秘地冲撞、调和、或者殊死搏斗着,它们没有完全消亡,甚至可能也从未减弱。这样的情景所产生的青年人与成年人之间对于现实和未来理解的巨大差异,曾在沈从文那里被称为“思”与“信”的矛盾,它也曾经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就有所昭示过。而今,它又再度出现了。
在农业生产进行到一段时期以后的1957 年的东山坞,各种旧的、新的历史“记忆”仍然鲜活地在场,它们彼此冲撞搏杀不已,形成了和平时代应该说颇具杀机的驳杂的想象景观:一方面,普通社员们对于物质丰裕及主体尊严的生活涌起不可抑止的期盼;另一方面,作为地主的马小辫仍然残存着“变天”(收回土地)的梦想,富农马斋对于刚过去不久的富裕生活抱有固执的留恋,而中农马同利、马连升等人对于单干致富、做“东家”,又有着本能般的痴迷。显然,这些想象都是同时并存而且彼此冲犯的。但是它们还不是最主要的,如果我们详加审察的话,会发现一些更加隐晦的图景或许存在于别的方面。
比如:其一,是马立本这一人物所蕴含的意味。应该说,马立本是东山坞公认的会计能手,但马立本同时也是一个积极追逐个人前途的农村知识分子。因此,东山坞农业社“高级知识分子”、“特殊技术人材”的马立本,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当年农村知识分子的寓言来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他自始至终表现着明显的“个人主义”,同时他在农业社这一“集体”内部的确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地位,工作轻松、工分不错,甚至暗中可以中饱私囊。而且他还依附于马之悦,这也意味着他与掌有权力的马之悦之间有意识地结成了某种共生互利的关系。引人注目的是,与这一过程同时发展着的另一面,正是他与劳动、以及普通农民群众之间感情和利益关系的日渐疏远。由此,马立本的故事,如果去除其政治意识形态的重彩,可否认为就是一个农村知识分子依靠他自身的“知识”和“特殊技术”资本,从而在“集体”内部获得了远高于普通成员(“社员”)的位置和利益,并出于自保意识而与某种“权力”资本形成结盟关系的例子?如果这样说并非毫无一点道理,这其中的含意将是较为复杂的,它恰恰证实了知识分子以“知识”为资本上升为社会组织的较上阶层时,可能发生的某种状态及其问题(有论者认为,1960 年代前期“党已为新的专家阶级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当然,同样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焦淑红,喻示着知识分子自我成长的另一种道路。其二,是马连福这个人物所体现出来的意味。马连福出身贫农但是住在“沟北”,他与沟北边的马姓户可能是族亲关系。这种人脉资源成为马连福在“依靠贫下中农”的年代所兼有的某种特殊资本,从而使得这个明显平庸的人做了沟北一队的队长,甚至被马之悦等人推出来当“枪”使,大闹干部会,成为“闹粮”一节的高潮事件,给萧长春一方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但作为乡村基层干部的马连福,其实是有他明显的个人利益考虑的:不仅“土地分红”事件他被沟北中农户的赠粮承诺所诱惑,也私下里违法支取过烈士抚恤金,而且他还多次挪用农业社集体的巨额钱物。其三,是李世丹这一人物所蕴含的意味。小说“第七十九章”这位大湾乡乡长的出场留下了太多令人回味的地方。但小说的确叙述了他的个人利益(“平时他不大讲究穿戴,只是愿意骑好车子、使好笔,这是为了工作方便;另外,也喜欢吃一点可口的,这又为的身体健康……”),以及相当强烈的支持“革命者”身份传统、也就是“老同志”的意识。如果说,马连福所谓“特殊人才”意味着他拥有某种特殊的“能人”资本,李世丹所谓不能让“老同志”寒心意味着他对农村干部系统的利益维护,兼之他们之间经由马之悦形成的密切的共生关系和个人交情,这些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或许意味着,在1950 年代后期社会生产初步发展之后,原先革命年代因物质匮乏而大致维持着的平均主义公平,可能已经难以为继了。社会上“物”的分配出现了差异,知识、技能、权力、能力等均成为取得“物”的分配份额的可凭借资本。这也意味着一个差异型社会在开始诞生,其实它也是迈向多样性、强流动的现代性社会无可避免的开端。但无论如何,它同时也是对于革命时代平均主义公平的一个巨大冲击,毫无疑问,它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和茫然。然而,更加引人注目的还在于,马立本、马连福、李世丹、包括马之悦等人取得社会的“物”的回报,并非全依着合法而公开的途径;不仅这种知识、技能、权力、能人等“资本”不可能为普通农民群众所拥有,而且他们之间的结盟关系和对于自身利益或者系统的维护,也同时意味着这种利益格局的某种固化和排他性,甚至形成放大效应。——这可能进一步意味着,以“物”的分配路径为隐喻的一种等级化的封建性空间,正在隐蔽地生成。这正是1960 年代前期的重要问题之一。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青年”话题在当年“革命”和激进浪漫主义的语境下,确实带来了某些全新的想象,从而成为可能引发我们思考的别样的生活内容。不过,这是问题的另外一面了。
三、浩然想象的农民“解放”
颇为吊诡的是,《艳阳天》中的农民生活,或许因为另一种与历史“记忆”之间的纠结关系,反而带来了一个对立的意义拆解过程。
小说《艳阳天》中,以往时代的舒适型生活及其相关劳动模式的记忆,最鲜明地体现在地主马小辫、富农马斋,以及中农马同利、马连升、马子怀等几个人物的身上。或许是出于当年“阶级斗争”凌厉笔法的要求,小说将马小辫描写成乖戾诡异、时刻梦想着“变天”的阶级“敌人”,但按迹追寻,却不难发现其中有着相当多的矛盾之处。诚然,作家浩然先生在《艳阳天》里做了更多巧妙的选择,从而可能回避了这一段麻烦历史的讲述的艰难,它们体现在更多的方面:比如,极少提及“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这一词汇;不愿意提到农民的饥饿而只愿提到他们的“集体力量”;不写大跃进以后的农村而固执地选择1957 年以前的农村作为表现对象;不认为文革是“浩劫”,等等——当然,这些仍然是需要继续讨论的话题。但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惊险的,可能是小说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上升为思想“宣传”与“教育”的对象这一处理方式。值得说明的是,土改后的时期,农村里的“新中农”事实上意味着勤勉生产、节俭致富的领头人,他们在乡村生活中有着天然的德性力量。这些即便在当年的中共高层文件中,也曾经屡屡得到过承认。由此,浩然的选择不仅可能罔顾了历史的真实,更可能是出于当年“继续革命”思维下某种深层的无奈:地主、富农已经在历次的人民运动中被反复地清算和管制了,他们早已经溃败和不成气候,那么,对于1960 年代更多指向日常生活的“‘物’的焦虑”,即更艰难的生活“革命”而言,由谁来继续承担作为思想批判对象的任务呢?结果,可能就是在这种逻辑下,“中农”被寻找了出来。
东山坞农业社的那些所谓“肥溜溜的中农户”,几乎都有一本勤力劳动、精于打算的过日子历史。我们讨论中农们勤劳、俭朴的生活,除了因为它的意义本身带有劳动的天然德性,同时也因为它指向了小说讲述的更大裂隙。从这方面看,《艳阳天》可能不如周立波先生同是写高级社的《山乡巨变》那么写实和坦率。小说虽然极力赞美了1957年东山坞极为罕见的麦子丰收,并将这一丰收称之为“农业社的优越性”,但事实是否如此,从小说内容来看,可能仍需存疑。这除了浩然先生的创作几乎一开始就伴随着“编造的神话”、“虚假的编造和不真实”等批评,他自己也将对于材料的“取舍”和“改造”视为创作的优先法则,此外的原因,更在于小说自身。《艳阳天》中,不仅中农们对于农业社的生产效率普遍表示着怀疑和消极,如马大炮称,不生着法子勤快点,“光等着你们农业社,就该把人活活饿死了”;一般的社员参加农业社生产,似乎也并不积极。比如在挑泥劳动中,人马来得相对齐全,从东山坞来看,“过去是不常见的”,因为通常“使什么法儿也找不齐”;就是找来了,“也得有一帮子人迟到早退”。小说虽然意指几个富裕中农有怠工倾向,但回顾赵树理谈高级社状况的文章以及周立波小说中的描写,恐怕事实不尽如此。况且退一步说,即便确实是几位中农,那么对于这个原本异常勤勉的阶层,为何要怠工也还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到小说第九十三章,一队打麦场上喜老头仍然表示,经过点名,这个队参加干活的人还是“有点不大整齐”,于是更生出挨门强制说服和命令村民、包括奶小孩妇女参加高强度劳动的事。这种相当普遍的怠工现象,显然与“个人”的生产消极性有着直接关系。小说在近末尾的第一二六章,出现了马大炮和马长山对于合作化道路的辩论,可以算做作者对此试图给出的一个阐释。这一“单干”或者“集体”的问题,同样也引起过马同利的疑惑。实际上,小说在这里无法解决的,乃是马大炮所谓“比着劲儿把地种得好好的”、和萧长春所谓“个体的日子就是你挤我、我挤你”的评价立场,到底哪一个更为正确的问题。当然,这在当年是一个极易触发某种政治敏感的话题,小说因而在这里表现出了可以理解的含混。《艳阳天》最为明显地表现出的“个人”对于“集体”生产的消极态度,可能要数第二十三章韩百安在原属于他的刀把地上捡石子,然后又放弃的事。也因此,小说中勤勤恳恳的马子怀对于萧长春说的农业社“要永世搞下去”,似乎出于一个朴实劳动者的直觉,并不大相信。甚至韩百安还叹息道,“唉,这年头还是没有东西好哇!”——我们无法忘记,马之悦向李世丹反映过,“咱们农业社……贫农比起中农是少数”,没有社员们普遍而积极的劳动,在自然条件的惠赐之外,丰收将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似乎让人凝思不已。
此外,小说更大的问题可能还在于,中农们的生活愿望其实可能只是经济的,而并非政治的,尽管从社会发展情势而言,经济的和政治的要求最终确实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但考虑到中农自身作为劳动者,以及以勤恳劳动换取合法收益的正当性,当年《艳阳天》所延用的高度政治化的“阶级斗争”策略,似乎确实是有些痕迹过重了。或许正是因为作家浩然先生对于中农“合法性”的阐释感受到了困难,我们注意到,与前述大多数以“历史”形式出场的人物不同,马大炮、马同利等极少数中农的出场,并没有连续采用“有一次……”、“有一回……”之类的时间形式,而是基本偏向了性格化。这到底是作者的一种回避、亦或是一种信任?或者是他的一种内心不知不觉的信任而外表倍觉艰难的回避?或许,后一种可能性才是最大的,因为不仅作者在小说中曾多次对于中农家庭发出过“勤俭人家”、“勤俭持家”的赞叹,它的反证亦在于: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浩然先生对于少年时代温厚地救助过他的“林南仓那边的白大叔”(中农人家;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被斗倒亡家),终其一生都保有深沉的感激与怀念:
自打那天,我的心里别扭了好多日子,总是暗暗叨念林南仓那边的白大叔一家人。不论怎么掂量比较,我都没办法把白大叔跟反革命的敌人联系到一块儿,跟我参加斗争会亲眼看到的那些恶霸坏蛋们画个等号。报纸上的文章和上边工作人员的演讲,曾经在我耳朵里灌输了许多有关地主老财搞压迫、搞剥削、喝人血、害性命的罪恶事例。所有这些我都不仅相信,而且激起过无数次的愤怒之火,烧得我想跳起来跟那班恶人去拼杀。可惜,这些在白大叔一家人身上全然失去效力,激不起一点我对他们的仇恨。相反,我倒觉着白大叔一家都是好人,斗争他们是好人受了冤屈。砖头他们不该斗争白大叔,更不该把柔弱的大婶和小小的玉子给吓唬跑,将他们一家拆散,背井离乡。那娘儿俩跑出她们的家,在人地两生的北平,肯定不会有舒服的日子过。我把这些想法都告诉了区干部黎明,他却说我被剥削阶级拉拢人的手段给骗了。
我听了这番话不禁委屈地摇摇头,说,黎明同志,你不知道我当时独自坐在漫荒野地里啥样呢,连肚子都是空的,饿得咕咕乱叫,他就算是那号剥削人的家伙,他能从我身上得到个啥呢?……
浩然为此流下了痛苦的泪水。而且,事实上,作家还对替他们姐弟俩主持公道从他老舅那里夺回一半土地、房屋,最后竟然被悲惨地虐杀的区干部黎明(原地主子弟),终生感怀着其厚德,等等。是否就是因为这种矛盾的心态,浩然先生遭遇到了对于中农们生活态度的阐释困境呢,甚至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了作为“并不太坏的地主”马小辫?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困境,浩然先生当年走向了政策化图解的“阶级斗争”策略——即在难以尽然阐释的意义含混之外,小说中延用了多重等级化的外在处理方式,以形成某种明显的区别或分野:村民有“坐地户”和“外来秧”之别,政治身份有“党内”和“党外”、“党员”和“团员”、“革命者”和“反革命分子”之别,家庭成份有地主、富农、富裕中农、新中农、贫农之别,干部有“自己人”和“敌人”之别,会议有支委会、干部会(社委会)、贫下中农代表会、社员大会之别,等等。——需要指明的是,这些都并不是为了同一种目的而形成的现代性层级组织形态,而是每一个层级都有着不同乃至对立目的(或者价值观)的区隔化政治形态。这可能是略显生硬的《艳阳天》与亲切诚恳的《浩然口述自传》之间,“阶级斗争”意识高涨的东山坞高级社与同甘苦共患难的山东昌乐东村之间,坚决支持互助组、合作社与无法直面农民的饥饿和苦难之间,等等极端反差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浩然先生的思考困境吧。这也使得《艳阳天》里的东山坞农业社的农民们,事实上只能是获得了一种区隔化的解放。
这种区隔化的解放从思想层面上来说,并未达到真正历史化反思的程度。进一步说,是否我们也可以认为,同样可能因为这种阐释困境,浩然先生对于帮助他夺回生活希望的黎明、对于与他本人有着终生情谊的萧永顺,以及助其成就了文坛声名的萧也牧、巴人等诸先生的感激,才最终都落脚到了个人的朋友之情上,而不是将其理解成理想或者思想上的呼应呢?它又与作家本人在多次政治风波中小心翼翼地规避政治风险、以保障自己可怜的写作权利这一面相映衬。我们就此断言浩然先生实际上面临着艰难的阐释困境,或者并不完全悖谬。
四、结 语
从1977 年北京工人体育场文联恢复大会上《我的教训》的检讨,到1998 年《环球时报》发表卢新宇、胡锡进的《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访谈,浩然曾经两次引起过争议纷出的“浩然现象”,一时间辩护者和质疑者纷纷著文参与了这一话题。但遗憾的是,正如有的文章提到的,批判仍然大都集中在浩然在文革时期的命运与行止上,而不是集中在对于其小说本身的分析批评上。李洁非先生的《样本浩然》一文,也对五十年来浩然研究的雷同与单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样的判断,至少说明了深入讨论和评价浩然创作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的艰难;而正是这种评说浩然的艰难,可以说,至今基本上依然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浩然又是一个麻烦的现象,包括他在山东昌乐时的作为,的确表现了对于贫苦农民的真诚同情和无私帮助。如果,我们能把1970 年代末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一定程度上认定为是对1960 年代前期某些趋势的延续(这里仅就“单干”或者“个体”而言),也许我们能够更多一点理解浩然先生对于集体生产制度的固执坚持吧,尽管当年他的表达方式或许有些粗糙和生硬。当然,小说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缺陷。譬如,在所有人物的内心独白之间完全随意地转换的全知叙事,本身就可能是一个讲述的神话,它的背后是叙事的极权与暴力主义,也是对于作者之外全部其他人物主体的全面忽视。《艳阳天》对于农民被征过头粮持歌颂态度,但同时期农民的付出与牺牲却不曾被作者深入地思考和表达;同时,他也通过对这种牺牲的改写(作家本人的创作谈中谓之“改造”)赢得了他个人写作事业的辉煌,这到底是一个关于诚实/真实的话题,还是一个关于思考力的话题呢?浩然坚信他自己是对的,或者深信“永远歌颂”的确是唯一正确的,甚至小说中反复出现了一个不容辩驳的词语“真理”,但是不管怎么说,包括他在文革中对于其他作家如老舍、章明等的态度,结果却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坚硬的“自我确信”的暴力。它也许意味着浩然先生可能对“历史”一词的厚重与严肃没有给予足够充分的关注,对于“主体”或者“批判”的复杂与纠结,亦可能没有予以更加深入的反思。小说中充满了各种关于“斗争”、“阶级斗争”、“整治”、“整”、“斗”、“收拾”等等激烈的人身治理的词语,让人为之惊悚。阅读之后,结果却依然让人悬疑不已。
〔注释〕
①毛泽东称:“一年多就会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抽大烟、放高利货,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7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
②例如,柯庆施:《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在1963 年底到1964 年初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 年8 月16 日,其中类似短语共使用10 次,仅“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就被提及了6 次。严家炎:《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 年第4 期,其中不足250 字的第一段即提及“新英雄人物”、“新英雄形象”4 次。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 年8 月1 日,该文亦提及“革命英雄人物”。等等。
③如浩然的《答〈文学知识〉编辑部问》(《文学知识》1959 年12 期)、《我写人物特写的体会》(《新闻战线》1959 年23期)。这些自述表明,浩然处理材料的方式与理性真实之间的关系,可能相当薄弱。
④浩然:《我是农民的子孙》(1980 年12 月),孙达佑、梁春水:《浩然研究专集》,第24 页。类似见解亦见于《永远歌颂》(1962 年2 月)、《永恒的信念》(1990 年4 月)等。
⑤浩然:《〈春歌集〉编选琐忆》(1972 年12 月),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浩然作品研究资料》(修订本),第167 页。另可参见浩然口述、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中的相关内容,第144 页;第190-191 页;第201-202 页,第205页,第234 页,等等。
⑥“小时候……马小辫听说了,堵着萧家门口骂半天,说萧家人是‘外来秧’、野种子,萧老大赔情道歉,才算罢休。”浩然:《艳阳天》第1 卷,第88 页。
⑦《文艺报》编辑部:《“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文艺报》1964 年第8、9 期合刊。同刊还发表了《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一文。这两篇文章后来被《人民日报》、《人民教育》、《长江文艺》、《山东文学》等多家报刊转载。
⑧毛泽东《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实习生、使馆机关干部的讲话(摘录)》(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及《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一)》(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六八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12),第250 页,第252 页,内部资料;六八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1960.12),第71 页,内部资料。
⑨例如,马小辫显然是因为财产而获罪。然而,关于土改前的财产问题,作家浩然先生本来有着亲身经历。参见浩然口述、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第34-43 页。但小说《艳阳天》将财产问题(“土地、房屋、劳动工具”等)几乎彻底原罪化了。
⑩浩然口述、郑实采写的《浩然口述自传》全本28 万字,仅提过“三年困难时期”这一词汇一次。参见《浩然口述自传》,第220-221 页,第227 页。其他在极少数创作谈里作者曾经不具有实际意义地提到过,如“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为谁而创作》,1971 年11 月),“三年困难期间”、“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春歌集〉编选琐忆》,1972年12 月)。参见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浩然作品研究资料》(修订本),第36 页;第166 页,第177 页等。浩然还表示,“农民只有合成一股劲,才能显示出战天斗地的力量”,但他实际上也有过怀疑。参见《浩然口述自传》,第138 页,第239-240 页。另外,浩然先生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故事时间均截止于1957 年。浩然先生不认为文革是“浩劫”事,参见陈徒手《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一文,原载《读书》1999 年第5 期。
〔1〕浩然.艳阳天(第3 卷)·卷后附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2〕佐平.贫下中农喜读《艳阳天》——记《艳阳天》农民读者座谈会〔J〕.文艺报,1965(2).王主玉.评长篇小说《艳阳天》〔J〕.北京文艺,1965(1).
〔3〕浩然.漫谈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几个问题——在一个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1972 年9 月)〔A〕.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浩然作品研究资料(修订本)〔C〕.内部资料,1974 年4 月印.
〔4〕浩然.永远歌颂(1962 年2 月)〔A〕.孙达佑,梁春水.浩然研究专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5〕浩然.艳阳天(第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6〕浩然.艳阳天(第2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7〕浩然口述,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柯庆施.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N〕.人民日报,1964-08-16.
〔10〕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64-08-01.
〔11〕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之一〔N〕.人民日报,1967-5-28.
〔12〕蔡翔.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3〕傅国涌.沈从文的“疯”〔A〕.耿立.21 世纪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14〕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5〕〔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M〕.谢亮生等译,谢亮生校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6〕浩然.艳阳天(第3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17〕曹鸿涛.浩然曾分辨:我不是爬虫,我是受了伤的文艺战士〔N〕.中国青年报,2008-02-26.
〔18〕李洁非.样本浩然〔A〕.典型文坛〔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