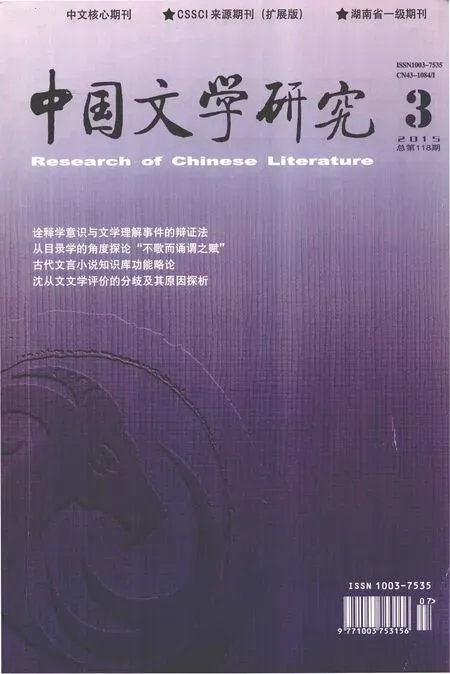诠释学意识与文学理解事件的辩证法
李建盛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北京 100101)
传统的方法论诠释学认为,在理解活动中,“理解者能够比作者更好地理解自己。”哲学诠释学把这视为一种天真的浪漫主义解释理论,它突出强调所有的理解特别是人文科学对象的理解总是从理解者的诠释学处境出发的理解,人们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人文科学对象的理解,都总是以一种时间性和历史性的视域所做的理解,诠释学意识充分意识到人文科学的理解事件所具有的此在性、有限性、历史性、语言性和开放性特征。文学属于人文科学,文学作品的理解属于人文科学理解的范畴。就文学诠释活动而言,哲学诠释学意识从作为人文科学对象的文学艺术和真理经验的特殊性出发,把文学诠释活动理解为一种此在性、时间性、有限性、历史性、真理性的事件,这种诠释学意识为我们理解文学诠释活动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根据理解事件的辩证法探讨和论述文学诠释活动的此在性与有限性、历史性与开放性、语言性与思辨性的辩证法。
一、哲学诠释学意识与文学诠释的此在性和有限性
在文学诠释活动中,我们是否可以在理解过程中毫无偏差地重建作者的意图?我们是否能够可以超越时间和历史从文学艺术作品中获得某种恒定的客观意义?对于这些问题,哲学诠释学做出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哲学诠释学认为,像所有人文科学领域的对象的理解和解释一样,文学的诠释活动同样具有此在性和有限性。
哲学诠释学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对象的理解,是建立在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基础上的,海德格尔把狄尔泰的方法论诠释学改造为一种事实性的诠释学,把作为工具论的诠释学变成了一种本体论的诠释学,伽达默尔进一步阐发海德格尔的事实性诠释学的哲学洞见。把理解看作是一种有限性和历史性的事件,一种“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理解不只是主体的各种可能行为中的一种,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它意味着构成了此在有限性和历史性的根本运动存在,因而包括此在对世界的全部经验。”从作为一种此在的根本运动的理解来看,我们就不能把文学的理解和解释看作是对文学作品中所再现的事物的认识,也不是一种超越理解者自身此在存在的理解,文学理解就是作为此在的我们的一种存在方式。
理解者作为一种此在的存在,意味着理解者始终是一种有限的历史性的存在,人的存在的此在性和有限性决定了理解者的此在性和有限性,同时也决定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所有人文科学对象的理解的此在性和有限性,由此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就不是一种客观的、中立的理解,对文学作品的所有理解都是从理解者自己的特殊历史条件、文化语境、审美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立场等等出发所作的理解,所有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都不能摆脱这种规定性。理解者总是带着这种“偏见”进入文学作品的理解中。正如鲁迅在谈到人们对《红楼梦》的读解时所写道:“《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与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因此,所有从不同的读者眼光里看出的不同意义都与读者所具有的前理解有关,他们带着某种“偏见”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
理解的此在性和有限性是哲学诠释学始终坚持的思想,文学的理解也始终是一种有限的理解。“每一种意义的诠释学经验都是有限制的。当我写下‘能够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这个句子时,便意味着被理解的东西是不可能完全被理解的。这意味着以语言的名义出现的任何事物总是意指超出用命题所能获得的东西。要被理解的东西总是要语言来表达的东西,但是,它当然总是被当作某物,当作真实的东西来理解。这是存在在自身中‘表现自身’的诠释学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保留了‘事实性诠释学’的表述,而且这种表述意味着诠释学意义的转变。”理解始终意味着有限的理解,任何理解都具有未完成性。正如格龙丹所说:“如果诠释学有什么是普遍的东西的话,也许就是它认识到它自己的有限性,也许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它意识到实际的表达是不可能穷尽的内在对话,因而推动我们去理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一种被动的始终被规定和被限制的生命存在,而是意味着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我们自身存在的境遇。我们对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的理解,以及文学和艺术的理解,都是在一种具有特定历史境遇的规定性中用某种已然具有的思想、情感、洞见去观看、理解和解释我们所面对的东西。这是我们理解事物,理解文学和艺术作品得以出发的某种前提条件。
理解的此在性和有限性的诠释学意识给予文学理解和诠释的重要启示是,每一个对文学作品进行理解的人都是一种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存在,作为有限性和历史性存在的人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都具有有限性、历史性。对于“终有一死”的人的理解来说,对于任何东西的理解都是此在性和有限性的,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想获得唯一的、最终的、客观正确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完全重建作者或文本的意义,理解始终是此在历史性的一种运动方式,文本的理解只能是有限的理解。从根本意义上说,人们对历史上的每部文学作品所做出的理解都是在一种历史性的环节中所做到有限的理解,所做出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历史环节中的环节之一,站在某种历史语境中的每个时刻的理解,而不是一种被终结了的理解和理解了的终结。
二、哲学诠释学与文学诠释的历史性与开放性
哲学诠释学认为,那种认为我们可以在理解中完全客观地重建文学作品意义的传统诠释学理论,严重地忽视了理解的历史性和开放性。“伽达默尔诠释学最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也是最困难的地方便存在于对理解以及对理解发展和变化条件的描述中。”在理解如何可能的问题上,哲学诠释学体现了对传统诠释学的挑战,也体现了它对这个问题的独特理解。这对于文学的诠释问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哲学诠释学通过如下三个问题探讨了理解的历史性和开放性问题:第一、根据我们历史性的存在,什么东西被带进了文学的理解事件中?第二、作为具有自身有限性和历史性的理解者,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同样具有历史性的文学文本?第三、在作为理解者的我们与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之间所发生的理解所产生的结果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理解过程所导致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对于第一问题,哲学诠释学批判了启蒙运动的理性意识,重新恢复了偏见(Prejudice)在人类理解活动中的合法地位。启蒙运动的理性意识认为,要获得客观的、中立的认识就必须摒弃和排除一切偏见,只有不带偏见地认识事物,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事物。但在哲学诠释学看来,这种认为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并且能够消除所有主观性地理解所有事物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偏见。理解者的此在性、有限性和历史性决定了理解者永远不可能消除他所具有的偏见。“如果我们想公正地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就必须从根本上恢复偏见的概念,并认识到存在着合法的偏见。”因此,对人类的理解事件来说,权威和传统并不像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必须抛弃的东西,恰恰相反,这是具有此在历史性的理解必须正视的东西。理解始终是由具有前理解的参与运动所决定的,哲学诠释学认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恰恰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历史性的真实存在,这意味着我们总是以某种方式理解世界。
同样,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也总是从我们所拥有的前理解、前见解和前把握出发的一种意义筹划,对前筹划的每一次修正都是进行新的筹划。“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所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文本,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在对文学作品的每一次理解和解释中所把握的意义,都将在不断理解的过程中被新的把握所代替。理解是一种不断地向未来筹划的过程,我们总是在这种筹划中联系着文学作品文本和我们自己,并在这种筹划中实现文学理解的可能性和意义的可能性。
对于第二个问题,哲学诠释学认为,理解者可以通过克服时间和历史距离达到对文学作品的完全理解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文学理解事件中,时间距离并不是一种需要克服的消极因素,而是积极的诠释学动力。“诠释学的任务是以熟悉性与陌生性这两极为基础,……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张力存在于传统文本的陌生性与熟悉性之间、具有历史地意欲的、距离化了的对象与传统的隶属性之间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介乎两者之间。”对于文学诠释活动来说,理解的熟悉性和陌生性也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前者是构成我们的理解得以实现的前提,后者则是构成某种事物应该理解的必要性。一部能够完全为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作品,就没有理解的必要性,一部完全不能理解的文学作品也无法做出理解,正是理解者与作为理解对象的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着这种熟悉性与陌生性的张力,才提供了理解的可能性空间和意义的阐释空间。因此,我们并不能够完全占有文本意义,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与文本的相互关系规定的,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不可能是超越时间距离和历史距离的理解和诠释。换言之,我们总是在时间距离和历史距离中理解我们所要理解的文学作品,而且正是这种时间距离和历史距离赋予了理解的动力和张力。
对于第三个问题,哲学诠释学用“效果历史意识”(historically effected consciousness)理论进行了回答,“效果历史意识”所体现的是理解的有效性与理解的开放性的辩证法。所谓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意味着理解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诠释学处境。我们的存在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这种效果历史规定了效果历史本身的有限性和开放性的真正意义。理解者总是处在所要理解的文本或历史传统相互关联的处境中,在这种处境中所做的对效果历史的反思,并不是在一次性的理解中完成的。但这种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却并不意味着缺乏反思性,理解者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一切自我理解都是从历史的已经给定了的东西开始。效果历史意识既是受历史影响的效果意识,也是对效果历史的意识。
就文学的理解和解释活动而言,效果历史意识就是一种持续性的、不间断的历史事件。在理解过程中,理解者从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距离去理解历史上的文本,只有在一种历史性的诠释学语境中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才具有一种真正的历史视域。“当我们的历史意识置身于历史视域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进入与我们自身毫无联系的异己世界中;这些视域倒是共同构成了在自身内运动的一种巨大视域,而且超越了现在的界限,囊括了我们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深度。”只有获得了某种恰当的问题视域,理解者才有可能不断地对自己的前理解、前见解和前把握进行修正,并在新的提问与回答中达到新的视域融合,从而实现文学理解的有效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
因此,在文学的理解事件中,理解既是一种历史性运动,也是一种开放性的运动,理解并不像浪漫主义诠释学那样所认为的是一种主体性行为,而是一种置身于历史过程中的行为,是一种历史事件,是过去和现在得以不断地中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解者与文学作品之间不断地获得新的视域,并在新的理解中达到新的视域融合,文学理解的有限性、历史性和开放性辩证地统一在理解的效果历史事件之中。
三、哲学诠释学与文学诠释的语言性和思辩性
哲学诠释学不仅把方法论诠释学转变成了一种本体论的哲学诠释学,而且把语言问题置于诠释学的中心地位,使理解的事件成为一种语言的对话事件。“伽达默尔把视域的融合扩展为一种辩证的视域融合,扩展为一种对话,本文向解释者提出问题,解释者也向本文提出问题。对话总是可能的,因为无论是本文的作者还是本文的解释者都用语言来言说,不管他们说的是不是同一种语言。对作者和解释者来说,理解就是发现一种表达他们所理解的东西的语言。”对话中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有限性和历史性存在,并在本体论上阐述理解的语言性和思辩性问题,这种理解的语言性的探讨对文学理论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阅读和文学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毫无疑问都是在一种语言事件中实现和展开的。
首先,哲学诠释学认为,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就是人的存在方式。“语言是我们在世存在的基本模式,也是包罗万象的构造形式。”人类拥有世界的同时就是拥有语言,拥有语言也就是拥有世界,我们总是通过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经验,语言使我们拥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来说,文学作品的语言就更不是某种简单地再现和反映外在世界的符号和工具,而是以其语言经验的方式为人们创造了具有自身丰富性的意义世界。伽达默尔写道:“很显然,对我们不断地变得熟悉的不仅仅语言中的词语和短语,而且是在那些语词中也被说出的东西。当我们在语言中成长起来的时候,世界就在接近我们,并且最终获得了一种特定的稳定性。语言总是为引导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提供了基本的表述。语言具有与世界一致性的本质,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与另一个对象交流,我们都共享这个世界。”正因为这种特性,人类才能通过语言的文学作品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经验,创造而不是复制可以为我们经验的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和意义无穷的文学世界,并让人类在这种语言创造的经验世界中认识世界和我们自身的存在。
语言的世界总是一种开放性的世界,我们总是能够从语言的变化中看到人类的经验世界的变化和发展。这开放性同样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诗歌通常成为对某种真实的东西的证明,因为,诗歌在似乎已经耗尽和废弃的语词中唤起了一种隐秘的生命,并向我们讲述关于我们的东西,很显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语言所能做到的,因为语言并不仅仅是反思思维的创造,而是它自身塑造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确定的方向。”因此,文学作品的语言总是反映着经验世界的变化,人们也通过文学语言所展示的经验世界理解自身。通过对人的存在的语言性、语言表达的事实性、语言的建构性、语言的开放性的论述,伽达默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语言中,世界本身表现自身。对世界的语词的经验是‘绝对的’。……语言和世界以一种基本方式相联系,并不意味着世界成为了语言的对象。毋宁说,认识和陈述的对象总是已经被语言的世界视域所包围。说人类世界经验是语言性的,并不意味世界的对象化。”所以,文学活动的所有方面,无论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还是阅读,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都必须经由语言这个中介,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文学活动。
其次,语言的世界经验的绝对性决定了理解事件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语言性的。理解就是一种语言事件,正是在理解的语言事件中,文学作品文本能够在语言中被理解,理解也能够通过语言被表达出来。
从被理解的文学作品来说,文学作品不只是某种被保留下来的东西,也不是一种仅供我们研究和理解的对象,而且总是以其自身的表现性向理解它的人述说某种东西。一切传统的文学文本对于一切时代都具有某种同时代性,它超越文本的过去世界进入到当前的视域中。因此,通过我们的理解,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意义可以成为我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并在理解和解释中延续着文学作品的意义世界。从文学作品的理解者方面来说,只有通过阅读和理解活动,文学文本才能转变为语言,才能把文字符号理解为意义。文学的阅读和理解的意识是一种有限性的和时间性的历史意识,是与历史上的文学作品自由交往的意识。对于具有有限性和历史性的理解者来说,任何阅读和理解都不是一种非时间性的或超时间性的阅读和理解,而是一种从此在存在的历史性和时间性出发所做出的阅读和理解。因此,在文学理解和解释活动中,无论对被解释的对象,还是对解释者来说,文学的意义和价值都是在解释性的语言事件中实现的。
最后,正是基于语言性的世界经验的绝对性和理解的语言性,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提出了“能够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的著名论断。“能够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这意味着它具有这样一种本质,其自身向理解显示着自身。这里也证明了语言的思辨结构,进入语言并不意味着获得第二种存在。更准确地说,表现自身的东西属于其自身的存在。因此,所有由语言显示的东西都具有一种思辨性:它具有一种区别,一种其存在与其自身表现之间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又根本不是一种真正的区别。”哲学诠释学不仅充分体现语言的本体论诠释学特征,而且把理解的语言性与人的此在存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结合起来揭示语言的思辨结构。这一点对于文学诠释活动辩证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种思辨结构首先体现了我们的文学经验的有限性与语言的有限性关系。哲学诠释学认为,在文学语言中,存在的结构并不只是一种反映,文学语言不断地创造着我们经验的秩序和经验结构,正是在这种经验有限性和语言有限性的辩证结构中,并以语言为中介,人类创造了文学作品,人类也经验着文学作品,感受着文学的审美经验,理解着文学的意义,走进文学创造的审美世界之中。同时,哲学诠释学意识也体现着理解的有限性和历史性的辩证结构,“只要每一个解释都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而且试图超越那种由陈规老套形成的片面性,解释就是具有所有有限的、历史存在的辩证结构。对解释者来说,似乎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必须被说出和得到解释。所有的解释都是由这种方式来激发的,并且从这种激发中获得其意义,解释通过这种片面性就强调了事物的另一方面,从而为了取得某种平衡使某种东西的其它方面也被说出。”语言的思辩性蕴含着理解活动中的对话辩证法,理解总是一种在语言性的对话中展开的事件。
这种语言性和思辨性的辩证结构体现在文学理解和诠释活动中,就是我们首先应该倾听语言向我们所诉说的东西,文本向我们发出召唤,向我们提出问题,并对文本提出的问题做出答复;同时,我们也向文本提出问题,文本也在理解事件中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在理解事件中,理解传统的语言文本的倾听者通过对文本的阐释,把文本的真理纳入到自身的语言世界关系中,当下和文本之间的语言交往就是理解活动中进行的对话事件。一个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甚至一首短诗(如《登幽州台歌》,所以能够体现无穷的韵味,展示丰富多维的意义世界,也许正因为它们深刻地体现了哲学诠释学所揭示的人类语言经验的辩证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学作品展开的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世界,是在有限性的语言表达中展示的一个无限的人类精神世界,延续着文学作品的生命,丰富着文学作品的内涵,传递着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和人文精神。
总之,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看,我们对历史上的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的理解,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对象性的理解,也不是一种超越当下经验的超验性理解,理解总是作为此在存在的人的理解,这些理解同时属于诠释学的经验。理解者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就像两个人之间的谈话一样,总是在谈话事件中通过倾听、提问和应答的过程来达到相互理解和充实丰富。文学诠释活动就是在具有效果历史意识的效果历史事件中展开的理解的此在性与有限性、历史性与开放性、语言性与思辨性的辩证运动,正是这种作为此在存在的历史性和有限性的诠释活动赋予了文学更丰富的内涵、更深刻的价值、更开放的可能性诠释空间。
〔1〕Hans -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M〕.New York: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9.
〔2〕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3〕Hans-Georg Gadamer. Foreword to the second Edition〔A〕.Truth and Method 〔M〕.New York: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9.
〔4〕鲁迅.鲁迅全集(第8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Hans -Georg Gadamer. Text and Interpretation〔M〕.Hermeneutics and Modern Philosophy 〔C〕.Brice R.Wachterhauser(ed.)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6.
〔6〕Jean Grondi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
〔7〕David C.Hoy. The Critical Circle: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8〕Weinsheimer,Joel.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Literary Theory. New Haven & London,1991.
〔9〕Hans-Georg Gadamer.On the contribution of poetry to the search for truth〔A〕.The relevance of Beautiful and Other Essays〔C〕.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