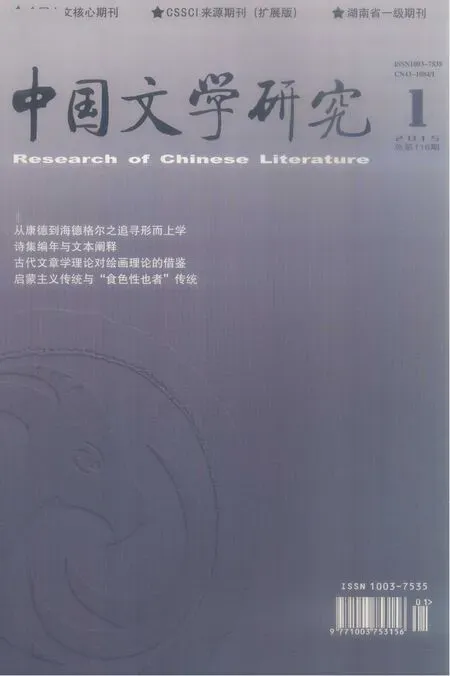学院传统与诗性情怀——评杨经建《20 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
董外平
(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都说文史哲不分家,但真正做到的并不多。随着学科发展的细化、专业化,文史哲之间的界线变得泾渭分明,学术研究朝着所谓“专业”的方向越走越狭窄,学科之间的壁垒和偏见日益深重。由于人类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单一的专业知识和视野已经捉襟见肘,不足以充分认识和解决问题,当今的学术研究需要交叉的专业知识和多元的学科视野,否则很难获得真正有效的研究成果。文学是一门包容性很强的学科,它几乎涵盖所有人文社科的命题,无论政治、经济、历史,还是哲学、宗教、伦理,都可以在文学世界敞开谈。文学文本是一个无限开放的文本,它的价值远远超越文学本身,如果我们还死守所谓的“文学性”,文学研究很可能变成自娱自乐、无人问津的东西。在文学不断边缘和衰落的今天,重建文学研究的影响力必须借助日益重要的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野,充分发挥文学文本的多维空间。
杨经建早期从事的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文学研究,曾出版《世纪末的文学景观——90 年代小说创作现象研究》、《家族文化与20 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这两本书探讨的都是比较“文学性”的问题。自博士论文出版之后,杨经建开始转向文学的“哲学性”研究,近十年他一直都在做“存在主义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课题,几乎花费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不用多说,自古以来,文学就与哲学紧密相连,优秀文学往往具备哲学的深度,形而上的哲学往往以文学为载体。在20 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潮中,与文学走得最近的当属存在主义哲学,萨特、加缪、波伏娃直接将存在主义哲学运用到文学创作,并且形成一种以哲学命名的“存在主义文学”,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存在主义文学既是文学的也是哲学的,文学与哲学融为一体,这为跨文学与哲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存在主义文学”概念的合法性无需再论证,问题的核心是“20 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合法性。“存在主义”与“文学”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关联才能被称为“存在主义文学”,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作品毫无疑问是存在主义文学,但那些未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却具有某些存在主义内涵的作品算不算呢?这是杨经建一开始就面对的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研究的合法性岌岌可危。杨经建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他专门写了《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2011 年出版)这本书,全程论证为什么存在主义是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的文艺思潮,大有“为20 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一辩”的气势。合法性问题解决之后,杨经建才敢着手20 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研究,只有先“存在”,才有“史”的问题,杨经建一贯严谨的学术态度由此可见。但是,从这部书可以看出,杨经建依然感到“合法性”的焦虑,他没有单纯地叙述文学史,而是采用史、论结合的书写方式,其中“论”的部分承担大量“合法性”的论证工作。
杨经建先从整体逻辑上论证为什么20 世纪中国会出现存在主义文艺思潮。判断某种国外文艺思潮是否存在必须建立在影响和实践的事实上,影响是最基本的证据,实践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能够证明存在主义影响中国并被作家广泛吸纳、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20 世纪中国的确出现存在主义文艺思潮。杨经建紧紧把握两个事实逻辑:其一是“西学东渐”,作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思潮,存在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性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存在主义能够扎根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与吸纳,杨经建认为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正是这种精神契合使得中国作家容易受存在主义的影响。
“合法性”的整体逻辑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文学实践层面的事实论证。文学实践的论证构成了本书“史”的框架,同时也显示了史、论结合的论述风格。杨经建必须双面作战,一方面要描绘出20 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一方面又要证明不同历史阶段的存在主义文学具有合法性。在杨经建看来,20 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可以划分为六个历史阶段:“五四”新文学运动、早期象征诗派、30 年代的新感觉派、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作家群、50-70 年代的红色文学、新时期文学。在这六个阶段建立统一、连贯、完整的历史逻辑和内部秩序并非易事,文学的发展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多变,从中拉出一条脉络清晰的线索总是会遇到各种梗节和断裂,若是不太重要的文学现象,我们当然可以随便跳过,若是重大的文学现象,轻率地绕过整个逻辑就会失效。杨经建的逻辑推理能力令人惊诧,他像一台马力十足的挖土机在杂乱无章的文学地形中打通了一条存在主义文学的通道,其中的艰难险阻也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杨经建一定遇到不少像花岗岩一样坚硬的难题,但是本书最富创见和思想火花的恰恰是那些顽石被凿开之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遇到的最大难题应该是如何论述50-70 年代的文学。红色时期的中国文学几乎与世隔绝,除了马列主义,其它现代思想都被拒之门外,存在主义根本无法进入人们的思想视野,也就是说50-70 年代的文学不可能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也不可能进行存在主义的文学实践。50-70 年代显然构成了一个表层断裂带,但是谈及20 世纪中国文学又不能绕开50-70 年代,杨经建面临严重挑战,他必须在真空地带建构一种关联。当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时候,杨经建发挥了他魔鬼般的逻辑思维能力,他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中找到灵感,否定并非消失,而是获得“非同一性”的存在。50-70 年代的文学对人的否定是“存在”的一种反证形态,人的“存在”并没有消亡,只是以“非同一性”的形态存在,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如是观之,50-70 年代的文学依然可以纳入存在主义文学的视域,它以逆向悖反的方式维持着与存在主义文学的价值关联,是存在主义文学一种特殊的反证式形态。这个论断太精彩,太让人为之拍手称快了,也许只有杨经建才能想到,我们没有理由再去质疑20 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合法性。
杨经建严谨、深入的逻辑思维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学院派批评,不知从何开始,人们对学院派批评的印象就是学究、刻板、晦涩、无趣,真正的学院派批评其实并非如此,如果读过耶鲁学派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学院派批评的正统、厚重和迷人的深邃。杨经建是典型的学院派批评家,比起花哨的遣词造句,他更擅长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深度的哲学思考,这也许和他多年来潜心阅读德国哲学有关,德国学派周正、严谨的学术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他,他从康德、海德格尔、胡塞尔那里学会了极具思辨的学术风格。杨经建是一个善于思辨的学者,我总是被书中咄咄逼人的思辨折服,学术思辨的魅力在于能使一个无序、混沌的世界变得井然、清澈,杨经建的思辨旁征博引、曲径通幽,在人意想不到之处妙笔生花。可以说,没有杨经建的思辨才华,就没有这部20 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
假如我们就此认为杨经建是一个严肃、冷漠的学院派,肯定会产生深深的误解,存在主义在德国是理性的,但在法国却是感性的,杨经建继承了德国学派的理性思维,又感染了法国学派的浪漫之风,他的内心同时住着海德格尔和萨特,很多时候,萨特更是占据主导位置。杨经建体验最深刻的也许不是“存在与时间”,而是“存在与虚无”,他之所以花费十年光阴研究存在主义文学,与其自身的精神危机有关,虚无感笼罩在他的精神世界,一直挥之不去。本真的学术是解决自己与世界的问题,他试图通过存在主义文学研究认识自己的人生处境,同时又把存在主义文学当做知音,分享、化解自己的虚无。这本书既是理性之书,又是诗性之书;既是学术之书,又是救赎之书。
从2011 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20 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到这本即将出版的《20 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杨经建十年的存在主义之路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项工程太艰难、太伤元气,十年之后,他由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我想所有的付出对于他一定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