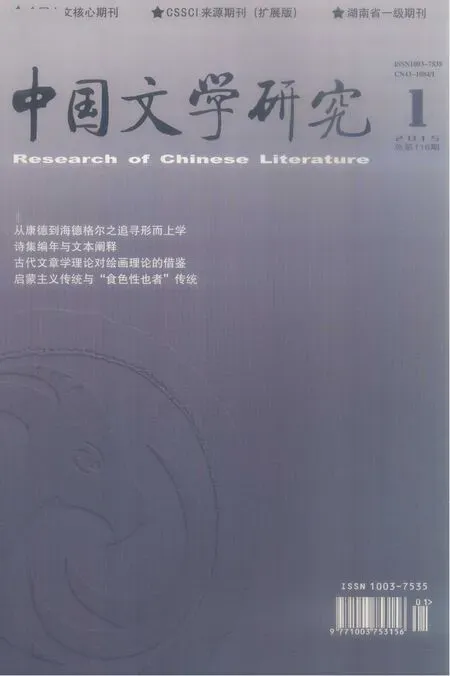从《运甓漫稿》探寻李昌祺晚年思想与诗风的转变
李 华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李昌祺(1376-1452是永乐帝首届翰林院庶吉士中一员,明初著名文人。他小说、诗词皆工,诗词集《运甓漫稿》在当时已广受瞩目。时人陈循曾作序赞之:“本之以理,充之以气,故雅淡清丽、宏伟新奇,无不该备。不必远较于古,就今而论,千百之中不过数辈”,评价颇高。李昌祺一生命运坎壈,其人生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永乐二年(1404),中进士二甲二十九名,次年选授庶吉士,得到了永乐帝的大力培养。此后与修《永乐大典》,并于永乐四年(1406)书成后升任礼部主客司郎中。翰林院、礼部的这段经历使他一度成为了儒家伦理的拥戴者、践履者与世俗名利观的希慕者、追逐者。随后他连遭两次罚役、两度外任,中年宦游飘零、贫病交加的境遇促使他跳出台阁、翰林的束缚,深入体察民生疾苦,痛惜自身遭遇,寻找疗救现世痛苦的良药。正统四年(1439),他“不待引年坚乞致仕”,此后隐居江西老家十余载,直至景泰三年(1452)辞世。隐居期间,李昌祺深刻反思了名利价值观,并最终在老庄、佛教思想的指引下,推翻了早年以“名”为核心的人生价值体系,摆脱了功名富贵的牵绊,从田园生活中获得了心灵的淘洗与重生。他的诗歌也逐渐从台阁体的窠臼中走出,形成了情感真挚深沉、语言明快质朴、用韵突破诗体限制的独特风格。李昌祺一生尤其是晚年的这种转变十分值得关注。作为其一生心血所集,《运甓漫稿》见证了这一转变,故本文以其中所收诗歌为据加以探究。
一
早年身居翰林院、礼部之际,李昌祺作为科举的受益者,对当时的主导思想程朱理学由衷信奉,将儒家纲常伦理奉为圭臬。他时刻以道德楷模为己任,不断在诗文中宣扬忠孝节义的重要性。就个体价值而言,他几乎全盘接纳了“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并认为不朽的根源在于“名”的确立。“名”是他早年人生价值体系的核心。“人生孰无死,礼葬固所贤。等为归腐朽,终当随化迁。所以旷达士,形骸岂复怜。佳名苟不没,讵必分乌鸢。”(《哀萧教授引之》)他认为“名”是人区别于自然万物的重要特征,是人内在精神和社会价值的显现,只有“名”可以超越生死的界限,通过“名”的确立,个体的社会价值和精神内涵得以流传不息、永垂不朽。
与此相应,李昌祺此时追慕、效法的是雍容典雅的台阁诗风。永乐帝雅好文学,时常召集庶吉士、群臣吟咏为乐,并亲自品评高下。他对庶吉士期望极高,要求他们“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除了参透儒家典籍,还需熟知史传文献、汉唐诗文,力争与前代大家媲美。出于争竞心态,庶吉士多以炫才为好,作诗好用典故,以铺排辞藻为美。作为政府代言人,他们又须遵循儒家“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作诗讲究格调高雅、中正平和,内容以颂为主,或歌功颂德、描写繁华,或表露忠心、宣扬教化,大体不离儒家教义。为了炫耀文才、渲染繁华,诗篇也多采用古体或律体长篇,极尽铺陈、华美之至。这样的诗风与当时杨荣、杨士奇为主导的台阁诗风并无二致。
庶吉士、礼部官员时期,李昌祺的诗风也大体如此。虽文辞华美、敷衍长篇,但碍于思想、视野的局限,普遍平庸肤浅,不仅缺乏新意,且流于板滞。如七言长篇《驺虞歌命补作》,洋洋洒洒,穷尽华藻,摹写驺虞的奇特之形和祥瑞现世、万民欣悦的盛世气象。“底须想象空摹影,幸遇升平真见形。共诧奇祥冠今昔,谁知宵旰存谦抑。所重年丰所宝贤,洛龟宛马诚何益。荡荡巍巍昌运开,熙熙皡皡似春台。永沐周南召南化,为歌为颂愧非才。”诗歌结尾极力颂扬皇家恩泽、渲染盛世太平,纯然台阁体的路数。
如果说李昌祺早年的科第、仕宦生涯是无数士子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命运多舛的中年遭际则令他逐渐走出台阁翰林,对社会人生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和更深入的思考。“两涉忧患”的经历让他深切感受到仕途的险恶和君臣关系的冰冷真相。“人心变幻几千般,带砺盟深亦易寒。秦网逃來逃汉网,谁将此意语萧韩?”(《舞阳留侯庙二首》其二)古往今来,君臣之间何曾有真正的平等与尊重,一切到头来不过是利益的计算。逆境之中朋辈的疏离也令他痛心不已,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现实让他备受折磨。广西、河南布政使的从政经历更让他切实体察到下层百姓的生存艰难。其七绝《过张茅镇见饥民》便描摹了遭受严重旱灾后百姓无力耕耘,为充饥不得不爬上高梯剥食树皮的惨痛场景:“土洞深沈土坑欹,田园枯旱废耕犁。一身馁困浑无力,犹上高梯剥树皮。”
在深入体察社会苦难,沉痛咀嚼自身苦楚之后,李昌祺发生了思想、诗风上的第一次转变。他不再是那个在台阁优渥生活下充满幻想的庶吉士、礼部郎中,而是一位经历过世事盛衰,见识过社会万象的“士”;他不再仅仅沉迷于个人功业的得失,而将更多心思放在社会大众尤其是饱受苦难的下层百姓身上,他在较高境界上领悟并践履了儒家的仁爱之道。与此相应,其诗风也逐渐转向杜甫、白居易一路。语言由浓艳华丽转为质朴直白,诗歌体式中歌行、排律有所减少,律诗、绝句大幅增多。也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李昌祺创作了笔记小说《剪灯余话》。小说在当时为文人士大夫所不齿,此举似乎意味着他开始有意背离、反叛自己所在阶级的价值观。
二
晚年致仕之后,物质、精神的困乏令李昌祺困惑、纠结不已,现实的矛盾、痛苦萦绕于心,他试图通过老庄、佛教思想来化解矛盾,寻求隐逸生活的精神支撑,寻觅田园生活的乐趣与美感。
初回家乡,李昌祺难以顺应从地方大员到一介平民的身份转变。由于为官清廉,没有多少财富储备,退隐之后,他的生活十分清苦。长期身处农村、远离政坛,他无形中被昔日友人疏远,周围又大多文化不高的农民,几乎没人能与他进行深层的思想交流,他难免有精神孤立之感。“小市三楹屋,荒村数亩田。南交同宦者,若个在林泉?”(《逢索员外话旧》)贫病交加、孤寂索寞是他乡居生活的真实写照。
作为隐士,李昌祺的最大思想难题在于消除对“名”的依恋,使自己安于困顿的生活现状。名与利关系密切,皆为世俗价值观的核心。“名”是个体价值的外显,“利”是个体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天下攘攘,皆为利来;天下熙熙,皆为利往”,追名逐利是人的本性。李昌祺早年也曾痴迷于功名富贵,虽然坎坷的仕宦经历使他一度厌弃名利,但作为曾经的庶吉士、地方大员,要真正背离世俗、断绝名利之念显然并非易事。
与世俗价值观相反,老庄对名利基本采取否定、摒弃的态度。老子说“‘道’常无名朴”(32 章),“‘道’隐无名”(41 章)。庄子进一步提出“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人间世》),视“名”为引起社会纷争的罪魁祸首,贬斥甚深。《骈拇》篇更总结道:“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认为个体无论处于何种社会阶层,追求的是名或利,都会给自己的生命和精神带去损伤。如此,生命和精神的保全才是第一位的,名利只是个体的负累乃至祸害,必须坚决加以摒弃。
但是,对士人而言,背离世俗意味着孤独,意味着被主流群体所孤立,要真正摒弃名利、摆脱个体的依附地位,必须割裂与统治阶层、官僚集团的联系,由此带来的失落感不言而喻。为了化解孤独、失落感,庄子提出了“无用”观念。他以散木为例,宣称“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人间世》),既道出了“无用”的自我保全作用,又暗示了“有用”的风险。他又进一步举例道:“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养生主》)指出被统治者任用、豢养非但不是值得庆幸的事,反而是对个体的束缚。所以庄子宁愿“生而曳尾于涂中”,也不愿“死为留骨而贵”(《秋水》),在名利与精神自由之间坚决选择后者。
坎坷起伏的官宦经历使李昌祺能够真正认同老庄的人生观。他早年曾对功名富贵孜孜以求,中年沉浮宦海数十载、历经荣辱兴衰,切身体察到繁华背后的虚伪、屈辱与风险,晚年最终调整心态,毅然切断与官场的联系纽带,坚守隐逸直至终身。“人生慕富贵,方寸徒忧煎”(《即事》)、“多财信为累,达宦真虚名”(《夹翠楼》)、“徇名与徇利,均死何后先”(《题亡羊图》)、“久矣厌流俗,稍与世背驰”(《题松菊堂卷》)、“俯仰天地间,百年复何如。寄语达生者,浮名岂能拘”(《题晩香堂二首》其一)等诗句,句句都是充满人生历练和感慨的内心独白。受老庄思想影响,李昌祺晚年彻底从名利的泥沼中脱身出来。“多谢天公着意栽,不教妆点艳亭台。无人剪折无人赏,赢得年年自在开”(《花答》);“生来骨相本拳奇,无复腾骧似昔時。太仆怜才如见惜,只教闲放莫教骑”(《题老马图》)。他不再以名利为念,反而庆幸于被统治者疏离的“无用”状态。
为了化解失落感,庄子还将精神境界作为划分个体等级的标准,希望树立个体的精神高地来蔑视、对抗流俗,睥睨众生。《逍遥游》中,庄子根据精神境界的差异划定了人的层次,而只有忘记一己得失、摆脱名利等世俗系累,才能成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至人”、“神人”、“圣人”。这些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达到了“无待而自由”的最高精神境界。如此,精神境界代替名利价值观成为了决定个体高低的标准。对隐士而言,背离世俗也便意味着超越世俗。站在自我的精神高地上俯瞰众生,隐士们会痛感世俗之人的卑微可笑,进而更珍视自己所保有的高贵与高洁。
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其思想、生存模式、诗歌风格不断被后人所学习、效法。众所周知,陶渊明爱松、爱菊。在他笔下,松、菊是他的化身,被赋予了他所崇尚的隐士人格。松、菊也因之成为隐士孤高精神的符号,渗透着遗世独立、高洁不俗的隐士精神。受陶渊明影响,李昌祺同样对松、菊情有独钟。如七绝《秋日对菊》:“席有尘埃径有苔,旧时知己少曾来。多情独爱庭前菊,肯不羞贫岁岁开。”显然在效仿渊明以菊自喻,彰显自己不因贫困羞愧的孤高气节。除松、菊、梅、兰、竹等常见隐喻外,李昌祺还构建了一些新的意象来表彰隐士精神。如夹竹桃,“气味原来自不同,枝柯讵肯轻相倚。翛然凤尾静且幽,下视靡蔓皆庸流。贞姿岂作俗花友,直节终非凡卉俦。”(《题夹竹桃花图》)又如枇杷,“岁晏不改色,傲睨雪与风”(《枇杷晚翠》)。这些意象成功彰显了隐士李昌祺卓然独立、直节不屈、傲视俗生的人格气质。“平生坚白意,未肯涅缁尘”(《寄南昌沈大尹》其三),孤高的隐士精神成为李昌祺十几年隐逸生涯的重要精神支撑。
三
老庄思想不仅帮李昌祺摆脱了名利价值观,而且使他寻觅到了隐居生活的乐趣,解决了死亡这一终极命题。与世俗社会相对,自然是老庄的精神依托之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 章),将一切的本源归于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崇尚“天人合一”思想,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融合为一。庄周化蝶的故事更形象地展现出人与自然的融合状态,提出了“物化”的理念。于是,自然成为个体的关照物,人赋予自然以人格,自然为人提供思想、精神的空间,徜徉于广阔的自然之中,人的思想、精神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舒展、自由。
隐居生活贫困艰苦、枯燥乏味,长久如此,难免有浮躁消沉、身心消磨之感。面对困境,李昌祺效法老庄,通过融入自然扩展精神境界,沉淀、淘洗心灵,使自己忘却现实烦恼,臻于“静”的精神境界。他竭力融入自然、田园的范畴之中,与万物融为一体。少了敬畏、排斥,多了关爱、相亲,自然在他眼中变得温润可喜、生动可人。从满怀激情、充满豪情壮志的庶吉士到安于平淡的隐士,李昌祺对自然的审美观也随之改变,如《题王司直所藏米南宫画》一诗所写,他早年钟爱的是名山大川、高峰激流,中年改志后,青睐平常自然的田园美景:“始知簪绂华,不与漁樵同。兴适随去留,身闲忘达穷。我生本放浪,中年抗尘容”。浮云飞鸟、清风雨露,或灵动悠然、无有羁绊,或浸润万物、冲淡平和,正是李昌祺所向往的精神境界。他尽情感受着自然的博大、宽和,驰骋于闲逸、松弛的自然之境,心境归于平静祥和。“只与漁樵长混迹,自缘轩冕久忘情”(《东溪钓隐》),“饮啄虽云豢养丰,何如自在林间宿”(《题鸂鷘图为陈则裕赋》),沉溺于物欲功名的追求使李昌祺一度淡忘了人间的真情、真趣,回归田园后,他陶醉于平淡自然的美景,浸润着质朴自由的民风,得到了精神的救赎,重拾了人的本真,获得了远胜于官场富贵生活的愉悦和自由。
老庄对自然的崇尚还能解决死亡这一个体的终极归宿问题。针对死亡问题,庄子首先提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现象,与黑夜白昼一样平常,无需惶恐。其次“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生和死没有差别,“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天地》),应该同等对待生死,甚至将死亡视作上天提供的修养机会。最后“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养生主》)如果将人纳入自然的范畴之内,人只是万物循环的一环,自然界生生不息,薪尽火传,个体生命消亡后还将以新的形式延续下去。如此,死亡的意义从根本上得到了消解。庄子的“鼓盆而歌”(《至乐》)正源于这种对死亡的达观态度。
李昌祺晚年对死亡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三首五古说理诗《拟影赠形》、《形答影》、《神释》互为问答,形象化地探讨了人的终极归宿问题:
太极生万彚,繄人最为灵。云胡浪自苦,驰骛迹靡宁。化机有恒运,疾急弗暂停。适见方红颜,髩发忽已星。人身非金石,终当归沉冥。不如学神仙,服食炼尔形。君我两无坏,永共天地龄。愿君取吾语,日进参与苓。(《拟影赠形》)
有形斯有影,物理固其常。我行尔必偕,我息尔乃藏。岂但相依附,实此同存亡。学仙非无术,却老亦有方。古称彭聃辈,其寿邈难量。于今竟安在,孰是长生乡?多君为余劝,兹道终杳茫。参苓且当止,莫若衔杯觞。(《形答影》)
人生斯世间,于物亦岂殊。二仪妙参赞,政由我中居。与子虽三名,其实本一躯。出处既弗异,如何乖所趋。老氏贵不死,长生出贪愚。神仙果何物,天地尚或渝。饮酒固所好,悲愁赖其趋。从古戒沈湎,先王有遗书。学仙非吾事,痛饮岂我图。但当委大运,俟命宁忧虞。既来谅必去,此理端不诬。逍遥以乘化,荷锸徒区区。(《神释》)
第一首是影子对形体的建议。影子认为人年寿有限、红颜易老、青丝易星,出于生计、名利之需,还得终日驰骛奔波,难有喘息之机,最终还难逃一死,不如学习道教的服食求仙之术来获得永生。第二首为形体对影子的回答。形驳斥了服食求仙的可行性,认为此道杳茫难求,不如将视线转入现实人生,通过沉湎酒精忘却现实的烦恼。第三首从精神角度对形、影的观点加以了辩驳。认为求仙不可行,酒只能短暂麻醉自我,问题的症结在于自我思想和精神深处的平和。只有将人纳入自然的范畴,效法老庄的安时俟命、逍遥无为思想,才能化解死亡等一切现实烦恼。
这三首诗是李昌祺晚年对人生苦恼,尤其是死亡问题的集中思考和总结。形、影、神的对话本质上就是作者自我的内心对话和思想对抗。死亡是个体的最终归宿,人到暮年,死亡的恐惧总会伴随年岁的增长愈加强烈。有感于此,李昌祺阐发了三种有关死亡最典型的思考模式和解决之道——道教式的服食求仙、现实的酒精麻醉和最深层次的精神思考,并最终超越了虚幻的仙境和无奈的现实,将答案定格于庄子的安时俟命、逍遥无为思想。这组诗被置于《运甓漫稿》卷首,无疑突显了它们对诗集的统摄作用和作者晚年对死亡问题的重视。
四
大约中年贬谪之际,李昌祺便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如《谪官后崇上人房话禅》一诗所云:“亦欲断缘依法住,经函茗椀了余生”,希望皈依佛门以了此余生。当然,这只是他在人生不顺时的一时决绝之语,不足以构成他是佛教徒的论断。类似的表白在他诗中并不少见,如“安得此身无系累,蒲团共坐阅空诠”(《峡山寺》)、“阎浮俱苦海,何处可安禅”(《郭外野寺》)、“我欲归投选佛场,蒲团贝叶共禅床”(《题意上人卷》)等。
在困境之中,李昌祺经常表达逃离世事、皈依佛门的愿望。晚岁之际,为了去除内心杂念,回归澄澈之境,他对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乃知向上机,无台亦无镜。徒劳费辞说,妙在悟自性。世无毘耶翁,孰拯众生病。愿言投空门,跏趺事禅定。”(《雪中偶至相国僧舍》)这几句诗中包含了不少佛教术语和典故。“机”,任继愈《佛教大辞典》解释为“众生对待佛教的态度、感受佛教的程度和速度等内在根据”。“无台”、“无镜”典出六组慧能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讲的是禅宗的顿悟之道。“既然自性清净,自性本觉,自然也就无须向外苦苦求索,只要反观自心,反求诸己,还得本心,就能够‘即时豁性’,‘顿现真如本性’”。“毘耶翁”是指《毘耶娑问经》中记载的以布施为好的毘耶娑仙。“跏趺”为佛教徒的一种坐法,又称“金刚坐”,是佛教徒修行的常用坐姿。“禅定”则是一种不为外界所动、专注忘我的境界。此诗明显有宣扬佛教教义的意味,着重表达了对禅宗的向慕,希望通过佛教修习来消解内心烦恼,获得心境的安宁。此外如“润师戒行如秋霜,蒲团趺坐十笏房。根尘识想已云泯,色香声味都宜忘。兹图谩尔时时对,外物岂能为已累。毕竟阎浮世界空,直须悟逗真三昧。寒灰心地槁木形,妄缘幻质难缠萦。无兰无石亦无画,此是菩提最上乘。”(《题雪窓兰为济润上人》)同样将佛教的清净无为视作极高的精神追求。禅宗与老庄原本就有很深的渊源,在李昌祺眼中,佛教的清净之境与老庄的自然一样,都是与世俗社会相对存在的,对老庄、佛教的崇尚均源于化解现实烦恼的需求。
在老庄、佛教的感化之下,李昌祺晚年终于从名利、贫病、荣辱等人世牵绊之中彻底解脱出来,达到了淡定从容、澄澈纯净的精神境界。七十岁生日时,他创作了《丙寅初度作》一诗,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转变过程:
余生如稚松,由寸望百尺。既承雨露滋,亦受霜雪积。蹉跎逾七十,勤苦曾备历。误蒙明圣知,谬忝中外职。顾已惭菲薄,于時乏禆益。处盈亏必随,履泰否斯即。至理谅在兹,昧者固弗识。叩阍乞残骸,休退恩旨锡。遂令犬马躯,获返田野迹。長揖画省僚,重负从此释。今辰届初度,厨传仍岑寂。傍人竞嗤笑,穷约犹曩昔。妻孥颇愧赧,而我固悦怿。平生守儒素,晚节敢变易。回思永乐初,岁月类梭掷。同年四百余,多已在鬼域。存者才十辈,犹被利名役。迂疏独何幸,林下得偃息。遗荣遂安闲,养静忘跛躄。游鳞泳清波,羁鸟殓倦翼。贫非吾所忧,病岂吾所戚。宠辱与升沉,宁复置胸臆。忘机侣鸥鹭,植杖随沮溺。浩然天壤间,俯仰惟意适。长歌自为寿,坐对远山碧。
回想官宦生涯,有荣耀,也有压抑,有追求,也有勤苦,但一切不过是场谬误。经历了人生的波澜起伏,洞悉了盈亏有定、丕泰相倾之理,他明晰到只有远离官场、回归田园才能实现自我的保全、畅达。所以隐居生活虽然贫苦寂寥,惹得旁人耻笑、妻儿不解,但他仍安之若素、怡然自得。进士同年们多已离世,在世的仍为官场名利所缚,反观自己,身居田园、自由洒脱,又不由感到庆幸。徜徉于自然田园的美景之中,不因贫穷疾病而忧戚,不以升沉荣辱为念,将物外之事一律置之度外,他明确了心之所安,实现了真正的自由、畅快。
回归田园、皈依佛老虽使李昌祺坚定背弃了世俗的名利价值观,但他仍十分在意儒家的家庭伦理,平淡幸福的家庭生活也给他的晚年增添了许多乐趣。“萧条掩关卧,蝶梦方悠扬。老妻唤我起,盘饤劝我尝。小孙颇慧黠,学语声琅琅。举目见之喜,欣然挥一觞。”(《丙寅端阳述怀》)虽家境贫寒、乡景萧条,但妻贤孙慧、和乐美满,温馨、畅达之感油然而生。
总之,李昌祺晚年兼取儒道释三家,思想较为驳杂。老庄的精神自由、死亡观,禅宗的心性修为,儒家的家庭伦理都帮助他化解了现实生活的苦恼,回归心境的平和,寻求到田园生活的乐趣和美感。
五
伴随思想变化,李昌祺晚年的诗风也发生了较大转变。他晚年对陶渊明极为推崇,试图追寻陶诗“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的风格,但刻意的模仿致使部分诗歌在意象选择、立意主旨、风格意境上都缺乏新意。如前所述,意象虽有独创之处,但大多沿用陶诗中习见的松、菊、浮云、飞鸟、老农、渔樵等,内容均为隐居之乐,思想亦是高洁之志、人生思考种种。不少诗歌明显可见陶诗痕迹,《渊明酌酒图》《渊明图》等诗更直接想象、摹写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场景。当然,长期的隐居生涯也使李昌祺能够真正体察、认同陶渊明的思想、生活状态,其诗歌尚能真实而不造作。《容膝轩》《松石间意轩》《题晩香堂二首》等佳作也能有几分陶诗的古朴纯净、平淡自然之妙。
十余载的乡居生活也使李昌祺有意向民歌、散曲学习、取法。《题喜鹊图二首》《村舍燕》《洧川田翁》等诗颇具民歌风味。如“少小为农今老大,不曾骑马只骑牛”(《洧川田翁》)之句,几乎纯以口语出之,很有乡民质朴的感觉和民间生活的真趣。《杨柳枝》四首等更纯然是民歌风味,如其一:“春來婀娜袅烟青,花落春江化作萍。随水东流漂泊去,比郎踪迹更无凭。”
同时,由于喜欢在诗中渗入沉痛的身世之感与人生体悟,他的诗歌也逐渐突破了陶诗的窠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如《湖山佳趣歌》:
半生甘作隐者流,两屐不到侯门游。老去高情付林壑,闲来乐事只渔舟。春水泛花漾孤屿,杜衡蘼芜满修渚。晴树远连江上村,晚云忽作溪南雨。自怜身世两悠悠,濯缨濯足忘吾忧。万钟悬爵本非志,一竿在手何所求。门前学种五株柳,逸兴雅怀到处有。对客石床抚古琴,留客山瓢斟浊酒。年年岁岁适闲情,皞皞熙熙度此生。已无天上鹓鸾梦,且结湖边鸥鹭盟。
此诗自陈身世之感和隐居之乐,情感真朴,语言明快,虽然也征引了不少典故,但已较好地避免了文人化过浓、语言陈旧的弊病。
韵律上,这类诗歌也不太遵循文体限制,时常突破诗、词、曲的用韵限制,有自由散漫、不拘一格的特点。如《咏小室前孤树》:“高枝已出墙,新叶方舒翠。赖尔豁忧怀,朝朝坐相对。”“墙”为“阳”韵,“翠”是“置”韵,“对”则是“对”韵,全诗通篇不押韵。由此可见李昌祺晚年对诗韵的随意态度。对诗韵限制的突破既是李昌祺长期接触下层百姓,熟悉民歌、散曲的结果,又是他在放达心境下对传统的一种革新和挑战。
可以说,李昌祺晚年无论在思想还是诗风上,都完成了从依附、遵循主流到违背、背离主流的蜕变。思想上兼容儒释道三家,而以道为宗;诗歌既崇尚陶渊明,又向民间文学取法,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显然与统治阶层、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审美倾向格格不入。在一些人眼中,李昌祺近乎时代的另类。明人郑瑗曾论道:“李布政昌祺人多称其刚毅不挠,尝观其《运甓漫稿》浮艳太逞,不类庄人雅士所为。”可见,由于渗入了较多俗文学元素,李昌祺的诗歌在当时引起了一些非议。然而,从诗歌史的角度说,与传统审美、创作观的背离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代表着一种对传统的突破与革新。两百年后的清人朱彛尊便与郑瑗的评价大相径庭:“李祯(昌祺)诗务谢朝华,力启夕秀,取材结体颇与段柯古(成式)相似。盖由其一变绮靡纤巧之习而以流逸出之,故别饶鲜润,迥异庸芜。”由此足以证明,李昌祺晚年流逸鲜润的诗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主流诗风的束缚,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甚至昭示了诗歌的一种时代转向。
〔注释〕
①本文所引李昌祺《运甓漫稿》原文均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出版社1986 年版,不再逐条出注。
②两次罚役:永乐十年(1412)董役长干寺、永乐十七年(1419)谪役房山。两度外任:永乐十五年(1417)至十七年(1419)任广西左布政使;洪熙元年(1425)至正统四年(1439)任河南左布政使。
〔1〕乔光辉.李昌祺年谱〔J〕.东南大学学报,2002(6).
〔2〕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钱习礼.河南布政李公祯墓碑〔A〕.焦竑.国朝献征录〔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
〔4〕明太祖实录(卷38“永乐三年春正月壬子”条)〔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5〕李昌祺.剪灯余话(序)〔M〕.台北: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
〔6〕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
〔8〕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郭绍虞.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0〕任继愈.佛教大辞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1〕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12〕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3〕郑瑗.井观琐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