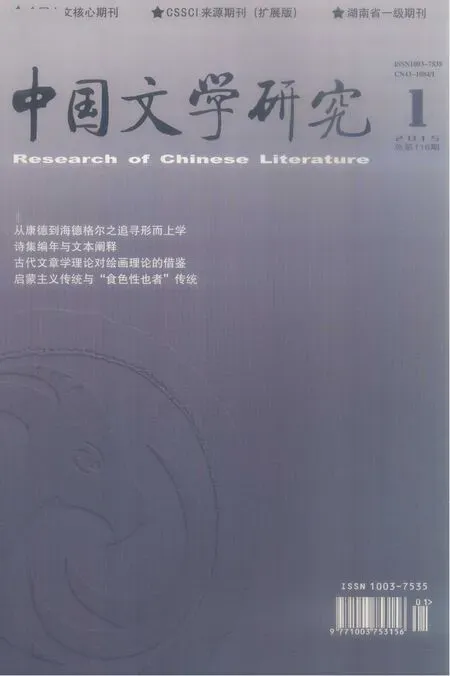克兰情节理论的比较研究
闫莹冬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在源远流长的文学理论发展史中,情节既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又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文学范畴。它是叙事类作品的构成要素,也是文艺理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概念,它的内涵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意义也随之不断变化更新。关于情节这一范畴的内涵所指,文学理论学家自古到今从未停止对它的争论,或者说,情节的涵义及其构成要素始终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中。特别是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几近于崩溃之边缘,在此覆巢之下,情节范畴也随之几经变化而终未有定论。那么,在此文学语境之下,小说研究或者说情节范畴研究又将走向何方,又如何在新的话语系统中取得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以上问题,我们或许能够从克兰的情节理论中找出答案。
一、情节研究的整体性原则:与俄国形式主义的比较
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情节就不再被认为是叙事作品内容的一部分,而被视为作品形式的组成部分,即对素材的艺术处理或形式上的加工,尤指在时间上对故事事件的重新安排。俄国形式主义强调对作品叙述方式的研究,即作家怎样运用情节材料构成艺术作品的问题。从情节故事内容的研究到情节形式的研究,俄国形式主义以文本的构成与结构的内在规律为研究的方向,从而拓展了情节研究的范围。但是,什克洛夫斯基等学者把情节归入到形式的部分,这就将情节与内容的建构彻底分离开来,即将情节限定在话语层面上并把它与故事对立起来,因此,这种简单的对等设置很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或者说,造成对二者情节观差异的忽视。
从以上文学理念中,我们不难发现俄国形式主义将叙事作品分裂为“故事”和“话语”两部分,“故事”是作品的内容,“话语”是表达方式或叙述内容的手法,因此,情节被归入“话语”层次。很明显,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虽然对叙事话语模式的归纳与总结可以突显出文本深层结构的叙事方式,但是,此种研究方法必然会破坏文本的有机整体性,即搁置文本自身的特殊性与个体性特征。正如休斯所言:
普洛普显然意识到了在美学上所应该考虑的东西(色彩、魅力、美),但却不真正关注它们。假如一个故事的结构本身有什么美学特点的话,那么他满足于对之视而不见,尽管他似乎显然会将美学效果归于一个故事在其实现过程中所具有的某个特点而不会将它归于这个故事结构。
与俄国形式主义不同,克兰从情节中提取的是情节建构的要素而不是情节的行动功能。克兰认为小说情节主要有三种元素:一、行动要素;二、人物要素;三、思想要素。在克兰看来,在情节建构时,情节因素表现为一种时间上的综合(temporal synthesis),且此种综合方式会受到作者的创作目的的影响。换言之,作者的创作目的是对行动、人物和思想进行组合,如果不对这三个元素与情节形式组合原则进行探讨,就不可能说明情节究竟是什么。
在此,就该词(情节)的更为广泛的意义而言,它不仅是人物、思想以及行动的特定材料的特殊综合,而是一种必要的综合,因为它以词语模仿了人类一系列活动,并形成一种力量,以特定方式影响我们的态度、观点以及情感。当我们读或者听,我们必定会生成种种期待,期待某种将来,并或多或少感受与我们的期待相应的、注定的欲念。
从文本分析论的角度来看,克兰把诗性作品(poetic product)看作是形式与材料的组合,即作品的成分存在于形式和材料的联系之中,或者说,存在于目的和方法的因果联系中,因此,克兰认为,情节形式建构的整体性原则才是小说结构的存在方式,而不是俄国形式主义提炼的叙事功能。也就是说,单纯的叙事功能没有表现出情节对文本内容的组织与建构作用,而只是对情节形式建构功能的总结,例如,在对《汤姆·琼斯》的评论分析中,克兰发现:
在对《汤姆·琼斯》的研究中,许多对于情节的评论和分析其实只是处在对普通的审美愉悦感知的层面上,有时仅仅是一些对小说判断的评述,很少与小说情节的发展相联系。按照此种研究模式,情节的产生只会与有趣的故事相关联的,因为它的作用只是创造一种愉悦的感受。
因此,克兰认为情节形式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情节是一种组织和联合的原则,只有借助这种原则,小说的材料才能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二,鉴于小说的阅读与体验是一种时间过程,因此,小说的情节的发展肯定会存在顺时性的特征,所以,研究的关键问题就是情节在时间上的组合是如何完成的。
克兰认为,决定事物成为一个整体的内在力量取决于该事物的形式,因为形式赋予了质料内在的统一性。换言之,只有获得了统一性之后,质料才能成为有机的整体。“我们要把形式作为一个为艺术整体来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论出形式潜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按照此种艺术观念,如果想获得对形式的正确认识,就必需首先分析出结构变化的各种可能性,即如果理解和认识是建立在已经完成的形式之上的,那么,作为关键性的文本形式因素,情节的影响效应以作者将行动、人物和思想组合成一个完整有序的整体为前提条件。按此推论,如果作品中的人物与思想以其行动要素为载体并随之变化,那么,这种故事结构只是情节的材料和内容而不是它的形式。以悲剧为例,如果悲剧的形式只是一系列组合行动的顺序和通过同情和恐惧等心理作用创造“净化”效应的能力,那么,这种类型的情节形式就不可能按照它的行动和事件的数量,或者它所产生的心理延迟和惊奇程度来判断自身的艺术水准。或者说,就艺术本体而言,情节形式的建构方式与作品的品质密切相关。因此,克兰认为,情节的形式不是要素的运作方式与影响效应而是将材料转变成具体的艺术作品的方法。也就是说,情节不是简单的语言框架系统或者写作技巧而是形式的情节,它与作为整体的作品相联系,因此,作品中所有的成分必需共同服务于作品的最终目标:修辞性交流的目标。
克兰对情节建构的整体性原则的设置将对情节范畴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不仅回答了情节的形式功能作用而且还带入了形式对文本内容的建构作用,从而反驳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情节所做的行为功能命题。因为情节不是一个单一性的概念,它存在于话语和故事两个层面上。如果纯粹的功能指向能够囊括所有的情节功能,那么,情节的艺术感染力或者说情节的艺术表现力也必定是相同的,这就与艺术的个体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相悖,即忽视了作家的结构技巧层面。可以说,克兰的理论从形式主义研究层面转向叙事伦理层面,从而打开了情节研究的新视域。
二、情节的艺术审美表现:与法国结构主义的比较
在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中,情节转化为一个叙事结构中的范畴,因此,情节的构成要素问题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结构主义理论家关注的中心问题。虽然结构主义采用的语言学的分析阐释模式能够有效地揭示出叙事作品的深层结构层次及其各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然而,其情节的研究仍然处在故事的层面上,且过分注重对情节形式方面的研究,这也就暴露了其研究视域的封闭性与狭隘性。虽然说对于小说结构的探讨离不开文本,但是,究竟是叙事结构创造了作品的形式审美特征,还是作品的整体形式产生了艺术审美的特质,或者说,叙事结构创造的形式审美特征是否等同于作品的艺术审美的特质,这是克兰与结构主义小说研究的分歧所在。如戴维·洛奇所说:相互关联的整个一组故事的意义要大大超过它的组成部分的总和。
对于克兰而言,作为一门阅读的艺术,虽然小说的目的是叙事,但是,故事本身不等于文学文本,或者说,故事素材只有在情节的组织变化中才显示出来,只有上升到情节的层面才能成为艺术阅读的对象,因此,情节在功能和目标两个层面都会产生对读者的影响作用。换言之,在小说艺术审美的过程中,艺术的魅力在于阅读主体所产生的情感共鸣。由此可以看出,克兰区分故事与情节的标准是:故事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叙述,而情节是艺术结构对艺术素材结构组织关系。所以说,小说目的的实现离不开情节的设计,或者说,小说修辞的中心在于找出合适的说服方式,使读者对小说的虚构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产生兴趣,继而从精神的层面对读者产生影响。可以说,克兰以“情节”研究为中心的小说研究超越了语言学研究的层面,上升到修辞艺术研究的角度,即关注作者是如何运用艺术技巧(情节小说建构的技巧)来调整和限定他与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如布斯所言:
我们对隐含作者的感觉,不仅还包括所有人物的每一点行动和受难中可以推断出的意义,而且还包括它们的道德和情感内容。简言之,它包括对一部完成的艺术整体的直觉理解;这个隐含作者信奉的主要价值,不论他的创造者在真实生活中属于何种党派,都是由全部形式表达的一切。
可以说,克兰超越了单纯的语言范畴内的研究,转向文本的艺术修辞性研究,即作者是如何运用艺术技巧建构文本,进而创造艺术的审美特质的。
依笔者之见,克兰理论与法国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别(或者说超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如果说结构主义力图建立一种凌驾于叙事之上的框架系统,并在这个系统内给予文本组织方式中呈现出的意义以合理的解释,从而探索支配各种小说叙事的内在组织特征,那么,这种凌驾于叙事之上的框架系统不能对作品的艺术审美效应给予合理的解释。克兰理论的超越之处在于,虽然其采用的也是语义分析的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将文本看作是孤立静止的物体,而是将文本研究与文本接受研究并置在相同的位置,从而将作品研究带入艺术审美的层次。
其次,虽然叙事之上的框架系统能够对作为文本形式的建构过程给予详尽的说明,但是,其不能对形式是如何具有艺术审美特质的这一问题给予解释,也就是说,创作主体的创作目的、结构技巧与语言表现力等主体性因素不仅对文本结构的形成而且与文本个体所具有的审美影响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即结构主义关注的不是情节本体的问题而是语言的结构组织问题。对于克兰而言,情节是“用语言模仿了一系列的人类活动,所以,情节自然地拥有影响我们的意见与情感的力量”,受这种情感力的影响作用的驱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形成对情节的发展产生相应的期待,或者说,出色的小说情节依托的是人物、事件、措辞和思想等因素组合而成的独特的艺术整体,这才是情节的感染力和愉悦感的本源。因此,克兰认为,无论是讨论情节的建构还是作品形式的组织原则都应对作品的审美情感效用产生的原因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也就是说,克兰的文本研究是建立在结构共性与作品个性相统一的基础上的,而结构主义只看到了前者。
三、情节的本质与修辞效果论:与英美小说理论的比较
在英美小说理论发展史上,自卢伯克的《小说技巧》开始,形式成为小说研究的正宗。布鲁克斯在小说批评上取得的成就并不逊于其在诗歌批评上取得的荣誉,他与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合编的《理解小说》可以说是英美形式主义小说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虽然克兰的理论也属于英美小说理论的一脉,但是其理论的中心与价值取向与前两者截然不同,将这两者的理论与克兰的理论进行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形式主义小说理论与叙事伦理理论的重大区别与分歧及其叙事理论的伦理学转向问题。
在《小说技巧》一书的第一、第二章中,卢伯克就小说模仿论展开批评,他认为,通过模仿小说能够创造一种现实的逼真感,从而迷惑读者的认知力,或者说读者会忘记作品的形式,将其当成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更加乐于尽量忘记作品是艺术的对象,而把它当作我们周围生活的一个片断;我们从作品中恰好最强烈地打动我们的那些部分形成自己的印象,使之具体化,如一个动人的场景,或一个出色的人物之类。这些东西在读者心中成形。
就以上卢伯克的论述而言,如果不破除小说情节创造的虚幻的情景,那么,小说的形式就无法变成艺术批判的对象。卢伯克认为,一旦小说的形式与现实生存分裂开来,那么,形式所关涉的所有问题都将是创造性的问题而不再是读小说,记住人物故事的问题,或者说与记忆力相关的问题。换言之,卢伯克认为,小说批评需要的是批评能力,因为它可以拆散崇高之物体、断开无限延展之想象网络,将结构分解为个体元素,从而可以考察文本的内部的机理,即需舍弃“实用目的”,读者才能被“美学目的”牵引,将兴趣集中与艺术形式本身。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批评力才能完成对于小说形式的分析。由此,卢伯克否定了情节建构与现实、读者的互动性,将小说情节研究带入纯文本研究的视域。
比较而言,虽然克兰也重视对情节形式结构的研究分析,但是,与卢伯克的观念相反,他并没有否定情节研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尤其是与读者的反应关系。克兰认为,情节研究的首要问题是情节的本质的问题,或者说,是情节评论的充分性问题。按照克兰的观念,情节是一个由行动、人物和思想组合而成的整体性范畴(synthesis),即在作者的创作目的的作用下,行动、人物和思想在时间上的结合。例如,许多文学史家把《汤姆·琼斯》与《俄狄浦斯王》和《炼丹术者》并列,认为它是结构最完美的世界三大名著之一。然而,在克兰看来,大多数的文学理论家只是把情节看作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所以,即使《汤姆·琼斯》的情节被认为是文学史上最完美的情节,也很少有人关注情节建构的本质取向问题。很明显,克兰的情节范畴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观点中衍变而来的。在亚氏的文学理念中,情节具有一种重要的性质—模仿,即“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所以,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为了行动才需要性格的配合。”克兰眼中的文学作品不是纯粹的自然之物,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具有一种本质特征,即模仿的结构,这是因为语言模仿的可能性能够创造模仿的结构,因此,文学作品能够通过展现人物行动背后的原因来达到它的影响力。
模仿的对象是内在的,因此,严格意义上的“诗性”,只存在于偶然事件可理解的、动态的运行模式,心境,以及意象之中,是诗人用他的语言序列通过类比人类某些经验模式所建构的。
也就是说,既然模仿的对象是人的经历体验,那么观众就能够被作品中与现实生活相似的经历或体验所打动并产生共鸣,因此,通过发现和分析行动、人物和思想的构成元素就能够对情节的建构进行具体说明。因此,对于模仿对象的评论标准不是建立在模仿的逼真性或者材料组合的逻辑上的,而是要看具体的情节形式是否被作品中的行动、人物和思想很好地实现了。在克兰的理论体系中,文本是一个存在的整体(synola),而建构此整体的是艺术的模仿(mimesis),因此,对于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放在有机的结构体系中考虑。也就是说,情节是以整体性的结构形式模仿人的存在体验,读者的在场或者说存在会对情节的设置产生影响,或者说情节设置的目的是引发作者想要的阅读体验。
在克兰看来,情节的设置与读者反应心理层面之所以密切相关,是因为以模仿的形式上演一些行动比通过语言陈述一些内容更容易触动读者内心的情感,或者说行动的情节会于无形中产生强大的说服力。既然情节形式对读者的影响效应是读者与人物复杂的相互反映和判断的结果,因此,只有对读者的愿望和期待进行艺术分析或者与期待相联系的事件一起进行分析,才是在艺术意义上理解了情节。这就如韦恩·布斯所说:“一个合理的判断取决于作品的伦理质量和听者的伦理力量以及注意力之间的交易。”
只要将卢伯克与克兰的理论比较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卢伯克的理论取消了情节研究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意义,因为他明白创作主体视角与生存经验会将小说的内容圈定具体性范畴之内,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模仿论基础上的,因此,在模仿论基础上提出的形式理论不可能使形式成为研究的目的。与之相反,克兰认为,从形式研究能够探寻出情节模仿的本质,所以,形式研究与模仿论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换言之,如果形式之外无它物,那么,情节的“净化”效应从何而来?就克兰而言,如果小说研究取消了作者的道德取向,那么,作品的审美的所指就会由于作者过分放任而被误读,从而失去作品存在的社会意义。如布斯所评,《小说技巧》是一本贡献了一套分析模式的著作,也就是说,这部作品的两套内在的话语结构:作为知识范式意义上的形式论和作为信仰体系的形式论没有得到有效的撇清,于是,卢伯克的“形式”似乎就被缩减为技巧中心主义。
站在文本结构的角度,卢伯克认为,文本是形式技巧与故事内容有机结合的中心,但是,这个中心并不在于故事世界的存在,因为事实本身并没有多大价值。也就是说,批评的视点是文本的形式,正是形式使得外部世界与读者的反应有了接触的平台,因此,这个视点不在文本外部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漠不关心上。站在文学终极价值目的的角度,克兰认为,如果抛弃了小说情节的模仿本质,就会将文学研究带入纯粹的形式研究的极端,从而割裂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从而消弱文学对社会发展人类道德完善的积极作用。总之,卢伯克与克兰都意识到了文学的模仿倾向,前者为了建构小说形式研究的目的而舍弃了模仿论的存在价值,后者出于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赋予了模仿论本质性的地位。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克兰对情定义更符合其情节存在的真实状况,或者说,卢伯克有意识的否定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克兰对情节范畴定义的合理性。
布鲁克斯反对情节至上论,认为小说应该重视技巧,因此,布鲁克斯认为:所谓的情节至上,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用文字来表达。因为一篇文学作品如果真的是有机的,那么它的结构的每一分子都应该是全篇作品大原则的必然或可然的后果。从文字到说出某些话语的人物,从人物到情节布局,都表明,“探索‘行动’为何的唯一路线,即是‘行动’的‘实现’,即是剧本的文字”。总之,布鲁克斯怀疑,在未见诸文字表达前如何能判断故事情节的适宜与否。
与布鲁克斯的观念相反,克兰认为,既不是语言创造了文本的特征,也不是修辞技巧创造了作品的说服力或者说影响力,因为作品的语言没有好坏之分而是与情节形式的要求有关。也就是说,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效力不是纯粹的语言修辞的结果而是作品的整个形式的作用,即不是语言而是形式对读者的情感思想产生影响效应。按照克兰的观点,小说研究应以对情节结构技巧的分析为中心,因为正是这些技巧能够让读者产生某种特定的情感反应,或者说,小说之所以与诗歌或散文不同是因为它独特的文本建构方式,因此,读者对小说这一文本体裁的审美阅读体验与期待区别于诗歌与散文。换言之,不同的文体有着不同的情节模式,而且这种由作品形式引发的情感反应不会随着作品个体性差异而变化,因为它具有固定不变与可重复性的特质。克兰认为,无论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怎样变化,它的基本组成元素都是相同的,即模仿的对象,语言媒介和模仿的技巧。可以说,这三者是作品质量和影响力的决定因素,那么,这三种要素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克兰提出,艺术结构(artistic construction)是小说研究的第一原则,同时,也不能忽视作品的构成要素对读者情感心理的影响作用。“艺术作品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dynastic whole),通过其中各种成分的共同运作,会对读者的心理情感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情节研究应当围绕着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作用和读者对情节的情感心理反应而展开评论,并以作品对读者的道德伦理影响作为终极目的。那么,由此又牵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即为什么情节形式能够对读者产生影响作用呢?
在小说研究中,布鲁克斯也认为情节分析是联系作者、作品与读者的重要纽带,因此,在分析情节中要注意作品、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联,即“在分析情节时,要注重作品故事内容的逻辑性和内在动机;注重情节带给读者的影响和启发;注重作家安排情节的方法和用意。”可以说,布鲁克斯的小说研究不再拘于语义分析立场,而是将文本研究与读者的反应关系纳入其中,以期获得对情节修辞效果的真实认知。然而,布鲁克斯并没有完全放弃新批评理论地位语义学立场,因此,他又提出情节是动作的结构、行动中的人物与主题的显现,所以,小说研究的是主题、人物、情节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样,克兰也将情节划分为人物,行动与思想三种要素,但是,克兰划分出的三个要素与布鲁克斯的三个要素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即前者建立在情节对话性的立场上,或者说,情节与读者的修辞效果关系的层面,而后者是建立在文本结构层面上的划分。
关于情节与读者的关系,克兰认为:“(归于此类的任何情节),当它展开时,它的特殊力量都是我们的知识状态与我们渴望人物成为道德分化的个体之欲求间复杂关联的结果;只有当我们研究了欲望以及与产生它的偶然性相关的可能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才会被认为是以完全的艺术感知理解了情节。”从这个方面来看,克兰把读者对人物的结局,或者说读者对人物的成功或失败的情感判断,作为阅读的终点。也就是说,当读者的价值判断进入最终判断时,他会对人物的类型和作品的艺术水平有一个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读者会不断地加深对作品形式的认识,同时,也会加深对作品思想主旨的理解。显然,克兰情节范畴研究的目的指向与布鲁克斯的不同,他试图将传统的模仿说、情感说、修辞伦理学与现代文本批评融为一体,以突显文本修辞的道德取向目的与对读者的影响作用,而布鲁克斯研究的目的是从语言结构中找出情节能够产生修辞效果的原因,即其所说的:“逻辑,其中包括动机形成的逻辑在内,把一个情节中的许多事件联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布鲁克斯的研究仍然处在传统的故事情节范畴内,虽然他注意到情节与读者的阅读愉悦感有关联相关,但是,情节只被看作是一种故事的连续性,而未能找出情节修辞效果产生的真正原因。所以,我们可以说,克兰的研究不仅将作者的创作意图纳入情节研究的视域,而且还从读者反应的角度分析了情节的修辞效果产生的原因,从而摆脱了传统情节研究的故事中心论的模式。因此,克兰不仅将情节研究带入形式整体论的高度,而且将叙事伦理性研究带入小说研究中,从而将小说研究带入叙事研究的新领域。
结 语
克兰的文学理论吸纳了文本批评方法的客观性、社会学批评的伦理性倾向,并将读者反应纳入研究之中,从而避免了一元论批评的片面性。同时,克兰的情节理论将接受美学和社会学批评统一在形式批评的模式之中,其既继承与坚守了经典叙事学文本分析的伦理学目的,同时又吸收和借鉴了文本分析方法的科学性,从而将多种批评模式的优势收纳在自己的批评模式之中,建立了以读者为本位、以修辞的伦理性目标为目的的文学批评模式。可以说,克兰理论的出现标志着形式批评的自我更新,即叙事伦理批评转向。
〔1〕(美)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Crane,R. S. The Concept of Plot and the Plot of Tom Jones:Critics and Critic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3〕(英)戴维·洛奇著,王峻岩等译.小说的艺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修辞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1.
〔5〕蒋晖.卢伯克的“形式思想”:重读《小说技巧》之前四章〔J〕.文艺理论研究,2011(4).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美)韦恩·布斯著,穆雷等译.修辞的复兴〔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8〕付飞亮,曹顺庆.克林思·布鲁克斯的小说理论与批评实践〔J〕.文艺理论研究,2013(5).
〔9〕Cleanth Brooks & Robert Penn Warren,Understanding Fiction(The third edition),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0〕(美)克林斯·布鲁克斯(C.Brooks)、罗伯特·潘·沃伦(R.P.Warren)著,主万等译.小说鉴赏〔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